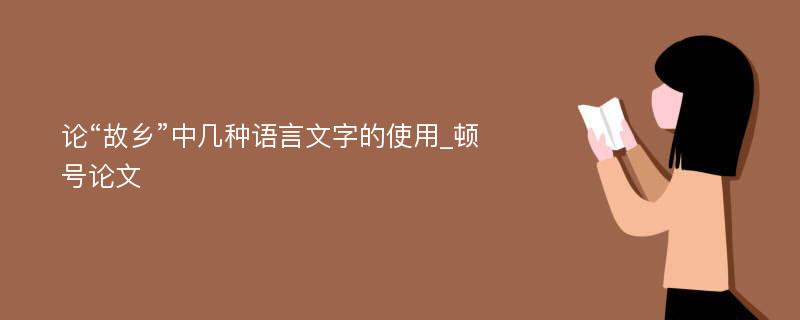
也说《故乡》中几处语言文字的使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文字论文,也说论文,几处论文,故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出现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教材中。而从其节选的《少年闰土》,则为多个版本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这篇小说创作的时间离现在很久了,因此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既有当时的特色,同时也体现了鲁迅个人的风格。老师在教学这篇课文时,对其中某些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也就难免产生疑惑。张镇权老师关注到了这一点,他所写的《(少年闰土)解疑》(《小学语文》2010年第11期51~52页)一文,结合方言、语法、文字、标点等专业的语言文字学知识,对几个有关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使人颇受启发。从语言文字问题的处理方法上来看,是非常可取的。不过对于其中的个别论述,笔者有些不同的意见,现提出来供大家参考,期望能对张老师的文章有所补益,并进一步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一、关于“月亮地下”
《故乡》中有这样一句话:“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
张老师认为,这句话中的“地下”,“下”读轻声,“月亮地下”的确切的解释应该是“有月亮照耀的(西瓜)地里”或“有月光的地面上”。他引用了明清小说“地下”的用例,来说明“地下”有“地面上”的意思。一个例子取自《儿女英雄传》十四回“自己便踱出店外,看那些车夫吃饭。见他们一个个蹲在地下,吃了个狼吞虎咽,沟满壕平”,一个例子取自《水浒传》四十一回“宋江听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此外,张老师还指出,在浙江和江苏的吴方言区,“地下”之“下”读轻声,可指“地面上”或“地里”“田里”。张老师所引明清用例,无疑是正确的。他所说的吴方言中“地下”的使用情况,没有查证,不作评论。
我们的问题是:第一,按照张老师的分析,“地下”应为一个词,那么“月亮”这个词和“地下”应该怎样组合呢?这个词组该如何分析呢?除了这个例子,我们还能找到“月亮”的类似组合吗?譬如,我们能说“月亮路上”吗?第二,从上下文(特别是开头的那一段)来看,读者已经能够知道这事件的背景就是在瓜地里了,作者不必在此着重强调“田里”了。
察看一下语言史资料可以知道,“月亮地下”可以有别样的理解。“月亮地”其实是一个词,它不仅在上个世纪50年代前广泛使用,即使是在今天,在山东、河北、天津一带的方言中,仍然存在,譬如冯德英《迎春花》“虽然在月亮地,可是人站在树身的阴影里,上水山家的人从树边经过,也不会看到”。初版于1937年的《国语辞典》(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收录了这个词,“【月亮地儿】犹言月下,谓在晴夜有月色之地面上”。明清时代的小说中,“月亮地里”有用例,譬如《金瓶梅词话》影印本五十回六页下第三行,“两个月亮地里,走到小巷内”。
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知道,“地”与“月亮”先组合在一起,然后再与“下”或“里”合在一处,“地”不能与“下”先组合在一起。“月亮地”是什么意思呢?这要从这个词的来源看。“月亮地”在更早的文献中,说成“月底”,譬如宋晏几道《六么令》词“遥想疏梅此际,月底香英白”、元刘因《玉簪》诗“花中冰雪避秋阳,月底阴阴锁暗香”,“月底”是“月下”“月光之下”的意思,“月光之下”的当然之物是“大地”,这是与“月亮”所“悬挂”的“天”相对的,所以“月底”在后来也说成“月亮地”,于是就如《国语辞典》一部分释义所说“清朗的夜晚、月光照射着大地”。“月亮地”的“地”是“大地”的意思,可不是专指“农田”的“地里”“田里”,比如汪曾祺《羊舍一夕》“别人都已经走净了,他一个人在月亮地里还绷楞绷楞地投篮”,这里的“月亮地”指“月光沐浴下的球场”,跟“地里、田里”可没关系,所以《国语辞典》又说“犹言月下”。此外,与“月亮地”组合的“下”“里”,都不是实指,它们用在名词后,表示一定的处所、范围、时间等,这在更早的古代文献中就有用例了,如《史记·乐毅列传》“齐田单后与骑劫战,果设诈诳燕军,遂破骑劫于即墨下”。
这样看来,老师将“月亮地下”理解为“月亮底下”虽然不很准确,但亦不可讲为“有月亮照射的(西瓜)地里”,可理解为“月光之下”或“明亮的月光照射着大地”,它描述的其实是一种情境。
二、关于顿号
《故乡》中有这样一句话:“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
张老师认为这句话中的逗号,本该用上顿号,但是鲁迅写作的年代尚未使用顿号,顿号功能是由逗号兼承的。顿号是新中国成立后才使用的,所以鲁迅作品(包括解放以前别人的作品)中当然就不可能出现顿号。为了支持这种看法,张老师引用了民国期间的官方文件。
仔细了解张老师的描述,我们有以下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张老师认为,“顿号既然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使用的,鲁迅作品(包括解放以前别人的作品)中当然就不可能出现顿号”。解放前,真的就没有顿号的使用吗?
查看解放前的书刊报资料,可以知道,《新青年》杂志从1919年第1号始就已经使用了顿号,该杂志公布的《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顿号用以标示形容词间和名词间的间隔。再如《东方杂志》1911年第4号第4页《论中国外债及财政之前途》,有使用顿号的句子,“已满期债票及息单。在邮传部管理之交通银行、官办各铁路、及电报局等。可与现钱一律通用”。而在1920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行《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之后,很多书刊报资料都显示了顿号的使用。譬如,陶希圣《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第446~449页)“在秦以前经过孔子整理的《诗》、《书》、《易》、《礼》、以及孔子自己所作的《春秋》,到了汉代,都是古典了”。
《故乡》发表在1921年5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上。而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知道,此时的顿号已经开始使用了。因此,张老师认为“鲁迅作品中找不到顿号的原因,是鲁迅写作年代尚未使用顿号”是不准确的。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了《教育部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法》,其中公文句读将点号分为逗号、顿号,该方案的颁行,以国家行政法规的形式确定了全国通行的正式标点符号。尽管标点符号的具体使用还不尽如人意,但若说顿号“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使用的”,则不免失之偏颇。
1919年11月,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该议案提到了点号,以“,”或“、”表示,但未对逗号、顿号作严格意义上的区分。不作严格意义的区分,指点号包含逗号、顿号两种功能。这与“兼承”这一概念所指不同,“顿号功能是由逗号兼承的”,指只有逗号一种标点,它可用在应使用逗号和顿号的地方。实际情况是,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的议案中,只提点号、不提逗号,因此也就没有所谓的“兼承”问题了。
第二,关于“鲁迅先生是我国积极提倡并带头使用新式标点的第一人,他对新式标点的普及及用法的日趋完善,起了重大作用”。
上世纪初,鲁迅确实结合自己的阅读、写作经验,指出“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讲国学,也仍然须嵌外国字,须用新式的标点的”。(《不懂的音译》,1922年11月4日、6日《晨报副刊》。)他在与周作人合译、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略例”中曾指出,“!表大声,?表问难,近已习见,不俟诠释。有虚线以表语不尽,或语中缀有直线以表略停顿,或在句之上下,则为用同于括号”。不过文献用例表明,鲁迅并非带头使用新式标点的第一人。早在1869年,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写成《再述奇》游记,记述了9种基本反映西方标点面貌的符号。1897年,王炳耀在香港出版了切音字著作《拼音字谱》,创制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10种新式标点符号。1904年,严复出版了《英文汉诂》,该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系统借用西方标点符号对汉语进行标点的书。1906年,朱文熊出版了《江苏新字母》,引进使用西方标点符号7种;卢戆章出版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和《北京切音教科书》,提出15种标点符号。这样看来,比鲁迅更早使用新式标点的人还不在少数。
第三,并列词语之间需要作稍大一点(比顿号大)的停顿时,是可用逗号表示的。这样的用例并不少见。譬如,鲁迅《好的故事》“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毛泽东《论持久战》“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因此,教师教学用书“并列词语之间本该用顿号”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
鲁迅《故乡》中这句话使用逗号,其实不只是稍大一点的停顿问题,还涉及到标点符号的修辞作用。它不但“表现了少年闰土介绍各种各样鸟的时候胸有成竹,如数家珍”,还活脱地展现少年闰土爽朗聪明、自信从容的可爱形象。
三、关于“带”和“戴”
《故乡》中有这样两个句子:
(1)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又,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
(2)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
张老师在说明“带”与“戴”的区别和联系时,提到了一些古代文化知识和语言使用情况。这些内容也有必要说明一下。
第一,张老师引用许慎《说文解字》对“带”的解释——“绅也”,然后由“绅”联系“玉佩”,引申出“佩带”义。
实际上,“带”在古代是各种带子的总称,同时又是腰带的泛称(一个词用于上位义)。腰带为古人身上重要的带饰,具有礼仪和实用价值,可约束宽衣大袍,悬挂一些饰物,显示官品大小、尊卑之别。腰带有大带和革带两类,大带围在身前交结、交结处以组带约束,并垂下余端作装饰,革带在大带之里,上面有革囊,可放随身杂物,由皮带、带钩、带环、带尾构成,带环套人带钩以固定,革带上常挂弓箭、金玉等物。“绅”最初指大带打结后垂下的余端,后来代称整个大带,常用作大带的专称。不过,“带”引申出“佩带”义,却与张老师提到的“绅”、“绅士”无关。如上所述,“带”为腰带的泛称,而弓箭、金玉等物又可附着在腰带上,所以“带”可转指“将物挂在腰带上”,并发展出“佩带”的意义。作“大带”讲的“绅”在语言史上却未衍生出这个意义,因此“绅”与“佩带”无关。同时,张老师提到的玉佩与“带”、“绅”也没有源流联系。古代的“佩”(佩饰)分佩物、带饰,玉佩虽可系挂在腰带上,但它只是佩物的一种而已。佩物要系挂在其他物体上,所以“佩”也可转指“佩带”义。这样看来,“佩”与“带”虽都发展出了“佩带”义,但二者却是分别沿着各自的途径进行的,它们互不牵涉。说“由于腰带上常常要佩挂些玉石之类的装饰物,因此又出现了‘玉佩’一词。这样,‘带’字就引申出了‘佩带’这个动词的意义及用法”是值得讨论的。
许慎《说文解字·巾部》“带,绅也。男子□革,妇人带丝”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带”与“绅”的意义是完全对应、等值的,段玉裁对此有解释,“古有大带,有革带;革带以系佩韨,而后加之大带,则革带统于大带,故许于绅于鞶,皆曰大带”。段玉裁的说法和我们上面的描述是接近的。
第二,张老师认为,词典上表示“佩带”义的“戴”,最初的意义为“把东西放在头上”(如“戴帽子、戴头盔”),这个意义的“戴”过去也不可以写作“带”。
查检语言史资料,表“佩带”义的“带”早在宋时即已演变出“把东西放在头上”的意义,譬如宋李清照《永遇乐·元宵》词“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簇带争济楚。”王学初校注“‘簇带’,宋时方言,插戴馒头之意”。该义在后世屡有沿用,《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二“头带斜角方巾,手持盘头拄拐”,《红楼梦》第五十二回“满头带着都是玛瑙、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20世纪初的用例有张天翼《包氏父子》二“‘包国维’一个带压发帽的瞅了一眼缴费单”。因此,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义为“把东西放在头上”的“戴”是可以写作“带”的。
第三,张老师认为,“戴”的使用范围后来从“头”发展到了“面、颈、胸脚”等部位,“戴”与“带”就可通用了。
这个说法也与语言史的资料不符。“戴”的使用范围从“头”发展到“面、颈、胸脚”等部位,秦汉之际即有用例,如《礼记·丧服大记》“皆戴圭”,孔颖达疏“谓诸侯六翣两角皆戴圭玉也”。从前面论述可知,这个用法的“带”与“戴”通用,只是在宋时才见用例,时间距离颇大。可见不像张老师所说,“戴”发展出此义后二者接着即可通用。
第四,张老师认为,“戴领结、戴领带、戴项链、戴臂章、戴孝、戴罪立功、披星戴月”等词语,其中的“戴”在过去较长时期内也写作“带”,且以写“带”的居多。
我们随机选择了几个词语,通过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检索使用频次:“带罪立功”出现29次,“戴罪立功”出现69次;“披星带月”出现9次,“披星戴月”出现125次;“带手表”出现3次,“戴手表”出现15次;“带孝”在晚清民国文献中出现44次,“戴孝”出现52次。这个数据表明,并非所有的词语以写“带”的居多,写不写“带”与这些词语指“把东西放在‘头’以外的身体其他的部位”无关。
如上文所述,在鲁迅先生写作这篇文章的20世纪初,不论是在“把东西放在头上”,还是在“把东西放在头以外的身体的其他部位上”,“带”与“戴”都可使用。那个时代的辞书在努力区分二者,但人们实际使用却并不依循辞书。譬如初版于1937年的《国语辞典》(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指出,“带……佩带。”“戴……负于顶上……插或架,如戴花、戴眼镜等是。”但仍有将“戴眼镜”写作“带眼镜”的,如方令孺《去看日本的红叶》(1936年)“另一个是中等身材,带着眼镜子,正伏在一本簿子上忙着抄写”。尽管如此,不同的人在选择“带”和“戴”时,仍有一定的倾向,比如一般写“戴帽”不写“带帽”。鲁迅写“项带银圈”、不写“项戴银圈”,只是一种个人偏好,而在更早期的小说《施公案》(成书于1903年)中,可以找到“细瞧,脖项戴着赤金项圈,心中一动”的用例,可见别人仍有写“戴”的情形。今天的语言文字研究者和辞书编写者,倾向于以“带”表示“随身携带”、以“戴”表示“把物品放置在能发挥其功能作用的身体某一部位”,便于词语表义的明晰和选择的经济,但是我们却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框定过去的语言现象。鲁迅用“带”还是用“戴”,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使用偏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