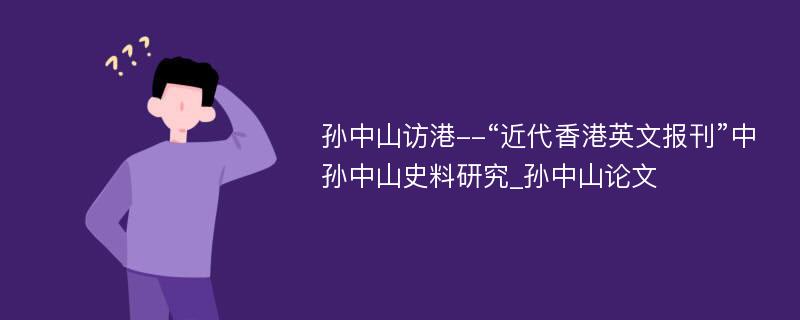
孙中山香港之行——近代香港英文报刊中的孙中山史料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英文论文,史料论文,之行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是孙中山相继接受近代中等和高等教育、萌发革新与革命思想的地方,是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据以发动中国民主革命的最早策源地。自从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组织乙未广州起义,因失败而被迫离港流亡以后,港英当局对他先后发出的放逐令至少达四次之多。然而,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始终将香港作为促进中国革命运动的前进基地,孙中山也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进入香港,指导党人开展革命活动。孙中山遭港英当局放逐之后的香港之行,对华南乃至香港的政治流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5年春夏间,笔者受孙中山基金会的委托,承蒙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坤耀教授的帮助,得以在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大会堂图书馆等处,查阅《mā孖剌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德臣西报》(China Mail)、《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等香港近代英文报刊,收集有关孙中山的史料。归来整理所得,计复印有报道和评论孙中山言行的史料数十篇,其中包括新发现的孙中山佚文12篇,可资订罅补漏的同题异文14篇。如果加上笔者先前在《香港华字日报》中发现的孙中山佚文31篇,则在香港近代中英文报刊中已检索出孙中山的佚文及同题异文共57篇。[①a]兹将在香港近代英文报刊中浏览到的有关孙中山遭放逐之后香港之行的史料,作一简略的摘译与论析,以求教于方家同好。
清末孙中山遭放逐之后的香港之行
1895年11月初,孙中山在领导乙未广州起义失败之后,离开香港,流亡日本。次年3月4日,港英当局应清政府请求,以“总督及行政局认为孙逸仙会危及本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为由,宣布从即日起,5年之内,禁止孙中山进入香港和在港居留。此后,港府还在这项命令期满之后的1902年和1907年,相继重申对孙中山的放逐令。孙中山在清末三度遭到港英当局的放逐,似乎已不可能再到香港,进行革命活动。然而,在革命党人日后的叙述中,却不乏孙中山入港活动的记载[①b]。不过,这些记载均属事后的回忆与补述,当代史家对此多持审慎态度。
1995年春,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举行“香港青山红楼与辛亥革命”研讨会,邀请大陆和港、台学者参加。1896—1911年间孙中山曾否入港活动,乃至曾否到过屯门青山农场,自然成为会上会下讨论的话题[②b]。香港学者吴伦霓霞教授在大会发言时,援引香港早期革命党人谢缵泰所著《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和杨西岩的回忆,指出:“唯一重要的可能性,就是一九○二年的一月,孙中山也许曾踏足香港。……这说法还需查阅其他革命分子的记录,看看有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③b]
笔者受此启发,在当年《德臣西报》发现一则报道,可以证明1902年1月底孙中山确实进入香港,并作短暂居留。这则报道题为《孙逸仙在香港》,载该报1902年2月1日。兹翻译如下:
举世闻名的中国改革家孙逸仙已返回本殖民地。我们通过非官方而又完全可信的渠道获悉,他正和另一位著名的改革家暂住在士丹利街(Stanley St.)。他穿着欧洲服饰,行动颇为自由。他在日本住了相当长的时间。鉴于最近一位香港改革者被绑架,以及一位担任教师的改革者在结志街(Gage Street)被暗杀,他来到如此接近中国的地方,正冒着极大的危险。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进行某种十分重要的活动。我们一度认为,本殖民地曾对他发出一定期限的放逐令,但显然此令已过期。
上述报道证实了谢缵泰于1924年发表在英文《南华早报》的《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的叙述:孙中山在1902年1月28日抵达香港,居住在士丹利街24号。另据日本驻香港领事稍后的报道,孙中山于2月4日离开香港,乘船前往日本。日本外务省有关档案称:孙中山此次“赴香港目的是与同志会合研究善后办法。到港后,有引起各国注意之嫌。本人见此情形,认为必须尽快离开英领,数日内别走他处”[①c]。
孙中山此次入港居留一个星期,是在香港政府对他第一次发出的放逐令业已过期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目前可以确定的清末孙中山离港流亡之后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返港居留。在此期间,“行动颇为自由”的他是否去过刚刚辟建为革命党人秘密活动据点的屯门青山农场?这一问题迄今仍为悬案。解答的关键在于发掘当年港英当局跟踪监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档案资料。
除1902年1月底、2月初一度返港居留之外,孙中山还在此前后利用乘船泊港的机会,进入香港水域,在船上会见在港革命党人,指导他们开展革命活动。现有资料表明,清末孙中山遭港英当局放逐之后入港而未登岸的香港之行,共有6次[②c]。其中尤应注意的,是1900年六七月间孙中山两度乘船泊港,在船上与香港革命党人磋商策反两广总督李鸿章、在华南发动反清独立和起义诸事宜。其时,港督卜力(Sir I.I.A.Blake)欲秘密支持此事,以便港英当局从中渔利。7月13日,卜力致电英国殖民地部大臣张伯伦称:“现在我只能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虽然孙已被放逐出香港,但如果他为了与李鸿章会商而悄然回港,最好不要干涉他。”[③c]然而,次日卜力接到英国政府的指示:对孙中山的五年放逐令仍然有效,不可和李鸿章谈及与孙中山合作事。因此,当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人在17日乘船抵港时,香港警方即向他们重申放逐令。当晚,李鸿章奉旨北上,途经香港,卜力仍欲劝其留港与孙中山会晤。次日,孙中山将港督意图告诉宫崎寅藏,并称“期以今日十一时与李密会。李行若止,余亦解保安条例,登岸共与密议一切”[④c]。可是,李鸿章以效忠清室的顾命老臣自任,不肯接受港督的劝留,仍然决定先行北上。7月20日,孙中山乘船离开香港,前往日本。此次孙中山在泊港邮船上停留三四天,是为历次泊港时间最长者。其间他是否一直恪守港府放逐令,始终没有秘密登岸?这一问题,或许也只有发掘当年港府有关档案资料才能得出定论。
7月24日,《德臣西报》登载《改革者孙逸仙及其一些活动》一文,介绍孙中山遭放逐以来在英国和日本等国避难的情况,及其刚结束的欲与李鸿章在港会晤的香港之行。文章称:
在当前中国的骚乱爆发之际,孙焕发起对未来行动的期望。我们相信,他与新近的叛乱首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首领幸而得以脱逃,分散在中国各地,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傲视本殖民地安居乐业的法则,其目标却是推翻中国的腐败政府,拔擢更为开明的统治者。
我们从最可靠的官方渠道得知,大约一个月以前,李鸿章施行收买对手这一典型的中国策略,致电日本,邀请孙逸仙到广州,以便与之商谈,使事情得以转圜。孙乘日轮抵达香港码头,但未上岸,因为对他的放逐令还未期满。不过,他在船上会见了李鸿章派来的代理人,那人向他陈述李鸿章希望得其协助实施的计划:李希望他去广州,以便安排和他一道起兵,进军北京,打败义和团,使皇上和皇太后摆脱顽固党的控制。假如皇上和皇太后死了,李便建议孙帮助他实现两广独立。然而,即使孙相信李鸿章的代理人所提计划的真实性,也不足以使他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到总督衙门拜访李鸿章。于是,他前往新加坡,试图与康有为打交道,据说被拒绝,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从新加坡经西贡回到香港,上星期二乘日轮泊港。他是否乘该轮或换乘别的轮船去日本,我们不得而知。他最近的行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
此外,1906年初夏孙中山从新加坡乘船前往日本,他在途经香港时,是否因与革命党人会商策动粤东起义等事而秘密在香港登岸,也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同年5月17日(旧历四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周馥致电清廷外务部,称孙中山现在香港居留,要求商请港英当局将其驱逐出境。该电文称:
前接新加坡总领孙士鼎电,探闻孙文有回华作乱之谣,当今电达大部。现访闻孙文改洋装,住香港公益报馆。又有同党邓子瑜住香港旅安祥客栈。前获逆党陈纯供,邓子瑜为孙文管外事,现闻招集香港匪徒,入内地勾引乱民滋乱。……务求大部速密电英使,转电英政府,饬港督速将二逆逐出,非此不足保护中外治安。[①d]
除上述孙中山香港之行以外,1908年3月10日《德臣西报》刊载的专题报道《孙逸仙医生在香港》[①e],还记载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孙中山又一次香港之行。该报道称:
孙逸仙医生是中国政府悬赏20万巨款的众所周知的叛乱领袖,他现在正在香港。他在泊港的一艘日轮上,该轮从日本前往新加坡途中路经香港,他的一些伙伴和他在一起。他在本港短暂停留期间不会登岸。向我们提供这一消息的是孙的一位同党,但他对孙的活动却缄默不言。
该报道追述1896年孙中山遭港府放逐与伦敦蒙难等事件之后,继续写道:次年孙曾在日本致函香港政府,要求允许他回港,但遭到拒绝。“此事在(英国)众议院中引起极大的关注,戴维德先生曾质疑其中的原因。有关方面对发出放逐令的方式进行严格的调查,认定香港行政委员会长官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并且指出,在放逐令发出之前,孙逸仙医生已离开本殖民地。然而,政界和报界都对他表示很大的同情。……自从1901年3月4日放逐令期满以来,孙逸仙医生已访问过本殖民地,并对本殖民地的革命党事务具有影响力。……他是一个精明的人,在他的同胞中有很大的影响。”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辛亥革命的凯歌声中乘船返国,途经香港,准备前往上海,领导组建中央政权。这时,港府在1907年对他发出的第三次放逐令仍未过期。不过,或许是感受到香港华人社会支持辛亥革命的热情和压力,港府破例允许孙中山公开在港岛上岸,在码头附近的兰室公司接见省港各界欢迎代表,即席发表演说。甚至有传闻称,如果时间上不冲突的话连港督都愿与之会晤。当天或次日,香港中英文报刊分别报道孙中山此次香港之行。其中,《德臣西报》在次日以《孙逸仙在香港——对中国同情者演说——提倡借外债》为题,报道说:
昨天,孙逸仙医生在香港短暂停留时最引人注意的事情,就是他在于诺道(Connaught Road)一家华人会馆(Chinese club)向一群中国同情者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谈到中国共和运动的未来。
中文《香港华字日报》对孙中山这次香港之行作了更详细的报道:
昨日孙中山君乘“地云夏”英邮轮抵港。九点钟时,抛泊码头。有胡都督、参谋部谢良牧、谢适群偕游欧学生某某二人及港商林护,乘顺利小轮到邮船谒见。随即有同盟会中人李纪堂、陈少白、容星桥等,乘广州小轮至船,先后相见,晤谈至十钟余,始偕往能都督乘坐来港迎接孙君之江固兵轮。当时有港政府派出暗查多名保护。众人与孙君谈至十二点半钟时,因有日本人到英邮轮候见,内皆与孙君历年交好者,孙君旋即回英邮轮与之接晤。少顷,即乘广州小轮由三角码头登岸,以相约至兰室公司聚话。三角码头离兰室公司不远,虽备有舆马,亦不乘坐,相率步行前往,到后进午食。至三点钟时,粤省七十二行、九善堂、总商会所派出代表来港迎接孙君诸人,亦到兰室公司晋谒……
至四点半时,孙君仍步行至三角码头,乘顺利小轮而去,众人送至邮轮乃返。并闻港督本约与孙君相见,因是日适为本港定例局会议之期,而邮轮开行时在五点半钟,是以未能晋谒港督云。[①f]
至此,我们可以作一小结:目前可以确定,清末孙中山离港流亡之后至少有9次乘船进入香港,与在港革命党人会晤,其中至少有两次名副其实的登岸活动。
民国时期的孙中山香港之行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成为首位临时大总统和开国元勋。然而,港英当局却一度坚持先前发出的对孙中山的放逐令。对孙中山的放逐,最初据称是由于“不愿容许任何人在英属香港地方组织策动机关以为反叛或谋危害于素具友谊之邻国”[②f]。如果说,港英当局的这一举措在1898年就被英国众议员戴维德批评为不以国际政治犯的待遇来对待孙中山,而是固执香港地方法例以对抗国际法则;那么,在民国成立、清朝覆亡、孙中山已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并获得举国尊崇之后,港英当局竟然继续执行以往对孙中山的放逐令,这就不仅不符合国际法则,而且也与港英当局最初宣称的“眭邻”初衷背道而驰了。
1912年4月24日,刚刚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乘船前往广州,途经香港。香港各界团体先期闻讯,纷纷准备举行盛大的欢迎活动。当天的《德臣西报》以《孙逸仙在香港》为题,报道说:
今天早上孙逸仙医生乘坐中国商轮泰顺号抵达香港。他是策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曾荣任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统。
华人社会为了欢迎他们的伟人——尤其因为他是华南人,而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本城到处飘扬着(中国)新制度的旗帜,这些旗帜的设计并不一致,显然至少有五种不同的款式。商会团体也安排欢迎这位前总统的庆祝活动,各团体选出四名代表,分别与他会晤,地点安排在西角(West Point)的遇安馆(Yu On Club);另一处会见地点在皇后大道中的中国会馆(Chinese Club)。
然而,这些安排都不得不取消,因为孙医生根本没上岸。他一直留在泊靠在码头(the C.M.S.N.wharf)旁边的泰顺号船上,在下午接见拥有数百名成员的团体代表。
香港安排的欢迎计划被取消一事,在华人中引起极大的沮丧,尤其是当最初宣称孙医生将离港赴粤而不接见本地华人的时候。不过,当他们得知孙医生打算在船上接见访客时,沮丧的情绪才大为缓解。
这篇报道没有说明孙中山为何取消计划,不上岸参加香港各界团体举行的欢迎活动。次日,上海《民立报》刊登该报“香港特派员”来电,才揭开这个谜:
香港政府因港人将开欢迎会,下令禁升悬欢迎旗,又禁登报,又禁派传单,又禁鸣炮,港人甚愤。
闻孙先生本云见港督后,赴欢迎会,继仅派廖君代表,实因港政府取缔,不便面却之故。[①g]
香港政府不许孙中山上岸出席香港各界团体专门为他准备的欢迎会,孙中山只好派廖仲恺为代表上岸出席,自己则在船上接见专门登船表达欢迎之意的香港68个团体和省城80个团体的代表。当天下午3时,孙中山一行改乘广东军政府派来迎接的宝璧舰,前往广州。
有趣的是,20多天之后,港府又允许孙中山在香港公开登岸,并作短暂居留。这年5月18日晚上,孙中山与家人抵达香港。22日,孙中山一行才离开香港,前往澳门。在此期间,省港各报记者纷纷前来采访,报道孙中山的政见与在港行踪。5月20日,《士蔑西报》以《孙逸仙医生访港并否认他将退居澳门》为题,报道说:
中国改革家孙逸仙医生星期六(18日)晚上抵达香港。他乘坐广州到九龙的晚班火车,正好在七点前抵港。陪伴他的有孙夫人和他的一个女儿,以及别的一些人。他们住在香港大酒店(Hong Kong Hotel)的房间里。晚饭后,他们前往九如坊戏院(the Kau U Fong Theater),欣赏大雷蒙德(the Great Raymond)的表演节目。
《南华早报》记者在《孙逸仙接受本早报采访,谈及为何主张取消通商口岸与所谓“黄祸”的真实性》一文中,写道:
他在香港度假几天,但这是很繁忙的假日。他经常接受来访消息或邀请。在我与他交谈的半个小时里,就有好几个来访者、一些便条和不止一封电报。[②g]
《德臣西报》则以《孙逸仙医生在香港——他的观点和抱负》为题,详细报道孙中山对列强迟迟不承认中华民国的看法,以及他的社会主义抱负和对中国与基督教关系的看法。这是一篇尚未为今人了解的孙中山佚文。文中所载“社会主义抱负(SOCIALISTIC ASPIRATION)”一节,是迄今所知的报道孙中山最早而又最详细地阐述其社会主义观的重要史料。兹译录如下,以飨同好:
记者问:“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知道你所考虑的中国将采取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也许你认为在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将会轻而易举,因为许多地方保留着共产均富的方式(a form of communism),尤其是乡村?”
孙答:“是的。”
问:“我听倡导社会主义的人说过,社会主义必须自然发展,而不是靠国会议决或革命行动突然转向。”
答:“对,是这样。不过在中国,若要防止资本家获取过大的权力,则应立即提倡社会主义。”
问:“那就不会是自然发展了?”
答:“我提倡国家社会主义。你必须记住,有很多事情在国家社会主义当中是人为的,不自然的,例如在德国就是如此。这种社会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过激的社会主义反对这种社会主义,但我相信这是中国要走的第一步。”
问:“你所指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什么?是否意味土地、铁路、工业的国有化?”
答:“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有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市政工程、自来水厂、煤气厂、铁路、有轨电车以及其他公用事业都归国家所有。”
问:“那是集产主义(collectivism)吗?”
答:“集产主义与共产主义(communism)是社会主义的不同形式,它们都殊途同归。国家社会主义是开端,其第一步是通向集产主义。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担心国家权力过大而反对集产主义。”
问:“就像德国一样?”
答:“是的。”
问:“那么,我想国家社会主义将包含土地国有化了?”
答:“不尽然。”
问:“国家不接管土地吗?土地不归属国家吗?”
答:“只有一些如此。”
问:“那是很特殊的事。”
答:“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倘若需要,我们会逐步接管土地。”
问:“土地国有化计划包括对业主的补偿吗?”
答:“包括。”
问:“补偿的钱从哪里来?”
答:“我们将建议施行地价税,如同莱德乔治(Lioyd George)在英国之提议。譬如政府既经更替,地主必须更换地契,换契时则可知会地主,国家如有需要可以收购其土地。因而要其估算地价,按价征收百分之一税款,国家需要土地时,即可按地主所定地价收购。如此便可低价收购土地,中国土地国有化当不致有别国之困难。如果地价上涨,涨价部分归于国家。中国未如别国先进,欲达别国之文明程度,必须有明确计划。”
问:“铁路国有化如何?”
答:“目前除粤汉路外,均已属国有。中国缺乏资金以发展全国铁路,必须借外债。私营公司不能为此借款,国家则易如反掌。将来国家必须引进外资,发展铁路。如此则可解决铁路国有化问题,因为每条铁路从一开始就是国家的铁路。”
问:“工业国有化如何?”
答:“小型企业确实以私营为好,其效益会更好些。自由竞争优于垄断。若其形成信用,则可将其收购。国家开始时之经营不及私人公司,至于需要行政管理能力之大事业,国家可予接管。”
孙中山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畅谈他理想中的源自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在未来中国施行的宏伟蓝图,阐述他对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和看法,显示出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超前意识,这应当是一件令后世史家较诸当时人更感兴趣的事情。如果将此谈话与孙中山在事隔半年之后在上海向中国社会党所作的社会主义长篇演说作一比较,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先声,后者是对前者的展述。因此这一谈话记录应属研究孙中山乃至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珍贵史料之一。
1912年6月15—18日,孙中山再度到港,作短暂居留。其间,他曾到四邑商工总局等华商团体发表演说,呼吁筹建中西合资银行,引进外资,开展全国铁路建设。他还出席了基督教美华公会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勉励教徒启导民国人心,促进世界进化。
1913年6月下旬,孙中山因南下策划“二次革命”及探视寓居澳门的长女孙娫,而有香港之行。此次香港之行的起止时期,今人已语焉不详;惟据当时报道,则可知实自6月20日起至25日止。同月25日,《南华早报》以《孙逸仙医生与广州的轰动传闻》为题,报道说:
星期五,孙逸仙医生悄然抵达本殖民地。昨天,《南华早报》的一位记者在香港大酒店看见他。看上去,他非常担忧他的女儿的病情。他的女儿住在澳门,生命垂危。星期五,他曾去过澳门。不过,他仍以常有的谦逊,欣然允诺回答颇滋物议的有关广东都督胡汉民离任的一些问题。……孙逸仙医生今天乘船前往上海。[①h]
这年7月中旬,“二次革命”爆发。8月2日早晨,孙中山因沪、宁讨袁军失败,被迫离开上海,乘船前往广东。香港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南下图谋再举的中转地。次日,袁世凯布置诱杀孙中山的行动,指使亲信化名“寄吾”,致电香港威灵顿街的“德宝华公实寿先生”,“望速密商‘宝璧’等舰,佯往欢迎,接赴粤省,诱上船后,出口时处死沉海”,事成后,“执行人员除补官赏勋外,并奖洋十万元”[②h]。此举因张继和马君武托日本驻香港领事转电孙中山不要在香港登岸而未得逞。袁政府又分别与日、英两国政府交涉,请求驱逐孙中山等人。8月14日,香港总督宣布奉英国政府训令,孙中山、黄兴、陈炯明、胡汉民、岑春煊等永远不准到香港[③h]。孙中山于是第四次遭到港英当局的放逐。
在接踵而至的护国讨袁与“一次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除派遣中华革命党人在香港组织“联义社”等革命机关,沟通海外联系,策应内地革命活动之外,他本人没有再作香港之行。
“二次护法”期间,孙中山有过两次香港之行;1920年10月底,陈炯明遵照孙中山的讨桂部署,率领粤军攻占广州,推翻桂系在广东的军阀统治。11月25日,孙中山与伍廷芳、唐绍仪、胡汉民及宋庆龄等人乘中国邮船公司“中国”号轮船,离开上海,前往广东,准备重新建立护法政权。28日早晨,“中国”号轮船泊靠香港,香港各界代表200余人登船欢迎孙中山一行。中午,孙中山一行登岸到九龙,转乘广九专车于下午抵达广州。孙中山等人此次登岸过境,显然得到香港政府默许。港府于1913年8月中旬宣布“永远不准”孙中山等人入港的禁令,看来黯然失效了。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悍然发动叛乱,指挥叛军推翻孙中山在广州创立的“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孙中山率领护法海军舰队在粤海省河坚持与叛军对峙50多天,终因外援不继,被迫离开广州。8月9日下午,孙中山与蒋介石等随行人员乘坐英国驻广州领事派遣的英国“摩汉”号炮舰,从广州前往香港。次日“上午六时船抵香港,旋即乘‘俄国皇后’号邮船,香港政府派员前来照料一切。正午十二时,由香港启碇,出口归沪”[④h]。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广州蒙难之后取道香港前往上海,其行程安排始终处于港英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8月14日,就在孙中山抵达上海的当天,英国陆海军联合情报局香港总部秘书W.D.培根致函上海情报局秘书,称:“孙中山现已去上海,我们就难于获得有关他的计划和行动的情报。如蒙将他留沪期间所进行的政治活动给我局每周一次报告,如有重大事情发生送一份特别报告,则不胜感激。”当天,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将此函转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总巡警麦高云,请其办理。25日,麦高云复函称:“兹准备每日寄上警务情报摘录一份,并建议从九月四日始每星期一送上一份这些报告的摘要。”从现已公布的档案资料来看,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在1922年9月4日至1923年2月19日,每周按时向英国陆海军情报局香港总部送一份有关孙中山与国民党要人在上海活动的情报摘要,共达24份[①i]。目睹这些史实,笔者不禁生发遐想:港英军政当局严密监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行踪的事例应该不止这一次,这类监视跟踪的情报档案在今天具有无比珍贵的史料价值,倘能发掘整理公之于众,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
港英当局协助孙中山一行撤离广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二次护法”期间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与港英当局相互防范的紧张关系。因此,孙中山返沪之后,在酝酿联俄联共政策的同时,还派人与港英当局联络,争取其支持国民党在华南继续发动的“三次护法”运动[②i]。港督司徒拔(Reginald E.Stubbs)认为,孙中山和国民党将会继续在华南发展,设法与之合作要比反对他们好得多。据说,1922年底,他曾向奉孙中山之意来访的傅秉常表示,愿意邀请孙中山访问香港。1923年1月11日和19日,孙中山两次派陈友仁拜访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暗示孙中山和香港总督之间的会晤,将会是符合人心的。下旬,港督司徒拔称:只要孙中山不以民国总统或英国政府未予承认的其他身份抵港,他都非常乐意接见,并与之共进午餐。2月1日,孙中山派陈友仁、伍朝枢拜访路过上海的英国驻华公使罗纳德·麦克利,表示他将重返广州。麦克利随即向英国外交部建议,只要孙中山不在香港工人中挑起事端,英国政府就应该对他保持友好态度,因为“他在南中国,在海峡和马来群岛以及在美国的中国居民中间,毫无疑问地具有突出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经常考虑的一个因素”[③i]。于是,孙中山遂有四遭港府放逐以来最受隆重欢迎的香港之行。
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与随员陈友仁等一行乘坐“杰弗逊总统”号邮轮离开上海,前往已由讨贼联军重新占领的广州,准备重组护法政权。17日下午5时,香港华人海员工会租用许多汽船,张挂彩旗,鸣放鞭炮,从中环驶出筲筲湾的鲤鱼门外,迎接孙中山等人乘坐的邮轮进港靠泊。6时许,邮轮进泊香港九龙仓码头,孙中山一行换乘汽船来到港岛干诺道中的卜公码头,受到早就等候在那里的香港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孙中山等人乘车驶往半山干德道9号,下榻于港商、国民党要员杨西岩的私宅,随即专程拜会港督。当晚8时起,香港全城鸣放鞭炮,欢迎孙中山到港,鞭炮声此起彼落,持续3小时之久。
18日中午,孙中山及其随从应邀到港督府,出席港督史塔士主持的午餐会。有消息说,这天港督接到英国驻华公使来电,让其以英国“理藩院”名义,欢迎孙中山[①j]。无论如何,这都是孙中山第一次受到港督公开给予的欢迎礼遇。而在1900年和1912年,孙中山先后共两次有意会晤港督,但都未能如愿。强弱尊卑各不同,此次港督肯与孙中山会晤,显然与孙中山在“三次护法”期间拥有足以令港英当局重视的实力和声望大有关系。
同日下午,孙中山一行应邀到位于西摩道的著名港商何东的住宅,与何东夫妇共进茶点。晚上,孙中山出席香港各工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20日上午,孙中山在何东、陈友仁等陪同下,应邀前往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聆听演讲的,有港大教师、学生以及香港教育团体的代表和当地中外知名人士,共400余人。孙中山走进港大,迎接他的学生便欢呼着将他抬进代理校长室。演讲会在大会堂(the Great Hall)举行,首先由港大华人学生会主席、何东的儿子何世俭和港府辅政司、港大代理校长施云(Claud Severn)致欢迎词。孙中山“是日穿长衫马褂,头戴毡帽,精神奕奕,用英语演说”,他的演说不断赢得与会者热烈的掌声。“演说既毕,忽有学生五六人将孙先生抬起,直抬出头门拍照,一(面)步行,一面揭帽欢呼,孙先生亦揭帽答礼,欢声震天”。拍照留影之后,孙中山还会见了与会的三位美国女游客,其中一位是罗斯福(Jean S.Roosevelt)小姐,她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侄女。当天下午,孙中山应邀出席汇丰银行总裁史梯芬(A.G.Stephen)主持的欢迎茶会。随后,他在杨西岩住宅设招待茶会,邀请香港工商界领袖40余人,会商资助广东善后与建设事宜。
21日清晨,孙中山一行到干诺道中省港澳码头,搭乘“香山”号轮前往广州。码头上挤满前来送行的香港各界人士,海员工会还派出多艘汽船相随送行,沿途燃放鞭炮。翌日,《德臣西报》发表评论说:“香港市民如此热烈地欢迎孙逸仙医生,其盛况在香港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更难得的是,这种热情完全是发自每一个市民的内心,没有任何外加的强制与胁迫。”[①k]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为了谋求国家统一,决定离粤北上,前往北京,与各方势力磋商召集国民会议。这天下午5时,孙中山一行乘坐“永丰”舰,在苏联巡洋舰“波罗夫斯基”号护卫下,于当晚12时抵达香港外海。次日早晨7时,“永丰”舰进泊香港铎也码头对开水面,受到香港联义社、工团总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总会等团体专门派出的20多艘船只的夹道欢迎。这些船只“各皆遍布周番旗及党旗,一时旗帜飘扬,招展于海面,真大观也”。“永丰”舰泊碇后,孙中山一行转乘东洋轮船公司的小轮,登上日本“春洋丸”号邮轮。孙中山随即在邮轮大会客室里接见专程前来送行的100多名省港军政工商各界人士。随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应邀步上甲板,由香港民新画片公司黎民伟用摄影机,拍摄孙、宋二人在甲板上漫步和各界人士欢送孙中山北上的动人情景[②k],从而使后人得以永远瞻仰孙中山最后一次香港之行的历史画面。
从1896年开始,孙中山接连四次遭受港英当局的放逐,但他基于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需要,却在遭受放逐之后多次坚持香港之行。其中,可以确认的至少有17次,包括清末9次,民初8次,其中共有7次登岸活动。孙中山多次进行香港之行,除利用过境机会指导在港革命党人开展革命活动之外,还尝试与港英当局联络以寻求某种程度的合作。香港政府之所以允许孙中山多次进港,既有实行自由港政策而不得不任其随船进港的客观原因,也有试图与之联络以谋自身利益的策略考虑,其间反映出港英当局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态度演变。无论如何,孙中山的香港之行与港英当局的反应,都给中国早期民主革命、近代中英关系以及近代香港的历史留下色彩斑澜的一页。笔者相信,海内外史家若能于此发掘更多的原始档案史料,揭示其间的奥秘,不仅可以还原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而且还可以新的发现和收获,促进孙中山研究与香港史研究的新发展。
注释:
①a 从香港近代英文报刊发现的孙中山佚文及同题异文,将译录于孙中山基金会正在编辑出版的《孙文全集》之中。此外,1992年笔者承蒙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吴伦霓霞教授的邀请,在香港作学术访问研究期间,曾从《香港华字日报》发现孙中山佚文31篇。这批佚文全部录入拙著《〈香港华字日报〉中的孙中山轶文研究》之中,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①b 如陆灿遗著《孙中山公事略》称:孙中山于1900年在香港“登岸无阻”,1904年“由广州避难于香港二日”,1913年6月“逃回香港”。见《孙中山研究》第1辑,第348、354、36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此外,日本作家车田让治《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献身于中国的一位日本人的生涯》一书称,1902年2月13日孙中山途经香港,曾秘密在梅屋照相馆小住(转引自俞辛焞等《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第33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此类记载均有待证实。
②b 青山红楼是香港现存的辛亥革命遗迹。1901年5月,兴中会骨干成员李纪堂在香港屯门青山购建农场,同时作为革命党人的隐蔽所和武器试验场。红楼为农场的办事处。倘若孙中山到过青山农场,红楼的历史意义将更昭显。
③b 吴伦霓霞:《“红楼与辛亥革命”几点补充》,《亚洲研究》第13期,香港珠海书院1995年4月。
①c 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75页。
②c 据《孙中山年谱长编》、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等资料所载,其时间分别为:1900年6月17—18日、1900年7月17—20日、1902年12月13日、1905年10月中旬、1906年4月16—17日和1907年3月15日。
③c 译自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129/300 P.90)。
④c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6页。
①d “两广总督周馥为孙中山现住香港致外务部电”,《清政府镇压孙中山革命活动史料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①e 该报道的英文标题为:DR.SUN YAT SEN IN HONGKONG。“DR.”可译为“医生”或“博士”。清末民初期间香港英文报刊以“DR.”称呼孙中山,其意应源自孙曾任“医生”的职业,而非如中国人日后以“博士”作为孙的尊称,故本文依其原意,译为“医生”。
①f 《中国革命元祖孙逸仙抵港谈话及离港时期纪略》,1911年12月22日《香港华字日报》。
②f 引自1897年10月4日香港辅政司史超活路克答复孙中山质疑其遭放逐的信,见陆丹林《革命史谭》,《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4—505页。
①g 1912年4月25日《民立报》第3页“广东电报”;另据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称,当时谢被推为香港欢迎团体的发言人,向孙介绍这些团体的代表。
②g 该文载1912年5月20日《南华早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8页据胡汉民编《总理全集》录入此次采访记录,但日期误定为同年6月。
①h 文中所指“星期五”为6月20日。孙中山在港期间,《士蔑西报》记者也曾来采访,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5—66页。
②h 《赣宁之役资料散辑》,《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
③h 据《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839页。
④h 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日记》,《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5页。
①i 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情报选译——有关孙中山在沪期间政治活动部分》,《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3期。
②i 关于孙中山与国民党在1917—1923年间三次进行的护法运动及与港英当局的关系演进,详见拙著《护法运动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i 参见〔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153页;陈福霖《国共合作以外:孙中山与香港》,《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第257—258页;余绳武等《20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1995年版,第91页。
①j 见1923年2月25日上海《申报》第11版。“理藩院”,今译作“殖民地部”。
①k 有关孙中山此次在港行踪的叙述,主要参考如下资料写成:周卓怀《民十二国父经过香港盛况》,台湾《传记文学》第7卷第5期;《孙医生向学生演说》,1923年2月20日《士蔑西报》;《孙文在大会堂演说》,1923年2月21日《香港华字日报》等。
②k 据《孙逸仙医生北上过港》,1924年11月14日《德臣西报》;《大元帅北上过港各界欢送之盛况》,1924年11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
标签:孙中山论文; 李鸿章论文; 德臣西报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上海活动论文; 香港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广州活动论文; 南华早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