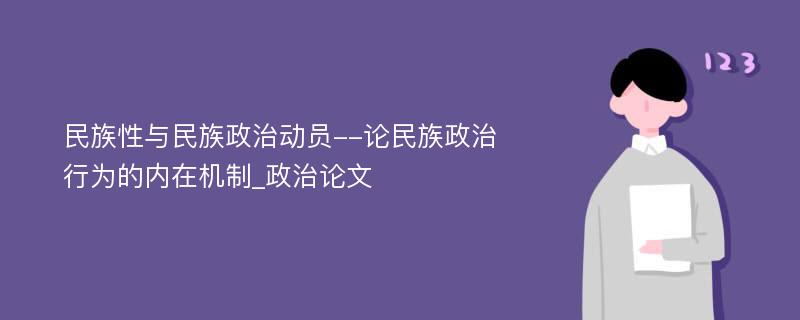
族性与族性政治动员——族类政治行为发生的内在机理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族类论文,机理论文,动员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3)06-0044-06
人类关于族类群体的认知差异源于不同族类群体自身的差异、源于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源于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价值诉求等因素。围绕族类群体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影响,中外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理路和话语体系,而族性(ethnicity)这一术语的出现,为我们较为准确地理解民族政治(族群政治、族裔政治)①提供了效度视角。
一、族类群体的名实之别
人们在族类群体认知和称谓方面存在不同,这些不同既体现在时间维度上,也体现在空间维度上。
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加拿大、南非、西欧、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具有使用“种族”这一概念区分不同族类群体的传统。这些国家或地区要么是殖民主义的策源地,要么是殖民主义的盛行地,在这些地方生物学意义的种族体验以及种族观念与政治观念的交织体验是主流。总体来看,在那一时期是以“白人”、“黑人”以及“有色人种”来区分族类群体的。作为传统民族国家大本营的西欧,往往更侧重于以政治意义的民族(nation)界线看待进入这些国家的劳动移民,并进行严格的入籍限制。毫无疑问,前国家时代社会层面的种族差异与地位差距被带入了国家时代的政治设计之中,国家时代的政治规制又赋予了不同族类群体不同的地位与权利,族际接触与族际交往被不同的政治框架所规约。
“族性”与“族群”是移民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产物之一。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兴起,政治上受到歧视的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美国土著人、西班牙语系移民开始进行民主权利诉求,并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族性(ethnicity),尤其是“族群”一词逐步成为对外来各种移民群体的称谓,这一概念还通过学术交流和教育交流的形式传到其他地区(包括我国的台湾地区)。同时,随着西方国家大多采取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政策,族群大有涵盖一切族类群体之势。但在西欧国家,还是保持以国籍和地区区分外来移民群体的传统。在南非,种族分群意识依然保持有很强的惯性影响。
20世纪70年代,原住民运动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兴起,他们不断强化自己对原来土地的主人身份,为自己正名:加拿大习惯上称“第一民族”;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屿称土著民;台湾地区称原住民;美洲大多数国家直接称“印第安人”;北欧的原住民群体则直接称“萨米人”和“因纽特人”等。原住民群体自我认定称谓的做法正是不同原住民群体凸显自我价值与地位的表现,甚至是对历史上“他称”的革命化摈弃。
在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主要是西亚和南亚),由于社会整合程度低,部族是当地的主要社会单元,这些国家的内部部族意识和部族认同依然很强烈,在这些国家,部族自然成为了族类群体的称谓。
而在冷战结束以前的东欧和苏联,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是这些国家确定和划分族类群体的主要依据。斯大林“四个特征”的民族定义主要是为批评当时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伦纳尔和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而提出的,同时也具有取代沙皇俄国时代的部族观念,唤醒各部族的政治诉求,共同推翻沙皇俄国统治的意义。在“苏式”民族定义和民族自决理论的指导下,苏联采取了包含民族自决精神的联邦制,加盟共和国层级的民族自决与加盟共和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存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挥发着浓厚的政治气息。
由于特定的时代原因,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我国民族理论界曾具有长期而深刻的影响,随着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民族理论界从中国族类群体的实际情况出发,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兼顾吸收世界不同国家对人类族类群体的治理经验,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与话语体系。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将民族描述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1]。我国的“民族”在中国民族理论体系中有其特定的含义,它不同于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公民集合体意义的nation,而是指作为集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为一体的族类共同体。
可见,不同国情、不同语境、不同时代、不同认知体系中的族类共同体的概念和所指是具有很大差异的。从民族政治学的角度讲,当代族类群体主要涉及四个类别:民族(nationalities)、族群(ethnic groups)、原住民或土著人(indigenes people)和部族(tribes)。在不同的场景下,以上四类族类群体也常常和种族(race)这一生物学意义上的群类划分及其种族主义绞合在一起。按照中国的理论体系和话语指代,可以将以上四类群体统称为“民族”。但在西方语境中,以上四类族类群体却有不同的所指。
民族凸显的是政治性②。民族就是或应该是与某个主权国家(state)或类似主权国家的政治形式联系在一起的[2]27。民族主义领域的大师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不是国家并且不是族群,他认为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强调的是民族的客观因素,认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民族的定义(“它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且被想象成天生拥有边界和至高无上”[3])又过于强调民族的主观因素。他建议给民族概念下这样的定义: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4]14。金利卡等西方学者认为高度的自治性和政治自主性是民族的特点[5]。
族群凸显的是文化性。族群通常是指移民群体和在政治上没有被动员起来的少数群体。主体民族往往不称自己为族群,族群的目标不是成为与更大社会并列的单独和自治的民族,而是希望改进主流社会的制度和法律,使主流社会更好地接受文化差别。族群强调的是文化特征,是某个民族——国家之内的一种子集,常指外国的、外来的或少数的群体[4]12-14。外来性、非主流、文化性是族群的重要内涵。
土著(或原住民)凸显的是原初性。“土著”一词是人类学用于描述一块土地上没有被统治的人,自称土著(或原住民)。原住民被认为是没有政府的人们,经常和没有实现工业化联系在一起[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萨米人、因纽特人、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人、夏威夷原住民等纷纷向所在政府提出身份认可、土地安置等主张。原住民运动所追求的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政治目标和自我决定的社会发展路径。
部族凸显的是闭合性。部族是对传统社会和原始社会人群的称谓[6]。通常是指人数较少、文化水平较低、现代民族意识较弱的群体。苏联学者将部族界定为人类群体由氏族向民族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欧洲学者也通常认为部落是原始的社会群体,用ethnicity称呼部落。而中东学者则不认为部落具有欧洲人看待非洲人那样的负面涵义,他们认为部落认同和一致性是中东国家的显著特征,他们认为部落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而不同于史密斯关于部落与民族的划分[7]。
可见,人类在不同的时空限域内形成了不同的族类群体,相应地反映在主观认知层面就表现为对于人类群体不同的概念界定、话语描述和理论解读等,不同族类群体之间既存在一定的共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二、族性是可被感知的族类群体特质
族类政治生成的基础是如何聚人成群。族性(Ethnicity)作为一个单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语中,作为一个学术术语则是由莫伊尼汉与内森·格拉泽提出的。莫伊尼汉在内森·格拉泽在研究中发现,在美国移民群体中存在一种“熔炉”政策难以熔掉的“东西”。1963年在《远离熔炉》一书中,他们将这种存续于族类群体中的顽固的东西称之为“族裔集团的性质和特点”,并第一次在学术意义上用ethnicity指代它[8]。斯蒂夫·芬顿在《族性》一书中系统地梳理了族性理论,认为族性是关于“血统与文化”的概念,是民族、族群、种族等人类群体所共同具有的东西[2]3-4。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在西方的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中涌现出大量关于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出版物,尤其是在社会人类学中,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20世纪90年代,族性是被持续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将族性研究与“全球化”、“认同”和“现代性”等范畴联系起来,解释种族冲突、族裔政治、族群政治动员等问题。
关于什么是族性?不同的学者从原生主义、工具主义以及沟通理论和符号理论的视角出发,进行了多学科、多维度的解读③。尽管彼此认知不一,但族性及其人们对它的感知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概括起来族性具有如下的特点:
族性所集中反映的是一个族类群体的普遍特质。族性是不同的族类群体都内含的特质,它蕴藏于族类群体的文化与传统中,它可以通过客观的族类特征外显出来,也可以抽象为主观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特点等。作为群体的普遍特质,族性可以成为族类群体内部成员团结的基础和纽带,进而形成族类群体的认知和行为的一致性。
族性是可以被不同族类群体所感知的。人们关于族性的感知是切实体验、专门化学习、与他族比较等综合因素促成的。被感知的族性是族属意识的重要内容,族属成员对族性的共同感知和彼此认可便形成了族类认同。当族性的外显特征被明确、被标准化,作为抽象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和民族特点被教化、被渲染时,族性的内聚功能就会越强烈、越普遍,族类成员“与众不同”的族属归属就会越凸显。
族性只有在一个族际关系的框架中才会变得有意义。只有在不同族类群体的接触和比较中,族性的意义才会显现出来。族性一方面可以由自我认知并确定,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对应的外者来比照和界定,内部的“我们”必须区别于外部的“他们”。族性比较和族性认知是在族际关系中萌生的,群体接触、交往和比较是族性被认知的条件。
如果进行话语转换,族性相当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所说的民族特征和从特征中抽象出的民族特性,是人们对于民族实体的表征认知和内在认知的综合。使用族性一词,表述和达意精炼,且能与西方的学术话语对接。
一个成熟学科的构建必须依托于一些可贯通于学科所有研究客体的基础术语,显然族性便是实现民族政治学科从对象化向学科化构建可资依托的术语之一,因为它是民族、族群、原住民、部族乃至种族这些族类群体共同拥有的东西。此外,族性这一术语还可以适应一些国家内部复杂的族类划分和超越明细族类开展一般化研究的需要④。
三、政治动员与族性政治化
中性化的族性可转化为政治力量。族性平时蛰伏于广义的民族文化之中,当民族成员和群体面对陌生的、富有威胁性的外部竞争者时,它才会被激活,并通过认同的环节,成为人们认可的内部力量聚集和群体一致性形成的纽带。精英或政治组织通过政治动员,可实现族性的政治化,将族类群体引入政治博弈中。
“族性是当今世界一种主要的政治力量”[9]。这是当代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大师——安东尼·史密斯的论断。族性并不能直接成为政治力量,而是要通过认同的环节。因为族性是形成群体认同的基础,进而会促进群体力量的内聚和群体认知与行动上的一致,从而引发群体行动。对共同族性虚构起源的信仰会随着组织或精英的描述,进入民族成员个人的联系之中,彼此产生“兄弟感”。对共同族性虚拟起源的信仰通常会限定“社会圈子”,并反过来通过圈内联姻等强化这个圈子,并形成对圈子的荣誉感[10]。因而,族性能够将个体的、分散的力量通过认同和情感的贯穿,汇集成群体的、集中的力量,而这恰恰是政治精英所希望得到的“动员法宝”和“廉价成本”。而且,族性动员往往通过点燃族属感性降低被动员者的政治理性与得失考量。
族性政治动员的要件之一是打造政治目的的一致性,即将族类群体认知和行动的一致性与权力或权利的获得勾连起来。也就是说,族性政治动员或族性政治化的目的是获得利益以及保障利益获得的相应权力或权利,而且至少在名义上宣称维护和实现族类群体的权力和权利。
宣扬和强化族性认同是实现族性政治动员的基础。群体认同是群体行动的前提。由于不同的民族成员对族性的感知程度不同,所以不同民族成员对民族群体的认同水平也不同。最宽泛的民族认同是以模糊的共同血统感觉和模糊的共同文化感觉来界定的;较为明确的民族认同是以共同的语言、关于共同祖先的传说或事实上的共同祖先和较为清晰的共同文化感知来界定的;明确的民族认同是在共同血缘和共同文化感知的基础上以清晰的、共知的民族特征来界定的。“我族”民族成员和“他族”民族成员对于族性感知和族性外显具体内容的认识不同,造成了民族成员认同强度的不同和自身眼中的民族边界的清晰度不同,认同界定标准越不明晰,民族成员的认同强度越低,不同民族成员感知的民族边界就越为模糊。认同界定标准越明确,民族成员的认同强度就越强。面对认同程度不一的个体,动员者往往通过宣传手段,张扬与本族相关的自豪、渲染与本族相关的委屈,以族类情感铺展和升华族类认同,从而强化族性认同一致性。
族性政治动员的手段和途径制约动员的效率、效益与效果。族性政治动员的手段和途径是由族类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在允许民族政党和民族社团存在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传统的组织化动员保障了动员的规范性和序列性;在族性政治受控制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有影响的族裔人士通常会发挥动员主体的作用,但其动员的效果有限,除非凭借族类社会中既有的信仰体系;新媒体的出现大大提升了动员的效率与效益,但需要一定的信息技术和设备支持。
族性政治动员和族性政治化会在特定的政治场域发生。其一,有序的、有效的族类政治参与管径被堵塞,族裔政治机会结构缺失,会生成族性政治发酵的环境;其二,族类边界清晰、社会资源配置呈现出明显的族别差异往往是诱发族性政治化和族性动员;其三,族类社会整合度低、国家管控乏力、存在族际冲突遗留影响的国家或地区,容易产生族性政治动员。
从行为学的角度看,族类政治行为的发生离不开族性政治动员的环节,而族性认同差异、多民族国家的族性认同调控策略等因素将综合影响族类政治生态。
四、族性认同的调控及模式
族裔多样化既是当今世界的事实,也是当今世界的总体发展趋势,族性认同调控因而成为各个国家内部治理的重要课题。族性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可以被感知的,通过认同的环节,族性被赋予凝聚族类群体功能。
戴维·米勒认为,我们不应当“将文化上的认同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或者至少当做政治系统之外的东西”,而应当“意识到这种认同所具有的较强的塑造性,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可以被有意识地创造或改变”[11]。米勒的观点告知我们,作为一种文化认同,族性认同时常被带入或卷入政治系统中,族性认同的潜在力量不容被忽视;同时,族性认同是可以调控的。
抛开族性政治动员价值层面的正当性或不正当性的判断,单从技术层面讲,族性认同调控的基本出发点是防止族性被政治化,防范族性政治动员的发生。举目当今世界,较为成型的族性认同调控模式主要有四种:
凸显国民一致性的族性认同调控模式。法国、日本、伊朗、柬埔寨等属于这一模式,这些国家的官方对外宣称为单一民族国家,不承认本国存在少数民族,不允许政治权利与民族身份挂钩,官方设法消除社会成员的族属意识。例如,法国1872年起开始禁止收集宗教信仰归属和种族来源的数据,因此,法国没有少数族裔人口的官方统计数据。[12]2011年4月11日《禁止在公共场所掩藏面部法》简称“罩袍禁令”在法国生效,规定禁止在公共场所用头巾、罩袍、风雪帽或面罩掩盖脸孔。法国因而成为第一个通过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罩袍并已付诸实施的欧洲国家。
在文化层面定位族性的族性认同调控模式。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针对移民和非主流文化类别,采取多元文化政策,承认文化特性和文化平等,主张文化尊重和文化宽容。1988年,加拿大政府颁布《加拿大多元文化法》,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多元文化政策。多元文化政策旨在尊重文化主体的平等地位,在文化层面体现对各族类群体族性的认可和平等对待。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自治也属于在文化层面定位族性的模式。民族文化自治是对特殊的族裔、宗教和语言群体实施的文化意义上的自治。与区域自治相比,文化自治的特点在于:一是文化事务的管理针对的是文化上不同的集团而与区域集团无关;二是这只适用于文化方面;三是只适用于属于该文化群体的人[13]。
社会一体化的族性认同调控模式。南美的巴西、委内瑞拉等大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做法是在推进社会一体化进程中,不划分民族成分,只承认阶层差异,宣扬单一种族不好,反思种族歧视造成的恶果,鼓励不同族类群体之间的混血和通婚,鼓励文化兼容。尽管存在事实上的种族歧视,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不但在种族构成方面相似,而且官方导向也一致,即鼓励各民族互相通婚,创造新的拉丁民族,而不是相互分离。官方已经在赞美意识形态中的种族民主,不是利用种族和民族,而是利用阶层和地位进行社会动员。有学者指出,拉丁美洲的种族联系是以个人种族认同为基础的交往,不是进行政治动员和形成族群的纽带[14]。
通过政治承认降低族性政治化的模式。中国和西班牙的民族区域自治、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地的部落自治等自治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赋予了不同族类群体的自治地位,以满足相关群体实现内部自主管理的需要。从逻辑上讲,自治是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妥协与让渡。作为国家一方,放弃了国民同质化构建的终极目标,从而放弃了民族同化政策,在主权唯一的前提下,为特定的民族提供了自我治理的空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特定民族的政治意愿。作为民族,放弃了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目标,在多民族国家的外壳下,在授权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主张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国家的授权力度和民族的政治满足度的互动决定了自治权力的弹性,由于自治的做法有限度地承认了相关群体的权力与权利需要,因而,能够起到减低族性政治动员的作用。印度尼西亚通过自治模式解决“自由亚齐运动”问题的个案就是佐证。
在现代国家的框架内,不同的族类群体结成不同的社会结构,而族类群体的地位与权利则是由所属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和政治民主水平所决定的。族性是不同族类群体的特质,是人们认知和理解族类群体集体行动的基础,而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承继性,恰如安东尼·史密斯而言:“无论一种民族认同是何时被铸造的,也无论它是怎样被铸造的,一旦形成了,它就很难被根除。”[15]族类政治行为的发生都是以族性认同为纽带或工具,通过政治组织或政治精英施以有效的政治动员为条件的。而从不同的国情出发,因循不同的族性认同调控策略,防范过当的族性政治化或族性政治动员,则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的重要任务。
收稿日期:2013-08-31
注释:
①“民族政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我们关于“民族”一词的理解,综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二字的叠合意指(文化不同的人民群体)和近代自东瀛舶来的“民族”(民权涵义的“nation”)一词的意指,囊括了对“中华民族”、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不同定位和理解。民族政治笼统指代种族政治、族群政治、部族政治、原住民等族类群体政治。族群政治、族裔政治是指以族性认同为基础的政治。族群政治主要是多数移民国家学术界对外来的、少数文化群体政治的界定;族裔政治更侧重从国籍、族源的角度考察群体政治(尤其是一些欧洲传统民族国家)。
②如果从国家形态演变的角度讲,“民族(人民集合体)”是民族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在王朝国家时代,国家的权力属于君王;在宗教普世国家时代,国家的权力属于教皇。“民族”是人民的集合体,是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王权后产生的政治术语。
③关于族性概念的详细述评请见拙作《族群动员:一个化族裔认同为工具的族际政治理论》(《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第35~41页。)
④以美国为例,人口统计部门对本国族裔的统计采取了多元化的族裔分类标准,一般采用白人、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人、亚洲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和夏威夷及太平洋岛屿原住民6大类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