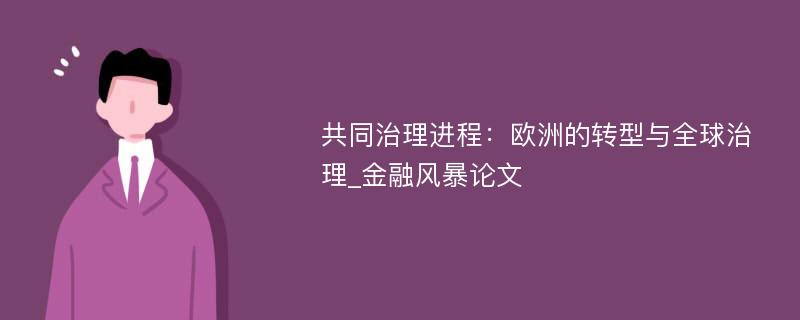
相互治理进程——欧洲与全球治理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进程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2)11-0050-14
一、导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被认为是治理全球经济尤其是治理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主要国际经济制度之一。作为一种“传统”,①自1945年IMF成立以来,欧洲控制这个机构,而美国则控制与IMF平行的世界银行。所以,就全球经济治理而言,“西方的自由秩序(western liberal order)”实则是美欧平分天下,是美欧联合霸权,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单纯“美国领导”。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通过和使用IMF,欧洲稳定地处在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地位。欧债危机是2008年始发的西方金融危机的最新发展。由于危机重创了欧洲,欧债危机使欧盟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欧债危机发生后,欧盟令人吃惊地接受了IMF的介入。IMF成为解决欧债问题的“三驾马车(troika)”之一,这可以看做是欧盟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欧洲在全球经济治理甚至整个全球治理中的主控地位得以巩固,主要原因是欧洲一体化取得巨大进展。但是,欧债问题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欧洲一体化的内在弱点,包括欧洲一体化的一些关键项目,尤其是欧元被广泛认为存在着“设计缺陷(design flaws)”——“自20世纪90年代创立以来一直缺少关键的制度来确保危机发生后的金融稳定”。②未来的欧洲也许将更加一体化。但是,在危机解决和新的欧洲一体化出现以前,欧洲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会历史性地下降或者弱化。
在西方金融危机下,IMF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通过介入危机解决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而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IMF就不得不接受改革。事实上,IMF中的非西方成员尤其是新兴大国一直在要求和推动IMF的改革,以使这个旧的国际经济制度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变化。
介入欧债危机解决的不仅是IMF,还有二十国集团(G20),其重要性明显高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七国集团(G7)和八国集团(G8)。所谓G20介入欧债危机的解决,实际上是G20中的非欧洲成员尤其是非西方的新兴大国对解决欧债危机施加的影响和作用。
在欧洲,许多人认为,当前的西方金融危机代表着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转折点。情况和趋势是否真的如此?本文以欧盟与IMF合作解决欧债危机以及G20对欧洲施加解决欧债危机的压力为例分析欧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的变化,以观察全球(经济)治理的转型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我们要提出和回答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新兴大国能否利用现有国际经济制度(如IMF和G20)影响西方的经济治理?西方和非西方之间通过共同的国际经济制度能否开展本文所称的相互治理进程(mutual governance processes)?
二、欧洲与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变化
有两大因素影响着欧洲与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变化:一是欧洲自身的特性,即长时期的欧洲一体化对欧洲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影响;二是欧洲外部世界的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尤其是新兴大国兴起和西方金融危机背景下发生的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权力转移现象。
作为今日世界多边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量,欧洲或欧盟在维持一个多边、开放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中心和带头的作用。地区一体化使欧洲获得的一个集体经验是,借助共同的规则和制度以及欧洲突出的长期政治传统——混合经济、公共产品、团结,欧洲比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更加倾向于采用多边规则和制度来治理欧洲地区层次和全球层次的相互依存。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京都议定书》等都是欧洲人最先提出和主要设计的。与美国相比,欧洲更加倾向于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在WTO的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讨论自由贸易,而欧洲则谈论全球经济治理。③依据规则的“治理”已转化为欧洲的一种“天性”。我们在这里使用了“天性”一词,意在指出一种逻辑:欧洲或欧盟在当代全球治理中作用的主要来源及其基础是欧洲一体化。如果欧洲一体化得到加强和持续,欧洲在全球治理(多边主义)中的作用就会上升和加强;反之,若欧洲一体化发生反复、后退,甚至危机,欧洲在全球治理(多边主义)中的作用则可能遭到不可避免的削弱。
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在西欧,后来在欧洲,地区一体化(地区治理)成为欧洲发生的最主要变化。欧洲最先提出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开展全球治理的实践。全球治理无不打上了欧洲一体化的深刻烙印。
长期以来,除了各个民族国家成员的外交政策,欧共体和欧盟并没有外交政策。为此,在欧洲政治共同体或者欧洲政治联盟尚未实现的情况下,为了欧洲的全球治理雄心和需要,欧盟推出了共同外交政策。但这样的外交政策缺乏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支持。欧盟贯彻共同外交政策的手段多数是偏“软”的。地区一体化上的“欧洲模式”等欧洲“软实力”都被当做欧洲对外政策的工具;在解决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财政制约之前,欧洲共同外交政策即使在表面上“张扬”(如对阿拉伯世界的干预和支持缅甸的民主化等),④总体仍然是“志大才疏”;在追求和落实一些外交政策目标上,如果需要使用武力,仍然倚重成员国的军事力量,而缺少必要的共同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欧洲针对世界权力格局变化所做出的反应正在推动着全球治理新局面的出现。
美国对全球“权力转移”的反应比较强烈,试图恢复其失去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霸权,针对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如中国的崛起)采取“再平衡(rebalancing)”的战略和政策。这样的美国战略似乎与全球治理根本不沾边,而且会让强权政治或大国冲突而非大国合作重新回到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
与美国不同,欧洲对全球权力转移的主要反应是,试图把新兴大国纳入现存的国际制度中,即促进现存国际制度的扩张或者扩大;同时,接受和主张对现存国际制度的改革,使现存国际制度更加合理和完善,加强多边主义,提高多边主义的效力。
在对全球权力转移的关注和焦虑下,欧洲可能正在面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新兴大国通过一直由欧洲控制的国际制度,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不同程度地介入一些欧盟成员的经济治理,进而参与整个欧洲地区治理。我们在此提出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欧洲“被治理”在21世纪初的出现,是否是全球治理转型的重要内容和特征?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二十国集团介入欧债危机⑤
欧债危机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解决也注定将是长期的过程,IMF也将由此长期介入有关欧洲国家的国内经济治理和整个欧盟的地区经济治理。⑥彼此的需要和利益使IMF和欧盟走到了一起。
德国学者弗朗兹·赛茨(Franz Seitz)和托马斯·约斯特(Thomas Jost)就此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以及该问题的答案:“三驾马车”是否是未来解决金融危机一个最好的制度安排?也即,把“三驾马车”模式用于世界其他地区金融危机的解决。所谓“三驾马车”模式,即地区组织(如欧盟)与IMF的合作。欧盟成为这种“三驾马车”模式的第一个“实验室”。
IMF介入欧债危机的考虑是,“尽管冒着失去独立性和信用的危险,尽管存在道德风险,IMF与欧盟的合作对于IMF的改革是有意义的。IMF需要如同欧盟这样的地区机构使其贷款变得更有效”。⑦如果IMF的介入不是恶化而是协助缓解了欧元区危机,那么这可能意味着欧盟和IMF共同创造了一种治理金融危机的新模式,也许未来欧盟可以在世界各地“兜售”其与IMF合作的经验。
作为“最终的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自这次西方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到欧洲起,IMF就高度聚焦欧洲。在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除了在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时涉及欧洲,IMF并不直接介入欧洲的经济问题。欧盟接受IMF的介入,不仅反映了欧债危机的空前严重性,而且反映了其内部问题确实需要外部解决方案。
尽管欧洲主控IMF,但不少欧洲人并不想让IMF等外力介入欧债危机。一些欧洲经济学家和政客坚决主张欧洲自己的解决方案,认为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建立“欧洲货币基金(EMF)”来对付金融(主权债务)危机,即使不去建立EMF,欧洲已有的欧洲央行(ECB)等地区机构也完全可以独立地应付危机。⑧目前,欧洲存在的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复杂而重叠的机构和项目,如“欧洲稳定机制(ESM)”等,都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但是,IMF之所以能够介入欧债危机,除了发生危机的主权欧盟成员国向IMF求助这一点外,亦来自欧洲地区经济制度在危机下的束手无策。法国和德国不能就一些欧元区成员国的短期债务需要提供欧洲解决方案。欧盟希望借助IMF完善和促进欧洲地区治理。比如,目前的欧洲机构尚不存在紧急贷款和有效监管接受贷款国家的经济调整计划等能力,而IMF正好可以在此方面弥补欧洲的不足。也许在未来,当欧洲机构增加了类似IMF的紧急贷款和监管功能,就可以不再需要IMF介入债务问题的解决。其次,欧盟和欧洲政客缺少必要的正当性和信用,所以,人们总是担心贷款“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的发生,IMF的介入可以有效地缓解道德风险问题。IMF的严苛条件性可以有效监管贷款和贯彻经济改革计划。此外,许多欧盟国家抵制德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稳定文化(stability culture)”。《欧洲稳定和增长公约》(SGP)并没有发挥作用。欧洲国家决策缓慢,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批准计划好的预算协定,失信于金融市场。德国存在着反对为其他国家经济失败买单的力量,这使欧盟对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的援助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这些原因使IMF找到了介入欧洲货币联盟的理由,也成为欧洲让IMF介入的理由。这一点类似于中国当年加入WTO的理由,即利用对外开放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
2008年10月,在咨询欧盟后,匈牙利第一个向IMF提出预备安排(stand-by arrangement)请求。而欧盟使用其“收支平衡协助便捷(BOP assistance facility)”加入IMF向匈牙利提供的附加金融支持。这是欧盟和IMF的第一个联合项目,是自欧盟成立以来,欧盟成员国首次求助IMF的案例。⑨
在伦敦G20峰会前的2009年2月22日,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等国家的领导人发表声明,正式向IMF求助,希望IMF的资源倍增到5000亿美元。面对金融危机的感染和扩散,欧洲领导人想到了IMF驾轻就熟的危机遏阻作用。⑩IMF最初答应提供150亿欧元救助希腊,占整个救助希腊计划450亿欧元的1/3。随着危机在希腊的恶化,并蔓延到西班牙和葡萄牙,IMF承诺在三年内对欧洲的救助份额增大到1200亿欧元。
在解决欧债危机的关键时刻,IMF在2011年却发生了一次其最高行政职务(即总裁)的非正常意外更替。由于欧洲人长期占据IMF的领导地位,除了美国,其他IMF非欧洲成员多有不满。在这次总裁更替中,欧洲遭遇到预料之中的挑战者。为继续保住自成立以来一直控制的IMF总裁位置,法国力克挑战者,赢得了新兴大国包括中国和巴西的关键支持,结果成功卫冕,法国前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接任IMF总裁。
为了解决欧债问题,欧盟更加积极地推动IMF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增资”(11)计划,以使IMF成为解决欧债危机的一个工具。为此,IMF的总裁极力游说中国等新兴国家,为IMF大力增资。(12)
2011年,IMF总裁拉加德批评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主要采用财政“节支(austerity)”措施来解决债务危机。她认为,欧盟创立的纾困基金(bailout fund)不足以解决欧债危机,主张采取刺激“增长”的措施。2012年4月,IMF宣布,已经筹措了至少4300亿美元的额外借贷能力(extra lending capacity),以便用于恶化的欧元区或全球金融条件。2012年6月,拉加德强力介入欧债危机:IMF号召欧元区快速走向财政联盟,因为欧元的存活正在成为一个突出问题。IMF还建议,欧元区纾困基金应该直接贷款给正在挣扎的银行,而非成员国政府,建议欧洲央行采取更为大胆的措施平息动荡不定的金融市场,增加货币供给或者恢复购买那些遭受压力的主权债务。
德国《明镜》周刊指出,“IMF对欧洲政客们逐渐失去耐心,呼吁欧盟对银行业联盟给出清晰的计划。与此同时,IMF警示道,欧债危机依然是对全球经济的持久威胁”。(13)
目前,欧债危机的解决已经呈现出“IMF风格”:几乎所有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尤其是希腊获得的每一笔贷款都绕不过IMF执行董事会。不过,欧盟和IMF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解决方法和处境不同,双方合作中的冲突在所难免。(14)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冲突不仅反映了作为国际经济制度的IMF与作为地区制度的欧盟之间的冲突,而且更体现了IMF中的新兴大国与欧盟的差异。
另外,G20在欧债危机的解决中也在发挥作用。2008-2009年,欧盟成员国政治领导人(如英国首相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奇)和欧洲机构(如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十分敏锐,意识到仅靠美欧和G7是根本无法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危机做出有效反应的。在此时刻,他们力主召开紧急的G20峰会(2008年11月在华盛顿、2009年4月在伦敦)。
德、英、法、意和欧盟五方是G20的成员,加上其他欧盟国家(如荷兰和西班牙)以不同的方式参加G20,所以,在G20中,欧洲势力最大,其作用仍然是关键的。
尽管如此,欧盟在G20中处在两难的困境:借助G20的集体力量应对金融危机,同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但是,由于西方金融危机对非西方尤其是对新兴大国的影响日益深入,G20中的非欧洲国家也要聚焦欧洲问题,甚至希望以合法的形式和内容介入欧洲问题。它们要求欧盟搞好自身的改革,以免欧债危机等其他欧洲问题拖累整个世界经济。结果,在G20进程中,欧盟既治理世界也反被世界治理。前者反映的是一直以来欧盟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后者则反映了世界权力格局的历史性变化对欧洲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历史性影响。
G20进行的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而且是更深入的宏观经济政策谈判。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不仅规定该组织是“主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而且建立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为落实这一框架,G20推出了“相互评估进程(MAP)”,以便确定各国的宏观政策是否相互适应。(15)这是G20取得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制度成就。当然,这一新型的国际制度仍然处在初期,但非常值得各国在理论和实践上加以完善。
2010年10月,在韩国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及后来的首尔峰会上,G20成员国就IMF份额改革达成协议:IMF将在2012年之前向包括新兴大国在内的、在IMF中“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2010年11月,IMF同意改革其决策框架(framework for making decisions),以反映新兴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反映当代世界经济的现实。这项改革号称是“广泛的治理改革(wideranging governance reforms)”。
尽管中国和其他G20中的新兴大国在国内存在着是否“援助欧洲”的激烈争论,但根据MAP规则,中国等拥有通过这一多边机制介入欧洲经济问题的充分国际正当性(international legitimacy)。此前,主要是欧洲深入广泛地通过多边途径(尤其是IMF和G7)介入中国等非欧洲国家的国内经济治理,而中国等则很少介入欧洲的经济治理。如果非西方大国能够通过全球治理机制介入西方的经济治理,这将改变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关系的长期失衡局面,开启我们所称的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相互治理的进程(mutual governance processes)”。
为了经济改革或解决问题(如亚洲金融危机),新兴大国长期接受和忍耐了IMF贷款的严苛条件性(conditionality)(如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等,都有与IMF打交道的痛苦经历),当它们介入解决西方金融危机的过程,按道理来说,也应要求西方做两件事:一是加速改革欧洲把持的IMF,使IMF的机构治理和决策体系更加反映世界经济的历史变化,即新兴大国的崛起;二是它们通过IMF对欧洲的援助也要附上类似的条件性。但实际上,目前IMF改革进展有限,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尚未自动转化为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力;欧洲需要IMF的介入,但并不接受新兴大国的援助条件,事实上,新兴大国也无法向欧洲强加其条件性,甚至无法提出任何有力或者有效的条件性。(16)
在这次西方金融危机期间,借助G20,一些欧洲和欧盟领导人多次批评全球金融市场(当然是出于其国内政治的权衡),要求对金融市场进行全球金融治理。尤其是,主权债务危机下的欧元区国家面对金融市场的干涉和投机困苦不堪,所以,欧洲政治领导人发誓要对金融市场进行政策和法律调控,例如制裁税收天堂(tax havens),甚至向金融交易征税。(17)
2011年,法国担任G8和G20的轮值主席,为这两大国际集团确定了几个雄心勃勃的优先目标,这些目标都是为了“对全球经济治理进行全面改革”:“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减少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强化金融监管;改革国际货币体制,改变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在G20本身的制度发展方面,法国希望G20能获得某种“决策能力”,不要成为数不清的又一个“国际清谈俱乐部”。(18)但是,由于欧债危机的继续恶化,法国政府确定的这些目标并未获得C20的充分讨论,反而欧债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巴西领导人希望欧元区国家早日结束危机,以免伤及新兴大国的经济,抱怨欧洲人行动迟缓。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指出:欧洲人往往花很长时间才找到解决方法,结果,这些解决方案每每来得太迟了。(19)
G20向欧盟施加压力,要求早日解决欧债危机的呼吁到2012年墨西哥洛斯卡沃斯(Los Cabos)峰会时就更加明显。由于久拖不决的欧债危机更加演变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欧债危机再次成为G20峰会的焦点。(20)该峰会发表的公报要求欧元区国家“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捍卫欧元区的完整和稳定,促进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并打破主权债务与银行债务之间的反馈回路”。(21)欧洲领导人在G20峰会开幕之际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们采取果断行动解决欧元区危机,这给本次峰会增添了紧张气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安杰尔·葛利亚(Angel Gurria)认为欧债危机“不再只是欧洲人的问题”。(22)
四、“新兴国家”与欧洲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制度
由于本文涉及新兴大国与现有国际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新兴大国通过IMF和G20介入欧洲地区经济治理,接下来,我们认为有必要讨论新兴大国与国际社会或者“西方自由秩序(western liberal order)”(23)之间的关系。
对于新兴大国来说,有两种方式可以走向新的全球治理:
第一,改革现存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制度,提升非西方的新兴大国及其代表或者象征的发展中世界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国际关系理论的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曾讨论过“国际社会”的扩张(大)。英国曾应用“国际社会”因应世界大变局(二战以后的新世界格局,尤其是非殖民化)。(24)这里的“国际社会”最初是以西方(欧洲)国家的规则或者制度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而国际社会的扩张就是“非欧国家(non-European)”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非欧国家被纳入国际社会是西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需要的,但是,悖论性的可能结果是,当这些非欧国家加入后,国际社会的基础和结构不再是简单的西方霸权(hegemony),甚至一旦非欧国家的力量超过西方,西方可能会失去在这样的国际社会维持霸权的初衷。所以,对于西方来说,非西方按照社会的标准参加国际社会以及这种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扩张)的后果——带来国际社会的改革或者改变,一直是一个核心而又敏感的国际政治问题。(25)
多数美国学者不使用“国际社会”的概念,但却使用类似国际社会的“西方自由秩序”来讨论上述这个核心而又敏感的问题。如同英国学派,由于事关西方或者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性(dominance),美国学者非常深入地把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崛起”及其加入西方自由秩序当做一个中心命题来加以讨论,因为这关系到西方自由秩序的存在或延续。(26)
欧债危机和“新兴大国”通过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制度介入欧债危机的解决,是否表明了国际货币秩序——“西方自由秩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进入“后欧洲”、“后霸权”或者“后美国”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在第一次“美国衰落”的争论和欧洲(法国)主导的G7兴起的背景下,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首先研究了“霸权后”的世界经济治理,即西方大国之间为稳定世界经济进行的“合作”。(27)基欧汉的“霸权后”命题在当时属于令人非议的大胆假设,因为单一强权,即美国,当时并未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衰落了,而是依然主导西方,并未形成霸权后的局面。直到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西方衰落和霸权后的局面才得以形成。G20在“后霸权”时代上升为主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这表明,仅有美欧合作是不够的,无法解决全球经济治理,而西方与非西方进行的范围更大的全球合作未必一定能够成功地管理世界经济,但至少比仅有西方大国之间的合作更有力。
第二,“另起炉灶”。在我们看来,“另起炉灶”可以有多样的情况和理由。一种情况和理由是,改革现有全球治理的先天缺陷和弊病很难,甚至不可能,所以,可以不必在改革方面下功夫,而是追求现有制度的替代物(alternatives)。例如,在英国,有人在研究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研究项目(Bretton Woods Project)”,主张建立新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如,有中国学者认为,可以建设一个新的IMF。(28)另一种情况和原因不是要建立一种如伊肯伯里所说的“非自由”和非“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29)而是因为自由秩序的西方主导性和其他进入自由秩序的非西方成员的附属性。“另起炉灶”的含义也应理解为多样的。人们一般把“另起炉灶”理解为推倒现存国际经济制度,或者建设替代现存国际经济制度的新制度的革命、激进方法。不过,在现实中,下述折中、温和的方法也许更有效:不是退出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制度,而是在现有国际经济制度之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制度。其实,如上所述,欧盟本身一直就是这样做的。问题是,欧盟作为西方的主体之一,是“西方自由秩序”中的“州官”,可以“放火”,即挑战现存秩序;如果新兴大国也另起炉灶,即使是“点灯”性质的另起炉灶,一般也会被西方理解为“挑战”现存西方主导的秩序。1997-1999年期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日本的提议下,东亚国家计划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这在西方看来明显是挑战现存西方自由秩序,即IMF代表的国际金融秩序,所以,这个提议遭到欧洲和美国的立即反对,“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不得不变相出笼(后来的东盟加中日韩的货币合作计划——《清迈倡议》)。2012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BRICS Development Bank)”的提议也被西方广泛评论为“另起炉灶”。(30)
G7扩大到G20,尽管G20包括了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不愿看到甚至不能容忍的其他政治体制(“非自由体制”),但这终究意味着西方自由秩序的扩大,至少在经济意义上是如此。(31)G20应该成为研究西方自由秩序扩大的最好案例。如果这种扩大意味着通过构造一种新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great powers)或者大国合作而塑造新的全球治理,则是颇具积极意义的。这个意义是,西方自由秩序——开放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可以演变为真正的全球自由秩序。
当然,如果G20仅是新兴大国继续利用西方自由秩序来发展自己的框架,也仅是西方在危机时代利用新兴大国的资源或者力量的方式,那么新兴大国无法以完全身份(资格)变成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制度的完全成员。在这一情景下,G20还不能称做西方自由秩序的真正扩张。
只有西方大国和非西方大国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G20才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全球自由秩序”的化身。为了塑造一种拥有普遍会员和吸引力的全球自由秩序,西方和非西方大国都需要改变、调整外交政策。西方长期以来通过诸如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制度介入非西方世界的国内经济治理,而非西方世界则由于种种因素不介入西方的国内经济治理,这就形成了一种被忽略的和没有充分讨论的世界失衡。西方应坦诚面对这样的失衡,非西方则需强调这样的失衡,最后,双方通过谈判解决这样的失衡。但问题是,新兴大国是否有原则、策略、手段介入西方的内部治理?也就是说,新兴大国是否准备好介入西方的国内治理?若G20中的新兴大国真正执行MAP,也参与评估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西方国家亦真心接受G20的非西方国家来评估其政策;如果IMF中的新兴大国提高了各自的决策地位,且能够采取协调行动,在IMF向发生金融危机的西方国家提供援助时,能够加入非西方的条件性,那么新兴大国则实际上已开始介入西方的国内经济治理。这种介入才是具有真正意义的全球经济治理的转型。
五、欧洲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未来
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终究取决于其内部治理的情况。西方金融危机说明西方陷入内部治理的危机之中。欧洲地区治理的成败决定着欧洲能否在全球治理中依然占据中心的、不可或缺的地位。欧洲的危机拖得越久,欧洲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就越小。诸如欧债危机这样的欧洲问题如若还将持续很长时间,(32)欧洲将变得更加内向,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主导地位将会动摇。
欧洲决策(政策)层等精英清楚地意识到需要推进欧洲一体化前行,一些国家如德国政府试图借助欧债危机加强欧盟的权力,欧债危机下的欧洲一体化仍“将不容置疑地前行”,“全部成员国将决心力保欧元”。(33)因为“进一步的一体化(银行联盟、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是挽救欧元和恢复经济增长的唯一可行途径”。(34)但是,欧洲一体化——真实的“民族国家的联盟”的动力也已经呈现严重不足的状况,许多欧洲人尤其是新的一代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欧洲团结和一体化,欧洲存在着分崩离析的可能性。(35)
研究全球治理的转型从欧洲入手最好,全球治理的最早提倡者和实践者陷入“治理”危机,暴露出(相对来说)“较弱的欧洲政治经济的治理”,(36)求助于自己一手创建和控制的国际经济(货币)制度,而其他力量则通过这些国际经济制度介入欧洲地区治理。这是全球治理转型最具戏剧性和历史意义的一部分。没有这样的故事或者案例,全球治理的转型也就无从谈起。
但是,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欧债危机的根本解决还要靠欧洲自身的地区治理创新,这种创新不仅是技术的和近期的(如欧洲银行联盟和财政联盟),而且是战略的和长期的(如欧洲政治联盟以及最终的欧洲联邦国家)。当然,走向新的欧盟的前景并不是乐观和顺利的。
从欧洲的角度看,无论是IMF还是G20,都是危机时期欧洲为摆脱危机可资利用的工具,而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提高,仍然是满足一定条件的和不完全的(有限的),也即新兴大国并未获得在全球治理中与西方完全平起平坐的资格。欧洲在维持其对IMF等的控制、即全球经济治理的现状上仍然是成功的,尽管与欧洲提倡的诸如征收金融交易税等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相互矛盾和冲突。但是,欧洲的保守性和开创性本来就是并存的。
我们现在所能确定的一点是:在西方金融危机下,全球治理的转型已经开始,未来的全球治理不同于现在或以前的全球治理;但是,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全球治理是否转型,而在于转型的方向、内容以及如何转型等。从IMF和G20介入欧债危机来看,全球治理转型的目标、方向(方法)、进度、后果等方面充满着不确定性。
(笔者十分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修回日期:2012-10-19]
注释:
①此种说法在欧美是惯常的。这里可引用的一个说法是葡萄牙财长维托尔·加斯帕(Vitor Gaspar)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的讲话,参见Vitor Gaspar,“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nd Globalization in Time of Crisis,”Opening Address at the PIIE-Bruegel Conference in Berlin,September 27,2011。
②Jacob Funk Kirkegaard,“Congressional Testimony:The Euro Area Crisis:Origins,Current Status,and European and US Responses”.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interstitial.cfm? ResearchID=1969.
③Loukas Tsoukalis,What Kind of Europ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93.
④复旦大学的陈志敏教授认为欧盟在内部虚弱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外交张扬”。参见陈志敏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2年8月18日。
⑤有关IMF在欧债危机中作用的系统而专门的讨论,参见德国应用科学大学“讨论论文”,Franz Seitz and Thomas Jost,“The Role of the IMF in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http://www.haw-aw.de/fileadmin/user_upload/Aktuelles/Veroeffentlichungen/WEN-Diskussionspapier/wen_diskussionspapier32.pdf。
⑥IMF副总裁朱民在2012年9月12日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天津)上指出,“欧洲的危机不仅局限在欧元区内”,这意味着IMF将长期面对欧债问题对全球经济的挑战,http://video.caixin.com/2012-09-12/100436551.html。
⑦Franz Seitz and Thomas Jost,“The Role of the IMF in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p.19.
⑧Franz Seitz and Thomas Jost,“The Role of the IMF in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p.19.
⑨Franz Seitz and Thomas Jost,“The Role of the IMF in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p.2.
⑩Carter Dougherty,“E.U.Leaders Turn to I.M.F.Amid Financial Crisis,”New York Times,February 23,2009.
(11)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IMF已经实现了一次增资,那次增资是在IMF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主持下进行的。与目前的第二次增资类似但也存在差异,类似的是,IMF日益感到掌握的资源不足以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作用,所以,从应付金融危机出发,决定增资;差异则是,第二次增资的目的显然是自私自利的,即为了欧洲自己,尽管IMF总裁指出:这笔资金与欧洲无关。“今后起草和签署的双边贷款,并不会形成一个贴着欧盟标签的专项基金或金库。它将用于IMF的所有成员国。”参见《IMF增资意义不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2年4月27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4308#utm_campaign=1D110215&utm_source=EmailNewsletter&utm_medium=referral。
(12)IMF总裁拉加德出席2012年1月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演讲时高高举起她的提包,以表她的参会是为IMF增资。
(13)“IMF Demands Swift Banking Union in Europe,”参见德国《明镜》周刊,2012年10月10日,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business/concerns-over-stability-imf-demands-swift-banking-union-in-europe-a-860510.html。
(14)《独家:IMF(与)欧盟对希腊纾困案有歧见》,路透社雅典/华盛顿2012年9月26日电,参见路透社中文网,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IntlBizNews/idCNCNE88Q01R20120927。
(15)IMF,“The G20 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 (MAP),”updated on September 26,2012,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g20map.htm.
(16)有人建议中国援助欧洲的条件之一是欧盟解除自1989年起就对中国实施的军事禁运。这样的条件性在政治和外交上是幼稚的,在金融上是缺少逻辑的,欧洲显然不会接受。
(17)金融交易税亦称“托宾税”,是指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因各国存在意见分歧,尚未统一实施。2012年5月23日,欧洲议会投票表决赞成开征金融交易税。
(18)克里斯·贾尔斯:《萨科齐:G20须有决策能力》,参见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1年1月2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742。
(19)http://en.wikipedia.org/wiki/2011_G-20_Cannes_summit.
(20)克里斯·贾尔斯等:《欧债危机将成G20焦点》,参见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2年6月19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117。
(21)参见G20墨西哥峰会公报,http://finance.sina.com.cn/focus/G20_Mexico/。
(22)克里斯·贾尔斯等:《欧债危机将成G20焦点》,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117。
(23)“liberal order”也译为“自由主义秩序”。
(24)有关这一点,参见威廉·卡拉汉:《对国际理论的民族化:英国学派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浮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49页。
(25)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eds.,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
(26)当“中国崛起”被美国学术界确认后,一直研究西方与国际制度之间关系的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的关注点变成“中国、西方和自由秩序的未来”,为此发表了多篇论著。值得指出的是,伊肯伯里认为,除了“自由秩序”,并无其他秩序,否定了“另起炉灶”的价值。如同其他西方学者,伊肯伯里也回避了关于国际规则的政治学,即谁制定规则,谁服从规则等问题。参见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Foreign Affairs,Vol.87,No.1,2008,pp.23-37; G.John Ikenberry,“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Order: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Foreign Affairs,Vol.90,No.3,2011,pp.56-68。
(27)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28)周寂沫:《争总裁不如另建一个IMF》,载《环球时报》,2011年5月28日。
(29)G.John Ikenberry,“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Order: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p.57.
(30)例如,英国有影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研究项目”发表了《一砖一瓦建造(世界银行)的替代物》(“Building Alternatives BRICS by BRICS”)的评论,http://www.brettonwoodsproject.org/art-569947。
(31)庞中英:《G20是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新版本》,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10月16日言论版。
(32)谢国忠:《欧洲陷阱》,载《新世纪》,2012年第12期,第30页。
(33)引自德国财长在一次学术会议的基调发言,Wolfgang Schauble,“The Euro Area Crisis and Future of Global Implications,”Keynote address at the PIIE-Bruegel conference in Berlin,September 27,2011。
(34)Andrew Duff MEP,“On Governing Europe,”Policy Network,September 24,2012.
(35)Timothy Garton Ash,“The Crisis of Europe:How the Union Came Together and Why It' s Falling Apart,”Foreign Affairs,Vol.91,No.5,2012,pp.2-15.
(36)Andrew Duff MEP,“On Governing Europe,”Policy Network,September 24,2012.
标签:金融风暴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欧债危机论文; 国外宏观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经济学论文; 欧盟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全球化论文; g20峰会论文; IMF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