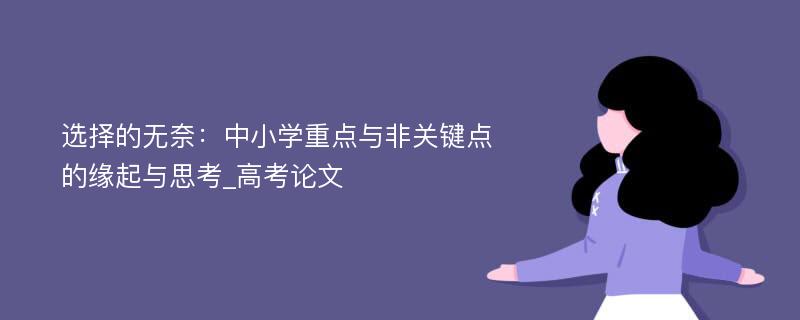
选择的无奈:——中小学重点与非重点的由来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点论文,中小学论文,由来论文,与非论文,无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年7月, 对所有参加高考的莘莘学子和他们的家长与教师们来讲都是一段暗淡无光的日子。7、8、9三天, 考生们需要经历一场人生中心灵与体能、喜悦与痛苦、希望与失望的刻骨铭心的磨难与煎熬。不幸的是,这一磨难与煎熬早已延伸到了全国数以亿计的初中生和小学生的头上。他们在进入高考冲刺之前的漫漫征程中,就面临着能否升入重点学校的巨大压力和无情淘汰。造成所有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紧张的直接原因,是普教系统20年来实施的中小学校划分重点与非重点的教育政策。背景与由来
这一政策的酝酿和确立始自1977、1978年,而其出台背景还得从“文革”中全国学校教育体制的瘫痪谈起。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空前浩劫,教育战线更是这场浩劫中的一个“重灾区”。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原有教育体制的彻底破坏;二是“两个估计”的出笼。(注:“两个估计”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革”期间在“教育革命”的口号之下,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奇特景观:在高教系统,“群众推荐,领导审批”的高招制度诞生了,一批批只有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兵学员”踏入大学校门。高教质量全线崩溃,大学办成了中学甚至小学。在“群众推荐”的幌子下,“走后门”现象迅速滋生并全面蔓延,人们在废除了高考制度从而取消了因分数高低形成的不平等后,所面对的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社会性不平等。
在普教系统,教学体制与教材被彻底“改革”,政治学习、批判会、背诵最高最新指示、参加劳动锻炼成为了学生们的主课。教师不敢教,学生不敢学,教育质量全面滑坡,交白卷、反潮流、批判“师道尊严”蔚然成风。在一片混乱的年月,“不学ABC, 照样干革命”的口号席卷了中国城乡每个角落。
仇视知识,敌视知识人才的政策使共和国由此得到的报复也是血淋淋的:据当时最乐观的估计,到1977年,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水平整整落后了20年!
对于十年动乱造成的中国教育的灾难,邓小平忧心如焚。他在第三次复出时主动提出分管科学教育工作。复出后不到一个月,邓小平排除阻力,果断决定立即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并提出了创办重点大学、重点中学、重点小学的构想。
创办重点大学、中学、小学是邓小平重整教育河山的一个重要思路。还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前两个月即1977年5月24日,他在同王震、 胡耀邦谈话时就明确指出,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走在前面;而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有知识、有人才;知识和人才的来源在于教育,因此,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邓小平强调,抓教育,必须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页)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同科技教育界人士座谈时,就教育界拨乱反正和提高教育质量问题重申,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教育部在办好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的同时,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院校。邓小平强调,高等院校学生来源于中学,中学学生来源于小学,因此必须重视中小学教育,只有中小学教育质量提高了,才能为大专院校输送优秀人才。
邓小平提出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小学、中学、大学的构想,是与他一贯倡导的领导方法紧密相连的。抓方针,抓典型,以点带面,统领全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久经摸索和总结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基本工作方法。面对十年动乱造成的教育界的烂摊子,从何着手,是令人颇费斟酌的一个棘手问题。邓小平在此后不久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等人谈话时曾这样表示:“我的抓法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71页)很显然,邓小平是把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作为教育战线迅速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抓手和重要政策来看待的。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迅速进行了研究和调查,讨论方案,拟定标准,平衡名单。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准备工作,1978年1月, 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校的试行方案的通知》。
《通知》确定了全国第一批重点中小学名单。从名单上看,第一批国家级重点中小学的确定,似乎更侧重的是地缘政治标准。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教育部命名的全国第一批重点中小学,具有示范和象征的意义。
教育部在《通知》中还提出:各省、市、自治区,可在省、地市、县三级举办重点学校。省和地市两级可各自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各地在举办重点中小学时要注意城乡兼顾;工交企业办的重点中小学,在教学内容上可以有所侧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今后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将确实办得好的中小学逐步纳入重点学校的行列。
根据教育部通知精神,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迅速开展了一个举办重点中小学的热潮。其声势和速度颇有“运动”的味道。这样,在短短的二、三年时间里,一批省级重点、地市级重点和县级重点的中小学校在各地涌现出来。仅以北京为例,先后列入市、区级重点中学的就达48所。
思考与点评
在中小学校中划分重点与非重点,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发展到今天,其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的消长也愈来愈加明显。
确立重点中小学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树立样板,将优秀生、尖子生集中起来,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带动整个基础教育质量的恢复和提高。这从邓小平在这一段时间中对于科教界的频繁谈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基础在于教育,教育界拨乱反正的首要目标是恢复教学秩序和提高教育质量。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和大学,一则可以将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为共和国培养和输送一批亟需的人才,以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才断档;二则可以在全国普教和高教系统尽快树立起一批样板和典范,以点带面,迅速推动教育界恢复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进而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可以说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有着明显的时代特点。
这一政策的收效是显著的。它首先表现在一大批优秀生、尖子生的集中脱颖而出。由于划分出了省级、地市级乃至县级重点中小学校,各地的优秀学生有了最为直接的奋斗目标与相对优越的学习环境,加之各重点学校纷纷敞开大门,广揽各普通学校的尖子生,使得优秀生、尖子生聚集于重点学校。学生们以考入重点学校为荣,重点学校以招揽尖子生为责,双向互动,压力倍增。在短短的几年间,重点中学的高考升学率就呈几何级数攀升,有的甚至达到了95%以上,从而使得高等院校很快就获得了一批批素质颇佳的生源。人们在十分欣慰的同时自然也会发现,在恢复高考20年来录取的800万大学生中, 来自于各地重点学校的生源有着惊人的比例,著名重点高校的生源更是几乎被各级重点中学所包揽。
其次,中小学校划分等级制推动了一批名牌学校的迅速崛起。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对重点中小学校实施了政策倾斜,诸如办学经费优先考虑,优秀师资力量优先调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比例极高的升学率,从而使这些学校迅速在社会上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以北京为例,原属于市重点的第四中学、第八中学、第26中(汇文中学)、第101 中学等学校早已跻身于国内一流的名牌中学行列。在重点中小学校的拉动下,全国基础教育质量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恢复并取得阶段性提高。可以说,中小学校划分重点与非重点的教育政策已达到了预期的社会效果。
然而,时移势异。这一政策所引发的负面作用也与日俱增。如果说20年前教育界对集中力量举办重点中小学是一片赞扬之声的话,那么,20年后的今天,教育界对此的批评之声则是一浪高过一浪。
教育是国家基础性、公益性的事业。它更应关注人的发展的主动性与整体性,关注人作为人的发展,而不是作为工具的培训;关注在充分开发个人潜能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并将之视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在这种意义上讲,国家的教育政策必须具备相对的恒定性与很强的未来指向。如果说,基础教育阶段划分重点与非重点学校的政策是一项非常时期实行的特殊教育政策,一种积极的却又是别无选择的选择,那么,这一本应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在其20年的持续发展中,对其承载主体——广大教师特别是上千万中小学生而言却成了被迫接受的无奈选择。其负面效应也就显得格外突出:
其一,在中小学中划分三六九等,并对重点中小学实行政策倾斜,使重点中小学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师资培训、教师住房和收入等方面都优于一般学校,造成一般与重点学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种好者更好,差者更差的马太效应,加剧了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不平等,使有限的教育资源更趋失衡。
其二,人为加剧了学生间的不平等和心态的过早分化。划分重点中小学,对考入重点校的少部分学生来讲,自然是一种压力和动力,但对于升入一般学校的更多的青少年而言,却是对他们身心健康与学习积极性的明显挫伤。一些学生中存在的“反正上的不是重点,高考没指望,就破罐破摔吧”的心理就是一种例证。学生心理感受上的这种不平等所映现的是社会公正与公平原则的错位,并将使整个社会为此而付出代价。特别是由于有限的重点中小学资源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的巨大缺口和国人长久以来望子成龙的思维定势,造成一些家长为了能让子女进入一个有优越的起点和学习环境的学校大门,不惜托门路,迁户口,交“赞助”,乃至权钱交易,甚至倾家荡产,使基础教育这块本应圣洁的园地染上了金钱的铜臭,在孩子们幼稚童真的心灵中投下了不该有的阴影。这无论如何也不是每一个善良的教育工作者与家长所愿看到的。
其三,助长了应试教育的推展。由于基础教育仅仅是对高考负责,评价教师和学校优劣的唯一标准是“升学率”,小学生们努力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升入重点初中,初中生们乃是为了升入重点高中,而高中生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考上大学;但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毕竟是少数,为了5%的人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0 %的学生从小学就开始跟着高考指挥棒转,90%的学生过早地被淘汰或被抛入候补淘汰的队伍。这样的基础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教育、专门教育,它制约了孩子们创造性思维的发育,破坏了基础教育的规律,也扭曲了义务教育的性质。
不错,中国的发展需要数以万计的高科技人才和高层次的文化精英,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讲,更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基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在于选拔精英,而在于培养每个人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基础教育面临挑战,中国的基础教育观念必须改革。当前各地启动的升学考试改革作为一种试点,令疲于应付的教师、学生和家长似乎看到了一线光明。但愿这种改革能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一个全民参与特别是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参与的讨论与论证过程,而不仅仅是主管部门或领导人的一时之想或激情飞跃。否则,这种改革势必简单化、绝对化,成为短视而乏力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