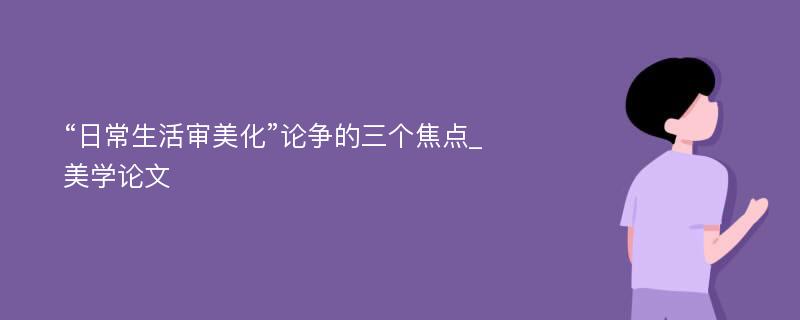
“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的三大焦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日常生活论文,焦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7)02-0048-06
“日常生活审美化”(以下简称“日”)以及由它衍生的文艺学科边界问题的论争,无疑是这近三年来文艺学、美学界最受瞩目的话题,《文艺报》、《文艺研究》、《文艺争鸣》、《文学评论》、《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众多权威报刊都为之辟出专栏,《文汇读书周报》甚至将之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这场引发了广泛关注的论争,尽管商榷质疑之声尖锐直截,你来我往颇有几分针尖对麦芒的激烈,但所幸参与论争的各位学者均能保持良好的修养和气度,使得对学理本身的探讨能够深入下去。时下,这场论争虽已过高潮,但仍未落幕,笔者以为,实有必要在这个冷静但尚未冷却的当口,即认识日趋理性而激情尚未退却的时候,对论争本身进行一番客观的回顾,并对论争的焦点问题进行总结梳理,以图发掘出论争本身的意义及其背后的问题。纵观这场论争,交锋主要来自对语境条件、主体身份以及对象性质的不同理解,而论争焦点也由此形成。
一、语境条件:“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不是当下中国的本土命题?
“日”最早见于陶东风的文章《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1] 根据陶东风的解释,“日”意指审美活动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具体表现在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诗歌、绘画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如广告、流行歌曲乃至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等。而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陶东风在提出“日”这一命题之后,随即摆出该命题的西方资源,如维尔什、博德里亚、费塞斯通等人的观点,以加强印证对这一命题关注的合法性和急迫性。
然而,恰恰是这一对西方资源的引征,诱发了许多学者的征讨,纷纷对这一命题语境条件的本土真实性和正当性表示怀疑,认为该命题作为“美学用语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当下语境中实质上是个“伪命题”,至多不过是个“局部命题”。赵勇饱含激情地表达了这种质疑:“这是一个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话题吗?好像不是,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这一命题出自西方理论家之手。……依我的判断,西方学者提出这一命题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了一个后现代社会,他们的这种判断实际上是要为当下的社会形态找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但是中国进入到一个后现代社会了吗?相信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作出否定的回答。……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关注‘日常生活的贫困化’而不是什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2] 朱国华也表示:“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未能摆脱生活的必然性困扰、还在向着小康社会迈进的时候,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课题虽然很有吸引力,但还不是一个普遍性命题。”[3]
可以说,赵勇和朱国华的这种担忧代表了许多“左翼”思想者的心声:在一个不仅理论资源需要进口,就连问题意识都依赖进口的年代,鉴于“唯西方”情结的扭曲和“伪命题”的泛滥,学术界应该警钟长鸣。因为这种忽视语境条件,将特殊阶层的话语在学术研究的合法名义下偷换为普遍性话语的做法,不仅有可能使自己的话语阵地为西方话语的跑马场,而且会有可能使研究者自身成为特殊阶层的共谋者。
总的说来,持“非本土论”的诸位先生具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是对“无远弗届”的西方理论保持着高度警惕,更对“盲目崇洋”的当下学风极为反感。王元骧曾在《文艺理论的现状与未来之我见》一文中忧心忡忡地写到:“关于当前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现状,总的印象,笔者很同意有些学者以‘跟风赶潮’、‘追新逐异’八个字来概括……西方一百多年来出现的各种文学观念,现代的、后现代的几乎都在我国当今文学理论界找到回应,以致有人把当今我国文艺理论界比作西方文艺理论的‘集散地’。像前几年流行的‘纯文学’,近年来又被人炒得火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等,何尝都不是一种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文学观念?”[4] 二是对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着敏感的认识,对草根阶层、劳苦大众怀有深厚的感情,对食利的权贵阶层持激烈批判态度。童庆炳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一文中对普罗大众的眷眷之情溢于言表:“今天的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绝不是中国今日多数人的幸福和快乐。他们提出的新的美学也不过部分城里人的美学,绝非人民大众的美学,或者用我的老师在上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的话来说,这不过是‘食利者的美学’。”[5]
为此,陶东风曾专门撰文《也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作为对童庆炳的回应,他着重指出:“我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发生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一种消费文化现象,而不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现实。(笔者按:这似乎与他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一文所提出的大众文化中心转移的论调有些出入)……我并不认为一个目前在数量上没有优势的事物就不值得去研究。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消费文化虽然是集中在中国城市的现象,但是正如在经济上城市对于乡村具有辐射力一样,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也是这样。我不能否定中国许多农村地区还较穷或很穷,但是由于电视这个最重要的大众传播手段的极大普及,城市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强有力地影响到农村。追求名牌、追求夸饰性消费的心理在农村同样十分普遍。因此我并不认为研究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更何况学术研究可以也应该具有超前性。”[6]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学者也对“日”的现实基础进行了积极的辩护。杨春时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审美批判理论是外国资源,因此不能成为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基础。这种观点之不妥当在于,审美批判是针对现代生存而发,而现代生存方式具有普世性,不独西方为然。中国目前已经开始确立现代性,现代社会的弊病已经显露,虽然没有发展到西方那样的程度,但性质是一样的。因此,开展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是有现实基础的。”[7] 朱志荣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话题近年开始在国内流行,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其中既有西方后现代理论影响的原因,又有着当前日常社会生活发展的现实背景因素。”[8]
“本土论”的诸位先生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之所以总是能风靡全球,并让中国等第三世界社会蜂拥跟随,是因为西方文化现象的背后总有强大的政治经济作其后盾。只要我们在政治经济上承认西方强势渗透的事实,那么在文化上步其后尘的处境也就不可避免。因此,“日”可判定为一个源自西方,但却具有或即将具有或迟早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命题。也就是说,“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客观存在,其不仅是当下中国的既成事实,而且将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主体身份: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应如何?
如果我们承认“日”的确是当下社会的一个日渐壮大、不容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对于这个现象,研究主体应该持有怎样的价值取向和言说立场,即研究者的身份问题便亟待揭开面纱。
总的来说,对“日”进行研究的学者,其身份可分为三类:批判者、阐释者和辩护者。不难发现,其中“批判者”的人数最为众多,否定质疑的声音也明显占了上风。以下信手拈出的观点尽为征讨发难之词:鲁枢元对“日”这一现象的定性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是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9] 赵勇的定性则是:“对现实的粉饰和装饰。”[10] 耿波慨然直言:“‘日’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代学术在当代文化生产中日渐显露出来的庸俗的一面:食利性。”[11] 姜文振更是沉痛呼吁:“我们需要的决不只是给‘审美化’的消费文化锦上添花、涂脂抹粉,更需要为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为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雪中送炭,更需要在工具理性、金钱力量独霸的消费文化日趋扩张之时保持澄明的人文理性与批判精神。”[12]
统而言之,“批判者”的主要理论资源是西方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他们继承了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一贯的精神血统,以“人文精神”守望者的身份为社会立法,对社会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对消费主义文化的种种流弊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人文精神的失落有着深深的焦虑。
“阐释者”是赵勇对陶东风的一个基本定位,也是当下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欣然扮演的一种角色。对此,尽管陶东风表示并不同意,但在我看来,这一定位大致可以成立。“阐释者”是相对于“立法者”而言的一个概念,指只涉及事实陈述,不作价值判断的一种研究身份。虽然陶东风多此撰文申明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声称“我的立场绝对不是站在那些中产阶级、白领或新贵阶层一边,而是站在真正的‘大众’与弱势群体一边的。”[13]。然而他在《也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中的一句辩词,却无意中泄露了身份,他写到:“批判性地反思一个对象——比如消费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提是对它的学理性的研究”。[6] 这句话表明陶东风的研究逻辑是:先阐释再批判,阐释是批判的前提。换言之,事实陈述是价值判断的先决条件,在研究中起到第一性的作用,言下之意:一个研究者首先必须是个阐释者,而后才有可能成为别的什么者。而对于真正具有鲜明价值立场的“立法者”来说,他们的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合二为一、血肉交融、没有前后之分的。
再者,依据陶东风一贯的行文风格和整体上的立论来看,尽管他的文章中有对消费主义忧虑和批评的文字,但这种文字常常是惊鸿一瞥、蜻蜓点水,而并没有构成他思考的重心和行文的重点,更多的还是对文化现实不动声色的描述。而这貌似客观谨慎的、价值判断缺席的、言说立场沉默的研究,很容易导致他人得出其“价值立场的暧昧”的结论。鲁枢元曾质疑过这种模糊不清的价值趋向。耿波更是预言了这种“阐释者”向“辩护者”的嬗变:“如果‘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不向前走一步,走出勇敢的批判的一步,那么这样一种仅仅满足于描述的理论,最终会变成资本生产商的‘超级广告’。”[11]
事实上,陶东风更倾向于被看作为“日”辩护者。尽管陶东风曾郑重声称: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事实陈述而不是价值判断,并不包含有为之辩护的立场”,[6] 但他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声援之词还是隐约可见的,在《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一文表现得则尤为突出。但与王德胜比起来,这种辩护的势头则有点“小巫见大巫”了。客观地说,将陶东风全然归入“辩护者”行列,的确有些冤枉。当然,这其中的委屈,陶东风本人的体会最为深切:“现在许多批评文章(包括赵勇的文章在内)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在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这个抽象的称呼下,把所有的作者‘一网打尽’,而没有进行必要的梳理,没有看到这些作者及其文章在具体观点上存在的差异乃至分歧。”[13] 明眼人不难察觉,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论者”阵营内部,陶东风最想区隔开来的人就是王德胜。
王德胜真可算作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辩护者”中最无畏、最典型的代表。他在《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一文中认为:“日”这样一种美学现实,极为突出地表现在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视觉性表达和享乐满足上,而视像的消费与生产在使精神的美学平面化的同时,也肯定了一种新的美学话语,即非超越的、消费性的日常生活活动的美学合法性,并将此看作一种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14] “新的美学原则”一提出,就引来了文论界、美学界不少的发难乃至“征讨”,对此,王德胜表示是“毫无预料的”,但更让人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竟不惜冒着成为“众矢之的”的危险,继续义无反顾地拥护倡导这种“新的美学原则”。在接下来的商榷文章《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教授》中,王德胜则将“日”公然看作“世俗大众的生活梦想”,并从大众感性生存的权利和人的感性欲望的伦理正当性出发,重申了他的辩护立场:“美学之为美学,恰恰在于它把感性问题放在自身的审视范围之中,突出了人在感性存在和感性满足方面的基本‘人权’,而不是重新捡拾理性的规则。对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的理解,同样也应该从这样一种美学本来的出发点去进行。”[15]
总的说来,“日”的辩护者主要借用的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市民理论,否认社会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和绝对性,回避探究现象背后外在的操纵力量,他们以“人在感性存在和感性满足方面的基本人权”的名义,欢呼这样一种后文学时代的来临。
三、对象性质:“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美的泛化,还是美的异化?
在对“日”这一美学现象的讨论中,最激烈的交锋还是源自对于对象性质即美本质的不同认识。一方观点认为“日”是美的泛化,而另一方则认为“日”不过是冠以“美”的名义的美的异化。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态度与对美学学科的不同认识有关。自美学学科诞生之后,美学观就可分为“人生论”和“艺术论”两派。“人生论”派持广义美学观,认为美的范围就是人生的范围,美学研究人的审美活动与人生意义的关联,将自然美、道德美、生活美、艺术美等都纳入其研究对象,主张艺术的美和生活中的美是相通的,不存在严格界限,其代表人物有鲍姆嘉通、康德、海德格尔等;而“艺术论”派则持狭义美学观,主张美的范围仅限于较为狭义的艺术(指文学、绘画、音乐等经典艺术门类),美学仅仅研究艺术的一般规律,并将日常生活与艺术活动刻意区分开来,其代表人物有黑格尔、霍迦兹等。
陶东风是典型的泛化论者,他是以“艺术论”的狭义美学观作为其理论建构的背景,从而提出“日”这一概念的,他甚至明白无误地将“日”和审美的泛化等同起来。金元浦也将“日”视为一种“文学性向非文学领域全面扩张”的泛化现象。[16] 在泛化论者看来,所谓“日”,就是审美由艺术领域向日常领域渗透扩张,从而使得艺术活动与日常活动鸿沟消弭的一种文化现象。
而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现代美学“人生论”观点出发,所谓美的泛化则无从谈起,因为“美”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人生当中,从不曾“狭化”,又何来泛化。童庆炳指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现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古时候,中国的仕宦之家,衣美裘,吃美食,盖房子要有后花园,工作之余琴、棋、书、画不离手……”[5] 朱志荣也同样表达了自己的疑虑:“从审美意识的发展历史看,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化问题,不只是今天的话题。起码早在新石器时代,在陶器遍地的时候,日常生活中就已经自发地出现了审美问题。”[8]
其实,对于像童庆炳这样持广义美学观的学者来说,“日”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话题,原因不在于其泛化,而在于其异化。综合诸学者的观点,美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真正的美是感官愉悦和精神愉悦的统一,强调神圣的精神性;而“日”却停留在单纯的感官快适,它一味刺激人的生理本能,却把精神追求搁置一边。童庆炳对此进行了犀利的讽刺:“什么审美无功利,这种带有精神超越的美学,统统过了时;审美就是欲望的满足,就是感官的享乐,就是高潮的激动,就是眼球的美学。”[5] 第二,真正的美是理性与感性的和谐,它不仅使理性本身感性化,体现出合乎个体人性要求的力量,而且还使感性本身理性化,超越自身个体局限,表现出符合社会普遍性的“类”的要求;而“日”却是感性对理性压倒性的入侵。杨春时指出:“在日常生活领域,主要是感性异化,后现代社会的感性异化更为严重,甚至取代理性异化成为异化的主要形式。”[7] 第三,真正的美无利害关系,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日”却是意识形态的功利性工具,“食利性”非常明显。耿波指出:在“日”的背后“我们可以辨认出真正操纵着这个物质社会的主人:资本家、商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以及种种的文化掮客。”[11] 第四,真正的美是终极关怀的诗意家园,对现实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而“日”却是对世俗的献媚和妥协,缺乏否定精神和彼岸精神。刘凯指出:当代所谓的“审美”“不是体现为对自我的不断提升,而是表现为对真正的现实的躲避和逃离”,它丧失了康德所赋予的“审美”的“先验性、超越性的内涵,失去了内在的精神”。[17] 总而言之,在异化论者看来,“日”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变种,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是非审美甚至反审美的。
在相互对比中,泛化论和异化论的交锋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其一,从词语的情感色彩来看:在陶东风这里,“审美”指的是“‘感性化’、‘虚拟化’、‘符号化’,它至多是一个中性的描述性术语”。[6] 而“泛化”一词并不具有褒贬之义,只是一个具有强大现实性的事实陈述;而在异化论者那里,“异化”一词的十足贬义自不待言,而“美”和“审美”则拥有无与伦比的绝对价值和毫无瑕疵的最高荣誉,如王元骧就把美“比作是人的‘精神家园’,看作人们精神的栖息之地,灵魂的皈依之所。”
其二,从理论和现象的关系来看:泛化论者更倾向于经验主义,其逻辑思维是外视的、归纳性的,他们奉行的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的原则,主张一切理论均要经由事实的检验,以适应现象。陶东风曾多次指出:“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18] 而异化论者则更倾向于先验主义,其逻辑思维是内视的、演绎性的,他们遵守的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的原则,更强调让人的心灵驾驭客观事实,因此应依据理论来批判、规范现象。王元骧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批判立场:“凡是理论总是带有某种反思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品格,它与现实总是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这样它对现实才会起到引导、规范和建构的作用,否则岂不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拍马屁的理论’。”
其三,从文艺有无本质来看:泛化论者否认文艺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认为“中国文艺学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文艺学在解释90年代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时依然显得十分无力”的主要原因,主张“文学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的概念。”为了反驳这种观点,捍卫文艺的本性,王元骧曾专门撰文阐发他对艺术和美的本性的理解:“对事物性质是我们考察问题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前提,没有这个依据和前提,就会陷入相对主义,我们的思想就会一片混乱。……我觉得艺术的本性是审美。”[19] 朱志荣也指出:“日常生活在随着时间的长河向前奔腾、不断更新,而审美的本质却是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8] 在异化论者看来,文艺的本性就是美,而美就是文艺的底线,而“日”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对美的逃离和背叛。
围绕以上三大焦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显示了学者之间不同观点立场的激烈对撞。应该说,论争作为人类认识史、学术史上的一种基本现象,是真理发展的必经之路。而论争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理解总是相对的和局限的。因此,论争的目的其实并不在于得到一个简单的孰是孰非、孰高孰低的判定(事实上这也往往不可能),而在于它能够让参与论争的人看到“硬币的另一面”,扬弃那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真理在握的独断论倾向,促使自身更为谨慎、更为开放地思考问题;同时也让旁观论争的人在领略过交战的“热闹”之后,能够驻足思考并有所创获。笔者相信,尽管学术界目前在对“日”的语境条件、主体身份以及对象性质的认识上,并没有达成全然一致的共识,但这场的论争,终究会像文学史上其它有意义的论争一样,深化我们对文艺和美的认识,在文艺理论研究史上留下自己或许短暂但却不可磨灭的痕迹。
标签:美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化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陶东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