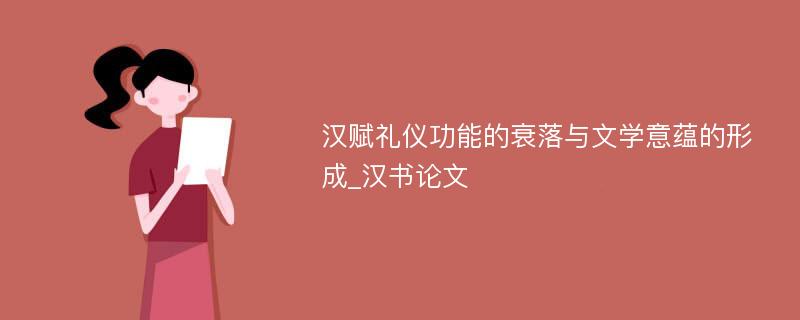
汉赋礼仪功能的式微与文学意蕴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赋论文,意蕴论文,礼仪论文,功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2)01-0142-07
从文体性质上来说,汉赋与《诗经》及汉代歌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先秦两汉,“赋”与《诗经》、歌诗的关系,绝非单纯局限在文体的渊源与发展上面。如果将赋与《诗经》的关系放在先秦,将赋与歌诗的关系放在汉初,结合当时具体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考察它们之间的种种关系,就会发现,赋在先秦作为造诗、用诗之法,承载着更多的社会礼仪、政治与文化功能,而非简单的由“六诗”之一到文体转化(文学体现)。在汉初,作为一代文体的汉赋,承担着一定的礼仪职能,但随着西汉赋家社会地位的降低与汉赋本身的政治化、社会化与文学化,汉赋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性质才逐渐确立下来,文学意蕴逐渐增强。
一、从诗、赋、歌之关系看汉赋礼仪功能的式微
据笔者观察,先秦典籍记载中的“赋诗”、“答赋”,体现了浓厚的礼仪功能。以《左传》、《国语》为例,赋诗、答赋皆有者,根据双方身份、地位的差异,引《诗》所用《风》、《雅》、《颂》的内容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其中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是答赋者以为赋者之赋与自己身份不符,故不答。二是答赋者认为赋者之赋不合礼仪,故不答。三是答赋者以具体的行动或其他礼仪形式作答。四是不知礼,故不答赋。
但是,先秦之“赋”的礼仪功能,对汉代赋作之“赋”的礼仪性质是否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有人认为,从春秋赋诗开始,“赋”这一观念已经进入文学领域[1]。认为,这恐怕与“赋”在春秋时期的政治与社会性质不尽相符。当时的“赋”,是实现《诗》的社会外交礼仪的一种手段,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是实现社会实践价值的载体。它有自己特定的礼仪规定,不知其礼制,则有逾礼之嫌。因此,班固称“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即指赋《诗》、答赋的社会礼仪而言;又称“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是就赋的礼仪规定而言。只有熟悉“赋”的礼仪程序,才能出使问对,不失礼制。赋在春秋是诸侯卿大夫必知的社交礼节,具有“观志”、“观兴衰”的社会与政治功能,这样我们就能更加理解班固所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2]1755-1756因此,“赋诗言志”不仅是士大夫的一项基本礼仪技能,而且熟悉“赋《诗》言志”的礼仪内容也是成为士大夫的基本条件。
《左传》所记之“赋”,与汉赋有着某种内在的文体关联。尤其是汉代通行的问答赋体,与《左传》赋《诗》、答赋的形式极为相似。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杜预注:“《蓼萧》,《诗·小雅》,义取‘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乐与华定燕语也。”主人为赋,客人不答,即为失礼。这种赋、答固定模式,是否是汉代主客赋的体式来源?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先秦时期的赋《诗》、答赋之“赋”,具有内在的礼仪规定,如赋诗者与答赋者赋《诗》、答《诗》内容的一致性,就大致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入汉以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汉赋,是否也具有这种礼仪功能呢?据笔者观察,西汉初期的乐府歌诗更多适应了社会礼仪的需要,汉赋则承担了政治、文化的功能。“歌诗”的流行,使汉赋在政治文化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诗与赋的关系,《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有所呈现。从其著录的题目看,“诗赋略”之“诗”,非《诗经》之“诗”。而为“歌诗”或四言诗。笔者曾经考察过这个问题,认为汉初四言诗与赋并未完全分途,直到汉成帝时期,诗、赋分途才基本完成[3]。《汉志》虽称“诗赋略”,然并无四言诗著录,且“赋”在“诗”前。笔者认为,当时并非没有四言诗,而是四言诗未成气候,诗赋分途尚未完成之故①。
但是,为何“赋”列“诗”前呢?章学诚质疑:“赋者古诗之流,刘勰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者是也。义当列诗于前,而叙赋于后,乃得文章承变之次第。刘、班顾以赋居诗前,则标略之称诗赋,岂非颠倒与?”《文选》所列,亦是赋在诗前,且其后还有骚。《文选》“赋在诗前”这种体例,盖源于《汉志》。故章学诚道:“每怪萧梁《文选》,赋冠诗前,绝无义理,而后人竞效法之,为不可解。今志刘、班著录,已启之矣。”[4]但奇怪的是,《文心雕龙》的体例,却是诗在赋前,其次序依次为:《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骚、诗、乐府、赋,具有清晰的文体进展轨迹。从这里看来,刘勰较《文选》编者具有更加清晰的文体意识。这说明齐梁时期,已经有人开始将汉代以来赋在诗前的体例进行修正。赋在诗前体例不当的认识,最早应该出现在这个时期。
问题是《汉志》、《文选》列赋于诗前,在当时真的属于体例不当吗?笔者注意到,《文心雕龙》与《文选》共同列有“乐府”,虽然二者所列“乐府”与赋、诗的位置有所不同,但这个时期“乐府”开始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出现在文学史上,则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对于骚的安排,《文心雕龙》将其列于诗、乐府、赋之前,而《文选》将之列于赋、诗之后,起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个时期的人,对这些文体产生时代的认识有所差异。第二,对其社会功能的价值判断有所差异。
《汉志·诗赋略》无诗、乐府名目,前者属于诗赋分途的问题,后者大概主要与乐府产生的时间有关。虽然我们可以证明汉武帝时期已经设立乐府,但这不能成为乐府在当时即为独立文体的标志。这个时期的乐府,很可能与《左传》中的“赋”一样,更多承担了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综合功能,而与文学相距甚远。这样,赋就退居其次,不再像先秦那样承担社会的礼仪功能了。这说明先秦赋《诗》活动演变到汉代之后,“赋”本身礼仪功能正在逐渐消退,而乐府采集的歌诗代替了先秦赋《诗》活动,逐渐成为汉代社会政治中礼仪活动的主体。
《汉志》赋后,为“歌诗”,这些歌诗皆为乐府机构采集而来。班固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5]这些“歌诗”,主要与祭祀有关。《史记·乐记》: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儛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6]1177
《三侯之章》即《大风歌》。高祖之后,这些歌诗被“四时歌儛宗庙”,显然歌诗具有了祭祀祖先的功能。汉之惠、文、景三世,“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即指在乐府训练旧的歌诗。这说明先秦曾经被乐工演习的赋《诗》,已经被楚歌取代了。
《汉书·礼乐志》对此也有记载,并且包含了更多的信息:
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2]1045
由此可知以下几点:一是汉高祖“作《风起》之诗”、“习而歌”等,与燕享有关。二是汉惠帝“令歌儿习吹以相和”的地点,在“原庙”,具有祭祀祖先的意思。三是文、景之时,研习高祖歌诗。四是汉武帝立乐府,主要意图是为了“定郊祀之礼”的需要,这说明以往应用于沛县四时之祭的歌诗,现在开始被应用于郊祀之礼。这说明歌诗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逐渐提高。乐府的成立,一方面有为了扩大歌诗内容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证明礼仪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如随着汉代歌诗的不断增加,及其与礼仪制度结合程度的不断加深,歌诗的规模不断扩大,制度也不断完善。《史记》记载: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6]1178
歌诗乐工人数的增加,四时歌诗内容的固定,都说明了歌诗与汉代社会礼仪制度的不断融合。
二、汉赋礼仪功能的程式化遗存——“诵读”
汉代“歌诗”,往往与赋并称,称为“诗赋”。西汉时期,多依此例。如《汉书·礼乐志》“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艺文志》之“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刘歆传》称其“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薛方传》称其“著诗赋数十篇”等等,此处“诗赋”皆指诗与赋。之所以如此称呼,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先秦赋还有诵、作的意思,故称“赋诗”容易产生概念歧义;第二,诗与赋具有相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皆可“诵”。《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2]1045诗可以歌,而赋亦“合八音之调”。这种“合八音之调”的赋,大概与先秦乐工演奏的赋是一脉相承的。既然《汉志·诗赋略》引“传”称赋“不歌而诵”②,那“颂(诵)”应符合一定的音乐节奏,有时候甚至不能排除有乐器、乐工的配合③。《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孙希旦《集解》:“诵,谓诵《诗》也。”此说未必得其实,因为先秦诵读的书目,不仅限于《诗》。郑玄注:“诵,谓歌乐也。”齐召南《礼记注疏考证》:“诵,谓乐歌,即大师职教六诗,以六德为之本也。”[7]这种说法证明“诵”与“歌”、“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由此推测,汉赋在政治生活中,也具有一定的礼仪需要。对这一点,皇甫谧《三都赋序》也有所认识:
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8]641
“节之以礼”,透露了汉初赋作的礼仪本质。另外,“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说明皇甫谧认为赋与《诗经》具有内在的文体演进关系。赋可“颂(诵)”的事实说明,它不仅继承了“风雅”的礼仪功能,而且还保留着“颂”诗的某些音乐特质。
“诵”与文学、文化活动的进一步结合,就是在教育领域出现了“诵读”。据“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推测,先秦时期,熟悉“赋”诗的礼仪规定,是成为士大夫的一种要求。并且,先秦已经出现了以“诵”为“学”的意思。如《韩非子》记载:“温人之周”,其自言“臣少也诵《诗》”[9]。“诵”在这里除了传统“诵读”的含义,还有“学习”的意思。而在《韩非子·难言》“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中,“诵”则成了一种学习手段。就此而言,“诵读”有可能是汉赋礼仪功能得以程式化的重要手段。
汉初“诵读诗赋”恐怕是少数人的特权。汉武帝时期有“采诗夜诵”,“夜诵”者乃“夜诵员”所为。《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称:“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2]1045既然如此,平常士人对“夜诵”的技巧与内容恐怕并不熟悉。汉哀帝时期,罢“夜诵员”④,“诵读”大致在此时进入平常仕宦之家。《汉书》、《后汉书》等对此均有记载。前者如卷九八《元后传》的“上召见(刘)歆,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后者如卷四十《班固传》的“(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等等。由此怀疑,当时所有的学者或者并非都能擅长“诵读诗赋”,而能够“诵读诗赋”的人,往往被认为是“通才”、“异才”。这是因为以往“诵读”技巧只被“夜诵员”所掌握,且“言辞密不可宣露”等原因,汉代别说“诵读”诗赋,就是理解文辞,也是有难度的。以汉武帝时所作十九章《郊祀歌》,文辞古奥,即使通经之人也不易理解: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6]1177
这些通五经之人共同研读才能理解的歌诗,即《汉书》卷二二《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的“十九章之歌”⑤。换言之,所谓“今上……作”,实际上,乃武帝使“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汉初歌诗在诵读和解释上,肯定存在很多疑难,不得不需要通五经之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完全明白歌诗文辞的意思。五经的复兴,或者也有政治因素的作用。
歌诗如此,汉赋恐怕也不例外。“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对歌诗之“辞”的诵读与解释,恐怕属于“赋”的范畴。笔者推断,汉代之赋与歌诗,皆有一定的诵读技巧。首先,诵读者要掌握一定的音乐知识。“不歌而诵”显然与音节有关,“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虽然主要针对“歌诗”而言,但赋亦应合于律吕;刘琰侍婢“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也说明诵读者熟悉声乐,更易学习诵读。
其次,“诵读”是在其他人的辅导下进行的。“诵读”有一定规律,需要专门学习才能掌握②。桓谭《新论》:“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10]《蜀志》:“刘琰为车骑将军……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11]结合二书之“教”,可知“教”当解为“教授”,非“使”意。
再次,“诵读”、“诵赋”主要是“诵其辞”。刘向、歆父子等人教读诵《左传》,刘琰教诵读《鲁灵光殿赋》,显然是主要诵读其辞。《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称:“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既然如此,在“诵读”这个环节上,“赋”更大程度具有了与“诗”相同的文学特征。“诗赋”并称,可以说自有其道理。结合“不歌而诵谓之赋”而言,“歌而不诵”即为“咏其声”,此已为“歌”的文学特征了。《诗赋略》中先赋后歌诗,是根据二者与乐声关系的远近而言的。
在先秦,各国语言有所差异。《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12]这证明齐、楚语言不通。《史记·秦本纪》:“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6]192这证明秦、晋语言相通,且晋言在戎有所保存。在这种情况下,“诵其言”在特定地域内是可以的,在语言不同的地区,语言障碍必然限制了“诗”的快速传播。但是,音乐就不受语言的限制,“咏其声”就承担了传播“诗”的更大作用。“诗”是如此,“赋”也具有相同的命运。所以,汉人诵赋必须要有专人教授,才可以掌握。这主要还是因为各地语言不同,导致了文字读法出现了差异。赋在汉代应该是比较难懂、比较难写的一种体裁。司马相如必须“与诸生游士居数岁”,才可以“著子虚之赋”;桓谭学赋,扬雄告之以“能读千赋则善赋”,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赋与歌诗相比,或者有近似于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关系。刘向、刘歆父子《诗赋略》先赋后诗,是否有这样的考虑呢?
关于“诵读”,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先秦两汉“诵读”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先秦时期,“诵读”主要是学习文化知识的活动,如《国语·楚语》记载,左史倚相曾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闻”是学习(口耳相传)的过程。“一二之言”是学习的对象。“诵志”包括诵读与记忆,是主动的接受过程。“训导”则是转化、吸收以利于传播的目的。在这些过程中,“诵志”是“言”进一步“行”的重要环节。其他如《墨子》云:“周公旦朝读百篇”,《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喜《易》,读之韦编三绝”,皆是。
自秦至西汉末,“诵读”一直如此。如《史记·留侯世家》:“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6]2035刘向、刘歆父子诵读《左传》,这里的“诵读”,仍然继承了先秦学习文化知识的含义,但随着此间诗赋的兴起,除了以往的学习功能,“诵读”逐渐成为学习“诗赋”的基本活动。如《汉书·王褒传》:“宣帝时……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2]2829《刘歆传》也称“上召见歆诵读诗赋”。
东汉以后,“诵读”的对象又逐渐由“诗赋”转向“经书”。《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称逵“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卷七九《周防传》载:“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卷八三《高凤传》云:“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后来,“诵读”还成为学习史书、诸子、佛教或道教典籍的活动。例如《蔡邕别传》云:“邕与李则游学,时在弱冠,始共读《左氏传》,性通敏兼人,举一反三。”[13]《魏书》:称董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14]《放光经记》:“晋梵音训畅,义难通诸,开士大学,文生书写,供养讽诵读者,愿留三思恕其不逮也。”[15]《云笈七签》卷四十六《大帝开结经法第五》有“凡道士修受上法,欲有所看省,诵读经文”[16]之说。由此推测,不同时代的“诵读”对象,都在本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诗赋”在西汉既然成为“诵读”对象,它们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价值,就不言自明了。
总之,汉代诗、赋与作为采诗机构的乐府都有一定联系,且二者皆与音乐有关。但后世所称的乐府,在汉初还是一种采诗机构,四言诗还是赋的附庸。很显然,诗赋在汉初承担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
三、汉赋“创制”方式的转换及其文学意蕴形成
对于汉赋来说,“诵读”未必不是一种礼仪规定。我们将这种仪式,作为先秦时期赋《诗》礼仪的遗存,或者有其道理。但是,这种“礼仪”已经不再具有政治或宗教意义的神秘色彩,开始具有更多的文学意蕴。对于制作、传播过程而言,汉赋自有其内在的生产、输出程序。对于汉代社会来说,这种程序或者也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而这一切文学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汉赋礼仪功能的丧失及其政治化、社会化与文学化的进一步加深。这一切都与汉代赋家的“俳优”、“弄臣”的社会地位有关。
汉人创制赋作,很多时候并非将它视作抒发个人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而是将其作为实现个人政治抱负、表达个人政治观点与社会态度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他们获取政治权益的一种手段。其结果必然造成赋家赋作的功利化与世俗化。赋在汉初尚存的一点礼仪职能,也就随之丧失殆尽了。
汉代帝王的好赋之风,对汉赋的发展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代文人擅赋者,多以此作为个人仕进的主要途径,如司马相如是因为“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枚皋是因为“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扬雄是因为“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畴、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等等。“以赋仕进”,是这些人的共同特点。
这些人将奏赋作为仕进的重要手段,这无疑会大大地提高汉赋的政治意蕴。当时的文人作赋,可能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汉赋的文学色彩,而过于重视其政治意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之赋,多数为侍御王侯或跟从帝王巡狩的应制之作,就说明了这一点。又如枚乘《七发》,实为阐述其个人政治思想而作;枚皋则被“诏使赋平乐馆”,且“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司马相如《游猎赋》乃“推天子诸侯之苑囿”之作,而《大人赋》使汉武帝“飘飘有凌云之气”。至于扬雄,其前期之作如《反离骚》,还有个人情感的抒发,但后来赋作,应制成分大大增加,如《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皆为从帝王巡狩而作。不过,据《汉书·扬雄传》所载,雄奏赋的目的虽为“讽(风)”,但他又认为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赋者一方面有劝谏之心,但还有深刻的政治顾虑。他们真实的想法,往往被“丽靡之辞”掩盖了。《史记》司马相如本传称相如“多虚辞滥说”,《汉书·司马相如传》说:“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其实都是有道理的。“览者已过”,说明文辞的淫丽,往往使其劝谏的意味大打折扣。《汉书》称:“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2]3775其实并不是真的“赋劝而不止”,实际上还是赋家过多的政治考虑造成的。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枚乘等人的赋作,已经具有这种倾向。刘勰称枚乘之赋“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杂文》),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可见,“文辞淫丽”,是汉赋的主要特征。皇甫士安《三都赋序》称:“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8]641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敷弘体理”、“辞必尽丽”,后人是将其视作汉赋的文学特征加以概括的,而在当时,应该主要体现了汉赋的政治需要。
汉赋的被政治化,在汉武帝、汉成帝时期最为严重。汉初赋家,自有其人格的独立性与文学的自主性。如《史记》记载屈原、贾谊等人作赋称“为”、“作”:屈原“乃作怀沙之赋”⑦,贾谊“为赋以吊屈原”、“为赋以自广”。即使司马相如、扬雄,前后也有不同。二人入仕之前,作赋也称为“作”、“著”:司马相如“著《子虚之赋》”,扬雄“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这里的“为”、“作”、“著”等词,体现了史家对他们为文之时的创造性与自主性的肯定。
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入仕以后,所作赋就不是“作”,而是“上”、“奏”,体现了浓厚的政治意味。如常“奏”赋,《史记》本传云:
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诛。奏之天子,天子大说。……赋奏,天子以为郎。……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关于司马相如、扬雄“上”赋情况,《汉书》扬雄本传云:
上《河东赋》以劝。……故聊因《校猎赋》以风;(风,即有上意)。……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借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
这里的“奏”、“上”,体现了史家对赋家政治身份的确认,以及对其此类赋作政治意味的认同。赋家本人的“上”、“奏”,也体现了赋家本人对其个人与赋作政治性质的认定。
这种记载方法,其实源于汉初吴梁藩国时期的游士文化。邹阳、枚乘客游吴梁,以客卿自居,即多以“奏”称赋,《汉书》卷五十一云:
邹阳,齐人也。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久之,吴王以太子事怨望,称疾不朝,阴有邪谋,阳奏书谏。
枚乘字叔,淮阳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
汉初藩国的游士,虽然也有谋臣的待遇,但其政治地位已经远远不如战国时期的客卿。吴王对待客卿的态度,恐怕不会太好。邹阳的忠直进谏,换来的是吴王“不内其言”。“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就是对游士在汉初政治遭遇的一个注解。即使梁王对这些人的态度稍微好一点,但入汉已久,游士文化毕竟已经失去了战国鼎盛时期的大环境。游士已经不能如战国那样,拥有“为帝王师”的崇高地位,当然也不能畅所欲言、勇于进谏。《汉书》记载:“梁王始与胜、诡有谋,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同上)这种情况必然造成游士政治身份的极度尴尬:介于谋臣与家奴之间的遭际,使这些赋家身上沾溉了更多的“倡优”成分。
直到汉武帝时期,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变化。马端临称“司马迁、相如、枚皋、东方朔辈,亦俱以俳优蓄之,固未尝任以要职”[17]17387。这个时期,如果说汉初藩国游士政治地位的降低,与其当时所处的大环境有关的话,枚皋等人却有“自降身份”之嫌。《汉书》枚皋记载,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默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说明枚皋为求仕进,有自甘“谄媚”之事。虽然枚皋后来“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但这也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了。因为,枚皋这种“诙笑类俳倡”行为,实际上是为了个人仕途的需要。从这里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在汉代,“倡优”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是能为王侯解颐之人。对于那些对权势极为向往但家境贫寒的文人来说,“自类倡优”不失一个步入仕途的捷径。这种情况,一方面使他们可以得到王侯的喜欢,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沦入在政治上不会得到更高地位的尴尬境地。生活在枚皋前后的赋家,如司马相如、东方朔等,甚至以后的扬雄,皆以赋入仕,但终其一生,政治上并不十分显赫。司马相如就曾以自己不受重用而郁郁寡欢。可见,此时的赋家,其身份颇类汉初藩国游士:够不上谋臣,也算不上家奴,只能算是陪侍皇家“倡优”[18]78-94。这种情况,必然造成赋家政治与人格节操的亏污。《文选·典引序》引汉明帝诏称:“司马相如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8]682可知班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赋家及其作品,只不过成了帝王之家的玩物与“帮闲”⑧。故桓谭有“茂陵周智、孙胡不为赋讼酬应之文”之说,可知汉人已将汉赋看作是一种“酬应”工具。汉赋神圣化的消除,终于使其不能承担参与国家大事的责任,自先秦以来“赋”承载的礼仪功能,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渐走下政治神台,真正汇入了文学史的滔滔洪流。
如果说,汉赋真的具有“以赋仕进”的功能,那么,西汉中期以前的汉赋,还不能算作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文学形态——起码当时人是这样想的——它只能与汉代“策问”入仕的形式十分相似。如此,汉赋在汉初只不过算一种求职技能,其文学性质则应大打折扣。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西汉赋家后来还是有将汉赋文学化的意识。有时候,赋家作赋并无政治考量,这种赋作与《诗》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文学意味也更为浓厚。枚皋“自悔类倡”,不仅仅是对自己行为方式的悔恨,也是对以赋谋仕的自我解嘲。扬雄“辞赋小道,壮夫不为”,非真以辞赋不入文学主流,实针对那些应制之赋而言。扬雄入仕之前与晚年的作品,应非“小道”。对于这一点,应该加以区别。其实,扬雄晚年,既有“小道”之作,也有文学色彩非常浓厚的“非小道”之作,如其晚年所作《剧秦美新》和《逐贫赋》。此时,汉代知名赋家,已经逐渐凋零,歌功颂德的任务,必然落在扬雄肩上。《剧秦美新》出于扬雄之手,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但《逐贫赋》则为出于真情的自然书写,与“小道”应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自扬雄开始,西汉赋家逐渐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赋家丧失了“以赋仕进”的政治机遇,创制大赋的政治热情与学术热情大为消减。汉赋作为一代之文体,开始成为汉代赋家抒怀言志的主要工具,体物小赋逐渐流行⑨。东汉班固等人,于大赋虽有佳制,然已无西汉大赋之政治理想与礼仪功能,更多的则寄寓着作者本人的历史反思,从而使其文学色彩渐趋浓厚。
收稿日期:2011-11-10
注释:
①当时韦孟、东方朔、杨恽等有四言诗撰作,汉乐府歌辞中也有不少四言之作,然多见于《房中歌》、《郊祀歌》或汉赋中,四言诗与汉赋皎然分别且四言诗蔚然成为规模,是刘歆之后的事情。
②《文心雕龙·诠赋》云:“刘向明‘不歌而颂’。”按:“颂”即诵,此引自《汉志·诗赋略》而省了“传曰”(近代以前之学者引文,往往如此)。至于云“刘向”,乃因《汉志》删《七略》之“要”而来,而《七略》复本《别录》故也。
③当然,如果“自诵”诗赋,或者不须乐器配合。另外,称述旧事之“诵”,如《韩非子·难言》“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与音乐的关系也不是很大。
④《文献通考》卷一四一:“哀帝罢乐府……夜诵员五人,亦在其中也。”
⑤参(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82页。张大可:《史记新注》(二),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711页。此处乃据力之先生意见补充。
⑥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诵读”这一学习技能主要是在官学习得的。《战国策·秦五》记载:“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变其名曰‘楚’。王使子诵,子曰:‘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于诵。’王罢之,乃留止。”
⑦我们考察的对象主要是汉赋,屈原虽然生活在先秦时期,但《史记》对其作品的记载,大致反映了汉人的文学认识,故将屈原一并考察。
⑧鲁迅先生说:“中国的开国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从帮忙到扯淡》,《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⑨写物小赋主要盛行于汉成帝时期。参见拙文《孔臧四赋与西汉诗赋分途发微》,《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标签:汉书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汉朝论文; 汉代礼仪论文; 诗经论文; 汉书·礼乐志论文; 文选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西汉论文; 大人赋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