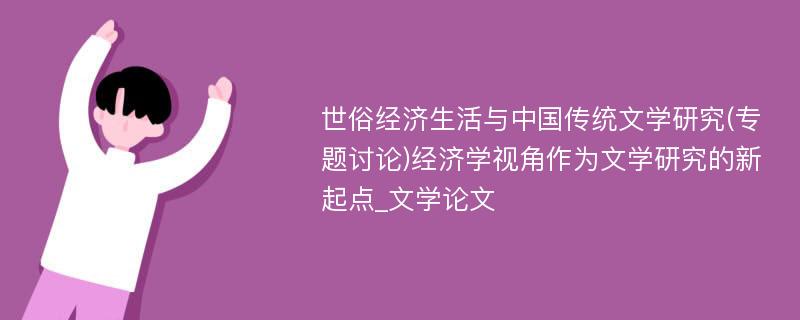
世俗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专题讨论)——1.作为文学研究新起点的经济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文学论文,经济生活论文,中国传统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9-0093-13
经济视角是文学研究的基本路数。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一些学者在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学时,就已经开始自觉地关注经济与文学的关系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等文章一开风气之先,接着又出了一批着眼于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考察文学现象的论者和论著。其中,以郑振铎的成绩最为突出,如他在1930年以后写的《元明之际文坛概观》、《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等文章,十分重视元代戏剧因“元这一代的那样的‘经济状况’在幕后决定着、支配着、指挥着、或导演着”的作用。到1931年,出现了第一部明确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这就是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这部著作鲜明地批评过去的文学史著作都“没有找到文学变化的社会背景和产生的经济条件”,而强调他的著作即“重在社会经济基础的变迁,因为文学是社会基础最上层的建筑”。到40年代,这种研究的态势还有增无减,乃至有《红楼梦与中国经济》这样将作品与“中国经济”直接挂钩作为题目的长篇论文(1944年2月《新认识》第8卷第5、6期合刊)。到 50-60年代,中国大陆的学者更是自觉地在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指导下,重视探索各个时代的各种文学现象。恩格斯的名言“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在人们的头脑里已是根深蒂固。所以说,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学,不但是个老视角,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处于主导地位。
但是,在“文革”以后,尽管还有不少研究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坚持注重分析经济基础与文学演变之间的关系,但在滚滚而来的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观点与方法的冲刷下,以社会经济为基础的文学研究被挤向边缘。铺天盖地地一会儿是强调研究纯“文本”,一会儿是宣扬纯形式主义,一会儿又反过来主张用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文化”来研究,都是有意无意地回避或绕过从“社会”与“经济”角度来研究文学。在此我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完全否定时下强调研究文本及其文学性与一些形式技巧,不是完全否定时下用广泛的“文化”多视角来研究各种文学现象,恰恰相反,我也认为十分有必要加强文本的文学性乃至形式层面上的研究,加强从哲学、宗教、心理、法学、人学、人类学等等多角度地去研究各类文学现象。我反对的只是不要将这些研究与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的研究对立起来,乃至将其他各种路数的研究作为抵挡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的盾牌,更反对一提到从社会经济来研究文学就扣上“简单”、“庸俗”等帽子。文学研究的道路应该是多样化的,更何况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是一种基本的路数。我们该将这个老视角作为新起点,真正下工夫去深入研究。
对此,或许有人会问,既然是一种基本的研究路数,为什么近二三十年来相对沉寂了呢?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只是在来势汹汹的各种新面孔的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你方唱罢我登场”时人们在口头上谈得少了,并没有去作正面的大张旗鼓的宣传而已。许多研究著作在实际上还是坚持“守正出新”的原则,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注意从社会经济的联系中去考察各种文学现象。比如,在考察春秋战国之际文学的繁荣时,就注意到与社会经济大变革所带来的文化上的百家争鸣的关系;在考察阔大的盛唐气象时,注意到文学创作与强盛的国力之间的关系;在描述晚明审美趣味在向世俗化、个性化、趣味化流动时,就从明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谈起。当然,不可否认,还有相当一部分论著在谈同一个问题时是明显地有意绕开“经济”来分析的。在这里,有的人是怕谈,还有的人则恐怕本来就是不喜欢、甚至厌恶从经济基础来看上层建筑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这与目前活跃在文坛上的有些论者本身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修养有关。当然,也应该承认,这同时与以往的研究、特别是“文革”以前的研究的确存在着一些不足与弊端有关,与以前没有把社会经济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工作真正做好有关。特别是,过去由于狭隘地将经济关系理解为劳动占有关系而忽略了劳动交往关系,僵硬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简单地画上等号,将文学与政治紧密相连,把一切文学都当作了阶级斗争的工具,使文学沦为政治的奴隶,从而取消了真正的文学研究,给“十七年”的文学研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因而就不能不使人对此产生一定的疑虑。
在今日,汲取以往的教训,做好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学,首先要注意的是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的经济模式、中国的文学形态。在某一时期的文学现象与社会经济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如何联系,都要作切实、细致的分析,不能用西方的框框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硬套。《水浒传》是反映了农民起义,还是描写了市民起义?《西游记》是写了阶级斗争,还是歌颂新兴市民?《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16世纪的新兴商人,还是基本上是一个封建老板?曹雪芹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还是更像一个地主阶级中的进步分子?这些问题之所以引起争论,都与生搬硬套、简单比附有关。实际上,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土地、赋税、货币等制度的演变与发展是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的,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深蒂固的封建经济体制同样有它的民族特点。中国古代强调“农本”,重义轻利;宋明以后,随着以矿冶业、纺织业、陶瓷业,以及制糖、制烟、榨油、木材等手工业的发展与商业经济的繁荣,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新的生产关系也在一点一点地萌芽,有人不断地对井田制、贵义贱利、打击富人等观点也表示怀疑,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乃至在晚明的徽州地方竟认为“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凌濛初《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但是,这种商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究竟占多大比重?手工业者与商人究竟有多大势力?这在思想界、文学界究竟有多少反映、有什么样的反映?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又有怎样的差别?对此都必须作细致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对其复杂性要有充分的估计。我们过去的问题主要就表现在:一是对其中国特色注意不够,二是对经济与文学间关系的复杂性注意不够,往往接到一只帽子,就简单地给一部作品或一个形象戴了上去,这就难免要招致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
其次,不能将文学与经济的关系的研究孤立化、绝对化、僵化,而是应当加强两个结合:一个是要与哲学、心理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各种各样有用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结合起来;另一个是要与创作主体、文本、接受、传播等各个方向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文学与经济关系的研究真正生动活泼、有声有色。
关于前一个结合,实际上是强调在社会经济研究的基础上与整个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文学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往往关系到方方面面,相互间纵横交叉,只有统一起来观照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经济固然是基础,但唯经济论并不能解决问题。例如,我们在分析李贽的“童心说”与文学思想的形成时,就应该考虑到与明代后期经济、政治、思想、宗教及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当时商业经济繁荣、李贽家乡福建沿海一带的海上贸易又特别发达,这对李贽思想的解放、言论的大胆创造了条件。同时,当朝政治的混乱,控制的相对放松,以及王学的盛行,也都对李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李贽归根到底还是个儒教信徒,而不是儒教的叛徒,但他又积极汲取了老庄、狂禅乃至洋教的思想而发表了一些相对于儒教“出格”的言论。他的“童心说”又与明代后期小说、戏曲的兴盛大有关系。“童心”两字,就直接从焦竑(龙洞山农)的《西厢记序》而来。所有这些(这里仅粗举其荦荦大端而已)相互作用,才有了李贽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文学思想。假如我们孤立地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显然就不能很好地分析李贽的文学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了。
后一个结合则更为重要。以前一说起社会经济,一般侧重于某一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大的宏观的社会经济。用这种大经济概念研究文学,又不与文学创作主体、文本、接受传播密切结合,就往往流于粗疏,而且一涉及文学内在的东西时便如强弩之末,显得话语苍白、内容单调乏味。而今强调“经济生活”的概念,去注重一个人与经济发生关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如功名富贵的追求、吃喝玩乐、游山玩水、饮酒烹茶、园林建筑、琴棋书画等等,它是个体的微观的经济生活,而且由于有些经济生活诸如《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诗社一类的文人宴集和书商选书、刻书等本身就是文学性的活动,故而个体的经济生活与文学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从这个角度研究文学,可更深入地切入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本身,可将经济与文学的关系发掘到作品内容、人物形象、艺术形式等更细微的研究中去。比如在《金瓶梅》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从“商人”的角度来分析西门庆这一形象,指出他并不依赖封建生产关系的自然基础——土地,而是主要靠经商来发财的。他经营管理的方法又具有一些新的时代特点。作者对西门庆这样一个商人在批判的同时,多少又流露了一点钦羡之意。这都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商业、商人与金钱的认识正在起着变化。这里的经济眼光就主要在审视作品的内容、人物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而在《聊斋志异》的研究中人们则发现,尽管小说作者没有经过商、贩过货,却在他的作品中写了七十余篇有关商人与商业活动的作品,描写到的经营品种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经营范围天南地北,十分广泛;有坐贾,有行商,乃至有泛海远渡、数年不归的海外贸易者;有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中介性行业(牙行、典当),也有为客商提供方便的旅栈业;有手工业作坊,有开采煤矿的商人;有“与王侯埒富”的大贾,也有“揭锱铢之本,求升斗之息”的小贩;有山东的商人,也有河北、山西、江西、湖北、四川、广西、江苏等省的商人。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真实而纷繁的当时商贸活动的画面,标明了那个时代商业经济的巨变。显然,蒲松龄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作家。然而,他的商业经济的头恼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要求我们加强作者主体的研究了。近年来,海内外的学者对出版、传播、接受等与经济的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出版了一些很好的专著与论文。但还有许多问题、许多作品尚未作深入的研究。比如《杜骗新书》,它是一部文学史上难得的专门(或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写给商贩们看的书,希望商贩们在行商的过程中不要上当受骗。它是一部小说,同时也可以说是一部有关经济、管理的教科书。像这类作品,研究得还不够,发掘得也不多。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