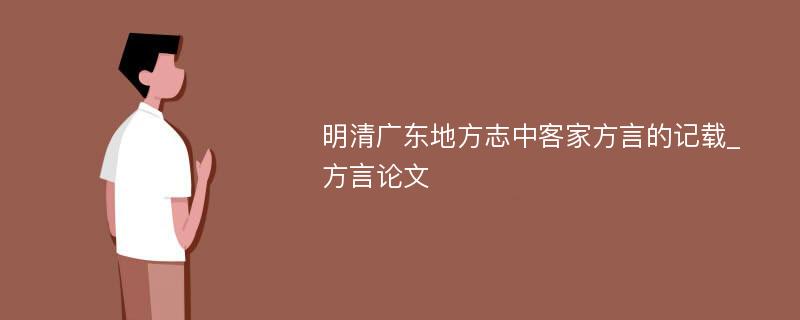
明清广东方志中有关客家方言的记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东论文,客家论文,明清论文,方言论文,方志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客家的论述,通常认为闽粤赣边区是客家人聚居的“大本营”,这一区域里的方言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客家话”,同时这个方言也是“客家”族群的重要特征之一。与今天这一区域里的人被称为“客家人”一样,这里的方言被称为“客家话”、“客话”、“客语”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是伴随着客家意识的传播与普及而渐渐被确立与接受的。本文仅以粤东北为例,结合有关史料,对该过程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一、清末以前粤东北地区的方言的记载
(一)《图经志》中关于潮客方言分布格局的记载
与岭南其他地区相较,今天粤东北是一个开发较为落后的地区,所以宋以前关于这里的记载较少。特别是关于这一区域方言记载的材料更是少见。目前我们见到最早记录粤东地区方言格局的是宋代《图经志》。明《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之“风俗形胜”引《图经志》曰:
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音以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于潮为近,语音不殊。至潮梅之间,其声习俗与梅阳之人等。[1]
以上这段记载中,把广、惠、梅、循等地所操的口音称为“土音”。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关于这两种“土音”词汇读音的记载,所以我们不能判断当时这两种“土音”的具体读音。但是,如果以今天潮客两种方言在粤东北地区的分布格局去对应,我们发现是完全吻合的。这段文字说潮州、海丰与“闽之下四州”——福、泉、漳、化语音大致相同,但与惠、梅、循的“土音”则不能交流;在潮州与梅州之间,即今天大埔县一带,其“声习与梅阳之人等”,与今天丰顺人口音大致相同,我们今天所谓的“客方言”。这种方言在不同地区上的细微差异,与今天的潮、客方言分布情况及其内部的细微差异仍然基本一致,因此也有学者从方言形成的角度来看,认为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时期。[2]但对于广、惠、循、梅这种与潮地不同的方言,当时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名称,而是以“土音”称之。
(二)《正德兴宁县志》中关于“客家”方言读音记载
在明代的方志中,《正德兴宁县志》留下了仅有的一份关于今天粤东北地区方言读音的记载。兴宁地处粤东北地区,在整个粤东北地区属于开发较早的一个县,现隶属于梅州市,属于“纯客县”。正德九年(1514),大书法家祝允明任兴宁县令,并主持编纂《正德兴宁县志》。在这部县志里,他记录并分析了当时兴宁的方言,并且和江南地区的吴方言进行了比较。这是目前所见对客家方言最早的语音、词汇描写,在客家方言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3]而《正德兴宁县志》中关于方言记载的部分散佚,所幸《嘉靖兴宁县志》因袭前志,收录了相关的内容,才得以为后人留下这份珍贵的方言记录。《嘉靖兴宁县志》因袭《正德兴宁县志》中方言读音的记载如下:
其声大率齐韵作灰、庚韵作阳,如黎为来,声为商,石为铄之类,与江南同,乃出自然,益信昔人制韵释经之不谬。亦有“杨”、“王”不辨之陋,如“天王寺”为“天洋”之类。至有姓王者自呼杨,问之,云“王乃吾上,避不敢犯”,此尤可笑尔。
谓父曰阿爸,母曰阿姐,哥嫂辄以亚先之,如兄则曰亚哥,嫂曰亚嫂。呼小厮曰孻,呼儿曰泰,游乐曰料,问何物曰骂介,问何人曰骂鄞,无曰冒,移近曰埋,其不检者曰散子,其呼溪曰开,岭曰两。[4]
上面记录的明嘉靖年间的兴宁话词汇与读音,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客家话”。特别是称何物为“骂介”,几乎是客家话里标志性的用语。①这说明,从读音来看,在明代已经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客家方言”。但是,当时文献中并没有将这些方言称为“客方言”,更没有将兴宁方言与特别的人群相联系起来,也没有用特别的称谓去对这种方言进行命名。
(三)《石窟一徵》中对客方言的考证
在粤东北地区,最早专门对今天所谓客方言进行系统考证与论述的人是黄钊。黄钊(1787-1853),字香铁,一字穀生,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人。
黄钊大半生均在外奔波,居乡时日不多,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冬,始归镇平,收徒授学,并在“课士之暇,辄随笔录记”,开始《石窟一徵》的撰写。黄钊在《石窟一徵》卷七、八《方言》中,记载了镇平县(今蕉岭县)方言读音。这些方言词涉及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语。其基本方法是,先列出书面词汇,列出本地方言读法或读音。在多数情况下,黄钊都会从典籍里寻找自己方言读法或读音的来源,这些典籍包括专门解释文字的《尔雅》、《说文》,包括《左传》等先秦古籍,以此论证本地的方言与正统文化的关系,有时甚至不避牵强臆断。综观全文,黄钊只是记载语音,考其来源。但对于自己家乡的方言并没有作任何的评判性的论述。在文中,他称通行的官话为“官音”,然而对于自己的方言读音,称之为“土音”,有的称之为“俗呼”,如:
遇事操心曰劳勑,劳勑二字见字林勑,音赖,土音读如辣。[5]4
细事作状曰鸭母状,鸭母状者,乡里细事,动烦执笔以一鸭酬之而已。母,土音读如嬷。[5]9
富曰发,土音读作“褒”字,放声,如官音之拨。贫曰括,土音读作平声,言空诸所有也。揖曰唱喏,喏,土音读如也。[5]10
爱子曰吾子,吾土音读如“厓”,又读为牙。[5]11
妾曰阿姆支,俗呼为阿姆支;轻贱之词也。[5]12
妻曰辅娘,言相辅以成家也,或疑婆娘之转音。今土语统称为辅娘子,当亦婆娘子之谓也。[5]12
麻雀曰禾毕,俗呼麻雀为禾毕。[5]13
这样称当地方言为土音或俗呼的例子,在《石窟一征》卷七、卷八《方言》中随处可见。但没有一处提到他们的方言是客话。因此,我们认为,黄钊在《石窟一徵》中对蕉岭方言进行考释时,因自己并没有客家意识,更没有将自己家乡的方言称为“客话”。后人在探讨客家问题渊源时,常常追溯到黄钊《石窟一徵》中的“方言”二卷,认为他从方言的角度来考证了客家与中原的关系,其实这是对黄钊的误读。[6]
二、广、肇、惠地区方志中关于客方言表述
在今天被认为是客家聚居核心区的粤东北地区的地方文献中,我们发现虽然有方言的记载,但没有将自己的方言称为“客”方言。然而自明中叶始,在广、肇、惠等府属的一些县志中,却一直有关于“客”或“客家”的记载,其中,有些方志中将他们说的方言称为“客话”。
(一)嘉靖《香山县志》
明清时期的香山县,约今之中山市、珠海市、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明中叶以来,香山县接受大量来自粤东地区的外来移民,又因其靠海,所以也有闽、潮移民在此。所以这里人群复杂,方言多样。这种局面在嘉靖年间即开始形成。在嘉靖《香山县志》中记载了当时的方言情况:
邑民上禀风气,下钟水土,故其气轻,其质柔,其音唇舌,其声羽,其调十里而殊。故有客话,有东话。
其下双行夹注又及:
客话,自城内外及恭常之半为一,通于四境。东话,良字之半及龙得、四大等为一外有谷字、黄旗、角愈侏離,近于潮闽,译以客话乃通。城中近于广而近正音,黄旗之半及大榄近顺德又其半、及黄梁、古岭近新会亦皆曰“客话”。[7]
以上引文显示,嘉靖时期,香山县主要有两种方言,一为东话,一为客话。而“客话”③在香山县分布甚广,“通于四境”。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称“客话”的文献。
(二)《雍正长宁县志》
在东江流域长宁县(今新丰县)县志中,也出现了关于客话的称呼。长宁县(今河源新丰县),位于广东省中部偏北,是东江上游一个山区小县。这个县今天被认为是一个“纯客县”,通行“客家话”。在雍正《长宁县志》中,第一次出现关于“客家音”这样的指称与记载:
语音。小儿读书多训官话。□言语则不然。语有两样,一水源音,一客家音。传说开建之始祖自福建而来则客家音;自江西而来则水源音。今各随其相沿,亦不拘泥。[8]
从这里的记载来看,这里的“客家音”指称的是来自福建移民的方言。结合明清以来大量福建人移民粤北山区开垦的事实,我们认为这里的“客家”即是今天所谓的“客家”,其族群指向性与今天是最接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的“客家音”应该指的就是今天所谓的客家话。
(三)光绪《四会县志》
光绪《四会县志》出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7),其有专辟《客民》一节,来讨论客家,并称他们的语言为“客家话”。
邑上路各铺多客民,土人称之曰“客家”,其来不知所自,虽习土音,而客家话久远不改。[9]128
细究这些引文,其实他们所指的“客”不是同一类人。长宁县志指的是福人,而香山县志等指的是惠、潮、嘉地区的人。但是,对于他们的称呼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以“客”称之。这说明,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在今天东江流域的一些地区,已渐渐形成“客家人”的概念,与之相伴的是,“客家话”的概念也相应形成,并且将其作为重要的族群标志。
三、客家聚居核心区对“客家话”称呼的接受
清末是粤东北客家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客家话的称谓也随之产生。对于这个外来的叫法,有表示抵触的声音,更多的是慢慢接受。我们从温仲和主持编纂的光绪《嘉应州志》可窥见一斑。该志书成书出版于1899年,此时客家意识经过晚清粤东客籍知识分子的宣传,已经在知识阶层产生一定的影响。温仲和在方志中也加入这些新内容。在讨论客家方言时,他写到:
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异,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10]
从这段话中,温仲和指出今惠州府七县,潮州府大埔、丰顺二县及嘉应州五县大致皆可相通的“土音”,就是“客话”。但引文显示,当时温仲和并没有言之凿凿的将自己的方言称为客家话,而是说“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这说明温仲和的客家意识以及关于客家的称谓,也是从外来者的称呼那里得来的。
除了温仲和外,即使当时的语言学家,也没有天经地义的将嘉应州方言称为“客话”或“客家话”。如杨恭桓在光绪丁未(1907)的《客话本字自叙》中说:
向谓西人有音即有字,中国有音或无字,今而知非也。中国有音有字者多,特人所不知,以为土谈,习焉不察耳!即如嘉应所属之土谈,外境人皆称为客话。④
由此可见,将当地话称为“客话”,可能来自外境人的他称。即使“客话”一词,并不是一次性定位的。1916年,杨恭垣在《韵学余谈》里将当地方言称为“哈话”,乃因“客”字在当地方言里读作“哈”。这一现象说明将“客话”用于自称的时期并不太久,乃至还没有形成标准的写法。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有关客家族群知识的普及,“客话”一词逐渐被固定下来。二十年代兴宁人罗其霭的《客方言》一书,不但研究客方言,而且也为客家方言的正式定名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同时,这部著作有从语言上论证客家音为中原古音,从而达到为“客家人”辩护的目的。章炳麟在介绍《客方言》时,说“兴宁罗翙云《客方言》十卷……上列客语,下以小学故训通之,条理比顺,元所假借,盖自是客语大明,而客籍之民亦可介以自重矣。”[21]与前述黄钊《石窟一征》不同的是,尽管都是证明自己语言有中原古音之遗韵。但《客方言》在论证时有明显的自觉意识,也有明确的族群色彩。
由此可见,清末“客家话”一词最初并不是粤东北地区“客家人”自创的,是由外传入客家聚居核心区的,然后再经过知识分子的宣传与推介,才渐渐被核心区的人们接受。之所以“客话”这个方言名称没有在核心区首先出现,是因为没有族群的互动,所以很难以产生一种族群的自我认同。只有在族群互动的区域,才可能较早的发现族群差别,激发族群意识。而当把另外一个族群给予特别的指称后,就将此名称用来指称与其相类似的族群。正如民国《赤溪县志》所言:
吾粤嘉应州(今改州治为梅县)全属五县与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归善(今改惠阳)、博罗、龙川、河源、连平、永安(今改紫金)、长宁(今改新丰)、和平八县,又南雄州、韶州府、连州(今改州治为连县)各属州县,除少数官音土音外,其方言大致相同。然据各州县志乘所载,则谓其先世俱系中州黄光间遗族,在汉晋间南迁江浙闽赣诸省,至五代南汉时复由闽之汀州赣之赣州转徙而来,分居以上各州县。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原属先来落籍之土著无所谓客,即其言语与汀赣相近,亦初无土客之分也。惟今广肇之人,辄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并谓其话为“客话”者,缘以上各州县人在明代清初间复多迁移于广州府属之番禺、东莞、香山、增城、新安(今改宝安)、花县、龙门、从化、清远、新宁(今改台山);肇庆府属之高要、广宁、新兴、四会、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及其他罗定、阳江、信宜等州县,或营商,或务垦辟,皆先后占籍焉。于是广肇各土著遂以客视之,因言语与土著不同,又谓其话为“客话”。因而凡以上惠、潮、嘉、南、韶、连各州县之人而语言同一者,亦概视之为“客家”。然在大江以南诸省,说客话者所在,蕃殖不独两广有之,虽其声音各因水土之异宜或随之而变,微有高下,特其中多含正音古韵,流传不失,而随处皆可八九相通,故说客话之人,无论何省何州县,一经见面,便可接谈,以视广肇土话,复杂多种,稍隔一县甚或稍距数里即彼此不能通晓者,未可同日而语。[12]
这段话道出了客家话乃至广肇地区人对客家这个族群的基本看法。
上文回顾了历史文献中关于粤东北、粤北地方方言如何从自称的“土音”变成“客话”的过程,其关键节点是晚清民国初期,客家话这个称谓才渐渐被客家核心区的民众认同与接受——这其实也是客家意识形成过程的产物。但是,这个由知识分子与媒体等建构出来的一个新名词,他的普及还在进行中。其实,即使是梅县地区,民间仍然将“客家话”称为“阿姆话”。这是民众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叫法,一直在民间延续,相沿成习。但有理由相信,随着大众媒介的深入、教育的普及,“客家话”这个方言名词会渐渐地深入人心。
①正因为这个特点,在今天广东西部与广西等地说“麻介”话的人,被认为是客家人。
②如在解释“和尚曰禾上”这条时,认为“此大有意义。盖秃字禾在上也。《说文》秃无发也。”
③其实在历史文献中,也有多次提到“客籍”、“客话”这样的名词,与今天所讲的“客家”无关。前者指户籍,后者指外地迁来的人及其所使用的语言。如宋代迁入雷州一带的居民,将清朝才迁到雷州的广府话称为“客话”。但我们认为本文所引《香山县志》中“客话”,即今天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客话”。
④杨恭垣《一日通韵》,出版地不详,1925年,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