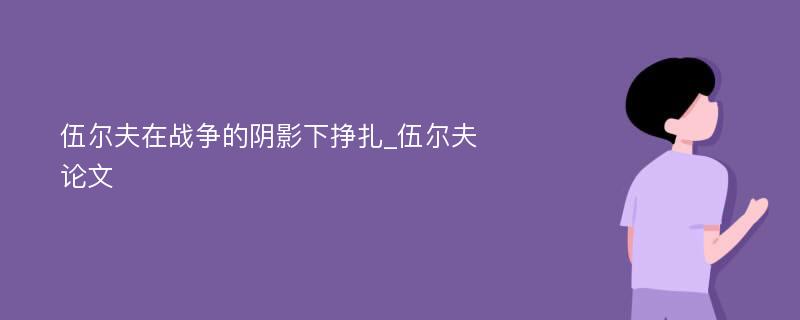
战争阴影下挣扎的弗#183;伍尔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阴影论文,战争论文,伍尔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细读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作品,无疑会发现她对男权主义的批判是与她对军国主义战争的控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一些文学史中,伍尔夫往往被说成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关心时势政治的唯美主义艺术家。卢卡契对乔伊斯、普鲁斯特及伍尔夫等“颓废派”作家的贬斥,影响了人们对她的公正评价。人们大都习惯性地认为她对人类社会是冷漠的、绝望的;就连比较了解她的爱·摩·福斯特也曾说:“如何改进这个世界,她可不愿意考虑”。[①]
事实并非这样。伍尔夫在《达罗卫夫人》(1925)、《三个基尼金币》(1938)等作品中,对战争提出了强烈的控诉,并提出自己的救世方案。这使她与乔伊斯等人有明显的差别。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詹明信(F.Jameson)90年代初在《现代主义和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对包括伍尔夫在内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必须在帝国主义的总体框架内、联系帝国主义政治与经济现象,重新思考并进行系统探讨。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伍尔夫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詹明信的论文主要探讨的是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新的空间关系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本文则试图具体分析伍尔夫作为一名女性,其作品怎样打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深印迹;她对生命与死亡的意识,怎样形成一种特殊的类似现代化战争的空间体验,这种体验及其表达既有创造性的审美价值,也有积极的政治道德意义。
一
虽然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中取得了胜利,但经济实力大大削弱,丧失了“世界银行家”的地位。战争还断送了英国整整一代最有希望的青年,而持续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使英国又笼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的阴影之下。两次世界大战使伍尔夫深受其害。一战加重了她从小染上的精神忧郁症,有一次发作,竟严重到精神彻底崩溃的地步。二战更加剧了她的精神恐怖,她在伦敦的住宅和藏书被炸弹焚毁,德国的轰炸机群经常在苏塞克斯丘陵草原边缘她的小屋上空盘旋。飞机与大炮使远离战场的妇女和儿童也成了牺牲品。伍尔夫的健康进一步恶化,终于在1941年3月投河自尽。
伍尔夫并不想逃避战争。她的自尽是因身体极度衰竭,力不能支。从她留下的遗言看,她是怕自己犯病给别人再添麻烦,怕拖累丈夫。对于伍尔夫来说,失去意识、不能写作便等于死亡,故她勇敢地死去了。1940年8月,她发表了杂文《空袭时关于和平的断想》,对法西斯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从她1940年9月17日的日记可知,她是鼓足勇气用忘我的写作去抗拒战争和疾病的:
今天早晨听说我们在梅克伦伯格广场的家的窗户震裂了,天花板坍塌了,大部分瓷器被压得粉碎。“我们需要全部勇气”,这句话马上涌现出来。……我仍然奋笔疾书,继续写《波宅》。[②]
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卓越的作家都有一种反战倾向。伍尔夫的重要之处,便是她将战争与男权主义联系在一起,从性别角度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三个基尼金币》是伍尔夫在纳粹战争狂嚣中发布的独特的反战宣言。一名律师写信给伍尔夫,询问她对于阻止战争有何看法。伍尔夫送给那位律师一基尼金币和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我们如何去阻止战争爆发——这个问题我在脑子里苦苦思索”,这涉及到男女间的整个社会关系,“难道不是父权制度使你们趋向战争吗?”伍尔夫问道。她认为妇女天生具有和平、抚慰的特质,可以大大缓解男人的攻击欲、狂妄与凶残,妇女对社会政治活动的参与,会使人类避免自我毁灭的命运。但至今妇女没有多少政治权力,“许多大门还对我们妇女关闭着,或者最多只是开启了一条小缝。我们对法律、商业、宗教或政治能起到什么样的实际影响呢?”她将家庭中的男权主义与政治上的法西斯主义暴政毗连:“众人的世界与自我的世界紧密联系,前者的暴政与奴役衍化出后者的暴政与奴役。”她认为要解决战争问题首先得解决妇女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男权统治下女性受教育和就业的问题,那么男性操纵世界的态势便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她回答男性通信者:“受教育的女性所反抗的敌人与你们的敌人是相同的,斗争的理由也一样。她们试图击溃父权制暴政,一如你们企图击败法西斯暴政。”为了挽救那尚存的一点人性,她号召妇女结成联盟反对现存秩序,如果妇女能说“我是我”,那她们也能说“我们是我们”。伍尔夫还将艺术与战争对照,认为“艺术的享受和实践将是多么称心如意,而那些老朽的战争角逐则多么枯燥乏味”。[③]故有论者指出,《三个基尼金币》是《达罗卫夫人》所描述的两种力量——艺术与战争的理论演绎。对于这一题旨,伍尔夫还计划在小说《岁月》中再度展现,但最终未能如愿。
某些评论家并不怎么看重《三个基尼金币》。法国伍尔夫研究专家莫尼克·纳唐说,仅《达罗卫夫人》中的一页,就比《三个基尼金币》中关于妇女的所有雄辩能给她带来的荣誉还要多。连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也对伍尔夫这方面的建树不屑一顾,认为《三个基尼金币》乃女权主义文论的败笔,是她“最坏的作品”,“令人发指,真是歇斯底里大发作”。[④]
然而,也有不少论者为伍尔夫辩护。桑·吉尔伯特和苏姗·格巴指出,《三个基尼金币》“是那一时期批判上层人物和国家纠结在一起的纳粹精神的最激烈的作品”。[⑤]罗莎琳德·迈尔斯说,“虽然伍尔夫本人珍视自己的小说胜于‘三个基尼金币’,但它的实际价值似乎胜过她的任何小说”。[⑥]托里尔·莫依认为,如果说女权主义批评家没能对伍尔夫作出积极的政治和文学的评价,那是因为她们在自己的批评理论和方法上犯了错误。针对肖瓦尔特的批评,莫依说:
但肖瓦尔特在她自己的文学批评中,并没有对粉碎资本主义打败法西斯的必要性发生任何兴趣,这也是事实。她坚持认为对于政治艺术的需要只能被限制在与性别主义斗争的范围内。因此,对伍尔夫在《三个基尼金币》中所创立的刻意求新的性别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关系的理论,她不屑一顾。因此,对伍尔夫在文中努力把女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相联系的做法,她也显得不那么赞同。[⑦]
莫依的批评显然是有道理的。当代重要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多罗西·乔道罗在《妇女,文化和社会》(1974)、《母性角色的再生产》(1978)等论著里还发展了伍尔夫的上述思想,影响很大。乔道罗认为,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很少扮演一个亲切的、创造性的角色,因为他很少与孩子接触;男孩对父亲的身份识别成了一种不真实的“位置识别”,这必然使一些扭曲的两性价值观念得到延续,为改变男权和男性文化霸权对性别角色的引导,应使男性也承担养育之责任。伍尔夫关于妇女与和平主义的建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男性理论家马尔库塞那里也得到激扬。他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女性渴望和平、快乐和结束暴力,正是这种特质,使爱欲压倒资本主义的攻击性、自私性,由此人类才能真正走上解放之途。
二
伍尔夫的主要小说,同样呈示了女性对男权专制及战争的拒斥与控诉。
在《启航》(1915)里,女主角瑞奇·温里斯对男性世界的暴力与歧视感到恐惧,她的同性恋,呈示了女性的独立与自我满足,而她的死,则象征了女性自我追求的夭折;《夜与日》(1919)中的女主角凯瑟琳·希尔伯里企图挣脱家庭的羁绊,向父权制和传统的婚姻挑战,针砭女性智力低于男性的陈腐偏见;《雅各的房间》(1922)强调男女意识的沟通,然而其背后仍是无法弥合的裂痕,雅各·弗兰德斯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灯塔去》(1927)中的兰赛姆夫妇表现了男女不同的品性,男人死板僵化,女人灵活多变,对事物和人际关系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团结众人的凝聚力,他们的儿子也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变成女性的奥兰多(《奥兰多传》,1928)以她女人的眼光审视世界可看出,作者认为女人在实质上异于男人,且比男人优越;《海浪》(1931)是一曲生命的颂歌,朋友的聚餐会使孤独的个人得到暂时的拯救(这也是《达罗卫夫人》所表现的主题之一);《幕间》(1941)通过英国农民在1939年某一天的生活,着重表现了正在向人们逼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达罗卫夫人》。像弗·伍尔夫所有主要小说那样,《达罗卫夫人》“被一种政治的鸣响所震荡”[⑧]。这部小说向专制政体提出质疑,向战争主义提出控诉,并企图用女性的抚慰力量去拯救人类。但“这部书未明言的对抗是生命与死亡,爱神(Eros)和死神(Thanotos)的喜剧性地趋于相爱、交流,以及富于创造性的幸存者与对于战争和毁灭的悲剧性直觉的对抗”。[⑨]这一主题分别由两股“意识流”来呈现,克拉丽莎·达罗卫和赛普蒂默斯、卢克西娅分别代表这两极。
小说一开篇便笼罩着战争的阴影。那是6月中旬的一个清晨,克拉丽莎出去为自己的晚宴买花。她在伦敦平静的人流中仍感到了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最近世界经历的创伤使男男女女都满含泪水。”即使在这和平的日子里,作者也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留下的创伤:
战争已经结束,不过,还有像福克斯克罗夫特太太那样伤心的人,她昨晚在大使馆痛不欲生,因为她的好儿子已阵亡,那所古老的庄园得让侄儿继承了。还有贝克斯巴勒夫人,人们说她主持义卖市场开幕时,手里还拿着那份电报:她最疼爱的儿子约翰牺牲了。[⑩]
对战争的回忆扼杀了现在,预示着未来。“欧洲大战的魔爪是如此阴险,如此无孔不入。”就连那天在天空盘旋作广告的飞机,也“预示某种不祥之兆”,似乎象征着死亡和毁灭。身为议员的理查德·达罗卫,思量着带一束鲜花回家给妻子,他的意识的流动也与战争搅在了一起:“当他回想起大战时,觉得那真是个奇迹:成千上万的可怜虫本来都有光明的前途,却死掉了,埋成一堆,如今几乎被遗忘了;而他却安然无恙,眼下正穿过伦敦,简直是个奇迹哟。”
无数人死于战场,而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的青年仍受着战争创伤的煎熬。战争使赛普蒂默斯·史密斯成了替罪羊。他作为一名志愿兵在法国勇敢作战,得到过晋升,但残酷的阵地战使他患了弹震性精神病。就在战后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感觉,便用婚姻作避难所,但大战中死去的朋友的亡灵折磨着他,阵发性的神经错乱使他最后不得不跳楼自杀了结一生。小说写道:“人性已判处他死刑”,朋友埃文斯阵亡时,他无动于衷,他并不爱卢克西娅,却跟她结了婚,“欺骗了她,引诱了她”。
人们往往关注表现克拉丽莎、彼德和赛普蒂默斯意识流动的三张油画布,但很少有人提及伍尔夫对赛普蒂默斯的妻子卢克西娅所承受的痛苦寄予的深深的同情。赛普蒂默斯的精神病主要是从卢克西娅的角度叙述的,这一特定视角表明,作者意在揭露战争对妇女的伤害。
赛普蒂默斯是在他对战争感到恐惧,发现自己丧失了感觉的情形下向卢克西娅求婚的。婚前的卢克西娅活泼愉快,有着艺术家一样灵巧的手指,“丝绸、羽毛,还有其他一切,在她手指的拨弄下都富有生命”。但与赛普蒂默斯的结合却成了无尽灾难的开始。受创伤的士兵陷入疯狂之中,而妻子却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感觉敏锐的正常人承受着他的罪孽。卢克西娅大段大段的意识流动,揭示了战争是怎样摧毁了女人的正常生活,使她们也成了替罪羊的:
她再也无法忍受。霍姆斯大夫尽可以说无关紧要。可是,她宁愿他不如死掉!瞧着他那样目光呆滞,连她坐在他身边也视而不见,这使周围的一切变得可怕。她确实不能再和他坐在一起了。但是他不肯自杀,而她又不能向任何人吐露真情。……他是自私的。男人都如此。……瞧!她的结婚戒指滑了下来——她已这般消瘦。是她在经受煎熬啊——却无人可以诉说。
卢克西娅向往未来,想生孩子,丈夫却逃避现实,惧怕未来。她灵巧的手指能使羽毛、丝绸变成艺术品,却不能抚慰受到战争伤害的人。受害的士兵顽固而不自知地扮演着害人者的角色。“我孑然一身,多么孤寂!孤零零地站在摄政公园喷水池边,……她是他的妻子,永远,永远不会告诉别人他病了!”难以忍受的卢克西娅终于发出了愤怒的呼喊:“救人啊!救人啊!”
随着60年代末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妇女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引起人们特殊的兴趣。“重新发现过去的妇女文学,是理解我们关于世界大战的‘记忆’的最好材料”。[(11)]但一些批评家关于世界大战中性别冲突的理解,如吉尔伯特等在《没有男人的地界》(1988)中“关于妇女的‘权力’即等于男人的‘无权’”的阐释,无疑过于简单化了。[(12)]她们认为送一名男人走上战场,便会给一名妇女带来一份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男权统治发生动摇,战争产生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也使妇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1918年以后,欧洲女性的机会来了,有了选举权,有了自己的房间和工作的机会,女作家开始成批涌现。但战争也使妇女大受其害。战争产生了女性过剩问题。由于许多男人死于战场,女性的婚姻没有着落;而那些已成家的妇女,像伍尔夫笔下的卢克西娅、福克斯克罗夫特太太、贝克斯巴勒夫人等,同样受尽了战争的折磨。伍尔夫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世界大战的‘记忆’的最好材料”。
相对于赛普蒂默斯和卢克西娅,克拉丽莎则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
在作为《达罗卫夫人》雏形的短篇《首相》(The Prime Minister)里,克拉丽莎和那位国家的头头象征性地对峙着。首相是一个只会运用男性独裁权力的机械死板的形象,作为对照,克拉丽莎则作为一名有个性的角色将女性创造和维护圣洁生活的能力表现了出来。《达罗卫夫人》中的克拉丽莎,同《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人一样,是一位以各种新奇的、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艺术家。从伍尔夫关于《达罗卫夫人》的创作笔记可知,作品的叙事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典悲剧的模式,建立在具有象征意义的牺牲和圣餐仪式上。作品用了各种方式表现生命,如对赛普蒂默斯死的描写,[(13)]克拉丽莎不啻是一名高级女巫和动情的献祭人。因此,评论家苏塞特·亨克指出,“就像耶稣基督的降生与死亡的古老悲剧情节,伍尔夫的小说通过天主教的圣餐仪式,呈现了死亡和非基督徒的大弥撒的理想境界”。[(14)]如伍尔夫后来在《三个基尼金币》中所阐发的那样,作者用女性的爱和抚慰力量与死神对抗,克拉丽莎的晚宴,是一首对于生命和再生的赞美诗。她的济世良方是女性的友爱、交流。
克拉丽莎与少女萨利的同性恋也具有一种反抗男性专制的性质。这种求诸同性的趋向,或许应视为女性的社会力量太薄弱而被逼出来的。克拉丽莎“对于萨利的处女般的情感由于青春的纯洁而显得美丽,没有被由成年人的异性爱关系而导致的性别伪装和社会角色所污染”。[(15)]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1928)里曾说,这种女性相互“喜欢”(like)的表现,在现代小说中很少见。
当然,我们也不宜过高评价伍尔夫设计的济世方案。诚如她在《三个基尼金币》及日记中所言,妇女的社会权力是很有限的,“像一片树叶上的一只小虫。”我们从小说结束部分可看出,作者对于克拉丽莎的努力是持保留态度的。青年士兵的自杀使克拉丽莎认识到了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乃至伪善,她的幻想是诗化的、浪漫的、脆弱的。
赛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出现在克拉丽莎的宴会上是体现生死对照原则的压轴戏。他的死使首相出席的宴会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使克拉丽莎感到“生命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灭了”。她的美妙心境已被死神缠绕:“据说那青年是跳楼自尽的:猛地摔下去,只觉得地面升腾,向他冲击,墙上密布的生锈的尖钉刺穿他,他遍体鳞伤。他躺在地上,头脑里发出重浊的声音:砰、砰……终于在一团漆黑中窒息了。”这是她想象的情景,却历历在目。克拉丽莎·达罗卫虽是上层显贵的妻子,对于政治,她则是“局外人”,她反而与被社会抛弃的赛普蒂默斯和卢克西娅有强烈的认同感。
不少男作家,如叶芝、爱略特、海明威、劳伦斯、乔伊斯及卡夫卡等人都描绘过一战给妇女带来的变化,表现了男性信心的丧失及其对女性的困惑。“旧世界在1915年告终了”,劳伦斯悲叹道:“男人作为主人的地位再度被削弱了,他会明白他将不再是主人了”(《母权制》,1929)。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女主角布莱特·艾希利,是一个以男女乱交来麻醉自己的色情狂,是现代小说中著名的具有破坏性的女人。劳伦斯倾向于表述女性实施报复的破坏性内容,《恋爱中的妇女》里的知识女性卡琼·布莱温使男人恐惧,并导致其死亡;《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守林人对前妻的抱怨,同样表现了男人对女性自主性的不满与焦虑。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莫莉造成布鲁姆的性变态,而她自己则相信开放的性生活会使青春长驻。爱略特在《荒原》中也奚落女人,战争使女人堕落,丈夫上了战场,女人则在家里偷情。在卡夫卡笔下,女人是陷阱,他对现实的厌恶与逃避也包括了对女性的厌恶与逃避。黑塞、乔伊斯、爱略特等人还塑造了一批半男半女的两性人,揶揄传统两性特征的变异,绝望地表现欢乐与恐怖的共生与同一。相比之下,伍尔夫则生动地展示了战争对女性的伤害,热情讴歌了女性特有的抚慰力量,呼唤和平与友谊。
三
伍尔夫的作品打上了她那个时代的烙印,其艺术形式也受其影响,似乎可以说,是现代化战争的空间形式启发或催生了她所钟爱的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叙事技巧。
当然,在战前,艺术上追求新奇的意象、内心独白、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融合等观念便开始萌生了。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也是导致艺术风格变化的主要社会原因。普鲁斯特、乔伊斯及伍尔夫等人的现代主义便是与战争的恐怖、混乱情状相应的艺术,它既是资本主义工业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文明和秩序遭到破坏的产物。人们普遍感到了时间与空间的多层次性、全方位性、偶然性、不连贯性、瞬息万变性。时空的距离变得微不足道,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战争对肉体与心灵的摧毁最终破坏了传统的小说叙述结构,使欧洲小说家观察、体验并把握了现代纪元的“极限悖谬”。[(16)]意识流小说的放射性、不稳定性、内向性、破碎性、不连续性及多层次性等进一步发展起来。譬如,相对于乔伊斯用零星细节塑造人物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916),与大战同步产生的《尤利西斯》则成了人物意识交错翻腾的“无意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巨幅全景”(T.S.爱略特语)。也正如《追忆逝水年华》,虽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但作者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将小说的篇幅扩大了两倍,战争将作者的回忆推向更久远的过去,迫使他将生活中正在形成的事件纳入更深的生存层次,“死亡成了统领一切的关键,它强调了记忆、重建生活和‘寻找’的必要”。[(17)]
伍尔夫关于“意识流”的比拟,便给人一种战火纷飞的意象:“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18)]伍尔夫指出,莎士比亚等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及后来的济慈等人,不会像现代人这样心怀恐惧,或者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妨害他们思想感情的充分流露,他们的表达是自由自信而连贯的。而现代人却不同了,战争及工业社会的机械主义,使人们充满恐怖与疑虑,游移不定,遮遮掩掩。“被分割成一幢幢的盒子般的房子”、“头顶上的天线”以及战争(伍尔夫曾将轰炸机的声音比喻为“就像有人在我们头顶上锯东西似的”)使空间变得立体化了。在一日之中,成千上百种情愫在心中交叉、冲突、消失,且惊人地杂乱无章,过去完整地进入人们心灵的东西,如今变成了碎片,“意识流”技巧能曲尽其妙地记录现代心灵的这种变异。克拉丽莎、卢克西娅等人关于战争的意识流动,像炮弹爆炸的碎片,像散射后纷纷坠地的原子,散落在《达罗卫夫人》整部作品中。
《到灯塔去》里,拉姆齐夫人的儿子安德鲁·拉姆齐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件通过一种巧妙的意识流联系呈现了出来:“炎热的盛夏,玫瑰花儿无比鲜艳,阳光把它的影子,清晰地投射在墙上,突然什么东西砰的一声坠落下来,打破了一片寂静、冷漠、完整的气氛。(一颗炸弹爆炸了。二、三十个小伙子在法国战场上被炸得血肉横飞,安德鲁·拉姆齐也在其中,总算幸运,他立即死去,没受更多的折磨。)”突然的声响与战场上的炸弹联接,不知不觉由此及彼,将和平与战争自然对照,毫无牵强附会。年青人的死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印象,一触即发,偶然的随想变得自然而然,无意识有了意识的、理性的支撑。战争与死亡,形成一种无时间的奇特压力,无边际的共振。
伯纳德在他儿子出生的当天接到珀西瓦尔的死讯,恰如安宁的巴黎市民突然遭到了长距离火炮的袭击:“‘这就是那种不可思议的结合,这就是事物的复杂性’,伯纳德沉思着”。(《海浪》)灾难性的组合、特殊的空间观念使人物的线性时间感觉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形成一种弥散的放射性结构。同样,在《雅各的房间》里,作者把死去的儿子与小鸡并置:“失去了莫蒂,西勒鲁克也死了;他的儿子们在为祖国的战斗中捐躯。但是小鸡们安全么?”各不相称的事物又有某些相似性,被战争杀害的孩子不是像小鸡一样任人宰杀么?这便产生了伍尔夫将“希特勒的百万大军”与“一片草叶上的一只小虫”对照的效果。基于相似性而非连接性的经验联系,各种意象不是以情节的进展结合起来,而是靠象征和隐喻的诗意组合,现实的感观印象与关于过去的内心独白形成一种新的体悟、新的张力场,扩大了读者的审美感知领域。故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既有十分明确的社会现实意义和进步的政治道德价值,也有很高的艺术技巧和丰厚的审美底蕴。
注释:
① 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载《伍尔夫研究》,瞿世镜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5页。
② 《伍尔夫研究》第501页;《波宅》即后来的《幕间》。
③ Virginia Woolf,"Three Guineas",in New Feminist Essays on Virginia Woolf,ed.,Jane Marcus,The Macmillan Press,1981,p.128.
⑤ 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The Tradition in Englich,New York & London,1985,p.1225.
⑥ Rosalind Miles,The Female Form:Women Writers and the Comquest of the Novel,London,1990,p.52.
④⑦ 托里尔·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林建法等译,时代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8页。
⑧ ⑨ (13) (14) (15) Suzette A.Henke,Mrs Dalloway:The Communion of Saints,New Feminist Essays on Virginia Woolf,The Macmillan Press,1981,P.128,p.125,p.130,p.135.
⑩ 弗·伍尔夫《达罗卫夫人》,孙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4-5页;以下引文均出自该书。
(11) (12) Carline Zilbourg,Women's Writings about the Great War:Memory and Supression,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32,No.3;Fall 1991,p.434.
(16)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17)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论普鲁斯特》,载《文学和新历史主义》,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1993年,第262-263页。
(18) 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