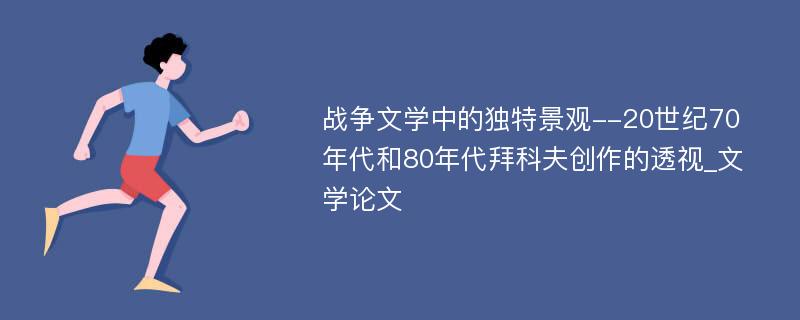
战争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贝科夫70和80年代创作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景线论文,透视论文,独特论文,年代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50和60年代前苏联当代文学中,以三位姓氏第一个字母是Б的作家为代表的前线一代作家,在真实地描写战争,描写战争中人的思想和心理,讴歌苏联军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等方面,无疑有了新的突破,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其中一位就是瓦西里·贝科夫。他以个人在前线的经验所写的《鹤唳》(1959)、《前线一页》(1960)、《第三颗信号弹》(1960)、《阿尔卑斯山的颂歌》(1963),在所谓“战壕真实”派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这位白俄罗斯作家从此驰骋在全苏的文坛上,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知名作家。
随着战争文学的发展,许多作家不断进行着探索和创新,到70和80年代,呈现了更为多元化的格局:既有描写“战壕真实”的作品,也有反映“司令部真实”的作品;既有全景式的史诗性作品,也有专注于道德心理的短小精悍的作品。在后者的创作中瓦西里·贝科夫在这期间接连发表的一系列中篇小说尤为引人注目,如《第三颗信号弹》(1962)、《克鲁格梁斯基桥》(1969)、《索特尼科夫》(1970)、《方尖碑》(1972)、《活到黎明》(1972)、《狼群》(1974)、《他的营》(1976)、《一去不返》(1978)、《灾难的标志》(1983)、《采石场》(1985)、《雾中》(1987)。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第三颗信号弹》、《狼群》、《他的营》曾获白俄罗斯国家奖金,《方尖碑》、《活到黎明》获全苏国家奖金,《索特尼科夫》改编成电影《升华》后获全苏电影节主奖,《灾难的标志》则获得了列宁奖金。他的作品在原苏联已出一百多版,被译成一百多种外语,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资料表明,贝科夫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谈论前苏联当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不可能不谈贝科夫的创作,他当之无愧地在前苏联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在描写战争的广度和深度上开拓
在前苏联当代文学中,战争题材是一股取之不竭的源泉,它所形成的潮流,一浪又一浪。在这一股股浪潮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作家,一位作家如在创作上没有特色,那么他的声音就会淹没在巨大的浪潮声中;即使他已取得了成就,如果没有创新和开拓,他的创作生命力同样会衰竭和消退。曾经一起在50年代开拓“战壕真实”文学的邦达列夫、巴克拉诺夫在60年代后,开始把战争题材和当代题材结合起来,战争已不再是他们描写的主体,而往往成为构成作品的插曲,如回忆和追叙。他们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当代的种种精神、道德、心理、传统乃至国际的问题,探索战争和当代的联系。而贝科夫依然坚定地以战争年代的生活为自己创作的中心题材。他说:“我继续写战争,因为我认为在人民的生活中,与军队、游击队、沦陷区生活相关的战争中,还有许多材料未为艺术家所掌握,特别是心理和精神、道德和伦理领域。”
确实,他这样做了,把自己耕耘的土地从前线战壕移到了很少有人反映的游击队和沦陷区生活。于是便有了游击队员去执行侦察任务而被捕(《索特尼科夫》),沦陷区的一对老农民如何在占领者眼皮底下生活(《灾难的标志》),游击队员护送伤员和孕妇回后方途中的遭遇(《狼群》),敌人占领下一个乡村教师的抉择(《方尖碑》),隐藏在敌占区的游击队员的经历(《采石场》)……等一个个故事。可以看出,吸引作家注意的并不是游击战争本身,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描绘游击队的战斗,没有描绘游击队不同于正规军的战略战术,没有描绘游击队除了战斗以外所特有的游击活动,甚至也没有去完整地描绘一支游击队的生活。游击队和沦陷区的生活虽然不像战斗前线那样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虽然没有战斗前线那样的规模和气势,可是它的生活和战斗与前线一样紧张和激烈,它所面对的敌人与前线一样凶狠和残忍,它所面临的生死抉择与前线一样尖锐和迫切。在某些方面那里的矛盾和冲突也许更为直接和深刻。这是整个战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如作家所说:“游击战争和沦陷区中‘选择’这一永恒的主题更为尖锐,它的解决也更多样化,人的行为的理由也更复杂,人的命运更丰富,往往也更悲惨……”这也就是说,作家把视线从战争的外部表现深入到决定战争的人的内部世界。
这样,贝科夫没有重复自己的创作,也没有原地踏步,在描写和揭示战争的广度和深度上他迈出了新的一步,从而在战争文学的浪潮中翻滚出一朵朵浪花,为战争文学增添了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
生死抉择的极端情境
战争中的人的道德抉择是处处存在、多种多样的,许多作家从不同方面描写了这种抉择,诸如邦达列夫在《岸》中就描写了克尼亚日科和麦热宁在对待爱玛姐弟和表示投降的德国童子军的不同态度,这种抉择的核心是人道主义。拉斯普京在《活下去,要记住》中描写的则是战争最后一年安德列·古西科夫伤愈后是回部队还是回家的选择。在全民命运和个人命运面前,在承担义务和享受权利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康德拉季耶夫在成名作《萨什卡》中描写的则是战士萨什卡在战时日常生活中遇到种种问题时所做出的选择,塑造了一个处处时时高度自觉的战士形象。总之,描写战争中人的道德抉择已成为70和80年代战争文学中的新倾向,是战争文学深入发展的标志。因此,贝科夫把注意力放到道德抉择上,并不是他个人独辟的蹊径。
那么,贝科夫究竟把什么作为描写战争中人的道德抉择的焦点?究竟写什么不至于重复其他作家呢?那就是极端情境下人的潜在的精神、道德面貌,这是作家选定的战争中人的道德抉择的焦点。
什么是贝科夫笔下的极端情境呢?受伤的列夫丘克随格里勃耶特赶的大车护送重伤员基赫诺夫和怀孕的报务员克拉娃回后方。途中他们遇到德国鬼子的袭击,伪警察的包围,偏偏克拉娃又在途中分娩,列夫丘克面临的是非常危险的处境。基赫诺夫不愿拖累大家而开枪自杀了,格里勃耶特和克拉娃也被敌人杀害了,只剩下列夫丘克一人,本来他能比较容易地逃脱敌人,可是却又面对着一个谁也不知道,大概也是谁也不需要的婴儿。撇下他,列夫丘克在谁的面前都没有责任,自己也安全得多;带着他,在周围都是敌人的险境中,列夫丘克就容易暴露自己,就多一份面临死亡的危险。他面前的婴儿不啻是对自己生与死的选择(《狼群》)。乡村教师莫洛兹面对的是这样的情境:他的学生破坏了桥,被敌人抓住了,敌人扬言要游击队交出莫洛兹,否则就绞死孩子,莫洛兹去还是不去?游击队长等人都认为,这是敌人的花招,只有糊涂虫才相信德国人会把孩子放出来,所以,去敌人那里等于是去自杀。队长甚至要以关禁闭来阻止莫洛兹前去。因此,选择去还是不去,也就是选择死还是生(《方尖碑》)。雷巴克与索特尼科夫去为游击队搞粮食,一路上的遭遇也可算处处是险境,雷巴克也都经受过来了,但是最后他和索特尼科夫还是落入敌人手中,面对着侦查官的审问,有两种选择:供出游击队的情况就可以活下去,可以当警察,否则就是死(《索特尼科夫》)。佐西卡去斯基杰尔执行任务,遇到了企图逃离游击队投奔敌警的安东。她对他颇有好感,甚至还和他发生了关系,面对安东的背叛意图,她或是服从他,用他的话来说是“为了日子过得更好”,过“正正规规的人的生活”,或是拒绝他,揭露他,但是那就会受到安东的死的威胁。佐西卡一样面临着生死的选择(《一去不返》)。
诸如此类,贝科夫描绘了一个个极端的情境,这种极端就在于,它是没有退路的非此即彼,是道德抉择的临界点,它最根本地决定着人的本质面貌,这个情境就是生与死。在战争中还有什么比生死更为无情的抉择?贝科夫让自己的主人公在各种不同场合下,单独去面对尖锐的生死抉择,也许是因为单独面对严峻的情境更能描写主人公的真实本质,因为在单个的情况下,谁也没有要求他怎样做,他也无需背负别人的压力,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意愿行动,也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才显现其真正的精神道德面貌。
极端情境下的潜在精神力量
对于不坚定的人来说,极端情境剥去了有的人的表层,露出其精神内质,它成为真假英雄主义,真假战士的试金石。对于坚定的人来说,极端情境则是其潜在精神力量的显示器。高尚的人也许平时是个显得很平常普通的人,然而到了关键时刻,却表现出英雄的本色。在贝科夫笔下,正面主人公往往是些很不起眼的人,甚至故意似的,他们在外表上都显得似乎是个弱者,乡村教师莫洛兹是个瘸腿,列夫丘克是个伤员,佐西卡是个缺少经验、单纯弱小的少女,《灾难的标志》中的斯捷潘尼达是个乡村老太婆。在这点上索特尼科夫更具代表性。可恰恰是这些看来孱弱的人却在极端的情况下显示了难以预料的惊人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体现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在行动上都是大无畏的,坚强不屈的,在精神上都是主动的,立于不败之地的。和雷巴克相对照,在同样的情况下,索特尼科夫表现出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力量。在遇到敌人追击时,虚弱的索特尼科夫落在后面,他明白自己马上要被人抓住,为了迅速制止最可怕的事态发生,他开了枪。他明白,他决不会乖乖投降。这种决心使他在受了伤预感到死亡即将来临的情况下,依然牵制住敌人,在脚掌到胯部失去知觉,浑身颤抖,眼前冒金星,阵阵恶心的情况下,做好一切准备,决不让敌人活捉。他为自己连累战友感到内疚,他怎么也不甘心承认自己为弱者,确实无能为力了,也要尽可能减少对别人的依赖,因此,他表示在找到农家以后他可以留下,免得拖累雷巴克。当他们被伪警抓住,焦姆奇哈被打时,他虽然非常虚弱,但极度的愤怒却使他迸发出全身的力气,大声喊叫,制止住伪警;在他的力气所剩无几的时候,他为焦姆奇哈开脱,拒绝讲出有关情况,与伪警唇枪舌战,公然咒骂;在他受了刑罚,极度衰弱的情况下,他还劝阻雷巴克当警察;他要拿出最后的力气,不失尊严地去面对死亡,将生死置之度外,获得一种特殊的、几乎绝对不为敌人暴力左右的精神力量,要在目前处境下去做他能做的事:承担一切,开脱别人。他要使死肯定某些东西,否定某些东西,可是现实根本不可能实现他的愿望,他无力自救,更无从解救别人。这时他给自己又定下了最后的目标——带着一个战士的尊严去迎接死,不能有丝毫的恐惧和惜命的表现。他甩开雷巴克扶着他的手,异常吃力地走向绞架,自己爬上木墩。索特尼科夫虽然在肉体上更加衰弱,然而他的思想和行为给人的感觉却是个强者,强过敌人,更不用说强过雷巴克,潜藏于虚弱身躯的内在精神赋予了他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正如小说中所写:“固然,一个人肉体的力量是受它本身条件所制约的,但是谁能限制他发挥精神的力量呢?当一个完全丧失各种能力的人,仍然能够爆发出大无畏的压倒一切的精神威力时,又有谁能计算出他在战斗时的英勇程度,以及他在敌人面前所表现的无畏与坚定的精神呢?”
贝科夫把注意力放在揭示人的潜在的精神道德因素,并没有把这种潜在的精神力量写成是一种偶然的突发的因素,而是着力展示这种潜在精神力量的基础和源泉。索特尼科夫在垂危时回忆起童年不是没有理由的。有三件事是索特尼科夫终身铭记的。第一件是童年时,他偷玩了父亲禁止他动用的毛瑟枪,打出了子弹,母亲让他向父亲承认自己的过错,他向父亲说是自己想这样做的,这虚假的回答却换来了父亲的“谢谢”,这使他非常愧疚。从此他记住了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再也不撒谎,敢于正视对方的眼睛,也为自己的话负责。第二件事是他曾经被德国人俘获,可是一位白发苍苍的红军上校在受审中坚强不屈的表现,令敌人也敬畏三分,虽然最终上校还是被枪杀了,可是索特尼科夫却觉得他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使他终身难忘。第三件事是在战地集中营他逃跑未遂被押去枪毙。可是腿部头部受伤、发着高烧、走路要人扶的中尉,却乘敌人不备用一把小折刀刺死了身强力壮、结结实实握着冲锋枪的押送兵,造成了众人逃跑机会,这个似乎只能坐以待毙、却以死相拼的中尉也成为索特尼科夫的榜样,他也凭着那种勇敢和拼命的精神从骑马追赶的德国兵眼前死里逃生。正是这种种精神的道德的教育和影响,使索特尼科夫也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境下英勇顽强从不屈服。在炮团受到重创、伤亡惨重、情急境危时,他英勇地击毁了敌人两辆坦克。在游击队里他依然是一名自觉的战士,在前面有两人找借口拒绝接受任务时,他虽然有病在身,却毅然受命。“正因为他们拒绝了,我才没有拒绝”,多么质朴的话语,可是却反映了他的崇高境界,在极端情境下他能发挥巨大的精神潜力,是长期精神道德锤炼的必然结果。
平凡的英雄主义
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家总是在作品中颂扬英雄主义的精神,而历来人们对于战争中英雄主义的理解总是与打死敌人,击毁敌人飞机、坦克,炸掉敌人碉堡等英雄业绩联系起来,这是传统的英雄观。战争中涌现许多这样的英雄人物,文学中也塑造过许多这样的形象,这样的英雄也教育和鼓舞了许多人。但是,随着人们对战争的认真思考,对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的深入认识,人们发现战争中并不是人人都有建立英雄业绩的机会,并不是人人都有手擎红旗插上高地的可能,他们更大量、更普遍地所做的似乎是并不起眼的行为和事情,战争中这些平凡的人所做的平凡的事是不是英雄主义?
《方尖碑》中争论的问题就是莫洛兹算不算英雄。按现任教育局长的话来说:“他究竟有什么功?他打死过一个德国人?”“我看不出这个莫洛兹有什么特殊的功勋。”而老教育局长特卡丘克却认为:“他做的胜过他打死一百个德国人,他献出了生命,是自愿献出的。”莫洛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战争中他究竟做过什么事?莫洛兹是乡村教师,他把培养学生成人看做是自己最崇高的职责,而这只有在师生相处过程中身体力行才能做到,因此,他虽是个瘸腿,却亲自带领学生准备柴禾,锯啊劈啊;他培养学生热爱动物,把不知从哪儿来的两条小狗崽和一只失落的椋鸟养起来;他说服家长让孩子上学,为了让家长放心又送学生回家;他收留经常挨家长打的学生,当家长通过法律要接孩子回去,可是仍然殴打孩子时,莫洛兹挺身保护了孩子;他帮助学生家长做事,学校新建,什么都缺,连教科书、图书都缺,他四处奔波,甚至因此陷进冰窟窿病了一场,可他躺在床上还给学生们念托尔斯泰的著作,他认为生病一个月耽误的全部课程加在一起也抵不上托尔斯泰的两页书;他还管课余的文艺活动,学生亵渎了祭坛,教士和信徒要求惩办学生,莫洛兹承担了全部责任,作了检讨;谁有什么困难或麻烦事,都去学校找他,他则有空就为大家奔走。战争开始后,他继续教学生,认为应该教,“我们不教育孩子,他们(指敌人)就愚弄孩子……我还将为孩子们战斗”。他搞到一台收音机,就收听新闻,为游击队传播消息,也为群众。孩子们偷偷实施向伪警“恶魔”报仇的行动,结果被敌人发现,抓去了,敌人扬言要是莫洛兹去,就放孩子,莫洛兹虽然不相信敌人骗人的花招,但为了孩子,不顾生命危险,不顾别人劝阻,自愿前去投案,结果被敌人处死。莫洛兹在游击队就两天,他没有参加战争,也没有打死过一个德国鬼子,他的死有什么意义?真如有的人认为的那样是“傻瓜”,是去送死吗?莫洛兹这样做是为了粉碎德国人说苏维埃当局“让别人替他们打仗,把孩子们当牺牲品”的诽谤,为了安慰哭哭啼啼的母亲们,为了减轻孩子们的痛苦,免受严刑拷打,为了鼓舞孩子们英勇地面对死亡,也为了尽可能帮助孩子们,他后来使米克拉维奇逃跑了。他的行为是崇高的,他的人性的力量是永恒的,他的榜样是不朽的。莫洛兹建立的是无法估量的精神道德功勋。在莫洛兹精神的影响下,活下来的米克拉维奇继承了事业,在和平年代做出了新的成绩,受到了人们的尊敬。
贝科夫笔下的主人公总是些平凡的人,莫洛兹、列夫丘克、索特尼科夫、佐西卡等无一不是战争中的普通一员,作家不仅通过直接参与战争的普通战士来显示平凡的英雄主义,更把笔端深入到沦陷区的普通群众,在反映战争时期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的同时,描写普通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从而使人们对英雄主义的理解更为深刻了。
《灾难的标志》中的斯捷潘尼达像莫洛兹一样,没有打死过一个德国人,她甚至没有像莫洛兹那样为孩子挺身而出并解救了一个孩子,她所做的只是她力所能及的事,她用自己仅有的财产来与敌人作斗争,最后又以生命来抗击敌人,这是她所能做的极限。她所做的一切弄得敌人不得安宁。她以她特有的斗争方式打击敌人,这是与前线部队作战、游击斗争和地下活动一起构成的整个抗击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即使后方的敌人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是敌人是无法征服斯捷潘尼达这样的基层群众的。
斯捷潘尼达的形象是与青年近卫军的年轻英雄们,与马特洛索夫式的战斗英雄们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她与那些英雄们一样表现出勇敢、坚定、英勇的精神,难道能说她的行为不是英雄主义?
精悍简练的形式
贝科夫除在创作早期曾经写过一些短篇小说,50年代末开始发表的作品,全是中篇小说,作家本人说过:“中篇小说是很好的体裁……它没有令人厌倦的多余的东西。”他用中篇小说的体裁精炼紧凑地表达了丰富深刻的思想,塑造了鲜明的形象。
贝科夫的作品,从情节来看都比较简单,描写一件事,一条线索,所描写的空间和时间也都比较有限。但是作家善于通过对一件事的叙述反映多方面的生活,常常用时空交错的手法,拓展叙述的广度和深度,提出具有永恒意义的问题,从而使其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具有了丰富的内涵。《采石场》通过阿格耶夫来到采石场挖掘战争中几位牺牲者的尸骨,引出主人公在战争期间的一段经历。在当时来看,阿格耶夫似乎并无过错,因为他有伤在身,他要取得地下组织的信任,玛丽亚自愿代他去完成任务。但是几十年过去了,阿格耶夫从今天的立场,从良心和人性的高度来审视自己过去的行为,谴责自己轻率地对待了他人的生命。《雾中》则描写了游击队员布罗夫及其助手沃伊季克对“叛徒”苏谢尼亚的不同态度,通过对沃伊季克经历的回顾,使人们看到了30年代肃反扩大化中沃伊季克的真实面貌,也更认清其对待苏谢尼亚态度的道德本质。而苏谢尼亚在战争的环境下身不由己地背上黑锅,两名游击队员的牺牲又使他陷于洗不清道不明的境地。他决心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说作家以前作品中提出的是面对敌人的生死问题,那么在他的这两部新作中则是把良心、人性、人格、信任与生命放在一起思考,历史的往事变成了探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源泉。在他的作品中有许多关于生死、善恶的思考和议论,充满了哲理,也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容。
贝科夫的许多小说都采用了相互对照的主人公,在相互对照中使主人公的正面或反面形象更加鲜明,而且作家常常用欲扬故抑的手法,赋予正面主人公柔弱、反面主人公强壮的外在特征,使人物性格更加突出。索特尼科夫—雷巴克,佐西卡—安东,就是这样的主人公。贝科夫在创作中用了较其他作家更多的注意力来塑造反面主人公,应该说,这些反面主人公的形象,不仅在情节上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对于塑造正面主人公,揭示思想内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与正面主人公是相辅相成的。
贝科夫在采用对照手法的同时,也很长于描绘人物的心理,如对索特尼科夫在被带去行刑时的描写。看到绞索,索特尼科夫先是感到万分憎恶,接着则是怒火中烧,内心发出抗议。他不愿意让人家看到自己全身瘫软无力、模样难看、一声不吭地死去,揭示了他对敌人的憎恨和大无畏的气概。接着他暗自劝说自己要沉住气,要处之泰然,丝毫不能有恐惧和惜命的表现,将此看做自己的最后职责,进一步揭示了他的高度责任感。然后他疲惫地走到绞架柱子前,想的是,在丧失最起码的力量奄奄一息时,还能做什么?他想到唯一能取决于他的就是问心无愧地保持着人应有的尊严离开这个世界,这便是他的最后奉献,充分展示了他潜在的精神力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用惜别的眼光看着周围的景象,大自然,人们,特别是一个戴布琼尼帽的十二三岁的小男孩,他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希望孩子不把他当做坏人,而从孩子眼中他感受到深沉、悲痛和无限的同情,他不由得用眼睛对男孩微微一笑——表现出他的视死如归和信念。作家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把索特尼科夫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不由得对这样的英雄表示由衷的敬意。
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语动作来刻画其性格,也是贝科夫常用的手段之一。比如对佐西卡,作家没有描绘多少外表,但是一开始就通过“小心翼翼”、“慌不择路”、“提心吊胆”、“忐忑不安”、“惊魂不定”、“战战兢兢”、“紧张心情”、“吓得发呆”、“慌慌张张”这一连串的词汇描写这个女游击队员孤身执行任务的路上的表现,使我们一下就感到这是个缺少经验、势单力薄、需要有人保护的软弱的姑娘。又如斯捷潘妮达第一次在家里遇上伪警古什。短短的对话,眯缝着眼,咄咄目光,一个坚强、勇敢、机智、不屈、蔑视敌人的形象就跃然纸上。类似这样的描写还有许多,使形象显得非常生动,个性显得非常鲜明。
阅读贝科夫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常常采用今昔相叉的结构。例如《方尖碑》是从悼念米克拉维奇开始引出了关于莫洛兹的话题,由过去的区教育局长对莫洛兹的回忆展开情节的。《狼群》是从30年后列夫丘克来寻找当年救护下来的战友的遗孤开始对战争年代的追忆的。作家一再地用这种回溯和交叉的叙事结构,不只是一种创作手法,更多的是服从了作家的创作意图,因为作家不止一次地强调,他之所以写战争,就是为了使人们从过去的战争中吸取崇高的精神,培养起高尚的道德品质。
“战争时期英雄主义是决定性的主要的问题,大胆、勇敢、蔑视死亡——是决定军人人格的基本品质,但是在和平时期我们不用去侦察,也不要求我们蔑视死亡,只是在非常情况下才需要勇敢,但是,战争中潜藏在英雄主义后面,孕育了英雄主义,成为英雄主义基础的东西——难道失去其作用了?是的,我们今天不用去侦察,但是这一情况并不妨碍我们现在珍重同伴身上的正直,忠于友谊,英勇精神,责任感,现在我们需要原则性,忠于理想,自我牺牲——就是现在这也决定着我们的精神道德,就像在战争年代它培养英雄主义一样……文学应该不停地敲响自己的钟声,执着地唤起人们对高尚精神的渴望,缺少这一点,任何最高级的物质文化的进步带来的将不是愉快的事。”贝科夫的作品感染力也在于此,它们不只是让我们崇敬他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主人公,更使我们在精神上得到一种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