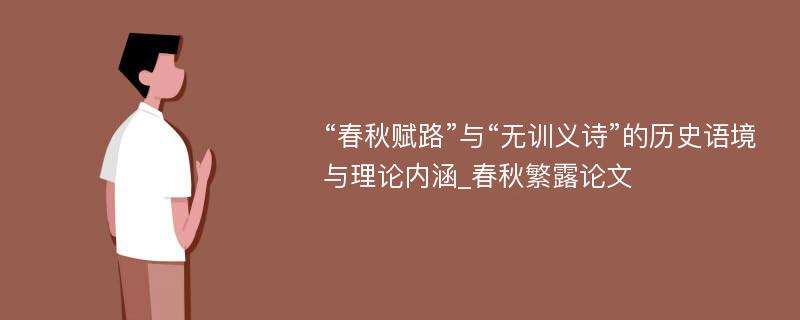
《春秋繁露》“诗无达诂”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春秋论文,内涵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人多有借助西方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来推重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篇中提出的诗学命题“诗无达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领域中也颇有对这一简约明快的理论归结津津乐道者。理解和阐发《春秋繁露》中的“诗无达诂”这一诗学命题,自然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而仅停留在字面上去望文生义,例如在对“诂”的认识就有简单化的倾向,甚至曲解和误读。若单从现代文艺美学的层面来理解这一诗学命题,由于偏离了汉代思想史、经学史的实际脉络和内容,脱离了《春秋繁露》内在的本文线索,也不能把握董仲舒提出这一诗学命题的深刻内涵,造成不必要的误解。下面,本文尝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诗无达诂”进行梳理和阐释。
一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篇中有:“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人”,卢文弨作“天”)。梳解“诗无达诂”这一诗学命题,首先要回到董仲舒当代的历史语境当中,在具体的汉代经学史、诗经学史的脉络中来理解这一诗学命题。(注:此处“经学史”,取徐复观先生的观点:“经学史应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经学的传承,一是经学在各不同时代中所发展、所承认的意义”。见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自序》,《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页。)因为董仲舒“诗无达诂”这一诗学(确切地说是诗经学或《诗》学)命题,针对的主要是《诗》三百和诗学现状;其内涵也是在这一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线索中得以呈现的。
西汉前期学术文化的面貌、格局相对于“百家争鸣”、“焚书坑儒”而言,已是渐行渐远,逐渐展现出自己的特质。汉初承续的是“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的凋敝现实;经过汉初的文化建设工作之后,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史记·太史公自序》)汉初的朝野上下,庙堂江湖,一起为学术文化的复兴努力,朝廷“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武帝诏令“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即使在僻远的蜀郡,在太守文翁的笃力践行儒家理想的情况下,也出现了“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的盛况。(《汉书·循吏传》)儒学经术在这一大格局中也获得了其命维新的契机。
学说学术还没有与大一统的政治权力绾结在一起之时,百舸争流的局面是难免的。汉高祖不喜儒术,文帝、景帝好刑名黄老,此时丰富的思想和学术潜流则厕身在藩国诸侯王对中央政治权力的割据当中,并较广泛地流布在民间。异质、异趣的学术得以并存。司马谈昌论六家要旨,辨析是非高下,成为学术文化进一步调适发展的必然诉求。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厥协六艺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等都具有明显的旨归。可以说,“异传”、“杂语”的涌现正体现了董仲舒所在的前大一统时期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这成为西汉多家诗学系统得以存在的思想底蕴,也是我们今天考察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这一诗学命题的前提。正如朱东润先生所言:“欲求汉人之文学批评,当知武帝以前,学术未统于一家,故论文者,张皇幽渺,各出己见,及武帝罢黜百家而后,立论之士必折衷于儒术,文学始于合而为一,故武帝时代,实为古今断限,不可不知也。”(注: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4页。)
董仲舒面对的前大一统时期的诗学呈现什么样的格局、状态呢?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有言:
至孝文皇帝……《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成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
《诗》、《书》为六艺统宗,曾经历了一个从掌于王官之学,到流播于民间的过程,其间《诗》、《书》之学等并不为儒家之学所专有。至汉兴,“《诗》始萌芽”,经学逐渐与政治权力结合,从民间向学官回归,传经之学成为进身之阶。此时百家学说并立的思想界在诗学领域内打上了深深的印迹,“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则说明了诗学在勃兴前经历了一个艰苦的酝酿、准备期,此后才如缕不绝地传承下去。
单就大的诗学格局而言,除立于学官的鲁、齐、韩三家诗外,还有毛诗,当然还可能存在别的一些在野的、被主流推至边缘的诗学——地域文化的丰富性使得这一时期的诗学极有可能是百家腾跃。(注:《汉书·艺文志》所录诗经学著作,经过了刘向、班固等的别择去取,不尽囊括一代所有。例如,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竹简《诗经》,在文字上即与四家诗不同,参见洪湛侯:《诗经学史》(上),中华书局2002年版。另《汉书·楚元王传》:“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史记·儒林列传》:“申公者,鲁人也……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汉书》作“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由此,可推论不同的地理地域下的诗经学当有更复杂的情形。《诗》学作为学术典范得以确立,以一统的姿态传播远方乃至全国,需要一定的历史机缘;毛诗的后来居上,三家诗的逐渐消泯可作如是观。)即以立于博士的三家诗而言,三家诗学的学术状态在班固看来也是“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汉书·儒林传》)暂且抛开班固衡论诗学“本义”的依据是什么这一问题,他确实为我们勾勒出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的面貌。综合而言,诗经学所呈现的总体情况正如清代四库馆臣总结的那样:“诸经之中,惟《诗》文义易明,亦惟《诗》辨争最甚。盖诗无达诂,各随所主之门户,均有一说之可通也。”(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虞东学诗”条后“案语”,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136页。)三家诗学各有承传的系统,面相不尽相同,即使在一家之中也有分野。如鲁诗中“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学官弟子在治学上“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史记·儒林传》),这说明即使治学有所本,但具体到治诗过程中,言诗的“殊”和差异还是不可避免的。
西汉诗经学呈现出来的这种局面,一方面是由于研讨的对象是今天看来为抒情、审美凝结的文学文本;而由这一文学文本进行历史真相的追寻,歧义杂出自然难免。如三家诗中仅存的《韩诗外传》,“其书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注:《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六,“韩诗外传”条,第136页。)一方面经历了燔书之祸后,继起的地域文化为释解《诗》注入了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理念,如赵人毛公所传的毛诗系统即宣称自己乃是得子夏正传,并得到了河间献王认可;加上功令的驱使;自然会形成了不同面相的诗学门户、系统。再者,更为重要的则是经学——诗经学自身的原因,“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为不确定”,“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期广泛难征之结论”。(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269页。这篇序言论及清世史学之不振的原因,对经学进行的检讨。陈先生此论对我们省思西汉董仲舒当代的经学特点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诗无达诂”,就其传达的历史内容而言,无妨看作是董仲舒对周秦,特别是汉兴至武帝时期诗经学历史的一个归总和陈述。当然,“诗无达诂”这一理论命题陈述的内容,主要还是在概括释解《诗》文本过程中的现象。正如清代学者总结的,诗三百是“文义易明”的,也是论争最甚的,那么,解诗过程中的方式、方法则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需要我们对“诂”、“传”等关键词进行厘定。
许慎《说文解字》:“诂,训故言也”。就董仲舒之时而言,“诂”所涵括的内容,是有其特定的时代内容的,并不能简单地以“以语言解释语言”(近人黄侃)来理解,也不尽如孔颖达所言的“诂者古也,古今异辞,通之使人知……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于此”(《诗·关雎》疏)。“诂”在董仲舒当代自然与语言上的训释有很大关系,但并不乏史实、义理的推阐和求索。其与诗经学中的“传”虽有别,但二者的联系似异常紧密。如班固在《汉书·楚元王传》中有:“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汉书·儒林传》则有:“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从班固这两段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申公始为《诗》传”和“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两者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别。
另《汉书·艺文志》有: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班固在这里对三家诗有一个总体的判断,“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为诗训诂”的鲁诗与“皆为之传”的齐诗、韩诗有一定的距离,“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班固显然更认同鲁诗,“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
司马迁《史记·儒林传》则认为,韩诗“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司马迁眼中,韩诗与齐、鲁二家之诗倒是拉开了距离,齐、鲁二家亦可放在一起并列,并且三者“其归一也”,这也无妨理解为一个整体的判断。司马迁、班固对三家诗的整体判断上是一致的,“其归一也”,“咸非其本义”。解诗过程中的“诂”和“传”的差别在更高层面的意义上是可以相通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列有《鲁故》二十五卷,颜师古注曰:“故者,通其指义也。它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故(诂)即有“通其指义”的内涵。
汉代诗经学中“传”的释解方式同样渊源有自。晚清学者陈澧据《荀子》文,推论周时的《国风》已有“传”;又据《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诗》传之语,认为这些都是不知何时的“传”,“《礼记·坊记》、《中庸》、《表记》、《淄衣》、《大学》,引《诗》者尤多似《外传》。盖孔门学《诗》者皆如此。其于《诗》义,洽熟于心,凡读古书,论古人古事,皆与《诗》义相触发,非后儒所能及”。(注:陈澧:《东塾读书记》“六·诗”,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第107页。)“其于《诗》义,洽熟于心,凡读古书,论古人古事,皆与《诗》义相触发”,表明了“传”对《诗》的释解方式和方法。这样来看,“通其指义”的“诂”和“传”二者只是在解诗的过程中侧重不同而已,其旨趣、宗旨上则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三家诗都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我们无妨从博士这一学官的传统来观照董仲舒当代解诗过程中的精神指向。(注:关于博士这一学官的传统可参王国维的《汉魏博士考》和钱穆的《两汉博士家法考》。)辕固曾就汤武受命与否的问题,“与黄生争论于上”;韩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年已八十余的申公,武帝仍“问治乱之事”。(《汉书·儒林传》)三家诗都有秦时博士的“掌通古今”,通经致用的精神指向。诗学的旨趣和精神指向并不为诗经学术所囿,通古议今还是其精神命脉。这是因为《诗》作为先秦两汉文化中突出的要素,不单是作为文学审美的文本(“兴于诗”《论语·泰伯》)而存在,主要承担着基本的社会文化教育、交流的功能(“不能诗,于礼缪”《礼记·仲尼燕居》),并作为重要的语言修辞手段(“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当然,诗学作为巨大的思想文化资源也是参与政治思想建构的重要力量,即所谓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论语·子路》)。朱熹《论语集注》中对此充分的说明:“《诗》本性情,该物理,可以验知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和而平,长于讽喻,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第143页。)这样来看,董仲舒所谓的“诂”,与我们今天把《诗》三百作为文学文本来进行审美方式的解读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诗无达诂”既可以作为诗学历史和现状的一个归结,也同时是董仲舒进一步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推明义例,说明“从变从义”的理论工作。下面,我们来进一步探讨“诗无达诂”的理论内涵。
二
刘勰《文心雕龙·议对》篇中有“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慁,事理明也”,对董仲舒文体上的才能推重有加。钱谦益一生服膺董仲舒的“析理精妙”,认为他能会通孟子、荀子二家学说,“非有宋诸儒可幾及也”。(注:钱谦益:《跋〈春秋繁露〉》,《牧斋有学集》(下)卷四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但,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在研读《春秋繁露》过程中有如下观感:董仲舒的对策及《春秋繁露》中时时流溢出一种内在的焦虑,即言说过程中的省思和警觉——语言表达和理论建构、指向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这在《春秋繁露》诸多篇目的往复答辨中尤为突出。例如:“《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春秋繁露·精华》),《春秋》“甚幽而明,无传而著”(《春秋繁露·竹林》)等等。董仲舒由《春秋》而阐发、推衍的关切现实政治,关乎儒家学说走向的理论,正是在这些可言说与不可言说,易与不易,常与变之间得以建构起来的。
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董仲舒有诸多相反而相成的言辞表述;而这些看似矛盾、牴牾的言辞,要成为一贯的理论结构,极需要一个理论上的疏通和说明。这集中表现在董仲舒在《精华》篇中回答“难晋事者”问辩《春秋》之法时所提出的“《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论断中。这一言简意赅的论断,在董仲舒的理论建设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为其理论的进一步阐释找到一个回旋、缓冲和提升的空间。
语言文字,是共有的表达、交流的工具——武帝时期的人主者、臣下和民众都在使用它,以了解、认识、获取公共的知识和观念。理论的表达,尤其是饱含命意的政治理论的建设和传达,则显然是属于言说者个体的。当这一具有神秘、天启性质的理论,通过“道之管也”的言说个体,在汉帝国社会政治体制特别是武帝的允可下传布到汉帝国社会文化的公共空间时,言和意之间的关系如“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春秋繁露·竹林》),对于“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专儒”(《文心雕龙·才略》)的董仲舒来说,不尽表现为庄周式的玄思层面上的哲学的痛苦,更成为关联到社会中的个体生命(当然也包括了理论言说者)和帝国政治结构中儒家学说的盛衰兴亡的问题。(注:类似于董仲舒的理论言说对人君产生相当大的作用。参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汉儒言灾异”条。当理论学说关切到现实政治时,往往在可言说和不可言说之间,而理论言说主体的处境颇值得我们去关注。在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之时,董仲舒尽管居于家中“推说其意”,不但理论上被不知其情的弟子吕步舒“以为大愚”,且有当死之罪;虽“诏赦之”,但“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董仲舒显然有“含得命施之理,与万物迁徙而不自失”的“圣人之心”(《春秋繁露·天道施》),并没有放弃理想的政治理论的建构。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对语言或《春秋》义例的警惕性——一方面多方面地加以限定,又极力拓展属于己意的表达空间和深度,以便符合自己的命意和政治理想。
诗学或诗三百,作为所谓的“六学”之一,在《春秋繁露》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中有“《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且表述了《诗》和《春秋》的功用和特质:“《诗》道志,故长于质”,而“《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之学作为“正是非”、“长于治人”的功能在董仲舒那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即如刘勰所言的“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依此来建构政治理论。
“长于质”的《诗》则在董仲舒进行政治理论建设中发挥道(序)志、达意、正言的作用。对《诗》这一功能的认识是汉代的共识:
陆贾《新语·慎微》:
故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矫以雅僻,砥砺钝才,雕琢文彩,抑定狐疑,通塞理顺,分别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
贾谊《新书·道德说》:
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
司马迁《史记·滑稽传》:
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
反观以上诸论,《诗》正是作为道志、达意、正言的功能出现。班固所言的“诗以正言,义之用也”,司马迁所说的“春秋以道义”,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看,可以理解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诸多引诗的现象,以及“诗无达诂”与“春秋无达辞”两者内在的关联性:《诗》,在推阐《春秋》大义的过程中发挥“用”的功能,而“诗无达诂”是表达“春秋无达辞”的一个顺理成章的过渡。
正如今天学者所认识的那样,人们“所引诗句,不论在讲论之前,或在讲论之尾,无论断章、意解,都是首先预设了‘诗’作为经典文本的权威性,都是用以加强言论的说服力量,都是以诗经作为被称引的论据”(注: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第166页。)。《诗》既然作为思想文化领域内公共的经典文本,那么对它的训释、阐发自然就会随着不同的思想文化背景、不同的运用场合而产生相差甚远的别异。自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诗无达诂”,也是有其鲜明的理论内涵和命意的。“诗无达诂”是在说明“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这一理论层面的合法性,其功能正如贾谊在《新书·道德说》中所言的“《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三致其意的是天的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建构;而“无达诂”所滋长的歧义杂出——“变”则尤其是需要用“义”来限定的,由此董仲舒接下来即用“一以奉人(天)”来归结。“诗无达诂”所要传达的理论内涵,在董仲舒所给予的语境和本文中得到了积极的限定,以服从更高层面的达意的要求。现代西方解释学的立论基础则是文本的意义超越其作者,“这不是暂时的,而且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止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注: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前言”,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页。)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接受者创造性地去解读他的文本则显然不是他所期望和预设的。
下面,我们再回到“诗无达诂”所在的篇章语句当中:
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天)。
其中“所闻”,即“谓闻之于师”;“汉世治经,最重师法,盖古道之遗也”。(注: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12月版,第14页。董仲舒称引前言,并不在少。如“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与《管子·形势篇》:“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诸今”,虽然董仲舒略去“今”这一环节,但两者在义理、文辞上可谓一脉相承。)由此可知,董仲舒在这里所言的“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者,自有学术思想上的师法传承,并非是董冲舒一人直接的空前的创构。司马迁曾亲闻《公羊春秋》大义于董仲舒,并有“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的叹服之语(《史记·儒林传》);但对董仲舒的诗学修养的渊源则没有提及。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虽引诗处颇多,但其诗学属于哪家系统在这里只能付诸阙如。清人陈乔枞《齐诗遗说考叙》以董仲舒通五经,治《公羊春秋》,“与齐人胡毋生同业”,即认为董仲舒“则习齐诗可知”。按《汉书·胡毋生传》:“胡毋生字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其实,《汉书》所载的“与董仲舒同业”并非有同师受业之意(注:徐复观先生以为“与董仲舒同业”,是共同治《公羊春秋》的意思,驳斥凌曙《春秋繁露注序》董仲舒和胡毋生有师徒关系。《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陈乔枞据《汉书》,以为董仲舒“与齐人胡毋生同业”,而推论董仲舒习齐诗,则同样是不可取的。
董仲舒“诗无达诂”这一诗学命题,还应当放在董仲舒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人性论、性情论的语境中来理解。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降及后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有求端于天之意。”(注:赵翼著,王树民校正:《二十二史箚记校正》卷二,“汉儒言灾异”,中华书局1984年1月版,第40页。)董仲舒哲学思想中最为突出的是建构起“天—人”的理论结构。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其一):“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人的“喜怒哀乐之止动”,是“天之所为人性命”,需要“临其时而欲发其应,亦天应也,与暖清寒暑之至其时而欲发无异”。(《春秋繁露·如天之为》)作为性之符的“情”是受“天”、“时”的限定的,是一个“应”的关系。属于“天之所为人性命”的个体的“情”,就其与“天”,与理想人格、个体养生的关系而言,还悬一个不自由,需要加以限制,没有解除束缚的因素。
董仲舒希求以“天德”来约束人群,并以“圣人”作为诱进:“我虽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其心以求其当,然后发庆赏以立其德。虽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其心以求其政,然后发刑罚以立其威。常若是者谓之天德,行天德者谓之圣人。”(《春秋繁露·威德所生》)董仲舒正是以外在的天的合理性和规范性,“和其心”,“平其心”,以期达到一个“天德”、“圣人”的境界。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君和臣民等一概需要的是“应”,与外在的合理秩序相“配”,做到“不失其时”;“喜怒之发,威德之处,无不皆中其应,可以参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时已。故曰圣人配天。”(《春秋繁露·威德所生》)
“怒则气高,喜则气散,忧则气狂,懼则气慑”,由此,董仲舒主张“君子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忧则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则反中而实之以精”,更加突出强调了“中和”的观念,(《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从养生的角度而言,董仲舒认为“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要“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气多而治,则养身之大者得矣”,而“气”与人情相应,不能过分向外逸散。(《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人性内在的喜怒哀乐并非要泯灭掉,当然还是需要“发”的。但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的因素,更需遵循外在的秩序,合理、合适地发出,即所谓的“喜怒之有时而当发,寒暑亦有时而当出,其理一也”。于是,董仲舒提出了“安其情”的主张:“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春秋繁露·天道施》)
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大方向在于“求端于天之意”,其思想体系中的个体与后世的审美抒情——如曹丕的“文以气为主”,陆机的,“情瞳眬而弥鲜”、“诗缘情而绮靡”,刘勰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的“神思”等——有本质上的区别。董仲舒所持“安其情”的主张,与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的“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是有着莫大的距离的。所以,诗在董仲舒那里如果有抒情成分的话,也是属于公共空间里的抒情,带有强烈的理智色彩。董仲舒《春秋繁露》称引的《诗》句,都在为自己阐述《春秋》大义找到“正言”的依据,可谓冠冕堂皇,顺理成章。《诗》,这一经典文本被当作董仲舒进行思想建设的刍狗,被当成不同场合下文饰言说的工具时——这一理性化、工具化、充满了目的性的解诗运动,自然与后世有所不同,也不如原始儒家所言的诗学思想如“兴观群怨”等那样完满、充盈、活泼。
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与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的“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比较而言: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更加倾向于理智层面,传达的内容是纷纭的诗学现状;它是为理论上说明“春秋无达辞”而存在的,其理论的命意还须回到文本方能得以确立的,与读者创造性的多元化理解是相悖的。刘勰《知音》篇中的内容则是从文学审美主体的角度着眼:“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在此基础上,刘勰还提出了“将阅文情,先标六观”的理论以确定释解文本的优劣。如果从主体性或文学接受者的角度来解读“诗无达诂”,对董仲舒的整体思想而言是勉为其难的,是一种曲解甚至误解。所以,董仲舒“诗无达诂”所蕴涵的理论价值自不能以后世诗学观念来考量,虽然这一诗学的理论归结是如此的醒目、简约、明快。
标签:春秋繁露论文; 董仲舒论文; 儒家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读书论文; 汉朝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汉书论文; 博士论文; 西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