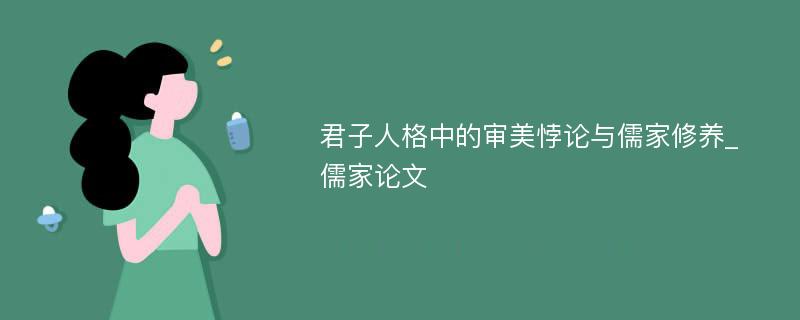
君子人格与儒家修养中的美学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悖论论文,美学论文,君子论文,修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4-0018-06
1
有效地调和人生的各种矛盾,实现人生在现实世界中的内在超越,是儒家思想的一大特色。儒家思想的这种内在超越理念,与世界上各大宗教的外在超越理念不同,它不是强调“在社会和人世间之外提高精神修养”,而是强调“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1]301各大宗教外在的超越目标是上帝或佛陀之类的有人格的神,儒家内在的超越目标是君子和圣人之类的理想人格。
如果我们把具有各种社会关系的世界称之为现实世界的话,那么超越各种社会关系的世界就是超现实世界。事实上,超现实世界只是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人构想出来的。①这种根据思想逻辑构造起来的超现实世界有自身清楚明白的起点,也许还有自己清楚明白的终点;但兀自存在的现实世界则处于各种矛盾纠葛之中,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它在哪里终结。儒家思想的对象就是这个充满矛盾纠葛的现实世界,以及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中存在。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君子,其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产物,是维持了各种矛盾关系的综合体。
对于现实人生中的各种矛盾,没有任何科学思想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就像戴维·奥本(David Auburn)的剧本《求证》(Proof)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Catherine)那样,具有卓越数学天赋的她可以完成惊人的数学求证,却无法摆脱情感纠葛,无法走出生活困境,无法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求证。人注定生活在矛盾之中,只能在各种矛盾的张力之中寻找一种暂时的平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没有关于现实人生的科学甚或哲学,只有关于现实人生的艺术。因为任何科学或哲学思想都建立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它们都得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都不能容许矛盾;能够在各种矛盾中求得暂时平衡的,是一种高超的人生技艺,一种人生艺术。因此,我们说儒家修养和君子人格中的悖论实际上是一种美学悖论,对这种美学悖论的最好解决方式不是科学或哲学,而是艺术。
2
《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们可以将这里的“文”与“质”的矛盾笼统地理解为文化与自然的矛盾,文化与自然的矛盾又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进取与归隐的矛盾。只有在有效地克服自然与文化、归隐与进取的矛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君子人格。
我们通常都是在与道家的“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的对照中,来确立儒家君子人格的特征。在这种儒道对照的框架中,儒家理想人格的典型特征是积极进取,用《周易·乾象》中的话来说,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道家理想人格的典型特征是消极归隐,用《庄子·逍遥游》中的话来说,就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里,自强不息的儒家君子形象,与无为而治的道家至人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可以找到大量文献材料来支持这种对照。比如,我们在一些儒家经典中,可以看到大量的不断超越自我的论述。《论语·为政》记载的孔子言论最为典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从这段自白中可以看出,孔子的一生是不断超越的一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生命不断攀越至更高的境界。《孟子·尽心下》在描述人生境界的时候,也充分体现了儒家的这种不断向上或向前的自我超越精神:“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里的善、信、美、大、圣、神就是一个个不断上升的人生境界。
与这种不断向上或向前的自我超越相反,道家主张不断向下或向后的自我还原。《庄子·大宗师》记载仲尼与弟子颜回的一段对话:“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它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它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枝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当然,这里的仲尼和颜回都已经道家化了,不再是儒家人物。颜回这里不断的“益”,实际上是不断的“损”。他所损去的东西就是儒家极力推崇的仁、义、礼、乐等文化形式。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家的人生修养概括为不断的自我还原,即不断的回归自然。
《庄子·达生》中所讲的一个故事,也能够很好地体现这种不断的还原和归隐:“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这里的“斋以静心”也就是一种向自然状态的回归,最终的目的是“以天合天”。
事实上,儒家的自我超越与道家的自我还原都是对现存自我的出离或否定,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目标和方式有所不同。儒家自我超越的目标是一种文化世界,道家自我还原的目标是自然状态;儒家自我超越的方法是积极进取,道家自我还原的方法是消极归隐。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最一般性的概括,如果要做仔细分析,无论是儒家的自我超越还是道家的自我归隐,都具有更加复杂和丰富的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儒道之间的这种对立,也许在更深的层次上是可以超越的。事实上,儒家的君子人格中就不仅包含了自我超越,而且包含了自我还原。自我超越表现在“文”的方面,自我还原表现在“质”的方面。如果只看到自我超越方面,那就不能对君子人格和儒家修养做出全面的理解。
3
在《论语》中,“质”更多是指人格构成中的自然方面的因素,与此相对,“文”更多是指人格构成中的文化方面的因素。《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里的“本”就属于“质”的方面。这种“质”一直深入到了人的自然本性,因为“孝悌”就是一种建立在自然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伦理规范。
不过,儒家并不将“质”仅仅局限于人的自然本性,一切真情实感都属于“质”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儒家讲的自然本性,并不是宇宙论意义上的“根”,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真情实感是儒家君子人格中的重要部分,因此《论语》中更多地是用“仁”来代表“质”。《论语·里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在《论语》中,“仁”除了具有“爱人”的含义之外,还有“情直”即“情真”的含义。比如,《论语·子路》:“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学而》:“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尽管不如“巧言令色”那样有文饰,但由于它是朴实无华的情感的自然流露,所以“近仁”;而“巧言令色”由于过度修饰,所以“鲜矣仁”。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孔子把真实情感看得比抽象的伦理规则还要重要。让我们以《论语》中所记载的两则事例来加以说明。
《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对做儿子的来说,总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做儿子的不愿意父亲的坏事被张扬出去,这是做儿子的真实情感。如果做儿子的根据某项抽象的道德规则而揭发父亲,从道德规则的角度来说,他的做法是对的,但从真实情感的角度来看,他的做法是错的。揭发父亲的儿子看起来大公无私,似乎是一种“直”,但在孔子看来,由于这不是他的真情实感的表现,所以不是“直”,而是“罔”。
另一个事例见《论语·公冶长》:“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有人向微生高借醋,微生高没有,而到邻居那里转借。这在孔子看来是不“直”。虽然微生高尽力满足别人的愿望,在某种意义上符合助人为乐的美德,但微生高隐瞒了自己家里没有醋的真实情况,这种隐瞒本身就是不“直”的表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真情实感与道德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孔子把前者看得比后者更重要。但是,这并不是说孔子不讲道德原则,孔子只是不讲抽象的道德原则。一项道德原则如果在具体实施时与人的真实情感相抵牾,这项道德原则就有变通的必要,甚至可以说,孔子希望把所有的道德原则都还原到真情实感的基础上。这一点同西方伦理思想特别是义务伦理思想相比,有较大的差异。西方义务伦理思想强调道德原则至上,只有无条件地服从道德原则,才是真正道德的表现。
但是,如果“仁”只是内在的真情实感,那么同样作为真情实感的贪欲怨妒也就是“仁”了,这岂不是刚好走到了“仁者爱人”的反面?毫无疑问,贪欲怨妒跟“仁”无关,因为在《论语》中,对“仁”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规定,那就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显然,这里的“克己”同上面的“情直”有矛盾。如果说,“情直”是为了保证“仁”的自明的基础的话,“克己”则是为了保证“忠恕之道”的实施,即为了保证一种在人类共同体之间可以共享的真实情感。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论语·颜渊》的原则,贪欲怨妒虽然是内在的真情实感,但由于它们不能推及到他人那里,就不可能是“仁”,而是作为非礼的“己”需要加以抑制和克服的。但“克己复礼”并不是将所有的真情实感全部克服,而是克服不能在人类共同体之间推行的真情实感。被克服掉的是“私”,保留下来的是“公”。尽管这里的“公”、“私”都是人的真情实感,但儒家极力主张去“私”存“公”,反对人的自然欲望。《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宪问》:“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这里讲的都是对人的某些不具备普遍性的自然欲望的克服。
4
要成就君子的理想人格,需要“情直”、需要“质”,但仅有“质”是不够的,还需要“文”。如果没有某种特定的文化作用,就不可能做到去“私”存“公”,在人类共同体之间推行仁爱,排除私欲。这种特定的文化作用就是儒家所强调的“礼”。根据学术界通行的看法,“礼”与古老的宗教祭祀有关。“礼”首先指的是礼器,即尊、彝、鼎、爵等祭祀器具。在商周文化中,这些礼器究竟起些什么作用,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一般说来,尊、彝、鼎、爵等礼器表现出政治、道德、宗教三位一体的思想。[3]78礼器首先是宗教祭祀的器具,正如张光直所说:“商周的青铜礼器是为通民神,亦即通天地之用的,而使用它们的是巫觋”[4]322。张光直还指出,这些礼器上的动物纹样的意义是助巫觋沟通天地。②礼器的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是由其宗教意义蜕化而来的。礼器作为巫觋通神的工具,在其通神的意义淡化之后,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可以服务于道德目的:一方面是礼器所包含的秩序意义,另一方面是礼器所具有的神秘威力。从甲骨文和现存的古文献中可以看到,宗教祭祀表现出严格的秩序。宗教祭祀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尊、彝、鼎、爵等礼器来体现和巩固的。这些礼器多用青铜铸成,可以历时不变,这就容易把祭祀活动中的秩序性凝定为一种规范性的制度。这种制度便是后来的伦理规范的雏形。礼器的神秘威力源于自然宗教中对神灵的敬畏。在自然宗教中,神灵是人们规避的禁忌对象,人在神面前只有小心畏惧,所以礼器上的动物纹样都表现为狰狞可怖的样态。礼器正是用这种神秘的威力来保证秩序、规范的普遍有效。[5]33
周公制礼作乐,借用了祭祀礼器所蕴含的秩序和威慑的意义。一般认为,周公营洛邑之后,尊、彝、鼎、爵等神器才蜕化出礼制。[6]79周公把原来凝定在礼器上的秩序抽取为一种一般的道德秩序,并把它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道德秩序由于刚从带有禁忌色彩的祭祀秩序中蜕化而来,因此,它还不是人们主动追求的规范,而带有强烈的他律性。[6]277
尽管周初的礼制系统已经由宗教祭祀系统转化为伦理规范系统,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自然宗教的束缚。随着自然宗教的对象——鬼神的存在被普遍怀疑,以鬼神为基础的礼乐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所以在春秋时期,自然会出现“礼坏乐崩”的局面。没有礼乐,道德理想还能否实现?舍弃礼乐,用什么方式来实现道德理想?显然,一个社会不能没有道德理想,而道德理想又不能没有适当的实践形式,由此,在“礼坏乐崩”的时代,自然会出现思想家对礼乐制度的重新反思,以探寻适合新的追求道德理想的行为方式。这个思想家就是孔子。
在孔子看来,周初确立起来的礼乐制度仍然是实现道德理想的最好形式,因此他对周礼和确立周礼的周公大加赞誉。但是,既然周礼已经被普遍怀疑,要重新确立它就必须给出新的理由、新的解释。孔子的伟大贡献正在于把周初带有宗教色彩的强制性规范转化成了自觉的伦理要求。在孔子那里,“礼”不再是禁忌对象,而是君子们主动追求、学习、爱好和发自内心的喜悦的对象。《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手曰:‘可也,未若贫而好乐,富而好礼者也。’”令人敬畏的礼乐制度之所以能转化为人们喜好的对象,在于孔子对传统的礼乐制度进行了革新,对礼乐制度的存在理由进行了新的说明。经过孔子、荀子等儒家思想家的改造,“礼”从带有浓厚原始宗教色彩的祭祀系统转变成了一种文明的伦理规范形式,甚至成了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这一点在荀子那里尤其明显。
荀子经常同时讲到“礼”、“法”,尽管“礼”与“法”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法”是“标准或规范”,“礼”是“照规范定出来的具体的项目”,[7]688但它们都是一种相对确定的社会规则和秩序。不过,除了将“礼”与“法”联系起来外,荀子还更多地将“礼”与“文”联系起来。儒家对传统礼制的改造遭到墨家的强烈挑战。在墨家看来,儒家不信鬼神却从事祭祀,这无异于没有客而举行宾礼,没有鱼而撒网一样。③为了回应这种批评,荀子对“礼”的作用做了新的解释。祭祀不是满足鬼神的要求,而是表达内在的情感。《荀子·天论》:“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久旱无雨,人们自然会产生焦虑的情感,举行“雩”这样的求雨仪式,并不是因为人们相信真的存在掌管风雨的神仙,而是为了表达内心自然产生的焦虑情感。同样,亲人去世了,人们在理智上知道亲人已经不再存在,但人们在情感上总希望亲人继续存在,怀念亲人在世的情景。这种情感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荀子称之为“天情”。自然产生的情感需要得到表达,“礼”就是表达“天情”的一种合乎节奏和秩序的仪式。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礼”成了表达人们内心自然滋生的情感的艺术形式。这种意义上的“礼”就是“文”。[7]725-727由此,儒家所谓“礼”就不仅仅是宗教甚或伦理意义上的行为,而且是艺术行为,一种生活的艺术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表现内在真实情感的有节奏的舞蹈。孔子的礼仪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这种表现内在情感的有节奏的舞蹈,如同我们在《论语·乡党》中所看到的那样: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閾。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5
到这里为止,我们将儒家修养中的两个对立的方面凸显出来了。要成为君子,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修养:一方面是“仁”,是“质”;另一方面是“礼”,是“文”。“仁”和“质”是内在情感或品质,属于个人的、自然的层面;“礼”和“文”是外在体制或风俗,属于社会的、文化的层面。理想的儒家人格就是既要尊重个体的真情实感,又要符合一般的社会体制。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腧矩”[2]《论语·为政》。这是如何可能呢?
事实上,在我们看来是完全对立的东西,在儒家那里似乎并不矛盾。人只要在社会上存在,他的身上就没有纯粹的自然属性,他所有的存在就都经过了社会的约束和文化的熏陶。因为人是被抛在世界之中的,人在对自己的存在进行反省之前已经在世界中存在了,已经接受了世界的塑造。在儒家那里,甚至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专门用来塑造人的“自然”素质,这种文化形式就是诗,大致相当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
《论语·泰伯》记载孔子言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历代注释家都认为这里讲的是人的学问修养的先后顺序。如果说“礼”是对人的自然天性进行雕琢和约束的话,那么在“礼”的雕琢和约束之前,人性并不像兽骨、象牙、玉石等被雕琢的对象一样是纯天然的东西,而是经过了诗的感发陶养之后的人性,是“文化”过了的“自然”。
但是,这并不能终止人们对纯粹自然的追求。人们完全有理由继续追问:在诗的陶冶之前的人性会是怎样的?难道它不比经过诗的陶冶之后的人性更自然吗?于是,答案自然而然会追溯到婴儿的天赋能力甚至动物本能上去。如果按照进化论的观点,这种追溯还可以继续,可以由高级动物追溯到低级动物,由动物追溯到植物,有植物追溯到微生物,如此等等,无穷无尽。但是,儒家思想并没有陷入这种无穷后退。因为在儒家看来,人的自然本性既是与生俱来的,更是在一种特殊的文化熏陶中发现的。在传统的儒家教育系统中,诗教占有十分特别的地位,原因就在于通过诗教可以发现人的自然本性。诗教是所有教育的基础,礼乐的教育形式必须在有了诗教的准备之后才能进行。这种意义上的诗教的性质非常特别,如果说诗教不管怎么说也是对人的一种“文化”的话,那么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文化,一种帮助人们发现其“自然”本性的文化。诗教的目的是“兴”,根据王夫之的解释,“兴”不是在现有的人性基础上增加另外的文化形式,而是剔除已经加在人性之上的各种文化形式,使人性呈现出其本来面目。王夫之说:
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8]479
人生在世,不可避免受到各种功名利禄的浸染和遮障,从而显得意志消沉,暮气重重。诗所起的作用,就是让人们从各种功名利禄中超拔出来,恢复本然的赤子之心。只有在这种荡涤沉浊暮气、恢复自然天真的心灵的基础上,一个人才有可能成为豪杰进而成为圣贤。显然,这种诗教所产生的文化作用跟礼教所产生的文化作用非常不同。如果说礼教所起的作用是一种“增”或“正”的文化作用的话,那么诗教所产生的作用就是一种“减”或“负”的文化作用,是一种以“质”为目标的“文”。但即使诗教所产生的作用是一种“减”或“负”的文化作用,它毕竟也是一种文化作用,而不同于白板一块。诗教意义上的“文”实际上就是“质”。儒家修养中自然与文化的矛盾,通过诗教似乎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6
人只有在高度文化之后才能显得自然,这就是儒家思想家对人生悖论的深刻认识。如果诗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今天的审美教育的话,那么儒家修养中的自然与文化的悖论就从美学的角度得到了解决。但是,与其说美学解决了这个悖论,不如说它维持了这个悖论。这与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有关。自从18世纪确立美学学科以来,它就一直没有确立起一套严格的知识体系。但这不是美学家们的过错,相反是美学家们的明智。因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就不可能形成一套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美学问题的知识体系。如果将美学的研究对象姑且确定为艺术的话,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不能有关于艺术的精确知识,而只能有关于艺术的具体实践。在现代美学确立的初期,两位卓越的美学家康德和休谟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显示了关于艺术的美学知识的有限性。
康德处理的是艺术创造问题。在康德看来,艺术(创造)领域中没有规则,艺术的规则是由天才艺术家确定的,因此他将天才确立为一种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康德说:
天才是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自然禀赋)。由于这种才能是艺术家天生的创造性能力,而且就其作为天生的创造性能力而言本身是属于自然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达:天才就是天生的内心素质(ingenium),通过它自然给艺术提供规则。[9]174
天才只是个案,不仅艺术本身没有规则,从给艺术提供规则的各个天才中也不可能总结出规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种恰当的美学就是讲述天才个案史的美学,而不可能成为一种解释所有艺术甚至所有天才的知识体系。
与康德不同,休谟处理的是艺术欣赏问题,也就是所谓的趣味问题。在休谟看来,趣味领域没有规则,艺术趣味的规则是由理想批评家确定的,因此他将理想批评家确立为趣味的标准。在《论趣味的标准》一文中,休谟试图给完全主观的趣味寻找客观的标准,但休谟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找到了趣味的标准,而是将趣味的标准问题转换成了理想批评家的资格限定问题。因为在休谟看来,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关于趣味标准的知识,只有关于趣味标准的榜样,这种榜样就是理想批评家。休谟说:
精致的敏感加上强健的理智,再得以实践的改善,比较的完善,以及清除所有偏见,只有这些才能授予批评家这种令人钦佩的人物的称号;而无论哪里发现的这些因素所做出的共同判断,都是趣味和美的真正标准。[10]112
在艺术领域,无论创造还是欣赏,都没有普遍的规则,只有具体的榜样。天才艺术家是创造的榜样,理想批评家是欣赏的榜样。我们在儒家的人生观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情况。
总之,我们不可能有关于艺术的知识,只有关于艺术的榜样;我们也不可能有关于人生的知识,只有关于人生的榜样。艺术中的悖论是由天才的具体实践解决的,人生中的悖论是由君子的具体实践解决的。与天才将木头、石头做成了艺术作品不同,君子将人生本身做成了艺术作品。我们通过天才可以适当地理解君子和他的人生艺术,就像我们通过君子可以适当地理解天才和他的美的艺术一样。
收稿日期:2009-05-26
注释:
①这种超现实的世界常常被形而上学假定为另一个真实的世界,而现实世界则被视为那个看不见的真实世界的外观或表象。尼采在《人性,太人性了》中描绘了这种信仰的谱系。人们最初是从梦中得到关于另一个世界的观念。当人类的反思出现的时候,他们发现另一个世界中的东西用经验方法是无法理解的,于是便得出这样的结论:经验的方法是不完善的,真实世界只有用非经验的方法才能理解。因此,人们将经验世界当作另一个世界的表象或扭曲,而那个另外的世界被认为是真实世界。形而上学就是关于这个非经验的真实世界的谣传知识。有关尼采这种看法的叙述和评论,见Maudemairie Clark,"Friedrich Nietzsche" in Edward Craig ed.,Rouf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8),vol.4,pp.848-850。
②参见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13-342页)和《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03-114页)。
③《墨子·公孟》:“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无鱼而为鱼罟也。”
标签:儒家论文; 文化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自我修养论文; 论语·学而论文; 读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修养论文; 论语论文; 道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