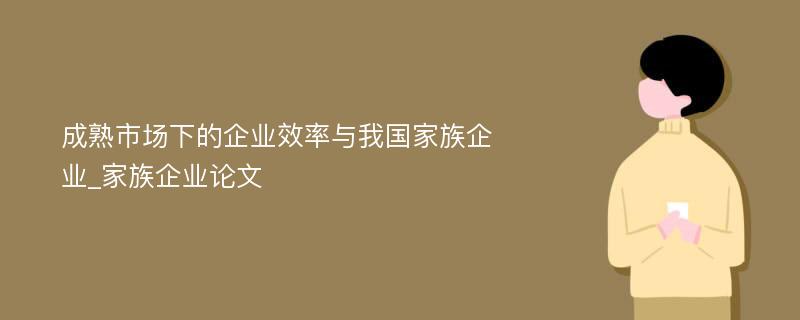
成熟市场下的企业效率与我国家族企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族企业论文,效率论文,成熟论文,我国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4)02-0038-08
一、问题的提出
在对企业效益差异的分析中,通常将除资源配置效率之外的影响效益的方面称之为组织效率,这也是莱宾斯坦因等人所谓的“X低效率”的内涵。但根据有效劳动价值说(朱富强,2001),企业组织方面效率,即“X效率”实际上却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劳动量支出的效率,二是劳动间协调的效率。相应地,“X低效率”也可分为:劳动低效率和协调低效率。劳动低效率主要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机会主义倾向所造成的实际劳动量支出的下降和不足,如表现在生产者的偷懒、在职闲暇以及代理管理者的在职消费、打埋伏倾向等。协调低效率主要是指企业中劳动间的协调性差,如认同基础差、信息不沟通等导致的隐性协调水平低,以及组织不完善、管理者能力低等所造成的显性协调不足,从而团队生产带来的协调收益较小。
企业的协调又可细分为两种:一是由专门人员来组织的,我们称之为显性协调,它主要涉及管理者能力、信息技术、社会制度设施、企业组织结构等;一是没有专门人员的活动而是基于相同背景认同基础上所达成的默契协调,我们称之为隐性协调,它主要涉及企业文化、社会伦理、隐性信息沟通机制、企业间关系、隐性规则等。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中,协调才是影响X低效率的关键因素,企业组织的产生也正是协调机制不断演化的结果(朱富强,2003);甚至,莱宾斯坦因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问题不在于管理者是否是剩余索取权的获得者,从而会进行高效率的监督,而在于管理者于其他雇员(以及两个团体内部同等地位的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否带来的最佳的工作态度”(斯密德,1999,162)。
然而,目前理论界的研究却存在很大的不足:一方面,没有很好地分析不同企业协调水平上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这一课题;为此,本文将以较为发达的市场为背景,根据上述对协调的两分法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尽管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企业都是家族经营的,但是有关管理的书籍和课程几乎完全是针对公共的和专业管理的企业,而涉及家族企业经营管理的却很少(德鲁克,1999,29);为此,我们将本文对协调的分析与家族企业结合起来,特别是对我国当前民营企业发展作基础性的研究。
二、显性协调的不同: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的比较
为了更好地分析显性协调和隐性协调对不同类型企业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将企业分为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组织结构以及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相似组织结构两组进行比较研究。
在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组织结构,我们着重分析家族企业与现代企业在协调方式上的差异。一般认为,家族企业的长期发展相对于现代企业具有劣势,这些劣势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由于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处于相同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就排除了企业的外部监督和协调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特别是,我们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问题,也就是说要比较研究规范成熟的市场经济下不同类型企业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分析认为,家族企业与现代企业的效率差异主要受显性协调能力的影响较大。逐层分析如下:
一般来说,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任何企业都必然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是监督方面,一是协调方面,家族企业也不例外。就监督而言,在一个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相对于协调,监督是相对不重要的;特别是,一般认为家族企业能更好地解决监督问题。首先,就管理者的管理劳动支出而言,在家族企业中,由于管理人员大多是建立在“缘关系”之上,而这种“缘关系”使得管理人员具有一种自律性,从而弱化了管理劳动的低效率。其次,就生产者的劳动支出而言,由于管理人员与企业有密切的联系,这促使了他们加强对生产者的监督,使得产生生产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更为窄小。事实上,企业发展史以及当前中国企业的实践都表明,在家族企业中偷懒是难以行得通的。现在有一些国内学者激烈抨击家族企业的弊端,但事实上,家族企业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甚至是主要的组织形态,如当前世界范围内80%以上的企业都归属于家族企业(盖尔西克,1998),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家族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监督能力。最后,更重要的是,相对协调(它可被看成是复杂劳动)而言,监督是一种简单劳动,这种简单劳动对家族成员来说一般是比较胜任的,而通常的监督缺失往往是由于产权不清所引致的“理性的忽视”而已。
当然,需要指出,在家族企业中也存在对监督的不利之处:(1)随着规模的扩大,由于家族企业中与“缘关系”相关的管理人员有限,企业的边际监督成本必然较其他企业上升更快,从而会制约企业规模的扩展;(2)由于对“缘关系”之外的成员的不信任,就会导致“缘关系”之外的成员机会主义倾向增强,结果可能迫使监督支出的增加;(3)由于实际上企业为管理人员所有,也就必然弱化对家族管理人员可行的惩罚机制,因为这种在自己企业内的在职消费实际上是个人自己的事,而与他人的利益无关;(4)在家族企业中,“大家庭为所有成员提供温饱,而不计较个别成员对家庭的贡献多寡,因此只要是自家人,不论是贫穷困顿或饱食终日者,都能获得同样的照料”(福山,1998,81)。这些都会降低家族企业的监督效率,从而也必然影响企业的整体效益。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监督上的问题相对协调而言都是次要的,大量的数据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企业的协调方面。就隐性协调来说,它也不构成影响企业效率的主要因素。首先,从大的方面讲,隐性协调与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传统有关,家族企业的企业文化也受这个大背景的影响。因而在一个相同的社会传统之下,家族企业的企业文化与其他企业的文化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其次,在家族企业中,由于受家族本身的“缘关系”的影响,这种“缘关系”可能并更容易扩展到其他成员之中,从而更有利于企业的隐性协调。事实上,早期的许多家族企业的创始人都以“缘关系”的家族理念来治理企业,将员工视为自己大家庭的一份子。其实,日本企业中高水平的隐性协调实际上也是基于这种“缘关系”而扩展开来的。当然,建立在“缘关系”之上的家族企业在隐性协调方面也具有自身的缺陷,相对于其他企业中存在的严重个人主义,这并不严重。
在显性协调方面,相对于监督这一劳动而言,协调是复杂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协调劳动也就越来越复杂。结果,家族企业越来越难以适应协调提高的需要,这也正是家族制企业低效率的主要原因。首先,就家族成员而言,由于家族成员的圈子毕竟狭窄,因而家族成员的协调能力往往有限,或者难以胜任家族企业的工作。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有限的家族成员的显性协调所带来的边际效益也是不断递减的。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易劳逸(Lloyd Eastman)考察中国的企业史后就指出,华人企业之所以缺乏行政管理效率,就是因为华人企业家并非从自由职业市场依据教育水准、工作经验和专门学识来专门招聘经营管理人员,而是将选择的范围局限于家族成员、同乡或其他人际关系网上的人物(高家龙(Sherman Cochran),1994)。其次,就外聘管理人员来说,由于缺乏信任,家族外的管理人员与家族成员的关系总很疏远,家族成员的利益可能与外聘人员的利益不一致,从而往往会在决策上发生冲突,而家族成员的看法也往往制约了外聘管理人员协调能力的发挥;而且,这些外聘的管理人员几乎没有成为最高管理者的可能性,他们的工作流动性较大,也就缺乏最大程度协调的主动性。如在华人社会里,不属于企业雇主家族的员工就往往不喜欢替人打工,也不愿终生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而是只要有可能就伺机到外面去独自创业。正因为如此,低信任度社会的家族企业的规模往往较小(福山,1998,86-89)。再加上继承制度等因素,家族公司就不断上演着创立、崛起、衰败的三部曲(杜恂诚,1993;K.盖尔西克,1998),王安电脑公司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最后,家族企业主要是以“缘关系”为基础的“缘协调”,这种“缘协调”虽然对“缘关系”之内的成员具有高协调性,但是却对“缘关系”之外的成员产生强烈的排斥作用,这会进一步降低对外的协调力。
社会的现实状况也可佐证我们上面的分析,一般来说,正是由于家族人员在协调能力上的局限,成功的家族企业往往都集中在协调能力要求相对较低,而监督因素起重要作用的产业上:成功的家族企业主要在劳动密集型的以及加工类型的产业上,如纺织、木材加工、橡胶制品、玩具、食品、皮革制品等方面;而在高度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基于复杂制造过程的产业,如半导体、航天、汽车、飞机、电脑等就很难成功(福山,1998,98)。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提高显性协调能力就是家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家族企业最终必然向经理管理的社会化现代企业转变的深层原因。
三、隐性协调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比较
上面比较分析了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家族企业与现代企业的效率问题,并将之主要归咎为显性协调上的差异,我们现在进一步比较分析组织结构相似但生长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的效率。同样,我们比较探讨的是两类企业的长期发展状况,因而也必然在成熟市场下进行讨论,这同样排除了社会监督机制方面的影响。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显性协调的特点。在非封闭式的现代企业中,由于企业的管理者可以从市场上自由、公开挑选,因而就两个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企业整体而言,应该说不存在协调能力上的显著差异;而且,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明显不胜任的管理人员都可能很快被炒鱿鱼,或者经过较长时间的筛选,最终能够留在经营管理岗位的大多数是该社会中管理精英。因此,我们说,在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相同、社会知识文化水平相似的社会中,企业管理者的显性协调能力没有明显的差异。当然,即使在同一社会,不同企业管理人员的显性协调能力也有较大的差异,这是不断演绎着企业兴衰轮回的原因。但在进行两个社会中企业的宏观、整体协调水平比较时,企业个体的显性协调水平差异可以忽略。虽然就整体而言,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组织结构相似但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下企业的显性协调没有明显的差距;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两种社会下的企业效率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协调水平的不同很可能是在于难以被发现的以及难以短时期内改变的隐性协调水平上。
人类社会学家E.霍尔(E.Hall)曾将文化分为高环境文化和低环境文化。所谓高环境文化主要是指像美国社会那样信息是清晰的和非人格化的,人们通过各种契约来规范各自的行为;在低环境文化中,人们则倾向于依靠事前人们在共同文化背景下的共识来体会默会的知识,通过何种人际关系来规范人的行为。在高环境文化的环境中,人们劳动之间的协调往往以制定的显规则(即正式规则)为准绳。但是,这种显规则作用的过分膨胀往往会排斥人们之间的隐规则,发展为形式规则主义,从而窒息了隐规则的发展。反映到企业的协调中,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显性协调就特别发达,而隐性协调则相对薄弱。而在低环境文化的环境中,人们则比较重视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默契,因而隐规则发达,而相对来说,显规则不成熟。反映在企业的协调中,则比较重视隐性协调的效率,也就是说注重企业内在文化的建设。
但是,从社会互动对两种规则发展的影响来看,在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中,显规则比较容易创造、设计或移植,因而原来显性协调机制不发达的社会能够在短期内通过引进显规则而弥补自身的不足。但是,隐规则却是难以被移植的,因为隐规则的效力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它能否被移植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状况,更重要是取决于后者的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因此,总的来说,隐规则要比显规则更加难以变迁,即使有政府的行动,像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也是不易改变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显规则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隐规则的改变却是长期的。因此,一些他国适用的显规则虽然可以从一国移植到另一国,但隐规则则由于内在着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很难移植,原来隐性协调水平欠发达的社会也不容易在短期内得以根本改观。结果,在处于同一经济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经过市场的发育,尽管显性协调水平已经极为相近,但隐性协调的发展状况往往存在明显的差异,由此造成了企业效率的不同。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协调状况与它的信息特征有关:信息越规范、越集中,则它的显性协调程度越高,而隐性协调水平相对则可能越高;相反,如果信息越集中,越不规范,则隐性协调水平越高,而显性协调可能较低。但是,信息特征和协调状况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主要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法制建设状况,即显规则的移植问题。如日本的信息很不规范,按理显性协调应该是不发达的,但是由于受强烈的市场竞争作用以及日本“接受创造性”的文化传统,日本积极着手“显规则”的建设,使得它的显性协调在短期内赶上了西方国家的水平。因此,与其说在日本这样一个信息分散而又不太规范的社会中显性协调不发达,不如说,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而言,日本的隐性协调的充分发达使得它的显性协调显得相对黯淡;但实际上,日本的显性协调也是很发达的,而且已经能够与较高的隐性协调在一个较高层次的水平上有机结合了起来。当然,由于传统的因素以及信息不规范而分散的滞存,从总体上看,日本企业中的显性协调发育程度确实与欧美企业有所差距,这反映在日本经常暴露出来的违纪事件和金融危机上。
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培育出高水平的隐性协调,就在于它有效地从家族或家族企业吸取了“缘协调”的养分,成功地进行了从“家庭共同体”(或“缘共同体”)向“企业共同体”的转换和变迁。日本的这种“企业共同体”意味着在日本企业里,具有超出劳动力买卖契约关系的共同性。如从家庭和大学进入共同体时都要进行宣誓,入社仪式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桥本寿郎,1997,193)。实际上,日本早期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以“财阀企业”的形态出现的。而所谓财阀,就“是在家族或同族的封闭性的所有和支配下组成的多角的企业经营体”(陈凌,1998),它的明显特征就是强烈的家族式“缘关系”色彩。而日本的现代企业正是脱胎于其上,因而不可避免地打有”缘关系”的烙印。福山等人虽认为,日本的企业集团早已超越了家族财阀的阶段,而与欧美企业相仿。但实际上,与欧美企业相比较,日本企业仍具有明显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正是在于其继承了家族制的一般特点,如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岗位轮换、企业文化、交错持股等。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日本企业已经超越了家族财阀阶段,但它们仍属于家族式组织(陈凌,1998)。当然,这不再是原来规模狭小的家族企业,而是更大规模上的松散的“泛缘式企业”。
虽然由于日本的长期衰退,使不少学者对日本社会协调方式产生了怀疑和否定,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泛家族主义,使得日本保持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日本在后期发展上的障碍在于这种家族主义只是扩展到企业内和一国狭隘的地域之内而没能够继续持续扩展下去,结果企业内部成员信任度高,而对外则陷入了原始的不信任之中;对本国员工很信任,但对外藉员工却极不信任,如在中国的日资企业相对于欧美企业而言对中国的员工就更为苛刻,采取更不信任的态度。
因此,我们在正视缘关系扩展中断而引起问题的同时,并不应该否定隐性协调对经济发展的长期作用。它的优势之一就是对内部的高度信任,甚至主要的管理人员也是从内部选拔的,从而保证了管理人员对企业内各事务、人际关系的熟悉,从而有利于隐性协调和显性协调的结合,发挥出更高的整体效率。在日本企业中,从内部选拔经营者是一个的基本原则,大约有70%左右的董事是公司内出身,但这种“土生土长”的经营者并非是资本的所有者,因为全部的公司要员合计持股比率也仅为6~7%;但这种“土生土长”的属性便于对企业共同环境的熟悉和对“基于协作的分工”的协调(桥本寿郎,1997,196~198)。
莱宾斯坦因针对劳动支出不足提出了X低效率,它的前提就是人只要有可能就会倾向于机会主义行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纯粹的监督和显性协调的基础上,而没有看到隐性协调的一面,这也正是隐性协调匮乏的西方企业的现实反映。尽管,在西方确实大量存在着潜在的劳动支出的X低效率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放眼世界、历史以及对人本性的真正内在考察,这种理论就显得相当片面了。正如D.M.麦格雷戈(D.M.Mcgregor)指出的,X理论对人所作的本性懒惰、逃避责任的消极假定并不符合人的本性。而实际上,正是以此为依据的强硬管理,才促使了这种现象的泛滥,这也是俄狄苦斯效应的结果;为此,他提出了与X理论截然相反的Y理论。而深受日本的高水平隐性协调熏陶的日裔美籍经济学家威廉.大内则进一步地发展了L.厄威克开创的“Z理论”,发现日本提高生产率主要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亲密关系以及一些微妙的东西。可见,隐性协调水平的差异是导致处在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组织结构相似但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下企业间效率不同的重要原因。
四、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启示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主要是以家族形态存在;而且,在可见的未来,我国的家族企业只会越来越多而不是消逝,现在的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合伙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承包企业等也都将越来越采用家族制或泛家族制(储小平,2000)。但是,理论界却对这种家族企业存在的意义、发展方向、竞争能力等问题都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根据上述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获得这样几点基本看法。
1.家族式企业治理具有积极成分,在我国当前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产权结构只是企业治理的一种机制,它对企业所属权利的有效界定从而发挥约束和激励功能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企业规模、产品特色、行业集中程度、产业技术、社会文化以及市场发育状况等。因此,家族企业和现代公司制度没有优劣之分,而只是适应的环境不同。
从总体情况看,我国目前的企业具有这样几个特色:规模较小,过分搬用委托—代理方式反而增加监督成本;产品集中(如希望集团专门做饲料),分工较细使得家族成员具有丰富管理活动的经验;产业技术水平较低,要求的协调能力也不高;产业资本密集度较低,通过积累家族具有企业发展的资金;社会文化以家族为基础,使得家族的凝聚力大;市场和信息机制不发达,社会上的机会主义倾向比较严重。正是存在这样的特点,家族管理方式基本能够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而且,家族企业在企业发展的初期往往表现出相对于其他方式更高效率。首先是经营者对企业资产是高度负责的,能够使有限的资源达到最佳配置,舒尔茨、林毅夫等就论证低收入者更具理性的。同时,他又能充分利用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关系、类似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从而较快的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李新春,2000)。其次,家族制使得领导者具有充分的权威,家族成员之间也容易达成共识,从而使企业反应迅速,政策能随时根据市场信息而变化。再次,由于家族成员彼此间的信任及了解的程度远高于其它非家族企业的成员,特有的血缘、亲缘关系,又使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因此,在监督管理上的成本较非家族企业要低。如首家上市的中国家族企业——“天通股份”——在十几年时间就成了国内软磁行业最大的企业,号称“中国软磁王”,占据了国内35%的市场份额。最后,家族关系还有利于在企业初创阶段快速筹资,Hamilton(1998)就认为,在台湾由关系支撑的投资结构使得企业家能够迅速投资而进入新的领域。
实际上,家族企业历来就是古今中外企业的普遍形态。当前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家族式企业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统计,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有大约30%是家族企业,法国最大的200家公司有50%是家族企业,整个世界500强企业有40%是由家族式所有或经营。而中小企业实行家族式管理的更普遍,日本的中小企业几乎都是家族企业,全球65~80%的私人企业是家族企业。华人社会的家族式企业更是常态,台湾的100家集团企业大部分都是由家族掌握控股权并对企业进行家族式经营;而近代中国企业基本由家族包揽,如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荣氏企业——就是典型的家族企业,据1928年统计,荣氏集团的19个企业中共有总理、协理职位54个,其中荣氏血亲的占了31个,姻亲14个,占总数的83.5%(杜恂诚,1993,129)。
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家族企业的发展更具有丰沃的社会土壤。因为我们上面的比较都是建立在发达成熟的市场条件下,而在社会不稳定、监督机制不发达的情况下,监督是企业持续发展的瓶颈。社会越不稳定,行业越不规范,就越需要加强监督,而家族企业在这种背景下更有利于发挥监督上的优势,从而快速促使企业的成长。
可见,家族式企业并不是所谓的落后形态,而恰恰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石。正是以家庭为基础,人类形成了自然的亲密关系,开始了有效的分工合作。也正如上面指出的,以家庭为核心的缘协调是最早的协调方式,其他协调方式都是由它扩展而成的;因此,它是各种协调机制的基础,完全舍弃家族企业中的“缘关系”是造成现代企业困境的根源。
2.家族企业应具有开放性,其发展要不断吸收现代企业中的有利养分
尽管小规模、低技术、差环境、缺乏信任是家族企业成长的沃土,但是,企业毕竟要做大,技术毕竟要提高,环境毕竟要改善,在这种形势下,企业的监督成本优势就逐渐消失,相反显性协调上劣势日趋明显。因为“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家族企业在抵御风险方面的能力日显不足,也难以适应企业发展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同时,在企业规模壮大以后,也就越来越难以保证拥有最佳的管理者。特别是,由于协调是复杂劳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协调劳动随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复杂;但家庭成员的能力有限、智力有限,越来越难以适应协调工作,这是家族企业的弱点,也是越来越多的所有者退出管理层的原因。因此,家族企业要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产权安排就要不断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断借鉴和吸收现代企业的治理方式。实际上,日本企业之所以长期在全球“独领风骚”,就在于成功地进行了从“家庭共同体”(或“缘共同体”)向“企业共同体”的转换和变迁;通过对西方现代企业“显规则”的创造性吸收,使隐性协调和显性协调在较高层次上有机结合了起来。
一些家族企业的老板也知道可能自己的亲属不是最出色的,但是仍然冒着企业衰落的危险也要选择这样的人来继承自己的事业。即使继承人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也要找个诸葛亮那样的忠臣来辅佐他。特别是,家族内外有别的伦理关系以及家族成员之间的争权夺势也常常会造成企业组织内部帮派林立和组织内耗(李新春,1998)。正因为大多数的企业没有“与时俱进”,结果其往往发展后劲不足。据国外的研究资料表明,家族企业的寿命,一般为20年左右;家族企业能延续至第二代的,仅为39%;能延续至第三代的家族企业,更是只有15%。因此,太太药业董事长朱保国指出,家族企业要做大只有两条路,上市或者卖给大公司。刘永好则认为,最理想的企业=家庭企业的效率+上市公司的规模。
近年来,我国一批家族企业纷纷上市,如天通股份、康美药业、用友软件、太太药业、广东榕泰等。企业既然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资金,企业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也必须吸收社会企业的方式。实际上,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技术的提高,必然伴随着吸收社会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仍抱着家族式的经营方式,采用“人”治而不是“规”治,必然会造成很多问题。因为缘内关系的过强,必然导致缘外关系的弱化,从而带来更严重的监督和协调困难,可能引起发展的休克。从最终发展来看,那些能够持久增长的家族企业一般都向经理式的社会企业转换了,如福特、杜邦。即使被认为有希望打破“家族企业三代衰败论”的李嘉诚帝国,也没有将企业全部让自己的儿子接手,而是将和黄集团交由霍建宁等专业经理负责。
3.家族企业要充分发其优势,必须形成有效解决“缘内”隐患的机制
上面的比较分析也表明,家族企业由于强大的内聚力而拥有监督上的效率,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社会外部约束机制“短缺”的情况下,家族企业具有深厚的发展基础。然而,这种基于特殊关系的机制也是软约束滋生的沃土,这种软约束造成了企业治理的混乱随着企业的成长就愈益明显。
有的是在企业壮大后,原先家族的几个共同创业者对有关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利益分配等产生冲突,家族企业并没有一个较有效的问题处理机制,从而导致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突然解体。更多的则是在第一代创业者去世后,旧有的家族权威不再,第二代的众多继承者往往为获得权威而展开争斗而导致企业动荡。其主要原因是,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是维持团体完整的必要条件,在以亲属作基础的威权团体里,如果两代之间还可以用权力来维持不太平等的关系,同代之间则越发困难(费孝通,2002,180)了。
在近代中国史上,即使为时人所称道的聂氏恒丰纱厂在第一代创业者聂缉槻死后,聂氏三兄弟聂云台、聂潞生、聂简臣之间也长期存在尖锐的矛盾。即使仅是同辈创业者领军人物去世,第二号人物也往往没有足够的权威保持企业的发展轨迹。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老大简照南逝世后,老二简玉阶的声望就不足以压众,特别是对老五简英甫的奢侈生活基本没有任何约束手段。荣氏企业在荣宗敬去世后,荣德生就感慨企业不如以前好管理了。特别是,中国伦理上讲究子女平等,常常是一旦开创者过世,家族企业就将面临被分拆的危险,因而导致企业不能持续壮大。如当著名商人叶澄衷病逝后,他留下的五金店老顺记、新顺记和钱庄等就成为诸房儿子的“公产”,不久因诸子的矛盾而将老顺记出售,叶家事业也只经历两代就结束了。
有的则是由于创业者与继承人对企业发展的观念不一致,从而展开了对管理权的争斗,引起企业发展的波动、甚至中断。特别是,继承者早熟而开创者留恋权力不肯放权,从而造成尖锐矛盾。如近代大隆机器厂的创办人严裕棠和他儿子严庆祥就因企业经营管理实权和资金运用上产生矛盾影响事业的发展;再如傻瓜瓜子也因其创始人年广久与他儿子之间关于经营上的矛盾而一蹶不振。
家族企业中这些隐患是其长期发展的肿瘤,一旦爆发,就将使企业休克死亡。因此,要保持企业的长治久安就必须时刻警惕家族企业中的内患,不要终日沉溺在家族成员的忠诚和团结上。新加坡的李光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案例。他自1928年创立南益公司,只用10多年的时间便执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橡胶及黄梨业牛耳,并成为金融界巨子。为此,有人总结几方面的经验:第一,在家族成员中,按其地位及作用,合理分配公司股权,免去了争夺家产的纠纷。第三,始终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控股权,不会产生大权旁落。第三,推行西方现代管理原则,把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形成一种法治精神取向的家族管理法;当董事的家族股东只扮演决策者的角色,实际管理及执行则放手由专业经理和属下负责。
当然,说来容易做来难。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家庭伦理的国度,引进制度理性来促进家族企业中价值理性的改变是一个非常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如温州低压电器生产企业新华公司董事长郑元孟为改变家族管理方式,几乎与家族其他成员撕破了脸皮,而在改制后却仍不能与新任总经理构成良性关系。方太公司的老板茅理翔为企业不受家族侵害,得罪了姐姐、大哥,不但被80岁的老母亲骂为不孝,职工也不理解。结果,方太二次创业,家里除了妻子和子女外,没有人愿意参与投资。
正因为变革的艰巨,它才显得重要。理论和经验也表明,经历时间越长的组织,就越稳定,这也是为什么百年老店罕见并受广泛认同的原因。庆幸的是,经过我国民营企业二十多年的发展,加上发达国家一些企业几百年成功转变的案例,以及遍布全球的华人企业发展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如浙江正泰集团的南存辉通过股权稀释的方式股东人数扩大到107人,既保证了家族的合力,又对家族成员形成了约束。吴泰集团的家族核心人物吴敏将自身资产做大之后,通过红利入股的方式在企业重新合并过程中把平均股权改变为不等股权。
总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安排来自实践,而不是相反。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就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发现适合家族企业管理的治理机制,就能够找到家族企业长治久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