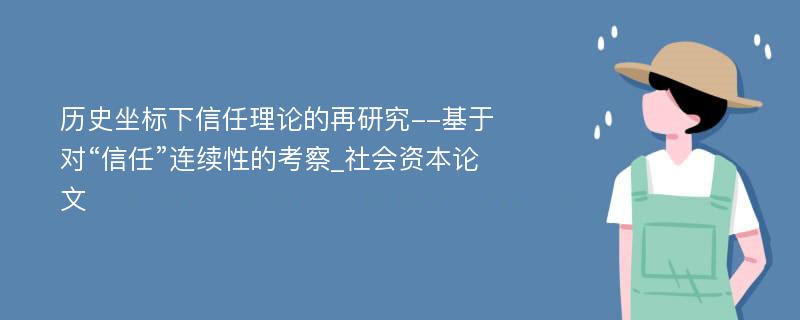
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再考察——基于关于“信任”的延续性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坐标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性调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1)03-0113-05
我们这个时代是最为强烈地呼唤信任的时代。无论是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或整个社会生活中,信任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罗德里克·M·克雷默认为:“信任促进了权力的分散,增进了真实的传播,并通过分配稀有资源实现合作。因而,拥有高度信任的组织更可能成功地渡过危机。”[1](P11)社会是由无数个组织构成的共同体,一个社会如果拥有富足的信任资源,那么这个社会无论在处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或是社会危机方面都会得心应手,保持稳定和繁荣。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提出了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即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这不仅明晰地勾勒出了信任的发展轨迹,而且也确切地指出了我们今天所需要建构的是什么类型的信任。笔者在2006年对南京市做了“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调查,又于2008年在该市进行了“信任与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行为意向”的再调查,基于两次延续性调查的数据资料,可以对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进行更为详尽的考察和解析。
一、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研究问题与研究概况
从信任问题研究的漫长学术史来看,如果说信任理论最早是通过政治学与哲学著作而进入社会学领域的话,[2]那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信任研究在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实现了复兴。在这方面,“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使人们真正意识到信任跟物质、人力一样,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相关理论着力于信任与民主治理、公民社会等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极具开创意义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亚当·B·塞里格曼的《信任与公民社会》、尼克拉斯·卢曼的《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埃里克·尤斯拉纳的《信任的道德基础》以及查尔斯·蒂利的《信任与统治》,等等。这些研究虽然以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对信任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解读,但都表现出了在研究趋向和结果上基本一致的一面,都试图去证明信任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性,并且也都得出了信任对于民主政治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结论。
我国学者对信任的研究稍迟于西方学者,20世纪90年代开始,《信任论》(2006)、《中国社会中的信任》(2003)、《关系与信任:中国乡村民间组织实证研究》(2004)、《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重建: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研究》(2007)以及笔者的拙著《基层政治信任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遥远的草根民主》(2010)、《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成长——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因素探析》(2011)等一批学术著作和论文相继问世。这表明信任问题已经被一批学者在社会学的视野下加以研究和关注,被推向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地带。在《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中,张康之教授将信任置于历史坐标中进行解析与考察,清晰地概括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信任类型以及基于这些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信任理论。张康之教授指出,必须将社会治理问题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来考察,而信任理论又是完整描述社会治理体系所必需的;于是对历史坐标中信任理论的考察就成为考察不同历史阶段社会治理体系所必须要做的工作。张康之教授认为,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三种社会治理方式与三种制度模式相对应的是三种社会信任模式,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3](PP206-218)
佩里·K·布兰登指出,信任和善治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循环的:对政府及其代表的信任可以促进善治,而善治也反过来促使和加强对政府及其代表的信任。[4](PP26-29)可是,治理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面相才算是善治呢?善治一词虽然日渐走俏,但是使用它的人却可能从未认真考虑过或者不能清楚回答这一问题。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合作治理本身就是一种善治,这种善治恰恰是在合作型信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习俗型信任与契约型信任是一种与合作型信任相对应的信任类型。习俗型信任是一种初级形态的信任关系,它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人际关系趋于简单化,人们只将信任给予诸如亲朋好友这样的封闭的“小圈子”;契约型信任比习俗型信任向前走了一步,它是建立在工业社会商品经济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开始复杂化,人们之间的信任则限于彼此之间的利益最大化考量,对于社会上与自己利益无关的大多数人则持不信任态度,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尤为突出。后工业社会形态中的合作型信任表现出了与前两种信任类型截然相反的面相和品质,人们基于主体道德的自觉,出于合作的需要而愿意信任“陌生人”,至少在初始形态中是这样。
以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为分析框架,2006年笔者在南京市城区、郊区和郊县地区进行“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抽样调查,并对此次调查中与“信任”相关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论文:《公民政策参与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习俗型”信任对公民法治意识之影响研究——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再思考》(《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等等。这些论文对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验证。
本文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08年的“信任与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行为意向”调查。本次调查采用的是多阶段抽样法、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系统抽样法、间隔随机抽样法、户内抽样法等方法。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最后共回收问卷776份,回收率达77.6%。在对原始问卷进行逻辑检查和幅度检查后,去掉无效问卷68份,剩下有效问卷708份,最后的有效回收率实际为70.8%。
二、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草根社区中的真实解读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人的信任行为是带有偏见的。某些西方学者将中国看作一个不诚实而且不信任他人的民族。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韦伯的《儒教与道教》、高伟定的《中国资本主义精神》、汉密尔顿的《中国社会与经济》等书中都有这类观点。福山在1995年出版的畅销书《信任》中一再重复中国社会是低信任度社会的观点。怀特利研究了华人家族企业的信任是如何产生的。他提出,华人家族企业习惯于努力发展与主要下属和生意伙伴的私人关系以实现信任的建立。华人社会中主要通过声誉和关系来产生信任。[5]这些学者对中国人社会信任问题的观点可谓一脉相承。
出于对“外忧”的学术自卫与回应,加之对“内患”的深切感受,以彭泗清、郑也夫、张维迎、李向阳等为代表的一批本土学者对中国人的信任问题作了或理论或实证上的探讨,得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结论。笔者2006年“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国外学者对于中国人信任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有些偏颇,然而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这三种类型的信任当前确实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格局。[6](PP202-205)在本次延续性研究中,笔者尝试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2006“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调查之基础上,从南京市城乡社区居民的主体角度出发,进一步考察社区人际信任的特征及影响其信任度的各种因素。在考察社区人际信任的现状之前,首先对社区人际信任量表进行因子分析。
对社区人际信任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后可知:KMO抽样适度测定值是0.925>0.9,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Sig=0.000<0.001,抽取两个主成分因子,这两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68.539%。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得到两个因子:第一个公因子支配了“您的邻居或社区里的大多数人基本上是诚实的”、“您的邻居或社区里的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社区里的大多数人基本上是好人并且是友善的”、“如果您需要,邻居或社区里的大多数人总是愿意帮助您”、“在邻居之间或社区里,一个人没有必要经常担心被欺骗”、“如果您为大家主持公道,社区里的大多数人都会回报您”、“社区里的大多数人都是相信他人的”。这类因子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故取名为“合作型信任因子”。
第二个公因子支配了“社区里的多数人通常只对他们自己的利益感兴趣”、“不管他们怎么说,社区里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不顾自己去帮助别人”、“在借贷问题上,邻居之间或社区里的人总是不能互相相信”、“人们只关心自己家的财产,并不太关心整个社区或邻居的财产”、“社区里的大多数人都是不可信的,我只相信我熟知的人”。这类因子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代表特殊信任,故取名为“习俗型或契约型信任因子”。
在本次调查中,合作型信任因子中各题平均得分与习俗型或契约型信任因子中各题平均得分基本都在3-3.5分中间,这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被调查社区里合作型信任度并不很高,而被调查者对“关系”和“熟人”的信任依然在较大程度上存在,即被调查社区中的习俗型信任仍大量存在。
接着,通过回归分析,对影响社区合作型信任成长的原因进行综合解析,即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职业、政治面貌、居民时间与居住地区等居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以合作型信任因子、习俗型或契约型信任因子中各题的均值(其中习俗型或契约型信任因子中各题的均值采用反向计算的方法)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综合考察影响社区合作型信任成长的各种因素,分析后得到如下回归方程:Y=0.233-0.039X1-0.01X2+0.138X3+0.101X4-0.25X5+0.241X6+0.32X7+0.297X8+0.039X9+0.108X10+0.164X11+0.053X2+0.476X13+0.742X14-0.059X15+0.066X16+0.001X17-0.483X18-0.087X19-0.331X20+0.087X21+0.205X22(其中:Y:社区合作型信任,X1:性别,X2:年龄,X3:月收入,X4:文化程度,X5:企业、事业单位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X6: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一般办事人员;X7:专业技术人员,X8:私营企业主,X9: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X10:个体经营者,X11:工人,X12:农林牧渔劳动者,X13:学生,X14:离退休人员,X15:下岗失业人员,X16:其他,X17:居住时间,X18:共青团员,X19:民主党派,X20:群众,X21:郊区,X22:郊县)回归方程的确定系数即模型的解释力R[2]=34.4%,说明自变量所有居民背景变量对因变量社区合作型信任的解释力一般。而在所有背景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学生、共青团员与群众比其他背景变量对因变量社区合作型信任有更显著的影响。
回归模型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社区居民的合作型信任度不断下降,而月收入对合作型信任有正向影响,随着收入的提高,社区里合作型信任程度也不断提高。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社区居民的合作型信任度也不断增加。在职业方面,社区里的离退休人员的合作型信任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高,离退休人员的合作型信任均值比党政机关干部高0.742分。最后,在政治面貌方面,共青团员比中共党员的合作型信任均值平均低了0.483分,群众比中共党员的合作型信任均值平均低了0.331分。
三、后工业社会的合作型信任:信任之理想类型
信任不仅对一国的繁荣与竞争力有重要影响,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信任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基本关系,也是编织政府与公民之间合作与互动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本研究的调查与分析向我们昭示:“习俗型政府信任”、“契约型政府信任”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大量存在,而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离合作型信任仍然路途遥远而漫长。这个调查结论与2006年的“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调查有较多的契合之处。而这两次调查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在多元社会形态并存的中国有着很大的生存空间。这种多元信任同生共存的生态格局,对中国当下多元社会形态并存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有着积极意义。但是调查结果还显示,对同一社会形态中的信任类型而言,三种信任的发展并不均衡,依靠“关系”、“熟人”等元素维系的习俗型信任仍占相当大比例,而代表未来信任发展趋势的合作型信任相对缺失,这对基层民主和社区治理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基础性障碍。因此,构建合作型信任关系对当下中国社会治理至关重要。
合作型信任是一种良性社会信任,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一种良性的社会信任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相当重要。在人类步入后工业社会的今天,对合作型信任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社会治理及其发展必须得到合作型信任的支持才能实现。合作型信任“是一种‘预先承诺’,是一种装置,依靠它我们就能对我们自己施加一些限制,而且因此限定其他人不得不对于我们的可信赖性的担心程度”[8](P221)。这两种信任决定了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对待同一个人,或同一场合对待不同人的关系和态度。因此,它们是特殊主义取向的,习俗型信任是一种魅化的信任,自然形成与惯性相继决定了此种信任类型下人的不觉醒;契约型信任是一种基于功利谋划的信任,谋私利己的功利驱动导致个人主义膨胀。这两种信任都不利于现代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的成长。合作型信任的形成更有利于草根民主与公共精神的培育与成长。[8](P141)源自人类道德自觉、满足人性向善需要的合作型信任对建构和谐社区与文明社会是必要的,它作为一种强大而持久的社会资本,不仅维持着社会稳定,而且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繁荣。
四、合作型信任之未来成长与展望
合作型信任关系可以使公众更加坦诚和充分表达自己的合理期待和愿望,也是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和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础。“当对彼此都有某种好的印象的双方或多方允许这种关系达到预期的效果时,信任便发生了”[9](PP250-257)。因此,对于有理性的公民来说,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型信任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是一种能够造就合作和促进合作的信任关系。在重建社区居民间合作型信任关系过程中,社区居民间以及政府与居民之间必须进行必要的合作和互动,政府的积极作为和有效的制度供给也必不可少。
阿尔蒙德等学者发现,教育可能是政治文化变革的重要源泉,它将会使人们变得适合于新的政治社会和政治行为模式的进程。[10](P181)现代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培育是构建合作型信任关系的基石,因而,加强公民素质培养与现代公民意识教育就成了建构合作型信任关系的必备之功。传统的道德教育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合作型信任关系建构过程中对公民精神的需要,塑造现代公民意识才是实现合作型信任关系建构的合理转向。中国历来不缺乏优秀的文化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互助与团结已深深融入进这个民族的血脉之中。深入挖掘并合理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给养,结合西方成熟公民社会的成功经验,积极培育现代公民精神、公民美德与公民意识,就能够促成合作型信任的星星之火延绵不绝,并形成光耀中华大地之势。
新共和主义视野中的现代公民意识与公民美德教育强调公民对国家的责任,强调公民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极力倡导通过公民教育培养有责任心的公民。金里卡指出:“通过公民教育,孩子们意识到了其他生活方式的存在,并且学到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去理解和评价其他生活方式”[11](P342)。英国“DfES”部门进一步描绘了关于公民教育的几个关键能力和行为。例如,在课堂内外培育自信心和负责任的社区参与行为;在生活中培育参与意识以及对社区事务的关切;通过技能和价值观以及知识使自己在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事务中发挥有效作用。[12](P7)可见,在公民意识与公民美德教育过程中,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相关措施保护公民权利,同时注重公共精神的培养,倡导公民对公共事务的民主参与意识,并提供有效的制度来实现公民参与。应当通过公民教育和公民权利保护来培育构建合作型信任关系的有利环境,并且依靠合作型信任来更好地实现政府与公民间的互动,在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同时,使公民权利得到最大程度实现。只有草根社会中的公民具有浓厚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具备积极、自治、真实、信任的公共参与,未来后工业社会的合作型信任之理想境界才会逐渐成为真实图景。
收稿日期:2010-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