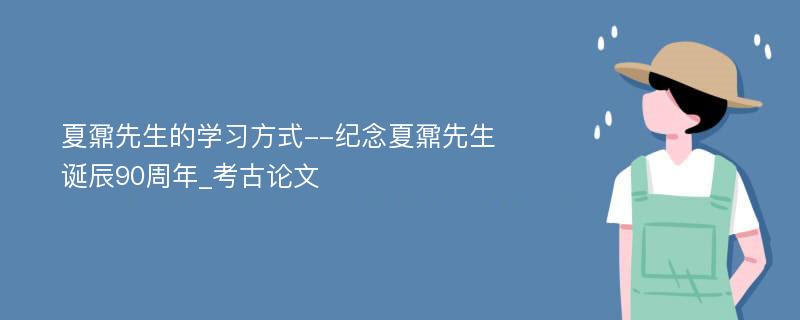
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纪念夏鼐先生诞生9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夏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卓越学术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已将夏鼐先生论著汇编为《夏鼐文集》,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过去出版的夏鼐先生论文集有《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和《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本文提到夏鼐先生论著,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二书。)。
一
夏鼐先生出生在一个经营丝绸业的商人家庭。少年时代就学于培育过众多知名人士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初中部(现名温州中学),后转至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他那勤于思考、善于钻研的好学精神,当时即已有所表现,曾在光华附中的刊物上发表与知名学者吕思勉商榷的文章,从科学常识和文字训诂上对“茹毛”指“食鸟兽之毛”的说法提出质疑。进入清华大学以后,夏先生在陈寅恪、钱穆、蒋廷黻等的指导下,进一步打下深厚的史学基础,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后转中国近代经济史,曾发表若干篇资料翔实、考证精到的论文,开始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随后,他以优异成绩取得中美庚款留学资格,决意出国学习现代考古学。为了做好出国前的必要准备,他于1935年春以实习生的身份前往安阳殷墟,参加梁思永主持的殷代王陵区的发掘,从此走上以田野考古为终身事业的漫长道路。
1935年夏,夏鼐先生经有关方面同意,改赴英国伦敦学习。那时的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可称全世界科学考古学的最高学府。日本考古学的奠基人滨田耕作,就是在那里师从彼特利(W.F.Petrie)教授,从而将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引进日本的。夏先生留学伦敦大学时,彼特利教授已经退休,田野考古学课程改由惠勒(M.Wheeler)教授负责。 他受教于惠勒教授,参加过由惠勒领导的梅登堡(Maiden Casrle )山城遗址的发掘,又曾在随英国调查团去埃及、巴勒斯坦进行发掘期间,谒见定居耶路撒冷的彼特利教授,得到这位考古学大师的直接教导。当时,夏先生的主攻方向是埃及考古学,他师从伽丁内尔( A. H.Gardiner
)教授,学习深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又在格兰维尔(S.Glanville)教授的指导下,对古代埃及的各种珠子进行了系统的类型学研究,成为我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专家。他的长篇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珠子》,至今仍是这一方面值得称道的重要论著。
1941年夏先生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争关系延至1946年正式授予),回到抗日战争中的祖国后方,投身于中国考古学的广阔天地。他先是参加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的发掘。后与向达共同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经费严重不足、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前往甘肃敦煌和河西走廊进行为期两年的艰苦考察,对新石器时代和汉唐时期的考古研究作出令人刮目相看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夏鼐先生领导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历时30余年。他致力于考古工作队伍的建设和实事求是优良学风的形成、考古研究规划的制定和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多种学科研究的协调、以及与外国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
建国初期,掌握田野考古技术的专门人才奇缺,急需迅速建立和健全考古工作的队伍,以应付国家基本建设发展的严重局面。当时,郑振铎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身份兼任科学院考古所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作为既在国外受过正规科学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田野考古学家被任命为副所长,协助郑振铎所长主持考古所的业务活动,指导全国的田野考古工作。由于梁思永先生卧病已久,行动不便,只有夏先生能够亲临田野考古的第一线。他到任刚刚一个星期,便率领当时考古所的全体业务人员(共计12人),前往河南辉县进行规模较大的示范性发掘。以后又连年为协助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并为中央和部分省区考古人员训练班的举办而尽力,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并曾多次进行实地操作辅导,从而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培养一批得力的业务骨干,使科学的考古发掘普及全国,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
夏鼐先生一贯坚持考古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工作,强调提高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要求大家在考古调查发掘中认真辨别复杂的地层情况,弄清楚遗迹、遗物的各种关系,并且要把观察到的一切有关现象详细正确地记录下来。1950年末,夏先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中,冒着严寒,以其娴熟的发掘技巧,第一次成功地剔剥一座大型的战国车马坑,被国际考古学界誉为战后田野考古方法的一项新的进步。1958年,他在北京明定陵的发掘中,忍着病痛,连日深入地下玄宫,匍伏清理棺内散乱的冠冕等物,耐心观察和记录种种细微迹象,使之得以恢复原来的形状。夏先生以其实践告诉大家:考古工作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你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看你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切忌有“挖宝”思想。
1962年,夏鼐先生在《新中国的考古学》(注:《考古》1962年第9期。)一文中,曾经通过总结已有的考古研究成果, 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课题归纳为:人类起源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时间问题、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问题、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文化问题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问题、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问题。多少年来,夏先生正是根据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部署考古所这一考古研究中心机构的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工作,有计划地着重进行黄河中下游和邻近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夏文化的探索和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以及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考古研究,并且注意开展甲骨文,金文,简牍、石刻等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为建立和完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作出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同时,先生还经常通过个别交谈和书信往来,耐心细致地帮助各地同志明确学科要求,解决田野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性问题。他曾多次亲临重点发掘工地,例如70年代以后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广州南越王墓、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等项发掘,都曾进行过具体的现场指导,直到突然与世长辞的前几天,还前往偃师商城遗址视察工作。在夏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我国一系列重点发掘工作显示了较高的科学水平,赢得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称赞。
夏鼐先生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突出地表现在及时将碳十四断代法引进我国。早在1955年,美国科学家开始发表有关著作之后不久,他便对其重要意义有了明确的认识,呼吁早日建立中国自己的实验室以应考古工作的需要。正是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多方筹划,考古研究所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于1965年建成我国第一座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并且在以后的全国同类实验室中长期居领先地位,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研究,发挥了非常显著的推进作用。夏先生还积极倡导考古学界与有关科技单位之间的协作,有计划地开展出土文物中金属、陶瓷和其他制品的自然科学分析鉴定,在判别一些器物的原料成份及其产地,究明它们的制作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夏鼐先生本人的学术研究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和且治学严谨的特点。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而且对中国传统的文史学、金石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从而善于把多方面学问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还具备优越的外国语文的条件,在与国外著名学者保持广泛联系的同时,经常涉猎大量新出版的外国书刊,因而通晓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各种动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研究工作便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善于从世界范围和多学科角度考虑中国考古学问题,既能追求现代的国际水平,又能发掘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我们长期在先生身边工作,还清楚地知道他撰写的每一篇学术论文,都是从收集资料、查对文献到成文清稿,乃至设计各种插图等等,事无巨细,亲自动手,从不假手于人,直到晚年仍然如此,为考古界树立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良师风范。
夏鼐先生在建国以后,特别是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坚持认为,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作研究不应局限于鉴别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及制作方法,而是应该将研究的最终目标指向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这便要以科学的调查发掘为基础,通过对大量实物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多学科研究,经过归纳,加以提高,进而从理论上探讨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他坚信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的研究,甚至歪曲事实真相,也反对忽视理论,脱离历史,重蹈为考古而考古的覆辙。
夏鼐先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我国与世界各国在考古学领域进行学术交流的总代表。他的卓越学术成就,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成为我国学术界接受外国国家级最高学术机构授予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这是夏先生本人的荣誉,也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光荣。
二
夏鼐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贡献,首先表现在对中国史前考古学进行了长时期的创造性研究,不断地拓宽道路,引导大家走向新的境地。主要是根据可靠的发掘资料,改订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编年体系,规范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多元说。他还是现阶段最早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著名学者。
建国以前,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基础相当薄弱,作过正式发掘的典型遗址为数甚少。20年代初期,应聘来我国工作的瑞典学者安特生,根据甘肃地区缺乏地层关系的实物资料,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划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后又臆测各期的绝对年代。1931年,梁思永在黄河中下游确认龙山文化,并从地层上判断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相对年代,揭开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科学化的篇章。后来,尹达根据类型学分析,判定安特生所说“仰韶文化”包含龙山文化因素,推断齐家文化不可能早于仰韶文化。夏先生则在40年代中期,通过对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从地层学上确认了齐家文化晚于甘肃仰韶文化(即“马家窑文化”),最终纠正了安特生的错误。他又因临洮寺洼山遗址的发掘,第一次提出中国史前时期的文化系统问题,认为晚于马家窑文化的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是同一时代的两种文化,沙井文化也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相互之间并没有因袭变迁关系,并且推测寺洼文化可能和文献记载中的氐羌民族有关。这便宣告,曾有相当影响的安特生的分期体系已彻底破灭,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的逐步展开,许多地方发现前所未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过去习用的几种文化名称已经难于概括。面对这种日趋复杂的情况,如何正确进行新的文化区分和命名,便成为考古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1959年初,夏鼐先生应各地同志的要求,及时发表《关于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问题》(注:《考古》1959年第4期。)一文,对什么是考古学文化、 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以及定名的条件和方法等问题,给予科学的明确回答。文章指出,考古学上的“文化”是指某一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观察的一群东西的总称,用以表示考古遗迹中(尤其是原始社会的遗迹中)所反映的共同体,通常以第一次发现典型遗迹的小地名来命名。文章又说,这样命名是想用简单的名称来表示一种特定的含义,以便大家在共同使用时互相了解,不致产生误解。他认为确定新的“文化”名称,需要具备三个条件:(1 )必须是有一群具有明确特征的类型品。这种类型品,经常地共同伴出,而不是孤独的一种东西。(2)这种共同伴出的类型品,最好是发现不止一处。(3)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至少有一处遗址或墓地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夏先生的基本态度是从实际出发,慎重处理,既不要迟疑不决,以致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时间的混淆在一起,延缓研究工作的进度;又不要轻率浮夸,看到某些片面的个别现象,就匆忙地给它一个新的名称,造成一些不应有的纠纷。他不赞成直接用历史上的族名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认为那只适用于年代较晚的一些文化,并且必须是考据无疑的,否则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而另行交代可能属历史上的某个民族,以免因乱扣帽子而产生种种谬论,反而引起历史研究的混乱。夏先生还预见到,区分考古学文化时,对“哪些可以算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哪些只是由于地区或时代关系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两个分支”,即在考古研究中如何界定文化、类型和分期的问题,学者之间会有不同看法,需要留待将来再作详细讨论,启发大家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夏先生的这篇文章,统一了我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从而极大地推进考古研究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布、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使之出现新的局面。
夏鼐先生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又一重大贡献,是他于1977年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注:《考古》1977年第4期。 )一文,根据当时公布的各种史前文化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它们之间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亦即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问题。该文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独到看法,尤其可贵的是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其实夏先生早就考虑这个问题,在1962年发表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便曾提到:“根据考古资料,现今汉族居住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连黄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也有很大的差异。古史传说中也有这种反映。”在上述1977年的文章中,他重提并发挥这一论断,指出所谓文化类型的不同是“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他在此文中又说:“当然这并不排除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有互相影响,交光互影。这种看法似乎比那种一切都归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响的片面性的传播论,更切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能说明问题。”要之,中国远古文化的发展由传统的黄河流域一元说改变为并非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是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最近20多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使多元说进一步确立,成为我国多数考古学家的共识。
夏鼐先生早就重视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60年代初期,他在《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的序言中特别讲到早期新石器文化,指出这在当时我国几乎是空白,而西亚的前陶文化遗存对于我们的探索有借鉴作用。陕西西乡县李家村遗址发掘以后,许多学者怀疑李家村文化遗址的年代未必早于仰韶文化。夏先生却根据李家村遗址所出圈足钵、直筒形三足器等独具特征的陶器曾见于宝鸡北首岭和华县元君庙仰韶遗址中的最早期墓葬或底部文化层的事实,当即表示李家村文化可能年代较早,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新线索(注:《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考古》1964年第10期。)。后来,李家村的一件标本经碳十四测定年代晚于仰韶文化,有的学者又怀疑起来,而夏先生则明智地指出测定年代与地层堆积前后颠倒“是难以接受的”,后了解到那件标本出土的地层情况不明时,便断然将该数据摒弃不用,仍然认为李家村文化的年代较早。磁山、裴李岗的文化遗存发现以后,他曾亲赴磁山遗址发掘现场视察,后又满怀喜悦地指出,“如果继续上溯,或可找到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的起源。”(注:《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经过广大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努力, 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更大的突破,先后在北方和南方的若干地点发现距今10000年左右的农业遗存。
随着有关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夏鼐先生又于1983年提出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中国史前考古学和世界文化史上至关重要的课题,强调其理论意义在于“传播论派和独立演化派的争论的交锋点”。(注:《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他从明确基本概念入手,强调“文明”一词是“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他还详细指出:“这个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衙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夏先生认为:根据现有考古资料,不仅深刻地认识到殷墟文化是高度发达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二里冈文化和更古老的二里头文化,三者互相连系、一脉相承;而二里头文化,至少它的晚期既够得上文明,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至少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各种文化,都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夏先生还特地讨论中国文明是否独立地发展起来的问题,着重分析那些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主要是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晚期新石器文化,断定“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夏先生还曾讲到,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同时又强调“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这便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指明方向,从而导致此后有关研究和讨论长盛不衰,不断深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三
夏鼐先生说过,考古研究进入“历史时期”,便要掌握狭义历史学中的大量文献和运用文献考据功夫。夏先生在历史考古学方面的一系列论著,突出地反映他本人熟知文献资料,擅长历史考据,善于从丰富的考古资料出发,结合可靠的文献记载,不断进行新的探讨。
40年代后期,夏先生根据甘肃考察所获考古资料,发表过两篇蜚声史坛的考据性文章。《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对1944年敦煌两关遗址和烽燧遗迹发掘出土的30余支汉简进行考释,判定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提出玉门关设置年代的新看法,又就汉武帝征和年号问题纠正了近人将其释作“延和”的谬误。《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一文,则在考释当地发掘所获金城县主、慕容曦光两方墓志的基础上,结合早年出土的四方慕容氏墓志,参以两《唐书》、《册府元龟》、《通典》、《资治通鉴》等文献资料,用年表的形式对吐谷浑晚期历史作了详细的叙述。
建国以后先生亲自主持和具体指导的田野考古工作,除渑池仰韶村等史前遗址的调查外,绝大部分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其中尤以50年代初期的几项工作意义为大。例如:辉县琉璃阁的发掘,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早于殷墟的商代遗址;郑州附近的调查,确认二里冈是早于殷墟的又一处重要商代遗址;长沙附近的发掘,初步判明当地战国两汉时代墓葬的演变情况,为楚文化的考古研究打下基础。这样,便使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在地域上从北方的黄河流域扩大到南方的长江流域,在年代上从石器时代、商周时代推延到汉代以至更晚,过去那种“古不考三代以下”的不合理状况,开始发生彻底的改变。
夏鼐先生关于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论著,往往是在对具体学术问题作独到论断的同时,又从方法论上给人以深刻启示,引导大家正确对待文献资料,深入细致地研究各种问题。例如夏文化问题,50年代末期当这项探索性考古工作开始着手进行的时候,他曾在考古所的会议上再三申明,对于所谓“古史传说”资料需要审慎地对待,这类资料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传的真正传说,又有先秦诸子编造的历史哲学。1977年有关单位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以后,有的学者认为王城岗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夏先生针对当时众说纷纭中的胡涂观念,着重从基本概念上进行澄清(注:《谈谈探索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他说:“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有人以为仰韶文化也是夏民族的文化,纵使能证明仰韶文化是夏王朝祖先的文化,那只能算是“先夏文化”。夏王朝时期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能算是“夏文化”,不仅内蒙、新疆等边区的夏王朝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化不能称为夏文化,如果商、周民族在夏王朝时代与夏民族不是同一个民族,那也只能称为“先商文化”、“先周文化”,而不能称为“夏文化”。他又指出:夏文化问题在年代学上很麻烦,商年和夏年都有悬殊较大的不同说法,目前并没有弄清楚;夏都的地理位置也很麻烦,“禹都阳城”说出自上距夏禹两千年的《孟子》,另外还有禹都安邑的说法,纵使“禹都阳城”可信,它和东周阳城是否一地仍需证实。这种周密思考、认真分析的科学态度,推动了夏文化探索工作的发展,使有关研究不断深入,现已取得较多的共识。
夏先生关于商代和汉代玉器的几篇文章(注:《有关安阳殷墟玉器的几个问题》,见《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商代玉器的分类、命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所谓玉璿玑不会是天文仪器》,《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在玉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首先,他注意探讨中国古玉的质料和原料产地,提倡对各地出土的玉器多作科学鉴定,从矿物学上判别它们的结构和所含元素,以便与地质矿产资料比较分析。其次,他强调正确判定玉器的类别、名称和用途,不能继续采取吴大澂那样的“诂经”方法,而应改变为谨慎的考古学方法,即根据考古发掘所见各种玉器的出土情况,以及它们的形状,结合传世品和文献资料考证其古名,无法判定古名的另取简明易懂的新名,用途不明的暂时存疑。他又着重论述礼学家所谓“六瑞”以礼天地四方的传统说法,指出这显然是战国和汉初儒生理想化的礼器系统,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强调历年发掘的上万座先秦两汉墓葬所出大量玉器并没有某种玉色和某种器形的特别结合,而汉儒关于周代葬制中六种玉器(璧、琮、圭、琥、璜)摆放位置的说法更是出于杜撰。夏先生还从器物形态的发展上论证,过去被称“璿玑”的这种周缘有三节牙形突起的玉器,实际是璧的一种,是带有礼仪和宗教意义的装饰品,而决不会是天文仪器,不必为其使用方法枉抛心力。他主张根据这种玉器形制的差异,分别命名为“简单三牙璧”和“多齿三牙璧”,总称“三牙璧”或简称“牙璧”,而将“璿玑”一名放弃不用。先生又考虑到,玉器研究中常被引用的《尔雅》所记璧、瑗、环三者的“肉”、“好”比例,无论怎样解释都与大多数实物不符,建议将这类玉器统称璧环类,或简称为璧,而将其中孔径(“好”)大于全器二分之一者特称为环,“瑗”字则因原义不明可放弃不用。这样,便为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开辟新的途径,使古玉研究从礼学家烦琐考证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对历史考古学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夏鼐先生对古代葬制方面的问题,更是从考古发掘所见实际情况出发,考证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对照起来进行研究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以前,在许多论述中对如何区分棺椁存在着一定的混乱。夏先生于1973 年发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棺椁制度》(注:《考古》1973年第6期。)一文进行辨析, 认为椁室是用厚木材在墓坑现场搭成的,内棺和外棺则是预先做成的“有盖的木盒子”,可以整体迁移,盛放尸体后套合起来葬入墓中。该文论据中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四层套棺均内外涂漆,而棺室的各个部位却不加髹饰,彼此区别是非常明显。弄清楚棺椁界限这个葬制上的基本问题,避免继续在礼书记载的个别文字上打圈子,便使棺椁制度的研究前进了一步。夏先生还最早列举汉代“玉衣”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进行考证(注:《关于“金镂玉衣”的资料简介》,《考古》1972年第2期。), 指出这种葬服在汉代文献中一般称“玉匣”或“玉柙”,偶尔称为“玉衣”,战国墓葬发现的缀玉面幕和衣服可能是“玉衣”的前身,也可能就是《吕氏春秋》中的所谓“鳞施”。他又指出,汉代的皇帝和贵族使用“玉衣”埋葬的重要原因,可能是迷信“玉衣”能够保存尸体不朽。
夏鼐先生对历史考古学的重要分支铭刻学非常重视,集殷周青铜器铭文大成的《殷周金文集成》,就是在他的亲自筹划和具体指导下编纂的。他为《集成》撰写的长篇前言中,对考古学(包括它的组成部分古器物学)和铭刻学的涵义,以及中国铭刻学的特点作了详细的阐述。该文指出,铭刻学研究“包括认识文字、读通文句、抽绎文例、考证铭文内容(例如考证纪年、族名、邦国、人名、地名、官制和史事等),以及根据字形、文例、考证的研究结果,来断定各篇铭文的年代和它们的史料价值。”他说,铭刻学研究除将铭文中的古文字经过考释改写为今日的楷书以外,“它的考证方法,和利用传世的一般古代文献记载一样,完全是属于狭义的历史学范围。”夏先生还严肃地批评,“现下仍有个别搞铭刻学的人,过分强调铭文的解读,有时完全不顾古文字的原则或通例,将一些不易考释的铭文中每字都加考释,每句都加解说,实际上不过是‘穿凿附会’而已。”先生不仅对铭刻学研究发表如此重要的指导性意见,而且亲自进行过某些具体的考证。例如,他曾列举传世秦戈,补释长沙新出吕不韦戈铭文,指出秦戈铭文中“职官名的后面都是或仅举人名,或兼举姓氏和名字,但没有仅举姓氏而不书名字的”(注:《最近长沙出土吕不韦戈的铭文》,《考古》1959年第9期。)。 他又曾根据《宋史》等书记载,印证长沙杨家山宋墓所出残缺姓氏墓志的有关文字,判明该墓墓主应为宋高宗时被秦桧罢官下狱的知名之士王趯(注:《长沙东郊杨家山南宋墓墓主考》,《考古》1961年第4期。)。再如,1972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陕西蓝田新出土的西周铜器永盂时,注意到铭文涉及的人名“井伯”见于穆王时器“长甶盉”和若干恭王时器,其人是周王左右的主要臣僚,因而判定永盂“应是穆、恭时期彝器。”(注:《考古》1972年第1期。)当时, 有一位古文字学家发表考释文章,将永盂考定为恭王时器,认为井伯是恭王时期的人,论证时虽曾提到长甶盉,却忽略该器铭文的“即井伯大祝射”一语,看到夏鼐的文章如此博通金文,赞叹不已。
四
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是夏鼐先生极为重视的一个方面,他为此花费很大的精力,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50年代初期,他根据自己亲手发掘的辉县战国车马坑和长沙汉代车船模型,进行古代交通工具的复原研究。60年代起,先生又创造性地利用考古学的资料,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深入探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中天文、纺织、冶金和其他方面的光辉成就,主要研究成果编集为《考古学和科技史》一书。他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同名文章被列于该书卷首作为“代序”,对1966年以来我国考古工作中有关科技史的新发现,归纳为天文和历法、数学和度量衡、地学、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纺织陶瓷和冶金、医学和药物学、农业科学等专题,进行全面的介绍。这实际是想说明考古资料对于科技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借以促进考古学家与科技史专家之间的协作,共同解决考古学上和科技史上的重要课题,使科技史研究得到更好的发展。
夏鼐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方面,主要是对几幅有代表性的古代星图进行了研究。我国古代的星图有两类:一类是天文学家所用的星图,它是根据恒星观测绘出天空中各星座的位置,一般绘制得比较准确,所反映的天象也比较完整。另一类是为宗教目的而作象征天空的星图和为装饰用的个别星座的星图。先生作过详细考察的有:后一类星图中我国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洛阳西汉壁画墓星象图,最早表现黄道十二宫的宣化辽墓星图;前一类中现存年代早的唐代敦煌星图(注:《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见《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洛阳西汉壁画墓星象图发现以后,有人对比现代星图提出过解释,由于不了解中国古代天文学和西洋天文学的起源不同,所作解释必然有很多不当之处。所以,夏先生的讨论便从辨明正确的研究方法入手,提出:(1)这星图的内容,并不是比较全面地表现北天的星图, 仅仅是选用少数几个星座,因而只能用我国古代星座对照,不应该用西洋星座对照;(2)这星象图是西汉末年的, 应该以《史记·天官书》作为主要的对比材料,而以《晋书·天文志》所载作为补充;(3 )比较不能漫无边际,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北天亮星的几个星座和天球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宿,它们可能是古人绘制星象图时用以选择的主要对象。经过这样的重新比较,先生确认这星象图既不是以十二个星座来表示十二次,更不是象征十二辰,只是从汉代天官家所区分的“五宫”中每“宫”选取几个星座用以代表天体而已。
夏鼐先生关于宣化辽墓星图的论文,根据辽墓壁画中的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图象,结合大量文献资料,进一步论证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特点,指出以赤道为准的二十八宿显然是起源于中国,后来由中国传入印度的,而黄道二十宫则至迟在隋代,随着佛经的翻译由印度传入中国(王仲殊在研究铜镜的论文中对此说作过补充)。至于我国二十八宿创立的年代,他认为“由可靠的文献上所载的天文现象来推算,我国二十八宿成为体系,可以上推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 真正的起源的可能稍早,但现下没有可靠的证据。至于文献学方面的考据结果,也和它大致相符而稍为晚近,现下只能上溯到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而已。 ”夏先生的意见,被公认为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中对于二十八宿创立年代这个聚讼纷纭问题的较为稳妥的提法。
关于敦煌写本中的两件唐代星图,夏先生将现存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一件称为甲本,现存敦煌县文化馆的一件残卷称为乙本。他所进行的探讨,首先把甲、乙二本的紫微宫图各星官列成一表进行比较,发现两种星图的内容与《丹元子步天歌》所述最为相近,而与《晋书》、《隋书》二史《天文志》的记述差异较多,但都属于一个系统。继而又就两本之间的大同小异互相对比,感到乙本的原来蓝本在星官数和星数方面,实稍胜于甲本的原本,但仍是一个系统的两个不同本子;至于两本中各星官的形状和位置,一般而论,都绘制得不很正确,却又没有很大的错误。先生又将甲、乙二本的抄写年代和《步天歌》的撰写年代一并讨论,认为《步天歌》的撰述时代不能早于李淳风活动的时代,歌辞和诠释的作者应该都是唐开元年间道号丹玄子的王希明;进而推测敦煌星图的原本应是根据《步天歌图》,它不会比《步天歌》的撰写年代(唐开元时即公元8世纪前半)更早,但其转抄的年代稍晚,甲本在开元天宝, 乙本在晚唐五代。这比英国李约瑟将甲本的年代定为后晋天福年间(公元940年),提早了200年。乙本则是第一次进行如此缜密的研究。
夏鼐先生是我国学术界根据考古资料进行纺织史研究的先驱。早在20年代,西方学者即已进行新疆出土汉代丝织品的研究,我国学者则开始于60年代初期。1961至1962年,先生通过新疆民丰、吐鲁番两地新发现的汉唐丝织品的若干残片和一些照片,参考过去其他地方出土的有关资料,考察汉唐时代绮、锦和刺绣的纺织工艺与图案纹样,并附带讨论中西交通史上的问题。1972年,他又发表《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一文,系统论述我国汉代和汉代以前养蚕、植桑、缫丝和织绸方面的发展情况,并对汉代织机进行新的复原研究,以进一步阐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类文明的这一伟大贡献。
夏先生指出:发明蚕丝生产技术的确切年代,目前虽然还无法确定,但我国在上古时期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至迟在殷商时代已经充分利用蚕丝的优点,改进了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能够织成精美的丝绸,遗存实物有普通平纹、畦纹和文绮三种织法。他说,我国当时除使用竖机之外,可能也使用平放或斜卧的织机,这便和古代希腊、罗马等国家专门使用竖机不同,可能改进到使用吊综提花和脚踏。东周时期已有织锦,更应该是使用一种有提花设备的平放织锦机。先生又指出,我国的丝织生产发展到汉代至少已有1000多年历史,达到了一个高峰,五彩缤纷的汉锦代表汉代织物的最高水平,一般是使用二色或三色的组织法,如果需要四色或四色以上,便需要采用分区的方法,在同一区内一般都在四色以下。至于汉代的织机,先生根据实践经验,认真分析,指出有些学者所复原的织机“是不能工作的”。遂以铜山洪楼画象石中的织机图为主要依据,经多次讨论、反复试验和修改,重新作出比较合理的复原方案。他指出,汉代画像石上的织机都是简单的织机,但根据出土的锦、绮、文罗等实物,可以推测汉代已有提花机。当时,先生从织物花纹单元的高度和纬线的密度考虑,认为有时需要提花综四、五十片之多,推测汉代的织机已有提花设备,可能是“提花线束”,而不是长方架子的“棕框”。后来,他对自己的这一影响甚广的看法有较大的改变,1983年在日本的讲演中说:“汉代提花织物可能是在普通织机上使用挑花棒织成花纹的,真正的提花机的出现可能稍晚。”(注:《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6年。)令人遗憾的是,先生没有来得及具体论证自己的这一看法,便与世长辞了。
夏鼐先生在中国冶金史研究方面,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首先,他最早指出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所出铁刃铜钺可能是用天然陨铁制成的。 1972年台西遗址出土铁刃铜钺,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项重要发现,表明我国人民早在公元前14世纪已经认识了铁,因而迅速得到夏先生的高度重视。开始进行的技术鉴定,以为铁刃属古代熟铁。他考虑到人类在发明炼铁以前有时利用陨铁制器,而鉴定结果中铁刃的含镍量又高于一般冶炼的熟铁,当即表示鉴定并未排斥这铁是陨铁的可能,还不能确定其为古代冶炼的熟铁,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注:《〈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读后记》,《考古》1973年第5期。)。 后经先生约请钢铁专家柯俊重新组织鉴定,多种现代化手段的分析结果证明藁城铜钺的铁刃不是人工冶炼的熟铁,而是用陨铁锻成的(注:李众:《关于藁城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从而避免了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场混乱。众所周知,夏先生还纠正了我国早在3世纪的西晋便能提炼铝的错误说法。1953年宜兴周处墓发现17 件金属带饰,发掘者将一块碎片请人鉴定,分析结果为铝。由于炼铝是19世纪发明电解法后才被人们掌握的一种新技术,这项发现迅速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但是,后来有人分析的一块碎片,却是银制的。为了澄清事实的真象,先生请人采取几种不同的方法,对现存的全部带饰重新鉴定,检验结果都是银而不是铝。他注意到周处墓曾被盗扰,小块铝片有系后世混入物的重大嫌疑,因而建议大家不再引用它作为晋代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证据。夏先生又根据考古所有关同志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进行发掘的资料,讨论这处古代铜矿由竖井→横巷→盲井掘取矿石的过程,以及为采掘矿石而在提升、排水、通风等方面采取的相应措施,推想当年矿工利用发掘中见到的那些采矿工具进行采掘工作的情况,并且亲自设计了提升用木辘轳的复原方案(注:《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他还指出:田野考古学的引入, 使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今天,我们不仅研究青铜器本身的来源(出土地点),还要研究它们的原料来源。对古铜矿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这是中国青铜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新开辟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中国陶瓷史方面,夏先生没有发表过专题论文,但一直是非常关心的。50年代,他曾在《考古》杂志上特地介绍陶瓷专家周仁等的专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注:《介绍周仁等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考古》1959年第6期。), 对国内采取现代科技方法进行瓷器研究的这一开端表示热情的欢迎。这篇书评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所最感兴趣的,不是作为古董来玩赏的古瓷,而是制造这些古瓷的陶业工人。我们所以要分析和鉴定古代陶瓷的原料的成分、成品的物理性能和制造技术,只是因为它们是陶瓷工人的技术知识和手艺技巧的表现。此外,古代陶瓷工业还有另一方面,便是当时的审美观念。这便须要研究古瓷的器形 和花纹。……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仍不能算是对于古瓷的全面研究。”后来,正是在夏先生的约请下,周仁和他的几位助手对古代陶瓷标本进行大量的分析鉴定工作。这便使中国陶瓷史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此外,夏先生的研究还涉及科技史领域的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幻方》一文,讨论了中国引进阿拉伯幻方和数码字的经过,属数学史问题;《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一文,讨论石串珠蚀花技术及其年代和地理分布,属化学史问题;《梦溪笔谈中的喻皓木经》一文(注:《考古》1982年第1期。), 对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部重要技术著作,进行整理和校释;《略谈番薯和薯蓣》一文(注:《文物》1961年第8期。), 所论则属农业作物史上的问题,等等。
五
利用考古学资料探讨中西交通史上的问题,是夏鼐先生学术研究的又一重要的方面。他所进行的研究,既包括中国古代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与波斯、拜占庭、阿拉伯等国家之间的交往情况,又包括海上交通和古外销瓷等问题。
夏先生对我国各地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作过许多研究,例如对新疆、青海、西安、洛阳和定县等地出土的钱币,大同、西安和敖汉等地出土的金银器皿,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织锦,都曾撰写专文进行考察。在逐项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他又先后发表《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注:《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和《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注:《考古》1978年第2期。)两篇综合性文章, 进一步讨论中国和伊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还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
我国各地发现波斯银币的地点,大多数分布在“丝绸之路”的沿线,或者在它东端长安、洛阳到其他城市的延长线上,共计30余批1100多枚。据夏先生鉴定,这些波斯银币分别铸造于萨珊王朝中期和后期的12个国王在位期间,从沙卜尔二世(公元310~379年)到最后的伊斯提泽德三世(公元632~651年),延续近350年。 其中半数属库思老二世式的阿拉伯—萨珊银币。铸造地点明确的,几乎都在萨珊帝国的中部和东部。他认为,这些银币的发现反映了萨珊帝国的权力起落和经济兴衰,也反映了它作为中国和东罗马(拜占庭)之间的贸易中间站的历史地位与发展情况,并且恰好能同中国史书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特别是根据青海西宁的发现,他引证《法显传》、《宋云行记》和《高僧传》等书,提出从公元4世纪末到6世纪初,即东晋南北朝时期,中西交通路线除甘肃河西走廊一线外,西宁也在重要的孔道上。他说,当时由西宁进发,或经柴达木盆地北行过当金山口至敦煌,然后西行进入新疆,或经柴达木盆地南缘越阿尔金山至新疆的若羌,这条偏南的交通线之所以骤形重要,应与吐谷浑的兴盛有关。在夏先生提出此说以前,中西交通史研究者对这条路线却不够重视。
夏先生根据一些地方发现的萨珊式金银器和织锦,深入讨论波斯文物在中国的流传及其深刻影响。他说:在唐朝以前,萨珊朝金银器已输入中国,唐朝初期输入更多,并有中国的金银匠人模仿制作,可能也在波斯匠人在中国制作的。萨珊帝国复灭以后,直到安史之乱,仍有这种风格金银器的输入或仿制。中国制造的仿制品,一般器形和波斯所制大致相同,但花纹常是唐代的中国风格。而在瓷器、漆器和铜器中,也有模仿萨珊式金银器的情形。他又曾指出:古代丝绸的织造技术有两种不同的传统,中国汉锦是经线起花的重组织,西亚和中亚的织锦则采取纬线起花的方法织成;新疆发现的资料表明,中国丝绸的织造技术和花纹图案,经过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由于西方的影响发生很大的变化,6 世纪时有一种可能为外销而生产的萨珊式花纹经锦,后来中国织锦的织法也改用纬线起花。这些都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互相取长补短的具体事例。
对某些北朝和隋唐墓葬中发现的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夏鼐先生也都进行过考释(注:《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见《考古学论文集》;《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61年第8期;《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77年第6期;《西安唐墓出土的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年第8期。)。据鉴定,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所出三枚属狄奥多西斯二世(公元480~450年)和查斯丁一世(公元565~578年),西安土门唐墓一枚则为公元635 年阿拉伯人开始占领拜占庭部分地区后的仿制希拉克略式,而西安窑头村唐墓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则被判定为公元702 年阿拉伯首都大马士革的铸品,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奥梅雅朝(白衣大食)时期的金币,也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伊斯兰铸币。夏先生在文章中根据这些金币,分别讨论了中国和拜占庭、阿拉伯之间的友好往来及相关问题。
对于东西交通的海上航路问题,夏先生同样十分注意。他除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南京东晋王氏墓出土印度所产“金刚指环”、广东英德和曲江的南朝墓出土波斯银币等早期物证外,又专文讨论了泉州两种文字合璧的元代也里可温墓碑(注:《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 扬州拉丁文的元代天主教徒墓碑及广州明墓出土的威尼斯银币(注:《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年第6期。)。 先生还较早地研讨中国古外销瓷问题,曾于1963年撰文介绍东非各地发现的中国宋元以至明清瓷片,特别提到他本人于1938年至1939年两度前往埃及福斯特遗址调查,亲手采集到当地仿制的青瓷和青花瓷残片,说明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悠久的历史友谊(注:《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后来,他又根据在瑞典看到的一大批18 世纪中国烧制的“洋瓷”,讨论中国瓷器在当时采用西方的珐琅彩和“泰西画法”的情况(注:《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文物》1981年第5期。)。
夏鼐先生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一书(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对元代周达观这位温州同乡根据亲身经历记载柬埔寨吴哥时代真实情况的名著进行全面校勘和缜密注释,是他对中外交通史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真腊风土记》是同时代人对吴哥文化极盛时代柬埔寨的唯一记载,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即有多种译注问世。夏先生以数十年的积累,收集十多种刊本、抄本,以及中外学者的有关论著,博采众说,择善而从,使之成为目前最好的、可依赖的一种本子。这也充分反映他在文献考据方面令人叹服的功力。
附记:本文是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一书所写专文,现值夏鼐先生诞生90周年,本刊特刊此文以示纪念。
标签:考古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夏鼐论文; 中国考古学论文; 文物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田野考古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