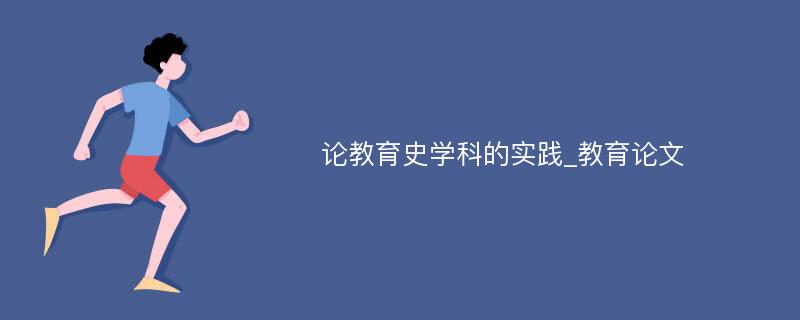
教育史学科如何走近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史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0)01-0032-06
从学术队伍来看,教育史研究者中既有教育学者也有历史学者,还有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但是从研究机构的设置来看,只有在师范院校的教育系或教育学院才有专门的教育史专业、专门的教育史课程(面向教育系、院或全校师范生)以及专门的教育史教师和专门的研究生,独自享有“教育史学科”的名称和地位。正因为这样的体制安排,才使人们有意无意地更倾向于把教育史学看作是一门教育学科、而非历史学科或者其他学科。
在教育学科的大家族中,所有的其他学科都有着强烈的、服务实践的学科抱负,教育史如果成为另类,必然难以获得平等的学科地位,因为“教育学科是人文学科中最具实践性、应用性的学科之一,它决定了教育史研究必须在梳理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积极服务当前教育实践”①。这样,“教育史的研究要能说明或解决当前的教育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对教育史由来已久的期望②。教育史学科的实用性问题由此而生。
然而令我们沮丧的是:“教育史学科确立一百多年来,它受到最多的批评即是对其缺乏实用性的指责”③。看到一些著名教育史学者发此感慨,不免使后学者如同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毕竟,人是一种追求目的和寻求意义的动物。但是,我们还是坚信,教育史学科是能够走近教育实践的,因为教育史本身就是教育实践与思考的历史记录,鲜明的具象性足以使它具有许多抽象的教育学科所难以匹敌的优势。教育史学科不缺乏走近实践的能力,而是需要找到走近实践的途径。
关于教育史学科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笔者以前曾经给予关注④,侧重谈了教育史学科何以要走近实践与能否走近教育实践之间题。本文则准备侧重探讨教育史学科走近实践的具体路径。在一定意义上说,讨论“能不能”的问题是无益的,关键在于“如何能”。
一、以史为鉴,树立服务教育实践的意识
教育史学科缺乏实用性,首先是因为教育史研究缺乏服务教育实践的意识,显得“太远”。
关于教育史学科应否追求实用性的问题,在教育史学界是存在分歧的。有学者认为:“满足于描述纯粹‘客观事实’的教育史学家已不多见,而相信教育史研究具有现实目的的人已占多数”⑤。但事实恐非如此。台湾师范大学周愚文教授就主张,教育史应力求打破教育与史学的隔阂,朝专门学术研究方向发展,如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在与历史学交融的过程中扩大新生领地⑥。他的思想就体现了一种纯史学路线的教育史研究取向。大陆史学界也有学者持近似的观点。
笔者认为,如果教育史不冠有“教育”之名,如果教育史学科归属于历史系,那么,我们只搞纯粹的史学性研究、不去追问这些研究有无现实性是完全可以的。当然,这只是一种不可能的假设。而即使在这些假设不可能的情况下,部分教育史学者的研究或者教育史学者的部分研究走纯史学路线也是完全可以的,并且是非常必要的。纯史学路线的教育史研究,是服务教育实践路线的教育史研究的基础。没有纯史学路线的教育史研究,服务教育实践路线的教育史研究就成为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教育史学研究是一项有分工的团队性工作。教育实践取向的应用性教育史研究好比钻头,历史学取向的基础性教育史研究好比钻杆。前者视历史为方法和工具,后者视历史为对象和目的。但归根结底,后一种研究的目的还是实用。在一个高度追求实用的时代和教育学这样一个具有很强实践使命感的学科系统中,如果远离实用,那么,教育史学科就难逃受歧视的厄运,因为我们放弃了学科的社会责任。
二、放下架子,开拓融入教育实践的途径
教育史学科缺乏实用性,还在于教育史研究成果很难为教育实践界的人们所看到,显得“太高”。
很多教育史学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得越高越好。越是著名的学者,越是只愿在“核心”、“权威”类刊物中发表文章。而这类刊物,教育实践界的人是很难看得到的。教育史学者写了许多“××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却不想让教育实践界的教师看,真不知道到底是要启示谁。这也是目前教育学诸学科的通病,虽然普遍存在,却很不合理。我们不是说不应该在“核心”、“权威”类刊物中发表文章,也不是说所有的教育学和教育史研究成果都应该写给教育实践界的同行。但是,如果所有的教育学和教育史研究成果都把发表到教育实践工作者看不到的地方作为最高理想,那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鸿沟首先就在信息流通的过程中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了,教育学和教育史的无用也就不可避免了。也许“制造”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些人也只是把服务教育实践作为一种口号说说而已,他们所追求的“有用”其实就是职称和科研经费。那么,这样的“成果”不“硬塞”给一线教师,也许倒是一件好事。
但是,一线教师毕竟还是渴望能够从教育理论研究、包括教育史研究成果中有所受益的。而我们的理论研究人员如果自觉其成果对他们还有些直接的用处的话,我想还是应该尽量发表在面向一线教师的刊物上。比如,《中国教育报》、《教师报》等,即几乎所有中小学都订阅的刊物。至于无直接的实用性,而只是教育理论界的内部探讨,自然另当别论。另外,在面向教育实践界的刊物上发文章,篇幅、语言都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鉴于网络的发展,论坛和博客也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界交流的很好平台。即使是发表在非实践类刊物上的学术论文,只要觉得能对教育实践有所帮助,作者不妨在论坛或博客中贴出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以扩大这些成果的社会影响,同时也扩大了教育史学科的社会影响。
近日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周勇先生的《跟孔子学当老师》一书。书中提到,他在“教师培训”课程中不仅经常与参加培训的教师一起讨论孔子和《论语》,而且还给他们讲“朱自清的中学教师岁月”、“寻找自己满意的教育与课程:朱熹早年的思想经历”这类题目⑦。笔者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讲的、听众是否欢迎(从该书汪洋恣肆的文风和它的热销可以推测,作者的课也同样精彩),但把教育史带进教师培训这件事本身就为教育史走进教育实践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而他的这部通俗生动却又大有嚼头的小册子,也称得上是“将孔子‘引见’给今天的教师”(郑金洲荐语,见该书封底)的一种很不错的方式。
三、与时俱进,了解教育实践问题与相关理论的发展
教育史学科缺乏实用性,还在于不了解当前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他教育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使教育史学科研究给人“太旧”之感。
所谓“太旧”,不是说教育史研究的是古老的材料(非此则不为教育史学),而是说我们得出的是人们早已熟知的结论。在这一点上,笔者比较同意单中惠先生对许多“借鉴与启示”类文章的批评,因为这些结论不过是一些套语——可以用来套任何一位教育史人物或者教育史事件。虽然结论的多少每次有所增减、填塞的史料每篇有所变化,但总之还是那些老生常谈、为人熟知的结论。当然,值得强调的是,教育史研究又不能彻底脱离老生常谈。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地方,在于往往不存在真正完全崭新的发现,也不存在毫无意义的重复。许多观点从孔夫子、柏拉图讲到现在,名异而实同;但是这些反复强调了千百年的东西在实践中却仍然存在问题,所以仍有反复强调的必要。以“量力性原则”为例,够老生常谈的了,但今日“减负”却仍然还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可见,有人讲过了的东西并不一定受到重视,或者得到贯彻。理论研究所做的,有时并非创新,而是变换角度、变换材料、变换方式地对着实践不断唠叨,直到能使一些东西逐渐深入人心、真正影响实践。无论是东方的孔子还是西方的耶稣,他们的学说都是在后人的不断反复言说中逐渐深入人心、直至浸入民族骨髓的,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因。爱因斯坦指出:“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强有力的性格的人重新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应雕塑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这种真理不总是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完全被我们遗忘掉”⑧。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家,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在对这样一些基本的教育真理进行不断重新刻勒的雕塑家。看看今天的教育学科以及一切社会学科,虽然一直在不断追求创新,却往往未跳出先秦诸子、“希腊三哲”这些古人的“一亩三分田”;更为令人汗颜的是,今人那些晦涩难懂、佶屈聱牙的观点,古人却用古老的文字和文体言简意赅、生动鲜明地表达了出来。今人往往误解了社会科学的创新性而一味求新,认为新的东西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如同病急的患者吃了两天药不见效就想换大夫、换处方一样,殊不知越是沉疴越需要慢慢调理。社会问题包括教育上的许多问题,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之道有时就在于耐心服用那些古老的处方药物。
这一点对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至少蕴含着如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不要刻意求新⑨。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和观点,因为其古,所以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也是一种新。通过教育史研究,我们得以与古人的心灵对话,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所感。我们经常会惊喜地发现,过去与现在虽然相隔久远,但我们的问题却有太多的相似。而那些智慧的先哲所说的,也正是我们所想说的,或者想而未透、说而未明的。如果我们同意教育是一种文化传统并且同意建构主义关于文化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观点,那么我们正是通过与古人的这种心灵对话而明确和坚定了关于教育发展的某些信念。教育史所能给予今天的人们的,首先正是这样一种来自历史的教育信念。再打个形象的比喻,其他教育学科喜欢“逛超市”,教育史学科则喜欢“翻箱底”,结果都可以穿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新装”。正如网上新闻所说的那样:“老奶奶压箱底的肚兜,成为爱美女性最钟爱的流行服饰”⑩。其实,衣服的新与不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给别人什么样的印象、从而决定了能给别人什么样的影响。
其二,要关注当前的教育问题。除了纯史学取向的教育史研究,其他的教育史学研究都应该与其他教育学科一样善于从当前的教育实践中寻找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实用性问题与教育史的学科智慧》一文中,我们不仅把教育史的“史”字看作是一种研究对象的界定,更看作是一种研究方法的界定:如果把“教育史”的“史”看作是一种方法论的界定,那么教育史学科就与它的延伸学科——比较教育学科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都对教育实践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只是前者从纵向上为当代中国教育实践寻求借鉴,研究对象距今越远,越是要注意时间距离问题(其实只是时代背景差异问题);后者从横向上为当代中国教育实践寻求借鉴,要注意空间距离问题(其实质是文化背景差异问题)(11)。把比较教育学与教育史做这样的对比,还有助于我们走出学科界限的牢笼。因为,比较教育学者并不管什么教育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管理、高等教育、学前教育的领地,凡有跨地域性的教育问题,他们都愿意加以研究,他们把学科的特殊性主要建立在比较这一方法论的基础之上。那么,教育史学者为什么要惴惴然怕侵犯了别人的领地?我们也可以把学科的特殊性只建立在历史方法的基础之上。同时,正如比较教育学不怕别人运用了自己的方法一样,教育史学也不必担心因此而失去自己的地盘。与比较教育学一样,教育史学应该以自己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的角度对现实教育问题提出自己的解答、乃至提出自己的理论。即使我们不能提出自己的解答和理论,也至少应该能为其他教育学者新的教育理论提供历史的证明。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历史的证明,各教育学科的学者往往自己来做。他们大抵不是把我们的教育史研究成果直接作为“镜子”,而是作为“地图”。在其他教育学科的学者中,有些人鄙薄教育史学者,却并不鄙薄教育史本身。他们喜欢读教材类的教育史著作。他们在这些著作中不一定能直接找到有用的材料,但借助它们却能够从史料堆中找到有用的材料。所以,对于教育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即使心存感激,也只是一种旅行者对于地图的感激。由于缺乏系统的教育史学训练,非教育史学者利用教育史为自己的教育理论所提出的证明,在很多受过教育史专业训练的人看来是漏洞百出的。他们或者由于教育史视野的狭窄,或者由于观念上的先入为主,在对史料的选择和引证中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许多重要的东西,以此来片面地支持自己的理论。至于那些不肯做更深入的教育史研究而只满足于从教育史教材中寻找理论支持的人,就像那些把看地图或导游图当作实地旅行的人一样,他们以教育史为证明的研究就更加简陋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轮到教育史学者来鄙薄他们了。但是仅此而已,教育史学者没有其他教育学者那样的理论创新勇气,也拒绝从教育史的学科立场对别人的创造性工作给予支持或者批评。许多非常热闹的教育和教育学问题论争,可以吸引各种学科的学者参与其中,唯独教育史学者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鲁迅《自嘲》)。事实上,鉴于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和教育实验研究的缜密性,对教育问题的最好的解答恰恰应该来自教育史,因为教育史是教育思想最理想的实验场。正因为如此,教育史学家绝不应该在当代教育问题的讨论中缺席,而要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三,要关注当前教育学界和其他相关社会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教育史研究必须努力走入古人的教育实践和观念世界。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我们以怎样方式走进古人的世界?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一切学习都必然建立在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结构基础之上。教育史研究者要进入古人的教育世界,不是带着空空如也的头脑,也不可能带了古人的头脑,而是用自己的头脑带了现代的教育问题和观念。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以我们自己的现有观念去理解古人(12)。古人的教育智慧将会启示我们,但这种启示绝不是完整的、也绝不是原原本本的,而只能在我们已有的智慧基础之上促进这种智慧的生长。智慧是智慧与智慧碰撞产生的火花。与古代教育家的对话必须是一种“高端对话”,双方都代表了自己时代教育思想发展的最高水平。我们对当代各种教育问题和教育理论了解越多,对各种相关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了解越多,对当代教育感悟越多、思想越深刻,就越容易从教育史中获得更多的启迪。这就必然要求我们积极关注和思考各方面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以作为我们与古人对话的平台。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当我们从历史返回现实、准备与其他教育学者和教育实践界的教师分享自己的收获的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使自己的感悟走人读者的心灵世界呢?我们不可能以古人的方式,因为我们并不是古人的传声筒、我们也并未能完全了解古人的世界。我们能与今人交流的,只能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也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内容——一种努力吸收了古人智慧的我们自己的智慧。但要使自己的方式和内容能为同代人了解,我们还需要回到共同关心的话题、使用能够共同理解的话语。这同样要求我们积极关注各方面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以之作为与今人对话的平台。
四、深入思考,为教育实践提供来自历史的学科智慧
教育史学科遭受鄙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学术性,遭受“太浅”之讥。
关于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一般的说法是研究教育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但事实上,恐怕是现象研究有余、规律研究不足。因为,教育发展规律的研究被认为是教育原理学科的主业,教育史研究教育发展规律似乎大有抢占别人地盘的嫌疑,如前所述。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主要用的是历史方法而非哲学思辨,因而与教育学原理学科的“边界”也是清楚的。
一个令教育史学界感到难堪的问题是,与其他教育学科相比,教育史学界多年来很少提出过什么有影响的教育理论。西方教育史学家为了走出传统叙述史学的困境而转向了“面向问题的史学”,即如勒高夫所说的“一种不是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史学家带着问题去研究的史学”,“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以便能在一个‘动荡不宁的世界中’生活和理解”(13)。这对于我国的教育史学界应该有所启迪。可喜的是,个别教育史学家现在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例如,吴刚的《知识演化与社会控制》就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出发,运用知识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等方法尝试破解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令人耳目一新(14)。
除了研究教育发展的规律,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还是古人的教育智慧。
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历史学取向的教育史研究只满足于历史现象的描述,而缺乏进一步的思考;教育实践取向的教育史研究虽然有些思考,但却止于表面,喜欢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从历史中找到今天应该怎么做的具体方法来,以为只有能告诉实践界的教师明确具体的做法才能真正体现出教育史学科的实用性来。笔者不否认能告诉人们具体操作步骤的学科是最具实用性的学科,但遗憾的是,教育史学科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今日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已经与古代有了很大的差异。而且,不仅教育史学科很难做到这一点,就是所有其他教育学科,包括教育技术学、各科教学法等这些以“技术”、“方法”自命的学科,其实也难以告诉教师具体的做法。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教育是一门艺术。而它之所以是一门艺术,是由于它需要教育者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采取富于个性和创造性的教育方式方法。历史与今天,属于因时而异,并且具有很大的时间距离,我们教育史学者更不能自诩可以给教师照搬到课堂的具体方法和模式。
教师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可以简单模仿的技术和方法。因为,只要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同时又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敢于思考与探索的自信,他们是不难想出那些具体的技术和方法的。即使普通教师也是如此。一个教师所以只能成为普通教师而不能成为教育家,常常不是因为他只有普通人的智商,而是因为他只具有普通人的智慧。所以,教师最需要的是教育智慧,也就是对教育和学生的大爱、正确的教育理念和勇于进行教育研究的开拓精神。教育史所要从历史中挖掘的,也主要应该是这样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五、“大教教心”,走进古今教育人的心灵世界
当前,教育史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喜欢研究一个太大的问题,结果显得“太空”。
比如“××教育思想研究”这样的题目,写专著或者硕士、博士论文还可以。因为篇幅长,所以可以挖掘许多新鲜具体的史料,也可以从容地展开自己的思考。但是,如果一篇文章用这样的题目,里面肯定只能是面面俱到但却都蜻蜓点水似的介绍,既无法给人较多的史料方面的素材,也无法给人较深的思想方面的启迪,充其量只是勾勒了古人的骨架,却无血无肉(15)。正如人之于人的主要区别并不在骨架一样,教育思想家的主要思想总是有太多的相似。前面提到“借鉴与启示”类教育史研究论文之所以给人千篇一律的感觉,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把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家的主要思想加以概括的话,那么这些思想早已被一代又一代地加以提炼总结,基本上都可以在任何一部教育原理著作中看得到了。希望依此从“故纸堆”中找出别人还没发现的大块的“金子”,恐怕现在也已经很难了。
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给教育史研究对象赋予血肉、情感和灵魂。前面提到的教育史研究要提供给今人的三种教育智慧,其中的对教育和学生的大爱、勇于进行教育研究的开拓精神这两个方面,如果套用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术语,则不属于知识范畴,而是属于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范畴。教育理念包含价值观的成分,也包含知识的成分,但这些知识应当属于基本的、核心的知识。这些核心的知识就是古人的论点。不要急着把古人的论点概括出来,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真正最有价值的,是古人对这些论点所进行的生动而精辟的论述以及他们自身那些足以令我们无数次感动的教育故事。所以,就教育史论文写作而言,与其面面俱到,不如只针对某一具体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古人对某一问题的论述或者古人的某一事迹非常有价值和意义,但是却极其简略,如何能做成一篇文章?在这方面,我也是从周勇先生的《跟孔子学当老师》一书中得到了启示。周先生谈孔子,却不限于谈孔子。他旁征博引、挥洒自如,既谈其他古今名师的遗闻轶事来正衬,又讲钱钟书的《围城》和叶小风的《前辈先生》两部讽刺类教育小说来反衬,其间又常夹杂有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这种写作风格,对于教师教育是非常合适的。至于学术论文写作,虽要求严谨一些,但引证现实问题和其他人的论述也应该是可行的。因为,教育实践取向的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教育的现实问题而非历史问题。如果是历史学取向的教育史研究,则另当别论。
周勇从孔子那里感悟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是“大教教心”(16)。大教育家通过自己的教育来改变学生的心灵世界,而不只是知识和技术方面的指导。这一点对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教育史家通过他的研究也应该能够给教师以心灵智慧的滋润,而不只是教育技术方面的细枝末节。大教育家要“教心”,首先就要“交心”,敞开自己的心灵世界去理解和感染受教育者的心灵世界。教育史学科是实现古今教育家心灵对话的桥梁,所以也要“交心”:一方面是与古人交心,用心灵理解心灵,用智慧解读智慧;另一方面是与今人交心,用心灵感染心灵,用智慧点亮智慧。我们说,教育史学科走近教育实践的关键之所在,就是要走进古今教育者的心灵世界。
收稿日期:2009-05-08
注释:
①杨孔炽.关于教育史研究的价值问题[N].光明日报,2005-1-12.
②③贺国庆,张薇.“教育史”学科面向未来的思考[J].教育科学,2005(1):31.31
④(11)王兆璟,许可峰.实用性问题与教育史的学科智慧[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1).
⑤高天明,彭玉生.教育史研究三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2):30.
⑥李涛.百年中国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回顾与反思[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112.
⑦(16)周勇.跟孔子学当老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8.41.118.53-63.
⑧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84.
⑨需要声明的是笔者并非反对创新,只是创新绝非教育史学科之所长,教育史学科的价值恰恰在于不断翻耕历史的土壤,为当代教育提供来自传统教育文化的养料。
⑩中国元素成时尚动力[EB/OL].中国服装网.http://www.efu.com.cn/data/2006/2006-12-09/176857.shtml.
(12)用今天的概念去理解古人的教育思想,也是教育史学科遭人诟病的地方之一。但是,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如果要以古人的思想理解古人,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理解了古人。但问题是我们正因为还没有理解古人所以才需要去理解古人。
(13)周采.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及其意义[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24.
(14)吴刚.知识演化与社会控制——中国教育知识史的比较社会学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15)考古学家常常挖出这样的骷髅来。要使它生动起来,就要还原以血肉,这当然要依靠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