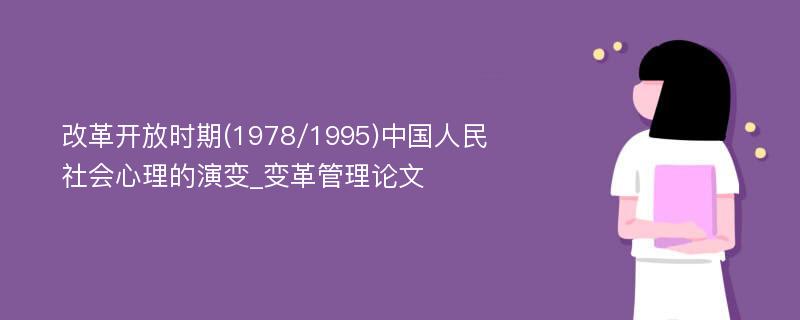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1978~1995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论文,中国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民众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已经历了17个年头,其间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和改观。从社会的层面来看,这种改变表现为社会的构成、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整体转型,由传统的以上下隶属的层级关系为主干的一元集权伦理型社会转变为以相互依赖的契约关系为主干的多元分权法理型社会。与此相应,社会民众的社会心理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无论是人们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及行为表现都伴随着社会的全面和深刻的转型而转变,新的观念、心态和行为方式不断更新替代着人们久已习之为常的传统的观念和心态及行为方式。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剧变时期,中国民众社会心理的这种变化从现象上来看,更多地与社会的生产、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形态及实际运行和操作的体制结构形态的变化相联系,更多地受这些方面变化的影响和制约,并且以形象直观的形式生动具体地反映和再现了社会的这种剧变,进一步才影响到由观念意识、精神风气所构成的社会的思想文化形态。
本文试图对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实际进程进行分析,并据此深入探讨中国民众社会心理在这一社会剧变和转型时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一
改革开放十七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经历了明显的几次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波动和变化[1],伴随和反映这种波动变化的社会变更不仅包括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新的方针政策的出台,还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的纷争、社会矛盾的对立冲突以及种种社会问题的凸现。对此,经济学家、从事社会研究的历史学家以及从事政策研究的政府官员各着眼于不同的问题和现象,根据不同的尺度和标准将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划分为不同的几个阶段和时期[2]。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改革开放时期这种社会变更的反映和体现主要表现为社会的构成、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变化,而所有这些变化又集中地表现为国家权力和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转让。权力的分放和利益的转让是促使和导致社会巨变的深层内在的核心动因,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也始终是围绕这一主题不断地尝试摸索逐步向前推进的,从最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后来在城市企业中推行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及至股份制和产权改革;从最初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开农贸市场到给城市职工干部一次又一次提薪补贴发放奖金;从缴利提成到利改税及至实行分税制;从计划经济为主的单轨制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及至现今“分权式的混合经济”[3],等等。在所有这些社会变革过程中,权力的分割下放和利益的转移出让始终是事情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经济的大起大落周期性变化及相应的新政策和新措施的出台实施,都伴随明显的利益的再度转让和权力的重新分放。正是这种权力的分放和利益的转让直接导致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新的经济成份和社会组织的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和规范准则的确立以及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产生,由此而进一步影响到社会民众的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变化。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民众所普遍关心注意并对之作出强烈凸显行为反应的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如社会分配不公、权钱交换的腐败、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等,无不与权力和利益有着直接的和密切的联系。
二
在改革开放的十七年中,国家权力的分放和社会利益的转让大体上经历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变更,即从以单纯生产经营权的逐步分放发展到生产经营权和国家行政管理权相结合的双重分放,再进一步转变为生产经营管理权的逐步全面放开和国家行政管理权的重新分割适度回收。利益的转让则经历了从最初直接运用国家行政手段实施让利和平均分配,逐步转变为集体个人凭借自身所拥有的国家权力捷径获利和差序分配,再进一步发展到利益转让的制度制约、政策指导和逐步的公平分配。
在1978~1984年这段时期内,改革的基本思路在于针对旧体制权力过集中的严重缺陷,实施放权搞活,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此时期内国家权力分放和社会利益转让的主要特征即是单纯生产经营权逐步有序地下放和运用行政手段及措施向社会民众转让利益。在农村中所实行的包工到组包产到户及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是此时期内国家权力分放的典型表现,与此同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开农贸市场,给城市职工干部提薪补贴发奖金,则是此时期利益转让的主要表现。生产经营权的下放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激活和启动了生产经营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4],然而基于平均分配构想的普遍范围的让利则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锐减,进而影响到经济建设的投入和增长[5]。但是人民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明显获益,尝到了改革旧体制的甜头。在七十年代尚为人们生活消费普遍需求的老三件(自行车、手表、缝纽机)在改革到来的最初几个年头(1983~1985)就迅速地被彩电、冰箱、洗衣机所组成的新三件所淘汰。改革初期的这种分权让利使社会民众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重新激起人们心中长期以来被压抑和排斥的对富足充裕物质生活的憧憬,增强了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使经受了十年文革浩劫磨难变得涣散疲困的社会各阶层民众重新振作和聚集在一起。这一时期作为十七年改革开放的初始启动阶段,其社会效果就在于团结聚集全体社会成员支持拥护并参与投身到改革之中,因而可以称之为社会聚合时期。与这一时期相对应,社会民众心理的嬗变突出地表现为心绪情感的舒朗渲畅、欲望渴求的萌动驱涨,人生态度的乐观奋发,以及社会观念和行为的活跃宽放,近乎于一种人们盼望已久的新世纪到来之时所表现出的获得新生般的“世纪初心态”。扬眉吐气,开朗乐观,意气风发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民众精神面貌的明显特征。
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颁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时开始,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改革开放逐步进入了全面推开和深入发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内,国家权力分放和社会利益转让的整体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伴随市场调节观念的产生、市场机制的发育和面临着全面开放,单纯生产经营权的下放已难以满足日趋明朗的计划和市场双轨体制并存的形势需要,仅仅拥有生产经营权既难以保证计划的执行,更难以较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和发展,同时,人们对改革初始时期着手政策改革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改革策略也开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地方、部门、集团的利益驱动日益强烈,所有这些导致了对下放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的强烈呼声和迫切需求。其结果即是伴随生产经营权分放的进一步扩大,国家行政管理权力也开始逐步被分割成为地方、部门、系统、单位所拥有的权力,国家的计划经济开始转变为地方区域的计划经济,在改革初期被分解为二区别对待的国家权力的行政、经济的双重职能,此时又在新的起点上重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权力涉足经济、权力进入市场开通了前进的道路。与此相应的则是利益获取的权力捷径和“红色通道”的形成与利益分配的权力差序和条块差序格局的形成。权力分放和利益转让的这种新格局使地方、部门的集团利益急剧膨胀,而社会民众所得到的则是相对剥夺,从而引发了尖锐的社会分化。这种社会分化既表现为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标志的国家权力的弱化和地方化,表现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鞭长莫及、疲软乏力和市场微观调节的失范和失度,同时也表现为社会各集团、阶层和普通民众在资源占有、利益分享上的两极分化的趋向,社会民众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不同地方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大幅拉开急剧扩大[6]。制定规则和参加游戏的合二为一所导致的无规则竞争以及权钱交换的腐败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瓦解了改革开放在社会民众中间所产生的凝聚力,动摇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稚幼质朴的认识和期望,激化了人们极端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表现。这一时期从1985年起至1989年发生全国大范围内的社会震荡时止,可以称之为社会分化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众的心理嬗变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心理的失衡。少数人的先富暴富和伴随全面开放而起的进口消费之风使人们追求财富和物质享受的欲望急度膨胀,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所造成的两极分化以及失去规范的社会竞争和失去制约的权钱交换又使得人们致富的期望和梦想化作水中泡影空中楼阁,社会的日益分化更进一步打乱了社会民众原有的身份、地位、权力、声望的判断尺度和价值内涵,“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不三不四赚大钱。”社会民众心理上的失衡由此产生,并进而导致行为、心态和观念上的极端倾向。失去理智的超前消费,疯狂的股市热潮,全民下海经商,人才劳工跨地区打工淘金,追求金钱财富和物质享受的行为活动漫溢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盲目冲动的攀比心态、比上不平比下不甘的怨愤心态、投机博彩的淘金捞世心态等应时而生,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观念空前盛行。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转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从八十年代以政策改革为导向的阶段转变为以体制改革为导向的阶段,诸如财政、税收、金融体制和企业经营机制、国有资产管理等宏观层面的改革排上了议事日程,同时,劳动用工、人事管理、社会保障、住房制度等社会层面的改革也开始逐步展开。由于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经济行为的失范无序导致了社会的急剧分化并引发了较大范围内的社会震荡,所以在九十年代初期改革的基本思想以整顿治理为主线,信贷、投资、物价、流通等方面成为整顿治理的主要对象。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目标,使改革的理论指导有了新的突破,但由于经济社会双重二元体制的长期并存,彼此间的利益唇齿相依,彼此间的关系犬牙交错,因而在实践中体制的改革和转型仍困阻重重,步履艰难,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新体制与旧体制的磨合,旧体制对新体制的顺应,最终才能走向合二为一,实现体制的全面整合和转型。在这一时期,伴随经济秩序的整顿和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深入,国家权力的分放逐渐转变为依权力的垂直隶属关系重新进行分割组合,宏观决策控制权力适度上收,微观管理调节权力随市场的发展完善逐步规范化和有序化,以扭转前一阶段权力分放的块状分割所导致的权力失控和无序化,例如取消财政税收的包干制而改为分税制。同时,通过加大社会层面体制改革的力度来强化国家、政府对社会利益分配的指导和制约,实施有倾斜的利益转让,以建立公平分配的新秩序。在这种发展形势下,社会整体逐渐显露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企业的生产经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金组合,到社会的管理运作;从社会事业的发展到人们的就业谋职和个人收入所得的增加,多元化成为谋求发展的首选之路和标志发展的重要特征。在这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时期,社会民众的心理嬗变则主要表现为心理的自我调整和行为的积极适应。面对着个人无法逆转的社会发展和难以把握预料的社会剧变,社会民众所能够作出的唯一选择即是心理的自我调整和行为的积极适应,这是一种近乎顺时应势式的理性抉择。认知的重新定向和观念的多元组合成为获取心理调整的重要条件,对环境刺激的积极回应和对环境变化的主动顺应成为实现行为适应的主要方式。在这种心理定势和行为倾向的支配之下,讲求功利的实惠心态,标榜“潇洒走一回”的即时享受心态,强调机会把握的赶车心态以及标新立异赶潮流的弄潮玩世心态应时而生,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和认命信天的世界观组成为一股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社会的观念意识和生存形态的世俗化日趋严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多元化时期社会自身整合的不断加强,社会民众对社会变革的承受能力和辨别能力日渐加强,浮躁不宁的心态渐为稳定求实的心态所替代,追求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望转化为对现实人生不同道路和生存方式的个人偏好和自主愿望,对分配不公及以权谋私腐败现象的情绪激愤逐渐转化为认知的理性分析和行为的自律自择,社会观念意识的主流化和个体化趋向开始形成。所有这些都表明,在社会日趋多元化的时期,社会民众的社会心理日渐成熟和稳健。
综上所述,与改革开放十七年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三个时期相对应,社会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社会心理的驱动阶段、社会心理的失衡阶段和社会心理的调适阶段。预计伴随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整合的逐渐加强和提高,社会民众的社会心理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调适之后会逐渐地获得平衡协调。
三
起始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一场深刻全新的社会变革运动。这一运动本身实际变化发展的不同进程影响和制约着社会整体的变革和更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嬗变,同时,这一运动本身不断向前推进和展开的实际运作方式及相应特点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嬗变,从而使得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表现出鲜明的、与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变革密切相联的时代特征。
十七年来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以经济改革为先、为主,通过经济改革的先行和不断深化来促进和推动全面的社会改革的独特道路。经济改革的首要目标就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借此来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搞活生产经营活动,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调动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谋取最广泛的社会支持。放权让利则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最易见效的手段措施,其作用就在于宽松对个人团体、地方部门获取利益需求的约束并使之合法化以及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因此,十七年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突显的利益驱动的特点,个人欲求愿望的满足和地方、集体、部门利益的实现成为促使改革起步并不断发展的强有力的动力。这种实际运作的方式和导向不仅影响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发展,同时也为社会民众心理和行为的嬗变确立下基本的环境前提和社会氛围,决定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民众心理嬗变的主要动因不是源自于理性层面的观念意识的转变更新,而是直接产生于感性的物质需求的满足和经济利益的获得,从而使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表现出明显的讲实惠、求功利的利益取向特征,即根据社会变革对个人需求满足和切身既得利益的影响和关系来调整变更自己的心理和行为。物质利益取向的需要和动机既制约着人们的态度和观念的转变,也决定着人们外显的情绪表露和行为表现。所以,在十七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中国民众心理状态的波动起伏和行为表现的变更转化始终是围绕着利益需求这一中心而展开的,利益需求成为标志反映人们心理和行为变化的“寒暑表”,成为影响和制约人们心理和行为表现的内在深层驱力。十七年来不同时期内所进行的众多的社情民意调查的结果也都具体和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民众心理嬗变的这一基本事实[7]。
十七年的改革开放还表现出以尝试摸索性的不断实践作为改革开放的探路石,根据“排除法”的逻辑和“效果律”的原则来寻找正确的、行之有效可行的改革举措和发展道路的特点,而不是根据依赖理论的先行探讨和发展进一步来指导和推动改革开放的进行。与此相应,在十七年的改革历程中,政策层面的微观变革就先于体制层面的宏观改革,从政策层面的改革入手逐步实现向体制层面改革的过渡,以微观局部的变革发展来启动激迫宏观全局的调整变革,就成为谋求短期内改革实效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阶段,政策的变更、调整和导向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明显地大于体制的制约调控作用。改革开放时期的这种实际运作的方式在作用于社会群体、组织和集团并转化为每一社会成员的个人行为时,就促成了个体行为的计策性和试误性的实用特征,先行而后知,不知仍可笃行,只求行之有效,行为的转变先于、快于观念的转变,外显的行为及其结果成为指导内在认知观念的主要依据,他人行为的示范则成为自身行为调适的重要判断尺度。因此,在十七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中国民众社会心理嬗变的实际过程基本上就表现为由外向内的逐步转变,外现行为表现和活动的转变先于、快于、大于内在认知观念的转变,并成为引导内在认知观念转变的主要依据。
与上述改革开放的实际运作方式紧密相联的另一方面即是,在十七年的改革开放中,以“放与收”交替更换、兼而用之的调控策略作为解决建设发展过程中活与死、乱与治问题的基本计策手段,并依此来促使“游戏规则”水到渠成般的自发形成,实现改革开放从无序到有序的过渡,而不是制订规则在先,各司其位,各循其道,按部就班地循序渐进。这就使得参与改革进程中的社会民众心理行为的嬗变表现出极大的机会性和适应性的应变特征,短期利益和即时效果成为驱动行为的唯一目标,对时势变迁的积极顺应和对风险机遇的巧取契合成为指导行为的主要准则,从而使强调把握时运机遇的正面宣传在缺乏稳定连续的社会规范约束的环境中转化为民众的投机意识和博彩心理,失范无规则的秩序环境更进一步助长了民众行为的应变性,最终导致行为方式和活动的选择取决于对环境条件的充分利用和依赖,取决于对时运机会不遗余力地把握和博取,而不是取决于行为自身的既定目标以及社会和行为者自身认同奉守的行为规范准则。因此,在十七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社会民众的行为表现随时势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演变为一阵阵“热”与“潮”的时尚潮流。
注释:
[1] 胡鞍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四起三落》,《战略与管理》1993年第11期。
[2] 萧功秦:《改革中期的社会矛盾与政治稳定》,《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1期;李青原:《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战略与管理》1993年第11期。胡鞍钢:见注[1]。
[3][5] 杨帆:《市场经济一周年》,《战略与管理》1993年第11期。
[4] 郭晓鸣等:《农民与土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76~88页。
[5] 刘力群:《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及其存在的问题》,《战略与管理》1993年第11期。
[6] 李若建:《从黄金海岸到黄土高坡》,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54~123页。
[7] 冯伯麟:《大潮下的情感波动——变革社会心理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江流等:《1993—199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江流等:《1994—199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