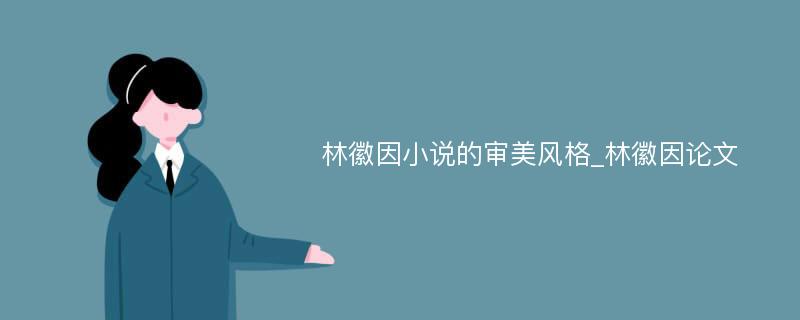
林徽因小说创作的审美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格论文,林徽因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 8444(2000)04—0114—05
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以她聪慧敏锐的思维语言,深厚渊博的知识素养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艺创作方面显露了卓越的才识,诚如梁思成先生(林徽因之夫)评价的那样,“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不论是在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1] 在当今众声喧哗的时代氛围里,昔日曾被历史巨浪淹没了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哪怕是声名甚微的)均被打捞出来,接受时间和历史的重审与评估。然而林徽因的小说创作则较少为人所论及,它们不是被她的诗情所掩盖,便是为她的建筑家声名所挤兑。事实上,林徽因的小说创作比起她的诗歌创作来说,虽然数量上要少些,但是它仍以其独具的艺术魅力,独立于同时代的众多女性作家的创作中。
林徽因小说创作大致有《窘》、《九十九度中》、《模影零篇》(包括《钟绿》《吉公》《文珍》《绣绣》)等。在对她这些小说文本的细致阅读之后,我们发现林徽因的小说创作既具有女性的温柔婉丽,又有学者式的聪慧睿智,同时还隐含了知识分子的忧时伤世情怀,从而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单纯与繁复,宁静与喧嚣,婉约与雄浑、静态与动态等多重对立矛盾因素的杂呈现象,呈现出审美风格的多元化趋向。具体来说,在写法上表现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结合,在创作上表现为传统文化特质与个人现实、性别处境的缠结,在人物塑造上则表现为静态与动态的统一。就是说,她的小说创作既有别于她本人诗作中的浓郁抒情走向;也异于同时期别的女性作家的创作,譬如:相对于“闺秀派”以善于勾画“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语),风格明显趋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适度、中和的古典美的凌叔华来说,她的小说创作充满了现代性的张力与繁复的一面;相对于过分的随意宣泄青春情感、倾泻个性解放欲求的庐隐、冯沅君等人的“狂飙式”创作风格来说,林徽因的创作则又呈现出和谐、节制和理趣的趋向。
一、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融汇
“人性或人道主义的情怀”可以说是贯穿林徽因小说的一根红线。林徽因曾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强调创作必须诚实。对于“诚实”的理解,她作了如是说:“所谓诚实……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极明了的,在情感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又说:“一个生活丰富者不在客观的见过若干事物,而在能主观的能激发很复杂,很不同的情感,和能够同情于人性的许多方面的人。”[2](P.110 )具体到她的小说创作中就明显地出现了作者以两种笔法叙述的人性或人道主义故事。一类是传统故事叙述型的,如《窘》、《绣绣》、《吉公》、《文珍》等。在这类小说中作者以淡雅素朴的笔致娓娓地向读者铺叙一些蕴含淡淡悲哀与愁绪的平常故事,并在淡淡的情节叙述及人物不幸命运的叙说中寄寓其人性或人道主义情怀。这类作品不论主旨内涵还是审美取向,可以说都很能体现出作者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如《窘》中对中年鳏夫维彬教授由于年龄沟壑、不适场合以及突发的非正常男女情感等,而萌生的“窘”的心理状态可谓刻画得细微而传神。再加以烦闷炙热的酷暑,闲而无事的假期等环境、气氛的烘托,使维彬的“窘极了”的神态心绪简直如电影屏幕一样醒目地划过读者的眼前,令人不能不对他生起同情之心:同情其孤寂的生活,其对环境的不适以及其种种尴尬处境。例如:
“我们”和“他们”!维彬好像在他们中间划出一条界线,分明地分成两组,把他自己分在前辈的一边。他羡慕有许多人只是一味的老成,或是年轻,他虽然分了界线却仍觉得四不像,——窘,对了,真窘!……他又不自在到万分,拿起帽子告诉少朗他一定得走了。“有一点事情要赶着做。”
素朴独白式的语言,纡徐的叙述节奏,看似平静冷淡实则蕴涵了人物内心强烈的情绪激荡。小说中的心理刻画手法可谓深得中国传统小说这方面的传承。不加藻饰,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外部形态等的白描及周围环境气氛的烘托来刻画人物心理,这正是中国小说的传统艺术手法。
在《文珍》、《绣绣》中,作者也以满怀同情的笔触,叙述了绣绣、文珍、文环等的不幸命运:绣绣因父母无休止的大吵大闹所遭受的巨大心灵摧残,文环因年轻貌美倍受凌辱而被迫致死,文珍的看破世事逃婚离去等,可以说都反映了彼时现实社会中女性的不幸悲惨遭际,体现了作者对弱小者不幸命运的同情,切合了当时的文学中流行的时代主题。在这类小说中,林徽因不是以虚构的引人入胜的情节取胜,而是以其作品中的强烈而浓郁的抒情气氛感人。无疑,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强大的抒情诗文传统渗入的结果。另外,线性发展的情节故事,素朴、平实的叙述语言,淡淡的抒情气氛与意境的营构,以及叙述节奏的舒缓、柔静,叙述人称的大体一致性等都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
另一类是现代性的拼链式的片断镜头重组型。如《九十九度中》、《钟绿》等。在这类小说中,作者的视野相对开阔了些,她以悲悯的眼光试着打量“窗外”纷攘的世情生活,写出了彼时社会现实逼真的一角。如果说在上一类小说中,作者的视线还落在“窗内”较狭小的家庭生活一角中,那么这类小说作者则把视线投向了社会,把自己的人性、人道主义情怀普施于社会上诸色人等身上。如《九十九度中》被李健吾称为“最富有现代性”的一篇小说,反映的是“人生的横断面”,而不再是传统章回小说的纵剖式的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通过十多个片断镜头的链接重组,描绘了一个大热天的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引导我们……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恋的,有作爱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有索债的,有无聊的,……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下一个比照,而这比照,不替作者宣传,却表示出她对人类的同情”(李健吾《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在《钟绿》中,作者也运用了电影语言——蒙太奇式的镜头组接方式,给我们描摹和承接了四幅有关钟绿的“油画”:虔诚的宗教画(“擎着一枝蜡”、“微微地垂下眼”的古代年轻的尼姑形象),古拙的村姑画(包着三角头巾的暴风雨中的村姑形象),妩媚的古典画(肩上扛着水罐子的古典汲水少女形象),雕刻式的现代美女画(有着雕刻般的形体,身着红色浴衣的美丽少女形象)等,艺术地呈现了一个热爱生活、热情漂亮的少女——钟绿的飘零不定的生活奔波及其“红颜薄命”式的悲惨结局,寄寓了作者对之的深切同情及对人生命运的思考。同时作者还借人物之口幽默轻俏地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下,资本家的罪恶进行了一番嘲讽和揭露。片断镜头的链接显然是一些现代性的艺术技法,而作者能在小说中如此娴熟的运用来构架小说的整体情节,一方面既得力于作者所学的建筑学艺术及当时所流行的外国现代派艺术思想;另一方面也与作者对现实人世的理解、认知有关。在《钟绿》中,作者借人物之口写道:“今天和明天的事多半是不相连续的多;本来现实本身就是一串不一定能连续起来的荒诞。”在《吉公》中作者又指出:人事、活动的错综复杂性,常常可以“在同一时间里,展演如一部戏剧”。可见,在作者的思维意识和情感志趣方面,她已接受和消化了电影语言的片断镜头组接法,也酿就了其小说情节构建的横截法。因而林徽因的这类小说画面很鲜明很吸引人,具有很强的可视性。当然这也与作者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有关。
以上是分类缕析林徽因小说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事实上,就是在同一类别的小说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也不是孤立隔绝的,而是融汇贯通的。传统性中有现代性,现代性中也融汇了传统性,形成了其传统性与现代性相融汇的艺术风貌。如最具现代性的第二类小说中,在片断镜头重组的现代型结构章法中,仍可以离析出传统手法。如对北京建筑及家中摆设的描绘;“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人物出场法;《钟绿》中在与钟绿相见前的众多“油画”的铺叙。如《钟绿》、《九十九度中》在整体故事的叙述上基本上是按线性发展的逻辑顺序,等等,尤其是对我国古代“诗画”传统的承传。在林徽因的小说中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她的作品中充满了“画”(或图画)这个词语及意象。这里撇开她在《九十九度中》如同电影镜头画面的闪回穿插,如老卢在洋车上思虑吃饭问题时,“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由他左侧冲过去,快镜似的一瞥鲜艳的颜色,脚与腿,腰与背,侧脸、眼和头发”,以及《钟绿》中的四幅“油画”式画面的描摹。单论“画”这个词的出现就几乎遍及了她的全部小说创作中。如《窘》中维彬对芝的形象产生的联想“叫他想起他心爱的一张新派作家的画”,“你此刻便是一张画”等,《九十九度中》“柳条的影子画上粉墙”,《钟绿》中写“我”对钟绿的记忆“如同他人私藏一张名画”,“怎不是一幅绝妙的图画”等,《吉公》中“立刻浮出一张鲜明的图画”,“在这幅图画后面”,《绣绣》中“那张小小图画”,绣绣的形象“美得好像画里的童神一般”,等等。“画”在这里有多种表意功能:其一是表示人物给人的印象之鲜明,意即当日的印象如今仍如电影镜头一样闪在眼前,强调其可视性,这点在前面已有所分析。其二,是强调所说的人(物)如画一般美丽,充满无穷韵味。在中国古代对诗、画的品评中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说,无疑这也是对诗画的最高赞誉,成了众多诗人、画家在创作中的自觉和刻意的追求。林徽因本人就是个才情饱满的诗人,且曾随美耶鲁大学的G·P·帕克教授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可谓对诗画有一定的造诣。书香门第的出身更使她浸染和熏陶了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这些都对她的创作构成了一定的潜在的影响。因而,从某种角度上说,“画”在林徽因小说中的频繁出现也是其对中国古代诗画传统承传的一个例证。
二、传统文化与个人、性别处境的缠结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等为宗旨而展开的。也即对于传统的东西是“破”字当头;同时又大力提倡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文艺思想理论和创作。甚至鲁迅先生在谈到创作时也强调:“所仰仗的全在先前所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3](P.512),而不愿提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事实上,五四一代先驱作家,尽管他们反抗传统很激烈,但他们的传统文化素养远远超过后来的任何一代作家。影响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他们身上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就会不自觉地流溢出来。这也就构成了他们作品中的一层抹不掉的传统文化的“底色”,体现在其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构设,整体风格及审美趋向、意境的营造等方面。
作为出身名门望族的才女林徽因,她所具有的传统文化意蕴、学识素养之深厚自不待言。传统文化中的那种“中庸平和”的美学追求使得她在创作时体现出一种雍容、和谐、适度的风范,形成了一种近乎超然事外的冷静客观的中性叙述,呈现出一种东方美学理想的审美趋向。如《窘》中那种冷静、纡缓的叙述节奏,淡雅而幽远的意境营造,白描式的人物对话等很到位地刻画了维彬教授“窘”的心态,契合传统文化审美特质中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美学风范。这样一来,维彬教授“窘”的心理,宛如一泓深潭,被轻风一吹微波涟漪,呈现出一种静态美。而《九十九度中》也如李健吾所评说的:“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的水波一样轻轻地滑开。”(《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同时,林徽因作为深受20年代新月派影响的诗人及30年代京派的代表性作家,其创作风格及流向也显得趋向和贴近这两派。譬如新月派的“理智节制情感”及“和谐、均齐”的传统东方美学理想;京派的有意和时代性强的重大而尖锐的题材保持某种距离,追求恬静、淡远、含蓄、超脱的审美取向等均在林徽因的创作中有所投射,形成其内敛式的情感发抒方式。
但是,作为一位有社会良知和爱国心的知识女性,林徽因早期所受的新式教育得力于她的父亲。如在她年少时,父亲“为了让她多观览诸国事物增长见识,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而带她出国考察[4](P.113),使她的创作视域不可能完全局囿于以静态美学对“窗内”的生活世界的观照。尤其是与著名建筑家梁思成结婚后,为搜集古典建筑材料而足迹遍及荒郊野外,极大地拓展了她的生活视域和丰富了她对人生、社会的知识容量。这自然会影响作者文艺思想的细微变化。《九十九度中》便是她试着以“入世者”的眼光突破“窗子”对她的局囿,开始打量“窗外”喧嚣的世界。
30年代中国风雨飘摇的特殊处境,每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完全沉湎于艺术的“象牙塔”内,这个时期众多作家创作面向大众生活的现实主义转向就是明证。自然,林徽因的小说创作风格也发展变化了。在她的《九十九度中》、《窘》那种知识分子闲情乐趣、儿女情态、家庭琐事的近乎静态的生活画面,被纷乱扰攘的乱世生活画面所取代。甚至在《文珍》中还出现了“革命党”。尽管作者是一笔带过,或是作为背景,但毕竟流露了作者一种式微的“入世者”对现实关注的前阶级意识,使她的作品绝然有别于同属于闺秀派的凌淑华的创作,也使她作品的思想境界提高了不少。
林徽因是一位现代知识女性,女性的性别情感特征以及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切身感受使得她的作品也抹上了一层“女性性别意识”的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她作品中出现了众多不幸命运的女性。如受过新思想的启迪且有意中人却被迫他嫁的阿淑(《九十九度中》);“红颜薄命”式惨死的美人和钟绿(《钟绿》);“好看”而“没好命”被“闲话”逼得跳井而死的文环(《文珍》);被丈夫喜新厌旧抛弃过着生不如死的绣绣妈(《绣绣》),等等。身为女性,作者对社会上女性的不幸境遇,尤其是下层女性的悲惨命运,由于广泛的深入社会生活的实践,应该说是有了较深切的了解,并充满了无限同情,故而写得较深沉且充满了感伤意味。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叙述风格的“变调”上,林徽因的作品叙述故事的整体风格基本上是客观、从容而平静的,体现了一种和谐、适度的风范。但是现实女性的处境,尤其是她自身类似的事业与家务的矛盾又使得她不能一贯的平心静气、温婉平和的叙述下去,往往在平静的叙述中出现“变调”的不谐音。
作者在1936年5月7日给她的美国好友费慰梅的一封信中说:“每当我做些家务活儿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2](P.4)这段话可谓道出了作者内心对家务干扰女性事业的烦闷和焦躁感。这自然会影响到她的创作。如同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对简·奥斯汀及夏洛蒂·勃朗特等创作所作的分析那样,由于没有安适的创作时间和空间,造成了女性创作的隐蔽及断断续续,风格的前后不一致,所以伍尔芙主张女性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林徽因的创作正是这种境况的体现。如《钟绿》中作者在平静的描述钟绿的美丽,想象漂亮的钟绿披上婚纱时的“奇美”与“幸福”时,突然插入一句,“至于他们的结婚,我倒觉得很平凡;我不时叹息,想象到钟绿无条件地跟着自然规律走,慢慢地变成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渐离开她现在的样子,变老,变丑,到了我们从她脸上,身上再也看不出她现在的雕刻般的奇迹来。”句式的由中长变短再变长,叙述节奏的由慢而快再到慢,体现了作者感情的波澜起伏,由惋惜叹息式的情感发抒,到紧张急促、激情涨满,再到一泻汪洋式的尽情喷吐。一股越乎中庸、平和之上的愤激之情跃然纸上。更不用说在《文珍》中,文珍对出嫁的恐惧和愤激的直接发泄以及对生命的自暴自弃,“不嫁老在那里磨着,嫁了不知又该受些什么罪!”“管他呢,命要不好,遇(嫁)到一个醉汉打死了我,不更干脆”等,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对现实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也一定程度上寄予了作者“浇心中块垒”式的抒愤快意。
作者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幸福安逸中度过的,交往也不出优裕的知识分子圈,几乎没有真正接触现实社会。因而记忆中的家庭生活是温馨而美好的。这就形成了她早期《窘》中对融融家庭中小儿女憨态的逼真绘写,充满了平静、祥和的气氛。一旦作者走出书房,接触现实生活,看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恶,她的心情就再也无法宁静,她后期小说中的叙述再也舒缓从容不起来了。而在作品的思想内涵方面隐约也有了对现实时事的一瞥。如散文《窗子以外》,反映的便是作者渴望走出封闭式的书斋生活,投身于“窗子以外”的社会生活中。在小说《九十九度中》便有了对下层劳动者艰难困厄生活的直接描述。这样一来,传统文化修养与现实境遇,性别意识与传统审美特质相缠结,形成了她创作上的宏大厚实风格的景象。
三、静态与动态的统一
“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小说要素之一,对小说的成败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家笔下均有其不同的人物群像系列。如庐隐笔下的热烈追求个性解放,但却命运多舛、前途未卜的感伤忧郁的现代知识女性形象;凌淑华笔下的既受新思潮的激荡又囿于传统封建道德礼教,只在内心里起微波的半新半旧的女性形象等,在林徽因的笔下则涌现了一些聪慧的知识型人物形象系列。
正如卞之琳所言:“从她的虚构与纪实的作品,主要是戏剧、小说和狭义的散文里写到的人物,(不是她自己)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出身和修养。这些人物中高门第、养尊处优的少爷、小姐等等都有一点洋气。掌握外国语文、出国留学、国际交往之类就像家常饭。”(《窗子内外·忆林徽因》)当然,这些主要是指小说中的中上层阶级的人物。事实上,林徽因小说中的人物不论是男女老幼,也不论其地位身份如何,大都是聪明、有见识、明事理的。如维彬是大学教授,他文质彬彬,知书达理,敏于思想而拙于言行;吉公虽然没有走正规的读书仕进的道路,但他是个“科学迷”,对自鸣钟照相机之类的先进机器有异于常人的痴迷;钟绿、芝、阿淑等可谓出身世家,是典型的秀外慧中的“中高门第”家族少女形象,钟绿多才多艺,勤工俭学;芝聪明伶俐,好学上进;阿淑是略接近传统型的半新半旧女子,但她也看过不少新文学作品,受过新思想的启迪,等等;至于女仆,如文珍及剧本《梅真同他们》中的梅真,等等,她们也略熏染了点文化的“香气”。如文珍做了我学诗背诗的老师,梅真上过几年的学,她们在言谈举止、行为处事上都表现出异于旧式一般女仆的知识趣味来,带有一点“书香气”。这些人物的知识性趋向,一方面固然是由作者的出身教养,她自身的多才多艺及她所接近的人群的知识层次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时代社会氛围的潜在影响。故而她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具有典型的两重性格:静态与动态的结合,宁静与烦躁的统一。如维彬教授身为中年高级知识分子,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有文化人的气质,虽然内心也许有诸多想法、念头,但在言表举止上绝对是适度、中庸的绅士形象,体现出他性格的趋静一面。然而作者又从环境场合、气氛等方面极力渲染酷暑的燥热以及他内心情感的波动,在一次不适场合的举止中使得他更烦躁不安、更窘极了,终于郁闷无聊至极而离走。这又刻画出了他性格的动态一面。《九十九度中》的阿淑,身为闺门少女,娴淑文静,任人摆布,然而天气的炙热,婚姻的不如意,激起了她内心的烦闷,一股无名的怨气由衷升起,从而爆发了电影及新文学作品无用论的思想及自暴自弃的想法;又如吉公,他终日似乎逆来顺受,心如止水,不顾外人如何看待他,只知道无声无息地做自己的活;然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中年的吉公也不耐寂寞,为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而出走。至于《文珍》中的文珍,身为使女,勤快能干,任人使唤摆布,低眉顺眼;但她也因被嫁一事而大发怨气,并最终“逃嫁”出走。可以说这些形象是集动静于一体的性格组合。
在林徽因的小说创作中,没有一个人物的性格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变化发展既有别于凌淑华笔下那种温婉娴淑的半新半旧女子的略起微波而又复归沉静的性格特征;也不同于庐隐笔下那些对前途充满希望憧憬却又前途未卜、命运多舛的女性的由喜入悲或由微喜(轻悲)到更浓郁的感伤悲哀的性格趋向。在林徽因的笔下,其人物性格的两重走向,是由于这些人物都或多或少受过教育或新思想的影响,但又身处“中高门第”,深受过传统文化及礼教规范的熏染。它既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同时也体现了创作主体的思想和情感趋向。林徽因塑造的这些性格两极化走向的人物,并不同于五四时期如庐隐、郁达夫等人塑造的两重性人物,即其性格的最终走向是趋于更深沉的感伤忧郁和悲哀,并终于导致主人公的幻灭或死亡;也不似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光慈式的光明尾巴;而是在一种较乐观明朗的氛围中孕育着人物对未来的朦胧期待,体现了人物合乎性格逻辑的发展趋向。是作者的理性思维及对现实前途深刻思考的艺术展现。
林徽因的小说创作正如一些论者指出的那样:是“厚积而薄发”的,但写得“相当精致”,她“超过了一些前代和同代女作家由于情感缺乏沉淀、提炼带来的浮躁之气,越过了情感宣泄和浪漫抒情阶段,一出手就表现出难得的艺术上的节制和宁静”[5](P.231)。而知识者的良知,特殊的现实处境及广博的知识素养使得其小说又充满了许多“变音”,总体风格呈多元化的浑厚走势。不管怎么说,林徽因的小说创作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在30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作中是有其典型性,又有其独特性的。
收稿日期:2000—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