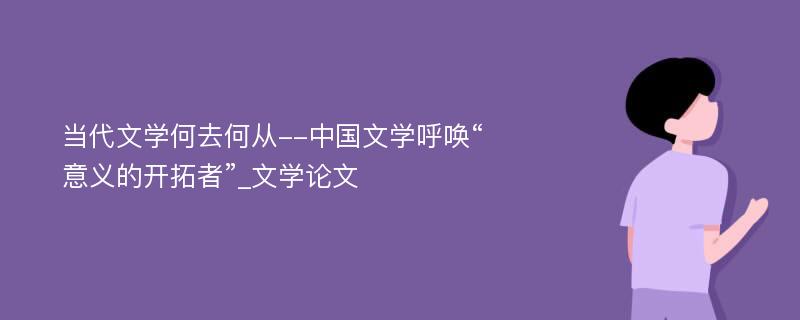
当代文学还能逃到哪里去——中国文学在召唤“意义的先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还能论文,先锋论文,当代文学论文,哪里去论文,逃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代文学的一种描述:正、反、逃
金:当代文学的危机已经叫喊很多年了,但是究竟有没有危机这个问题也还没有搞清楚。说有危机,那么如何看待这些年文学的某些显然的进步?说没有危机,又怎么看待眼下文学日甚一日的失落和尴尬?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也许应该多多拉开距离,仔细观察一下当代文学的来龙去脉,以及所面临的背景,以便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找到症结何在,出路何在。
当代文学似乎经历了一个“正、反、逃”的三部曲,种种现象我们平时在一起已经聊得很多了,我想可以更加清晰地归纳和梳理一下。
正即正统,那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心的文学,或者依我一位朋友的说法是“庙堂文学”吧;反即反思、逆反、反抗、反叛,也许可以叫“在野文学”,“抗衡文学”,当代文学的“反”,是从《班主任》,从伤痕文学开始的;“逃”即逃亡,逃离政治功利主义,意识形态中心,逃离“庙堂文学”与“在野文学”的二律背反的焦点,当代的“文学逃亡”我想王蒙是始作俑者,他开“形式主义革命”之先河,以一种滑开的,惹不起还躲不起的方式成功地启发了一次胜利大逃亡的宏大文学运动。这一“文学逃亡”我以为无论就目的论还是方法论讲,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意义都十分巨大,逃亡就是消解,消解唯政治功利,唯意识形态的僵化模式,为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健康化、广阔性和丰富性扫清了道路。
陈:这个问题可以和“重写文学史”扯在一起,正、反、逃三部曲这种说法是适用一般性地描述人的精神发生,同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中国当代文学是一贯重视政治功利,重意识形态的正统文学,有其历史必然性,这是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使然,它使中国文学长期自愿放弃对自身的关注,而把自己统一在“文以载道”的对某种绝对精神的追求中。文革之后的所谓“新时期文学”,是被提到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度来认同的,一言以蔽之可以用一个“反”字来概括。反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哭泣、漫骂、嘲讽、把身子背转开去等等,例如我们讲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先是一种诉苦诉泪、令人心碎的倾诉,然后是控诉与思讨。这些都不出“反”的形态,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新时期文学”对所谓“人学”的关注,至多是表达在变幻莫测,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历史潮流的淹没中想到自己的存在。而被意识形态中心论长期遮蔽的个人本位文学,生存为本位的文学并没有得到彰显。这在文革后复出的一批“复活的作家群”中得到充分表现。这批作家最典型的情结就是“平反”情结,这就基本上为“反”的形态定了性。喧哗一时的“知青文学”以英雄史诗般的神话色彩主要还是打上了一个部落、一个集体的印记,其诗性宣泄最典型的情结就是“祭献”情结,以悲惨或悲壮的青春岁月表达了反的内涵。“逃”起源于何时何地何作家,这不是一个很容易说清的界线,当厌倦了平反要求、厌倦了自我证明,一种无所谓的新情感就产生了,开始有了逃跑的欲望,想想《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就很清楚,这在“复活的作家群”之后,新生代作家中就很明显。当然,这种欲逃不逃的姿态不过是一种想被挽留的表达,和以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等“先锋派”的逃不是一回事,先锋派的逃有一个很自觉的共同追求:规避上述正与反的纠缠,他们各自演绎的故事侧重于文本、风格、叙述模式的追求、重在形式上的革命,例如通过语言圈套、纯粹的幻想、变形、随意并置等等,成功地甩掉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模式。
温:这个话题很有意义,也有必要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一次全新的扫描,就算是换一个新的审视角度吧,观察者所处的时空条件不同,所观察对象的形体、性质相应会有变化。我们当下的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文学界的状态如何,文学将何去何从或者说作家们对于文学的作用,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作用,都应该有个说法。从76年到现在,又一个十七年过去了,我们将这段时间当作特殊的阶段来度量,找一找其中的共性和异质,至少对于批评个体来说,应该是一次有趣的旅行吧。用“正、反、逃”三字来概括新十七年文学的精神特征,我以为是胆大之举。看起来有些粗率,仔细思量,还真是那么一回事,我不能不承受这个说法的准确性和击中要害的力量。文学现象当然是十分复杂、丰富的,不可能用一两个字眼便穷尽其源,画尽其形。但是文学批评只能借助理论的概念来进行,其实就是概念批评,话语批评,由概念而至现象本身那是批评行为过程中带来的,是批评的根本走向期望达到的目的。
陈:中国当代文学当下的混乱、无标准,令人困惑的状况正是正、反、逃三者的相对运动造成的,三者的关系可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正与反是底边的两个端点,两者的张力是以对方互为前提而存在的,在性质上同在一个层面或系统,逃是这个三角形的顶点,上下左右位移就是逃的轨迹,这样我们就可以看一看文学逃亡究竟能逃得多远?
金:正和反是在一个系统内的,“在野文学”其实也就是“庙堂文学”,关心焦点是一个,方向正好相反就是,我把它们叫做“社会本位文学”,立足点在整体的社会上,或者叫做“白毛女模式”,《白毛女》是正与反的结合,“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是反,是缺德;“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是正,是歌德,指向唯在“社会”二字上。当然,“反”不一定都有这样激烈的性质。
温:以“反”形态出现的文学是新十七年文学史中最值得骄傲的一页,它掀起的激情狂潮,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渐远渐去的辉煌的景观。知青文学、反思文学、前期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包括新写实小说都可以看作是这一类。另外,报告文学是“反”类的重要的方面军,它显然常常以“在野”的声音,针砭时弊,揭露黑幕,纵论国事。“反”是根源于作家对中心权力话语的厌倦心理和反抗意识,而且这个时代已越来越充分地呈现出商品经济话语时代的特征,普通人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标准,价值向度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作家不可能无视生活的观感和远离时代特征对其心灵的冲击,因此,“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在80年代必然要遭遇的结果,是时代潮流。“反”形态的文学改变了长期以来文学被文化控制系统任意驱使和涂抹的厄运,回到了自身应属的文化调节系统。这是文学发展的大幸。“反”对作家群体的影响之巨是难以估算的,先是通过政治意识上的反叛,进而发展到文学观念上的反判以至生存姿态上的反叛,作家获得了一次大解放。新十七年的文学发展,“反”是个极其关键的枢纽,但是,80年代初期“反”的文学所具有激情和认真,到了80年代后期都荡然无存了,“反”仅仅作为操作指令,操纵作家去反一切可以被反的地方:意义、价值、信仰、秩序以及语言规范、叙述模式……“反”不再是写作者的需要,而是写作行为的需要,对于一部分作家来说,“反到极端是恐惧”,对于另一部分作家来说,“反到极端是无聊”,便不约而同选择“逃”之一途了。
二、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奇观:胜利大逃亡
金:“逃”的文学至少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逃向“形式主义”,王蒙开的头,至马原等的先锋派形成高潮,后来的先锋则逃得更远,逃到几乎没什么意味的纯形式花招,逃到几乎完全没有思考基础的纯表面感觉,消解的作用是很大的;第二类则是逃向“玩文学”,逃向“痞子文学”,这在八九年后几乎一时独占文坛,以一种似乎超然物外的状态,打起“玩笑人生”,的旗帜、以调侃世界的方式,迎合了希图从政治重负下逃离出来的社会情绪:第三类是商业主义文学,也即通俗文学、消遣、娱乐、搞笑、宣泄、补偿云云,改革开放之初即从海外涌入的武打言情小说是这一潮流的源头,此后随我国市场的深入,文化工业的迅速发展乃愈演愈烈,可谓波澜壮阔。这一潮流,就消解而言,威力最大,就未来而言,生命力最强,因需求最盛。新写实主义也是一次小小的“逃亡”尝试,试图逃到琐屑的、纯粹偶然的日常生活中去,只是未成大的气候。
陈:“先锋派”文学所制造的“胜利大逃亡”的景观让人看到逃离意识形态中心、离开价值承诺可以有多远,它给自我表白开拓了一个自由空间,不过要让我相信,此类写作可以象卫星挣脱地球的引力一样挣脱价值关怀、意义落实,那是不可能的。既便可以成为太空垃圾一样的存在物那又怎样?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姿态就是:我做我的,关你什么事!但是没有一个先锋作家不象歌唱家、演员一样渴望成为明星的,他们和大众传媒取得某种“共谋”,以扩张和流行为旨,你会感到书店、广告、电视的围剿,他们塞过来的虚构、随意拼贴的虚假幻象就象你在超级市场,大街小巷、电视节目中无聊的歌曲对你的侵犯:你听着、拿着、看着,总之由不得你。
温:由破坏而至逃避,无所谓的姿态给批评家们暗示了什么?我觉得“逃”的方式是东方哲学影响下的一个必然结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态度,知其不可为则寄情古玩优游山林也是一种态度。当然,影响的因素,除以上一点外,还有许多,诸如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物质享乐时代的影响等等。
对“逃”应作具体分析。“逃”的方式和意义也是有多种差别的,起码应看到,一类“逃”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是有意为之,它讲述的是现代哲学命题,勒内·夏乐就说过,现代人终其一生所为,就是奔逃,是被刑讯室阻隔的奔逃。这是一种文化精神现象吧?另一类“逃”是失控行为、盲目举动,是非理性选择,仅仅受情感驱遣。这一类的“逃”大抵和作家的思想不成熟有很大关系,或者和作家的意志薄弱有很大关系。昨天讲古墓、秦淮风月、麦子和农耕,今天谈下海,感官刺激,废都,媚欲倾向很明显。
金:最近报上刊载的王一川等编的《二十世纪文学大师丛书》,声明从审美角度来判别大师与否,也许可以看作是“形式主义”逃亡思潮的一次大总结。
温:“形式主义”逃亡思潮的最致命之处是知识分子的自主意识和个体审判宣扬价值标准能力的丧失。后工业文化时代商品谋算地位的不断被提升和商人形象的愈来愈红火,使知识分子愈发感受到被遗弃的酸楚感,支撑知识分子地位的精神信仰、道德责任、价值意义被视为对改变命运一无是处的空中楼阁、纸风筝,因此,先有王朔系列小说“顽主”们对知识和文化的嘲弄,后有新写实小说对一地鸡毛一串串尿布的把玩、庄之蝶式的自诡和自虐,继有先锋小说的麻木、冷漠和颓丧、落寞的世纪末黄昏情调。偶有残留不去的知识分子情结,又能向何处消遣呢?自然是唯有“逃”向寻根”,“逃”向山野,“逃”向红粉和风月里了。记得五四时期的作家是把文学看作“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而现在的作家打出的宣言却是“文学是一门应时手艺,给同时代人茶余饭后消遣的”,作家们的观念变化已至此等地步,我们的文学发展,由“反”而至“逃”,也就不足为怪了,文学的地位的严重滑落,也是咎由自取的!
陈: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一个嘲讽对象就是“关怀”。在解构主义时代,功利性、享乐性是最具普罗意义的话语,谁还需要未来?谁还需要等待明天?谁又还需要对过去认真地承担责任呢?大批作家在时代面前随波逐流,他们不再关心文化本质,仅仅关心文化的适应性、致用性、功利性。
金:功利性不是不应该关心,相当一部分作家转向现实性、功利性较强的通俗性、快餐性、传播性文化工作乃势在必然,但文学的基础工程(其实也就是人类灵魂的基础工程)这一阵地必须有人坚守,倘全部从此“逃”开,那文学就真的完蛋了。
三、跨世纪的文学使命:意义的先锋
陈:“先锋”这个原先军事性的用语,在艺术领域何为?“先锋艺术”在查探存在、开辟道路上究竟做得怎样?现在看来,“先锋艺术”在形式上的革命是够辉煌的,形式的丰富可以逃离历史沉思、当下现实,对摆脱僵化的模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形式的危机也是几乎同时出现的,丰富和危机,是形式的一体两面,说到底形式的危机即文化的危机。因为“先锋艺术”一味追求意义的解构,中心的消解,既然内涵被取消,意义被瓦解,“先锋派”所推崇的“形式即内容”正在或早已成为一种胡说。取消形式与内容二元划分正是文学逃亡的一种说法,为逃亡的文学话语取得合法性,在叙述、语言、文体上的追求主要着迷于如何把时间转化成空间的形式。在这方面,当代小说的叙述骨子里都离不开马尔克斯。加西亚《百年孤独》中开头的那一长长句子的影响,着迷于制造“叙事圈套”以及游戏功能。多为结构与功能上的形式重复。此外,“先锋派”小说对“共时性”空间形式的迷恋,部分来自对乔依斯《尤利西斯》的有意误读,《尤利西斯》的神话框架具有包罗万象的当代生活内涵,它不仅仅是对意义、价值的解构,而同时关注意义的彰显,在“共时性”框架中,形式与内容是结合一体的,例如灵魂的漫游这个主题是由斯蒂芬来暗示的,对价值的关怀其实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旨趣。
金:诚然,当代先锋——形式先锋的文学还可以继续进行形式主义的探索,但是它作为一种消解传统模式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文学运动已不复存在。这正如本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当它与桎梏人的精神,扼杀新的文化,对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文言文作斗争时,它是极具革命意义的。在那时,形式当然即是内容,而当白话文胜利并普及,顽固派也能操起漂亮的白话文继续卫道,敌视进步时,形式就绝不再是内容了。尤其当代先锋文学,当各种杂志都争相以先锋标榜,而自身也愈益向感觉化、宣泄化、生产化、表浅化、COPE化,总之是所谓后现代化滑去时,它的先锋性就越来越可疑,而很容易成为商业主义文学的一种优雅的变体。
温:商业主义文学将更加发展、更加丰富、更加日新月异,但是它的冲破政治功利樊篱的逃离作用已大大减弱,它将只是作为市场社会的一种日常的人们基本文化需求而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当商业主义文学发育起来之后,必须要有一种与商业主义的从众媚俗性、生产性、宣泄性、娱乐性、表浅性相抗衡的具有特定独行性、创造性、内蕴性、严肃性、意义性或本体性的崇高的精神的文学发育起来,否则,市场文明下的新文学将由失衡而变为一片瓦砾甚至是垃圾。
陈:现在看来,在所谓后现代主义侵入与比较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当代先锋派文学倒是更贴近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消除中心,拆除深度模式、游戏旨趣等,若要彻底一点说,那就是几乎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现代主义作品——换言之,少数的现代主义作品被忽视与埋没。自八十年代初译介国外现代主义作品以来,都是大谈解构,消除而无视或不承认现代主义同样强调重建的一面,大谈破坏而忽视建设旨趣。我们只要想一想黑塞、卡夫卡、梅特林克、加缪、马蒂斯、蒙克、乔伊斯、普鲁斯特这些人的名字就足够明白,现代主义的拯救精神是无处不在的,对超验价值、对存在的关怀,对人性的自我救赎使现代主义显得困难而高贵,因而当后现代主义完成了它最初的形式上的革命意义之后,我认为现代主义是困难的,而后现代主义是相对容易的。
温:先锋派的出现,一开始就是以意识的前工性为特征,遗憾的是,发展到后来,许多先锋作家只是走向文本形式的探索而已。
谈到意义,不能不涉及到后现代主义对“意义”的清算,一定要分析清楚,什么样的“意义”应“破”,什么样的“意义”应“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信仰发生巨大危机。人们不得不一次次地遭受精神崩溃的打击。米歇米·福科说“人死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更是断言“知识分子死了”,而保罗·里柯强调的又恰恰是“把意义给予无”。连意义都是虚无的了,这个世界也就给拆解得七零八落的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先锋派一直忙于解构的一个重要原因。
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时间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它与消费的资本主义有着内在逻辑一致性。谈到消费,就不能不谈一谈市民文化,谈市民文化的合理性及局限性。这其中必然要牵涉到媚俗这个话题。我们的文学对形而上的关注和表现还是太少,太不够了。
金:“文学逃亡”无疑是有辉煌业绩的,但是,时至今日,“文学逃亡”还能继续这么“逃”下去吗?
很显然,“逃”锋已开始疲软,“逃亡”很可能演变成溃散。“玩文学”已率先失宠;先锋——形式先锋的文学正在降温;商业主义文学在大涨特涨之后也有落回本位的趋向。
“文学逃亡”之初的积极性随着逃亡的普泛和成功已在逐渐消失。“文学逃亡”的负面影响却在日益显现出来——“逃”的文学在逃离文学的政治目的和社会指向时,也逃离和否定了文学的一切意义,逃离和否定了文学的内容、内在感受、寻索和沉思、使命感、崇高感、创造性和人文精神。当消解成为时髦,营建就开始成为需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倾向是批判和消解,批判和消解属于传统形态的旧文化,但缺乏营建方向的批判和消解破坏性极大,而破坏的结果常常是旧模式的轮回,造反与坐桩的链条在政治上绵延不断,在文化上同样可行。因此,反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第一个跳进我们眼里的字眼就应该是“营建”,我们太缺乏营建!我们太需要营建!
温:对!营建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来说已是至关紧要的,文学要实现自我救赎,便不能不重新考虑营建这一至大事体。文学不能一味消解而不营建,消解不是最终目的。消解是为了拆除旧的价值秩序,为新价值秩序的建立清扫出基地,譬如拆除旧的棚屋,是为着在那里营建高楼,如果没有营建的打算,拆除便成为丧失期待意义的破坏行径。对我们的文学来说,被解构主义情绪裹挟而进行的一系列“拆除”行为已进行多时,已发展到“破坏”地步,现在更迫切需要的是营建(当然营建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对旧秩序的拆除)!我们的文学已被拆除得遍地瓦砾,十分的破碎不堪:小说文本呈现的景观常常是性欲、谋杀、死亡、变态和鸡毛蒜皮的邻里口角、争风吃醋;诗歌文本呈现的是一窝蜂赶趟式的换旗号勾当,大量重复主题和复制词汇意象,反语言、反逻辑、反价值、反意识,诗的整体面目彻底“非非”起来;批评文本呈现的是术语的不间歇的改头换面行动,最终发展到“失语”阶段;……现实存在是龌龊景观,人生是一场游戏是可供拆解的杂物,人性更是不屑一顾的垃圾。因为解构,作家不再需要情怀,拯救意识成为笑柄,寻找精神家园成为欺世妄谈。作家不再需要洞察社会众生,不再需要深邃超前的思想,不再需要考虑叙事建构,更不必谈论什么时代精神文化关怀生存价值,作家所不可缺少的倒是种种揄揶、自嘲、反讽和焦虑、狂躁、发泄。无情、无义、无恨、无爱成为部分作家的写作表征,他们对此直言不讳:我们纵欲!我们蔑视理性精神!应该承认,社会败坏了作家的口味,结果,作家便报复式地败坏文学的口味,败坏读者的口味。但是,这些可以成为消解的理由,不能成为不营建的理由!
金:参照二十世纪西方市场文明的发育史,可以发现一种消解与营建的变奏始终不断。
启蒙时期是以消解为主的,朝向个人与现世的人文主义的一种消解,消解中世纪的致密的结构,消解宗教的威严和崇高。但是存在不能承受之轻,消解的结果是人们感到必须营建一种新的,个人的,现世的有序、威严和崇高,于是出现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分别以理性和激情作为新的上帝——人间上帝。本来就处于二元分离状态的人间上帝所规划的精神秩序很快又出现许多纰漏,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残酷面又带给人们诸种怀疑,于是一轮新的消解——批判现实主义——又着手新的清算;直至现代主义出现。无休止地描画和批判琐屑的现实使人们重又渴望宗教式的提升效果,于是现代主义打出艺术乃是现代宗教的旗帜,在纸上、画布上、音响里,亦即人心里营建起精神教堂来;再后,当市场的势力从地理上说全面侵入东半球,从层次上说深嵌入文化领域,以构成文化产业革命时,最新一轮的消解——后现代主义出现了……
近百年的中国史有如一跑马场,西方的各色主义都在我们这里跑过了一圈,跑得我们满地泥泞,糊里糊涂。到世纪末我们盘点时,似乎该清醒了,我们需要的恐怕不是某一、二种西方的主义,我们要借鉴的是他们的发育规律,首先是消解与营建的对立发展经验。
我们会发现,我们太缺乏营建。
营建太难,营建不能抄袭,营建须因时因地因人来综合。
那么营建什么呢?营建意义!最关键的是要营建意义。不是回到过去的唯政治功利的意义上去,而是寻找一种属于新文明的新意义。
市场经济带来的最突出的变化之一是,人的物质欲望被赤裸裸地勾引了出来,所谓人欲横流。
温:个人出台了!
金:对,个人出台了,物质的个人出台了,但精神的个人却留在老巢臼里。在传统中,我们的精神是结构在群体里,结构在家庭、家族、民族、国家、阶级、党派、团体等等里,如一段时间,我们的精神曾主要结构在“工人阶级”里,今天我们则更多结构在“爱国主义”,这种精神动力今天仍然是巨大的,但是远远不够!因为物质上平均的群体已经瓦解,物质的个人已经出台,如何能够指望继续压抑精神的个人,让它仍然完全留在群体的结构里呢?试想想,今天不要说整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即使一个村庄,一个班组,都很可能出现百万富翁和赤贫的区别,那么过去那种结构在群体里的精神能够完全奏效吗?
所以我们今天愈来愈需要对于个人和人类灵魂的博大关怀。过去我们的观念里是个人渺小,群体伟大,其实个人乃指人类每一分子,才真正博大,而群体总是指某一部分人的集合。
我们需要营建真正的人学——人的本体之学,不是人的社会之学,而是人的本体之学。这里是对终极的关怀和激情,是对意义的沉思和寻索,是对属于新的人文精神的发见与弘扬——它将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新的生存的烛照和指引,引导我们走出纯粹物欲的迷营,达成灵肉统一的境界。
陈:说建构,说营构总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总是要落实到精神要求的描述上。象现在文化转型期,商业主义大潮下凸现的个人,是不是说只见物态的人,而精神的人仍然停留在旧的巢臼里,那也还不能这么说。人的欲求也可以看出精神变奏的东西。现在,金钱衡量一切价值其实早就超过金钱本身的价值,这是转型期实用主义价值取向的表现,值得肯定的是这一个转型期虽然迟到但毕竟是来到了,幸福的定义虽然存在于个人的理解之中,但稳定,富足的要求是大多数人的理解,所以,物质的追求是一种必然,对于奢谈精神世界,则比较漠然。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是不是一种新精神产生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呢?
当然,问题如果不是奢谈精神,而是不谈,甚至是鄙视,这就有点问题了。所以,才有人要感叹“知识分子”的“痞子化”与堕落;才有不少人感叹今日文坛没有正义感,往昔的凛然正气荡然无存。要呼唤崇高、要追求精神性,这其实是到了很迫切的时候了。
想象文学艺术可以左右社会大潮,改变文化走势,其实是一种自欺。在当代,文学艺术再弱不过了,试想一幅画挂在墙上的价值不正是等待着卖价提高吗?然而坚持文学艺术应该是人心平衡社会、提升人们的永恒存在形式,那就是对信念的坚守。总之,时下精神萎顿也好,堕落也好,混乱漠然也好,这样的存在状况恰恰构成了真正关心精神营构者之“炼狱”,才可能继续言说建构。
温:也可以这么说,我们这里所提出的“意义先锋”,根本出发点就是首先营建人的本体之学,是文学对人性、人的生存权利的可能性的追问!换言之,就是以个体的睿智和情怀对生命世界进行“命名”,通过不断的命名寻找新的价值秩序和神圣事物。强调个人自由,并不是赋予个人无限大的权力,而是强化个体的自觉意识,主动地自愿地而非被强制性地察问群体的精神状态,并为人群服务——真正的终极关怀得以体现!不强调这点的话,机械地理解个人本位主义,文学又将向四处奔逃、溃散。因此,文学要重振旗鼓,要发掘弘扬新的人文精神,必须要有两个前提:一是作家要自信和自律,二是肯定“意义”在存在中具有必不可少的地位和作用。
陈:“意义的先锋”,应当被提到跨世纪文学使命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必须以价值的重建与守护为使命,从而使之有益于人生。文学的鼓舞作用,人生价值的设置必须由对人生及存在的关怀来完成。呼唤“意义的先锋”,也可以说是召唤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精神,对精神现象的深度挖掘,对精神救赎的深切关注。现在,精神的萎顿、侏儒化正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焦点。
金: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这是一种振臂一呼,万众跟随的工作,在很长时间里,这也许还只能是为数不多的真艺术家真思想家的艰难痛苦的使命,但是现在是时候了,中国文学需要一种“意义的先锋”,它们通过痛苦的体验、坚实的沉思和漫长的寻索,在新生活的基础上为我们打通通往未来之生存的精神空间的甬道。
在营建人的本体的同时营建文学的本体,在营建存在的意义的同时营建文学的意义,在营建民族新人文精神的同时营建新的中国文学,这恐怕就是我们文学的跨世纪使命,这是一种我们的文学中过去始终被忽视或遮蔽,而未来却绝不可或缺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