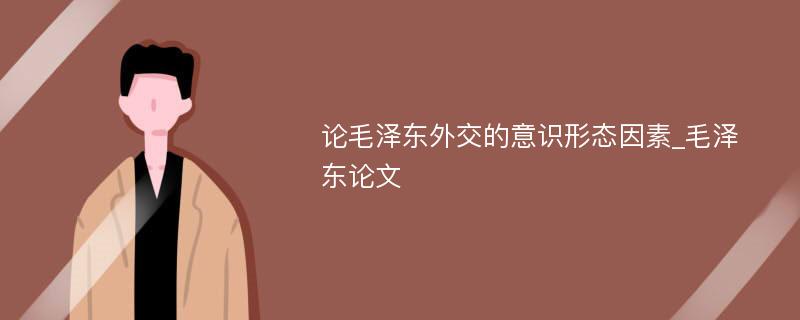
论毛泽东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外交论文,因素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1)04-0019-08
毛泽东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问题,是一个看似古老实际上尚欠深入探讨和发掘的课题。说它看似古老,是因为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或多或少地触及了这一问题。不论是从历史视角论述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和演变的,如章百家的《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还是从毛泽东外交的某一特点出发进行研究的,如胡长水的《毛泽东“武装和平共处”思想初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以及从毛泽东三个时段外交战略的得失出发进行分析的,如颜永琪的《新中国“一条线”外交战略评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1期)等,莫不如此。说它尚欠深入探讨和发掘,是因为多数相关论述,或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反意识形态前提下,把毛泽东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当做一个可对照和被批评的对象和参照,或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作为一个附带的争议点,均欠缺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系统的论述和探讨。少数从意识形态角度论述毛泽东外交的,也仅是从意识形态与某一个别事件,或是意识形态与毛泽东外交的某一方面的关系来论述其影响,诸如栾景河的《中苏分裂:意识形态的分歧,还是国家利益的冲突》(《中共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3期),李才义的《论毛泽东外交中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6期)等,因而仍然缺乏对这一因素基本属性、地位、特征及其深层次影响的系统分析和探讨。笔者试对此作一些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探讨。
一、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意识形态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而外交学中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指政治思想、理论、信仰和政治观念等”。①它与大多数人理解的意识形态概念基本吻合,其最主要的内容是政治价值观,并深深植根于各国的文化传统中。
外交与意识形态因素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单从价值观考量,多数政治家都会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美好的和善良的东西予以坚持,而对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丑恶的东西,予以毫不妥协的斗争。而当代民主国家的民众则更会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支持或反对本国政府对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从而给决策者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动力或压力。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往往会受到更为重要的国家整体利益的影响,而不能不在政治价值观,也就是意识形态与国家的其他利益之间进行权衡。不同的决策者在不同的时代,对于意识形态在国家整体外交利益中的地位的看法会有所不同,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外交决策上的表现。
中外学者大多认同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我国学者多从国家利益中的精神利益出发,阐述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得到广泛认同的关于国家利益的概念是这样表述的:所谓国家利益就是“主权国家在开放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其决策主体所认定的物质与精神的,生存与发展需求的总和”。②著名学者阎学通也认为,国家利益就是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力和受益点。它反映这个国家国民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在物质上主要指安全和发展,在精神上主要是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尊重,以及价值观等。③俞源甚至直接指出:“在对外关系中,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利用国家政权维护和争取本阶级的利益,比如要维护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会运用外交,甚至军事手段扩展自身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④这些都清楚地指明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精神利益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外交中具有一定的影响。
西方学者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意识形态对国家利益的影响。亨廷顿认为,国家利益来源于认同,而认同又包含文化和信仰两部分。在这里,文化是指价值和机构,信仰则是“普遍的意会和原则”,如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等。⑤约瑟夫·乃认为:“国家利益可以包括价值观,如民主和人权,假如公众感到这些价值观对他们的属性和特性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们愿意承担代价去促进这些价值。”⑥
在实践中,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意识形态有时甚至在外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如果太大就会发展成为革命主义外交。革命主义外交范式的分析是一种阶级分析方法,它依据经济条件来理解现实的世界体系。它认为现实的世界体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由两大阶级或两大地区所组成。
而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则往往从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出发,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势,这是西方国家自诩他们的政体为“自由和民主”象征的必然结果。如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和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外交等,都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外交的一种较为极端的例子。而克林顿政府也曾把“推进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作为其外交的三根支柱之一。
即使是中等国家,甚至是弱小的国家,也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选择本国的盟国,并以警惕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的敌对者。这也是新中国建国后,许多亚非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持续怀有狐疑心态的根本原因。就连极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也会坚决维护本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反对其他大国的干涉。众所周知,邓小平坚定地放弃了毛泽东的革命主义外交,但面对西方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制裁和颠覆,他仍然坚定地宣称:“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并指责西方“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⑦这表明意识形态在邓小平外交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是缺少了毛泽东时期的进攻性而已。因此,本国的价值观始终是政治家“认识本国和世界各国的基础,是他们对本国和其他国家态度和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⑧
因此,意识形态对国家外交的影响,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其影响大小的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的只是在不同决策者心目中,意识形态这一精神利益在外交中的地位有所不同而已。
二、意识形态因素在毛泽东外交中的地位
从毛泽东外交被西方称为革命主义外交就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因素对毛泽东外交的巨大影响。不过,若因此就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在毛泽东外交中一直占主导地位,那就不符合实际了。意识形态因素在外交中的地位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问题,不能离开与其相对的其他因素单独地进行论说。这里的其他因素主要是现实的物质利益,以及包括国家的国际声望等与意识形态相并列的其他精神利益。若是从范式的角度讲,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中,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范式因素在外交中的地位的比较。
地位,实际上就是各单位要素在一定体系中的重要程度的比较。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利益在整个国家利益中的排序问题。⑨而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利益在外交中的地位,只能是意识形态利益所属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因素在国家外交整体利益中的地位,与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所涉及的国家利益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三种范式因素地位的排列,不能像一般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排列那样,简单地用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进行对比。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意识形态因素、现实主义所涉及的发展利益和生存利益,以及理想主义所涉及的国际声望等,都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都不能简单地把其归结为核心、重要或是次要,只能以三种范式因素在国家外交中的比例来大致确定。
而三种范式在国家外交中的比重主要取决于国家决策者自身的认知,这也正是不同的国家领导人,三种外交范式因素在其外交中的比重一定会有所差别的重要原因。在西方,不同的政府,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因素在外交中的地位,其差别往往也很大。
即使在毛泽东外交的各个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因素的地位也并不相同,这主要是毛泽东在各个时期对意识形态在外交中地位的“认知”不同所致。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内心活动是不断互动的过程。”⑩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领导中国外交的20多年时间里,在国际环境的变换下,意识形态因素在外交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本文将从毛泽东外交的三个时期的国际环境及毛泽东本人的社会性“学习”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外交的三个时期,意识形态因素在其外交中的地位的不断变化过程。
包括美国学者在内,大部分的中外学者都认为,“一边倒”外交整体上是现实主义的,这就说明,在那个时期意识形态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是次于现实主义的。在美国“遏制”政策出台的背景下,中苏结盟有三大现实主义的利益。首先,“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11)其次,“一边倒”外交对于巩固国家政权,争取国际承认,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迅速获得国际援助,使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得以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2)这些足以说明,虽然以毛泽东为领导的新中国第一个时期的外交战略名为“一边倒”,但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地位是比不上现实的物质利益的。
当然,“一边倒”这个名字本身就能说明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外交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毛泽东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时和建国后一个时期内,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的建交问题,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13)这说明了“一边倒”战略的意识形态影响有多大。越南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这两个重大的决策,都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重大影响。“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14)这表明建国初期的中国外交,始终与革命和社会主义两个词密切相关。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外交开始逐渐“习得”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从事外交,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逐渐淡化,甚至理想主义范式的因素都有超越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趋势。正是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1953年,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毛泽东强调它“应当适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首先是为了逐步扩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和有些学者所说的“和平统一战线政策”是一致的,其主要内容都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为了中国的和平,毛泽东积极扩大和推动与西方国家的民间交往。著名的中日民间外交和中国争取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就是毛泽东试图用“和平共处”方式来推动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例证。因此,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甚至赶不上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和平共处”外交。
意识形态因素对毛泽东外交的影响,在“两条线”外交时期达到了高潮。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外交被西方国家称为“革命主义”外交。以1957年莫斯科宣言为起点,意识形态因素在毛泽东外交中的地位开始上升,经过对王稼祥试图反思“左”倾激进对外政策的批判,再加上“文革”的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末,革命主义在毛泽东外交中的影响已超越了包括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在内的所有范式。
如西方学者所说:“毛泽东在整个60年代推行‘反帝反修’的‘两条战线’战略,同时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甚至主张‘世界革命’……‘这一政策使得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国内建设也受到极大影响。”(15)随着外交困境在60年代末发展成为苏联威胁,毛泽东对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考虑逐渐压倒了意识形态的冲动。以基辛格访华为开端,毛泽东改善了与以美国为首的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关系,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开始了与西方国家的非正式的结盟,以对抗苏联的霸权主义及其对中国的安全威胁。
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退潮,理想主义范式因素的地位随之上升并超越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三个世界”理论在这一时期成为毛泽东重要的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热情,在这个时期转化为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积极支持。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对霸权主义的态度(而不是以以往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属性为标准),作为政治斗争的基本出发点。曾经作为“各国反动派”之一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也成了中国团结的对象,这让新中国站在了前所未有的道义的高度,也让中国外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对意识形态的坚持,其突出的表现是,尽管毛泽东积极改善与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关系,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许多第三世界共产党游击队的支持,只不过是降低了支持的力度而已。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与东南亚国家建交时,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共产党哪能不支持共产党呢?不过我们现在可以让一步,以后在武装方面少支持,但在道义上还是要支持的。”(16)这充分表明,意识形态因素仍然在毛泽东外交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三、意识形态因素在毛泽东外交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原因分析
国内制度因素。“外交是内政的继续”这句名言,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外交是一定时期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延续;其二,外交是一个国家内政的基本框架的反映。因此,内政,包括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政权的稳定、国内政策的走向等,都对毛泽东外交中意识形态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毛泽东时期,新生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意识形态因素在毛泽东外交中的地位。近代中国人民屡次抗争却不断失败的经历,与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经验后中国革命的成功,使得毛泽东对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极其赞许。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和苏联两个词非常重要。同时,历史上从太平天国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敌对甚至直接的武装干涉,也早已塑造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对西方国家的强硬态度。所以,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17)也正因为这样,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建国后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新中国建立以后,美国长期坚持对华敌视的政策,对新中国进行封锁和遏制,即使在中苏分裂的情况下,美国这一政策也丝毫没有松动。这就更加使得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在其心目中关于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泾渭分明。这也是毛泽东外交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为革命主义外交的一个重要原因。(18)因此,一些学者所说的,“中苏意识形态的同一性(为“一边倒”战略)提供了天然的基础”(19)是具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政权的新生性,决定了意识形态因素在毛泽东外交中的重要性。对于新生政权来说,国家安全首先是与政权的安全和稳固紧密相关的。同时,新生政权的国际承认,也是政权国际社会合法性的主要依据。因此,毛泽东时期作为新中国的第一届政府,必然首先面临着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在国际社会中争取合法性的问题。
中外学者多次论述了毛泽东“一边倒”战略选择,在美苏对立的国际环境中求得政权稳固的战略选择之目的。有中国学者提到“‘一边倒’是战后国际环境的理性应对;也是建国蓝图谋划的迫切需要”。(20)也有学者提到“冷战把世界分裂成互相隔绝的两个部分,中国在亚洲冷战中首当其冲,对外政策的回旋余地受到极大限制。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十分关键的问题是选择怎样的对外战略才有利于新政权建立和巩固”。(21)而多数西方学者到现在仍然坚持,毛泽东对美国可能对新中国政权采取武装干预的忧虑,是毛泽东选择“一边倒”战略的主要原因。(22)
俄罗斯学者从中苏分裂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角度,论证了“两条线”战略中隐含的维护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战略目的。他们认为:“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与斯大林有关的苏联社会体制,在中国看来,这都是对社会主义和中共当时遵循的所有理论的背叛”,(23)是对毛泽东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否定。而且“苏联的言论对毛泽东来说,不仅是理论争论,而且还是对其创造人民公社等国内政策的直接打击”。(24)因此,毛泽东“两条线”外交中强烈的意识形态进攻性,与毛泽东对其自身政权合法性基础的维护有着密切关系。
再次,国内政策的走向,对毛泽东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地位也有较大影响。对内政策变化必然引起对外政策的调整,因为国内政策反映的是决策者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基本观点,政策的变化反映的是该国国内政治面貌的变化。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实际上就带有刚从革命时期走来的“惯性”。从“一边倒”确立的过程看,革命过程中带来的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已根深蒂固。学者们也论证了毛泽东从国共内战形势开始明朗之时,就开始等待苏联的支持,这也是1941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早已定下的基调。(25)而在对美国短暂的试探得不到善意回应后,毛泽东就决定“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26)即使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革命时代对蒋介石政权的记忆也已经成了对这些国家政策的出发点。刘少奇在1949年11月亚澳工会会议上,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宣布新中国还要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27)因此,中国学者说:“‘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28)
朝鲜战争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安全环境的恶化,与1953年开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需要的和平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种情况下,外交政策就必须以争取和平为目标,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关系的国家,甚至包括西方国家。5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政策的出台,以及中国多次缓和对美关系的努力,都证明了中国当时对和平国际环境有多么的渴望。
50年代末期中国外交的“左转”,也与中国国内政治思潮的日益“左倾”密不可分。在“大跃进”、“反右”等政治运动的氛围下,中国外交不可避免地带有“左”的倾向。也正是在“大跃进”等国内“左”的思潮冒头之时,旨在与世界各国推行“和平共处”的周恩来卸任外长职位,不久解放军炮击金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成为过去,中国外交开始了从“和平共处”向“革命外交”的转变过程。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内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外交的“革命主义”不可避免地发展到了极致。
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和解,实际上是毛泽东“左”的思潮走入死胡同后,首先在外交领域进行调整的一种表现。许多学者都曾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60年代末期“两条线”外交面临的重重困境,特别是来自苏联迫在眉睫的安全问题。这是一种比内政更能直接感知,并更具紧迫性的问题,所以毛泽东首先在外交领域纠正了极“左”的现象。“外交政策的转变也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意义,它与当时‘左’的意识形态要求严重背离,是此后一系列国内政策转变的先导”。(29)
国际环境原因。许多学者都曾经做过这样的论述:对“中国这个亚洲大国来说,无论从地缘政治角度还是从历史沿革角度看,中国都处于美苏在远东矛盾的风口浪尖上,很难走中间道路”。(30)在这种情况下,考虑中国外交政策时,意识形态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封锁,甚至军事威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势不两立的历史记忆,在这种情况下被继续放大。包括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以及美军进驻我国台湾,都使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厌恶不断增加,也使得毛泽东进一步坚定地选择了“一边倒”战略,并用斗争的方式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
50年代中期,随着中共执政党地位的逐步稳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也曾试图推行与民族国家“和平共处”,对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时放出缓和和发展关系的信号,但是国际范围内美苏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却在不断继续显化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我者”和“他者”,并再造“两者”的对立和斗争。
中苏分裂进一步推动了毛泽东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增强。“因为北京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理论水平方面相对薄弱,决定了它必须采取咄咄逼人的斗争姿态,在中苏冲突的过程中,如果中共不保持连续进攻的姿态,那么它就注定不断后退,直到最终认输”。(31)
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20世纪的历史巅峰,50年代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或民族解放运动也发展到新阶段。具有革命热情,并对第三世界相似经历一直持同情态度的毛泽东,进一步激起了要在第三世界掀起新的革命高潮,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愿望。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新中国外交的“外张力”,也就是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和“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32)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想象中的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起点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人似乎重温了那种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旧梦,(33)就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错误了。
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个人性格因素。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沃尔弗斯认为:“我们习惯所称的国家行为实际上受到特定决策者或特定参与者集团的某种预先倾向所影响。因此这些个人的心理特性,如动机、价值偏好、气质和推断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就被看成是基本的变量。”(34)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他们自身的生长环境、经历、已有世界观,在他们心目中早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有些学者所言:“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35)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36)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和辉煌,与近代百年耻辱的反差,使得毛泽东具有了强烈的民族复兴和建立美好国际秩序的使命感。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又是一个杰出的革命家,一个把革命和社会主义视为毕生事业和生命的人。而中国革命在艰苦条件下的成功,也给了他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走向美好世界,并重温中国世界中心地位的热情和勇气。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外交领域里所展现的革命热情就可以理解了。因此,有西方学者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最终目标是改造旧中国和摧毁旧世界,同时,在世界上作为范例,向其他被压迫民族提供‘中国革命经验’,使中国重新建立在国际社会中的中心地位。”(37)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对毛泽东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的评价
对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评价的关键,是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比重是否能正确地反映国家利益的构成。由于毛泽东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在其各个时期的比重并不相同,因此对毛泽东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的评价只能从三个阶段分别进行。
“一边倒”时期。“一边倒”初期,意识形态因素在我国外交中的比重总体上是合适的。其原因就在于在美苏对立的国际环境下,这是一个为了国家安全和政权巩固不得不如此而为之的“倒”。而且,中国的“一边倒”是在维持国家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的“倒”,在当时的环境中能做到这一点已是难能可贵。因为,结盟政策的选择往往是在安全、财富和独立自主之间进行平衡后做出的抉择,(38)在这种选择中,要做到既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又能独立自主是极其困难的。
只不过在“倒”的度的把握上并非没有可商榷的余地,有点超越了国家整体利益的需求。其主要表现是,在外交中出现了不应有的对第三世界国家输出革命的倾向,偏离了巩固国家政权、保障国家安全和为国家发展借力的目标。所幸的是这种偏离除了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外,更多的只是一种领导人头脑中的意识,并没有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现实。而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如诸多学者所论述的那样,是一种为了国家安全和独立不得不为之的战争。
随着“和平共处”原则的提出,意识形态在国家外交中的地位变得更为恰当,并且中国领导人早已意识到利用外交为中国已经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环境的重要性。这从中国坚决结束朝鲜战争,周恩来为争取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的签署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随后,毛泽东又把除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看做是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后来,他把这些国家称作第二中间地带),并将其列为可以团结的对象,(39)极力在这些国家推行“和平共处”原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为缓和中美关系所做出的积极努力。
当然,这时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地位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感情与国家的独立自主没有分清楚,主要表现在对苏联和南斯拉夫冲突中对南斯拉夫的批判,缺乏了自己的立场,以及对越南的支持有脱离国情的嫌疑。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对美外交的斗争色彩可能过于浓厚,延缓了中美关系改善的步伐。
“两条线”时期。这一时期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远远超过了国家利益的需要,对此学者们多有论述,在这里不再赘述。不过需要强调的是,除了1966-1969年“文革”高潮时期那个短暂的荒唐年代外,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合法性而发动的对美、对苏“两个拳头打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50年代中国崛起前景已较为明朗的情况下,除非中国愿意长期屈服于大国的压力之下,中国和美苏的决裂和对抗在当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就在于美苏作为既得霸主,是不会轻易容忍新崛起的后来者的。(40)其二是如前所述,中苏意识形态冲突,作为弱者一方的中国,在这方面是没有退路的。
更为重要的是,若没有中苏的冲突,和毛泽东领导的“两条线”外交的强烈斗争性,中国就不会开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正是从中苏产生裂痕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中,毛泽东开始考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论十大关系》就是证明。同时,也正是毛泽东“两条线”外交强烈的斗争性,让中国外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气魄和活力,并初步具备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道路的可能性。就连俄罗斯学者也认为:“中共领导在冲突中所表现出的顽强的战斗性和进攻性,保证了中共和中国能够摆脱苏联的影响并保持自己独立的地位,并有助于发现中国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为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41)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毛泽东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超过了国家利益的正常需要,但其积极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
“一条线”时期。“一条线”时期意识形态因素在外交中的地位开始向理性回归。毛泽东再一次把国家安全置于外交的中心地位,并成功地维护了这一核心利益。就连挑剔的西方学者都认为中美缓和首先“加强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有效地抵制了苏联对中国的威胁”。(42)同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带动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使中国摆脱了革命主义外交带来的严重困境,并彻底解决了新中国的国际承认问题。而且中国和西方关系的改善,也为中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恢复打开了大门,中国成为了国际社会真正的大国。所有这一切,也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关系的发展敞开了大门。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当今美国众多商场充满“中国货”,可以看出70年代毛泽东“一条线”战略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因为中美关系从1972年起“揭开了新篇章”。(43)
毛泽东也再次提升了理想主义在国家外交中的地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中国继续支持第三世界对抗包括美国在内的霸权主义的斗争,著名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并得以实施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也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鼎力支持下,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并成为除美国和苏联之外的世界第三支力量。西方学者常常把1971-1989年的国际格局,描述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在这一描述中,中国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但也显示出中国开始成为主导美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44)
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共产党游击队的支持,仍然给国家整体利益和形象造成了损害。如一些华裔学者所言:“中国形象欠佳的部分原因是国际冷战政治的歪曲,部分原因则在于东盟对中国本身所创造的革命词句的误解。”(45)这说明毛泽东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仍然存在“超标”的现象。
五、毛泽东意识形态外交的启示
意识形态因素在毛泽东外交中的影响有得有失,回顾毛泽东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可以给今天的外交留下一些有益的启示。
其一是外交中意识形态的地位必须在把握时代形势和矛盾的基础上确立。许多学者在分析毛泽东“两条线”外交时,都强调了毛泽东对时代矛盾把握的偏差。多数中国学者认同,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夹带着‘大跃进’的激情,认识继续‘左’转,愈益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强调武装斗争,非和平过渡,强调与帝国主义无法和平共处”,(46)这是毛泽东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发展到极端的最根本原因。可见,对时代矛盾的把握,是处理好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作用的根本性环节。
其二是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的比重必须结合国力,量力而行。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外交中什么时候都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但关键是比重必须适当。对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帝斗争的支持,更要从国力水平出发。不管是推行革命主义外交的苏联,还是推行“人权外交”以及把推进民主和人权作为自己外交支柱的美国,都是以其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如若对此运用不当,必然会对国家整体利益造成根本性的损害。因此,约瑟夫·乃认为,人权等价值观仅仅是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价值观等问题占据政策的支配地位,往往是以A类问题(国家的最重要利益)的转移为代价的。(47)国力最为强盛的美国尚且如此,我们更应该深思。
其三是必须处理好国际主义和革命主义的界限,避免输出革命。毛泽东历来主张“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48)在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外交也大致如此。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一是哪些“革命”是正在争取解放的“革命”?是否所有冠以“共产党”名称的反政府运动都是“正在争取解放的革命”?这是我们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基础。二是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是否必须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甚至这些国家的政府立场鲜明地进行斗争?60年代,我们“不得不在极其困难和危险的局面下面对世界,不得不在孤立的状态下勉力支撑我们的外交工作”,(49)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没能把握好这个度有一定关系。
意识形态在外交中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大比重才是合理的问题。意识形态因素在毛泽东外交中一直占有较大比重,因而也在其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毛泽东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就都是有失理性的,而应该依据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分析,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注释:
①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②秦朝英:《论国家利益——生存与发展需求》,《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③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④俞源:《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91年,第152页。
⑤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9页。
⑥Joseph S Nye,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1999,23.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4-345页。
⑧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⑨国家利益重要性排序有不同的方法: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曾在1996年和2000年两次依据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依次将国家利益排列为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我国学者白希把国家利益排列为最高利益、战略利益和战术利益;而更多学者则把国家利益排序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
(10)[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48页。
(1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32页。
(12)王国学:《对建国初期毛泽东“一边倒”战略方针的再探讨》,《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4期。
(13)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46页。
(15)陶季邑:《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一条线”外交战略的研究述评》,《史学集刊》,2005年第5期。
(16)资中筠:《从变化中把握大国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3期。
(17)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8)有学者专门论述了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对新中国外交的持续敌视,对新中国“两条线”外交形成的重大影响。参见张秀华、曹国慧:《对60年代中国外交的新认识》,《理论前沿》,2004年第8期。
(19)程珂:《再论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20)王国学:《对建国初期毛泽东“一边倒”战略方针的再探讨》,《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4期。
(21)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2)陶季邑:《近10年美国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一边倒”外交思想研究述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
(23)孙艳玲:《〈苏中分裂:原因与后果〉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
(24)孙艳玲:《〈苏中分裂:原因与后果〉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
(2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81页。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35页。
(27)《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5—150页。
(28)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29)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30)王国学:《对建国初期毛泽东“一边倒”战略方针的再探讨》,《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4期。
(31)孙艳玲:《〈苏中分裂:原因与后果〉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
(32)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3)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34)倪世雄、金应忠编:《当代美国国际关系流派文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53页。
(35)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6)《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07—109页。
(37)陶季邑:《近10年美国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一边倒”外交思想研究述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
(38)[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79页。
(39)《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40)李优坤:《国家利益视角下的毛泽东外交》,《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41)孙艳玲:《〈苏中分裂:原因与后果〉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
(42)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43)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44)Gerald Segal,The Great Power Triangle,London:Macmillan,1982,126.
(45)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Regional Order,London:Routledge,2000.179—180.
(46)林祥庚:《周恩来与中国外交纠“左”》,《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5期。
(47)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
(48)宫力:《毛泽东外交风云录》,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年,第169页。
(49)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8页。
标签:毛泽东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