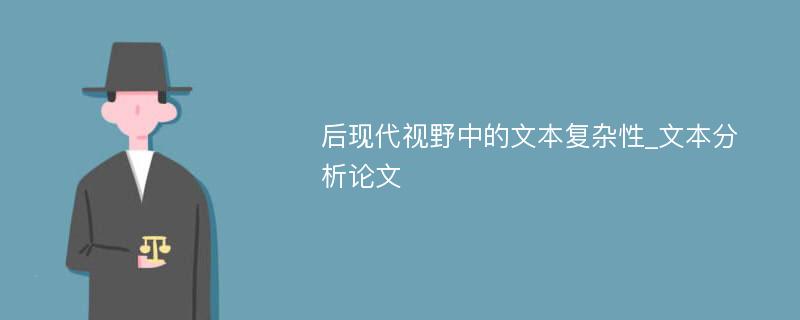
后现代视野中的文本复杂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杂性论文,后现代论文,视野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2)01-0021-05
关于文本的传统观点认为,文本一旦形成就只有一种含义,即文本自身的含义,阐述 者的批评和读者的阅读,都是努力还原文本的本文真义。后现代哲学家和文论研究者则 从自己的角度发掘文本的作者含义和读者含义,并且彼此争论不休。[1]其实,从复杂 科学角度解读文本,这三种视角(即本文、作者与读者)都可以统一在文本演化的过程中 。(注:Paul Cilliers的Complexity and postmodernism:Understanding complex s ystems(Routledge,1998)、Paul Cilliers虽然没有就文本进行复杂性的后现代主义分 析,但是讨论了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认为后现代社会和后现代思潮有许多复杂 性特征。另外,在Magoroh Maruyama主编的Context and Complexity:Cultivating con textual understanding(New York:Spring-Verlag,1992)中,虽然没有对文本的复杂 性分析,但是对经济、文化以及其他环境因素的文脉分析方法,对我们的文本复杂性分 析颇有影响。)
一、文本研究中的意义演化三论
任何文本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作者、读者和本文。从系统论角度来说,系统中诸要素 是要发生相互作用的,它们的功能也因在相互作用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表现出差异。事 实上,文本系统是十分复杂的,这从人们对文本认识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中就可以反映 出来。纵观历史,人们对文本系统的认识大体产生了如下几种关于文本意义的观点:
1.作者中心论。作者中心论强调“作者-文本”的互动模式,并认为文本只不过是作者 思想、意念的苍白铺陈和拙劣显现,文本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难以本真地传达作者所 思所想,从而将作者神圣化、神秘化,同时亦将系统中读者对作者、文本的互动贬低到 极限,否认读者在该系统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作者中心论观点,隐含了文本 不能彻底完全表达作者意义,从而在阅读中应该努力发掘作者意义的意义延伸观念。
2.文本中心论。作者中心论从未将作品视为独立的存在,在原意说的禁锢下,它径直 将作品等同于作者,将整个阅读过程视为是作者向读者的叙说,是一种单向的传输过程 。20世纪以来,以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语义学、符号学等为代表的西方文本主义 ,显然是看到了作者中心论的弊端和不足,因而突出强调文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为 对作者中心论的反动,文本中心论正确地凸现了文本的地位,使文本从作者的浓重阴影 中走出——文本不再是作者的代名词和附属物。文本中心论专注于寻找文本内部的本体 特征,在文本的语言、形式、技巧、结构、符号、语义等研究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它局囿于文本的自在性之中,斩断了文本与作者、读者以及其身后的社会、历史和 意识形态等的一切关联,将文本视为一个孤立的封闭系统,最终落入文本惟一论和形式 至上论的窠臼。
3.读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的崛起打破了文本自在性的封闭圈子,将读者的地位提升 到新的高度,重视“文本-读者”互动交流模式中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读者的阅读就是 不断地向文本提问,而文本则不断地以自身世界的丰富性来回答读者的问题,显现、展 开、改变、超越读者的问题视野;同时,文本作为等待解释的对象,又意味着向读者提 出一个问题,读者每一次阅读文本,都是理解文本提出的问题并对之作出回答。这样解 释就与问题有了一种本质上的联系,文本的意义在于读者与文本共同生成的意义。这就 将狄尔泰、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等人开创和完善的解释学理论引入到文本系统中,并 将对文本意义的寻求作为一项必然的任务来做,将文本意义复杂性的触角投入到文本复 杂性的呢喃话语之中。
显然,文本系统是个开放的、不断演化发展的系统,文本系统边界的确定,物质、信 息、能量的输入与输出,文本系统的形态特征等等都是应该讨论的问题。
二、“文本”语义分析(注:关于文本,目前学界尚缺乏规范界定。在研究 过程中,我们发现,王一川在《通向本文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给出 的界定与复杂性思想十分嵌合,遂略作取舍,引用于此。详尽研究尚在进行中。)
“文本”,英文原作“text”,又可译为“本文”、“篇章”或“话语”。首先,顾 名思义,文本就是指“本来”或“原本”意义上的仿佛未经任何人阐释的对象,它的意 义总是有待于阐释的,向读者开放的。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未定的,不能 被简单地等同于原作者创作时的意图,或某种权威阐释。无论是作者意图还是权威阐释 ,都不过是对文本的多种可能性的阐释之一,不能被用作为文本意义的惟一或最终裁判 。这样理解的文本,无疑地就成了读者、批评家越出前人或他人阐释框架的限制尽情地 从事新阐释的自由空间。与此相对应,作品(work)则是已被作者意图或权威阐释固定了 的文本,它无法满足人们在阅读活动中实现自由愿望的要求。
其次,文本是与抽象的概念以及思想性、情感性内容相对的具体可感的形式(form), 涉及人们常说的音调与言语、对话与独白、反讽、含混、形象、节奏、比例、表层结构 与深层结构等等,在这里,形式往往就是进行重新安置、变形或移位从而获得新的阐释 的场所。
第三,文本一词一旦被运用,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或隐或显的语言学含义;它指的是 具体可感的语言性或符号性物品,这种物品的阐释自然需要依赖语言学或符号学模型。 所以,文本又是可以用语言学模型去把握的东西。
第四,文本的意义总是被置于特定语境(context)中去阐释的。这种语境既可指文本内 部语句的上下关联性,也可指文本与外部种种复杂因素的关联性;而无论是内部还是外 部环境,就其性质而言,它既可能是语言学的,也可能是文化的以及更为根本的历史、 哲学的。就语境与人的关系而言,它可以指作者原来创作时带有的,也可以指读者阐释 时新带入的。总之,谈论文本总是要联系它的某种特定语境,这实际上意味着要作“文 本-语境”的关系分析。
最后,文本的上述含义表明它绝不满足于任何单一理论模式的规范,而是不断要求获 得新的多方面的具体阐释,这就使它不是成为单一理论模式的简单例证,而成为活的批 评对象。而且通过这种活动,文本还成为新的理论模式得以萌芽、生长的基础,而这正 是复杂性分析的内容和任务。
三、文本、阐释与解构
1.阐释学关于文本意义的理解、演化过程
“阐释学”(Hermeneutic)是关于怎样理解作品的一种理论,又译作“解论学”、“诠 释学”或“解释学”。阐释学源于基督教牧师诲经布道、注释《圣经》,以及专家学者 对古代各种典籍的注疏等活动。(注:Hermes(赫耳墨斯)是希腊神话中为神传递信的 信使。他聪明诡诈,未卜先知,难题迭出,常将神意传达给人类,并激起人们的困惑与 思索,因此阐释学又被称为“赫尔墨斯之学”。)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利希·施 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将语义学和《圣经》注疏的某些规则结合起来,建 立了阐释学。从此,古老的阐释学开始成为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学问。
从早期的阐释学到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关于文本理解的观点实际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有一个从文本作者意义到读者意义的流动、演变过程。
施莱尔马赫从具体文字的诠释技巧出发,首先探讨了如何将阐释过程各方面统一起来 等核心问题,并将“误解”放在研究的优先地位。误解之所以自然产生,是由于词义、 世界观等随着时光的流逝,在作者和阐释者之间起了变化。过去人们能理解的内涵,现 今已不能理解,其意义必须经过对它所由产生的历史情境或生活环境的严格准确的重建 才能发现。只有通过一套诠释技巧,利用科学方法,才能将隐浸的含义再现出来。
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深受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精神的影响,对 阐释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并将其上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认为借助前人不断 遗留下来的符号和痕迹,通过阐释,可以认识前人,认识当时生活,并最终认识历史。 他还将理解和诠释最能传诸后世的文字符号,视为最基本的阐释活动。与施莱尔马赫一 样,他将文本及其活动的意义等同于作者的主观意图。
狄尔泰的阐释观点,涉及到文本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他将文字的理解和解释作为最 基本的阐释活动,一部作品即是一个整体,要通过个别的词和词组来理解,可是对这些 词的充分理解,又需要有对整体的理解作前提。于是整体须通过局部来了解,局部须在 整体联系中才能了解。两者相互依存、互相依赖、不可分割。这就形成一个怪圈即所谓 的“阐释的循环”。根据这一原则,对一部作品的任何一种理解和解释,只要能自圆其 说、合乎逻辑、适于情理,都可成为一家之言。因此狄尔泰说:“从理论上来说,我们 在这里已遇到一切理解的极限,而阐释永远只能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到一定程度,因此一 切理解只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完美无缺。”[2]这样,虽然在狄尔泰这里,作者意义 还是文本的最基本意义,阅读文本就是要寻找作者原义;但“阐释的循环”已迫使其不 得不具有了读者意义的韵味。
促使传统阐释学向现代阐释学过渡的重要人物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 eidegger)。他从狄尔泰那里吸取了人是历史的存在物这一思想,而且还吸取了理解阐 释学的方法,狄尔泰力图从人本身来理解活生生的人,并与变化中的世界观相联系,他 认为,这种解释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把人理解为社会历史领域的一个环节,把人纳入历 史过程的生成关系和相互作用关系之中,通过对人的过去的可能性的设身处地的事后体 会,人就能够把自己从他当下的狭隘视野中解放出来,并学会在自己的历史性中理解自 己。海德格尔认为,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而是以头脑 里预先准备好的“前理解”为基础,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与理解。[3](PP181-186)
德国现代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针对传统阐释学企图消除一切主观成 见的倾向,矫枉过正地提出“成见是理解的前提”,充分肯定解释者或读者在阐释过程 中的积极作用。他所谓的“成见”即海德格尔的“前理解”,就是解释者的立场、观点 、趣味、思想方法等这些由历史存在所决定的主观成分。按伽达默尔的说法,“在理解 活动的一开始,就有一种对意义的预期引导着我们的理解努力”[4](P10),这种“成见 ”与“理解”意味着读者的参与,意味着作品的意义并非作者给定的所谓“原意”,而 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历史进程所决定的。理解文本并不主要意味着回溯 到过去的历史生活中去,而是要在当前参与到文本所说的情境中去,因此,不存在对一 件文本的规范性解释。相反,对于它总是可以有新的理解,权力就掌握在读者手中。这 样就完成了阐释学从作者意义到读者或阐释者意义观的彻底转变。伽达默尔的文本阐释 学隶属于文本的读者观中最彻底的一列。
2.文本与解构
解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中之一种,是从结构主义阵营中分裂出来的,它是在对结构主 义进行否定、反诘、驳难、叛逆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哲学、文化和文学批评理论,法国是 解构主义的策源地,其代表人物为法国“四子”: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e)、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克丽斯蒂娃(Julia Kyiste va),拉康等人也做了不少贡献。解构主义的文本观与阐释学的文本观有着明显的差异 ,表现为:
第一,阐释学认为文本是体验和理解的过程,作品打开了一个通道并清理出一个领域 ,事物在此相遇并彼此作用;解构主义则认为,文本是语言活动的领域,文本之外别无 他物,文本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指涉的体系。
第二,阐释学认为:文本在读者的理解中复活,作家、作品、读者是一个整体,作品 具有共同编织而成的特点;解构主义则坚持认为:文本与其它文本交织,文本间性或互 文性使其终极意义不复存在。
第三,阐释学认为:作者是作品之父,读者则是作品的再生之父;解构主义则认为: 文本与作者无涉,是多元的网状关系;
第四,阐释学认为:写作与阅读通过文本而联系起来,阅读即创造;解构主义则认为 :写作就是阅读,阅读就是误读。(注:有三种误读:作者对自己文本的误读;阐释 者的误读;后代对前辈文本的误读。参见张首映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第448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五,阐释学认为:文本说话并呈现意义,它使解读达到视界融合并超出原有视界; 解构主义则认为:文本就是一切,文本是语言游戏,文本会使人愉悦。
第六,阐释学坚持认为文本在言说,总在揭示某种现实存在,语言是存在之家;解构 主义则认为,文本无意将词与事物一一对等起来,语言无法掌握现实,语言是存在的牢 笼等等。
四、文本演化分析
从文本演化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文本”,其历时性形态均会有“前文本(pretext) ”、“文本(text)”和“后文本(post-text)”这样三个阶段。
前文本,我们界定它为文本正式形成之前,能够为他人感知的、部分符号化但尚未系 统化的雏形文本。形象地说,它就像建筑师正在建造的、尚未完成的、带着脚手架的建 筑物。前文本,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主体力图把握并表现客观世界所作的、能够被外部 世界感知的努力。这种努力效果好坏与否,是受诸多的因素制约的,比如主体的认识能 力、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媒介形态的完备性,非可控的、不确定因素的介入和影响等等 ,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前文本向文本的跨越。这也关涉到复杂性理论所探讨的两个 重要内容:本体复杂性和认识复杂性。这还涉及到现象学对该问题的理解和处理。
一旦前文本经过特定的编码并以波普尔所说的“第三世界”状态出现,“文本”也就 应运而生了。不过,这里的“文本”指的是未经任何人阐释但同时又是开放的、有待于 读者去阐释的“元文本”,元文本的载体(或媒介)有多种形态,如电子文本、印刷文本 、手写文本、雕刻文本、绘画文本等等。正因为文本得以寄存的载体是以实物形态出现 的,所以它的存放和延续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异或损坏,甚至消亡,从而加剧文本理 解的复杂性。譬如电子文本受到病毒感染,使得原本易于读解的文本变成一堆乱码,导 致随后的读解困难重重。再有印刷文本的物质形态受损,如遭遇水、火等可控或不可控 因素而发生的文本变异,同样加剧了文本理解的复杂性。正是基于这些因素的介入和影 响以及人们对文本阐释读解的需要,还有后人本身的历史文脉与原文本的差异,才产生 了“后文本”。“后文本”字面意思是在文本之后亦即“文本的文本”,文本的开放性 和不确定性,以及阐释者个体和环境的差异所造成的多元化理解,乃是造成“文本”向 “后文本”进一步演化的真实原因。这里涉及的话题应包括:解释的可能性、有效性和 局限性等;阐释者的认识指向,如出于功利目的的读解、力图恢复文本原义的本真指向 的读解等;还涉及“作者-文本-读者”多元互动的读解格局,进而引申出文本意义的复 杂性等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我们初步发现文本的含义在演化过程中首先形成的是作者的含义(常常与前文本对应) 、然后是文本自身的含义(常常与元文本对应),最后才形成了读者的关于文本含义的理 解(即后文本)。今天当文本的新形式——电子文本出现后,文本的意义交互性和演化性 更加凸显。文本自简单性中演化出的复杂性的广度、深度愈益扩展。
而且,文本的这三种含义并非是静态的、不变的,由此形成一种历史的意义演化,从 而使得文本意义越来越复杂化。当把文本意义视为演化过程而加以理解时,三种文本意 义的观点似乎可以得到部分的融合。这里要指出的是,误读并非没有意义,它可以演化 原有意义,解析原有意义,但是不能由此否认原有意义的存在。
五、余论
在上述论证中,似乎我们还没有清晰、明确地给出我们关于文本意义的倾向性意见。 这并不是我们故意要含糊其辞,而是因为我们在此试图以一种复杂性演化的观点,把这 三种意义观点安置在一个流变过程中。换句话说,三种意义在文本演化过程中是依次逐 渐生成的。(注:需要说明的是,三种意义依次而生,并不是一个出现后,然后才出 现另一个。它们的生存可能存在交叉,即应该是一种非线性的生成关系,而不是线性关 系。)当把这三种意义按照演化过程排序安置在文本意义过程中时,我们还能够说它们 必然是矛盾的,必然是有你无我的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和文论研究者的巨大功 绩在于他们分别将一种意义观推至极端,使其意义挥洒得淋漓尽致。而复杂性科学的诞 生给了我们一种视角和一种机遇,它让我们运用复杂性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论, 去考察文本,进而从新的视阈对以上观点和文本进行解读。
当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这三种意义既然都是文本的意义,那么三种意义总不 能是一种平行并列的关系吧,哪种意义更基本、更重要呢?这当然也涉及到作者的学术 立场。我们认为,简单地回答上述问题有违复杂性科学本意,事实上,这个问题本身也 是复杂的。
我们初步认为,作者意义是首先生成的;元文本一旦形成,文本自身意义便内含其中 ;读者意义当然在演化过程中最后生成。
至于哪种意义更重要,则涉及文本意义的客观性问题以及在某种环境或条件下它表达 意义的重要程度等方面。
就文本意义的客观性而言,只有文本本身的意义似乎最为客观,但是文本自身的意义 是需要阐述者加以解读的,谁给出的文本自身意义是它真正的客观意义呢,这本身就是 一个问题。是作者吗?作者给出的是文本的作者意义,很显然,在文本分析的语境内, 我们根本无法了解文本的真正的客观意义,它的客观意义只能近似地达到,而且是需要 在对历史和文本整体的文脉、结构等进行全面的分析后才能近似地达到。当然,对不同 类型的文本还要具体分析,例如对科学文本而言,似乎相对好办一些,因为科学文本有 一个经验事实与其相对应,文本的意义客观性似乎更容易确定,因此科学文本相对其他 文本有其独特的地方。那种认为科学文本是科学家制造出来的观点,似乎只说对了一个 方面,科学文本的客观性还是可以保证的。
利用现象学的方法,即所谓把文本以外的一切都置于括号内不顾,仅仅对文本进行还 原分析,并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这样理解的文本很可能是对文本意义的缺失理解和读 者理解。但是,文本的现象学分析,的确减少了文本之外的缠绕。
至于文本的哪种表达意义更重要,则更需要在某种语境或文脉中才能加以判断。其实 ,抽象地讨论哪种意义更重要是无意义的。另外,我们更倾向认为,三种意义分析结合 起来才能给出对文本的全部意义的认识。
我们也反对故意把文本理解或解读复杂化的倾向,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伪复杂性的文本 意义观,它不利于文本的解读。
最后,文本的解读,看来只能在文本的语境中来实现,不能绕出解释循环的怪圈。文 本与实际经验世界的分离,使得我们认识世界更为困难。后人解读前辈的历史和社会, 如只会依据当时的文本是远远不够的。人文社会的运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这也许就是 文本与文本所描述的经验世界的复杂关系吧。
收稿日期:2001-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