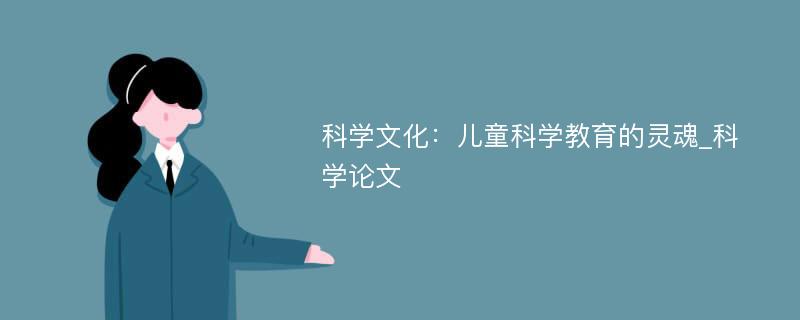
科学文化:儿童科学教育的灵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文化论文,灵魂论文,儿童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什么点灯啊?”“因为天黑了。”“为什么天黑啊?”“因为太阳落山了。”“为什么太阳落山了?”……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小孩子与大人之间的对话。这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反映了小孩子那种天生的好奇心理,而且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小孩子几乎对所有的事物都很好奇,最喜欢向父母问“为什么”,有时甚至会问得大人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提出的“为什么”却在渐渐减少。我们常见的情境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叽叽喳喳地向老师问个不停,小学生也会不时举手向老师发问,而到了初中、高中,发问的学生就越来越少,以致于大学的课堂上不但无人发问,而且即使老师发问,也无人回答。随着年龄的增加、知识的增多,本来可以让孩子们自由探索和发问的领域会越来越广,为什么孩子们年龄越大反倒问题越少呢?面对这一司空见惯,然而却是不合情理的现象,或许我们的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需要好好反省自己了。
一、当前儿童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个对花、鸟、鱼、虫、山川、河流、房屋处处感到新奇,缠着大人问个不停的小孩子,为什么长大之后对周围的这一切不再有任何的探索热情了呢?看一下我们典型的科学课堂或许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情景一:老师严肃地在黑板上讲解着一元二次方程,要求学生一定要按照步骤,整齐、规范地解答,绝不可跳过某一步,否则要扣分。学生只好一个个认真地在本子上按老师的示范一丝不苟地写着;情景二:老师费力而工整地在黑板上画着一个个的实验装置图,同时讲解题目中每一问的标准答案,要求学生一定要用语规范、表述完整;情景三:面对试卷上一个又一个的化学方程式、元素符号、一连串的制取、收集装置,大多数学生都是眉头紧锁、面色凝重,手中的笔也因手心不断出汗而握不紧了……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科学课堂洗礼下,不断长大,一步步踏进更高学府的。他们记住了一个又一个的概念、公式,学会了解一道又一道繁难的题目;他们能按题目的要求,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最正确的反应。这与赫胥黎1868年批判英国古老大学时描绘的情形没有什么差别。他说:在这些古老大学里,“学生们被训练去获得各种考试的第一名,就像一些马被训练去赢得一个奖杯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孩子所接受的科学教育,从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到评价都非常狭窄。如科学教育的目标似乎就是为了在大大小小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科学教育的内容就是教科书上的知识点和习题;教学方法就是教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以及无休止的习题训练;评价方式就是纸笔测验,家长与教师只关心学生的名次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原本丰富多彩的科学教育就这样被一步步地狭窄化了。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早就指出:“像填鸭般地用那些诸如形而下之‘器’的东西,塞满学生的头脑,而对本真存在之‘道’却一再失落而不顾,这无疑阻挡了学生通向自由精神之通衢”。可见,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科学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形而下的科学教育而已。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进行剖析,笔者以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科学教育缺失了科学文化这一科学教育的核心与精髓,由此实施的科学教育必然只是舍本逐末的科学教育而已。
二、对科学文化的考察
自有人类以来,文化就开始成为人类生活和存在的一种重要样态。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产生了很多对人类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形态,如宗教和艺术。在各种文化形态中,科学文化出现最晚,但自产生之日起,它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其他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断言:“科学是人类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那么,什么是“科学文化”呢?
“科学文化”一词系舶来品,其对应的英文为“culture of science”(科学之文化),或“scientific culture”(科学的文化)。前者似乎指称科学自身内在的、固有的文化属性。后者除了可作和前者相同的理解外,似乎还包括具有某些科学成分或特征的少数非科学文化。在日常用语中,我们一般对这两者不加区分,而统称为“科学文化”。具体来说,所谓“科学文化是科学人(man of science)在科学活动中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态度,或者是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遵循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态度。科学文化以科学为载体,蕴涵着科学的禀赋和禀性,体现了科学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精神气质,是科学的文化标格和标志。”和人类的其他文化形态类似,科学文化也可分为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次。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由于科学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科学文化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如20世纪中期英国学者C.P.斯诺(C.P.Snow)的《两种文化》一书就对科学文化作了详尽的论述。其实远在古希腊时期,这种文化因子就蕴藏于西方文化之中了。
人们公认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而希腊文化起源于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这种自然哲学可以说就是当时的科学。故此,也可以说希腊文化起源于科学。“作为西方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科学内在于西方文化,同时又作为这种文化的根本精神而影响文化其余形态的发生和发展,而这一切是以古希腊的哲学或者说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科学方面为中介的。”古希腊人热衷于探究自然,以寻找各种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而且他们这样做根本不是为了任何功利的目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在他看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为了能够对各种自然现象给予理论的解释和说明,他们找到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通过理性思维,即合乎逻辑的推理来进行论证。在理性思维的引导下,柏拉图首开西方主客二分的先河,把客观的本体世界和主观的主体世界对立起来,从而为科学认识确立了对象。同时,亚里士多德还为理性思维确立了必须遵循的规则——形式逻辑。正是在此基础上,西方人注重对概念进行严格的定义,因为这是逻辑推理的前提,于是也就有了今天众多的诸如质量、密度、速度、单质、细胞、素数、质数等被严格定义的概念。也正是在逻辑的指引下,西方科学为光电效应、苹果落地、黑体辐射的紫外灾难等现象找到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并产生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的、影响至深的科学发现。此外,“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怀疑、批判、不崇尚权威的古典民主精神,以及文艺复兴以来平等、自由的思想均为西方科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可以说,正是在这种科学文化思想的催生下,才有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大发展以及科学教育的繁荣。西方科学文化也孕育了西方科学教育的传统,如算术、几何、天文这古老的“三艺”,在西方的教育体系中就一直绵延存在了几千年。
三、我国儿童科学教育应高度重视科学文化的宣传与渗透
反观我国的科学发展与科学教育就会发现我们还十分缺乏这种科学文化的熏陶与支持。首先,我国的传统文化本就缺乏科学文化的基因,并且从根本上来说是与科学文化相对立的。“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一基本观念过分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统一,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分立和斗争,忽视了对各种自然规律的主动探寻,也就未能激发起人们研究宇宙与自然的兴趣。传统伦理取向的文化更是使人们求善甚于求真。即便是求真,其最终目的也被规定为“止于至善”,而不是为了达到“真”本身。道德判断优先,这与科学的求真精神是不统一的。长期的小农经济、家族意识浓厚、家长制下的权威崇拜心理也使中国传统社会更重人伦秩序,讲究长幼尊卑的名分,这也与科学发展所需的自由、平等、批判精神格格不入。可见,我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科学文化基因的,也就很难生长出真正意义上的重大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
其次,我国在引进西方科学教育时未能高度重视其科学文化之维。进入近现代以来,我国开始引进西方的科学和科学教育。由于当时我国正处在一种内外交困的特殊形势下,国人更为看重西方近代科学在发展了几百年之后所产生的附属产品——发达的物质文明也就不足为怪。也就是说,国人当时更看重西方科学文化中“形而下”的部分,如具体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手段、科学组织、物化的科学成果等,而对属于科学文化“形而上”部分的科学思想、科学信念、科学精神、科学审美、科学伦理等价值观念则置若罔闻。由此,我们仅仅学到了西方科学文化中“形而下”的部分,而且受当时国情与条件的制约,即便是对西方科学文化中“形而下”部分的学习和引进也是不全面的。加之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占据了主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失科学文化的底蕴,我国的科学教育一直以来只是把科学视为“有用”的知识、方法和技术手段,学生只需掌握这些工具就可以了。
再次,受一种流行看法的影响,我国科学教育一直未能充分重视科学文化的建设。这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求真,涉及的是事实判断;人文求善,涉及的是价值判断。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由此被人为地划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尤其是在斯诺明确提出“两种文化”这一论断之后。但其实在人类早期的文化中,并无所谓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对立。只有在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发展充分,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后,人们才把这一部分文化形态称之为科学文化,余下的称之为人文文化。由此可知,科学文化本就与人文文化同出一源,“科学在本质上是人文的”。美国科学史专家萨顿对此进行了诠释:“自然的研究必然是由人研究的。尽管这种研究是客观的,并且科学家们试图使它尽可能的客观,但是它仍然是以人类的经验和观察来解释一切的。个人的癖好能够并且必须被消除,但是人类的天性却不可能被消除。科学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无论我们是研究人的历史还是研究自然的历史,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人”。为了人和属于人,始终是科学最本质、最深层的价值诉求与归属。
受事实、价值二分思维模式的影响,当前我们往往过于强调科学与科学教育求真的方面了,而认为求善、求美是人文教育的事情,以至于有“科学教育教人做事、人文教育教人做人”的说法。当下备受热议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就是要求科学的求真与人文的求善互补。这看似在弥补科学教育的不足,实际上是把我国科学教育中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固化了。这种截然的二分法必然只会使儿童在科学学习中只见到冷冰冰的、板着同一副面孔的概念、原理、定律、公式,而感受不到任何温度、激情与美,即使学得再好的学生也很难从内心的情感深处去贴近科学、喜爱科学。为改变这种现状,笔者以为我们的科学教育不仅仅要求真,更要认识到仅仅求真的科学教育远远不是完整的科学教育。缺少了“扬善”和“达美”追求的科学教育必然是残缺的、水平不高的,也是难以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的。
科学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维度,即文化精神的维度与世俗实用的维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理性传统与功利传统。余英时教授曾尖锐地指出:“中国‘五四’以来所向往的西方科学,如果细加分析即可见其中‘科学’的成分少而‘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变本加厉。”我国由于片面发展了科学的功利之维,致使科学教育也自始至终以功利为导向,而忽视了其中暗含的文化因子。科学文化所具有的求实、尚真、不迷信权威的精神正适宜于构建崇尚理性与和谐的社会。尽管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与求索,从精神气质来看,我们的民族还普遍缺乏理性的精神。这可能是因为科学在中国没有经历像西方那样同宗教反复斗争,使人们不断经受精神洗礼的过程。不仅如此,我国的科学发展受多次政治运动的影响,至今还未能完全打破政治权威的束缚。针对这一历史现实,笔者以为我们当前的科学教育更应重视让儿童理解科学,使科学文化在我国扎根,进而转化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气质。
自20世纪中叶以后,强调科学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世界科学教育的主要趋势,科学教育已经从斯宾塞、赫胥黎时代功利主义的学科知识型科学教育进入到了注重学生理解与探究的科学教育新阶段,我们的科学教育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就应紧跟这一世界趋势,为提高我国国民的科学素质奠定扎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