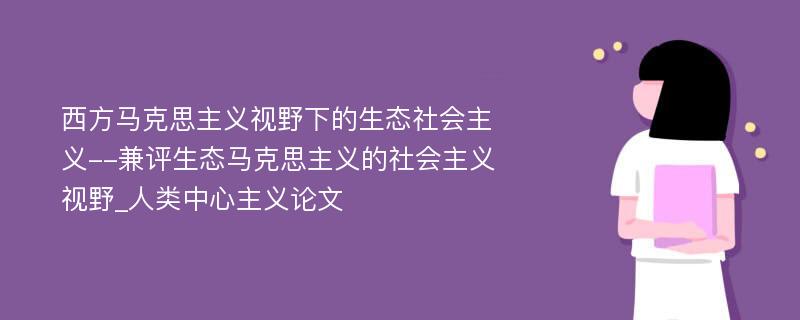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生态社会主义——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愿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生态学论文,愿景论文,视野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10)02-0196-06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生态学思想结合起来,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描绘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愿景,成为最具“红色”标志的“绿色”思想。它提出“社会主义应该是绿色的”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愿景,对于我们全面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生态社会主义论人与自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将形成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统治”自然。这里的“统治”含有“计划”和“管理”的意思。它不是指像主人对奴隶那样的绝对支配,而是指在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的合理控制。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而应该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尺度。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
格仑德曼批评生态中心主义者采取拟人化的立场定义生态问题,并要求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当适应自然和自然法则。他指出,只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能够提供估价生态问题的参照点。无论以人类为中心的参照点是以当代生存的个人、社会、人类,还是未来世代来定义,它都稳定地确立了一个判断当前生态现象的清晰尺度。
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并不是以生态为中心,不能像一些生态中心主义者那样,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人对生态环境的支配,从而认定只要放弃人对生态环境的支配,实施生态中心主义,就能解决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实施人类中心主义。当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不是现行资本主义中流行的技术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目前一些人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技术中心主义,即表面上把人而实际上是把技术放在中心位置。佩珀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是同义。他明确写道:“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不过不是资本主义技术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它反对生物道德论和自然神秘论以及由它们所导致的任何各种可能的反人道主义体制。它强调人类精神的满足有赖于与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质性的交往。人并不是一种污染源,他既不是生来就是傲慢、贪婪、好斗、富有侵略性,也不是生来就具有其他的种种野蛮性。如果人沾染上这些的话,那也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遗传因素或原罪所致,而是流行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虽然不能把人与其他的动物同日而语,但人也是自然存在物。我们所设想的自然是社会地被设想的和社会地形成的。而人所做的也是自然的。”[1](第232-233页)
在佩珀看来,生态社会主义所实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所实行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在不超越自然的限制和规律的前提下,通过集体控制的方式,有意识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集体的利益。而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通过技术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自然,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资本家的个人利益。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将形成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模式。在这种新的模式中,人居于中心地位,自然是人的可爱的家园,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新的和谐关系,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
我们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它既是对以往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又是对当代人类科学知识及人类实践活动深刻反思的结果。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其核心思想就是:主张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应将人类的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尺度。它与近代形而上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要求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模式;后者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盲目追求人对自然的控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的态度时,不要放弃“人类尺度”,而应该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尺度。这既突出了人类利益的整体性、长期性,又承认人与自然的休戚相关性,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途径。它对绿色运动中流行的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使它与后现代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成为最具“红色”标志的“绿色”思想,并为生态环境保护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它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阐释,挖掘和探索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被遮蔽和忽视的生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由于历史原因而附加于马克思主义之上的一些误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摆脱陈旧的教条化的倾向。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观
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上,除少数人主张实行某种形式的公有制外,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重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问题,而比较重视对生产资料的管理问题,主张建立一种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混合型”的社会主义经济;注重产品的分配以及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问题。
从具体的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的特点。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大多反对大规模、集中化的经济体制,崇尚“舒马赫主义”,主张实行小规模、分散化的经济体制,要求建立零增长的“稳态经济”。
莱斯指出:“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在各国内部使物质目标和生活环境方面的模式荒谬地趋于一致,是工业化经济一般化的市场交换的主要趋势之一。”[2](第107-108页)他批评工业化经济一般化的市场交换所带来的全球化使生产结构集中并使大城市以外的与生产组织中心没有直接联系的那些社会的经济基础受到损害。现存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包括我们对能源密集、大规模的工业技术的依赖)的方式阻碍了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责任感的发展。
莱斯认为,为了减少人们对这种结构的依赖,就必须改变社会政策和资本投资的方向。应尽量用能源消耗少、物质资源需要较低的方法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此,他提出了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the conserver society)的目标。莱斯所谓的“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就是把人均使用能源降到最低限度,减少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重要性,使技术的发明服从于环境保护的社会。
阿格尔赞同舒马赫主义关于“小的是美好的”的主张,把小规模技术的概念与从质上对主要社会制度进行的变革联系起来。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3](第501页)指出:“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可以理解为集中化与分散化这两极之间的连续统一体。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力都集中在克里姆林宫),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则是高度分散化的(投资之类的决定权都掌握在每一个工业企业的工人委员会手中)。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分散化的程度与非官僚化的程度成正比。换句话说,社会生活全面非官僚化的可能性在一个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工人管理)的制度中要比在一个集中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控制)的制度中大得多。”“社会主义所有制必须被看作是由工人进行管理的(以及工业技术分散化、最终非官僚化的)所有制。”[3](第513页)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反对“稳态经济”和“舒马赫主义”,主张经济的适度增长。他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南北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由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已经形成一个整体,小规模的、分散化的经济是不现实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解决广大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更不可能实行零增长或不发展的经济方案。他们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该随着人们需求的增长而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必须是理性的、适度的,以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利润为目的。高兹提出“生态重建”的口号,要求实现生态现代化,即经济的增长应符合生态原则的要求;并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而不是工业社会的生态重建,才能解决生态危机。
高兹和格仑德曼提出建立一种“不自主领域和自主领域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们主张在未来社会应保留市场的调节功能和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政府的经济职能应当是行政管理、计划、协调,也就是说,利用计划与管理等方式,按照人的理性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满足人类真正的物质需要。他们提倡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折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作用的生态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既强调国家计划及其调节,又不排斥个人在生产生活领域的自主和市场等现代经济运作手段。格仑德曼明确指出:“市场与计划就其本身而论并不是不兼容的;混合经济或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是适宜的社会(经济)形式。”[4](第270页)
佩珀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像缺乏增长一样是其制度所特有和规定的。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期,为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工业会更明显地抵抗和破坏环境保护的规定。同时,这也会削弱工人反对经济剥削和生态剥削的力量。并且,在经济衰退时期,人们对其他问题的厌恶将超过对经济必需品的厌恶。贫困仍然是自由最大的敌人。摆脱贫困的自由对我们追求其他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摆脱恐惧的自由——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应当承认正确评价经济决定论的社会意义。而且,生态社会主义的增长必须是理性的,是为了每一个人平等的利益的有计划的发展,因此也是有利于生态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批判集中化、官僚化和技术统治论出发,进而批判现代化大生产导致了劳动的破碎化和异化,其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它由此而完全否定现代化大生产和大型跨国公司的作用,企图建立一种小国寡民式的经济单位,用小规模技术和分散的小生产取代现代化大生产,把现代化大工业分化为前工业化时期的自给自足的小手工业;这既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具有浓厚的“向后看”的浪漫主义色彩,是一种历史的倒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批评过这种“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5](第297-298页)。
实践证明,小规模技术和分散化生产并不一定是生态化的,而许多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生物技术、再循环和生态式的能量供应技术都离不开大规模技术和现代化生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生产和技术的规模大小,而在于生产和运用科技的社会机制。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放弃早期的“稳态经济”的主张,转而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该适度增长,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反对为了发展经济而破坏生态环境的做法。这使得其理论既超越了传统的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又超越了一般环境保护主义的理论视野和绿党的“非工业”乌托邦,在一定的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我们正确认识现代性以及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它把人与自然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相互协调作为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提出未来社会主义应该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发展,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借鉴。
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重视所有制,只强调生产资料的管理,这使得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终并未真正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并没有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找到真正有效的“处方”。它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改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也就不可能使工人真正获得当家做主的权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同起来进行批判,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都不利于生态保护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都应该废除。它企图建立一种超越私有制和公有制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所有制之上的第三种所有制,并认为所有制不是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这些主张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决定社会性质的基本原理,而且混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具有回避社会现实的反历史的倾向。
三、生态社会主义的民主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是官僚主义民主,只具有一种程序性或形式上的意义,传统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它主张生态社会主义应该在经济、政治和生态相互统一的基础上实行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受绿色运动的影响较深,大都接受了绿党所提出的“基层民主”的原则,强调政治过程的分散化、非官僚化,要求实行一种以工人自治(即工人对生产和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管理)为特征的基层民主。阿格尔批评传统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极权的社会主义,认为只有激发起工人阶级关于非官僚和分散化的社会意识,建立一种以美国民粹主义为基础的新的解放意识形态,才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他说:“如果人们能把社会主义看作不是更大程度地实行高压统治的政体,而看作是一种可能由工人和消费者直接进行管理的制度,那么这种民粹主义就可以转向激进方面了。我们关于新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正是建立在这样期望基础之上的,用这种意识形态把具有异化性质的现代失落感引发为一种协调一致的政治努力,从而将大规模的工业资本主义改造成小规模的非极权的社会主义。”[3](第513页)显然,阿格尔的意思是:未来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由工人和消费者直接进行管理的非极权的社会主义。高兹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一书中,提出“一种可能的二元社会(dual society)的乌托邦”设想。在这个乌托邦社会中,保持了中央和地方、自主和他主的二重性。整个社会是自主领域和非自主(即他主)领域的统一体。一方面,个人和社会的自主性增强了,避免了国家独裁的形成。另一方面,国家将尽量使政府非中心化,例如,通过使生产单位非中心化和缩小生产单位的规模来降低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对全社会的操纵职能。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基层民主”的原则是不现实的,也是无助于生态问题的解决的。奥康纳明确指出:“大多数的生态问题以及那些既是生态问题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在地方性的层面上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区域性的、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计划也是必需的。”[6](第433页)他批评地方主义不但无法有效地解决生态问题,而且还会带来这样一种威胁,即人们会仅仅从地点的角度来为其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拒绝作辩护,——而没有同时考虑到工人及妇女的主体性、农民文化、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等因素。而且,由于各地的天然资源有着很大的差异,为了解决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以及这些国家与北部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必须有某些中央权威来把财富和收入从富裕地区重新分配到穷困地区。因此,“地方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而中心论则已经自我毁灭了。废除国家是行不通的;依靠那种‘民主’在其中仅仅具有一种程序性的或形式的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同样行不通。在我看来,唯一可能行得通的政治形式,——即也许可以很好地协调生态问题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的政治形式,应是这样一种民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社会劳动的管理是民主化地组织起来的。”[6](第439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是官僚主义民主,只具有一种程序性或形式上的意义,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欺骗性,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它批判传统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却有失片面。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由于长期实行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一度形成了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消灭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工人阶级当家做主,获得了政治上的自主权。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一直致力于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因此,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不是极权国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反对权力的过分集中出发,进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提倡实行基层民主和自治,其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它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把主要权力都交给基层组织,实现全面分散化的社会活动(组织原则),试图用“生物区”取代国家,这在当今社会中是不切实际和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对于人民来说,它是一种管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是有系统地实施统治。生态社会主义所强调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论。
四、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在社会文化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基础,以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为核心,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新的社会文化和生活范式。
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中批判了现代工业社会把满足等同于无止境的物质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范式。他指出,现代工业社会导致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们集中居住在城市的高楼中,其能源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甚至废物的处理都依赖于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人们错误地以为不断增长的消费可以弥补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于是,便盲目地追求消费以发泄劳动中的不满,最终把消费与满足、幸福等同起来,用消费的数量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尺度。莱斯认为进步的社会变革的前景取决于在消费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也可以确立人的满足和幸福感,要求改变把消费与满足等同起来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范式。他指出,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方案重新建立的生活方式不是要求人们重新回到过去那种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环境中去,不是强迫所有的人都采取一种特殊的单一的生活方式,而是提供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让人们有比现在更富有吸引力的其他种种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个人就可能愿意在不同程度上依靠日常需要的生产活动来获得满足,而不是从一般化的市场中的消费来获得满足。他强调,只有减低人的需求、改变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使人们通过直接性的生产活动获得自我实现,才能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活动和自由时间的活动都具有丰富的意义,并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幸福。
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导致了生态危机,社会变革的动力就植根于人的需求与商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而这种过程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确定的。他强调需要提出一种新的能重新评价人的需求的新的危机理论,认为需求理论是后正统社会主义学说不可缺少的。阿格尔反对自由和必然的二元论,反对把人的存在分为劳动和闲暇两个组成部分(劳动是指“必要劳动”,而闲暇则是指“自由”)的做法,主张劳动和闲暇可等同的观点。他认为,克服异化消费的关键是改造生产使其不再异化,对需求方式的重新思考可以使异化消费变成“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再参加劳动,将不再把这种劳动看作是获得应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人们可以在社会有用的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本身的基本愿望和价值(而且,这无疑将改变社会公用事业的意义,包括改变像艺术这样的某些非物质性事业的意义)。他明确提出:“非异化的社会不仅是实现经济无增长的社会,而且还必须使人们能通过生产性活动来自我表达。”[3](第499页)“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3](第475页)
高兹认为,要在消费领域真正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实现“更少”与“更好”的结合,就必须摆脱经济理性的束缚,实施生态理性。未来社会将是一个与现存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为经济目的所进行的劳动的进步性的减少将使自主的行为在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成为可能;‘自由时间将压倒非自由时间,闲暇将压倒劳动’;而‘闲暇将不再只是剩余或补偿,而是必不可少的生活时间和生活的原因,劳动将降低到仅仅是一种手段的地位”[7](第139-169页)。他说:“这里涉及的是从一个生产主义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向一个时间解放了的社会的转变,在时间解放的社会中,文化和生活被赋予比经济更大的重要性:简而言之,这是向一个德国人称之为‘文化社会’的社会的转变。”[7](第183页)
高兹指出,只有让这种自由时间成为一切普遍价值的承担者,即让创造性、欢乐、美感和游戏战胜劳动中各种效率、谋利的价值,才能出现“一个可能的其他社会的远景”。
在高兹看来,只有实行“更少地劳动”、“更好地消费”的原则,才能使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增加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才能改变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从而实现马克思所期望的理想社会的生活方式。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批判,对消费活动与生态危机之间的联系的揭示,无疑有不少可取之处。它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生态危机的成因,对于我们积极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具有重要启示。正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范式所带来的过度消费,很大程度地破坏了我们的生态环境,加重了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并严重地腐蚀和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风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要求人们通过参加直接性的生产活动来追求满足和自我实现。这种劳动闲暇一元论的主张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的思想,有助于我们从受支配的、异化的消费中解放出来,树立新的需要和幸福观,从而最终实现创造性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它倡导一种“更少地劳动、更好地生活”的新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根据他们的想象而不是需要来进行生产,使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利润率服从社会—生态标准。在全球性生态性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生态社会主义所倡导的这种生活方式对于我们反思传统的生活方式,树立新的符合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克服异化消费、实施生态理性作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把社会变革的动力植根于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变革,这却有失偏颇。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是和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仅仅依靠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变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谓的需求革命和消费革命,本质上是一种主观革命。它试图通过观念的变革实现社会变革,这使得它的生态社会主义愿景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
标签:人类中心主义论文; 生态危机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生态学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生活管理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所有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