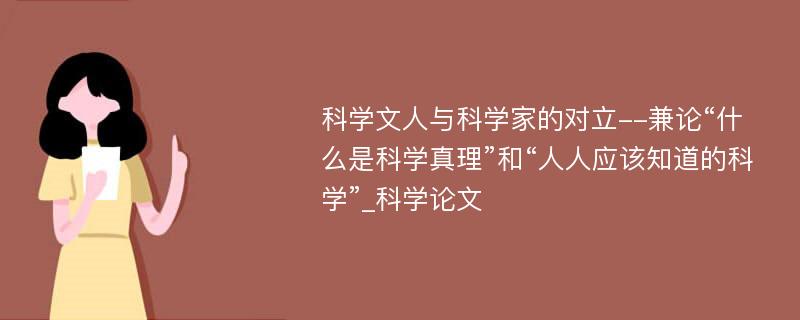
科学文人和科学家的对垒——也谈《何为科学真理》和《人人应知的科学》这两本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文人论文,何为论文,科学家论文,真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哲学显得不能为无偏见的人所了解,或不能与现代科学并行不悖,这过错必定在哲学家方面。
——赖辛巴赫(H.Reichenbach):《科学哲学的兴起》
写下这句话的赖辛巴赫的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在爱因斯坦的《对批判的回答》这篇著名的文章里,他把赖辛巴赫和主张采用什么样的几何学仅仅是一种约定的庞加莱两人作为假想的一对论敌,写下了一串精彩的对话。爱因斯坦明白地表示不同意庞加莱的约定主义观点,而赞成赖辛巴赫和亥姆霍兹应当由物理学来检验几何学的适用性的观点。
应该说,科学理论里的确含有约定的成分,但科学理论不仅仅是一些约定。例如,初学者往往会以为,电学里的欧姆定律无非是把电压U与电流I的比例定义为电阻R的一种约定。我们说,是的,欧姆定律里确实包含了R=U/I的约定。但这一物理学定义是建筑在对一段异体两端的电压U同通过这段导体的电流I呈线性关系这一实验结果之上的。有了这个实验结果,才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把保持恒定的比例常数R定义为这段导体的电阻。欧姆定律的实质内容,正体现了这一并非来自约定,而是反映了某种物质性质的实验规律。进一步还可以思考:为什么要约定电阻R=U/I而不约定R=(U/I)[2]呢?为什么对那些不满足这种线性规律的荧光管、晶体管之类的器件,就不可以定义其电阻呢?可见这里确实包含了不是能够由人们的主观意愿或者社会影响来决定的东西。难怪,由一位注重形式的数学家庞加莱倡导的约定主义,并没有得到多少注重实质的物理学家的积极响应。
爱因斯坦和赖辛巴赫的时代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在那个年代里仍然显得势单力薄的科学哲学,如今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庞杂的行业了。新进的研究者把赖辛巴赫那样的“传统科学哲学家”撇到一边,推出了一批又一批新名词,新主义和新的学科分支,令得人们应接不暇了。
去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表示,希望我能为R.G.牛顿的《何为科学真理》中译本写一篇书评。在我还没有动笔的时候,先后读到了在《中华读书报》上登载的刘华杰的文章《反击科学相对主义》(2001年7月11日)和柯志阳的文章《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交锋》(同年10月17日,以下简称“柯文”)。柯文里还把柯林斯和平奇的《人人应知的科学》同牛顿的《何谓科学真理》这两本书,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角度作了褒贬分明的对比。
顾名思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是把科学当做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的学科。从这个角度看,如像“社会建构论”那样的观点,应当会提供一些积极的启示。但是,那些社会建构“原教旨主义者”(这里借用了柯林斯书上的术语),却把科学看做是与自然界无关的一种完全由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了。实际上,对于社会建构论者,同样可以提出与上面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建构出来的是R=U/I的欧姆定律,而不是R=(U/I)[2]的定律呢?
牛顿的《何为科学真理》一书里,对约定主义和社会建构论,都分成“强形式”和“弱形式”两种。他既在一定的程度上肯定了那些“弱形式”的积极意义,又不赞成那些走向极端的“强形式”的主张。在我看来,这实在是颇具说服力的分析。
牛顿的书一共有11章,全书讲的是科学哲学的方方面面,只是在第2章里专门谈到社会建构论。所以,这本书不是像柯文的编者在按语里说的一本“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作,至多只是涉及到这方面内容的一本著作。因此,我们不必按照那篇“编者按”所设定的框框来展开讨论。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那么,把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各个学科,自然就不属于自然科学。这个学科群里应当包括有科学哲学、科学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社会建构论只是其中一个分支里的一个影响有限的派别。因此,我们在这篇评论里,先从大处着眼,不准备深入地评价社会建构论。
怎么称呼这个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呢?本来,“科学学”就是一个很好的现成名称,可惜它已经用来指一个特定的学科分支。国外有称作science studies的,译成“科学研究”亦同这一名称的常用意义相混淆了。还有,“科学的历史和哲学”(history and philosophyof science)的叫法早已存在,在缩写符号满天飞的今天,也可以称它为HPS,不过所包含的范围要稍窄一点。我建议把这个学科群称为“科学人文学”,其从业者的群体称为“科学文人”。汉语里“文人”的传统意思已经包括了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所以“科学文人”就连科幻作家也能够包括进去了。
照这种说法,牛顿是一位科学家,而柯林斯则是一位科学文人。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他们这两本书的分歧以及在国内外的有关争论,反映了以科学家为一方,以科学文人为另一方观点上的对垒。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可能是有一定普遍意义的。
本来,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等“科学人文学”的领域内,我们固然要重视在这些学科里从业的专家们的意见,亦要欢迎各个学科的科学家们的关心和参与,两方面携起手来,互相取长补短,才有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可惜,我们常常见到的是,许多科学家轻视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不屑于参加有关的讨论;而不少科学文人则认为,只有他们才具有足够的“专业”水平,科学家根本没有资格在这些方面发表意见。
举一个例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去年出版了由我翻译的一本维格纳的自传《乱世学人》。书的原名直译过来是“尤金·维格纳的回忆——根据他对安德鲁·桑顿的口述”。桑顿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这本书是由他根据维格纳的口述记录整理而成的。我发现这本在国外颇受好评的书里有不少外行话。我不晓得这些是桑顿的误解还是维格纳的口误。维格纳开始接受桑顿访问时已经有86岁,年纪这么大,一些事情记不清楚也是难免的。然而,无论如何,这里的主要责任应当由桑顿来负,因为他应当做核实校对的工作。
我在这里只举出原书里的两处严重错误。其一是说“群论是一门……物理学。”(译本105页)其二是说到爱因斯坦的一部著作《Modifications in Relativity Theory》。(译本74页)如果说由于未受过高等理科教育的桑顿缺乏数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发生了把一门数学误认为一门物理学这样的错误,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把子虚乌有的一本书说成是爱因斯坦的著作,就确实太离谱了。因为,爱因斯坦的论著目录是很容易查到的。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桑顿,他处理史料的基本功到哪里去了?
由此可见,当我们阅读哲学家、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谈论科学的著作时,不得不倍加小心。
哲学不是动物学。要研究动物学,当然必须以现今公认的动物分类为基础。但是,不承认哲学家们定下的种种框框,仍旧能够研究哲学。正如我们不钻进SSK的圈套,依然可以谈论牛顿和柯林斯的两本书以及柯志阳的文章一样。
柯林斯书里的主要内容是对7个科学事件的个案分析,一共占了这本书1993年初版不大篇幅的90%。柯林斯的这些“微观案例研究”被柯文誉为“专业研究成果”的“鲜活的历史”,以同牛顿书里“科学史案例的匮乏”相对比。按照柯文的意见,不仅是牛顿,而且“一般说来”,“科学家在科学史方面,……除了对一些技术性问题比较熟悉以外”,是没有什么“强项”可言的。
就拿柯林斯书上对“‘证明’相对论的两个实验”的案例分析来说,这也是柯文里乐于称道的,“社会学家”通过“第一手材料”“用历史显微镜让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典型”。不过,我们在柯林斯书的这一章的30页译文里,大量看到的是有关这两个实验的一些技术性细节的描写。难道同样的一些内容,物理学家写出来就只是“技术性问题”,社会学家写出来就立刻变成“微观分析”的“专业研究成果”了吗?
至于这种“专业”分析的目的,柯林斯自己说的是:“揭示大多数科学家向公众所解释的关于相对论的建立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注意他这句话说的是“大多数”,但事实上又只举出了3个例子,为什么他在这里不使用拿手的“微观研究”的统计功夫了呢?而柯文里则变本加厉,宣称“科学史书上不是都说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证明’了狭义相对论,爱丁顿的日食观测‘证明’了广义相对论嘛”。这就上升到一句全称判断,殊不知全称判断的命题乃是最容易被“证伪”的。
事实当然并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例如,本文作者前几年出版的《物理学史选讲》书里就没有那样写,并且许多物理学史的著作也没有那样写。由此可见,并非要等到柯林斯的“专业研究”结果出来之后,包括只懂得技术问题的全体科学家在内的天下人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专业”的物理学家早就在这方面有了符合实际的精辟描述。因为,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原意并不是检验光速不变,而是测定以太漂移。已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胡宁教授,1978年为张元仲的《狭义相对论实验基础》一书写的序言里说:“初次学习狭义相对论的人,往往误认为迈克尔逊实验或‘光速不变性’是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但是,在相对论出现以前,斐兹杰惹和索末菲已经在以太论的基础上对迈克尔逊实验的结果给出了解释。因此,迈克尔逊实验的零结果既可用太论来解释,也可用相对论来解释,也就是说,它既不否定光速不变,也不肯定光速不变。所以,企图用迈克尔逊类型的实验来进一步更准确地验证光速不变将是没有意义的。”
胡宁这段话,说的当然不是什么“技术性问题”,而是对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历史意义的科学概括,其价值远远在柯林斯书上的那近20页的“案例分析”之上。这才真正是“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啊!胡宁不仅在专业书籍上,而且在面向“公众”的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3期)上,亦发表了相同的意见。原来,柯林斯费力去澄清的所谓错误观点,不过是初学者的一种误解,或者是在一些有欠严肃的科普读物或者人云亦云的教科书里的马虎说法而已。读者由此亦可以看出柯林斯那本书的层次了。
至于星光偏折的观测,在秦荣先和阎永廉1987年合著的《广义相对论与引力理论实验检验》书中也说得很清楚:“用现在的观点看来,1919年的观测结果对于广义相对论几乎没有说什么,它最多只能说明牛顿理论必须加以修正”。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使用了过于简单的近似处理。那么,按照现代的观点,那时候的观测结果大一点小一点,都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按照这种观点,柯林斯分析的有关案例,乃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问题。
柯林斯书上提到在爱丁顿的数据处理里,舍去了样本数目最大的一组数据。这一点亦被柯文所强调。然而,那一组数据恰好亦是误差最大的。我们知道,在作最后的误差结算时,每一组数据对最后结果的贡献,并不简单地与其中所包含的样本数目成比例。误差较大的一组,在结果中的贡献会减低。所以,即使计入了那组数据,对结果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柯林斯对全部原始数据的误差分析。到底是他不会做这种分析呢,还是他知道结果不会对他的结论有什么重要意义而不去做呢,那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柯林斯“微观案例研究”的本领,似乎并不怎样到家。
总而言之,被柯文推崇为“专业研究成果”典范的柯林斯的两个案例分析,从现代物理学的高度看来,实际上都没有多大的科学意义,并且正好属于柯文里用来攻击牛顿的书所说的那种“‘科普’级的‘事实’”。而且,柯林斯并没有站在现代科学已经达到的水平来讨论历史上的案例,一般只限于就当时的情况就事论事。这一点正是国内国外的科学文人们最容易犯的毛病。
例如,关于卢瑟福提出原子的有核模型这一段历史。当他看到a粒子大角度散射的结果时,马上领悟到原子内的正电荷必定集中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区域之内。这的确表现了他非凡的洞察力。然后他计算出这种“卢瑟福散射”的微分截面公式,同实验数据符合得很好,由此“证明”了他的结论。绝大多数教科书和科学史著作里,都是这样叙述的。但是,后来有了量子力学,就知道卢瑟福的推导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微观粒子的散射,是不能像他那样用经典力学来处理的。奇妙的是,在这个问题(低能库仑散射)上,量子理论的结果又是同卢瑟福那个结果完全一样的。所以,卢瑟福用错误的理论能够得出正确的结果,仅仅是一种巧合,或者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凭运气。《何为科学真理》一书(95-96页)对这个案例有恰当的叙述,虽然文字不多,却表达出不多见的高水平见解,远远胜过那些就事论事的“微观分析”。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全面地评论社会建构论的得失,要把这两本书涉及到的各个主要问题都说清楚,恐怕也得写一本书才行。事实上,1997年在美国圣克鲁斯加州大学曾就这些问题举行过一次专门的会议,主题叫做"Current Debates on Science,Science Studies and theirCritics",讨论的就是科学和科学人文学的当前争辩,反映了科学家和科学文人发展着的对垒。说严重点,则是科学和反科学的对垒。G.霍尔顿在1994年出版的《科学和反科学》一书里,最后的一章也专门谈了“反科学现象”的过去和现在,讨论了在20世纪后期重新兴起的这股潮流。在国内,这类对垒亦早已有之,如今科学文人们又乘着西风挑起争端,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
但是,通过对以上两个案例的分析,已经足以看到社会建构论的某些鼓吹者和支持者的基本论据,是多么经不起认真审查了。特别是他们对科学家的排斥和攻击,使我想起1862年亥姆霍兹针对黑格尔反对艾萨克·牛顿的颜色学说这件事所讲过的一段话:“黑格尔自己觉得,在物理科学的领域里为他的哲学争得他的哲学在其他领域中十分爽快地赢得的认可,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他就猛烈而尖锐地对待自然哲学家,特别是牛顿,大肆进行攻击……”(见《物理学史选讲》158页)现代社会对于科学上的成就,早已有了成熟的(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评价标准。但对于科学人文学的成就如何评价,就不像对科学本身那样清楚。这也许是近期这场争论热起来的原因之一。希望今天的科学文人们不要重蹈黑格尔的覆辙,不要总想通过攻击科学家来为自己赢得认可。况且,这两方面的学科性质不同,亦是不应该和不可能树立统一的评价标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