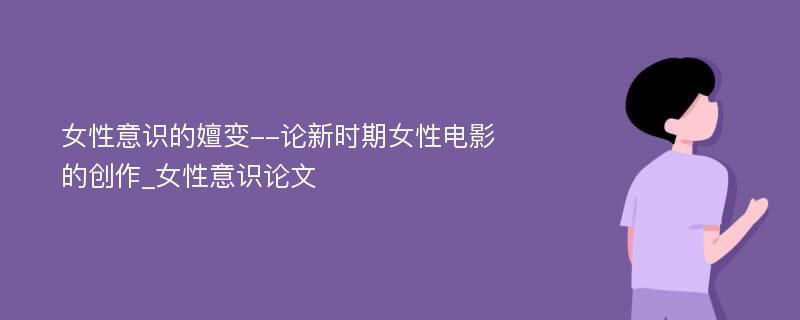
女性意识的嬗变——新时期女性电影创作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新时期论文,意识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毫无疑问,我国新时期以来所涌现出的令人瞩目的女性导演阵容,不仅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也成为世界影坛的一大奇观。全国八大影厂现拥有女导演50余人,其中数十人已具有不同程度的世界知名度,如黄蜀芹、张暖忻、王君正、王好为、广春兰、胡玫、刘苗苗、李少红等。这批中青年女性导演以艺术家和女性个人的双重身份跻身于电影世界,她们凭藉着女性敏感的心灵和独特的目光,感受审视着绚丽多姿的世界与人生,自觉不自觉地将女性意识、女性情感灌注到艺术的创作中,最大限度地承载着当代女性的幸福与欢乐、迷茫与苦痛,显示出男性导演所创作的妇女题材影片难以企及的美学优势。同时,她们的影片在各国际电影节的屡屡获奖,也足以证明其艺术水准已令西方电影大国的同行们刮目。在她们创作的大量影片中,尽管能够从严格意义上被认为“女性电影”的为数尚少,然而它们毕竟是这批女导演们迈着蹒跚的步履,朝着女性电影王国艰难跋涉的足印。面对她们的探索与努力,我们无法保持沉默,更不该漠视,而理应作出认真的思考与分析。本文试图从女性电影的重要因素——女性意识入手,对我国新时期女性电影的曲折历程做粗浅描述。
1
笼统地说,女性意识就是女性所特有的一种对女性自身的意识,即女性从生理——心理结构,社会——群体结构和历史——文化结构三方面来透视女性自身的意识。女性意识是衡量界定一切女性文学艺术作品的天然标尺,电影自然也不能例外。尽管很久以来人们一直为究竟什么是“女性电影”而争执不休,但是女性导演以自觉的女性意识去观照女性题材,无疑应是最为规范的女性电影。女性意识很显然是三个重要因素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具体到电影创作中来看,我们认为“女性意识”必须要包括如下两层涵义:一是指影片文本中应蕴含和体现出女性独立自主、自强自重的精神气质和男女平等、互敬互补的平权意识;二是指影片文本不把女性置于男权文化的视域之下,成为男性的“色情奇观”〔1〕,而是力求刻画和呈现女性自身的命运遭际、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的形象塑造意识。这两个层面的有机融合,才能构成较为完整的电影叙事意义上的女性意识。
然而,在我国女性导演的电影创作中,对于上述两个层面的女性意识的表述,都显示出严重的倾斜。我国从电影诞生之日起直至80年代初期,电影导演领域大都是男性一统天下,(虽曾出现过王苹、董克娜等新中国初期杰出的女性导演,但毕竟凤毛麟角。)性别角色注定了在男性导演的影片中去阐发女性意识几乎无任何可能。虽然在谢晋、凌子风、黄健中、张艺谋们的片子中也塑造出了一系列熠熠闪光的女性形象,但这些女性形象却无一例外地被操纵于男性中心话语或父权文化形态之中,她们或者是“一些情感和道德的代码,是男人们精神上的守护神”(如谢晋的女主人公们)〔2〕;或者是“一些本能和欲望的符号, 是男人们肉体上的承欢者”(如张艺谋的女主人公们)〔3〕, 而女性主体的自我意识则成为一种历史性的缺席。因而摆在新时期女性导演面前的是中国女性电影传统的空白,除此而外还有对西方女性文艺理论及创作的陌生。这一切造就了相对于我国新时期社会文化的迅疾发展,电影创作中的女性自我意识、自觉意识的呈现就显得相当艰难和缓慢,而且充满着误区与歧路。
2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妇女赢得了在世界范围内程度最高的妇女解放。在诸多领域中她们都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话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其代表着新中国妇女踏入社会舞台的心理动机和目标追求,她们在有意无意间把男性当作了行动的楷模甚至竞争者。于是我们看到这一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妇女精神上的解放和肉体奴役的消除的同时,文化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张扬则被忽略,这恰恰说明中国妇女解放的特殊性在于社会解放在前,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后。绝大多数女性对于自己的精神性别茫然无知,正如美国女权主义电影理论家卡普兰一针见血所指出的:“中国妇女的根本问题似乎不是走进社会生活——工作的权力,同工同酬(西方女权主义者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所关注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新的、没有充分表述过的问题,那就是对主体性的意识。”〔4〕正因为具有这种特殊性,所以幸运地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导演的王苹、董克娜其成功的标志就是娴熟地驾驭了从前只有男性才能驾驭的题材,出色地制作出“和男人一样”的影片。由于她们更多地是以“花木兰式”的社会角色而非女性个人的身份进行创作,因而无论是王苹的《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还是董克娜的《昆仑山上一棵草》都难以辨识其创作主体的性别特征。她们只是用社会主义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成功地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演绎出了一部部社会情节剧,当然也非常准确地诠释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及社会一般性的集体意识。在她们的影片中也塑造女性形象,然而即停留于对优秀女性作简单而平面的热情讴歌上,这些女性表面上的“在场”,实质上仅仅是一种经典编码与传统意义上的“空洞的能指”〔5〕,很多时候成了土地与人民的象征,真正的女性自我、女性意识则无法寻觅。30多年过去了,这种成功地抹去性别的女性导演群落中,仍然不乏王苹们忠实的继承者,从王好为(《迷人的乐队》)、季文彦(《血,总是热的》)、姜树森(《花园街五号》)到第五代导演中的后起之秀李少红(《血色清晨》、《四十不惑》)无一不是以自己作品中鲜明的社会主题而与男导演比肩,成为成功的“男性扮演者”和新时期主流电影、艺术电影的制作者。在充分肯定她们创作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作为女导演本该渗透于作品之中的那种体验最深、感受最切的女性意识则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化过程中完全被消解。
3
在我国80年代中后期社会历史——文化反思浪潮的冲击下,一批女导演们终于痛切地意识到现代文明在给予她们理性关注的同时,竟使其女性的生命意识陷入某种程度的虚妄。于是,在一片迷茫中,她们承受着难以摆脱的传统文化的重负,开始了探索女性自我意识的艰难历程。陆小雅的《红衣少女》塑造了一个试图以人格的自立来对抗文明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与扭曲的女中学生安然的形象。导演对安然那种“我谁也不象,我就是我”的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的赞赏:“我感到了人的心,我的感情和她是相通的。”〔6〕但安然式的“自立”仅仅属于少女的一段纯真梦想,由于影片描写的是中学生,导演出于社会责任感只能对女性性意识进行小心翼翼地回避,从而使这部集原著作者、导演和主人公均为女性的影片,女性意识仍处于明显的匮乏状态。史蜀君的《失踪的女中学生》似乎比《红衣少女》大胆一些,它触及了女中学生早恋这一敏感的社会问题。我们也可以隐约感觉到导演对被“文明”所压抑的女中学生青春萌动的同情,但已届中年的史蜀君难以忘却自己作为母亲所应承担的文明代言人的职责,社会性的忧虑最终置换了感情上的同情,影片的结尾只能让失踪(逃离)于文明社会的王佳重新回归到文明社会所指定的位置。刚刚萌发的一点女性生命意识,最终又被湮灭于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
如果说由于以上两部影片的主人公毕竟是女中学生,导演在传达女性生命体验时不能不存有无法排除的禁忌,致使影片中女性意识的显现还相当含混,甚至无以确认的话,那么张暖忻的《沙鸥》、《青春祭》则使我们欣喜地看到了闪烁着朦胧的女性意识的隐隐微光。《沙鸥》里的主人公是一个“我爱荣誉甚于生命”的女排球运动员,“不打成世界冠军绝不结婚”是她的铮铮誓言。这个形象一反传统女性的谦卑面孔和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寄托与男性的依赖心理,而是在对事业成功的追求中显示出现代女性渴望得到社会认同和实现个人价值的独立性,体现了女性意识中要求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一面。但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她同样无法逃脱事业的最高象征——“世界冠军”与女性生命的庄严仪式——“结婚”之间的尖锐冲突。然而还未允许她来得及在事业/家庭、 女强人/贤内助的二元对立中做出抉择, 灾难便无情地夺去了她的一切:冠军梦破灭,未婚夫沈大威遇难。“能烧的都烧了,只剩下大石头了。”圆明园废墟上的大石头作为历史的寓言蕴含着沙鸥(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是导演)对“一切都离我而去”的无限怅惘。可是沙鸥毕竟没有消沉,她经过由绝望到再生又重返球场的历程,无疑是一个抹杀性别角色的仪式,也完成了一代人(而不仅仅是女人)对幸福的追求,拔高了沙鸥形象的社会意义。影片结尾当沙鸥坐在轮椅上欣慰地看到中国女排获得冠军时,不再是作为女性沙鸥个人的胜利而是国家、民族的胜利,沙鸥只是一个社会“集体梦”的体现者,是一个被理想信念所填充的空洞的能指。《青春祭》所呈现的是张暖忻对女性自身与文化关系的热切关注。她把对女性命运的思考放置于现代文明与原始生态相互冲突的语境之中。当身穿辨不出性别的灰布衣服的女知青李纯来到美丽的傣家山寨时,傣族人民大胆追求幸福的古朴民风使她感到神秘与新奇,也逐渐唤醒了她那在文明象征秩序中被压抑的女性意识,当她穿起了流溢着女性青春艳丽的傣族筒裙时,便最终完成了由惧怕、胆怯到认同、接纳的心路历程,这一历程可以说暗含了李纯自身女性意识渐渐复苏的过程。然而这种复苏给她带来的是更多的磨难、更大的尴尬:未进傣寨前,她所缺失的是自我的女性意识,而进入傣寨后,她缺失的将是整个汉民族文化意识,这就使得李纯的自我审视始终游移于女性/非女性、文化/蛮荒之中。象征着“清醒的智者”的知青任佳的出现与死去,最终使李纯告别傣乡考上了大学,重新回归到现代文明的怀抱。当她以大学生的身份怀着一腔难言的困惑与伤感再回傣乡时,她只能于痛苦中回忆那刻骨铭心的情感,在迷惘中祭奠那段为历史的泥石流所湮没的青春岁月。由此李纯的反思也就失去了女性个人意识的成份,而衍化成为一代人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反思。李纯也如沙鸥一般成为社会群体的符码和载体。
胡玫的《女儿楼》把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与女主人公的内心欲望和爱情渴求的冲突作为叙事焦点。影片尽管大胆地表露了女性的内心欲望和内在激情,然而更主要的却在于“有意识地表现了一种社会禁止的情欲和浪漫主义的爱情以及由国家所支配的主体之间的分裂”。〔7〕作为一名军医的女主人公与男病号之间虽彼此倾慕却未曾表露过情感,这明显地体现出对国家的义务责任高于个人欲望要求的价值取向,女性的青春与爱情成为某种外在于女性自身的政治目的与道义责任的祭品。由于导演的创作意图是以女性的情爱来暗指个人愿望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因而使得这部本该能够较充分地呈现女性意识的影片走入误区,即把对女性意识的探索置于了普遍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其结果必然是消解了女性意识的纯粹性与深邃性。
4
黄蜀芹的《人、鬼、情》被许多评论家誉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女性电影”。影片借助一个以扮演钟馗而饮誉海内外的京剧女艺术家秋芸的情感生活,象喻式地揭示了现代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困境。它之所以被称为真正的“女性电影”,首先在于影片打破了以满足男性视觉快感为基点来建构女性形象的传统模式。影片的开头出现在观众面前的秋芸只是一个背影,当我们通过镜子的反射看到她的正面形象,却是一张被五颜六色的油彩涂抹成的丑陋不堪的钟馗的脸。这表明秋芸是拒绝成为男人观看的客体或曰“色情奇观”的,她要通过自我审视、自我抗争向男性社会、男权意识提出质疑和挑战,其女性意识的表露不可谓不鲜明。其次影片完全从女性的角度揭示了女性自我的内心世界及沉重的心理负荷,表达着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秋芸之所以将整个生命倾注于舞台上“鬼情”的建构,实际上是一种试图逃离女性命运与女性悲剧的绝望的挣扎。秋芸的悲剧主要来自于围绕在她周围的现实社会中“人情”的极度匮乏(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匮乏)。从亲情来看,童年的小秋芸第一次心灵的创伤源于无意间发现了母亲与“后脑勺”(在影片隐含的线索中证实此人是她的生父)在草垛上的偷情。随着母亲与生父的私奔,秋芸陷入了无父无母的悲惨境遇;从爱情来看,青年时期的秋芸与省剧团的张老师曾萌发过朦胧的爱情,但面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压力,张老师无力完成从“师长”到“情人”的角色置换,秋芸的初恋只是一段苦涩的回忆;从夫妻之情看,秋芸最终尽管组织了家庭,但丈夫心胸狭窄,嗜酒如命,不能给她丝毫的温暖与慰藉,夫妻之情名存实亡。这种父不父、师不师、夫不夫的生存困境,使秋芸在父权社会的边缘苦苦挣扎而又一次次地饱尝着被放逐的酸楚与悲凉。为了逃脱女性的悲剧命运,也出于女性天生就有寻求男性庇护的渴望,秋芸只能去舞台中,向冥冥鬼神世界索取一份温情,通过扮演男性角色来获得想象性的满足。同时这种“扮演男性”,更意味着秋芸一心要改变自己女性命运的最终选择,当然也极其生动地成为了现代女性生存困境的指称与象喻。导演以浓重的人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具有丰富文化意蕴和哲学高度的完整意义的女人。她在对秋芸努力挣扎逃出女性既定命运之网抱以深切同情之时,又不无深刻地揭示出这一挣扎带来的更为困惑的女性命运:秋芸不能因扮演了男人而成为一个获救的女人,因为具有拯救力的男人只存在于舞台上,存在于她的扮演之中。现实生活中的理性男性——拯救者则是一个永远的“缺席”,因此,秋芸的“女性家园”仅仅只能在艺术中得到“精神”建构,而现实家园的构筑恐怕在短时期内还难以实现。这种理想与现实的难以整合,是使秋芸及所有现代女性陷于人格分裂状态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认为《人、鬼、情》的深刻性决不仅仅在于它第一次以女性的心理、女性的意识表述了女人的艰难,更在于印证了当代中国女性意识的现实存在。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影坛上涌现了一批由女导演们拍摄的,反映当代女性文化困境的影片,如鲍芝芳的《金色的指甲》、董克娜的《女性世界》、王君正的《女人·TAXT·女人》、《独身女人》等,这些影片都试图有意识地呈现当代女性的独立人格,或表现出女性对实现自身价值的追求,然而由于它们的制作者大都站在某种经典的道德判断与性别价值判断立场上,塑造了一系列并未对男性中心话语和男权文化构成反抗和颠覆的“正面女性形象”,再加上采用了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即影片常以一个不规范的、反秩序的女性形象、女性故事开始,而以一个经典的、规范的情境为结局。于是这些影片与其说表现的是女性的一种反叛、抗争,不如说是一种归顺与臣服。鲍芝芳的《金色的指甲》是根据女作者何娅的纪实作品《女十人谈》改编的。这是一部十个有着不规范、不“道德”的婚姻、家庭生活的女人的自述之作。而鲍芝芳则将其演绎为一部生活彼此相关的五个女性的情节剧,进而由她们的婚恋生活构成了一个现代社会女性生活的表象。令人遗憾的是影片只是在一种崭新的外形式下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俯首称臣。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所谓女性的“不安分”,无非是想从一个围城杀入另一个围城,所谓的“痛苦”无非是得不到社会,实际上主要是得不到男人的承认。这些女性在极度自尊的外表下潜藏着极深的自卑心理,并未摆脱对男人依赖的传统观念。于是结尾那太过经典的大团圆婚礼结局给五个“不安分”的女性都安排了完满的归宿:三个妻子、一个待嫁的新娘和一个刚刚获得爱情的女子,这则本该属于女性自己的故事也就衍化为社会期待视野的故事——道德的故事。影片本文中的女性形象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具有某种色情观看价值的银幕表象,成了男权中心文化认同、认可的女性角色。由是,导演对女性自主、自尊的目标追求和叙述指向便滑入更深的迷惘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价值观的迷失。至于《女人·TAXT·女人》、《独身女人》、《女性世界》等影片走的则是另一条路子。它们均以极端化的方式从女性视点有意丑化男性。通过对男性萎缩人格的批判来体现女性解放、女性独立人格追求的主旨。无论是秦瑶(《女人·TAXT·女人》)、欧阳若云(《独身女人》)还是黎晴、吕云、陶天怡(《女性世界》)都经历了爱情的痛苦与失落,她们所面对的男性不是自私、懦弱,便是偏狭、虚伪。导演们也许认为只要通过对男性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嘲讽便能实现女性独立的人格意识,熟不知由于她们自身观念的模糊致使这种表达全然成为赶了一下这个时代“阴盛阳衰”的时髦,使本该由两性共同支撑的世界出现严重的倾斜,而对作为真正文化意蕴上的女性意义的阐释未免过于简单和粗糙。
以上我们对新时期女导演们所制作的一批描写女性题材、体现女性意识的作品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数影片并没有能够从真正意义上完全表述出女性独立自觉的意识,而是或多或少地在被主流意识形态的同化中所消融,这大该是同中国女导演的女性意识总是隐匿于社会总体的道德规范之中分不开的,她们的女性人生态度的形成总要受制于社会规定的观念,因而尽管影片中大多数女性形象具有丰富的性格表层,仍难以摆脱贫弱和空洞的既有女性模式。然而无论怎样,这批女性导演毕竟提供了与男导演们不同的女性形象,理应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导演群落的不断发展和壮大,随着越来越多的女导演们更清醒地意识到、领悟到作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中国的女性电影和电影中的女性意识必然会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发展和开拓。
注释:
〔1〕〔5〕(英)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转引自《影视文化》1989年第一辑。
〔2〕〔3〕屈雅君《“女为悦己者容”——关于男性电影的女性批评》,《当代电影》1994年第6期。
〔4〕〔7〕(美)E ·安·卡普兰《令人困惑的跨文化分析:近期中国电影中妇女的地位》,转引自《当代电影》1991年第1期。
〔6〕陆小雅《〈红衣少女〉创作后所思所想》载《当代电影》1985年第4期。
标签:女性意识论文; 女性电影论文; 当代电影论文; 独身女人论文; 女性世界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