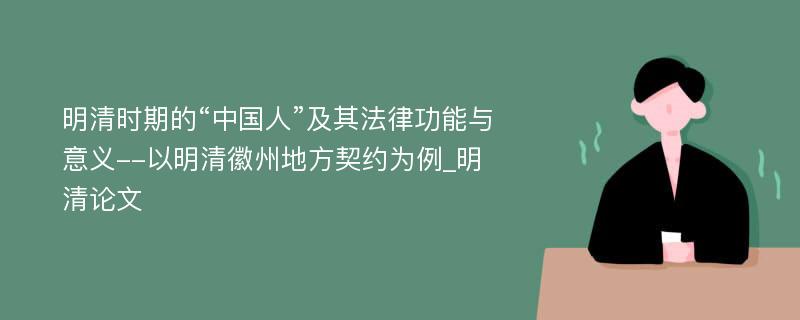
明清时期的“中人”及其法律作用与意义——以明清徽州地方契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徽州论文,为例论文,契约论文,中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人”,在明清时期又被称为凭、凭中、中见、见、居间、中证人、见中等等,是契约订立过程中除当事人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参与者。中人的出现是伴随着契约的不断发展而活跃起来的,早在西周的金文中,就有有关中人的记录:“卫盉”铭文中,在记录了契约签订的时间、双方当事人的姓名及标的物之后,还有有关“五伯三有司”的记载,并将其作为除当事人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来监督并主持交割的进行。(注:“陕西省歧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载《文物》1976年第5期。)《吕氏春秋·尊师》中也有记载:“段木干,晋国之大驵也。”有关学者考证:“驵”通“侩”,可能是最早以说合牛马交易为主的中人。(注: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其后,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到唐代便出现了以说合为职业的职业经纪。“今人谓驵侩为牙郎,本谓只互郎,谓主互市事也。唐人书互市作牙,压似牙字,因讹为压耳。”(注:[明]陶宗仪:《辍耕录》。)明清时期,在商业气氛浓郁的徽州社会中,理性的徽州人在频繁的商业生活,滋生出了强烈的契约意识,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显示出了几乎“无中不契约”的情形,中人成为契约成立的“要件”。那么,中人在徽州的民间社会中具有怎样的法律意义,它对明清时期民间社会秩序的维护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以往的文献记述以及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集中于中人的“中保人”角色,如《居延汉简》中载:“终古燧卒东郡邑高平里召胜,字海翁,贳卖酒楼曲布三匹,匹三百卅三,凡直千。得富里张公子所,舍在里中门东人。任者同里徐广君。”(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编号262·29。)徐锴《系传》中认为:“任,保也”,即保人之意。具有成文法性质的唐宋杂令也规定:“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注:转引自戴炎辉:《中国法制史》,三民书局1956年版,第337页。对于该问题,戴炎辉又认为“有应注意者,所谓保人,并不是都有代偿责任。俚语说:‘媒人不保生子,保人不保还钱。’即使为保人、中保人、保证人,只不过为中人、说合人,负督促债务人清偿,或居中调处的责任而已。”)该项规定从中保人连带责任的角度明确了中人的作用。现代学者也着重从“面子”的角度考察了社会精英充当保人时在民间社会秩序维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注: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二者对“中人”的作用有着殊途同归的认识:对村民来讲,特别是在与村外人打交道时,找一个有“面子”的中人非常重要;中人的“面子”有很大的效力,所谓中人的“面子”越大,交易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二、侧重于中人的“经纪人”和“中介”的内容:“居间,谓当事人一方为他人报告定约之机会或为定约之媒介,他人给 予报酬之契约。他方委托人,前一方称为居间人”。(注:潘维和:《中国民事法史》 ,台湾翰林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页。这种情况主要是指职业牙人,职业牙人以抽取 行佣的比率为生。比如《册府元龟》卷504《邦计·关市》中就记载:“四年七月,兵 部员外郎赵燕奏:其市牙人每贯收钱一百文,甚苦贫民,请行条理。”)三、还有些文 献明确了中人“调解人”的身份:“宾客居间,遂止俱解”。(注:《史记·灌夫传》 。但在现代人研究的有关调解的事例中,中人调解的情形是非常少见的,比如在张晋藩 的《清代民法综论》中将民间调解的责任归之于“宗族调处和乡邻调处,而以宗族调处 最为普遍”。在徽州的地方宗谱《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8《家规》中也强调:“ 凡遇族中有不平事,悉为之处分排解,不致经官。”所见中人的调解功能是较弱的。) 应该说前人对中人的特征及身份的界定是十分清晰的,对其作用的分析与理解也相当深 刻。但因为这些记述或研究成果中的“中人”大都不以主体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契约 或债权研究的附属物而存在的,所以,当我们着眼于明清时期的徽州下层社会时,大量 的契约提供给我们有关中人的更为具体、详实的信息,为对中人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提 供了广阔的资料背景和进一步补充、修正前人研究成果的可能。虽然徽州地区的中人研 究只能作为区域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对它的分析可能并不带有普遍性,但至少它能为我 们研究徽州社会提供一定的借鉴。比如,一般人们都将中人的身份定格在具有完全权利 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族人、姻亲、近邻或地保等人的身上,(注:叶显恩先生认为:“土地买卖必须有中人,中人大多数都是卖主的族人、姻亲、近邻或地保等等。”叶显恩: 《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仆佃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但在徽州契约 文书中,却有妇女和仆人这些没有完全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的人成为中人的契约,这表 明了中人身份的日趋复杂化。另外,作为一个集合体,虽然“中人群体”与个体中人的 同质性是明显的,但在契约中“中人群体”的“合力”作用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于 它所反映出的人们对中人及其所代表的秩序的理解,也没有从其作用和意义上与个体中 人的个人行为加以区别研究。如果说契约本身代表了一种秩序,那么中人就是这种秩序 的维护机制;它既属于书面契约的文本化内容,又具有契约所不具有的书面之外的约束 力;它既扎根于民间习惯法之中,又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尤其是中人所具有的公开性的 特征足以使它成为不成文的成文法,不强制的强制力。
本文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以《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第一辑。在前书中,笔者选取了《康熙黟县李氏抄契簿》、《雍正休宁金氏置产簿》、《乾隆休宁黄氏置产簿》、《乾隆休宁程氏抄契簿》、《嘉庆祁门吴氏誊契簿》、《同治休宁张氏置产簿》共六个姓氏的830例买卖契约作为分析、比较研究的主要对象,以期从中人的个人身份及他与当事人的关系、中人群体的存在状况等多个角度去考察中人的实际作用。
二、中人的身份
中人的身份在本文的研究中不但包括了中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地位,而且也包括他们 与当事人尤其是卖主的关系,这种关系除去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宗族、亲戚、家属、夫妻 、父母子女及监护人等关系外,还包括了官民关系、主仆关系等等。
(一)中人是地方基层组织中的领袖人物
地方基层组织中的领袖人物一般是指保长、里长、图正等等。虽然基层的保长之类并不真正属于国家的行政官僚体系,但在民间,他们却被认为具有“官”的身份和象征意义,例如在《休宁金阿汪的卖契》中就直接将保长称为“官人”:
“二十四都二图三甲立契妇金阿任,全男金千寿,今因急用,恃先年阿夫金六生手当过山五号,今内取山三号……出卖与黄×名下为业,今恐无凭,立此存照。
雍正九年七月×日 立卖契:金阿任
全男:金千寿
凭中:巴佑徵 官人(东沟人,任保长,名加寿)
程春雷
依口代书:程景虞”(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十,第100页。)
在这一契约中,立契人将具有保长身份的巴佑徵称为官人,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保长就是代表国家的官方人员。其实在官方的文献中,对保长、里长等地方基层领袖也有类似的称谓,如“身充甲保,即属官役,一切事件,地方悉惟该役是问。”(注:《清高宗实录》卷549,乾隆二十二年十月戊子。)既是官人,本身就具有了官方所赋予的诸多权利,也因此会增加他们倍受信任的砝码。从另一个方面,就他们的来源看,一般这些人是经由“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注:《清高宗实录》卷548,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庚午。)同时,他们也应具有这样的个人威信:“十家立为一甲,务选殷实老成、端正勤慎者,公举为甲长报官”,(注:于成龙:《弭盗条约》,见贺长龄、魏源编《清朝经世文编》卷74,《兵政五》。)所以,这些由乡绅们推荐,并与地方官打交道的人在当地会有较强可信度。但笔者在前文列出的六姓氏的830件买卖契约中却仅见到2例由官人作中的契约,并且这两例也都属于族外契(买卖双方不是同族之人)。可见在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中,人们请保长、甲长作中的现象并不十分多见,也就是说,在经济交往中,人们所倚重的并非是代表官方的、具有政治意义的、从理论 上更具有保障作用的地方基层领袖。对这一问题,应着重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徽 州地区宗族组织十分发达,“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 ,丝毫不紊”,(注: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一般“乡有争竟,始则鸣族,不 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再不决,然后送于官,比经文会公论者,而官藉以得其 款要过半矣,故其讼能解。若里约坊保,绝无权焉。”(注: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 6册,《歙风俗礼教考》。)从这一记载来看,里约坊保在当地的权威有赖于宗族的支持,在“敬宗收族”的观念支配下,人们更愿意相信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信任体系,尤其在族内更是如此。第二,保、甲、里长等人自身的瑕纰。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的“更定保甲”之法就是针对此前“州县编查保甲,日久生玩□率以具文此事,各乡保长、甲长类似市井无赖充之”(注:《清高宗实录》卷548,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庚午。)的情形而制定的。所以保、甲长本身可信任程度的降低,也会使人对其行使中人权利的能力及其在法律上所应负有的连带责任产生怀疑。
(二)中人是族长、族众
此类契约以族内契最为多见。笔者现将所统计的830件契约列表如下:
名 称 族内族外合
计
A B C D E F
道光休宁吴氏 358 2 7 7 061
同治休宁张氏 490 9 3 0 768
乾隆休宁程氏1074 4 0 2 4
121
乾隆休宁黄氏152314 5 6 6
186
雍正休宁金氏181312 4 7 11
218
康熙黟县李氏1506 9 2 7 2
176
注:表中A代表中人与立契者完全同属一族;B代表中人与立契者部分同族,部分异族;C代表中人与立契者异族,但与收契者同族或有其它族人;D代表中人与立契者同族,但与收契者异族或有其它族人;E代表中人与买卖双方都不同族;F代表中人与买卖双方都有同族。
上表中的数字很直观的显现出三个结论:一、六姓氏的买卖契约中,族内契占到了大部分,分别为70%、66%、92%、83%、84%、91%。这主要是由于在“寸土寸金”(注:乾隆《绩溪县志》卷1《方舆志·风俗》。)的徽州地区,地权转移应是迫不得以的事情,并且惯例也对此有所规定,在一般包括地权在内的不动产的转移过程中,宗族和姻亲具有购买的优先权,其一般顺序是亲者优先,次及地邻、典当主、原卖人。在优先者不要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人购买,否则,姻亲旧主就要从中作梗。(注: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仆佃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对于“先买权”产生的根源,杨国桢先生认为,这是乡族共同体或豪强的暴力的结果,是来自血缘共同体关系残留下来的限制。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但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却认为这是当时人们对认为是过分了的土地流失采取的一种防卫性反应。参见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一文,载《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一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以为,不管是前者所说的客观发展,还是后者所认为的主观设置,从秩序的角度而言,先买权的存在为土地的买卖提供了一个框架,成为一种非强制的规则,并且有着十分强大的限制力量。)二、同族契约中,完全由同族人作中的数目较大,分别占到族内契的81%、100%、96%、98%、98%、96%的比例。这又进一步证明在同族买卖中,人们更愿意或必须选择族内之人为自己作中。三、在为数不多的族外契中,笔者按中人与买卖人的关系分为四类,从表中来看,几乎没有什么规律,这也表明在族外交易中,人们对中人选择的随意性较大。
在族内契中,立契人对中人的选择也有一定差别。首先是族长、房长、门长等族内领 袖。因为他们“分莫逾而年莫加,年弥高而德弥邵”,故“合族尊敬而推崇之,有事则 必禀命焉”。(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八《家规》。)“所举族长,皆系绅衿 土豪”(注:《清高宗实录》卷1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辛亥。)和“徽俗重长上,一家 则知有族长、门长”(注:傅岩:《歙记》卷五《纪政绩》。)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氛围及 权威人格导向,使得人们在“地小人众”(注:万历《歙志》卷19《食货》。)的现实生 活中,更愿意选择族内权威来为自己作中。
其次,中人是一般族众。一般族众是相对于族长、房长而言的在族中没有特殊权威的 人。他们与立契人的关系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立契人有较近的亲属关系,是立 契人的兄弟、侄子、叔伯等。如《休宁吴事一卖契》中就写明:“见:叔吴仲宽、吴内 孚;弟:吴惟时;侄:吴素瞵”。(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十二,第206页。)近 亲属作中的最大优势,一方面在于可凭借血缘亲情确保中人对契约投入最大限度的关注 和支持;另一方面则在于可以免去惯例中“亲属优先权”而带来的阻挠。
另一种是立契人和中人虽属于同族,但相互之间的关系较远。在《乾隆休宁黄氏置产簿》中有一个名叫黄朗仲的人,从所有的相关契约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他的基层或族内领袖的身份,但他却在顺治六年到康熙二十五年间共为人作中28次。其中在他为黄羽仪作中的契约中共有两名中人,一个是黄羽仪的弟弟黄兆于,另一个就是黄朗仲。(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七,第11页。)因为契约中已明确了黄兆于与黄羽仪的关系,这也从反面证明了黄朗仲与黄羽仪的非近亲属的关系。在黄朗仲作中的28个契约中,只有三个写明了立契人与他的关系,而其余25件中这种关系是十分模糊的。虽然25件中有可能出现漏写的情况,但所有的这些人又不可能都与黄朗仲的关系特别亲近,况且其中还有三件属于族外契。那么,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黄朗仲在族内有着较高的威信。虽然他在当地的经济地位不是很好,也曾于康熙24年、29年两次立卖地契,并于27年因生活贫困将土地当掉,(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七,第54、117、197页 。)但这并未影响到他作为中人的地位。可见对买卖双方而言,中人不一定有较高的社 会地位和富裕的经济状况,个人的品行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的个人威信是一种很 好的信用保障。
(三)中人是立契人的亲戚
与同族契约中中人多是族人的情况不同,在异族契约中亲戚的比例较大。在《休宁王 鲁山卖契》中,中人是亲:李明仆、吴志之。而在《休宁戴纳如卖契》中共有九个中人 ,其中就有族岳汪传来,侄婿汪永生和另外四个未表明实际关系的亲戚余健中、黄子重 、洪旺至和金联玉。(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十二,第135页。)
亲戚是跟自己家庭有婚姻关系的家庭及其成员,《礼记·婚义》中称:“婚姻者,合 二姓之好”。二姓之好的含义,除却祭祀祖先及传宗接代的功能外,还在于用宗族观念 维护同族关系,通过结亲的办法增加异姓亲属间的联络。在徽州“邑中姓多故族世系, 历唐宋以来两姓缔盟必数百年婚姻之旧”,(注:嘉庆《休宁县志》卷1《方舆志·风俗 》。)亲戚作中,既可以为异族之间相互生疏而又都与之相熟的人作财产转让的中介, 又表明了他们在“优先购买权”方面的态度。
同族契约中较少有亲戚为中介的情况,但作为见证人,也有些立契者请亲戚作中。在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五《康熙黟县李氏抄契簿》的契约中,我们见到了立契人李邦 待、李邦卫、李有功、李东升都曾邀请过亲戚吴有孚作中,而李邦卫和李邦衡也请过姑 夫汪士鳌作他们的中人。在笔者统计的830契约中,所见亲戚一般为:姑夫、姐夫、妹 夫、女婿、表兄弟、岳父等等。
(四)中人是妇女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在“三从”之礼的严格约束之下,妇女没有专用之道,她们的 行为能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尤其是结婚以后,妇女的人格几乎都被丈夫所吸收,失去 了独立性。国家法律也明文规定:“凡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监外,其余杂犯责付 本夫收管”。(注:《明律·断狱》。)不但如此,在权利能力上妇女也是不完全的,《 大清律例》规定:“若妇人,除谋反、叛逆、子孙不孝,或己及同居之内为人盗诈,侵 夺财产及杀伤之类,听告,余并不得告。”(注:《大清律例·刑律·诉讼·见囚禁不 得告举他事》。)表现在经济活动中,妇女财产权的实现方式却是多样的,“除了一般 意义上的家产分割时妇女的继承份额外,寡母,尤其是在子年幼时,对于其子的财产拥 有很大的处分权。”(注:阿风:“明清时期徽州妇女在土地买卖中的权利与地位”, 载《历史研究》2000年1期。)
中人在契约中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信用——中人本身的信用以及其对买卖双方信用的证明。信用来源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而道德所依附的主体——人并不存在性别差别,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之下,妇女作中的问题也具有了理论上的依据。在明清时期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妇女作中的具体行为是存在的,并且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种中人是立契人的族中长辈。例如:
“卖契妇程阿朱,今因年荒,日食无办,自央中将故副夫分得……山……尽行卖与族 叔名下,……
崇祯十五年四月×日 卖 契:程阿朱
中:津叔婆
代书:亲 汪文运”(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六,第214页。)
虽然我们无法从简单的契约中弄清立契人程阿朱与中人津叔婆的关系,但从“津叔婆”这一称谓上来看,中人显然是立契人的族中长辈。
第二种:中人是立契者家庭内部的同辈。崇祯四年,程道升的卖契中写到:
“卖契程道升将在字……号,土名……共租四秤卖与亲兄名下,……
崇祯四年九月初五日 卖:程道升
中:道乾嫂”(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六,第236页。)
在此之前的八月,程道升另一件卖与亲兄的地契,也是由道乾嫂作中。这一契约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女人作中,而且还在于买卖双方都与中人道乾嫂有着特殊的亲属关系,这使得土地物权在兄弟之间的转移以及对中人的选择都没有超出近亲属的范围。
第三种:中人是立契者的仆妇。如《休宁胡阿朱卖契》的中人除了亲人程元粮和黄朗仲之外,还有一人名曰蔡腊嫂。从接下来康熙贰十六年胡兴旺(他是前契胡阿朱的孙子)的卖契中我们得知蔡腊嫂是胡家的“经管仆妇”。(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七, 第48、49页。)尽管作为佃仆同时又是妇女的蔡腊嫂在身份与地位上与主人相差甚远, 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依然可以成为主人地权转移的中介与见证。
虽然在众多的契约中,笔者仅发现了八例妇女作中的情况,并且根据她们的特点所划分的类型因为数量较少也很难说是十分典型和普遍的,但它们的存在毕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尽管受到传统的礼制以及习惯的制约,但在实际生活中,中人的某些特性,诸如个人威信、个人身份、人际关系也会和某些个别妇女所具有的道德、身份和经济因素相结合,从而将她们推到中人的位置上。当然,仅以个别状态出现的女中人始终无法成为中人的主流。
(五)中人是佃仆
佃仆或庄仆是明清时期因“种田、葬山、住屋”而形成的与地主既有租佃关系又有主仆名分的贱民阶层。(注:经君健:“试论清代等级制度”,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仆佃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0页。)虽然主仆之间的身份差异是存在的,但在实际的契约中,中人的角色却可以由佃仆来承当。例如,天启四年,十五都的郑九买了汪向党的荒田及岭山,中人就是汪向党的庄仆李新柯。事后,李新柯因郑“伐伊坟边木植”,一纸诉状将郑九告上了县衙。县令在此案的判词中写到:“审得郑九弃买汪尚党等山木,即系李新柯为中。李向为汪之庄仆,其安葬之山出之于汪者,柯既为中,意欲近伊山界,使九晋木不伐,为他占争之地。但九实价买,安得阻之。今突告其砍祖坟顶巨木三根,索其醮礼,遂驾伐冢杀命之词。身为原中,本钉界定业必不容其侵伐,而山主汪尚党同事汪时震供未曾砍其坟木,则柯之词所告不实,合以杖惩。”(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四,第117页。)
我们暂且不管县令的判断是否正确,仅从他对庄仆李新柯为中的态度来看,他已经承认了李为中的身份。这表明至少官方在仆人为中的问题上并不持反对态度,没有因为李的仆人身份而剥夺他的中人权利。并且在这一判词中也可以得知中人的一个职责是“钉 界定业”,对买卖的不动产有丈量勘测确定见证的作用。事实上,在界定业址的问题上 ,仆佃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作为实际的耕种或看守者,他们对业址的了解要比实际上 的主人清楚的多。尽管如此,佃仆的身份还会影响到他作为中人的作用。由于主体资格 的不平等,一旦发生产权纠纷,仆佃是不具备中人所拥有的调解人身份的,他不可能凭 借自己的力量使纠纷双方达成某种妥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人的作用更多是中介 或见证。
(六)中人是主人
主人是相对于佃仆而言的。虽然徽俗“仆佃一般都没有土地”,并且也“不得私置”,(注: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仆佃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9页 。)但由于有些佃人对田地或山地投入工本就因此拥有了出卖的“田皮”和“力夯”的 权利,但一般要先卖与主人。例如康熙17年,金六生因欠人钱财,将土地尽先卖给了家 主黄仲立。(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七,第140页。)再如:
“立卖契汪小龙,今因无银使用,自情愿将续置山一亩……出卖与房东李名下为业……
康熙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立卖契人:汪小龙
中 见:房东 李心如”(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五,第139页。)
很显然,在这一卖契中,买者和中人都是房东李心如。按徽州习惯:凡“佃田、住屋、葬山”就证明了一种主仆关系的存在,所以汪小龙和李心如之间应该是主仆关系。虽然我们承认“绝对的契约自由和平等主体是根本不存在的”,(注:苏亦工:“发现中国的普通法——清代借贷契约的成立”,载《法学研究》1997年4期。)但订立民事契约的当事人双方尊卑之间的不平等也会影响到契约的实质内容。如何保证契约在相对程度上的真实合意,便是中人的一个作用,因为他在当事人双方之间起到了一个支点的作用,使双方在契约签定的过程中局部的、暂时的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之下,否则契约关系就很难成立。既定的主仆关系以及中人与当事人的“合二为一”的前提,都会使得这种相对平衡出现偏差。从根本上说,主仆的不平等从本质上决定了契约的签定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而中人作为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这种偏差以弥和的个人化、人格化的保障,也因中人与当事人和主人的合一而把中人变成了一个有名而无实的“唯书面主义”的形式。
以上六种中人的身份及他们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从中人作为一个个体的角度来论述的,但笔者在徽州契约文书中却发现大量的契约中的中人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作为一个群体,中人又集中了人们对契约、对惯例甚至对秩序的哪些理解?
三、中人群体及其法律作用
笔者之所以提出“中人群体”这一概念,一方面因为在徽州地区的买卖契约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有两个(含两个)以上的中人组成的群体作中的契约;另一方面是因为仔细考察中人群体的存在状况,可以更加容易理解人们对契约以及契约所代表的秩序的认识和理解。当然,这里所谓的中人群体并非一个具有一致的共同特征的十分固定的人群,而是一个因与当事人有着某种关系而形成的、临时性的群体。在笔者统计的六姓氏830买卖契约中,个体中人与中人群体的比较如下表:
名
称 族 内 契 约 族 外 契 约
1个中人 2个以上中人(含2个)1个中人 2个以上中人(含2个)
道光休宁吴氏 52.3%47.7% 26.3%73.7%
同治休宁张氏 42.9%57.1% 10.5%73.7%
乾隆休宁程氏 33.3%66.7% 33.3%66.7%
乾隆休宁黄氏 41% 59%
35% 65%
雍正休宁金氏 37.7%62.3% 24.2%75.8%
康熙黟县李氏 38.3%61.7% 28.5%71.5%
从上表量化出的结果看:(1)除道光休宁吴氏外,其余卖契中2个以上(含2个)中人的契约要比1个中人的契约要多。(2)除乾隆休宁程氏持平外,其余契约中,族外契前后两者的差要比族内契前后两者的差要大。这两个结果又表明了这样两个事实:一、人们在立契的时候,可能会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人来为自己作中;二、在与族外人订立契约时,为保证契约的效力,人们更会找较多的中人为自己作中,从而使这些临时被邀的中人形成了一个中人群体。
这些群体的搭配方式是不尽相同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单纯由“官人”组成的中人群体。如程春雷的租约中,中人是巴佑徵(官人)、黄洪达(官人)。(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七,第272页。)二、由族长及族众组成的中人群体。如黄阿陈卖契的中人是族长黄兆于及其余族众8人。(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十二,第163页。)三、由族人组成的群体。如黄明裕卖契中所写中人为亲伯:黄元白;族人:黄焕文;兄:简詹圣文。(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十二,第174页。)四、亲戚和族人共同组成的群体。如李邦卫卖契的中人是姑夫:汪士鳌,弟:邦待、邦徵、邦快、邦星等等。(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四,第129页。)五、由异族中人组成的中人群体。如:汪 金奎将土地卖给了张姓族人,为他作中的就是堂兄汪志檀和另一个张姓族人张焕同。( 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十二,第108页。)
契约就其实质来说,是当事人之间权利的预设,在这层意义上,契约的证据意义远大于它的象征意义。但在权利意识并不发达、国家民法系统效率低下的传统中国,契约预设的最大保障恐怕更多应来源于道德。在契约中这种道德又应该被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当事人本身以诚信为主的道德,另一个就是由中人的公开性所带来的道德监督。在这个意义上,较多中人所形成的公开领域远比个体中人要大得多,也就是说,中人群体所形成的合力会给违约方以更大的阻力。
虽然如此,但立契人对中人的邀请也并非无限制的扩大。在830例契约中,实际中人超过四人以上的契约仅有153件,占到总数的17.6%。对这153件契约进行对比分析,我们会发现它们一般具有如下的特点:
1.标的物的价格较高,一般都在10两以上。这样的契约在153件中有71件,占到总数的 64%。它们的一般形式如下:
“立卖契人程用和全弟程凝祉,今因急用,自央中将父阄分得系体字……立契出卖与族叔祖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定,时值价九七色银二十两整,其银一并收足,其地即交于买人管业。……
雍正十三年十三日 立契人:程用和 号 全弟:程凝祉 号
凭 中:程君衡 号 程万资 号 程天章 号 程汉乘 号
程华敷 号 程卜安 号 程渭吕 号 程炳如 号
程其安 号”(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十,第370页。)
在这一契约中共有九位中人,标的物的价格是九五色银二十两。中人与标的物价值之间的联系在于:较大数额的标的物会给买卖双方带来更大的收益,从而为其请较多的中人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较多中人形成的合力和公开性又会使契约效力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虽自唐宋以后,契约一般不写对中保人致酬事,但致酬事一直是存在的,有用宴请的形式,也有送银钱的。(注: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在徽州契约文书中,也有少数契约在契约之后写明了对中人的酬谢情况。如休宁黄实启的卖契就写明:“给中人礼二两二钱;成契日酒:六钱;印契一两;推税礼:一两九钱;收税:八钱九分;本家请酒用银一两,共花去柒两肆钱玖分”。(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七,第272页。)该契共有两名中人,二者各得银一两一钱。因“俗买卖产业有居间人谓言议与中,见契约成立后,由买主给与酬金(花红)”,(注: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页。)所以这种单方付费的俗例更会加重买主因买卖而带来的负担。试想,如果此契的标的价值在柒两肆钱玖分以下,甚至在柒两肆钱玖分到十两之间,那么附加费与标的物之间价值的比值越小就会越增大买主的负担。所以,中人的中资问题也就变成了制约中人数目的一个因素。
2.立卖契者是妇女,且以寡妇居多。在153件契约中有17件是由妇女立契的,占到总数的11.7%。例如,休宁程阿毕卖契中的中人是程于民、程佰朋、程斐然、程昭如、程誉良。(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十,第500页。)作为妇女,在明清地权变动日益频 繁的大背景下,她们也更多的参加到土地买卖中来。但相对于父权制的家族而言,她们 所具有的附属的身份和地位是先赋的,固定不变的,她们个人无法凭借自己的意志和努 力摆脱父权和夫权的限制。处在家庭所编织的网络之中,她们完全没有可能理解契约本 身所创设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相反,她们的权利会受到家族或家庭的干涉。在顺治六 年到宣统二年歙县卖田契散件中,大部分妇女的卖契都写有“并无威逼等情”的文字。 而在相同时期由男子立契的契约中,这种写法却较为少见。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契约 的书写有很多程式化的东西,但从中也能反映出妇女立契更容易具有受到“威逼”的可 能。所以,既然妇女本身无法生出权利义务的观念,那么她们求助于异己力量保护的思 想应较男子更为强烈。因此较多中人会比个体中人能给妇女以更多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实 际上的保障。
3.参与立契的人较多,也就是说参与交易的卖方并非一人,而是由具有行为和权利能力的近亲属或族人组成的卖方群体。此类契约在153件卖契中共有19件,占到总数的16.3%。例如:黄开文等21人因重建水口楼,需众听工费,将共产王家仓屋空地壹号……尽 行立契出卖与……,时值价银30两整,凭中共六人。(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七 ,第334页。)立契者人数的增多表明标的物的产权所有者并非一人,那么这一标的物的 出卖势必会牵涉各方的利益,也会增大契约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因此在因某种原因达成 共识的前提下,来自不同方面的中人所具有的合力和公开性,也会对任意一个企图违约 者产生更大的阻力。
以上三种类型反映了中人群体存在的一般形式和它在契约中的实际作用。作为一个群体,中人群体集合了来自更多方面的理解、保证、鉴别等信任元素于一体,使契约在得到公众认同的基础上享有了更大程度上的效力。中人群体与个体中人的不同除了公开性问题上的差异外,还为契约上升至诉讼阶段时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人证”的保障。例如,光绪二十四年绩溪县发生了这样一例民事诉讼案件:程肇荣、程象离等人认为族人程灶发所建造房屋之地侵占了族内“文昌阁”的旧址,并为此将程灶发告上县衙。但程灶发却在随后提交的诉状中称:“身价买程兴富服字等号基地,税五分,一切载明卖契。成交后,身即割税完粮,无人异议……”。为查明事实,县太爷要求核实程兴富的卖契。在经过调查之后,衙役提供了一份详细的中人情况表:“契内中人注明叩核:出卖人:程兴富,及程象离之堂侄。凭中:亲房程谷村,即程象离之堂侄,年五十余岁,现居宁国,为董事。程振遂,即程象离之堂弟,年六十余岁,于去年作故。监生程隐鱼,年六十八岁,于去年作故;生员程平章,作故;监生程四妹,年六十余岁;武生程振寿,年五十余岁;程万广,即敝都推收书;程宪章即卖主兴富之子;程兴樟,即买主灶发之弟;生员程炳西,去年作故。”(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三,第285—316页。)
显然,在程兴富的卖契中曾有十个中人,但其中有四个都已经去世,又因程谷村、程宪章、程兴樟等三人都与原被两造有某种亲属关系,以致最后县太爷只能命承行胥吏在中人中选择了程四妹、程振寿和程万广三人带至县衙作证。由此可见,个体中人的意外变动都会直接影响到诉讼的结果。这里的意外既包括了人身意外,如中人的死亡或外出等情形,也包括单一中人对买卖双方任意一方的偏袒,都会使真正的事实无法澄清。而中人群体的存在则可能最大限度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从而真正起到了预设的作用。这也是中人群体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中人及中人群体的法律意义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人是契约成立不可缺少的要件,是伴随契约前、中、后全过程的一种程式化、固定化模式。在官方的文献中,中人的法律身份是伴随着契约的标准化而得以被承认的。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敕诸县典卖牛畜契书并税租钞旁等,印卖田宅契书,并从官印卖。”(注:《宋会要辑·稿食货·钞旁印帖》。)这是政府让民间契约走向标准化的命令,而契约格式在整齐划一的同时,也使得中人的地位被法定化和格式化。因契约取得官方地位的主旨在于契税,“凡典买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仍追契内田宅价钱一半入官”,(注:光绪《大清会典》卷七五五。)同时也有“防讼结信”的功能,所以在成文法典中契约总是以禁止性的面目出现的。作为契约的附属物,国家对中人的认同也多是从反面来反映的,中人更多应属于民间习惯的范畴。虽然没有关于中人参与立契的程序性的文字规定,但在民间,这种程序却是人们熟稔在心的;虽然没有中人身份的明确限制,但人们却会按照自己的不同需求和条件选择不同的中人。那么,中人在民间、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又具有怎样的法律意义呢?
(一)中人是民间法律的一种象征
作为一种立契时既定存在的社会事实,“中人”的观念应来源于习惯。这种习惯是社会成员通过反复确认或否定的互动过程,逐步保留那些有利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行为积淀而成的。因为它是“集体的,也是累世创造的,并有着令人不得不承认和尊崇的特别权威”,(注:[法]E·迪尔凯姆:《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页。)所以人一生下来,就会被已有的习惯所围绕,并逐步内化为人们的稳定心理结构,进而支配着人们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当人们自然不自然的将内心的价值体系投射到客观事物上时,这些事物也由此具有了各种人的价值,于是,便形成了一套社会文化符号。“行契立中”的习惯就是遍布在民间社会的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人们口耳相传的实践中已经内化为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在现实 生活中的形象化的代表就是中人。
“中人”在私法中的象征或符号化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发端时便已具有的法律制约力量和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目的,而在于几千年的使用和传承过程中,它已经演变成一种具有保障契约实施功能的符号而沉淀于人们的心中。例如在前曾例举的汪小龙的卖契中,中人本身就是买者。显然,在这样的契约中,中人并不具有实际中人的作用,仅仅是一个“摆设”,即便如此,买卖双方依然会认可中人是契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中人只是一个象征性符号的意义十分显见。中人身份和威信的高低可能会使契约的约束力有强弱之别。但事实上,正是这种代表公正的符号,才使不想违约的人得到心理的保障,使企图违约的人有所畏惧,而这种符号的隐性作用就在于它符合了民间社会自我存在、自我发展的秩序性要求。
(二)中人是民间秩序的一种保障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从来不缺乏私权的意识,缺乏的是对私权的有效保障。(注:苏亦工:“发现中国的普通法——清代借贷契约的成立”,载《法学研究》1997年4期。)这种说法大抵是不错的,但笔者认为这种私权的概念无法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私权的内容,由于受家族和身份的制约,人们对本身的权利义务的认识是有限的。而正是这种限制,才会使人们更多的寻求外在的异己力量来获得帮助和保护。从这一点上来说,国家立法上确实缺少对私权的保障,但这并不代表人们的私权无法得以保全,正如日本学者所言:“清代社会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未开化社会,在日常社会生活上远远超过面对面的范围,而是一个大规模的社会。而且在那里有相当程度分化了的民事契约诸多类型同时并存,并在起作用。这样一个社会用这样一种方式得以运行,至少大体上还能维持民事秩序,这本身是应该由法制史研究解决的一个谜。”(注:[日]寺田浩明:“关于清代土地法秩序“惯例”的结构”,见刘俊文主编:《日本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73页。)在这位学者的眼中,契约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大部分内容,但事实上,虽然只是契约的附属物,中人才是保障契约实施的民间最常见也最有效的保障机制。
中人的保障作用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它的公开性。在“不以富贵为事啬,而以礼义为胜衰”(注:道光《徽州府志》卷二,程敏政《政世忠行祠记》。)的世代相传的既定价值观念中,逐步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评价定式,由此也就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以公开性为前提的,中人的公开性就在于他是除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参与者。“第三方”并不仅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而是一极力量,它来源于中人对“介绍、商定、确认和事毕后的宴请”等一系列活动的参与及第三方的立场,并且交易的事实又会通过他们辐射到更大的范围。于是,在一定范围内,人们的评价会形成强大的舆论,以最大限度来维护契约的公正性,并由此使社会秩序维持在一个大致平衡的状态中。
其次是权威性。权威性是特指那些有身份和威信高的人作中的契约。仅以族长作中为例,在“徽俗重长上,一家则知有族长、门长”的氛围中,违约就等于违背了族长的意愿。所以,即便是在“事起渺茫,讼乃蔓延”(注:万历《祁门县志》卷4《人事志·风俗》。)的徽州社会,和处在“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注:万历《歙志·风土》。)的风气中,人们也会对“产业相干,口角争仇,祠正副会同门尊,公道处分,或毕情劝释,不许竟烦官府,力逞刁奸”(注:《溪南江氏家谱·祠规》。)的劝戒知所规避。
同时契约中的“三面议定”,不仅是对契约当事人的一种信义考验,而且也是对中人的一种考验。实际上中人对任何一方的偏袒都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个中人都会在得失之间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与形象。而在中人群体中,由于群体合力的作用,更会使其中的任意一个中人对“偏袒”有所顾忌。所以,既然“契约本身标志着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注:蒋先福:《契约文明:法治文明的源与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那么中人便是这一秩序的有形和无形的维护者。说其无形,它是伴随契约始终的一种无形的力量,中人个体或群体的地位之高低,只表明了这种制约力量的强弱程度的高低。说其有形,就是中人的中介、见证、调解、作证的功能的运用,而这些功能的主旨就在于维护经济交往中的正义。所以,如果一个中人能够对“法律之上的正义”(注:[美]金勇义:《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陈国平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有正确的理解以及能在行为上彻底执行的话,那么,这就是民间手段对民间正义与秩序的一种强有力的维护机制。
(三)中人对契约合意的维护与破坏
作为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一个支点,中人在其中的平衡作用也对契约的合意与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身份平等是契约缔结的前提,但明清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所以人们在必然的经济交往中一方面只能默认“主观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在主观平等所创造的权利义务的制约中,作为一个支点,中人在双方之间主持着公道,将双方的分歧维持在一个共同认可的基础上,使契约的订立处于一种局部、暂时的相对平衡的状态下,从而使契约关系得以成立。
但我们又不能对中人的平衡作用有过高的估计,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中人对契约合意的破坏作用也是明显的。以下以找价契约为例,对这一问题予以解释。“立杜重复加添字人徐天玉,因上年杜卖田种一业,已经杜加,今年荒歉,无处掇价,凭托中证,情恳奈劝,加添到陈XX名下,当日三面言定,加添大钱叁千文整,亲手收讫。自重复加添之后,永不再藉田生端,今恐人信难凭,立此杜重复加添字收据存照。”(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二,第197页。)显然,在订立这一找价契之前,卖主徐天玉已经立过一次杜加契约,此次再次找价于理不平,并且从“情恳奈劝”的言辞中,我们也能知晓卖主的理亏与中人的不情愿。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再次找价获得了成功。在其中,中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正是这种作用使买方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显然中人的这种平衡作用并不是建立在合意的基础之上的。
(四)中人凸显了民间法律的“人治化”特色
提及“人治”,人们的概念中更多的是“权利行为不受法规约束,个人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定义,因其有“权大于法”的嫌疑而被现代人所不耻。但对于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而言,中人的个性和人格化的特点几乎在每一个契约中都有显现。由本文第二部分可以看出,在徽州社会中,上至“官人”下至佃仆都有可能成为中人,或邀请别人为自己作中。但这种个性或人治化的内容并未影响到整体契约关系的稳定,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从上到下所有的人们都是法的外行,或者换言之,法只是由外行的人们所创造和支持——这一点难道不正是中国社会的底力所在吗?”(注: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其实,人治化的中人机制只是中国底力的一种表象,它的本质则在于创造了一种“柔性秩序”,相对于具有国家强制力的“刚性秩序”而言,它具有更大的弹性,更注重运用社会的情感功能,从而也更加符合中国人的认知的规律、道德情感和价值认同。
同时,中人的存在虽是习惯法的一大内容,但它又不同于风俗、习惯、惯行这些隶属于民间法的约束机制,而带有了更多人治化的特色。作为集体的力量,风俗、习惯、惯行等内容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规范,这些规范虽来源于个体但不等同于个体,无法以个体的面目出现,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自我约束。相比之下,中人的约束作用虽也来源于人们之间口耳相传的习俗,但在执行约束的功能时,它的个性和人格化的特色是十分明显的,是作为一种鲜活的外力对当事人施加压力的。因而,强调内省的习惯与中人的外力作用的结合对民间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起到了双重作用。
五、结语
对于明清社会而言,中人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契约中的一个固定化、程序化的要件,而应被视为在经济及法律领域都具有重要作用的一种人性化因素。其人性化就在于中人是 作为“人”出现在契约中的,而并非是象国家法律或地方习俗一样具有强制力或必然影 响力的作用,它同地方官吏、乡约、老人一起,从人的角度构筑了对民间社会秩序的影 响与维护。应该说,中人是在人们不断的进行各种交易与财产分割的过程中自发而形成 的,这一方面体现了传统民事契约与封闭的古代社会相适应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人际 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的一种必然选择。说其必然是因为国家成文法只将“户婚、田土、 钱债”等民事关系视为“细事”,(注:《大清会典事例·刑律·诉讼》中有述:“户 婚、田土、钱债、斗欧、赌博等细事,既于犯地告理”。)因此也就并不关心这些关系 是否真正得以维护。所以,尽管中人人为因素善变的特点注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国家秩序 性结构中的主要内容,但它却弥补了成文法及其维护机制在民事秩序中的不足,并将人 们已有的价值观念、对社会习俗的认同、对秩序的理解集合于一身,在“介绍、见证、 调解”的过程中自发的制约着人们通过契约建立起来的民事关系,从而使社会秩序维持 在一个大致平衡的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