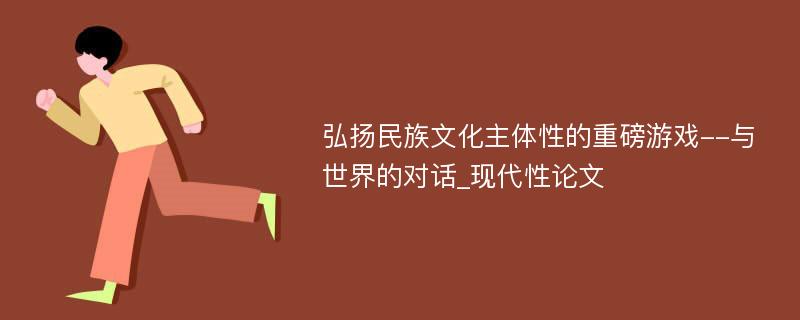
大片“博弈”——以弘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与世界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民族文化论文,而与论文,大片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大片崛起于21世纪伊始,蔚为一时之盛。其崛起原本是为了在市场上与好莱坞相抗衡,展现出一派文化“博弈”的锐气与风采,具有历史自身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转瞬七八年过去,中国大片竟陷于与自身初衷相悖离的处境,种种“后大片”现象一层层地浮出了水面,电影的叙事竟出现了一种背离现代性的逆转,只注重好莱坞式视觉奇观的营造,却忽略了对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叙事智慧的深入发掘与弘扬,令我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遭到解构,呈现出一种踩着好莱坞脚印亦步亦趋的文化趋同性现象。
着眼于中国电影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一个迫在眉睫的战略性课题便是,如何坚守并弘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主体创新,克服中国大片文化品位的沉落,与好莱坞求异存同,促成中国电影跨文化与世界展开有尊严的对话,并使自身在全球竞争、国际传播中牢牢地立于不败之地。
一 大片之兴:世纪性文化焦灼与我们的战略对策
新世纪伊始这七八年来,我们的文化思考躲不开也绕不过去的一个焦点就是,如何与好莱坞博弈。融入“现代性”的命题,就在与好莱坞的博弈中,渐次深化地体现为如何弘扬本土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话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下,诚如年轻的文化学者王宁所清醒地看到的,“中国电影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民族文化吞噬吗?”①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取得了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那就是:中国电影是以主动的、积极的姿态去迎接全球化挑战的,一贯注重博采世界现代文明的最新成果,并且始终坚持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凸显民族文化主体创新的中国式发展道路,由是锐意进取而迎来了今天这样一个大好的文化局面。离开解放思想这个立足点,离开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守,就无从实现我们电影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更新,就不会有今天中国大片的生长与发展。
中国式大片之兴,恰恰是回应全球化挑战的一个重大战略对策和行动。人所共知,好莱坞大片是以1975年的《大白鲨》和1977年的《星球大战》为标志而兴起的,制作豪华型、奇观化的大片恰恰是好莱坞手里一张通吃全球的王牌。于是,“大片博弈”,就成为当代世界电影产业较量的一个焦点。中国诚然不能孤立于这一世界电影潮流之外。中国大片的应运而生,实属于我们时代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它恰恰标志着我们电影产业意识和产业力量的苏醒,也是我们电影艺术复兴的必由之旅。事实上,中国大片起步亦晚,不过是最近七八年间的事情,与好莱坞积30多年磨砺且操练娴熟的大片模式似乎无可匹敌。但事实却并不尽然,华语大片的制作,以《卧虎藏龙》肇其端,继而,从《英雄》、《十面埋伏》、《功夫》、《神话》、《霍元甲》、《夜宴》到《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国产大片接踵而至,迭创票房佳绩,重振了中国电影产业之雄风,令好莱坞不胜惊讶和惶然。
中国大片的历史性功绩是昭然而卓著的,它敢于跨界而与好莱坞博弈,交手于国门之外,这就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势崛起,不妨说,中国电影由此而迈出了走向海外、并在拓展国际传播空间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英雄》曾首度创下国内2.5亿元的高票房,在2004年夏季《英雄》还连续两周稳夺北美地区电影票房之冠军,并占有2175家美国的主流影院,赢得5370万美元的罕见票房,在海外总票房则达14.5亿元(折合人民币),刷新了中国电影百年难期的市场纪录。中国大片的优势在于,为中国电影产业化领航,扛起了商业大片之旗而抗衡好莱坞,提升了我们民族电影在全球主流市场里的竞争力,扭转了中国电影产业命运的颓势,其历史业绩是不容低估的。
中国电影产业结构的重组由2003年发轫。在此之前,好莱坞大片基本上占了中国电影市场份额的60%到70%。单举2002年来说,中国电影市场在该年度的票房总额不足10亿元(人民币),而到2008年则达到43.41亿元,渐次从市场的低靡走向了昌盛。自2003年起,国产电影在本土市场上竟连续六年超过了好莱坞大片而拿到了从55%到60%的票房份额,迄2008年乃占到61.9%,该年度比2007年的33.27亿增幅达30.47%,连续五年年均增幅为35.89%,五年累计增长5.57倍;2008年的电影综合收入达84.33亿元,较之2007年的67.26亿元,增幅为25.38%,连续五年年均增幅为31.72%,在本土市场稳居领先优势;与此同时,我们在国际主流市场上也赢得了骄人的票房业绩,显示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尊严和气势,初步彰显了中国电影与世界对话的产业实力。
中国大片制作迄今业已有了“八年之痒”,在与好莱坞博弈的第一个回合告捷之后,可以说,我们首先解决了中国电影产业转危为安的生存问题;当下,我们与好莱坞的博弈,不妨说已进入到了更为关键性的第二个回合,其核心命题就是努力提升电影文化的软实力,尽快向现代化大电影产业升级,不断实践民族文化的主体创新并努力拓展在国际空间的传播实力。自2008年到今年的“贺岁档”,留在银幕上的光与影,既有文化的辉煌,也潜伏着挥之不去的隐忧。比如2008年初的《集结号》与跨过年来的《梅兰芳》,俨然是凌空升起的我们民族文化的彩虹。那“集结号”悲壮的号声穿透历史,为“牺牲与辉煌”正名,昭示了一种正义与崇高的精神价值;而诗剧化的《梅兰芳》,则将梨园小天地与抗日救亡的时代浪涛相衔接,梅兰芳面对日寇胁迫,“蓄须明志”,其凛然民族气节感人肺腑。这两部新作,无疑标示了一种令人鼓舞的新的民族风骨和美学风范。
《集结号》与《梅兰芳》为我们的大片创作开拓了一种新的思路,依托着我们民族文化丰厚的资源,中国式大片制作根本无需单一地固守着古装武侠类型而踯躅不前,其叙事样式与风格的多元性尚有待拓展,大体上可以有如下三类(还可有多种新的可能性):其一,侧重于商业性大片的建构,强化视觉的奇观化,以技术元素制造既炫又酷的镜像,如《英雄》、《神话》这类古装武侠传奇;其二,着力于史诗性大片的建构,凝聚历史诗情,以审美元素统领全局,如《集结号》将镜头对准了现代战争中人性的尊严与崇高,而《梅兰芳》则向经典叙事回归,以梨园世家和抗日战争为背景,感人至深地呈现出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舞台风采及其民族气节;其三,涉及人类与宇宙关系的科幻类型题材,以科学畅想或浪漫神话(包括《山海经》等古代传说)为叙事元素而做新的建构,如可以相对于《星球大战》的“羿射九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或者对中国宇航员探索太空的英雄化演义等等,这在中国电影里显然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
然而,无可回避的现实是,中国大片制作的主要走势其实仍然是以古装武侠类型来问津银幕的,到《无极》则以“镜花水月”的镜像呈现出向西方文化的漂移而舍弃了民族的风骨,特别到《色·戒》、《投名状》与《赤壁》的问世,乃成为划开“后大片”时期的一个分水岭。这类大片,以扭曲并牺牲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为代价而去换取一时的市场业绩,遭到从纸质传媒到电视与互联网络的质疑或诟病。然而,却有人竟编织出一种逻辑,说什么《赤壁》将故事演化为“特洛伊”式的西化版而令西方人易懂好看,恰恰体现了吴氏独创的一种“现代性”。是焉非焉,这岂不是颇值得玩味和探究的么?!
二 “后大片现象”:坚持或者放弃民族文化的主体创新
当今之世,东西方关系成了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焦点,其间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就是第三世界电影的崛起。从根本上说,它们别无选择,这是它们对于好莱坞文化霸权的抵御,也是它们从本土文化困境中的奋起抗争。这种抗争,在霸权与抗衡、趋同与求异、互动与共赢中,逐步推进了世界电影在文化和审美上多边互动的新格局而日趋成型。
那么,何谓“后大片现象”?其主要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它所带来的负面文化影响究竟是什么?人们看到,主旋律影片、艺术片和主流商业大片三分天下,其间尤以主流商业大片独占高端、引领风潮,初步形成了与市场经济法则相适应的竞争新格局。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当今电影的生存和发展,主要是由跨国资本、跨国营销来决定的,中国的电影市场早已不再是封闭的、自足自守的了。这期间,中国大片在本土的生长竟发生了某些文化沉落的现象,大片被人诟病的主要问题是:类型雷同单一、人文底气不足、艺术创新乏力,其叙事偏执地、一味地追求视觉奇观的营造,或提供快餐式的“即食即弃”的文化消费,却往往忽略了对民族文化“原点”及其人文传统的深入发掘,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民族文化的主体创新以及我们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乃一步步陷于被好莱坞大片蚕食与同化的文化困境。
张艺谋以前拍片,无不以人文情怀来包容大千的,在他背后总是有莫言、刘恒、苏童、余华、陈源斌等一个个杰出的“作家群体”给他托着底的。但是,从《英雄》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不再相信文学的情思,断然放弃了由衷而发的人文情怀,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解构,一味地“炫”技而营造镜像奇观,竟走向“图像/景观崇拜”,他所失落的岂止是艺术家主体的可贵情怀,同时也失落了我们民族的风骨及其美学精神。
中国大片的拐点,是以《色·戒》、《投名状》与《赤壁》为其显著标记的,这类大片在文化的品位上竟出现了令人惊诧的沉落,如《色·戒》其实存在着它自身若干不可克服的矛盾,该片碰到了一个“性、爱情和民族性”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三者的界限模糊不清,由于将性、爱情超越了民族的大义、爱国的大节,这就必然导致王佳芝最后的下场只能落得个纯个人化的悲剧而非历史性的悲剧,她的死其实也只留下了一个“叛徒”的骂名。影片《投名状》首映时,曾被标榜为“中国电影新世纪第一部清末史诗战争巨制”,其故事原型则借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张文祥刺马”。该片所倾力塑造的第一号“史诗”主角庞青云,原系清廷的一名将领,因战败独自落荒逃命,后与赵二虎、姜午阳结义并被尊为“大哥”。在他所生存的年代,恰值清末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之狂飙即将迅速衰落的当口,其人狡诈成性,野心大、城府深,竟以“三结义”之名而行诱骗之实,带领由赵、姜等“揭竿而起”的农民队伍投奔了清廷官府,并被收编为官军,此后乃在其统帅下踏上了为清王朝剿灭太平军而卖命苦战之旅。一路杀戮,历时五年,先克苏州、后破“天京”,立下赫赫战功而平步青云。他曾奉慈禧太后懿旨晋京,由慈禧亲自赏其“黄马褂”并赐封江苏巡抚。就历史叙事在其质的意义上来论说,由李连杰所塑造的这个“史诗”式的英雄角色庞青云,充其量不过是一条效忠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鹰犬,一个双手沾满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军的血腥屠夫民贼。该片的叙事明明关涉到千秋功罪的评说,却偏偏以“掉花枪”的方式,把“春秋大义”十分偷巧地遮蔽起来,转而在亦实亦虚,似史非史的情节里大做文章。其“实”的地方端在兄弟间的信誓旦旦、焚香立状,或反目成仇、绝情残杀;而其“虚”的地方则是将清朝末年历史、政治大局里革命与反动、正义与邪恶、先进与落后等等界限,一律加以模糊化或统统予以泯灭,“虚”到无边无涯,诸如湘军曾国藩、淮军李鸿章等作为剿灭太平军的主力,他们还可耻地勾结了洋人(英、法、俄、美等帝国主义)来镇压革命的太平军,凡此种种,俱被巧妙地“蒸发”出了历史叙事的视野之外,由此也就布成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无史之阵”。
令人费解的是,一些学者却认为《投名状》与《集结号》“渐显国产大片的‘史诗’格局”,“更有可能作为国产大片的里程碑及民族电影的新标尺”②。如若封《投名状》以“大片的里程碑”,总得拿出可以说服人的理据吧。而有的人明明发现《投名状》在无可回避的主要情节上曾涉及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血腥镇压(如屠城杀俘以及攻克“天京”等等),但却为之打圆场,说什么“影片将历史背景隐匿得不错,也就没有太多人会去想这个事情。大家更多的是感觉看这三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否建立起来了,基本不将它看作历史故事,而是人性故事。”而作为这部影片编剧之一并任总监制的人则顺水推舟地说:“我也觉得,普通观众可能糊里糊涂的,比方说三兄弟打谁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历史的感觉,但是普通观众不知道,也许不在意。”如此这般的“对话”,岂不是有意把观众从“有史之境”硬推向了一个“无史之阵”么?笔者要问:我们创作者的艺术良知与评论者的文化良知究竟又该置诸何地呢?!
转眼来到2008、2009年,《赤壁》上下集轮番上映,其总票房达5.8亿元(上集3.2亿,下集2.6亿),不独在国内市场上创下轰动性纪录,同时在日本、韩国及港台地区也都有可观的市场收获,但是,偏偏在北美市场迄今依然是水波难兴。何以然?这一点,不是颇耐人寻味的么!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里,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无论在陈寿的《三国志》里或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所述史实虽有详略之分,但它们所彰显的历史之瑰丽、奇伟,它们所讴歌的英雄人物搏击风云的政治智谋与历史豪情却是浑然而无二致的。吴宇森自好莱坞回归华夏母语文化,首选三国,信誓旦旦,要将魏蜀吴三国“逐鹿中原”这一段亦悲亦壮的英雄史诗重现于银幕,人们对他原本是寄以厚望、抱以期许的。然而,在隔年悬置中,从08年的“暑期档”到09年的“贺岁档”,相继看罢影片上下两集,笔者深有所感的是,电影《赤壁》竟然将这一部流传千载而脍炙人口的民间历史传奇做了所谓“后现代”式的解构与颠覆,令人不觉怆然而失落,愤然而失语。
客观地来评说,吴宇森虽擅长于《英雄本色》式的盗亦有道的“英雄片”及其以枪战(非冷兵器)交火的暴力美学,然而,要进入中国史诗式气壮山河的大格局而纵横自如,则显然尚未做好相应的历史、军事以及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准备。尽管吴宇森在影片叙述里,也曾以奇观化的造型十分机巧地再现了小说里“长坂坡救主”、“智激周瑜”、“草船借箭”、“火烧连环船”等经典段落,但是,当推到全剧的高潮则是小乔“夜闯”曹营的美人计,她以煮茶品茗令曹操贻误战机而战败。火烧连环船以及攻城的场面虽然壮观,到此刻竟成了一块薄薄的历史衬景,叙事的重心只是落在曹操与周瑜共争一个绝色美人小乔,最终小乔自楼顶被赵子龙救下却恰好落入周郎怀抱,如此“结局”果然好不浪漫!看到这里,“赤壁之战”无疑地就被置换为一场特洛伊式的“三角情缘”了,华夏文明的底蕴岂不也就被“解构”到片甲不存了吗?!是的,在吴宇森手里,中国古装大片的创作,竟一味地效仿好莱坞大片娱乐化的叙事套路,成就了一部东西方大杂烩式的商业娱乐大片。
吴宇森曾说过,“我的目标就是能够超越文化和历史背景的隔阂,让西方观众欣赏到‘亚洲版的《特洛伊》’”,“不是把它看作是中国大片或者好莱坞大片,而是世界大片”。③他在上海与媒体的见面会上,又曾一再表白说,(《赤壁》下集)“在情节安排上少了周瑜打黄盖,多了小乔‘色诱’曹操,主要是为了‘照顾’西方观众的口胃,将‘赤壁’演化成人物线索集中又有感情戏的故事。”④凡此种种,吴宇森原本企望东西方对此“西化娱乐版”的《赤壁》都能照单全收的,其叙事的策略和基调因之便是,以西方的“海伦”情结作为主体(或主轴线),而将中国元素则仅仅作为衬底而予以杂糅,还将历史的庄重性解构成后现代式的种种杂耍段子(包括穿插诸葛亮出手救难产的母马、给小马驹命名以及怕鸽子着凉而搧扇子等笑料)的拼贴,这样一种做法,实际上已经将艺术叙事沦为一种工匠式的机械模拟与复制,其间究竟又有多少美学的创意可言则是令人质疑的。
吴宇森在将中国历史虚空化并乌托邦化之后,中国式的华语大片还能剩下些什么呢?说到底,至多是一个“亚洲版的《特洛伊》”,他跳的不过是一种迎合好莱坞的“独脚之舞”,即一只脚让好莱坞套住了,惟好莱坞的大片模式亦步亦趋。但吊诡的是,如此这般的曲意迎合,却偏偏并未得到好莱坞的欢心与接纳。该片分明以北美市场为主攻的目标,但却一次次遭到退回拷贝再剪的冷落与尴尬,对方甚至不讲理地提出,要将“三国”减为“两国”交战则更易于发行,又何其荒诞乃尔?!
但是,恰于此际,颇为让人惊诧的是,竟有人站出来言之凿凿地为这一“世界大片”的做法极力捧场,还撰文论述道:“这一次看《赤壁》,除了场景与明星,人们一定津津乐道的就是它的现代性与娱乐性……恰恰是它的现代性与娱乐性,才真的是吴宇森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又说,“现在影片的处理完全参照了好莱坞影片的写法,周瑜变成了反抗殖民者入侵的义军首领,在战胜了敌人之后有权让敌人‘回到你们来的地方去’,而曹操居然也接受了这番裁决,表现了一个入侵者失败之后的全部懊丧。”在这里,打黄盖的“苦肉计”乃被偷换为小乔的“美人计”,而关云长在华容道“捉放曹”竟被置换为由周瑜亲手大义释曹,如此种种的肆意“改编”,完全丧失了任何可考可信的历史的与性格的逻辑。而对于该片的关键性赞赏则是,“真正的现代性就在于此,即影片是拍给国际看的,导演的思维就不能单纯地只用本国的方式。”⑤——这位业界论者的“关键性”溢美力捧之辞,岂不是令人十分费解而不知其所是所非?!在这里,中国大片文化品位的沉落,不妨被看作是好莱坞文化霸权的单边化、一体化战略正在日渐得逞,由是而在我们九州方圆的大地上日趋奏效,并一点点无声地侵蚀着我们民族文化主体的精神底线。
《赤壁》作为一部商业性娱乐大片固然有其市场生存的合理性,但是,它在国际文化传播空间里,则无疑会对不谙中国历史的外国人造成某种误读或谬读,甚至以为“海伦”情结与东方的“小乔”乃同出一源。以牺牲三国这样文化厚重的东方瑰宝来换取一时的票房“巨无霸”,岂止是巨大的文化资源的浪费,甚至是对民族文化经典的自我践踏。
三 破除文化迷思:以我为主,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对接
在全球性的文化视野里,必须正视的是:好莱坞文化霸权是无所不在的,它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以它为核心从而实现世界文化的一体化(或称“同一性”)。自20世纪70年代起步,到新世纪伊始,好莱坞建立起了高度成熟的电影产业机制及其跨国经济实力,并以全球化的市场营销作为其主导战略,进入了所谓的“巨兽时代”,其霸权的扩张可谓达于巅峰状态。这就必然激起了具有强烈世界意义的众多弱势民族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反弹(诚然也包括以法国为代表的第一世界的一些国家),由此就再一次凸现出一个带根本性的、“逆向运动”的文化命题,即:世界电影的多元性文化汇萃,绝不是靠任何强势文化的恩赐,它恰恰是依托于世界不同国族间文化的互动来实现的,特别是透过各个民族文化自身主体性的伸展,籍此以实现有尊严的、有建树性的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新局面的。
在全球化时代,电影民族化的论题随之就被提升为坚守并弘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新鲜话题,这其实就是一个文化“逆向运动”的命题。正如有独具文化见识之士所看到的:“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还说,“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⑥
如果缺少这种文化逆向运动的自觉或条件,则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就难以成为现实。文化多样性生长艰难之际,则必然是文化趋同性日益得势之时。任何离开民族文化主体性而奢谈什么对西方文化的适应与“融合”,什么“异质文化的趋同与融合”,这里所呈现的不过是一种在文化上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式的迷思。所谓“文化经由碰撞而融合再生”,其实是不可能自动地实现的。“文化经由碰撞”可形成平等的或不平等的两种对话,要么是强势侵蚀弱势,要么是弱势逆向而动,籍由文化多样性的拓展而真正获得“再生”。
胡锦涛主席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曾深刻地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⑦
将中国置放于世界当代文化演进的历史脉络和各种思潮的激荡之中,胡锦涛同志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和谐文化观”,显然,这一立论高屋建瓴,有力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其意义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衡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产业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要遵循建设和谐文化的要求,坚守人文关怀与产业诉求的统一,坚守社会道义与创作自由的统一,自觉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文化责任,努力弘扬自身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努力创作出与时代共脉搏的主流大片,并使之在现代审美的维度上呈现出更富于自主创新、更具有民间亲和力的特色。诚如已故著名文化学者王元化先生所做的论述:“各国现代化的过程,跟不同的文化资源有关”,并指出,“中国的传统有很多可供开发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资源——不仅仅是形式、作风、气派,而是涉及到内质的一种普遍理念的东西。”⑧
中国大片到底怎样才能在全球市场空间里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产业基础,这里,关键的条件是,要靠对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掘和调用,要靠在弘扬自身民族文化主体性上的力度,舍此断无捷径可走。正如文化学者厉无畏所论证的:“文化也是一种资本。……先进的文化、能引起人们共鸣的文化就能带来巨大的增值。”又说,“文化力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权威‘准入证’”。⑨而放弃这一权威的“准入证”则是很不明智的。
在20世纪最后20年间,海峡两岸暨香港三地的中、青年导演的创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贵的实证:他们从传统突围而出,有力地体现出本土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觉醒。当民族性以文化的主体性觉醒而获得新的生机,其电影叙事便以现代性的文化品格和镜像语言而彰显出特异的风采,呈现出“东方新大陆”般的煌煌文化气派,堪称实现了华语电影的世纪性文化整合,跨界而引来国际影坛的瞩目和褒扬。如《黄土地》、《黑炮事件》、《红高粱》、《老井》、《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以及台湾的《悲情城市》、《恐怖份子》、《喜宴》和香港的《蝶变》、《投奔怒海》、《阮玲玉》等等,无不体现出中国历史/社会风尚的变迁及其丰盈的人性美、人情美。集中地说,这些新人新作艺术地发掘并重构了历史本真的“原生态”,以本土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纷纷在诸多国际电影节上摘桂夺冠,呈现出一派东方原初性的人文亮色,率先迈出了走向海外的第一步,并为西方电影学界提供了一个中国电影与现代性相交融的热点话题,其艺术成就赫然卓著。由《黄土地》、《黑炮事件》、《悲情城市》、《喜宴》以及《阮玲玉》等的实践证明,我们所倡导的民族化或民族性,它显然并不是排拒现代性的、自闭式的民族性,而是具有其明朗的开放性的。它以“有容乃大”的胸襟,广泛吸纳并包容了文化现代性的诸多命题(主要是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启迪),它坚持以本土为主体,“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不断充实着并丰富着自身的,由此所唤起的乃是我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张扬。事实上,当今所谓“纯粹的民族性”(即所谓“国粹”),是只能被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的。美籍亚裔著名的文化学者爱德华·W·赛义德主张一种“多元文化观”,他曾论述道:“一切文化中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⑩
但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不是半斤八两、平分秋色的,更不是曲己从人、主宾倒置的。赛义德似乎就此止步,并未能将文化主体性的思考纳入其“多元文化观”之内。在全球化时代,恰恰是透过文化主体性的思考,赋予民族性的命题以新的维度和力量。面对全球化,唯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就是“以我为主”,将艺术家个体融入自身民族文化的主体,从而获得某种超越与升华,并将自身民族融汇于当今世界文化多边对话的大趋势和新格局。倘若一厢情愿地曲已从人、任凭好莱坞怎么“融合”都默许或无所谓,任凭将西方原型与东方元素怎么“混合”也都默许或无所谓,那么,这样炮制出来的影片真的就是不伦不类的,其民族文化的身份必然也是含糊不清的,在任何国际交流或对话的空间里它又能有什么独立的文化品位和尊严可言呢?!
著名文化学者汤一介先生曾在一次关于东方思想的国际论坛上,对于先秦儒家哲人关于“和而不同”的理念,做出了当代学理延伸的阐释,强调“和而不同”应当是21世纪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准则,他说:“如何使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和地域能够在差别中得到共同发展,并相互吸收,以便造成在全球意识下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形势呢?我认为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或许可能为我们提供有正面价值的资源。”他还进一步论证说,“‘和而不同’的意思是说,要承认‘不同’,在‘不同’基础上形成的‘和’(‘和谐’或‘融合’),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11)
这里所谓的一味地追求“同”(即“融合”),大概正是笔者在前文所提及的那种在文化上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式的迷思。在全球化的特定语境下,任何弱势文化在面对好莱坞式的霸权文化时是绝对不可抱有任何幻想或此类“迷思”的,就连法国的文化界人士都对好莱坞秉持着“文化差异”、“文化反弹”的共识,更遑论我们第三世界的弱势国族了。事实上也惟有坚持文化的差异性,强调“和而不同”、存同求异,这无疑正是我们文化的立足点,也正是我们与“好莱坞霸权”相抗衡并争取平等对话之权益的必然选择。任何剥离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好莱坞化”,除了被同一化或被吞噬掉,好莱坞那只隐形的资本之手是断然不会轻轻就放你逃脱的。
随着好莱坞璀灿炫目的镜像奇观风靡全球,凡是具有一定文化判断力的人们,自不免会发出这样的质询:其一,遭遇好莱坞之后,那种早先如影随形、同电影与生俱来的对现实的“渐近线”和“亲和力”,是否正在受到严重的阻隔或削弱,电影艺术家的个性是否正面临着被泯灭的危机,电影的美学品质是否正在被异化而再度沦为娱人声色的杂耍呢?!其二,在大片与好莱坞的“博弈”中,倘若剥离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一味地去效仿好莱坞,亦步亦趋地走“好莱坞化”之路,如此选择显然是既没有出息,又绝对不会有出路的。
汤一介先生前不久曾郑重地重申了一个“多元现代性”的命题,他论证道:“‘现代性’就其根源上说是源自西方,因为西方早已实现了现代化,而且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正是在走现代化的道路。”他深一层论述说,“‘现代性’就是‘现代性’,有着共同的基本内涵,只能是不同民族进入现代化的道路不同,形式有异,实现方法更可能千差万别”。(12)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电影创作里强调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伸张与弘扬,特别就这一文化主体性实践的过程来看,它显然是对于“多元现代性”的一种可贵探索,它既以本土为主体同时绝不排外,更对西方他者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和尊重,尊重他者作为主体在文化上的独特性或差异性,由是乃在全球性多元文化的对话与融汇中实现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对接,并由此而获得了自身文化的更新(或称真正的“再生”)。
时代给予我们的昭示是清晰而有力的,即:惟有坚守我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及其尊严方能自立于世界电影之林。那么,这种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和实质究竟是什么?概括地说,它所凝聚的恰恰是将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与现代人文性的拓展相对接、相交融,这样一来,毫无疑义的,我们历史、文化创造的自觉也就被唤醒了。历史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是,惟有不断提升我们民族文化的主体创新,努力推进电影产业体制机制、电影产品内容形式以及市场营销传播格局的革故鼎新,以高扬我们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并锻铸我们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为了赢得在国际主流电影市场上的民族话语权,我们需要不断地深入发掘本土民族文化资源的“原点”,继续坚持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进取、自主创新的道路,弘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及其尊严。事实上,越是弘扬了民族文化主体性及其东方美学品味的大片,就越是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并且,势必为推进当代世界电影在文化和审美上多边对话的新格局作出我们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注释:
①王宁.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文化批判[A].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8,P28-29。
②李道新.国产大片:史诗格局的渐显[J].艺术评论.2008(2)P35。
③吴宇森.《赤壁》:东西方观众都会认同(记者林莉丽访问实录)[J].中国电影报.2009(1)。
④吴宇森.焦点偏移是“可爱的错误”(记者王磊、邵岭访问实录)[J].文汇报2009.1.8.第7版。
⑤赵军.从《赤壁》看大片的现代性与娱乐性[J],中国电影报.2009(3)。
⑥同①,P30。
⑦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J].文艺报.2006.11.11。
⑧王元化、胡晓明“对话录”:传统资源:具体中的普遍性[J].文汇报.2004.7.18。
⑨厉无畏.文化资本与文化竞争力[J].文汇报.2004.5.24。
⑩爱德华·W·赛义德著,谢少波、韩刚等译.赛义德自选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P 179。
(11)汤一介.中国文化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J].文艺研究.1999(3).P 38-39。
(12)汤一介.寻求文化中的“共通价值”——汤一介教授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讲演[J].文汇报.2009.5。
标签:现代性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主体性论文; 集结号论文; 英雄论文; 梅兰芳论文; 投名状论文; 赤壁论文; 色戒论文; 战争片论文; 史诗电影论文; 武侠片论文; 剧情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