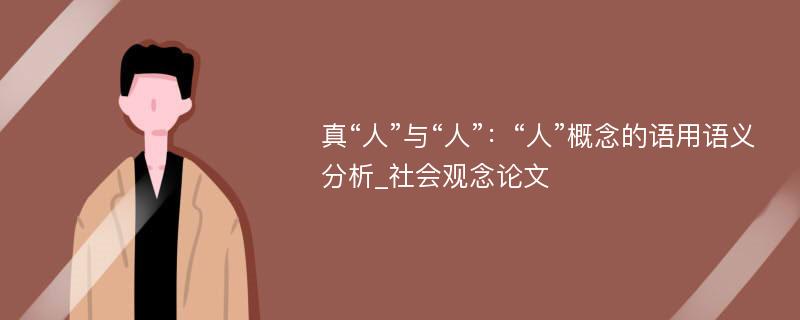
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关于“人”的概念的语用语义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用语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4-0016-08
“一、“人是什么”与“‘人’是什么”
关于“人是什么”问题的任何实质性而非描述性或解释性的回答,都必然会涉及“人 的本质(或本性)是什么”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包括科学和哲学(神学可视为哲学之变体) 在内的人类智慧迄今未能解决的一大难题。考虑到这一点,笔者以为,不妨避难就易, 调整一下问题及其思路,把“人是什么”的问题变换为“‘人’是什么”的问题,以便 在思考人的问题时避开以往那种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及其所导致的困境。所谓避难就易 ,当然只是相对而言,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人是什么”的问题被置换之后,该 问题所蕴含的“人的本质(或本性)是什么”的问题已无需直接回答,因而也就不必再像 以往那样,为那个“人或人的本质应如何定义”的问题去费心纠缠;换句话说,与“人 是什么”的问题不一样,“‘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其追问的对象或着眼点,已不再 是人本身而是“人”这个概念及其意义,因而其答案不要求弄清“人是什么”或“人的 本质是什么”,只要求弄清“人”意味着什么或“人”这个概念的意义是什么,即只要 弄清人们在使用“人”这个概念时所表达的意义(含义)是什么就可以了。
诚然,这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实际上,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或在不同的语用语 义环境中,人们使用“人”这个概念所表示的意义或含义,往往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 不仅如此,这种差异有时甚至表现在同一场景的同一语句中,例如,在人们多少有些耳 熟的“那个人真不是人!”这句话中,前后两个“人”所表示的意思就是迥然有别的。 与此有关的一些情况及其所涉及的问题,本文将在后面作进一步的分析讨论。这里笔者 要强调的是,尽管“人”这个概念可以被用来表达不同的思想内容,其实际的意义或含 义可以有多种多样,但在特定的语用语义环境中,它的意义或含义还是比较容易为人们 所把握和确定的。正因为如此,人们之间才有可能使用“人”这个概念进行思想交流。 如果说,那个“人是什么”及其所包含的“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因其所固有的形 而上的性质,难以进行科学的实证分析并求得相对确定的答案,只能任其在哲学思辨的 领域中继续“百家争鸣”下去的话,那么,这个“‘人’是什么”即“人”的概念意味 着什么的问题,则更多地带有形而下的性质,因而是可以借助于经验科学的方法进行分 析并找到相对确定的答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用“‘人’是什么”置换“人是什么” ,把“人”的概念及其意义作为分析的重点,既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同时也是一种 研究方法的调整。
关于“人”这个概念及其意义的分析,必然会涉及语词概念与思想概念两个方面,因 而从方法论合理性的角度考虑,选择一种较有解释力的语言意义理论是至关重要的。语 词概念(名词或术语),通常是用来表达相应的思想概念(思想内容或观念)的,而思想概 念则是人们头脑中对于相应的现实存在(或称“实在”)的反映、理解、重构及其产物, 由此形成了“语言—思想—实在”三者之间的复杂联系。仅此一点便足以说明,无论是 关于语言指示实在的“指示理论”,还是关于语言描画实在的“描画理论”,其有效性 及合理性都是颇成问题的。大家都还记得,著名哲学家L·维特根斯坦在后期放弃了他 原先曾主张的关于语言意义的“描画理论”(Picture theory)或“图像论”,转而倡导 由语言的实际用法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由语言对实在的描画关系来确定语言的意义,“在 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不是所有情况——我们使用的‘语义’一词,可以这样来定义: 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注:参阅L·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三 联书店,1993年,第31页。)虽说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的这一变化,不过是20世纪上 半叶语言意义理论发展变迁的某种缩影,但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语言毕竟是 一种既为别人同时也为自己存在的实践的意识,其直接的功能和意义在于表达并传递思 想,因而相比较而言,这种基于语言实际用法的语言意义理论,无疑更具有合理性和解 释力。因此,关于“人”的概念及其意义的分析,必须从作为语词概念的“人”入手, 即通过分析“人”这个语词概念的不同用法,以确定它的不同意义或含义即它所表达的 不同思想内容(作为思想概念的“人”),进而通过分析作为思想概念的“人”(即人们 头脑中所理解的“人”)的不同规定性及其差异,弄清它们所由以形成的多样性原型及 其现实基础。这项工作决非一篇文章所能完成,本文的主要意图是提出并倡导这样一种 新的研究思路,其中所做的有关分析和论述只是些初步的尝试。
读者也许会问,把“人是什么”变换为“‘人’是什么”,有什么必要呢?或者说,这 种变换是否真的意味着一种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思路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从问 题的表述形式上看,新的问句只不过是在原有问句的主词上加了一个引号,但这决不是 一种无关紧要的“文字游戏”,因为问题及其提法的这种变换,意味着把“人”的概念 及其意义作为分析思考的重点,而这恰恰是以往的思想家们所忽视的。“人”这个概念 的使用频率之高,是众所周知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献著述或许有所例外,在人文科学 或社会科学方面,恐怕古今中外还没有哪一部著作是不与“人”打交道的,而人们的日 常生活更是几乎每天都会提到“人”。人们谈论“人”,却未必真正明白自己在谈论什 么。人们使用“人”这个概念,却不一定清楚这概念意味着什么。这样说并非耸人听闻 ,这种情形实际上是相当普遍的。类似的现象曾被哲学家们称之为“语言的迷障。”人 们往往是处在语言迷障之下而意识不到自己被迷障。在理论思维以及在日常意识的领域 中,许多与人的问题有关的分歧或争议,往往是因为未能澄清“人”的概念的不同用法 及其意义所造成的。任何有效的以语言为中介的人际交往或思想交流过程,都有某些相 对稳定的语用语义规范可循。当然,一项研究只能涉及有限的范围,不可能一一检索并 罗列出“人”这个概念的所有各种不同用法及其意义,但要讨论或思考人的问题,就必 须了解并阐明“人”的概念的一些基本用法及其意义。这对于摆脱“语言迷障”达到思 维的确定性和清晰性,无疑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
不仅如此,通过语用语义分析澄清“人”的概念,将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 视“人是什么”的问题。人们头脑中的“人”是以现实世界的人作为基本原型的,虽说 两者之间往往并不一致,但人们除了用自己的头脑(思维)去理解和把握现实世界的人之 外,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途径。因此,“人”的概念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是与 人是什么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按照那些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近代思想家们的理解,人 生来就是独立、自由、平等、利己的,而这种所谓“合乎自然的个人”,既是社会历史 本身的起点,同时也是社会思考的逻辑起点。包括古典经济学和近代社会契约论在内, 都是以这种天生独立的个人作为出发点的。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西方大多数思想家所理 解的“人”的概念。透过这一概念的语用语义背景及其所关涉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其 真实含义、恰当性及适用范围,是不难鉴别和判定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 判>导言》中所分析的那样,这些思想家头脑中的“人”的概念,是对16世纪以来就进 行准备并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某种预感,他们当作历史起点的所谓“ 合乎自然的个人”,实际上只是近代社会历史变迁的产物和结果,而那些被他们视为“ 人类天性”或永恒本性的东西,不过是由近代社会历史进程所赋予人的规定性(注:参 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87页。)。马克思对这些近代思想家所理解的“ 人”的概念所作的分析澄清,不但深刻地揭示了他们所说的“人”的真实含义和实质, 同时也为我们思考人是什么以及人的本质或本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二、“人”的概念规定的多样性
关于“人”的概念及其意义的分析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从语词概念的用法入手可视 为一种方法论上较具合理性的选择,因为对相关语用语义背景的分析是把握语言意义的 基本途径。当然,这只是从语词概念进到思想概念的必要步骤,还不是概念分析的重点 所在。一般说来,作为语词概念的“人”,即“人”这个名词或术语本身,虽然因语言 文字方面的差异,往往有不同的读法(语音)或写法(字符),例如在汉语中读作“Ren” ,写作“人”,而在其他语言中就不一样了,但这些不同的读法或写法是可以相互通译 的,即语音或字符方面的差异,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同一个语词概念(名词或术语),因而 就“人”这个语词概念本身而言,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的可能性。可能存在实质性差异 的,是作为思想概念的“人”,即人们头脑中所理解或所设想(构想)的“人”。正像大 家所熟悉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作为语词概念是相同 的,而作为思想概念却是不同的。由于相同的语词概念(名词或术语)可用来表达不同的 思想概念(思想内容或观念),且此种情形无论在文献著述还是在日常语言中都相当普遍 ,因此关于“人”的概念及其意义的分析,除了从语词概念进到思想概念,揭示“人” 这个相同的语词概念所表达的各种不同思想概念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弄清这些作为 不同思想概念的“人”的具体含义及其规定性,阐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实质性差异, 以及它们各自可能具有的特定的认识实践功能。
说到人们头脑中的“人”(作为思想概念)可能包容的多样性及其实质性差异,其实是 很容易理解的。当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或以不同的标准去理解人时,他们心目中所形成的 “人”的概念(观念)或形象不可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逐一掂量 几乎是因人而异的各种各样的“人”及其差异。对概念分析来说真正重要的,只是其中 那些带有实质性的差异。这方面似乎还不曾有前人作过专门的论述,所以笔者无法像某 些读者可能期待的那样引经据典,只能基于学理上的思考、体会或感悟做些不那么“学 术味”的阐述。为便于分析和叙述,可将“人”的概念之间的各种实质性差异划分为两 大类,一类是不相容的或互拮的,另一类是相容的或互补的。
所谓“不相容的或互拮的”,意即存在着这样一些关于“人”的概念,它们相互之间 有着实质性的内在矛盾或不可兼容性,或者说,人们不可能同时接受它们而不违背起码 的思维整合性原则。一般来说,那些对人是什么以及人的本质或本性之类的问题有着截 然不同理解的人们,他们头脑中的“人”的概念或观念必然无法相互兼容。即使这些人 不是思想家或学者,他们也会由此形成人生观及为人处事准则方面的相互抵牾,因为这 种日常意识水平的“人”的概念或观念,是一种被意识到了的有待付诸生活实践的自觉 的人格标准或形象,譬如说,对于一个以“利己本性”诠释“人”的概念、信奉“人不 为己,天诛地灭”的人,恐怕很难指望他能够自觉地为他人做出贡献或牺牲。如果这些 人是所谓思想家或学者,那么,由于涉及人的问题的各种思考、推理或论证过程,都是 以对于人的理解作为基础概念和出发点的,思想家们头脑中所存在的无法彼此兼容的“ 人”的概念或观念,必然会导致他们在基本观点及理论体系方面的相互矛盾和对立。
话说回来,假如思想家们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并自觉地表明或承认,他们所谈论的实际 上只是人的某种具体的社会历史规定性,或者只是某种特定时间空间范围内的人,上述 不相容的情形原是可以避免的,可问题恰恰在于,思想家们似乎缺乏这样的意识和自觉 。对于那些习惯于在理性思维领域中摸爬滚打的思想家们来说,从个别进到一般、从特 殊进到普遍已经是一种职业本能,醉心于建构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人”的概念规 定也是无可非议的,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在这个“从经验上升到思辨”的概念建 构过程中,并没有严格遵循合乎逻辑的科学抽象程序,而是借助于某种“思想跳跃”的 方式完成的,其基本方法论特点是:直接地把个别变成一般、把特殊当作普遍,亦即用 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人(特殊)去冒充所谓“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规定(普遍)。此处仅举 边沁和费尔巴哈为例,都是马克思曾经分析过的,前者“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 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后者把 德国人当作“一般的人”或“人本身”——“‘人本身’实际上是‘德国人’”。(注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由于各自所依据的现实原型不同,他们 心目中的“人”的概念或观念也就难免相互径庭,边沁的“人”所遵循的是某种实实在 在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原则,而费尔巴哈的“人”则以理智、意志、情感作为基本规 定性而不愿为“不洁的利己主义”所玷污。从思想史上看颇多类似情形。某一时代的思 想家通常只能以自己所处时代的人(特殊)作为原型来刻画“人”的概念(普遍),不同时 代的思想家们所建构的“人”的概念往往难以相互兼容,而常见的结果是后人不满意前 人并对前人进行否定或修正,并由此导致思想史上“人”的概念及其理论的不断推陈出 新。顺便说一句,把生活在近代社会的特殊类型的人设定为一般的人及其概念规定,进 而把由近代社会历史进程赋予人的特殊规定性视为人所固有的自然本性,这个借助于思 辨思维从特殊“孵化”出普遍的过程,正是近代抽象人性论得以形成的重要方法论根源 。
所谓“相容的或互补的”,意即存在着这样一些关于“人”的概念,它们之间虽有实 质性的差异但却并不相互矛盾或抵牾,或者说,它们对于以人为对象的思维过程来说都 是有效的和必要的。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概念规定的多样性,与关于人的描述性分析 的多样性还不是一回事。人们常说人是直立行走的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或者说人是 社会动物、理性动物、情感动物,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各有其道理的而且并不相互排 斥,因而也是“相容的或互补的”,但这只是从不同方面或角度对人所作的描述性分析 的多样性,严格说来还不是关于“人”的概念规定的多样性。当然,从生物分类学的角 度来看,这些说法当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而且从分类学上确 定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以及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也是必要的,但关于这些区别及 其特征的各种描述性分析,所勾画的只是同一个概念即“人”的普遍的类概念,它们之 间的差异及多样性并非不同概念之间的差异及多样性。
一般说来,在特定的语用语义背景(包括文献著述的上下文联系及整体思想关联等)中 ,“人”这个语词概念意味着什么或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概念,是比较容易确定和把握的 ,其具体思想内涵及外延并不需要专门加以界定。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概念界定,概念 划分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但通过对不同语用语义背景的分析比较,仍不难发现一些具 有实质性差异的“人”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彼此兼容或互补的关系。最常见的例子 是,“人”的概念在逻辑上表现为普遍(全称)概念、特殊(特称)概念或个别(单称)概念 的多样性,它们之间的差异有时是借助于相应的量词特征来标示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 则是量词往往被省略,因而弄清“人”究竟是普遍性概念还是特殊性概念抑或是个别性 概念,就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虽说大多数情形可能比较简单,仅凭日常智慧应付起 来也已经绰绰有余,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人”的概念的这种可相互兼容的多样性 。另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是,“人”的概念在内容上,往往有作为生物学生命之“人” 与作为人格生命之“人”的实质性差异(或多样性),前者不过是生物分类学上属于脊椎 动物门—哺乳类—灵长目—人科—人属的有机体,实际上只是一种“生物的人”,后者 则是具有自我意识或理性并在道德及法律上承担一定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主体,因而是 一种“社会的人”。这两种意义上的“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诸如“人的骨骼”、 “看到人来了”、“人能够直立行走”等语句中的“人”,主要是指“生物的人”,因 为作为人格生命的“人”是没有骨骼、既看不到也不会直立行走的;而像“人的权利与 义务”、“人的道德责任”等语句中的“人”,则一般是指“社会的人”,因为作为生 物学生命的“人”是既没有权利与义务也无需承担道德责任的。20世纪生命伦理学领域 中的两大争议,即关于胎儿(胚胎)算不算“人”或人工流产是否有违道德与法律,以及 如何判定“人”已经死亡或以脑死亡者作为器官移植供体是否合乎道德与法律的争议, 都是与上述两种彼此不同的关于“人”的概念规定紧密相关的。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不 便扯得太远。本文拟作为重点加以讨论的,是另外两个关于“人”的概念,即实然之“ 人”与应然之“人”的实质性差异,以及它们在人类思维过程及人文社会科学中所起的 作用。
三、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
当然,关于“人”的概念的这一划分主要基于抽象的概念分析,——所谓实然之“人 ”与应然之“人”,并不是同时并存于现实世界中的两种彼此不同的人,而只是思维领 域中的两个彼此不同的关于“人”的概念或观念。“应然”即意味着尚未“实然”,只 有实然之人才是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人,才是“人”的概念据以形成的现实原型和出发 点。既然如此,人们头脑中又何以会形成上述两个彼此不同的关于“人”的概念或观念 呢?这个问题已涉及人类思维特别是概念形成过程中所特有的某种可称之为“二重化” 的现象及其机制。虽说关于概念“二重化”的具体机制,迄今还没有从哲学认识论上得 到必要的揭示和阐明,但概念“二重化”的现象却是相当普遍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 多概念,特别是那些与人以及人的职业、身份等等相联系的概念,相当一部分都是表达 “二重化”思想含义的概念。例如,当人们对某位父亲、某位教师、某位干部、某个人 甚或自己表示严重不满时,往往会说“他哪是个父亲!”“他哪是个教师!”“他哪是个 干部!”“他哪是个人!”“我真不是人!”等等。也许,这只是些哲学家们不屑于深究 的常识性例子,但其中所蕴含的某些道理却是有待思考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不具有父 亲身份、教师身份或干部身份的人,上述相应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对非人事物例 如一棵树说“它哪是个人!”毫无意义一样。显然,诸如此类的说法要有意义必须满足 两个条件,即主词与谓词之间,必须既具有某种肯定性关联,同时又具有某种否定性关 联,而这样一来,它们的展开形式就成了一些在逻辑上相互矛盾的双重判断:“他是父 亲——他不是父亲”、“他是教师——他不是教师”、“他是干部——他不是干部”、 “他是人——他不是人”、“我是人——我不是人”。仅从语词及语句结构看,这些双 重判断似乎都具有“S是P而且S不是P”的自相矛盾的形式,但从实际思想内容看,—— 如果把由同一语词概念所表达的两个不同思想概念分别记作P1、P2的话,那么,这些双 重判断的基本结构就相当于“S是P1而且S不是P2”,因而并不包含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换句话说,这些双重判断中的“父亲”、“教师”、“干部”、“人”,都是些表达“ 二重化”思想含义的语词概念,就其与主词之间的肯定性关联而言,它们所表达的是经 由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具有实然含义的描述性思想概念,就其与主词之间 的否定性关联而言,它们所表达的则是经由从现实到理想的提升建构而形成的具有应然 含义的规范性思想概念。这就是概念“二重化”现象。
那么,人类思维中的许多概念为什么会被“二重化”呢?考虑到这里所讨论的概念“二 重化”,主要是指概念被“二重化”为实然含义的概念与应然含义的概念,我们不妨进 一步作如下假定,即那些与人的存在、活动及其结果没有任何联系,仅以非人事物的存 在、变化及其结果作为现实原型而形成的概念,通常是不可能在上述意义上被“二重化 ”的,因为对于完全缺乏自觉意识或自由意志的各种非人事物,除非我们引入人类自身 的价值追求及其评价标准,谈论它们应该或不应该如何的问题,就像谈论牵牛花是否“ 应该”爬在墙上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尽管人们有时也会说出诸如“猫应该捉老鼠而不 应该捉小鸡”之类的话,但“应该”(或“不应该”)一词的这种用法完全是童话式的, 生活的童话色彩往往会赋予某些无意识意志的非人事物以人格特征,而关于“应然”问 题的分析是不能以此作为根据的。只有以人类自身的存在、活动及其结果作为现实原型 ,才会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具有实然含义与应然含义的“二重化”概念,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在描述性概念基础上能动地建构规范性概念的“二重化”过程,往往是必要的甚 至是必然的。
作为具有意识意志或自由自觉特性的行为主体,人类不但会在头脑中形成关于自身存 在、活动及其结果的实然状态的概念或观念,而且必然会通过概念“二重化”机制,进 一步形成关于自身存在、活动及其结果的应然状态的概念或观念。这两类彼此不同的以 是如何与应如何、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为思想内容的知识(概念或观念),对于人类来说 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类认识世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目的或意图改变世界,而所谓改变世 界(包括改变人类自身在内)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使世界从人类所面临的实然状态 向人类所期待的应然状态转化的过程。人们之所以会对自己或他人的存在、活动及其结 果感到满意或不满意,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上的关于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的相互对照 比较。城市的一座标志性建筑竣工了,多数市民感到比较满意,那是因为该建筑的实然 状态比较符合他们心目中所期待的应然状态;相反,如果预先所构想或期待的应然状态 未能转化为实然状态,人们就会感到不满意。像城市建筑这类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结果的 有形事物,无论是对其实然状态的描述反映,还是对其应然状态的理想建构,在人们头 脑中所形成的都是些具体的观念形象。除了具体观念形象的领域之外,关于实然状态与 应然状态之间的观念上的比较对照,也同样适用于抽象概念规定的领域。以前面提到的 “父亲”、“教师”、“干部”为例,这些都是由特定社会关系赋予人们的社会职能身 份(法律关系上的“父亲”属于社会职能身份),而任何关于社会职能身份的概念规定都 具有“二重化”的思想含义,即一个社会对诸如“父亲”、“教师”、“干部”之类的 社会职能身份,除了有着相应的实然规定及描述性判据之外,还必然有着相应的应然规 定及规范性要求或期待。当然,各类词典通常只提供关于语词概念的描述性解释,而语 词概念所表达的规范性思想含义往往被忽视,例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只有关于“ 父亲”是生养(或领养)有子女的男性、“教师”是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干部”是担 任一定领导或管理职务的人员等描述性规定,而没有诸如“父亲”应尽抚养教育子女之 责,“教师”应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干部”应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等规范性内容。但是 ,可以按照上述描述性判据确认的实然含义上的“父亲”、“教师”或“干部”,不一 定就是符合规范性要求或期待的应然含义上的“父亲”、“教师”或“干部”,这个道 理人们是很容易也是经常可以体会到的。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继续讨论“人”的概念的二重化问题。为便于叙述,前面曾经提到 的生物学生命之“人”与人格生命之“人”的差异将被省略,因为这里所说的被思维当 作现实原型或出发点的人,可视为人的生物学生命与人格生命、社会规定性与自然规定 性的统一体,即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科动物。只要是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科动物都 是实然之人,无论其年龄、性别、种族、国籍抑或语言文化、家庭出身、健康状况、受 教育程度、智力发展水平等等有多大差别,都可毫无例外地归属在实然之“人”的概念 之下。实然之“人”的概念作为关于人的普遍概念或类概念,像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其他 许许多多普遍概念或类概念一样,在方法论程序上,是通过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 遍的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其概念规定只是描述或反映了人的一般共性规定或人所共有的 一般规定性。不用说,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实然之人的存在,也就不会有实然之“人”的 概念或观念,而没有实然之“人”的概念或观念,即使再富有想象力或创造力的头脑, 也不可能完全凭空臆造或构想出应然之“人”的概念或观念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应然 之“人”的概念须以实然之“人”的概念作为描述性基础,但它们据以形成的方法论程 序却是很不一样的。与实然之“人”的概念不同,应然之“人”的概念并不是经由从个 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抽象概括,而是经由从描述到规范、从现实到理想的提升建 构而形成的。这种方法论程序上的独特性,甚至可以说是由应然之“人”的概念规定及 其本性所决定的。
大致说来,以外部世界实然之人的存在作为现实原型并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实然之“人 ”的概念或观念,是一个思维能动地描述或反映存在的过程,像一般科学认知过程所要 求的那样,实然之“人”的概念形成过程必须严格遵循对象性事实决定的原则,即其概 念规定必须如实地反映并符合作为对象性存在的实然之人本身所固有的规定性。但这还 不是“人”的概念的二重化过程。所谓“人”的概念的“二重化”,指的是人们在头脑 中以实然之“人”的概念或观念作为思想原型(思想素材)并进而形成应然之“人”的概 念或观念。这是一个思维能动地建构或塑造关于“人”的理想性概念的过程,其特点是 在对象性事实决定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并遵循主体性价值决定的原则。就像艺术 创作主体基于特定的审美追求或期待,把源自生活即具有事实意义的“生活的真实”提 升加工或塑造为高于生活即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的真实”一样,虽说形象思维与概念 思维有所不同,但无论艺术形象还是理性概念的思维建构过程,都少不了主体性价值内 容的渗入,这个道理恐怕还是相通的。人类在以自身作为思考对象时,除了探究“人是 什么”的问题并对“人”作出描述性界说之外,还必须探究“人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并 对“人”作出规范性界说。正是由于把人类主体对于自身的规范性要求和期待等主体性 价值内容及其判定标准纳入了关于“人”的概念规定,“人”的概念才从实然含义的概 念被真正提升建构为具有应然含义的概念。换句话说,“人”的概念的二重化即实然之 “人”与应然之“人”的概念规定及其差异,是人类自身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现实 存在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差异在思维领域中的反映及其产物。
四、应然之“人”与人文社会科学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中,不管思想家们是否意识到,“人”的概念的二重化都 是一种潜在的方法论模式,而关于应然之“人”的概念规定更具有核心概念的重要性。 当然,从思想史上看,虽说许多思想家都曾经明确区分“是什么”与“应如何”的问题 ,并由此引出了关于事实与价值的两类不同学科知识及其分野,但对于“人是什么”与 “人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却缺乏有意识的或明确的划分,尤其是在自然主义的本质( 本性)论思维方式的主导之下,“人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往往被归结为“人是什么”( 诸如“人生来是什么”或“人的自然本性是什么”等)的问题,——由于人之应然(应该 如此)已被归结为人之本然(本来如此),而人之本然不过是某种被特定化了的人之实然( 实际如此),思想家们在从“人的自然本性”过渡到“合乎自然本性的人”,即从“人 本来是……”过渡到“人应该是……”时,并没有明确引入关于实然之“人”与应然之 “人”的概念设定。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未被意识到的潜在的方法论模式,“人”的概 念的二重化仍在人文社会科学思考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诚然,我们不可能详细罗列 思想史上各种关于“人”的概念规定,更不可能逐一甄别判定它们当中何者相当于实然 之“人”、何者相当于应然之“人”。我们在这里想要指出的只是,包括所谓“自由自 觉的人”、“理性的人”、“独立自由的人”、“权利平等的人”等等在内,这些在人 文社会科学中最常见因而也是最基本的关于“人”的概念规定,决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 的那样是描述性的,它们与其说是对于实然之人或本然之人的某种客观描述,还不如说 是关于应然之人的某种理想建构,其中所包含的人类对于自身的应然期待是不言而喻的 。任何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都有着自由与不自由、自觉与不自觉、独立与不独立、 平等与不平等相统一的双重规定性,而且从以往的人类历史进程来看,人的不自由、不 自觉、不独立、不平等,甚至可以说比人的自由、自觉、独立、平等有着更为广泛的经 验性存在。思想家们之所以更愿意强调和突出人的自由、自觉、独立、平等,并把它们 作为“人的本性”纳入关于“人”的概念规定,是因为他们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意识到 了人的自由、自觉、独立、平等的稀缺性,正是这种“稀缺性”使自由、自觉、独立、 平等成为人类对于自身的价值追求和应然期待。
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是否也有关于应然之“人”的概念设定呢?笔者的答案是肯 定的。大家都还记得,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曾经构想过 某种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目标的“作为人的人”、“合乎本性的人”或“真正的人”,并 由此提出了如何使“人的存在成为人的存在”、“人的行为成为人的行为”、“人的需 要成为人的需要”、“人的效用成为人的效用”、“人的感性成为人的感性”,以及如 何使“人真正成为人”、“人解放成为人”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在他(当时)看来,实然之人即现实世界中实际存在的人,还不是“真正的人”或“作为 人的人”,而是某种处于异化状态的人或“异化的人”,因而其存在、行为、需要、效 用、感性等等,还不是合乎本性的或真正的人的存在、行为、需要、效用、感性。以本 文作者的理解,这种在现实世界中尚不存在的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目标的“真正的人”、 “作为人的人”或“合乎人的本性的人”,正是一种由思维所建构的关于应然之“人” 的理想追求和价值期待。诚然,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的那样,马克思早期的一些著 作受旧哲学特别是人道主义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但我们恐怕不能仅仅因为这一点,就 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于应然之“人”的概念设定及其重要意义。虽说随着唯物史观 的创立,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 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已极少使用诸如“作为人的人”、“真正的人”之类的术语,但 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关于应然之“人”的概念设定,恰恰相反,“人的解放”、 “人的自由个性”以及“自主活动的人”、“自由的人”、“全面发展的人”,始终是 马克思主义所追求和期待的人的发展的理想目标。换句话说,以唯物史观的诞生为标志 ,马克思所经历的思想转变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无关于应然 之“人”的概念设定,而在于如何设定和论证应然之“人”的概念。大致说来,人道主 义主要依据本然来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某种关于本然之“人”的抽象假定出发,由“ 人”的本然状态(“人本来是什么……”)导出“人”的应然状态(“人应该是什么…… ”),而马克思主义则主要依据必然来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实然之人的真实存在出发 ,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依据,来设定和论证人自身发展的应然目标如“ 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个性”、“人的全面发展”等等。与人道主义不同,马克思主 义学说中所包含的应然之“人”的价值目标和理想,已不再是“人”的概念推演过程的 某种逻辑结果,而是以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