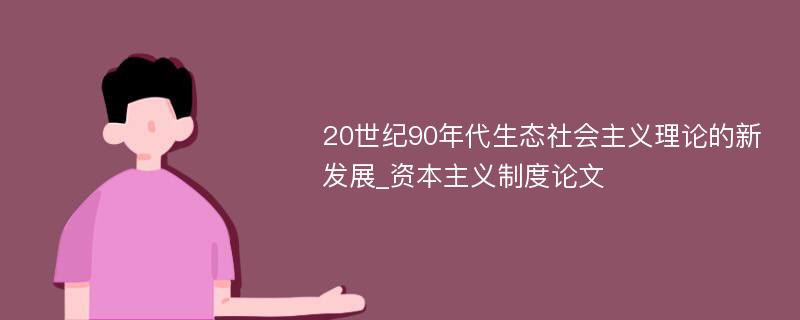
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发展论文,生态论文,年代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生态问题的日趋严重,西方兴起了一股批判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要求保护环境,建立一个符合生态发展规律的社会思潮,这股思潮很快同社会主义相结合,从而出现生态社会主义思潮。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自70年代产生以来,经过80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到90年代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其理论主张更加成熟。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途径的思考及对未来社会的经济构想等方面,都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理论,成为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引入注目的思潮和流派。
(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深刻
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一直是生态社会主义者首先关注的问题。
长期以来,西方生态运动者总是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科学技术、归咎于工业化,过分夸大科技的负面效应,把工业制度作为批判的直接对象。尽管他们也意识到生态危机与资本家贪得无厌地追逐利润的本性有关,但却不能就此深入观察现象的本质,而是片面地认为正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毁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因此,他们大都崇尚“回到丛林中去”的浪漫主义自然观,要求人们回到乡村去,用手工劳动去取代现代化大生产,用分散的小生产同现代化的大生产相抗衡。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大都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有消化全球生态危机的能力,因此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内以自由市场、分散化的经济、基层民主来对资本主义进行局部改造。其代表人物莱易斯、阿格尔等人就曾提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模式,设想“一种能把某些生产部门的自动化与其他部门的小技术结合起来的混合技术方案”(注:[加]本·阿格尔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498页。), 号召人们“从小规模的生产和工艺式的消费中得到快乐”(注:[加]本·阿格尔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491页。),以此来向生态社会转变。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触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它只是一种改良主义形式的批判,而且具有“开历史倒车”的倾向。
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则要深刻、激进得多。他们认为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去寻找原因,而不是片面地把生态危机归咎于科技的进步和消费的异化,因此,他们大都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对大自然的统治与掠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欠下了生态方面的巨大债务。现在它们仍以占世界25%的人口消耗着占世界75%以上的能源和80%以上的原料。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造成目前地球升温的罪魁祸首,它们所释放的日产温室效应的气体占全世界释放总量的2/3。在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家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导致了奎尼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制度不断地吞噬着它所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注: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第231页。 )英国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大卫·佩珀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所谓‘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成了不可实现的梦想,并且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注:[英]大卫·佩珀著:《生态社会主义:从纵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伦敦洛特雷出版社, 1993年版,第95、96、232—233、232页。)
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加深刻的原因在于:从绿色运动内部来看,80年代末90年代初,绿色运动内部出现了“绿绿派”和“红绿派”的分野。“绿绿派”以绿色党为代表,“红绿派”则以生态社会主义为代表,表明生态社会主义已发展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同时其内部的激进力量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看,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达剧变,传统(或现实的)社会主义受挫,欧洲政治风向普遍右转。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一些共产党、社会党采取与绿色运动结盟的政策,解体后的共产党组织的不少成员加入了绿色组织,出现了“红”色绿化的现象。这一方面在客观上起到了抬高生态社会主义身价,尤其是提高它在绿色运动内部的地位的作用;另一方面,原共产党人加入绿色组织,也使得绿色运动中的左翼力量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响扩大,从而使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能够更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更加深刻的批判。
(二)政治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更为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他们形成了一套更加完整、系统的政治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方面,更加重视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由于受资本主义的歪曲满足需要本质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已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了追求无限消费的习惯,被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一体化”了,已丧失了自身的革命性、否定性和批判性,因而暂时还不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变革的主力。意大利的卡斯特林那认为在本世纪以来,尤其是在“福利”时代,“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获得的利益使它把那些从它专注于资本主义劳动而衍生出来的价值原则看作是积极的东西——对生产力发展的绝对信仰,由社会精英所诱导出来的竞争品格,纪律和权威的等级观念以及生活领域相当保守的观念。”(注:[南]米洛斯·尼科利奇编:《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特别强调“生态意识”,认为只有那些既热衷于生态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又关心社会主义前途的人,才能领导和推进这场革命,他们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广大的“中间阶级”即中小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和青年大学生身上。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导致西方大量的“中间阶级”普遍右转,纷纷倒向民主社会主义一边。在对中间力量的“领导”作用丧失信心后,生态社会主义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组织上。尽管他们仍不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却也意识到,工人阶级由于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受环境污染最重,因而最具革命性,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较之于70、80年代,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更加重视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组织的作用,这是其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之处。在社会主义变革的承担者方面,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安德列·高兹认为,“新社会运动”不自觉地和具体地攻击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的统治,当它与无政治权利的、受压迫的、处境悲惨的无产阶级包括后工业社会的失业的无产阶级,偶尔被雇佣的,短期的和半天制的工人结盟时,“新社会运动”将成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承担者。(注:周穗明:《生态重建与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载于《新视野》(京),1996年第6期,第60页。)因此, 他提出了欧洲左翼应与“新社会运动”结盟的建议。
此外,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还特别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反生态帝国主义运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反环境种族主义运动、妇女运动等社会力量应联合起来,形成一支世界性的“反资本主义体系力量”。
2.在社会变革的途径方面,既坚持“非暴力”原则,又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非暴力”是“新政治学原则”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它来源于马丁·路德·金的信条“我们已经再也不可能在暴力和非暴力之间进行选择,只能是或者非暴力,或者死亡。”“非暴力”有两重含义:一是反对统治阶级使用暴力,二是反对被统治阶级使用暴力。70、80年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非暴力是生态运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注:[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著:《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78页。),他们把甘地的“无所谓和平之路,和平本身即为道路”当作座右铭,甚至认为“‘敌人’像我们一样是有缺点和错误,有友谊和力量的人民;他们是父亲和母亲、女儿和儿子,是俱乐部成员,是学生,是工人;他们有欢乐和苦恼,他们会争吵和和解;他们可能受煽动,他们可能进行抵抗,他们服从和怀疑;他们像我们一样希望过和平生活。”(注:[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著:《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120—121页。)但是这种一味迁就、忍让,甚至不分原则是非的所谓“非暴力”的斗争方式,在生态运动内部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质疑,认为它不可能引导生态运动取得斗争的胜利,而只会造成一种无谓的、不必要的牺牲。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苏东剧变,“红”色绿化现象盛行,生态社会主义内部的革命成分增多,部分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社会变革的途径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非暴力”只能是一种斗争的策略,如把它变成一种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那只能使人们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遭到大量的不必要的牺牲,因为反动阶级是不会因为你放弃暴力而不使用暴力的。因此,尽管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仍然把“非暴力”作为实现未来社会变革的一条基本途径,但也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如罢工等)来作为其它政治斗争形式的补充。然而,尽管发生了上述变化,大多数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仍持这样一种观点,“在资本家仍然控制国家的情况下,试图用暴力去推翻资本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先应接管国家,并将其改造为以某种方式为全体服务的机构。必须将达此目标的手段限定在这种范围内,即用教育和示范生活的方法去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注:[英]大卫·佩珀著:《生态社会主义:从纵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伦敦洛特雷出版社,1993年版,第95、96、232—233、232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在未来社会变革的途径问题上,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仍未摆脱改良主义的泥潭。
3.在对基层民主和分散化原则的考虑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基层民主原则是“新政治学原则”的四大支柱之一。西德的联盟纲领曾指出:“基层民主的政治学意味着,更多地实现分散化的直接民主。我们的出发点在于,认为基层的决定原则上必须予以优先考虑;我们给与分散化的、易于管理的基层单位以具有深远意义的独立和自治的权力……。”(注:[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著:《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68—69页。)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作为基层民主的特征是未来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人物本·阿格尔指出:“我们的两个主要概念即‘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既适用于技术(生产)过程又适用于社会和政治过程。我们认为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注:[加]本·阿格尔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1 版, 第499—500页。)
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植被破坏、土壤流失、酸雨肆虐、地球升温、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等社会问题早已超出一国界限,变成全球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的政治、经济及生态问题“是不能在地方基层层次上得到解决的,……区域的、国家的、乃至国际的计划是必要的。……更进一步说,如果将生态学的概念扩展到城市环境,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一般公共生产条件’,那么诸如城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房租昂贵、毒品交易此类的问题,本来是可以由地方解决的,但现在均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了。”(注:奥康纳:《生产的外在自然条件》,载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1991年版第1卷,第34 页。)而且,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也都普遍认识到,那种主张实行基层直接民主,把主要权力都交给基层组织,实行分散化和基层自治,追求一种“没有官员的网络系统思想”的政治纲领只能导致议而不决和无政府主义,在当前形势下更没有实现的可能,因此,他们大多数都放弃了这一基本原则。
(三)经济理论更趋现实
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与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基本一致,即都不太重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主张建立一种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混合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较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等。但较之于70、80年代,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有了极大的进步,其经济理论也更趋现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反对“稳态经济”,主张经济的适度增长。
“稳态经济”(即生态经济)是西方生态运动的一个基本经济纲领,其含义就是指实现经济的“零增长”,以此来保护生态环境。西德绿党主张“我们根本反对一切数量的增长,特别是当它由于追求利润而受到刺激时……。”(注:[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著:《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153页。 )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大都支持这一观点,认为只有限制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将生产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稳定下来,实现经济的零增长,才能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稳态经济的主张虽有其可取之处,但在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是不现实的。因为对于广大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是他们摆脱贫困和和饥饿状态的重要手段,如果要这样的国家也搞稳态经济或无增长经济,无异于让他们自杀,后果只能是维持世界范围内各国人民的不平等现状,第三世界的各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而且鉴于目前生态失衡和资源短缺的现状,若想消灭污染和减少资源损耗,就得依靠科技进步,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而要实现科技进步,就需要经济继续增长,在零增长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建设或扩大有利于改善环境的工程的。
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因此,他们一般都主张放弃稳态经济,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应保持适度的增长,当然这种增长是以满足人们的有限制的物质需要而不是利润为目的的,而且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必须是理性的,与生态环境的要求相容的。法国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学家安德列·高兹提出生态重建的理论。他指出,所谓工业社会的生态重建(或现代化),具体包括从产品的设计(产品将必须是“耐用的”和“易于修复的”)到消费和物质循环,涉及生产和能源改造的一切形式,并要求化学工业、运输和农业的生态重建。生态重建的要求就是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生态合理化。英国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学家大卫·佩珀指出,“一个社会如果是建立在公有制和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并且生产仅仅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出售和利润,那它将为人们提供一个为生态环境所接受的满足需要的框架。”
2.反对“小即美”的舒马赫主义。
英籍法国经济学家E·F·舒马赫在其一本很具影响的书《小的是美好的》中指出:高度集中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并不存在什么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他提倡一种“适宜的技术”,即小规模的、分散化的技术。他还从各种道德和政治的前提出发论证说,最大的并不一定就是最好,而小的才是美好的。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大多接受舒马赫主义,其代表人物本·阿格尔就曾指出“只有按小规模技术发展起来的民主地组织和调节的生产过程才能使工人从官僚化的组织系统中解放出来。”(注:[加]本·阿格尔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503 页。)舒马赫主义不仅代表了一种反文化的倒退主义倾向,而且带有严重的乌托邦性质。因此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大都放弃了舒马赫主义,认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下,庞大的失业大军、严重的资源短缺及人口爆炸等问题早已超出一国范围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本无法将其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再来提倡小规模、分散化的经济,根本就是开历史的倒车,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四)在价值取向问题上,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长期以来,在绿色运动内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应当并完全可以征服统治大自然的技术中心主义;另一种是认为人类应该顺应大自然,对大自然“毕恭毕敬”,在大自然面前“规规矩矩”的生态中心主义。受后一种倾向的影响,70、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的掠夺时,一般都采取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他们普遍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的主人,而人类则是大自然的奴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大自然。这种主张颠倒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并将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者则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正如其代表人物大卫·佩珀所说:“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当然不是资本主义技术中心意义上的)和人道主义。”(注:[英]大卫·佩珀著:《生态社会主义:从纵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伦敦洛特雷出版社,1993年版,第95、96、232—233、232页。)他还认为, 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主张生产的目的首先应当满足社会需要,即“把人放在物之上”,而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反对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要求使劳动成为满足“人自身发展的手段”,拒绝把劳动仅仅作为生存手段。生态社会主义者普遍设想,在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将形成一种全新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统治”自然,这里的“统治”意味着人类按照理性的方式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如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来发展生产,以满足人类有限度的而又丰富多样的物质需求。在这种关系中,人是中心,大自然是人的可爱的家园,人与大自然形成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
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能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导致大批的原共产党人加入到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中去,生态社会主义内部的左翼力量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响也扩大了。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们在详细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的方法论之后发现,马克思把社会和自然看作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又是社会化的自然,二者是对立的统一;另一方面,二者又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自然制约并改变着社会,社会又反过来改变着自然,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一种无限循环的发展过程。正是受这一方法论的启发,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明显地开始摆脱生态中心主义,重新返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有了更新的发展,其体系渐趋成熟、完善。但从总体上来说,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仍有本质的区别,它试图用无政府主义的部分主张来改造科学社会主义,更接近于欧洲历史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现代的“民主社会主义”。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大自然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