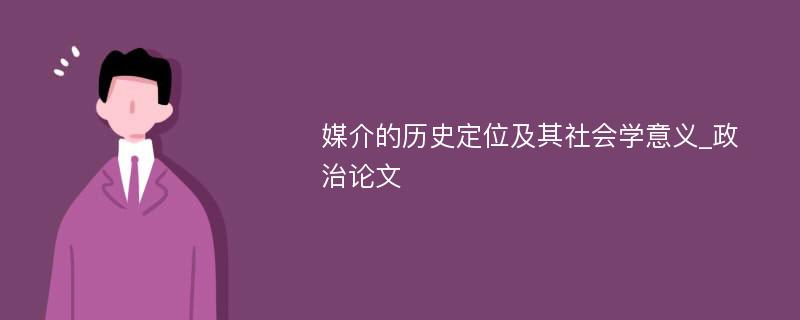
传媒的历史定位及社会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意义论文,传媒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信息论的观点看问题,传媒是发展人类交往关系的一种手段,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交往方式。正如信息不等于传媒一样,信息是物质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属性,可以说,有物质存在就有信息存在。天体变化、生命物质的演化、从宏观世界到微观客体,任何一种物质现象,都散射着本身具有的某种信息,其存在、发展和消亡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然而,传媒却不同于信息,它与社会同生同在,可以说:有人类社会就有传媒。人类是社会性存在物,集群性、合群性是人类的一大特征,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借助于交往,协同动作,这就需要最初的传媒,它既具有主体性活动的性质,又是主体性活动的一种需要。人类最早的传媒工具就是声音、语言和形体动作。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传媒又被客体化了,形成一种独立于人类自身的控制力量。这时,传媒已被异化为“拜物教”的东西,极大地影响、控制着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迄至今日,传媒已经变成为如有人说的是一种“第四权力”,成为高踞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这是为什么?我认为需要从传媒的历史定位说起。
一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随着社会的变迁,传媒经历了由人平等地发布、传递信息到对传媒的控制再到传媒对人群的控制的演变过程。
早期的人类社会,传媒不过是从学语开始的一种呼唤,传媒表现为人类社会日常生产生活的协作方式、话语方式,它的传播带有平等性、直接性、具体性和可感性。在农业社会时代,人类交往方式的简单化,对传媒的依赖极其有限,晨钟暮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社会生活交往的简单性,使得传媒的作用仅仅局限于人们的直接表意的状态。纣王为博妲姬一笑,在烽火台点燃火把,它传递出了权力的象征,似乎从这时起,传媒逐渐上升为一种权力,文字的出现,它已成为信息的重要载体,从这时开始,传媒已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它折射出社会变迁的过程,这时传媒主要是文化人的独特活动,但它的普适性却由于农业经济的封闭性而受到极大的限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文化传媒不过是知识分子所享有的一种“特权”。当然,正在此时,文字传媒已成为统治者发号施令、影响受众的一种工具,其活动方式往往是线性的,传媒为活动的主体所控制。这说明传媒的活动方式取决于上层建筑的性质及其活动方式。还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说清楚了:上层建筑简言之,就是印把子、刀把子和笔杆子(这里讲的笔杆子主要是就舆论而言),三者相互支撑、相互作用,传媒当属上层建筑。我们还可以对传媒从两个方面定义:即广义的传媒,表现为社会的交往、舆论的扩展,它具有普遍性、普适性和自发性,另一方面是狭义的传媒,表现为统治者根据其统治的需要,是做为统治者的一种工具而存在的,它具有特殊性、权威性、强制性和注入性。媒体的作用是随着统治权的扩张而日益显现出它自身的重要性和张力。我们可以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对媒体的历史定位,作出如下的概括:即历史顺推,媒体的作用日益强化,范围日益扩大,影响力增大。逆推媒体的作用在收缩,范围逐渐缩小,影响力式微。从历史上看,媒体总是同政权、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它的工具性的特点是一贯的,它的依附性是明显的。正如经典作家所召示的:任何统治者的思想就是该时代的统治思想,对于媒体来说,情形是一样的。它的工具性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在当代,只不过是用“传媒自由”、“新闻自由”的外衣给遮盖住了。
应该强调的是:当代传媒的性质、作用和社会定位同以往任何时期、任何领域有了巨大的差异。一方面传媒对权力的依附性和作为权力的主体性作用依然保持强劲势头,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传媒手段的现代化,使得传媒的影响力、渗透力在全球化范围内扩张,而代表不同权力象征的媒体总是企图超越时间、空间所造成的阻隔和障碍,去谋求传媒的霸主地位。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新闻战、宣传战,至今美国权力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依然要求传媒为其主导地位的有力助手,甚至演变成为企图颠覆某国政权的强有力的工具。同理,我国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政权的巩固,也为了传达中央的声音,也总是把传媒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并控制和阻碍外来的影响而不遗余力。谁如果动摇了对传媒的控制力和主体性地位,权力的象征意义被淡化,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中国古代有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并非言过其实。它传达出国家政权对媒体的重要性的深刻反思。这说明传媒的主体性作用将与国家制度和保持政权的同在性。
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传媒的主体化作用又同时被客体化了,即传媒在不同国度、不同制度条件下,可能被同时异化,而不论在东方和西方。从1967年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论断,到现在的“第四权力”说,这其间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经过上个世纪几十年的发展演变、模塑,造就了传媒今天的形象与品格,即带有相对独立性的姿态,因为传媒总是一种媒介、桥梁、工具,即联系上和下,联系着东与西,它不仅仅是政权、权力、政府、政党的喉舌,不仅仅是只容许发出一种声音、一种舆论,代表特定的意志,它总需要为了受众,取得受众的信任,服务于受众,而且对传媒已成为人们日常社会生活须臾不能离开的东西,人们也实实在在地从中得到了说不尽的好处和便利。但是,命运似乎注定古希腊神话中的那把达摩立克斯之剑将永远悬在人类的头上。1982年罗马俱乐部在完成的第12分报告中指出,“微电子技术所带来的、改善人类处境和消灭贫穷的许诺,是相当有力;而愚蠢地开发这项技术,所造成社会堕落的可能性也是同样巨大。”(甘特·佛德里希著:《微电力社会学》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51页)社会实践也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微电子技术的进步,无疑对社会进步以巨大的推动,同时也对社会造成某种严重的后果、苦果。任何国度都是如此,无论东西方,现代传媒所结出的种种苦果,其中之一便是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青少年社会问题,包括青少年犯罪,我们已经看到传媒的教唆,这又是任何社会任何政府所不乐意看到的结果。就政治问题而言,例如,在反恐斗争中,美国传媒不时有半岛电视台的报导和正式新闻媒体,同白宫截然相反的东西在转播。在我国,法轮功的邪说和歪曲不时地从海内外严重影响着受众。这是为什么?笔者认为:这就是传媒的异化或传媒二重性。是权力的失控么?是传媒的主体性作用的丧失么?显然,不是,答案只能从传媒的历史定位中去寻找。或者说,从传媒的历史演进去解读。
现代传媒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应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同时也体现为三种社会含义),即大众社会的、技术社会的和信息社会的。它不同于工业社会特别是农业社会,也只有进入信息时代,传媒才真正体现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大众享乐和消费的对象。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得传媒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前我们还不能把媒介与信息看成具有同等的价值,许多社会信息并不直接影响到大众生活,这与所谓“信息闭塞”与“媒体不畅”有关。至多信息只在知识阶层传播而与大众无关。然而,在当代,传媒已是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宠儿,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造物。传媒的“权力”即是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权力,即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市场的营销和运作的权力,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权力。因此,我们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介即是信息社会本身。媒体从过去对“权力”对政治的依附,转化为社会公众生活的独立部分,甚至传媒也转化为一种产业,一种经济行为,此时,大众传媒以其高度发达的手段,独立地广泛地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渗透到政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可以改变社会政治结构、公民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心理;改变传统权力的性质、分配方式以及权力的运作方式,成为政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大众传媒已演变成为民意的代言人,就像议员由于选民的投票而具有的权力一样,传媒因与大众相联系而具有权力,它不是立法权和司法权,也不是财权和军权,它是一种舆论的权力,道义的权力,这是一种无形的权力,它不是一种刚性的权力,而是一种柔性的权力;换言之,没有人必须服从它,但是,也没有人能忽视它,与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相比,正如前面我们引述的所谓“第四种权力”。这可能就是当代传媒的历史定位。它对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这已是人们所公认的事实。
二
传媒的社会学意义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迄今为止,尚无论者涉足这一领域。笔者认为:对传媒的社会学思考,旨在使人们认识传媒的性质、社会的功能。
传媒的社会学思考在于提醒人们认识它的本质属性,由于其多重性、多元性规定了它的中性属性。正如市场经济的社会属性不能简单地回答为姓“社”姓“资”一样,传媒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今天的传媒,已不能用传统意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宏观组成部分来界定。因为现代传媒已经是一种巨大的产业,特别是在西方出现了传媒的托拉斯,例如,电脑本身它既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经济实体,同时它又具有传媒的属性,它既是一种科技的产物,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既服从于官方,又服从于民间,既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又有负面的消极的影响,它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它既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又是当代社会的“虚拟世界”的制造者。随着电子技术的飞跃发展,人类的传播媒介,以其信息公开、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特点和功能使之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今天传媒的多样性令人眼花缭乱,文字、报刊、广播、影视、电脑和信息网络,覆盖全球的信息主宰着社会生活。不仅传媒的品种是多元的,而且其影响力也是多元的。几乎遍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休闲乃至家庭生活……传媒都在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就目前国内学者对传媒的多元性论述,大体分为三种:一是工具说,即计算机是传媒的一种得力的运算工具,即计算机网络的应用,使得传播工具化,依靠应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使之运用于社会生活提供了可能和便利。二是传播媒介说,即信息网络只是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媒介和手段方式,并没有改变其本质属性和内容。三是实体内容说,到20世纪90年代末,信息网络它本身是传媒实体,对国际经济、政治的作用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传媒不仅是一种工具、一种传播媒介,而是深深地嵌入了国际政治、经济权力的运行之中。信息网络对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手段形式的层面上,而是从根本上丰富和改变了国际经济、政治的研究实体和内容,这种观点同时代表了对社会未来发展的一种预测。
由于传媒的多元化,社会学的研究有必要对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审视,系统地把握传媒演进和嬗变的规律,即打破时空的界域,无论东方和西方,传媒的正面和负面,积极和消极作用,都需要探索其共同的特征,很难说传媒对我为天使,对彼为魔鬼,中性的传媒,很可能在未来社会将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实力较量,而是传媒本身在科技层面上的竞争。我们有理由相信,信息网络化对世界多极化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现代社会美国在信息传媒领域享有“信息霸权”的优势,但以因特网为媒介的国际社会,更加强调权力的分散。因特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分布性和无中枢性。例如在网络作用下的国际政治也必然导致政治中心的分散化发展。而且任何一个中心的瘫痪都不会对国际政治局势产生全方面的致命影响。这就为多极化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信息霸权”只是在科技领域显现其实力,各国对科技的竞争,将会使“信息霸权”淡出。“9·11”事件后,美国对恐怖势力在传媒上的全面封锁,也显得无能为力,就很能说明问题。
传媒的社会学意义还需要从传媒的社会功能进行分析。当代对传媒的功能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解,传媒具有四大功能:即环境监视(新闻和宣传)、社会协调(联系和沟通)、知识传承(科学和教育)、文化娱乐(消遣和游戏)等,在信息网络的环境中,这些功能都得到了充分地拓展。
传媒处于信息网络时代,除了有信息量大、更新速度快、查询检索方便等优势外,还使传统的线性叙事、单向传播、转变为主体式发布、双向互动传播。对于网络媒体,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大众媒体”来概括,因为“大众”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网络媒体包含了多层次的传播过程。而且信息互联网与计算机、电信和广播融合在一起,已经在彻底改变着媒体和出版业。实时、交互和受众主导是网络媒体的主要特征。互联网用户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提供和发布者。也就是说:任何人、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向任何一个人提供和获取信息已在成为现实。任何一个人网上办报、办刊、建立网上电视台和网上出版社的客观技术条件已经具备。网络媒体已经具有实时、互动、跨地域、跨文化传播的特点。传统媒体的管制规则不再适应网络媒体的发展,信息开放成为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信息社会的基础是网民。它不同于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农民,工业社会的基础是市民,在以网民为基础的信息社会里,人们的行为方式、思想方式甚至社会形态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代的网民社会正在形成,它已冲破了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社区的划分,网民的行为方式在网络环境的时间和空间中活动都有无限的广泛性和多样性。网络时代处于一个无始无终的状态,而网络空间是真正的“咫尺天涯”,鼠标一点,漫游全球,人们所期望的全球化、多极化、个性化的特征,在网络空间里获得了充分的体现。从社会形态上说,网络基本上属于虚拟社会。网民既无身分证又无社会安全号,网上无法律的制约,国家政府有疆域,网络无国界,网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公民。网民在网上活动是跨国界的,不受海关约束的,可以说,由政府、法制和秩序构成的现实社会与匿名、无序和跨国界网上虚拟社会的结合构成了我们今天新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互联网正在催生着新的社会形态。这就是新媒体所发挥着的巨大功能。可以说媒体的功能已经泛化了。相应地,对媒体的管制,就不是社会某一个部分所能尽其功,通俗的讲,就是齐抓共管。因此,我们社会学的研究,必须认真思考信息网络化对社会建构和上层建筑方方面面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企图否定我们曾经在传统意义上从科技、产业和经济的角度去思考社会学所面对的诸多问题。
三
人们对当代传媒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思考,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无论文字传媒、印刷传媒、广电传媒到信息网络,其社会价值依其各自不同的传播方式而有所不同,方式不同,影响和意义也不同。媒介是人生存与发展空间的的延伸,可以说文字是欣赏的延伸,无线电通讯是听觉的延伸,特别是现代信息网络的扩展,使有限的人体有了近乎无限的延伸,传媒已经全面触动人们的感觉器官进而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人们的心灵和思维方式。传媒的社会价值就在于它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和特性,已经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即传媒文化,在社会总体文化系统中,以传媒影响人的方式(不是通常讲的文化积淀,文化传统的影响力)为主要原因而构成的亚文化系统。人们在发明制造各种媒介,可以控制媒体,让它为表达自己的目的服务,但传媒又可以反过来对人施加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一定都符合传播者的本意,现代传媒以其快速、面广,而使传媒所发出的信息,对不同的受众会发生动机与效果的不一致。传媒者有其自身对某一信息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同样,受众对信息依各自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不同而存在极大的甚至相反的差异。
我们还必须看到:对传媒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支配。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传媒是社会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必然将文化产品的商品价值视作生产的惟一目标。另一方面,人们的观念、行为、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的支配下也在改观,使一切文化产品的价值标准受到强劲的挑战。市场经济决定了现有传媒所制造的文化产品必然受到市场的利益原则支配,决定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不能不考虑经济效益。在多数情况下,媒体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在于经济价值的大小、多少,作为衡量、评价、取舍文化产品价值的惟一标准。例如,广告成了各种媒体的惟一选择,甚至成为事关媒体的生存、发展的条件。
然而,现代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媒体本身是分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从而导致媒体传媒内容的多元选择。况且,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媒体当然会介入政治领域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任何一种媒体其容量都是有限的,这也会迫使传播者做出“选择性传播”,即决定传播“什么”和“怎样”传播,效果如何?任何事件,不管其社会生活影响多大,多么重要,只要传播者不予承认,它就成不了新闻。相反,只要大众媒体着意加以渲染,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也有可能变成重大新闻。也就是说,大众媒体可以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些事件上的同时,也可以让人们忽略另外一些事件,以此来设定社会的“议事日程”。我们从美国主要媒体对科索沃危机的报导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就是传媒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的一个价值选择。
在资本主义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传媒具有了商业性质,为了赢利它们必须取悦于更多的公众。因此,故意避免鲜明的政治立场、标榜价值中立和客观报导就成为资产阶级大众传媒的一种价值取向。实质上无非是“拥有金钱占有媒介,占据媒介,从而影响统治”。实际上,西方社会,特别是那个超级大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看不到的隐蔽的信息王国”,这个王国有它自己的政府,政府控制着信息的流动方向,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与利益。这正是媒体异化的表现,即从自在存在到被自觉利用的过程日益显现和扩大。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传媒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是基于主体与客体辩证关系的认识论原理和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的唯物史观为依据的。传媒是科技和信息的物化,但人类主体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的能动作用,并非西方科学主义所认定的那样是完全独立的第四权力和无法调控的魔方。任何传媒的传播以及接受传媒的受众,其主体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状况依然是具有重大的作用,因为人对于技术,对社会文明任何条件下都起着主导作用,那种认为“现代”传媒是世界的主宰,传媒的异化是人无法控制的悲观主义的观点是不足取的,特别是在中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环境中,我们对传媒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总是基于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团结和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需要。首先,我们应当继续不遗余力追踪当代世界科技的发展以及科技对传媒的改进、推动作用。在传媒领域充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力争在国际传媒的交往活动中,以足够的科技力量,应对挑战,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打破所谓国际传媒霸权的垄断。其次,我们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保证传媒的一切活动,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弘扬文化事业中的主旋律,不断清除文化垃圾和精神垃圾,始终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最后,传媒的一切活动,也都以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我们审视传媒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