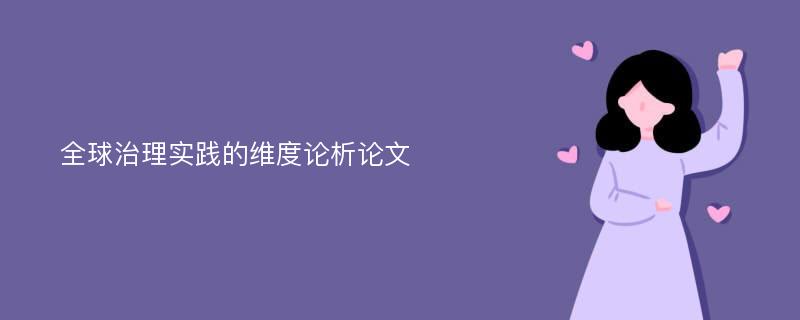
全球治理实践的维度论析
肖欢容, 张沙沙
(中国传媒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 100024)
摘要: 全球治理是当代全球政治研究中的最重要学术主题和话语,但学术界对全球治理的实践维度与理论研究仍然存在很大争论。本文撇开国际关系流派中全球治理理论论争,从全球治理的核心概念出发,对全球治理实践的观念逻辑、全球治理实践的空间层次、全球治理实践的功能和全球治理实践的结构四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以期实现对全球治理这一重要主题实践维度的充分阐释。通过四个实践维度的探讨,本文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要应对的四组权力关系挑战。
关键词: 全球治理;观念逻辑;空间层次;功能;结构
全球治理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视域,将民族国家与超国家、非国家和跨国家关系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复合体式的合作解决全球事务的复杂的结构与进程。如何理解这一复杂的结构与进程,学术界并没有共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仍然是从权力视角,以国家利益实现的旨趣看待国际合作的方式来理解全球治理,自由主义从制度视角,以制度嵌入国际组织机制的方式理解全球治理,建构主义从文化观念视角,以规范内化和制度实践的文化认同建构和共识实现的方式来理解全球治理。三派主流国际理论,从各自的核心概念出发的阐释并没有实现对全球治理实践的完整理解。
本文从全球治理实践的核心观念逻辑出发,指出责任与信任、机制与制度、规则和遵从以及权威与善治四组核心概念,构成了全球治理实践逻辑的观念逻辑基础。而国际关系领域全球治理研究者空间视角下的霸权治理、跨国治理、地区治理和地方治理,与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国家治理一起,形成了全球治理自上而下的实践空间层次。此外,全球治理实践功能中,议程架框与设计、国家能力建构、规范创设、标准设定、争端解决和强制是其主要功能。最后,必须注意到的是,全球治理沿袭着原有的国际治理结构层次,其中权力、制度和观念对立是其重要结构分野,因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发挥,需要处理结构性关系中的四组重要的权力平衡关系。
一、全球治理实践的观念逻辑
全球治理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过程,学者们对全球治理的视角和核心概念理解也不尽相同。权力、权威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戴维·赫尔德与安东尼·麦克格鲁就是从该视角来理解全球治理。[1](p13-15)复杂性与变化是另一个重要维度,韦斯和威尔金森就是从该角度来对全球治理进行再思考。[2]此外,作为全球机制治理中的规制、规范与法则,特别是软法则与硬法则,也是考察治理机制及其效用重要视角。[3]总体上,在全球治理实践核心观念中,这样四组概念承载了全球治理实践的理念逻辑,即责任性与信任,是全球治理实践主体的内核与前提;机制与制度,是全球治理实践的载体;规范与遵从,是全球治理实践机制与行为主体的互动和互为模式;权威与善治,是全球治理实践的效能。
某种生物如果由于人为或自然的原因,由其原栖息地迁移到异地,并经自然选择后逐渐繁衍开来,打破当地的生态平衡,威胁当地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生态恶果,即形成生物入侵。伴随着人类活动日益加剧,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入侵现象愈演愈烈,已经对各国的经济、社会、民生以及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澳大利亚的兔灾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第一,责任性与信任,是全球治理参与主体的特质与主体参与进程的重要关系前提。 “责任性(accountability)”这一概念来源于公共管理,指的是与某一特定职位或机构相连的职责及其所需承担的义务。[4]职能、职责与义务是责任性的内在含义。行为体的责任性特质表明其占据一定职位,有义务承担该职位职能所连带的职责。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治理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中重要话语,责任性也成为善治的重要要素。随后,全球治理成为国际关系中重要研究主题,责任性也就成为全球治理中参与主体的重要特质内涵。
众所周知,全球治理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源于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重要性和问题解决的难度,依靠主权民族国家无法独力解决,因此,多元行为体共同参与全球性问题解决的机制与进程。这种参与,特别是非民族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并不是为了利益收益,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价值实现和道义责任。因此,主体之间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其责任性特质充分显现。这种责任性,首先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等联系在一起,由此探讨多元行为体,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平等参与地位。[5]
将斑点叉尾鮰放入CO2浓度为550 mg/L的水溶液中,浸浴15 min后将鱼装进保活袋充入纯氧,每组分别放入0、2、4、6、8和12 ℃的培养箱中,5 h后取出放入清水中,观察存活数并记录存活率。
另一方面,就主权民族国家行为体的参与而言,主要的参与行为体,特别是大国行为体的参与,责任性与信任特质非常重要。就责任性而言,近年来全球治理领域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这种供应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美国霸权供应失灵。也就是说,作为国际霸权的美国无能、无力和缺少意愿参与全球治理,是导致当前全球治理困境重要原因。
美国的国际霸权缺失尤其体现在美国特朗普总统执政后重心从国际到国内的转移: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实行“美国优先”战略,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退出,2018年4月开始更是无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制,悍然与中国进行贸易战,恶化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业已出现的全球治理危机,其作为全球治理大国的责任性荡然无存。2019年2月1日,美国政府宣布2日起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并启动退约程序。美国军事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为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实践实现的后果——好的治理或善治,使得参与的行为体权威进一步强化。权威与善治,由此而成为全球治理实践效用的重要观念。多元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特别是跨国倡议网络和知识共同体,他们不断提出治理倡议与议程,促使治理目标良好的实现,由此实现善治。善治的效应,使得这些行为体不断获得权威,由此权威更在国家之外扩散。全球治理中权威与善治由此而互生,体现的是治理实践实现的效应。
第二,机制与制度是全球治理实践的载体。 全球治理的本质就是世界政治社会是如何组织和治理的。当前世界治理的形式主体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国霸权治理。这种霸权治理是以联合国为总体的政治组织和安全治理,以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后为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世界经济治理来实现的。19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兴起,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美国霸权治理难以实现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大任,其他的单个民族国家也无法独力面对,全球治理由此兴起。
在全球治理的实践中,二战后的霸权机制治理仍然是实践载体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他的各种机制治理平台也相继出现,成为全球治理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G20等横跨南北关系的国际机制平台的出现,是当代新兴全球治理机制实践的首要部分。在冷战时代,除了霸权治理组成的各种机制外,为了处理复杂的国际经济等问题,美国组建了工业化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后来俄罗斯加入,形成八国集团,就国际事务重要议程等进行大国治理。冷战结束后,八国集团也难以独立协调众多的全球性问题,众多南方国家参与的G20适时出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近年来,G20等重要性发挥越来越大,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发挥,与八国集团相比也不遑多让。
第二,行为体的能力建构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功能。 能力建构是指参与全球治理的各个行为体,包括个人、民族国家和非国家的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行为体等,有效地发展其参与能力。这些能力体现在行为体增进其技能技巧、态度和知识以及管理作用等,结果是使其有更大的权力、更多进入决策的机会甚至是更大的社会利益。具体地说,就个人与非国家行为体来说,能力建构重点是信息获取能力与参与能力,其目标是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发言权,非政府组织则还包括增进其本身组织机制的能力建设。就各种倡议网络来说,能力建构是将更多的与其价值相关的议程纳入全球治理实践解决的问题之中,并促使其实现预期目标。[14]
其次,在问题领域各种协商协作性机制平台与公约协定规制不断出现,成为全球治理广度和深度发展重要载体。最突出的领域是在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领域,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16年的《巴黎协定》,气候变化公约虽然不时遇到一些挫折,但共同责任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并不断取得新进展。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全球卫生健康和传染病的保障维护成为重要国际合作议程。其他的如国际人权、全球安全、全球贫困与全球发展以及跨国犯罪等领域,各种协商和解决平台也在不断发展。
最后,南方发展中的新兴国家不断通力合作,创建新的国际合作机制,成为全球治理实践机制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金砖机制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其合作内涵不断夯实的内部新合作机制与平台的创设和金砖机制在全球机制制度治理中的革新推动作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的举措和实践,比如中国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其发展效应也在不断推动全球治理实践机制发展,甚或成为全球治理实践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规范与遵从,是全球治理实践机制与行为主体的互动和互为模式。 规范是行为体在一定环境中如何行为的集体预期。规范成为指引行为体行动的规则网络,甚至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强制遵从权威的时候,也是如此。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的全球治理,就是规范治理,其具体体现就是国际机制或制度规范治理。比如,国际法在国与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交往中界定了各国都应遵从的规范,外交公约规范为各国外交官提供了行为准则,避免了无意识地引发国际争端的情况发生。
国际机制与制度的治理行动,是通过机制与制度规范扩散与遵从方式实现的。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秉持责任性与信任的多元行为体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时候,首先在于创建国际机制与制度,设立制度规则规范,然后,通过规范的扩散与遵从,各个行为体将国际机制与制度规范内化为国内规范与国家利益,在国家内外行动中践行规范,全球治理效用因而得以实现。温和建构主义学者玛莎·费丽莫将这种规范践行互动方式归结为“适应性逻辑”和“推论逻辑”。[6]
由于全球治理是一个多元复杂的进程,议程设计和问题的提出方式也形式多样。在正式的国际机制治理中,国家是主要行为体,大国特别是投票权重且多的国家,在此类机制的议程和问题设定中地位特别重要。在当代,非国家行为体也更多参与正式国际机制治理,他们通过游说活动、项目策划等智力支持、甚至直接参加会议进程等,将其价值利益旨趣相关的议程纳入国际机制治理。在非正式国际机制特别是跨国治理中,非国家行为体更是越来越活跃,积极参与议程设计和问题设定。许多非正式机制,就是非国家行为体直接设立或推动设立,以解决其关心的问题。议程设定和问题提出,由此也成为当代全球竞争中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在调研各高校图书馆网 页过程中发现,部分高校在图书馆主页设置的与新生相关的栏目称为新生专栏、新读者专栏等等,发现情况如下:有的新生教育栏目实质内容很少,仅为传统新生教育活动的PPT课件;有的仅为各种规章制度的罗列,其实在图书馆主页当中都有,为重复内容;有的新生专栏还没有放在图书馆主页显著位置,在某栏目下级目录下,十分不方便查找;有的新生专栏打开为陈旧内容,并没有实时更新,没有人员定时维护等等。建议将新生专栏重新规划一下,每个模块简单生动且方便读者查找。
国际规范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其影响全球治理中特定行动路线的成本与收益,还在于因为其改变行为体行动内容,成为行为体行为变化的原因。比如,种族平等的规范使得南非白人政府在国际上受到排挤,从而使其屈从于国际制裁。规范能够改变行为体关于对错的观念,能够改变个人和社会互动的方式,从而使得治理得以实现。
第四,权威与善治,是全球治理实践的效用观念。 一方面,全球治理承接了全球政治中权威分散性特征,导致国际政治中民族国家权威向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体扩散。国家权威的扩散是权威转移到其他层次,即体现在权力从国家到市场的扩散、军事权力向经济权力的扩散、权力从国家到社会的扩散、世界政治权力结构的国家中心模式向多中心模式的转化等层面。由此在全球治理中,权威的代表从民族国家向超国家、跨国家、次国家和私人领域等行为体扩散。
与美国的国际霸权缺失相对应的,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金砖国家在责任性与信任方面的替代作用尤为突出。与美国责任性缺失不同,金砖国家多年来相互信任相互结伴,在美国无意、西方无力推动全球治理的情况下,着力推动甚至引领全球治理,体现了全球治理参与主体的责任性和信任关系,在全球经济治理改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今年的南非峰会,金砖国家更是提出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进而提出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目标。金砖机制近年来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体现了全球治理行为体的责任性和信任特质的效用。
二、全球治理实践的空间层次
第三,跨国治理(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是全球治理社会维度的扩展。 跨国治理指的是跨越民族国家边界事务领域的政策协调或强制。跨国治理主要涉及的是非国家行为体,比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或国际组织对跨民族国家管辖权领域的事务,这些事务通常是民族国家政府较少介入的。一旦民族国家政府建立的正式协调机制无法解决特定的跨国问题时,跨国治理就出现了。[11]
第一,美国霸权治理( hegemon governance)是当代全球治理秩序的基轴,其当前主要特征表现为霸权治理失能,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其他层次治理和其他领域治理的兴起。 根据现实主义视角下的霸权稳定论,霸权的存在(比如19世纪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产生了国际稳定的模式。霸权有维护体系存续的自我利益,一方面,霸权用军事实力护持体系安全,另一方面,霸权创制体系中的治理规则。英国霸权时代,金本位是英国霸权治理的重要规则。二战后,美国霸权创制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机制,来护持世界霸权治理秩序。[7](p27-35)
后冷战时代,尽管美国霸权秩序机制仍然存在,但国际社会要求改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原因在于霸权秩序体现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华盛顿共识不能有效地维护世界经济增长,特别是那些曾经践行新自由主义规则的拉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经济效果。1997年东亚危机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更暴露了新自由主义规制的失灵。另一方面,后冷战时代全球化伴随的全球性问题的增长,霸权无法有效进行解决,其他行为体越来越多参与全球进程,参与全球治理。此外,美国本身不时地回归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本位政策,破坏国际治理的规制规则,导致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霸权供应不足,全球治理陷入危机。[8]当然,尽管霸权治理失灵,但必须看到,霸权治理机制规则效用仍然是当代全球治理基轴。
第二,当代国际地区主义的不断发展,地区治理( regional governance)成为当代全球治理中的重要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超国家层次的地区性组织不断涌现,成为国际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冷战时代,伴随着全球化的强劲发展和欧盟发展的深化,出现了地区主义新浪潮,从地区层次进行国家间合作,甚至走向深化的一体化形式,是当代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发展。[9]
当代地区治理的特点,首先表现在治理的地理范围大,几乎每个国际区域都出现了地区主义组织。欧盟的发展,从其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地区治理的标杆。在欧盟之外,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的发展与成效,也是地区治理的重要组织。其他的地区治理组织,比如拉美的南部共同市场和非洲联盟以及非洲次区域的各类合作组织,都取得不少进展。此外,地区治理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从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合作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到当代安全治理、人权治理、公共卫生、发展治理、气候与环境治理等,地区治理也毫无疑问囊括了全球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10]
从空间层次视角看,作为公共管理中重要主题的国家治理并没有直接纳入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研究者的视域。很大程度上,国际关系研究者研究的是超国家层次的霸权治理和地区治理,跨国家层次的跨国治理以及次国家层次的地方治理。冷战的结束,作为两极结构一方的苏联解体,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多边机制秩序没有改变,国际机制秩序的美国霸权治理仍然存续,霸权治理是当代全球治理秩序的基轴。地区治理,特别是新地区主义发展,是当代全球治理地区空间的重要扩展。早在1960年代以来就业已出现的跨国现象,在后冷战的全球政治时代更是快速发展,跨国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社会维度重要层面。国家治理之下的地方治理,则是全球治理秩序的根基。
跨国治理首先体现的是应对跨国家边界的移民、劳工或走私跨国犯罪等事务议程,这是正式的政府治理机制较少或治理不足的地方。其次,跨国治理并不强化正式的国际制度权威,而是体现在“软性”的国际非政府的监察和协调等层面。再次,与正式的政府间治理机制不同,跨国治理具有灵活性特征,有助于促进利益攸关者各方的协调和协作。此外,必须注意到,国际非国家行为体和跨国市民社会在跨国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通常引发跨国治理,促进政府或企业在正式规制不足背景下的善治行为。同时,跨国治理反过来也促进非国家行为体和跨国市民社会的成长。
第四,地方治理( local governance)是全球治理秩序的根基。 地方治理源于西方民主社会中分权政府的决策和服务传送制度观念的发展,政府日益依赖其他社会组织来实现公共服务提供的目标,政府及其机构不再是公共服务分配中的唯一决策者。治理,特别是地方政府治理,政府和私人组织的合作、共同决策和共同承担公共服务的传送等成为重要特征。地方治理与地方政府成为平行关系。[12]
就地方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来说,地方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根基,地方治理最少从三个方面拓展了全球治理的权威扩散、社会性和多元性等特征。首先,地方治理中广泛地采用公私伙伴关系。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传送,非政府行为体非常多的参与,形成各种公共领域的公私伙伴关系。其次是各种地方组织协会、利益集团和私人行为体形成政策伙伴关系,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分配决策之中,是国际层面全球治理决策形成的范例。最后普通公众也广泛参与地方治理,类似在全球治理中,国际名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总体上,地方治理是缩小版的全球治理形式,地方治理是全球治理的根基。
霸权治理、地区治理、跨国治理和地方治理与国家治理一起,从空间视角形成了整体的全球治理的空间视域。当然,要更深化地理解全球治理的其他治理形式,则还必须考察多层治理、社会网络治理、政策网络治理、治理网络模式、复杂性治理和最近出现的新治理模式等,方能形成对治理的其他内涵模式深层的理解。
除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作家之外,江西还吸引了大量的流寓作家。江西地处“吴头楚尾”,南抚百越,北望中原,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宋代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和政治中心的南移,江西一度成为南宋京畿地区的屏障,并自宋至晚清一直拥有着巨大的交通区位优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政要官员、文人学士出入江西、流寓江西,促进了江西文学的发展及与全国文学和文化的交流。这其中最典型的是辛弃疾,辛弃疾是南宋爱国词人的领袖,他虽生于山东历城(今济南),不是江西人,但他长期生活于江西,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江西度过,终老于江西,他融入了江西的文学和文化中,对江西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全球治理实践的功能
全球治理是不同的行为体在缺少世界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国际关系中的协调行动。但是,在现有研究中,许多研究并没有明晰全球治理实践的功能并非仅仅是制定和实现规则规范。事实上,哪些事务能够成为全球治理应对的问题,是全球治理的前提。所以,议程的设计和问题的框定,是全球治理的首要功能。其他功能中,其次体现的是全球治理行为体的能力建构,再就是全球治理实践的规则创设和标准设计,最后是全球事务问题的治理实现以及实现进程中争端解决与强制等功能。
第一,议程设定和问题的提出是全球治理的首要功能。 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的兴起,是当代全球治理产生的重要因素。但是,国际社会如此之多的全球性问题,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纳入全球治理解决的视野。哪些问题能够纳入全球治理议程,成为全球治理实践解决的问题?这是全球治理实践的初始。因此,议程的设计和问题的提出,是全球治理实践的首要因素和功能,在此过程中,众多行为体成为议程设计的倡导者,他们通过各种行动方式,促使其价值取向相关的事务,优先成为全球治理实践解决的问题。[13]
规范的存在使社会中的治理成为可能。具体的国际规范可以分为规制性规范(regulation norms)和构成性规范(constitutive norms)。界定何种情况下什么行为是合适的规范即为规制性规范。规制性规范是行为的指引或标杆,它澄清了行为体的选择。如果行为体的某种行为方式与规范相悖,随之而来的是战略成本上升。如果行为体行为方式与规范一致,行为的成本就更低,而且可能有因遵从规范的额外获益。构成性规范是特定行动的集体意义和行为体的认同。构成性规范通过建构一定认同产生行动权威,即界定特定行为和特定认同。比如,规制性规范反对杀人,而构成性规范将“杀人”的行为者定义为“杀人犯”从而界定了杀人犯的身份认同。
AL:0为AL≤3 mm;1为4 mm≤AL≤5 mm;2为 6 mm≤AL≤8 mm;3为9 mm≤AL≤11 mm;4为AL≥12 mm。
对民族国家而来,其能力建构是全方位的,最直接的就是参与权与国际话语权。具体说来,包括议程设定和问题提出能力、规则规范设置和指标标准设定能力以及治理实践的实现能力。
第四,有利于改善农村信用环境。非正规金融利用信息对称性,首先将一部分策略性违约的借贷者排除在外[4],对于非策略性违约的农村经济主体,非正规金融组织通常会增加其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甚至拒绝为其提供借款,让其为自身的失信行为受到相应的惩戒。而信用良好的农村经济主体在向非正规金融组织办理借贷业务时,可以享受优先贷款权、优惠利率、灵活的借贷期限和较高的授信额度。非正规金融为农村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方便守信者融资,强化正向激励,不断壮大守信群体,从而有利于降低信贷风险,增强农村经济主体信用意识,改善农村信用环境。
第一阶段是1990年代,民族国家权能衰减与全球治理兴起。在1990年代,冷战结束,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兴起,全球治理随之产生,人们发现国家中心主义范式衰减,民族国家主权受到越来越多侵蚀,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治中作用日益突出,多元行为体与民族国家共处,共同参与全球政治和全球治理。[15]
虽然在教学方面各个学校已经意识到每个学科应该有侧重的能力提升,高中物理中比较重视的能力便是解题能力的培养,但是由于新课改倡导的时间有限以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使得目前解题能力在高中物理教学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1990年代末到2008年金融危机是第二阶段,是民族国家权能重振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全球治理中的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制效能的反思和机制改革,民族国家在其中的作用突显,更多的全球机制和全球治理发展,也得益于民族国家的推动,由此体现的是全球治理中民族国家权能的重振。
游客到景区游览,普遍具有留下自身印记的倾向,比如最被人诟病的景区不文明行为——“乱涂乱画”,尤其是“某某某到此一游”,可以说在大部分景区普遍存在,对此,不能不能一概批判,而应正视景区旅游者自身的特征,可以说,由于多数旅游景区对于游客而言,是“一期一会”,一辈子只有一次,所以,通过拍照、刻字、留下纪念物等方式留下印记,是可以理解的,当景区不能提供此类留下印记的机会,并没有有意识的引导,那么自然就会导致游客的内在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被动的不文明行为,这种行为因旅游景区的不作为而得到强化。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是第三阶段,是民族国家权能的重构时期,民族国家权能与全球治理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在本时期,美国霸权治理失能加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权能越来越重要,成为全球治理实践的重要推动者,在某些事务领域,甚至起到引领作用。总之,当代全球治理中,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个行为体都在竞逐全球治理中的权力权威。
第三,规则的创立和指标与标准的确立是全球治理实践量衡的基本功能。 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与解决是否实现,需要一定的衡量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规则的创立和指标与标准的确立成为重要准绳,由此也成为全球治理实践量衡的基本功能。[16]在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设立了许多规则与标准。首先在全球政治与全球安全治理中,人道主义干预与保护者的责任成为重要规范与治理标准。其次在全球经济与全球发展问题上,联合国确立的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全球发展治理重要指标。最后,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公共卫生与传染病等方面,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也设置了行动和实现标准。
从民族国家权能与全球治理历史进程关系来看,从全球治理发展至今,可以清晰看到三个历史阶段。
在联合国与国际政府间组织之外,规则与标准创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西方主导民主治理与善治标准,是当代全球治理重要研究领域,与发展中世界的观念存在重大分歧。民主治理的指标包括自由、宪制、善治、腐败指数和人权等五项指标,用以考察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17]其次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断地在国际机制中提出革新建议,以期对现有国际治理机制朝着更公正和更有效的方向发展。再次是各种地区主义行为体,即地区性组织在地区治理中的规则规范与标准指标创设,也就是全球治理中的地区治理,比如欧盟,在新世纪以来一直试图成为全球治理中的规范行为体。最后是私有行为体与跨国倡议网络,他们在自己价值和利益攸关的领域,不断提出新的倡议和规则标准,以期实现有效的问题解决和治理。[18]总之,规则规范创设与标准指标确立,是全球治理实践功能实现的核心,是所有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话语权权能的直接体现。
第四,治理实现、争端解决与强制是全球治理的直接和最终功能。 全球治理的实现,是规则规范实践效应的直接后果。而规则的实现,实则是一个存在竞争和争议的过程,全球治理就是在解决争端,有时甚至是强制实现的过程中实现治理目标的。全球治理是包括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各种社会性倡议网络以及作为国际名流的个人参与的复杂过程与进程。在特定的问题领域,不同的参与行为体的价值与利益目标均有不同,由此导致在治理实现方式与治理目标等层面,都存在竞争的观点与立场。全球治理的实现,既是全球治理各种规范规则和治理方式践行的过程,也是解决相歧异的观点和立场实现治理的过程。
基于空间句法理论[7],将余荫山房平面转化为二维平面模型,运用凸边形地图法和轴线地图法从可视层以及可行层两个层面计算余荫山房的空间连接值和整合度,并对其可视图解进行对比及量化描述[8]。
在争端解决与治理实现进程中,评估、监察和调适也是重要的治理实践功能。因为全球治理进程的多元行为体参与的特征,导致有时候很难区分治理实践管理者和监察、评估者,所以对治理实践的评估与机制效用,有时很难有一个理性的结果。因此,在规则规范实现和遵从的过程中,需要对实践进程进行评估、监察和调适。评估、监察和调适随之也成为治理实现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23]
分别以HPS、PCV2、APP、SS、B.subtilis、E.coli、Salmonella、S.aureu的DNA以及CSFV的cDNA为模板,按照优化后体系进行ddPCR检测,验证特异性。
四、全球治理实践的结构
在缺少世界政府的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背景下,全球治理为我们了解超越国家和社会、建构新的政治现实和重构旧的政治现实所进行的规则设计、政治协调和问题解决的复杂体系与进程,提供了适合的理论范式。然而,正如全球化研究者对全球化现象和进程的描述仍然是模糊的一样,全球治理研究中对全球治理的结构与进程描述也很混乱。[19]在无法对全球治理结构进行完美论述情况下,以全球治理中权力、制度、观念三个层次,来管窥全球治理中南北关系视角下的结构性维度,可以对全球治理结构现实进行有益解释。
第一,从权力视角看,全球治理就是在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政治兴起背景下出现的,全球治理中的权力结构特征承接了全球政治的分散性特点,同时又呈现自身的特性。 美国霸权在全球治理中的失能是全球治理中权力结构的首要特征。美国霸权治理失能体现在美国霸权的限度和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供应的意愿不足以及对世贸组织等国际规则的主观破坏等方面。与霸权治理失能相对应存在的权力结构特征是全球治理中权力的分散性、权力的共享性和权力网状交织的特征。全球治理中权力的性质呈现去中心化、社会性、责任性和发展性特征。全球治理中权力的上述结构特征和权力性质,有助于不同行为主体的连结、联合、合作和非结盟地参与和建构治理行动与进程。比如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不断机制化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重要动向,就是在这种权力分散性特征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8]
第二,从制度角度看,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机制秩序,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霸权治理所形成的多边秩序。 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等西方意识形态主导。大部分的国际规则,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确立的,体现的是西方的价值和利益。[4]在地区治理层次,欧盟地区主义的高度机制化,一直是其他地区主义发展和地区组织治理的标杆,其他地区的地区主义组织形成和地区治理发展,一旦遇到阻力,欧盟的规制规则,无形之中也成为压力。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参与现有国际机制治理中规则的革新和扩大权能,另一方面也力图创建符合自身利益又有益于全球治理的机制。很大程度上,非西方机制稍有不顺,即受到西方的唱衰。国际机制制度治理中,美国霸权和西方主导的结构性特性明显。
第三,从观念角度,全球治理中许多重要规范和原则,也同样体现出霸权和西方意识形态属性。 在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机制治理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者的责任,就是西方国家自二战结束以来贬抑国家主权,贬抑发展中国家贫困、不发展和治理失能,因而需要外部干预下产生的。在国际经济治理中,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是其主要意识形态规范,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中,其固守的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其意愿宏观调控的条件,往往使得发展中国家发展状况更加恶化。在国家治理中,善治和民主治理等观念,是西方文明标准一脉相承的。当然,非国家行为体和社会倡议网络推行的一些治理理念,也在全球治理中得以扩散和实现,但也无法改变全球治理观念中西方优势的事实。况且,很多规范规则,不说是西方理念的痕迹,但其对西方偏向对发展中国家贬抑的趋向,也表现得特别明显。
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维度中矛盾处理与实践建议
从全球治理维度角度看,面对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西方优势特性,越来越多参与全球治理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把握好四个方面的权力关系平衡。
一是全球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与霸权治理权力关系的平衡。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越来越重要的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权能的发挥,首先要协调的就是美国霸权治理权力。美国2018年4月开始的对华贸易战,与中国实力上升和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的扩大等因素有重要关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应最大程度兼顾沿线国家的利益,将俄罗斯、印度以至沙特等国家纳入中国战略共赢框架,实现国际话语权最大化,更好地拥有与美国霸权治理的对话与协调能力。
二是全球治理中西方治理权力与发展中国家治理权力关系平衡。 全球治理中西方权力特性明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作用发挥,要求革新现有治理机制,并不时建构新的治理机制,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利益,必然会与西方治理权力发生矛盾,因而需要平衡应对。如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时主导成立亚洲投资银行之初,曾遭到美国极力反对与阻挠,这与亚投行挑战美国霸权治理中的美元霸权地位密切相关,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亚投行,创新的治理机制的作用愈发显现,最终令美国霸权不得不妥协,这是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成功介入全球治理的成功范例。
三是国家治理内部权力关系平衡,包括经济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平衡。 发展中国家仍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内部治理机制和权能实践肯定存在不足。这些不足,在当前信息时代很容易外溢,并招致外来干涉。因此,国家内部治理的好坏,是全球治理权能发挥的重要前提,需要郑重应对。如中国作为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都是西方颜色革命的重点目标,同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处理是否得当,能否有效抵御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分化、西化的冲击,都将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四是国家治理中战略性权力和地区治理合作间的平衡。 各国所在区域的地区治理,越来越成为当前全球治理重要部分,也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外部世界第一步,因而国家战略性权利和地区合作之间权能平衡很重要。只有有效地把握这些权力平衡,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权能,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如在英国脱欧过程中,出现因与欧盟矛盾向中国示好的迹象,表现为英国积极扩大对中国出口,通过放松对中国感兴趣的高科技产品管制,如芯片、机载雷达等,扩大英国对中国出口。中国可利用此契机推动诸如人民币国际化、密切中英经济联系等,提高中国与英国合作程度,开拓西方治理与发展中国家治理权力合作的全球治理新模式。
1.2.2 签订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责任状 结合我院抗菌药物使用情况,医务处要求临床科室签署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责任状,对抗菌药物使用率、Ⅰ类切口手术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比例等在内的抗菌药物指标分科室予以明确,年底不达标者,追究科室主任领导责任。
六、余论
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治理一个重要体现是美国霸权治理失能,特别是2016年特朗普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优先”成为首要国家战略,美国更明显地从国际主义退回,走向民粹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使危机中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供应更加恶化。但是,必须注意到,全球治理仍然在向前发展,一方面是信息技术发展,全球性议程全球共同解决的共识在当前国际社会成为促使新全球化和新治理的动能;二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显著,在有些领域,甚至起着引领作用;此外,欧盟仍然试图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规范作用;三是非国家行为体和倡议网络在全球治理中仍然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这种动能背景下,全球治理中的范式研究,特别是治理网络和新治理模式的发展,将带来新的研究动向。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发挥和更多的丰富实践,一方面将成为全球治理实践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也将使得全球治理中的非西方规范与理念,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而西方与非西方的比较研究,也将纳入研究的视野,成为全球治理重要的学术话语。
讲评时,我采用“兵教兵”与“师教兵”相结合的方式,对于错误率低的题目,由平台随机挑选答对的学生进行讲评,而对于错误率高的题目,由我讲评,进行究因和纠错。讲评完后,我再推送“预习检测”答案解析,让学生深化理解,对于仍不明白的学生可在“提问区”进行提问,课后对提问的学生再给予指导。
参考文献:
[1]〔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M].曹荣湘,龙 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Thomas G.Weiss and Rorden Wilkinson,“Re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ity,Authority,Power,Change”[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14,Vol.58,No.2,pp.207-215.
[3]Kenneth W.Abbott and Duncan Snidal,“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00,Vol.54,no.3,pp.421-456.
[4]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20-32.
[5]Elena Sciso,ed.,Accountability,transparency and democracy in the functioning of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Cham,Switzerland:Springer,2017.
[6]〔美〕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M].袁正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7]约翰·鲁杰.对制度的多边主义的剖析[A].约翰·鲁杰.多边主义[M].苏长和,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8]肖欢容.全球治理中的权力特征与金砖机制治理的挑战[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8,(6):25-30.
[9]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10]Tanja A.Börzel and Thomas Risse,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art II.
[11]Thomas Hale and David Held,“Editor’s Introduction:Mapping Changes in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in Thomas Hale and David Held,eds.,Handbook of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institutions and innovations,Cambridge,UK:Polity,2011,pp.1-36.
[12]Bas Denters,“Local Governance”,in Mark Bevir,ed.,The Sage handbook of governance,Los Angeles:Sage,2011,pp.313-329.
[13]Deborah D.Avant,Martha Finnemore and Susan K.Sell,“Who governs the globe?” in Deborah D.Avant,Martha Finnemore and Susan K.Sell,eds.,Who governs the glob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34.
[14]Hok Bun Ku and Angeline W.K.uen-Tsang,“Capacity Building”,in Mark Bevir,ed.,The Sage handbook of governance,Los Angeles:Sage,2011,pp.469-483.
[15]James N.Rosenau,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16]Stefano Ponte,Peter Gibbon and JakobVestergaard,eds.,Governing through standards:origins,drivers and limitatio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
[17]Pippa Norris,“Measuring Governance”,in Mark Bevir,ed.,The Sage handbook of governance,Los Angeles:Sage,2011,pp.179-199.
[18]Axel Marx,et al.,Private standards and global governance:economic,leg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Northampton,MA:Edward Elgar,2012.
[19]Arie M.Kacowicz,“Global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Order and World Order”,in David Levi-faur,ed.,Oxford handbook of govern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686-698.
An Analysis of the Dimens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Practice
XIAO Huanrong, ZHANG Shash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governa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academic theme and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global political research,but there is still much debate about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academic circles.This paper puts aside the debate on the theory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arting from the core concept of global governance,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global governance practice:conceptual logic,spatial level of global governance practice,func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practice and struc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practice,in order to realize the full interpret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an important theme practice dimension.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four practical dimensions,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four groups of power relationship challenges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especially China,need to deal with in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Key words :global governance;conceptual logic;spatial level;function;structure
收稿日期: 2018-12-10
基金项目: 中国传媒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高端人才支持项目“中国与全球机制治理”(编号:YLTS180613)
作者简介: 肖欢容(1971-),男,江西高安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安全与冲突管理,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以及国际关系思想与理论。
张沙沙(1990-),女,江西九江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全球机制治理、东亚安全机制。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备荧光检测器,型号为LC-30AD):岛津(上海)有限公司;MK3酶标仪: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ROSA-M孵育器和读数仪:美国Charm公司;离心机:盐城凯特实验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旋涡混匀器:德国IKA公司;锤式旋风磨:波通瑞华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9)03-0017-09
(责任编辑:余小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