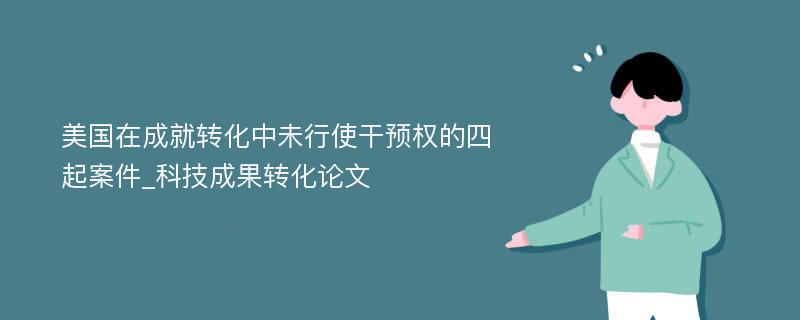
美国未行使成果转化“介入权”的四个案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成果转化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技成果转化是促进科技经济结合的重要措施,美国通过立法确定政府的介入权,对政府资助产生的科技成果进行强制转化。几十年来,美国曾发生4个申请强制转化科技成果的案例,但政府最终都决定不行使介入权,没有强制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本文拟介绍美国科技成果转化“介入权”的具体规定条款和这4个申请科技成果强制转化的具体案例,分析美国政府实行“介入权”过程中的困难、障碍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对“介入权”所持的态度和观点等,以期为我国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1 美国“介入权”的规定 为避免财政资助成果的搁置或不当使用,美国政府采取法律措施强制科技成果转让,会根据第三方的请求,要求受资助机构转让科技成果,或由资助机构直接授权。[1]《拜杜法案》(The Bayh-Dole Act)中的“介入权”(March-in Right)条款,[2]规定了财政资助科技成果强制实施的条件,具体内容如下: (1)受资助的机构未能在合理期间内采取或可能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研发成果的实际应用; (2)受资助的机构在转让成果时未能满足公众健康及公共安全所需; (3)受资助的机构在转让成果时未能满足联邦法规所要求的公共使用; (4)受资助的机构在转让成果时未能在免责的情况下确保该成果所形成的产品在美国生产。 该权利由研发资助机构行使。如果出现前3项情况,资助机构会强制执行成果的转让;出现第4种情况,资助机构会禁止该成果的转让,扣留该成果的所有权。在接到企业转让成果的请求后,研发资助机构会通知成果持有单位提供相关信息,并在调查后决定是否要求成果持有单位进行成果转让。尽管有这一规定,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很少发生。 《拜杜法案》实施以来,美国曾出现Fabrazyme、CellPro、Norvir及Xalatan 4个案例,申请人向成果资助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其行使“介入权”,强制相关专利成果的转让。作为成果资助部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调查后认为这些案例不符合强制成果转让的条件,因此,均未行使介入权。 2 四个案例 2.1 案例1:Fabrazyme (1)被申请强制执行的科研成果[3] 2010年8月,卡力克(Joseph Carik)等3名美国公民向国立卫生研究院提出申请,要求行使介入权,强制西奈山医学院将与Fabrazyme有关的专利以公开、非专有的方式授权第三方,尽快生产Fabrazyme,满足病患者需要。 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下,西奈山医学院(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研究开发了Fabrazyme,并申请获得了专利,授权Genzyme独家生产。该产品为α-半乳糖苷酶制剂,用于治疗Fabry氏病。此病是一种由α-半乳糖苷酶先天缺陷引起的遗传代谢病,其特征表现为四肢疼痛、严重的肾脏和心血管系统病变和中风。Fabrazyme作为酶替代药物,获得了罕见药资格。 2009年年中,由于遭受病毒感染等,Genzyme公司的Fabrazyme产量大为减少,导致市场上Fabrazyme短缺。而且,在2009年11月,FDA发现Genzyme公司生产的Fabrazyme包含污染物,因此,对该公司处以1.75亿美元的罚款,并做出监管7年的决定。受此影响,Genzyme公司的Fabrazyme只能满足30%患者的需要,而患者又没有其他的选择来替代Fabrazyme。当时,Genzyme承诺到2011年年底会增加Fabrazyme的产量,但患者并不相信。为了治病,卡力克等3名患者提出了这一诉求,希望根据《拜杜法案》将Fabrazyme的相关专利公开转让给第三方,尽快生产患者急需的药物。 (2)国立卫生研究院不行使介入权 2010年12月6日,国立卫生研究院通知卡力克等3名诉求人,决定不行使介入权,其理由是:根据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判断,将Fabrazyme的相关专利转让给其他第三方,根本不可能解决患者所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看来,Genzyme是生产Fabrazyme最佳的选择,因为,从实力和条件上看,其他公司若通过转化这一专利而生产Fabrazyme,将需要数年的临床研究和药品审批。但同时,国立卫生研究院也表示,如果有第三方愿意或有兴趣申请转让Fabrazyme专利,或者如果Genzyme增加Fabrazyme的承诺不能实现,国立卫生研究院会进行重新研究。 鉴于Fabrazyme的生产和销售关系众多患者的生命,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西奈山医学院和Genzyme公司就Fabrazyme的生产和销售情况每月向国立卫生研究院报告,包括:Fabrazyme的生产和市场紧缺情况及向病人的分配和供应情况。另外,如果西奈山医学院和Genzyme公司收到第三方愿意转让Fabrazyme专利的申请,需在两天内通知国立卫生研究院。 2013年2月13日,国立卫生研究院再次向卡力克等3名诉求人发出通知,重申不行使介入权并将Fabrazyme案结案,其理由是,从2011年1月到2012年12月,西奈山医学院和Genzyme公司每月都提供报告。根据报告,美国所有Fabry患者都能及时得到足够的Fabrazyme,也即,市场上Fabrazyme充足,而且没有任何第三方提出转让Fabrazyme专利的申请。[4] 2.2 案例2:CellPro (1)被申请强制执行的科研成果 CellPro是美国一家从事药品开发和生产的公司。1997年3月3日,该公司向国立卫生研究院提出申请,要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将关于My-10单株抗体的专利授权给它。 CellPro公司申请强制转让的技术主要是用于骨髓移植及其衍生的免疫系统移植手术。骨髓移植技术可以治疗白血病、淋巴瘤及乳腺癌等重症,因为骨髓中含有少量单极其重要的干细胞。通过传统技术将骨髓移植到病患体内,干细胞将会产生各种血液细胞,然后于病患体内制造新的血液及免疫系统。然而,骨髓中有些其他细胞,如癌细胞等对人体有害,因此,科研人员、药厂及生物科技公司开始研究在进行骨髓移植前精华隔离干细胞的方法。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Curt Civin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下,发现了与干细胞有直接关联的My-10单株抗体,并申请获得了4项专利。约翰·霍普金斯将专利授权予Baxter公司,该公司通过成果转化开发出一个产品Isolex System,用以净化隔离干细胞。然而,直到1998年7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并未核准Isolex System用于临床。几乎与此同时,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也发现另一12.8单株抗体,并授权公司CellPro将该成果实现商品化,成功地研制出一产品Ceprate SC,并在动物实验中被证明有效,从而获得FDA的核准。但此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却向法院控告CellPro侵犯其专利。 CellPro曾在1992年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Baxter公司协商My-10专利的授权,但未达成协议。面临控告,CellPro可能自知即将败诉,便在陪审团裁决宣布的8天前,要求国立卫生研究院行使介入权,强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将My-10专利授权给它。 (2)国立卫生研究院不行使介入权 1997年8月1日,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Dr.Harold Varmus宣布拒绝行使介入权的决定,并陈述两点理由:一是Baxter公司的产品虽然未获得FDA的核准并用于临床,但已用于临床实验,而且在1997年2月为其产品申请了“销售前核准”(Pre-market Approval),因此,不符合介入权条款第一条所描述的“未能在合理期间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研发成果的实际应用”的规定;二是在FDA批准Baxter公司的产品生效前,CellPro依然可以销售其产品,因此,不符合介入权条款第二条所描述的“未能满足公众健康及公共安全所需”的规定。 2.3 案例3:Norvir[5] (1)被申请强制执行的科研成果 2004年1月29日,Essential Inventions公司向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DHHS)部长Tommy Thompson提出申请,要求他行使介入权,强制Abbott Laboratories药厂(简称“Abbott”)把与Norvir有关的6项专利以公开、非专属、依销量缴纳专利费等方式授权给该公司。[6] Abbott在1988-1993年接受国立卫生研究院下辖的国家过敏与感染性疾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i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的资助,专门从事抗艾滋病毒药物的研发工作,取得了6项相关专利,成功开发出艾滋病毒蛋白酵素抑制剂Titonavir(商品名为Norvir),在1996年正式通过FDA的上市核准。 本来,Norvir是当作单一病毒抑制剂使用,但是其副作用过于严重,所以被迫停止销售。后来,研究发现,如果将Norvir作为追加剂,与其他药物合并使用,将有助于提高药效,因此Abbott开始与其他药厂核准,Norvir也开始为Abbott赚钱。 从2003年开始,Abbott将Norvir的价格提高5倍,其他药厂因成本原因也相应提高产品价格,增加了病患者的负担。然而,Abbott自身生产的艾滋病用药Kaletra却没有提高价格,因此,Abbott被认为是利用价格差异来控制市场,使患者被迫选择其生产的Kaletra,同时,也使得其他相关企业深感不平,从而发生了Essential Inventions公司要求Abbott转让专利的申请。 (2)国立卫生研究院不行使介入权 由于Abbott得到过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因此,Tommy Thompson把这一案例交由国立卫生研究院办理。2004年7月29日,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Elias A.Zerhouni宣布对Norvir案拒绝行使介入权的决定,并陈述两点理由:一是Norvir符合“实际应用”的规定,已“在法律以及行政管理规定的框架内,基于合理条件有益于公众并为公众所利用。”而且,Norvir早在1996年就已获得FDA核准上市,并用作抗艾滋病毒的单一抑制剂以及其他药厂抗艾滋病药物的追加剂;二是Norvir符合“公众健康及公共安全需要”的规定,因为截至当时,Norvir已在市场销售长达8年,被广泛地用于治疗艾滋病。 Essential Inventions公司提出对Norvir行使介入权申请的原因,是不满意Abbott不能以较低价格提供Norvir。Essential Inventions公司所关心的价格控制问题不能援引《拜杜法案》来解决,而是应该寻求联邦公平委员会(FTC)审查,或者游说国会订立特定法规来规范。如果国立卫生研究院以行使介入权的方式介入企业竞争领域,将会影响市场机能。 2.4 案例4:Xalatan (1)被申请强制执行的科研成果 同在2004年1月29日,Essential Inventions公司向DHHS部长Tommy Thompson提出申请,要求他行使介入权,强制Pfizer公司把与Xalatan有关的专利以公开、非专有、依销售量支付专利费的方式进行授权。[7] 哥伦比亚大学在1970-1980年接受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研发出一种可以治疗青光眼、用以降低眼压过高患者眼内压的前列腺素。数年后,以该前列腺素为基础,哥伦比亚大学与企业合作成功研制出处方药Latanprost(商品名Xalatan),获得美国专利。哥伦比亚大学将该专利专属授权给合作企业,后来,该企业被Pfizer公司兼并。Xalatan在1996年获得FDA第二线用药的许可,在2002年获得第一线用药许可。不过,Pfizer公司为扩大Xalatan的销售,采取了国内外价格不同的策略,结果造成美国境内Xalatan的价格远远高于加拿大和欧洲,从而引发了患者和研究机构的极大不满。因此,Essential Inventions公司才提出了这一诉求。 (2)国立卫生研究院不行使介入权 Xalatan在研发过程中也曾得到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因此,同Norvir案,Tommy Thompson将这一案例交由该院办理。2004年9月23日,Elias A.Zerhouni宣布拒绝行使介入权的决定,其陈述的两点理由同Norvir案完全相同,因为,Xalatan也是早在1996年就已获得FDA核准上市,截至当时,Xalatan也已在市场销售长达8年,也即,Xalatan早已被青光眼患者广泛使用。 Essential Inventions公司提出对Xalatan行使介入权申请的原因,与Norvir案完全相同,也是在价格方面,主要是不满意Pfizer公司的价格差别策略。 3 对“介入权”的评价 根据美国审计总署的报告,美国“介入权”的实施效果不明显[8]。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和航空航天局是联邦政府主要研发资助部门,但20多年来,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向这些联邦政府部门提出过行使“介入权”的请求。国立卫生研究院虽然受理过4个请求,但最后也没有行使这一权利。在美国审计总署的调查中,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和航空航天局的官员赞同这一“介入权”,认为该条款有利于促进成果转化,而能源部的官员则持否定态度。 从具体实施方面看,这一强制成果转化的条款形同虚设。根据美国审计总署的分析,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资助部门认为此条款可能影响研究人员参与政府科技项目的积极性,过多地参与政府资助科技成果的强制转化可能给研发人员增加一定的负担。 (2)“介入权”的程序较为复杂,调查取证需要较长时间,在紧急或有实效要求的情况下难以实施。目前,各部门在执行《拜杜法案》时所遵循的是商务部制定的规则,其中涉及介入权的规定严密细致,各方面的意见都要充分听取。 (3)所涉及的成果往往不只是获得政府一个部门的资助,还获得其他政府部门的经费,有的还有其他方面的资金,特别是企业自身也常常有很大的投入,从而导致“介入权”的行使更加复杂,更加困难,如,Abbott在Norvir研制过程中,从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资助347万美元,但在该药的临床试验和使该药上市的过程中,自己投入了3亿美元。 (4)在成果转化对技术背景有较高要求的情况下,资助机构一般不愿意行使“介入权”,因为请求行使“介入权”的企业可能不具备成果转让所需的技术。同时,已经有另一家企业获得了该项成果专利,而且正在开发,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把转化后的产品投入到市场中。 根据国立卫生研究院对4个成果强制转化申请的调查和审理实践,成果转化法中的“合理的时间内”、“实际应用”、“满足公众健康”等要求,在解释上有很大的自主性,这也给“介入权”的行使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且,国立卫生研究院一直强调其学术机构的地位,不愿意干预市场机制,介入自由经济市场的运转。 4 结语 规定政府科技成果“介入权”的《拜杜法案》自1980年颁布实施以来已过去34年。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仅有4家公司申请政府行使这一条款,而结果都是政府在调查之后确定不进行介入,个中原因值得深思。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渠道不畅以及科技经济两张皮等问题一直是困扰和制约我国科技界的痼疾,从2013年开始,我国开展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并广泛征求意见。从美国的实践看,科技成果“介入权”实行条件的解释不一致、执行程序复杂、资助部门交叉等因素使得“介入权”这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条款一直悬在空中,不能落地。尤为重要的是,在美国文化的浸润下,美国认为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美国政府部门虽有法律赋予的科技成果“介入权”,但不愿意过度地干预科技成果转化。希望美国的做法能为我国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提供借鉴。标签:科技成果转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