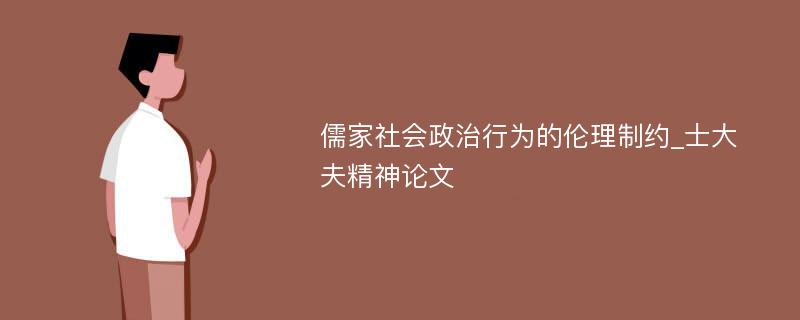
儒学社会中政治行为的伦理制约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伦理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儒学社会的概念
儒学社会指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为依归。从形式上说,儒学社会的正式起始,在儒学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时也即汉武帝确立“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而其正式结束即在于“儒家法”的被终止(注:“儒学社会”概念的具体含义请参见拙文《儒学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学分析框架》,载《浙江学刊》2000年第1期。)。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是儒学精神,儒学精神可以简要概述为: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仁爱为基础,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其内在规定是伦理理性。伦理理性在社会实际生活中表现为伦理关联,伦理关联的维护及其修复则表现为伦理控制。
伦理控制指的是,儒学社会中宗法伦理成为一种激发行动的实际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对内)在皇位继承、对经济活动的漠视、守寡抚孤等,(对外)在世界秩序的控制等现象中都可以找到;宗法伦理成为个体行为的函数、成为社会制度变迁的函数,成为一种具体的心态;虽然它受到现实中种种力量的制约(如物质的利诱),但它型塑了特定时空条件下(儒学社会)所有的个体行为或社会行为的方向,型塑了特定时空条件下(儒学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运作的倾向。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伦理控制即个体行为的社会环境控制,其控制对象不直接指向人的单个社会行动。伦理控制由于控制的是个体行为的社会环境,因此伦理控制呈现为一种网状控制,而非某一面的或点的控制如法律等。由此,伦理控制使得所有行动都获得了社会学中所谓的社会行动的意义,也即它把所有个人行为都归结为社会行为,把所有社会行为都归结为伦理行为,最终所有个体行为都获得了道德的意义。所谓政治行为是指那些涉及到国家(君主秩序)的组织或运行的行为,儒学社会中政治行为的伦理制约性突出地体现了儒学社会的伦理控制的特征。
儒学社会的伦理关系的行动者或担待者简要地可以分为君主、臣僚(士大夫)、父(子)、夫(妇)、师(徒)等,这里我们简要探讨一下儒学社会中君主和臣僚的政治行为的伦理制约性及其限制。
二、君主行动的伦理控制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自称皇帝建立皇帝制度,到1911年清宣统皇帝逊位,共2133年,有帝王名号(包括在地方称帝的)可统计人数达二百八十多人。皇帝制度是儒学社会的重要制度,而君主则是皇帝制度的主要操作者。儒学社会中君主的行动主要有哪些呢?他们的行动是否受到伦理控制呢?刘永杰先生说“系统的官僚制度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主体,而皇帝则只是这种制度的名义上的代表,是徽号和招牌。只有少数英明的皇帝,才能有效地通过官僚体制来行使自己的权力,而那些平庸之辈,则被强大的官僚体制所限制,不仅无所作为,甚至被钳制。即使那些有所作为的皇帝,也逃不开庞大官僚系统的制约,他只能在代表这种制度和官僚阶级的利益时,才能行使权力,而当他违背这种利益时,轻则会遭到抵制和反对,重则会被剥夺皇位,乃至丧生”(注:刘永杰:《中国现代化导论》,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梁任公也说“及其立而为君,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膳只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设为种种限制机关,使之不得自恣。盍遵吾先圣之教,则天下之最不能自由者,莫君主若也。犹惧其未足,复利用古代迷信之心理,谓一切灾异悉应在人主之一身,而告之以恐惧修省。及其殂落,则称天而谥,动以名誉,名曰幽厉,百世莫改”(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册,《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可见,唯我独尊的君主也并不是为所欲为的。
君主的行动主要有继统、祭天、罪己、尊师倡学、内宫生活等等。根据君主的社会行动所带来的实际历史后果,我们已有的研究往往把历史中的君主分为开国之君、中兴之君、守成之君、亡国之君等等类型,这种对君主行动类型的划分早已有之,如《吕氏春秋》曾经把君王分为圣君、中主和暴君三种类型。这种对君主的行动类型的划分其实包含着对君主行动的褒贬,也就是说是对君主行动的一种外在或舆论控制。研究表明儒学社会中君主行动的伦理控制或君主行为的伦理制约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儒学社会中把理想的君主类型化为圣王。有关理想化的君主类型,经历了一个古帝理想化的过程。据韦政通先生研究的结果显示,荀子主张“法后王”,《老子》未涉及古帝之名,《庄子》偶有美尧之语但多为批评,韩非反对期古。在先秦诸子中,参与古帝理想化的工作,儒家以孔孟为主,此外还有墨家墨子。孔子理想化古帝的内容,大都是一些空泛的话;至孟子以古帝为始源的道统雏形以告完成。根据儒学伦理理想化的古帝,主要有“内圣、外王、实行礼乐、发明器物、厘定历法、尚贤、尚俭、教民稼穑、树立五教、孝”等特质。孟子“以德定王”,荀子“以王定圣”。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公孙丑上》)。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解蔽》)。至《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则更具体的说明了达到圣王的具体过程。
儒学把理想的君主类型化为圣王的主要意义在于,儒学社会属于传统的农业社会,而经、子等古籍中有关道统人物(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记载,是儒学道德力量的根源。在儒学社会这样一个伦理社会中,社会的伦理控制的主要方式,便主要通过学习正统的经典而得以延续;通过经典的学习,加上制度化的结果,儒学的理想化角色就被典型化,以至以后的新类型的出现被认为不合正统而遭贬抑。
其二,通过各种方式如谥号等力求实际生活中的君主以圣王为角色榜样。谥号是君主死后举行殓葬仪式时,由臣子们对其一生行事用一或二个字作为盖棺论定,企图达到对已逝君主以褒贬、对未来君主以警戒的作用。据说源于周文王、武王或周公制礼作乐之时。《礼记·乐记》称:“闻其谥知其行”。《史记·谥法解》说,“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秦统一六国后,认为周代谥法是以子议父、以臣议君,有失君臣父子的体统,曾下令废去谥法,采用始(二世、三世以至无穷)皇帝称呼;但秦及二世而亡。汉兴,废去秦法,恢复谥法,自此之后,历代相随而不衰。谥号一般有三类,如褒扬、哀矜和贬责等;褒扬的如文、武、成、康、昭、穆、宣、平、景、惠、桓、庄等,哀矜的如殇、哀、愍、悼、怀等,责贬的如厉、炀、灵、缪等。谥法反映了儒学社会对皇权的一种伦理控制,例如汉代皇帝除高祖刘邦外,其死后的谥号中一律加有“孝”字,表示汉王朝以孝治国的理想,如孝惠皇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等。
其三,将超人间的力量拟人化即将人与超人间的力量的关系伦理化。人间秩序的伦理控制的不足,必然要利用超人间的力量。人间秩序的伦理控制的不足,一般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或者人间伦理秩序对君主的淫威无法加以控制;或者君主的道德力量对人间的世俗力量的控制不足。无论哪一种形式的不足,必然要利用超人间的力量;前者如儒学传统中起到某种对君主进行惩戒作用的天人感应理论,后者如各种历代君主的各种具有浓烈的伦理意义的政治行为如祭祀天地、改元、纪年、封禅等等。前者表现出君主在伦理秩序中的被设定,后者则表现出君主在伦理秩序中的积极作为,但二者又是一致的,它们共同显示出君主的行为在儒学社会中的伦理意义。总之,帝王生活在一种以伦理控制为核心的儒学社会中,一方面他们的个体生活和政治生活受着伦理的控制,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动或自觉地运用这种社会控制。
其四,道高于位的伦理控制,在儒学社会中师代表一种“道统”,君代表一种“政统”。在儒学社会中道统是政统的阐释者、道德根据、合法性来源等。儒学社会中的道统是具有伦理品位的,并且道统是由“师统”传递的(而师尊如父,这更增加了道统的伦理性),正如康熙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注:罗厚立:“道统与治统之间”,载《读书》,1998年第7期第150页。)可见儒学社会政统是承认道统的,并且受到“道统”的一定程度的制约。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将士与君的关系具体到师友臣几个层面,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的观念等,从而形成了儒学社会中与“君尊臣卑”观念相对的另一观念“道高于位”。余英时认为,“自哲学的突破以来(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引者注),知识分子即产生一种身份的自觉”,开始寻找到一种精神的凭借;并且“知识分子代表道统的观念至少自公元前四世纪以来以渐渐取得了正统方面的承认”(注:余英时:《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公元85年,汉章帝曾到曲阜孔庙致祭,问前来致谢的孔门后裔孔僖:“今日之会,宁与卿宗有光荣乎?”孔僖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注:转引自《读书》1998年第7期罗厚立“道统与治统之间”一文。)。皇帝所幸孔庙乃是为增辉圣德而已,也就是说增加统治的合法性而已。
凭借道统的精神慰籍,儒学知识分子们不绝如缕地发挥着抗争精神,矫正着君权的方向。儒学的抗议精神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政权自身的官僚中有一个内部反馈系统即,谏议制度;其二,地方讲学(如东林学子)。除此之外,还有各地的隐逸之士、缙绅阶级等都发挥了抗议精神。
三、臣僚士大夫行动的伦理控制
社会学家默顿认为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总是为其社会成员规定了相应的目标和手段,并且一定的手段总是能达到一定的目的;不同的成员对其所处的社会所规定的目的和手段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如服从、创新、程式、遁世和造反等。从这种意义上说,儒学社会为其成员特别是这个社会中的士大夫阶层规定了一定的目的和手段,这种手段和目的就其本质来说使得儒学社会表现出伦理控制的特色。如果我们考究儒学社会中的官僚士大夫的一生的、与政治相关的行为,就会发现它都受伦理的控制。儒学社会中的官僚士大夫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读书和求仕两个阶段。
在科举取仕之前,两汉取仕以察举征辟为主,被察举和征辟的大都要求孝弟廉公,他们或者德行高妙、或者学通行修、或者明达法令等,尤其汉武帝时设博士弟子,他们都是研读儒家经典的,这样以来儒家学说便开始与入仕做官联系起来,而成为后世科举取仕的先声。魏晋南北朝则实行九品中正制,对人物的品评也主要以德行为主要依据。在隋唐实行科举取仕后,读圣贤书便成为官僚士大夫进入儒学社会的第一步。儒学社会的圣贤书即四书五经,它便成为官僚士大夫认同儒学社会的目的和手段的基本读物。四书五经是儒学社会的经典,它突出地反映了儒学社会的伦理控制的本质。
“内圣外王”、“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学社会的最高理想;实现这个理想的一个手段就是“学而优则仕”。“外王”就是把儒家的理想付诸现实,“外王”小可体现于“齐家”,大可体现于“治国平天下”;仕就是一种“外王”。“内圣外王”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于伦理修养。《大学》为他们求取功名设定了一个程序:最高目标是明德、亲民,致善,基本方法是止、定、静、安、虑等,基本步骤就其反向程序来说即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根本原则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第一章)。
在仕途生活中如何处理各级关系,是我们考究儒学社会官僚士大夫政治行为的伦理制约性的重要依据。儒学社会的经济属于小农经济,其社会中所处理的主要关系表现为家族内部之间的各种关系和超越于家族之上的帝国内部的君臣、同僚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深刻地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组织形态,儒学社会的伦理控制的特色也由此彰显出来。官僚士大夫在儒学社会中处理各级关系主要的原则有哪些呢?让我们看看儒学社会中侍君以子的原则和朋党政治行为。
“仕君以子”的原则是说,处理君臣关系的原则来源于处理父子关系的原则,前者是“忠”,后者是“孝”,忠是儒学社会中官僚士大夫行为的最高规范、是对皇帝官僚制下士大夫行为的最高要求。何谓臣?雍正云,“夫所谓诚者,即忠也,乃人臣之本,天下未有本立而枝叶不生之理”(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6册,第589页。)。忠者对皇帝尽己而无私。忠来自于哪里呢?忠出于孝。“居家孝于亲”出仕则忠于君。忠在孝亲中生根,于事君中开花。如果说忠君还具有一种政治行为的意义,那么侍君以父则完全是一种伦理行为。
如何处理同僚之间的关系呢?朋党的政治行为的研究将表明,儒学社会中官僚士大夫的行动受伦理控制的性质。朋党不同于政党。政党是近代政治斗争的产物;朋党则是专制政体下的产物,它指的是专制政体内因各种原因而分裂的、对立的政治派别。虽然君主为防止大权旁落,都严禁臣下朋党比周,臣下也讳莫如深。根据朋党政治的研究,表明尧舜禹时代就已萌芽了朋党现象,几乎每一朝代都不可避免的陷入朋党之争,并陷每一个朝代于亡地。朋党的形式多种多样,如阉党(宦党)、戚党、后党、帝党、逆党(奸党)及官僚士大夫党等。伦理控制在官僚士大夫朋党之争中表现为,不论纷争因何种原因而起、不论是君子党还是小人党等,官僚士大夫结成朋党都往往以坐主、门生、府主、故吏、同年、同乡、同宗、同族的关系为彼此的纽带;也就是说不论每个朝代的官僚士大夫朋党之争的内容如何、残酷性如何、结果如何,其斗争的组织形式是一样的,即主要以血缘关系及其延伸的地缘关系和狭窄的业缘关系为组织的外在形式。在儒学社会中所有社会关系都已经血缘化,因此儒学社会的官僚士大夫的朋党之争都已经伦理化,即是说在儒学社会中官僚士大夫的政治行为或外显地或潜在地受伦理控制。在以伦理关系为组织原则的儒学社会中,建立一种准伦理关系就是获得一种资源,就是获得一种权力、一种财富等。
四、家庭伦常关系的政治化
伴随着政治行为的伦理化的,是家庭伦常关系的政治化,它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儒学社会中政治行为的伦理制约性。
父子关系是儒学社会中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政治化,师徒关系则是父子关系的业缘化。早在春秋,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易》云,“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措”。儒学始终把父子之伦放在人伦规范的首位。前面我们说过儒学社会的仕途理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儒学社会中“齐家”不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动,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儒学社会的意识形态试图以“孝”作为对民间社会的伦理控制手段,其制度性设置主要表现有丁忧制和旌表制等。
如何“齐家”呢?“齐家”在于“孝”,对父母尽“孝”道的内容十分广泛,如顺从父母的意志,继承父母的遗愿,家庭居常,对父母应如礼而侍,照顾备至,传宗接代,爱惜躯体,因为身体是父母所予,尽其所能增加父母、列祖列宗的荣耀,此之谓显亲——光宗耀祖,士大夫们往往把追名逐利、出仕入宦这种赤裸裸地功利行为放在社会首要的道德原则——孝的题目之下等等,儒学社会中,父母死,儿子必须在籍守丧三年,以尽孝道,称作“丁忧”。《唐律》规定,官吏在为其父母服丧的二十七个月当中必须辞去官职,清代减为一年;唐律还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在为其父母服丧的二十七个月中生育孩子,否则要处一年徒刑。丁忧制是一个非常苛刻的制度,不论其居官品级多高、不论其所守何职,皆不能出其外。如果隐情不报,被革职后一般永不留用,甚至更重的惩罚;这往往也被官僚们(或者用于彼此之间、或者用于消极抗议皇帝)当作一种斗争的武器。另外儒学社会的文化上甚至法律上都支持或纵容一些由孝所引起的反社会的行为,如儒学社会观念上普遍认为:偷窃失德,但为养亲,是孝子;杀人大逆,替亲报仇,是谓英烈等等。旌表制度是一种对忠、孝、贞等合乎伦理要求的行为进行劝善、嘉奖的制度。儒学社会中,孝子的称号是一个非常光荣的称号,人人欲得而居之,因此演出了很多离奇百怪的孝子行为。如以孝心感动强盗,甚至割骨疗亲、取肝疗亲等一些令人发指的行为。
五、政治行为道德制约的限制
米勒利尔著《社会进化史》,说“中国国家就靠千千万万知足安分的人民维持,而欧洲国家没有不是靠武力维持的”(注:转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版,第204页。)。儒学为其社会中的个体规定了适当的社会角色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妇从幼顺,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儒学社会的角色承担者如果各从其是,那么儒学社会的秩序是和谐的。但是儒学社会把社会秩序的健康存在仅仅建立于人的一种高度自觉的意识即所谓“诚心正意”上,这不免不是将社会秩序的基础建立在人的心理上,把政治学的问题归结为心理学问题。儒学社会的政治结构长期不变,但其中王朝更替也是常见现象;从王朝的更替中我们略可以认知到儒学社会中政治行为的伦理制约的限制。这种限制具体说来主要在于政统的暴戾\道统的式微以及心法的脆弱。
首先,对于儒学理想中的君主类型来说,现实中的君主的角色扮演绝大部分是一种失败。儒学理想化的古帝的主要品质有内圣、外王、实行礼乐、发明器物、厘定历法、尚贤、尚俭、教民稼穑、树立五教、孝亲等特质;孟子“以德定王”,荀子“以王定圣”。“内圣外王”是儒学对君主的总体要求。但现实生活中奉行现实原则的君主们践行的却是“外王内圣”的道路,并且内圣只是对暴行、荒淫和愚蠢的虚饰而已。
其一,残忍是皇帝的一个属性。孟子在将社会规范化为人的道德自觉方面,把孔子的“为仁由己”推至极端,把仁政的基础归结为“不忍人之心”。把实行王道之政寄托于皇帝的“不忍人之心”上,无异于把大厦建立在沙滩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的理想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实现过。皇帝或在未登隆基时,就弑君杀父;或已登基后,杀兄屠弟、诛戮大臣、骄奢淫逸。多数皇帝尽管没有暴君之名,但决不意味着不残暴。残暴乃是皇帝的一个属性。纵为明君也残暴有常如汉武帝杀掉戾太子、唐太宗杀掉哥哥及弟弟、明太祖滥杀功臣、雍正乾隆大兴文字狱等等不一而足。儒学要求仁政,但并没有实现仁政的机制。皇帝的残暴反映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反映了人性中恶的一面。皇帝的话是圣旨、皇帝的一句话不可违抗。在这种虚悬的“仁政”下的君主秩序碾过了多少无辜的生命。这正是仁政与君主专制的内在矛盾,并且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
其二,荒淫腐败是角色失败的皇帝的又一个重要属性。荒淫并不是就皇帝的后妃数目而言,礼制规定,“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傧、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礼记·昏义》)。荒淫是就皇帝的生活或欲望的个人满足是否危及到天下黎民、社稷而言的。儒学“仁政”学说无法克服皇帝专制下的荒淫无度。儒学给予了皇帝荒淫无度的机会和权利。而荒淫腐败也正是儒学社会中王朝从兴盛到腐败、从腐败到亡国的必由之路。夏桀、殷纣、周幽王是三代有名的荒淫之君,并因之而亡国;儒学社会中步其尾者比比皆是如汉成帝、汉灵帝、晋武帝、宋废帝、齐东昏侯、陈后主、北周宣帝、隋炀帝、唐玄宗、宋徽宗、金海陵王、元顺帝、明武宗、明神宗、清穆宗等皆以荒淫危殆社稷。
其三,低能无知者登御龙座。传统社会中皇帝被视作系乎天下安危,国家兴亡的最关键角色。儒学的嫡长子继承皇帝使得许多低能者、幼龄者、病残者等坐上皇帝宝座。西晋东晋15个皇位中先后有两个完全是傻子。“前有惠帝,后有安帝,皆行尸走肉,口不知味,耳不知声者也”(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由这些人扮演皇帝的角色,当然与儒学所要求的“圣君明主”有很大的角色距离。他们不可能施行“仁政”,更为可惜的是他们往往为奸臣所胁、甚至生命不能聊以自保。
其次,道统的式微意味着伦理控制下的君主秩序的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的道统精神。据研究,在儒学历史上始终存在着道统与政统的抗争,“道高于位”与“君尊臣卑”在传统社会中就象一枚分币的两面。如何守住“道统”?这需要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和政统保持一定的张力,二是培育士人心中的道统精神。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道统都在日趋式微。由于君主专制力量的日益强大,以君主为代表的政统日益压迫道统、操纵道统。战国时郭隗提出,“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役处”的观点(《战国策/燕策》),说明了道统的尊严。但当政统取得道统所给予的合法性后却张狂起来,这或许也是儒学道统自身的异化吧!从可以坐而论道到站着或跪着禀告,再到皇帝滥用君权动辄廷杖大臣,道统在君权的淫威下只能保持沉默并逐渐丧失纠正政统方向的力量。道统的式微意味着君权的放大,意味着儒学设计的伦理控制模式的君主秩序的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它既主张“道高于位”又主张“君尊臣卑”,这本身就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理论矛盾。在实践中,这个矛盾更加突出,“君尊臣卑”是现实的、制度的,而“道高于位”却是理论的、心中的;当君主专制强大到无法克服时,道统或者只能泯灭在心中或者只能以身殉道或者只能“枉道以从势”。伦理控制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走向了扼杀生命活力的深渊。
再其次,心法的脆弱,儒学社会中将政治行为的合法性的来源归结为“诚心正意”,突显出将政治行为伦理化的道德虚幻性,道统之形必须落实于孔子及其传人身上,道的尊严完全要靠它的承担者——士——本身来彰显。《论语》和《孟子》是道统抗争的最为重要的力量来源。但是和政统相比较而言,道统是虚拟的无组织的。
由于儒学的道统缺乏组织的力量,儒学只能靠求助于卫道者的内心的自我搏斗。很多人败下阵来。即使在高级的知识分子群中也有许多人守不住道的基本防线。孟子曾经斥责公孙衍、张仪为“以顺为正,妾妇之道”(《孟子/滕文公》),荀子对当时许多“仕士”和“处士”的丑行进行过暴露(《荀子/非十二子》)。“枉道而从势”或“屈学以阿世”者比比皆是。道德约束或伦理控制暴露出它的虚空性。心法的脆弱性还突出地表现为臣僚的角色失控。臣僚的角色失控有几种基本类型或如王莽等“取而代之”者、或如曹操等“狭天子以令诸侯”者、或如魏忠贤等“结党营私”者等等。新儒学认为儒学是“为己之学”、“君子之学”、“内圣之学”或“成圣成贤之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有道理的。但这些角色失控的大臣又何尝不是饱读诗书的呢!从正统儒学的意义上说,他们皆属于角色失控者,但儒学要求他们“修身齐家”之后要“治国平天下”呢!臣僚的角色失控或许是式微的道统对滥施淫威的政统的抗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