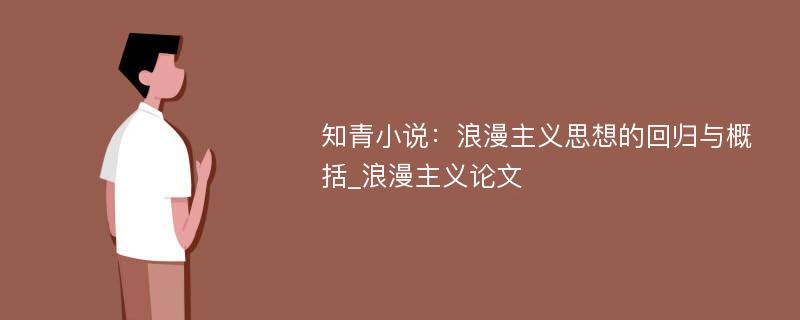
知青小说:浪漫主义思潮的回归与泛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青论文,浪漫主义论文,思潮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3)06-0097-06
一、知青小说的浪漫主义风格
新时期浪漫主义思潮的回归是以一批情感型知青小说家的创作为标志的,他们是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铁凝等。这些人在上山下乡中奉献了青春,当回首往昔时,目光中常露出悠远而凝重的神色。他们的作品最感人的地方,往往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从文本中流露出来的一种浪漫的精神气质。当然,另有一些作家不是正宗的知青出身,如邓刚,但他们也用自己的色调给新时期的小说涂上了浪漫的一笔。总之,这些作家风格各异,可是其创作都或多或少让人联想起浪漫主义的一些重要特点。
首先,是回归自然。浪漫主义者看中大自然的常常是它的辽阔、静谧、荒芜、人迹罕至。人从大自然敞开的胸怀里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大自然也因此获得了人格化的特点。当然,人格化的过程在浪漫主义者那里又是非常私人化的。新时期的一些作家就表现了这一特点。如邓刚《迷人的海》,最大限度地简化人际关系,充分突出了人与大海的联系。海是汹涌的海,人是孤寂的人。老海碰子和小海碰子远离人世,投进自然的怀抱,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生命舞蹈。海的轰鸣成了他们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仿佛是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使他们感到适意和满足。
有意味的孤独本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象征。它使人沉潜到生命深处,激发起神奇的想像,把自身的力量投射到对象中去。这些知青作家正是由此改变了前辈作家通常把大自然当成单纯的背景来写的态度,而在作品里尽情地展示自然的富于人性的一面。换言之,这些作家是把大自然当成自我的象征来写的,写出了精神的高贵,其中写得最出色的要数《北方的河》。在这部中篇小说中,张承志把北方的六条河作为主角,既是写河,又是在写他自己的心灵史——他从额尔齐斯河学会了宽容,从湟水认识了生活的残缺美,从黄河找到了父亲,从永定河懂得了坚忍的意义,从梦中正在解冻的黑龙江,这蕴藏着北方的秘密的大河,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一个成熟的“我”正自信地随着一泻而下的滚滚洪流向前挺进。难怪王蒙发出这样的感叹:“妈的,河全被这小子写完了。”张承志的成功就全在于他把河当做人来写,从河的品格折射出自我的精神历程。
把自然当做人来写,不仅普通景物成了精神世界的生动象征,而且还出现了通灵性的牛(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有感情的马(张承志的《黑骏马》),人格化的狼(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这些动物被赋予了人的品质,人与动物相互依恋,读者可以从中看出人的主体力量的扩张和精神世界的趋于丰富。这是新时期人性突破了教条束缚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浪漫主义思潮重新抬头的一个标志。
其次,是追求神秘和神奇。浪漫主义者认为,“除了神秘的事物外,再没有什么美丽、动人、伟大的东西了。”[1](P68)法国作家夏尔·诺蒂埃直截了当地说:“我喜爱善于从事神秘创造的巧妙想象,它能给我讲述世界起源的故事和过去时代的迷信,从而让我迷失在废墟和古迹之间。”[1](P65)神秘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蕴涵着可以逗人遐想的品质。浪漫主义者总是把“美”放在“真”之上,在奇幻的想像中追求精神的自在。在新时期作家中,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灵魂》创造了一个魔幻世界:桑杰达普活佛在弥留之际说的一桩往事,正是我写成后从来没给人看过的一篇小说的内容,说的是一个女子跟一个过路的男人出奔。汉子要去寻找北方的净土香巴拉,她就跟着,别无所求。荒原,雪山,峡谷,低矮的小屋,漫无目标的流浪,宗教……扎西达娃描绘了一幅充满神秘色彩的原始生活图画,汉子临死之前听到第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上的英语广播,严肃地说:“神开始说话了。”这里,宗教已经成为一种伟大精神的象征。小说在神秘的氛围中表达了人对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是趋向无限的。
不过,中国文化中的神秘主义传统的根基不像西方那样深厚,新时期的作家从那个特定时代走来,又几乎都抱定了入世的态度,要在当下的生存境遇中寻求实现精神自由的途径,因此他们没有从神秘走向虚无,而是渴望达到神奇的境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梁晓声)谱写的是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一批知青用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在北大荒令人恐怖的“鬼沼”——神秘的“满盖荒原”,创造了奇迹。这里发生过人性扭曲的悲剧,有眼泪和哭泣,但最终青年们赢得了人的尊严,懂得了爱的意义。一切牺牲,都是为了证明一个青春的梦想——要赶在解冻前跨过沼泽,把荒原改造成良田。青春是美丽的,连同她的缺点。在倒下去的青年背后,是他们的战友,一支从远远的地平线上浩浩荡荡奔涌过来的农垦大军。在这样的境界中,人们能感受到青春的热血在涌动,人的精神在升华。这是一种崇高的浪漫主义。
第三,寻找精神家园。浪漫主义者不谙世务,喜好幻想,比一般人更需要精神家园。精神家园可以是大自然,是宗教,是关于未来的一个动人的想像,也可以是对于一段已经逝去的时光的深沉回忆,只要能够使心灵有所皈依就行。在西方浪漫派作品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回到中世纪。这对西方人来说,就是认同宗教,同时也是回到“过去”,它关系到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传统,新时期浪漫主义者所能找到的一个精神家园就是回首往事,借此给过去的岁月注入生动的意义。史铁生写他的“清平湾”,孔捷生写“南方的岸”,实际上就是在回想,而且这些回想都具有“遥远”的特点。因为透过“遥远”的时空回望艰辛的来路,由不得会产生一种忧伤而美丽的感情,使精神生活变得丰富生动。这方面,张承志又具有代表性。他写知青返城后独自践约千里迢迢重回插队的山乡,寻找青春的印迹(《老桥》);写白音宝力格返回乌珠穆沁草原,寻找与他从小一起长大、由于命运的播弄多年没有音讯的恋人索米娅(《黑骏马》);写“他”重访草原上象征着他的青春的小姑娘奥云娜(《绿夜》),这些都是在回溯已经逝去的感情之流。可是很明显,寻访这些失落了的梦又不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因为岁月不会为了你而止步,他们所找的或者已不再存在,或者已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的那般模样。这是一种宿命,就像张承志自己在《北方的河》的题记中说的:“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意识到幼稚和错误,却“无法重新生活”;懂得了珍惜,可是已经永远地失去,这是残酷的。执拗地寻找逝去的梦又是件可怕的事,结果只能是转向宽恕,进而实现自我心灵的净化。这是相当典型的浪漫主义者的精神生活方式,它使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充满了激情。
第四,超越自我。浪漫主义者的精神追求是没有终点的,德国浪漫派作家诺瓦利斯在他的长篇小说中通过主人公把所憧憬的目标设定为“蓝花”,勃兰兑斯认为这“蓝花象征着完全的满足,象征着充满整个灵魂的幸福”[2]。就是说,它是一个向着满足和幸福的永恒的过程。中国新时期具有浪漫气质的作家,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他们从小接受理想主义的教育,又在广阔的天地里“磨炼”了意志;生活嘲弄了他们,他们则学会了坚忍,懂得如何在逆境中憧憬未来。这使他们的精神生活不是趋向消沉,而是从“过去”汲取力量,扬起生命的风帆,超越平庸。《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的河》等作品就是不甘平庸的告白。其中包含的“回到过去”的主题,仅仅是为了从感情上替“过去”做个总结,以便通过“过去”这座桥梁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当然,各人憧憬理想、超越自我的风格是有所不同的。有的表现得楚楚动人,如铁凝,她的《哦,香雪》写了一座大山两条铁轨的故事:现代文明通过铁轨传进了大山深处的小村,勾起了山里姑娘对山外生活的憧憬。香雪,为了拥有一个会自动合上的铅笔盒不顾一切地跳上火车,让火车载着她跑了30里,再用腿走回来。但这是值得的,因为当她拿着用40个鸡蛋换来的铅笔盒在月光下沿着铁轨往回走时,她“忽然感到心里很满,风也柔和了许多”。而当她迎面向沿铁路线找来的伙伴们跑去时,“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欢乐的呐喊。……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颤栗了,它发出宽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欢呼着”。很明显,香雪和她伙伴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一次裂变,她们成了新人。作者也借这个故事表达了对于遥远未来的美好憧憬,达到了新的精神境界。
与铁凝的细腻风格有所不同,张承志的作品则充满了阳刚之气。他的《大坂》写一个知青翻越冰山回家的故事:大坂是海拔四千米的冰山上的一道山口,是新疆准噶尔和吐鲁番两大盆地的分界线,历来有人把它视为生命的禁区,山口上至今还留着不少倒毙者的白骨。可是作品里的“他”收到五千公里外妻子流产病危的电报,必须在隆冬季节翻越这座冰雪覆盖的大坂才能回到等待着他的亲人身边。于是,以生命作赌注翻越大坂,成了一次悲壮的男性的证明。这是凭信仰和亲情的鼓舞向大自然设置的限度挑战,更是向自我的勇气和体能的挑战。他向极限冲击,攀登上了大坂,就像作品所发的感慨:“古希腊的艺术家是对的,经过痛苦的美可以找到高尚的心灵。”这的确是张承志的风格。无论张承志写的抒情主人公叫什么名字,他所表达的其实就是他自己被感动了的一种人生姿态:孤独地思念着过去,遥想未来,傲视一切艰难险阻,而在成功时又默默地忍住多少难言的伤痛和巨大的牺牲不说,心中一片苍凉。于是,他们又开始向新的目标前进(《北方的河》、《晚潮》、《雪路》、《春天》、《顶峰》,还有他的长篇小说《金牧场》等)。在这样的精神长旅中,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一起不断地超越自我,走向精神的圣洁和完善。
新时期具有浪漫气质的作家,由于他们充满激情,其浪漫主义的风格其实在文体上也有所体现。他们的作品没有复杂的人事关系,所展现的生活比较单纯,包含的感情却非常充沛;其描写多是从主观出发,景物涂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显示了动人的生命意识,而不是为了简单地给人物提供一个活动的背景;叙述呈现跳跃性,常常模糊了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的界限,勾销了对白和独白的区别,使之融会成心灵的袒露;结构多是散文化或者诗化的,即从主观的时空出发,把一些感受、联想、描述、抒情、独白、对白随意地杂糅在一起,谱写成一曲心灵的乐章。这种主观化的文体,是与浪漫主义的情感内容相称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现。
二、浪漫主义思潮在世纪末的回归与新变
现代浪漫主义,是自由精神贯彻到情感领域的产物。席勒认为感伤诗人的任务是“无限的”[1](P321),史雷格尔认为浪漫主义的诗是“无限和自由的”[1](P382),连反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倾向的海涅也认为,“浪漫主义艺术表现的,或者不如说暗示的,乃是无限的事物”[1](P401)。无限,就是自由精神超越思想层面、深入到情感领域后才有的审美感受。雨果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浪漫主义,其真正的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萌芽于20世纪初,崛起于五四时期,后又在低谷中蜕变出以沈从文、废名和30年代初的郁达夫为代表的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注:郁达夫后期最能显示其风格的是以《迟桂花》为代表的浪漫抒情小说。沈从文在《水云》中则自称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见《沈从文文集》第10卷,第294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废名被鲁迅称为“无党派的浪漫主义”(参见《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到30年代末,随着左翼方面放宽了文艺批评的标准,面对国民党当局实行的专制独裁,包含个性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重新获得了反封建的意义,因而以郭沫若对浪漫主义的重新肯定和他历史剧的丰收为标志,浪漫主义思潮又以较小的规模回归文坛的中心(注:郭沫若于1936年4月接受蒲风的采访,提出“新浪漫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的侧重主观一方面的表现,和新写实主义并不对立”。这显然是对他自己五四时代的文艺观点的继承与发展,并且为他稍后浪漫主义历史剧的创作扫除了理论上的障碍(见郭沫若《诗作谈》,1936年8月《现世界》创刊号)。40年代的上海,还出现了“新浪漫派小说”。)。这一切,都跟个人享有自由的程度密切相关。中国人民长期而艰苦卓绝的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是浪漫主义思潮得以延续的土壤,而这一斗争的波澜起伏又决定了它时强时弱、不绝如缕。
知青浪漫主义小说的出现,是以彻底否定极“左”路线、恢复人的尊严为前导的。它代表着民众在经历了长期政治压抑和心理摧残后倾诉内心郁积的强烈愿望,代表着他们对自己所经历的岁月的爱恨交织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充满激情的想像,它实际上宣告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世纪末的又一次回归。与大跃进民歌运动和后来江青兜售的“三突出”理论所体现的伪浪漫主义思潮不同的是,知青浪漫主义小说是新时期重新涌现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潮在文学方面的反映。只有确立了人的价值,承认个性的自由,才会出现“新的美学原则”,才会产生真正浸透浪漫主义精神的佳作。而这些文学现象所贯穿的自由精神,也只有到推翻了文化专制主义的新时期才可能被人们所接受。虽然开始时也经历了一段曲折,新的原则受到非议、甚至责难,但毕竟其基本的方面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社会认同。因此,可以认为知青小说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回归又成了新时期个人自由空间不断扩大的一个生动象征。正是在追求人的自由解放这一根本点上,知青小说沟通了与五四浪漫主义思潮的联系。它们前后相隔半个世纪,形成遥相呼应之势,共同向世界宣告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可歌可泣的勇敢精神和取得的重大成果。
当然,新时期的知青小说不是五四浪漫主义的简单重复,也不是30年代田园浪漫主义的翻版。具体说来,它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
一是加强了人道主义的内容。五四浪漫主义者高举个性解放的旗帜,所否定的是压抑人性的整个旧传统,更多地带有文化反叛的性质。30年代的田园浪漫主义者比较超然地退居人生边缘,为心灵的自由而甘于寂寞。新时期具有浪漫气质的知青作家,反叛的则是现代迷信,极“左”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对人具有更为内在的强制性,因而他们的斗争有一个更为直接具体的目标:争取做一个人。这使一些浪漫主义作品虽然采取了“我是……”的句式,初看充满了个性解放的精神,但骨子里却有很强的公民意识,代表了“我们”的共同立场,有的作者甚至摆出一副殉道者的姿态,愿为人的自由的理想献身。这就是说,在这些作品中,个性主义的内容是从属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个性的解放服从于人的解放的更高目标,而不像五四浪漫主义和30年代田园浪漫主义把个性的自由摆在首位,认为有了个性的自由,也就实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五四浪漫主义充满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的精神,30年代的田园浪漫主义显示了宁静和谐的美,而新时期知青作家更多地承诺了对他人的责任,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刻在心上的名字》、《黑骏马》等作品所表达的无私关照同伴,渴望友谊、爱情,希冀宽恕和谅解,表现出英雄主义的精神,因此这些作品大多趋向崇高之美。
二是增加了历史和心理的沉重感。五四浪漫主义者所面对的传统对于他们来说,具有明显的异己性,因而他们乐于离经叛道,创作时如天马行空,神气飘举,毫无拘束。30年代田园浪漫主义者则因为自觉疏远政治斗争,所以写起来也能做到心宁气静,笔调优美。然而,新时期具有浪漫气质的作家所反对的教条主义和现代迷信,曾是他们自己深信不疑甚至亲身参与制造的,要把这些东西从自己心灵上剥离,就显得格外的痛苦和沉重,甚至会感受到人生的荒诞。不少作品,如《老桥》、《大林莽》、《南方的岸》,既想否定过去的历史,但是又留恋那段艰难岁月里青春的记忆、纯洁的友谊和美好的爱情。这种矛盾的情感就来源于历史造成的作者自身的矛盾,也即由于记忆的永恒和时间的不可逆转,他们产生了这一辈子无法重新开始的沉重遗憾。所以这不是天马行空的浪漫主义,也不是怡然自得的浪漫主义,而是承担着历史重负的铭心刻骨的浪漫主义。
三是包含了化苦为乐的宗教情感。五四浪漫主义者的宗教意识,主要是从西方文学思潮中得来的泛神论观念,这为他们的想像和幻想插上了有力的翅膀。30年代田园浪漫主义者,则转向民族传统文化,叨佛教和道家哲学之光,崇尚空灵淡雅、自然和谐,表现出退隐的倾向。新时期的知青在神圣的使命被证明是历史的误会后,大多经历了信仰的危机。有人自怨自艾,用物质追求来填补精神的空虚;也有人看重精神的自由,把思绪投向留下了青春足印的昨天。这样的人孤傲,精神上具有潜在的宗教素质。但这种宗教情感并非受某种教义的启发,而是基于个人直接经验自然地形成的,其特点是认同苦难和追求超越,而没有一个明确的宗教信仰。史铁生的“清平湾”象征着青春、健康,成了他永远无法重圆的一个好梦。那头通人性的老牛摔折了腿,被人拖到河滩宰杀。牛的眼中流着泪——命运无常,人生可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他的充满悲悯和坚毅精神的宗教情怀在此已露端倪。张承志对待苦难和遗恨的态度同样体现了宗教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知青作家中最具代表性。可以说,他的创作是在回味艰难的岁月,想给世人一个证明:你看,我挺过来啦。如《春天》,乔马为保住被暴风雪裹挟着南去的马群,千里奔截,最后朦胧地怀想着姑娘粉红色的身影,在天地一派宁静中冻死在春的雪原上,其中以艰难岁月的回忆为背景的对于春天的静观,包含着激情的历史沧桑感和由忍受达到自我净化的心理过程,体现了一种化苦为乐的宗教化的人生观。
但这种带有宗教感的观念,也注定了张承志要把回想当做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就像他在作品里经常写到的那个踯踽独行的骑手:在辽阔的草原上,细细地回首往事,思念亲人,咀嚼人生的艰辛,淡漠地忍受着缺憾和内心的创痛,他一言不发地缓缓向前。对骑手,对张承志,这种以孤独对抗孤独的方式都是一种挺有味的境界,从而表现出既感到痛苦,同时又觉得是欢乐的信仰者的心理特征。在新时期作家中,赋予苦难以神圣的意义,张承志首屈一指。他给浪漫主义注入了辉煌的激情。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代作家大都经历了理想被嘲弄、心灵遭受创伤的年代,但回顾这一段岁月的方式却存在不同。现实主义作家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客观的立场,而浪漫主义者的重点在于通过那段岁月的某些侧影来表达作者当下的特定心境。这是一种含泪回顾过去、又与它庄重地告别,要朝着未来挺进的强烈冲动,一种内心深处渴望理解、温情、抚慰、自我完善的真诚呼唤;而所憧憬的未来又只是一种美好心愿的投影,一种浪漫的想像。他们看重的是过程,而不在目的。重要的是有一份执著的憧憬:憧憬证明了人的高贵、生命的伟大。所有这些精神特征,是很难用一般现实主义的概念来概括的,它显然属于一个独立的具有内在规定性的浪漫主义思潮。
三、汇入现代主义的潮流
高尔基认为:“浪漫主义乃是一种情绪,它其实复杂地而且始终模糊地反映出笼罩在过渡社会的一切感觉和情绪的色彩……它的(情绪)基调是:对新事物的期待,在新事物面前的惶惑,渴望认识新事物的那种烦躁不安的神经质的向往。”新时期初,就是这样一个过渡性时期——坚冰虽已打破,但陈旧僵化的观念在社会上仍很有影响;曙光初现,然而关于未来的前景还十分朦胧;人们长期受压抑的感情喷射而出,呼唤着人的尊严,要求抚平心中的伤痕,一时还来不及对历史做出全面的理性思考,因而浪漫主义思潮带着这一过渡时期的痛苦、迷惘、不安、悲愤、诅咒和希望,以鲜明的主观色彩和抒情基调引人瞩目地再次回归文坛。
但是,过渡时代的混乱无序和巨大的包容性也有利于其他文学思潮的兴起。因而这时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渐渐恢复,现代主义的潮流也已初露端倪。尤其是后者,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将以新锐之势迅速崛起于文坛,它具体落实在后“朦胧诗”、“寻根”文学和以徐星、刘索拉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上。这种情势对知青浪漫主义作家无疑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因为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仅仅是文学视点向内转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所不同的只是浪漫主义表现的还属于常态的心理,是一般人都不难理解的激情、憧憬和大胆的想像;现代派文学则深入一大步,到达潜意识的层面,涉及了直觉、本能的内容。这意味着,现代主义并没有完全背离从浪漫主义开始的“自我表现”的原则,它的生命直觉在非理性这一点上与浪漫主义的情绪表现之间存在着相通之处。基于这种亲缘性,在现实困境的逼迫下,或受到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学等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浪漫主义文学是很容易兼容现代派文学的因素,或者向现代派分流,甚至被现代派文学取而代之的。
面对这一挑战,知青作家事实上被迫做出了选择,从而导致新时期初的浪漫主义思潮很快就开始分化了。具体地说,一些作家在情感宣泄的时期过去以后,为适应重建某种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开始用理性的精神审视历史和现实的种种问题,致力于思考未来的出路,其创作风格逐渐转向现实主义。梁晓声后来写出《雪城》等作品,邓刚去反映工业题材,走的就是这一条道路。另一些人高举信仰之旗,用哲理思索或宗教精神来抗拒世俗的平庸和堕落。如史铁生,从自身的残疾明白了人(类)命定的局限和终极的虚无,因而要把生的价值从追求终极、完美之类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上移开,移到人生的过程,给“活着”注入一种意义。他后期的一些作品(《命若琴弦》、《中篇1或短篇4》)大多贯穿了这样的人生哲理。张承志则皈依伊斯兰教,写出了诗体小说《黑山羊谣》、《海骚》、《错开的花》以及记录了哲赫林耶七代宗师的事迹和二百年间回族同胞反抗清王朝血腥镇压的悲壮心史的长篇小说《心灵史》。他坚守着精神的家园,从信仰的高度对世俗下了否定性的判断,早期的浪漫激情也就逐渐为宗教的虔诚所取代了。
这种情形表明,新时期以知青作家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在回归的同时,就开始了泛化的进程。它像一颗闪亮的流星划过夜空,给人们留下了美丽,然后便消失在新的文学潮流中。这包含两层意思。从较浅的层面上看,这些具有浪漫气质的作家,其创作风格还不成熟,“浪漫”还没有真正深入到他们的骨髓,没有像五四浪漫主义作家那样成为其生命存在的方式。他们写出了一些体现过渡时代情绪的浪漫主义特点非常鲜明的小说,但随后又有一些不属于浪漫主义的作品问世。真正能在相当长时期里保持浪漫主义风格一致性的作家并不多见。所以这时的浪漫主义思潮不够集中强烈,人们只能从其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中去把握它内在的一致性,甚至从相互混淆的文学倾向中分辨出它作为呼应了历史要求的一种文学思潮的质的统一性。
从更深的层面上看,这些作家具有向现代主义发展的潜在可能性。他们在上山下乡、支边插队中丢失了青春,回城后又处于被放逐的边缘地位,还要与自己也曾参与其中的造神运动所确立的现代迷信决裂,因而充分地感受了人生的荒诞。这种感性经验极容易与汹涌而入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发生共鸣,使他们不再满足于浪漫主义的倾诉,而是转向展示人生的困境和自我的异化,采用调侃、反讽、变形等艺术手法,这就通向了现代派。像扎西达娃的一些作品,就包含了较多的现代派文学的因素,诸如重构历史的叙事,荒诞的感受等等。浪漫主义的倾诉、诅咒、抗议,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人生抱着过分热切的期望。而在80年代中期一些比较有思想深度的作家看来,抱着这样的期望是幼稚的。“理想”已经破灭,价值发生动摇,就像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人们必须进行“别无选择”的自我拯救。因此,文学自然要超越浪漫主义,向更能表现或探究人的生存困境的现代派文学推进。事实上,即使是并不主张悲观的史铁生,当他对人生的思考涉及一些玄妙的哲理时,他的作品就带有很强的理性思辨的色彩,因而艺术上也开始明显地向现代派风格靠拢了。张承志的《奔驰的美神》、《金牧场》以及大量黄土地题材的作品,由于负载着过于沉重的命题,表达了汹涌如潮的宗教神秘主义的感受,人们也许可以说它深刻,却不能否认它写得相当艰涩,情绪纷繁,时空颠倒,同样呈现出现代派的一些特点,远不如他早期的草原小说酣畅流利。
这当然是一个大致的趋势。但随着这些小说所承载的现代主义成分越来越多,作为一个文学思潮,它的浪漫主义特点便日渐模糊,到80年代中期,它就整体性地消失在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浪潮中了。这与西方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现代派的发展进程倒是大致相似的。所不同的是,浪漫主义思潮在西方只存在半个世纪,而在中国,它虽然在大部分时期里势单力薄,可是延续的时间却远为长久。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迟迟没能超越个人情感自由的浪漫主义阶段。直到本世纪末,人的价值和地位得以确认,情感自由也大致得到了保证,这才基本实现了与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的关于自由的目标。但是显而易见,“自由”又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思想自由、情感自由,到回头追问自由本身的意义,相应地制约着文学从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80年代中期在个人情感自由获得基本保证后,人们关于自由的提问方式也便发生了变化——自由究竟有没有可能,即“自由”的现代主义一面的意义被凸现出来了,并逐渐为人们所关注。于是,与情感宣泄相联系的浪漫主义方法虽然还会被一些作家采用,但作为一个思潮的浪漫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此后的文学,因而呈现为一种新的格局。
收稿日期:2003-0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