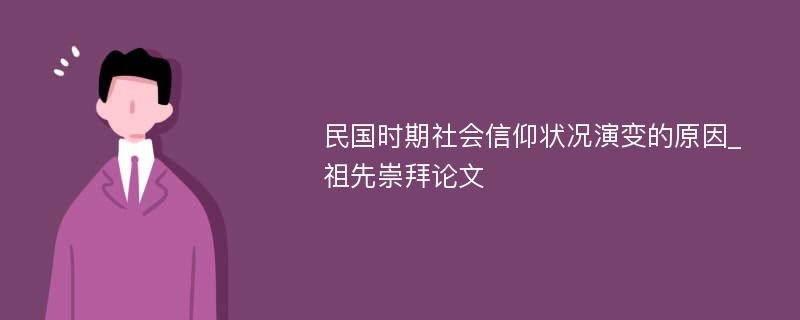
民国时期社会信仰态势嬗变之缘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由论文,态势论文,民国时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02-0095-08 中华民国的建立,既推翻了封建皇权统治,也突破了为专制统治张势的封建神权的藩篱。在政治变革的影响下,社会信仰中有关祖先崇拜、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等思想态势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嬗变。 一、祖先崇拜呈现凋零态势 祖先崇拜是人类最原始的信仰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学思想中的孝道、“天地君亲师”等观念为其延续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祖先崇拜找到了适于生存的土壤,形成了一套完整、有序的尊崇先人的方法,并赋予其顽强的生命力。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在商品经济及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的宗族制度和宗法观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诸多知识分子开始从理论上对祖先崇拜进行猛烈的批判,使其遭受极大的打击,呈现凋零之势。 1.专制政体的瓦解,使祖先崇拜失去了封建皇权的庇护 祖先崇拜作为中国传统宗族组织祭祀思想的核心,通过封建皇权对宗族组织的支持而得到庇护。首先,两者具有共同的伦理基础。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族伦理强调“孝道”、“人伦”和“亲情”,而传统国家政治也以其为伦理基础。这就意味着,宗族中的子孙“尽孝”与国家的臣下“尽忠”是一致的。其次,封建皇权给予宗族组织以法律的仲裁权以及族权至上、族长至上的自治权力,族长代祖先言事,行使最高权力,赋予祖先崇拜合法性与权威性。因此,中国封建宗族修家谱、置族产、订族规、建祠堂、行祭祀等完整、有序的敬天尊祖的做法,实际上是族权与君权、神权的结合。 民国肇兴,封建专制政体随之瓦解,传统宗族制度也难逃衰微的命运。特别是一系列相关法规的颁布与实施,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宗族观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华民国民法》,该民法典中虽然保留了家族制,但更侧重于家长的责任与义务,而刻意规避家长的权力;在继承法方面,大胆取消宗祧继承,规定男女拥有平等的继承权,①进而从法律的层面向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法观念提出挑战,加速了传统家族关系的解体。宗族制度中的祖先崇拜失去了政治基础与法律保障,其地位逐步下降,渐呈陵夷之势。 2.儒学正统地位的丧失,使祖先崇拜失去了精神依托 中华民国初年,作为祖先崇拜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的儒学即受到公开批判,尤其在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撰写系列文章,直接针对儒学。陈独秀《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李大钊《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以及鲁迅发表的一系列为人熟知的杂文和小说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礼治秩序对人的精神压抑和对社会进步的障碍。吴虞认为儒家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掣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②,这在当时的思想界激起不小的波澜,使“孔教的权威和传统的伦理观念受到根本性的和致命性的打击”③。儒学地位的转变成为祖先崇拜衰落的“加速器”。在“祖宗革命”的倡导下,他们视祖先崇拜为反科学的迷信、最愚谬的行为,认为其本质是“肆行迷信之专制,侵犯子孙自有之人权”,而且“耗民力民财于无用之地”,号召“平坟墓、火神牌”,废除修祠、立碑、祭祀、厚葬,“以为警世之钟”。④周作人强烈抨击祖先崇拜:“令人废时光,费钱财,很是有损,而且因为接香火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借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买卖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⑤祖先崇拜被视为破坏社会风气的“元凶”,地位一落千丈。 3.社会的动荡使祖先崇拜失去了可操作性 在传统宗族制度下,祖先崇拜集中表现为族田与祠堂的数量、祠祭的次数与规模、族谱的延续等内容。其中,族田是物质基础,是祭祀祖先及相关各项活动的主要经济来源,只有拥有相当数量的族田,才能把族人聚集在一起,建祠和举行大规模的祠祭。清末以来,农村社会经济破产日趋严重,族田侵吞或买卖的现象频出,使诸多宗族根本无法拥有足够的族田,如江苏省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大家族,原本拥有200多亩族田,因受族长的侵夺,最后仅剩下七八亩。⑥广东、河北等地的族田状况也大体相类似,因而无法聚拢族众,使宗族呈分化、解体状态。至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战争连绵不断,农民背井离乡,族产丧失,宗族分崩离析。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性的宗族无法进行祠祭,也很少拥有作为宗族象征的祠堂。 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农民运动实行打击农村宗法制度的措施,使许多宗族解体或处于涣散的状态。其矛头直指族权,镇压族绅、占据祠堂、破除族规,打破了农村宗法制度,进而动摇了祖先崇拜的核心地位。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同时,将族田充作教育经费、多余房屋和祠堂改建为学校及办公场所等,摧毁了家族的经济基础与象征;在缴销封建地契债券的同时,焚毁了家族谱牒,中断了维系家族的主要精神纽带。 在中华民国时期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原本至高无上的祖先崇拜这一传统信仰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据20世纪30年代初一项对大学生进行的调查,188人中有82.4%不赞成祖宗祭祀,73.9%的人认为应废除祖先祭祀而代之以其他纪念方式。⑦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都市,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受革命运动洗礼的乡村,祖先崇拜的纪念方式发生很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祭祀礼节趋向简单,祭祀仪式“昔时拜跪礼,今已改用鞠躬”⑧;祭祀名目减少,往时先辈忌日“每设席致祭”,而“今渐废”⑨;祠堂也有废弃的倾向,“昔年巨族皆建祠堂,今存者什之一,新建者寥寥”⑩,祭祀活动难以为继。而在闭塞落后的内陆地区和未受革命洗礼的广大乡村,除宗族大姓继续祠祭外,一般家庭中的家祭与墓祭还很盛行。每逢元旦、端午、中秋和冬至时节,农家一般在家自祭;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的日子,农家要赴墓前祭祖。 二、宗教信仰的此消彼长 佛教和道教作为中国传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社会信仰的主角。中华民国时期,伴随社会转型,它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呈现出陵替之势。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开始在诸多地区逐步站稳脚跟,拥有了相对稳定的信徒群体,并不断壮大。 1.传统宗教信仰日渐衰替 (1)传统宗教组织涣散、宗教精神衰微。佛教和道教呈现出组织、戒律涣散,无力与外界抗争的态势,为意图打击它们的力量提供了可乘之机。佛门教徒庞杂,戒律松弛,劈佛骂祖之风日盛;宗门视经典文字为障道之本。一些寺庙当权者据寺产为家私,对佛教的公共利益和存亡问题置若罔闻。教风日坏,时常出现僧侣吃喝嫖赌(11),寺僧在“诵经礼禅时夹唱淫词小曲”(12),尼姑参与贩卖鸦片烟土(13)等情况。道教界内部矛盾丛生,领袖人物只关心个人私利而置道教整体利益于不顾。这致使佛教、道教成为清朝末期与中华民国时期国家政策变更的直接受损者,如清末民初施行“寺产兴学”和废止教观政策时,他们不得不唯诺履行。 在近代科学兴起并逐步发展之时,中国传统宗教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根源在于教理的停滞和落后,如佛教只强调出家、死后的问题,或“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14)而忽视现实社会的改良及人类的进步。部分民众逐渐放弃传统宗教信仰,福建龙岩“从前颇尚僧道祈禳,此风今亦渐熄”;(15)河北省蓟县亦是“延僧道唪经,糊纸张”,后则“风气开通,多半废止”;(16)山东临淄的丧礼“有用僧尼道士作佛事者”,然“近多非之”。(17) (2)“寺产兴学”风潮中宗教载体遭破坏。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管理寺庙条例”,将管理寺庙的权力交予地方,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寺产兴学”的风潮,大量寺观被改建为学校、机关、军营等。在山东泰安,1915年全县共设学校348所,其中328所为寺庙改建而成,(18)占学校总数的94.25%;在河北定县,1914年有200处庙宇变为学堂,1915年又有45处改为学堂,而且“原有庙宇中的寺没有一座不被毁坏的”;(19)河北定县的东亭乡在辛亥革命前共有佛寺435座,到1928年仅存104座,其“62村中现在没有一个和尚或者尼姑”;(20)在江苏南京,清初共有佛寺69处,到民国年间只剩下11处;(21)在河北香河,“城内暨乡镇庙宇,尽为学校占用,无复僧道踪迹”。(22) 寺庙和道观的兴建与重修同样受到影响。据统计,山东22个州县的704处佛寺中,兴建于1860-1916年间者仅有1处,兴建于1916年以后者无一处;重修于1860年以前者165处,重修于1860-1916年间者有25处,重修于1916年以后者仅有5处。(23)在四川金堂,“寺庙多建自前明,历来但有修补,而无创建者”,且各处旧有寺庙“现在多借其地设立国民学校或半日学校”。(24)道观的情形亦是如此,山东省21个州县的328处道观中,兴建于1860-1916年间者仅有4处,兴建于1916年以后者无一处;(25)在定县被占用的135座庙宇中,仅有一座是供道士居住的,其余则作为学校或者办公地点。(26) (3)革命与战争对传统宗教的冲击。辛亥革命后,思想界视传统宗教信仰与活动为迷信,大力提倡“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高呼“戒除迎神、建蘸、拜经及诸迷信鬼神之习,戒除供奉偶像牌位、风水及阴阳禁忌之迷信”的口号,(27)同时发起社会改良会,使“专祠淫祀”大都被取消。四川安县,“人民智识进步,亦有仿而行之不信僧道之术者”(28);福建上杭县,僧道诵经“明礼之家多屏不用,民国后不用者尤众”(29)。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知识分子主张“破除迷信神权之说”,而且“一唱百和”,到处出现“毁坏佛像,打碎城隍,占据寺院庵观,驱逐僧道女尼”(30)的现象。在河北,昌黎县“僧徒日少”,“释教之式微久矣”;(31)香河县城内关帝庙“尚有男僧三人”,刘宋镇娘娘庙“女僧七八人而已”,不及过去的十分之一。(32)佛、道二教大受打击。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使中国传统宗教遭受到更大的损失:一是日本飞机的轰炸对寺庙、道观的破坏,二是日军驻扎在寺庙和道观,使其建筑设施被损毁,如用木匾、楹联烧火做饭等。这一时期,教徒人数与庙宇数量明显下降。以道教为例,山东蓬莱1920年有道观、道院、祠庙共339处,道徒9000多人;1936年道观锐减至159处,道徒仅1900人。(33)河北定县东亭乡的62个村中,仅有6个道士,均为娶妻者,以种田为生,不能再靠香火钱度日。(34)整个华北地区的道观亦很少,太原纯阳宫被当作手工业作坊,太原元通观成为咖啡业同业公会的办事处,济南迎祥宫成为纺棉的场所,济南长春观部分房屋被警察占用,泰安玉皇观连一个参拜者都没有。(35) 针对上述状况,佛教领袖曾力求通过创新佛学、改换僧制、兴办教育等方法,以实现佛教佛化世界的理想,受其影响,佛教界一度出现讲经成风、皈依佛门的复兴现象。但因中华民国时期的传统宗教失去旧时国家政权的支持与保护以及缺少团结一致的宗教组织和符合时代潮流的教理,其颓势难收。对于道教,因长久的历史影响,在一些地区民间道风犹盛,虔诚的信徒仍一如既往地崇奉灶神、财神、土地神等道教诸神,在云南、四川、福建、安徽等地香火尤甚。尤其是荒村僻壤之民祈福祝寿、安宅镇土、祈晴祷雨、避妖除邪、操办红白喜事等,仍请道士设坛作法。 2.西教信仰发展 西教自晚清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以来,发展较慢。中华民国成立后,在信教自由的大环境下,西方传教士千方百计地探索最佳的传教路径,以期增强其认同感及群众基础,使西教信仰得到了快速传播。一是信教人数不断增加,如新教徒1914年为25万,1918年35万,1926年40万,1937年65万,到1949年则达到70万左右;天主教徒亦是如此,1913年130万,1921年200余万,1932年250余万,到1949年则达350万之多。(36)二是宗教载体迅速发展,以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建造数量为例,20世纪30年代,安徽省的35个县共有清真寺168座,(37)广西的9个县有26座,(38)察哈尔的11个县有59座,(39)绥远省的13个县有38座,(40)江西省4个市县有7座,(41)河南省的55个市县有335座;(42)至20世纪40年代,其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宁夏有162座,(43)湖南省有58座,广西有29座,贵州省有23座,云南省有13座,(44)四川省有41座,西康省有13座,山东省有33座,北平市有27座,(45)青海省有163座,甘肃省有42座。(46)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清真寺已遍布国内。 西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调整中西文化差异,增强西教信徒的认同感。诸多在华传教士吸取清末教案的教训,纷纷著书立说,努力调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将其理论与儒家文化相结合,表达西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相通之意,诸如“中国最重五常,唯仁为首,与西教之爱人为己,同出一源”(47)等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同时,对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禁令的取消,使中国的西教信徒避免了因崇拜祖先而违反教规和因信仰西教而为世俗不容的两难境地。另外,培养大量中国传教士,以利于西教的传播与教徒之间的沟通。 其二,兴办慈善事业,扩大西教的群众基础。基督教根据中国各地不同的教育状况,兴办各类学校。据1914年统计,基督教会开办各类学校12000余所,学生达250000余人。天主教还致力于兴办孤儿院、育婴堂等福利慈善事业。又据1930年统计,天主教在全国兴办的孤儿院360余所,收养20000多名孤儿,育婴堂共收容50000多名婴儿。(48)这些措施扩大了西教在中国城乡社会的影响,吸引大批中国人加入教会。 其三,信教自由的宗教政策,扫除了西教的传播障碍。辛亥革命后,由于信教自由得到了历届政府的承认,社会各阶层也开始对义和团运动的后果进行反思,整个社会氛围有所改变。人们不再盲目地排斥基督教,而是更加理性地对待之,减少了许多传教障碍,推动西教在中国迅速传播。许多军政要人也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如孙中山、陈少白、冯玉祥等。 另外,宗教报刊的不断涌现为西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作了舆论上的宣传。如伊斯兰教,从1908年到1949年出版的涉及中国穆斯林的报刊不下百余种。一些报刊陆续报道朝觐者启程、回程的消息,产生了很大影响。至20世纪40年代,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中国特别是西北地区具有重大影响的宗教信仰,有的少数民族甚至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如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等。 中华民国时期,社会变革引起了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变化。以佛教和道教为代表的传统宗教信仰因封建政权与儒学文化支持的失却,日渐衰替之趋势不可扭转;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该时期发展较快,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冲击着传统的宗教信仰,中国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宗教信仰结构呈多元化趋向。 三、诸神信仰与迷信的混杂 晚清时期,民间信仰多元、驳杂,时人所信之神众多,构成一个庞杂的体系:除高位神玉皇大帝和西王母外,还有自然神灵、家庭神灵、吉庆神灵、爱情婚姻生育之神、凶恶之神、法力人物神、俗化的佛教道教神灵。对神灵的信仰已渗透于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民间仍流行相面、算命、测字、星象、风水、祈雨、祈子、求签、祈祷、巫术、跳神之俗等。神灵信仰与迷信杂糅的习俗广泛流传。至中华民国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破除神祀和废除迷信的政策,使诸神信仰与迷信活动“渐息”。 1.新旧事物更替与诸神废止 在制度革新方面,教育制度对文昌神祭拜的影响最具代表性。古代中国的读书人为考取功名,都希望得到文昌神的庇佑,对它顶礼膜拜;鸦片战争后,西学之风在中国逐渐兴起,科举不再是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读书人逐渐放弃了对文昌神的信仰;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文昌神失去了制度的庇护而不再流行。如河北武安,文昌神“大都皆文人热心功名利禄者祀之,今则减少”(49)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及新式教育的发展,文昌神几乎无人信奉,时人还编写了具有嘲笑意味的打油诗:“昔日蒙童来上学,无人不拜我文昌。自从开设学堂后,粽子糕儿久未尝。”(50)同时,作为庆祝中举的“开贺”之俗,“自科举废后,斯风遂革”(51)。 在新旧事物更替方面,城市管理对城隍神的影响最为突出。城隍原本是古代城市的保护神,但随着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发展,城市管理逐渐由“神佑”向“人治”转变,城隍祭拜自然废止。在河北,完县设建设局,“祀事久废”(52);昌黎县“官请城隍神像出门,祭于厉坛”(53)的活动辍停;阳原县因“科学时代知县事者”,县人“已不若前之迷信矣”,城隍“香火已衰”(54)。在河南封丘县,知县要去城隍关帝庙焚香祈雨,然民国后“此举近来以鲜行之者矣”(55)。 2.政府干预与迷信活动“渐息” 中华民国政府为“匡谬正俗,一扫妖妄”,颁布了一系列办法、条例,以限制社会中的迷信活动。如内政部于1928年9月公布“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1930年颁布“取缔经营迷信物品办法”。同时,视“迷信为进化之障碍”(56),督饬警察机关践行,以劝导民众,禁止迷信活动,扭转社会风气。 跳大神、巫蛊等迷信活动随政府禁令而得到控制,贵州仁怀“奉文禁革,其习渐息”,庆坛者“寥寥无几”(57);上海法华乡,延巫治病之风“稍戢矣”(58);吉林临江“官府禁令频颁,此等恶劣风气渐就泯没”(59);辽宁凤城自设巡警后“不时捕治,巫风渐息矣”(60)。烧香还愿被视作有伤风化的“巫风”,在辽宁安东“与跳神一并禁止”(61),桓仁“愚夫愚妇多被所惑,屡经严禁,此风稍息”(62)。另外,对土地公和土地婆的祭拜亦被废止,如四川巴县,“凡城市土地及福德会皆废除”(63)。 一些时令节气的习俗也被视为迷信,渐行止息。如河北迁安的盂兰盆会,向年“有僧道荐蘸,投河放灯,以救溺鬼”,中华民国后则“其例废除”(64);完县祭祀雹神时“旧日演剧四班,今渐衰落”(65)。在河南封丘旧时每年清明举行迎神赛,下元节城隍要出巡,人们举行大规模赛会,但“民国后出巡事停,此风亦革”(66)。在陕西宜川,过去每逢重阳节,人们登高远足,效桓景避灾之意,然“今乡民行者极鲜”(67)。 3.民智渐开与迷信“衰息” 鸦片战争后,西学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具有开启民智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除及新式教育的兴起,使国人的认知能力逐步提高;新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使科学、民主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因此,民众逐渐认识到封建迷信毒害社会、蛊惑人心的弊病。 四川金堂县旧时巫祝盛行,“近日民智渐开,知信巫不如信医,故斯事渐罕见”,“迷信之风亦早自破矣”(68);合江县术数“浸渍已深,贤者不免”,而“今者科学日明,笃信者渐鲜矣”(69)。贵州兴仁县政府明令破除迷信,加以教育渐展,科学输入,信巫之风“稍杀矣”(70)。广西武鸣县“夫仙婆之为害固巨”,然近来“民皆渐开,迷信者亦罕矣”(71)。湖南龙山县祈禳之风盛行,而“近土民读书讲礼教,多惭为是者,其俗竟衰息”(72)。 中华民国时期,封建礼教约束下的包办婚姻开始被自由恋爱取代,因此,青年男女也不再祭拜月老。时人发出感叹:“今日红线多不用,由他男女自成亲。”(73)另外,随着封建皇权的终结和民主自由之风的兴起,当权者也不需要利用玉皇大帝这一传统崇拜偶像来为政权张势,人们亦有“人间处处倡民主,天上谁人奉玉皇”(74)的慨叹。 民间信仰虽呈陵夷之势,但植根于民众内心深处、属于意识层面的传统观念仍有着深厚的生存土壤,且自然神、人物神、宗教神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被涂抹上浓厚的迷信色彩,巫术、占卜、星象、风水、灵物、祈禳等迷信手段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些神灵的精神力量。因此,迷信活动被人们看成人神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破除。所谓“穷乡僻壤巫风最盛”,虽政府有破除迷信举措,但“信仰既深,尚非仓猝所能挽回焉”(75)。如辽宁义县,对财神“商铺必供之,住户供之亦夥”(76);河南荥阳,敬神之风“愈演愈奢”,虽“绅耆累议裁制,而势不能禁”(77);四川巴县“尚鬼信巫,巴俗至今犹然也”(78);华东许多地方“习俗尚鬼,信卜筮,好淫祀”,且“迷信之风,盖牢不可破”(79)。即使在严禁跳神的东北,也是“习俗既深,迄今尚有暗中偷行者,未能一律禁绝也”(80)。 社会上层掌权者中仍有运用权力进行祀天、信鬼、修仙、扶乩活动及迷信宣传,发出“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81)的危言耸听之辞。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平日主有鬼论勘”,断言“鬼之存在至今日无丝毫疑义”(82)。特别是社会下层因无力改变残酷的现实,只能乞求鬼神避祸求福、逢凶化吉。社会各阶层的上述信仰寻求状态,使得左道邪术横行,加之民间信仰的混杂影响了人们的客观判断,一些人乘机把民间信仰作为装神弄鬼、敛钱惑众的工具。在北京,有人先行蛊惑“妖术”,欺骗妇女、儿童,并以画符破解,“每符一道,铜元一枚”,以此敛财(83);上海有女巫杨氏“妖言惑众,骗人钱财。声言三老爷能治疾病,并可求财得财,求子得子。以致一般愚夫愚妇,不惜金钱前往烧香祈祷”(84);天津、南京等大城市也不断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大公报》等媒体时有报道。更有甚者,还有谋财害命之举。在黑龙江双城,跳神之辈在为人治病时“有害命及奸淫之事发生”(85)。 中华民国时期,社会信仰态势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嬗变,总体呈现出新旧并存、传统衰微的局面。一是多元化倾向明显,社会转型给人们的社会信仰注入了新的成分,西方传教士极力推动西教的传播,基督教、伊斯兰教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改变了中华民国社会宗教信仰的结构;祖先崇拜、传统宗教信仰及民间信仰仍有较大的市场。二是宗教信仰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在少数城市,西教信徒甚至超过了传统宗教信徒,严重冲击着以佛教与道教为代表的传统宗教,但在广大乡村,西教还是无法与传统宗教相抗衡。三是迷信仍占据重要地位。民初,迷信现象虽“历经严禁,其风少息”(86),但由于“一般无识愚民遂深滋迷惑,牢不可破”(87),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此风仍未艾也”(88),盖“非一朝一夕之积习故也”(89)。 可见,社会信仰的嬗变与社会环境的变革有着直接关联,社会制度与政治权力决定了社会信仰的发展方向,外来宗教势力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内部的社会信仰。因此,对中华民国时期社会信仰嬗变的缘由进行探析,有利于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社会的变迁。 ①西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1辑,西安:西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1985年,第472-473、474-475页。 ②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论据论》,载赵清、郑成编:《吴虞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4页。 ③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页。 ④李石曾:《祖宗革命》,《新世纪》1907年第2期。 ⑤周作人:《祖先崇拜》,《每周评论》1919年第10期。 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上,上海:黎明书局,1935年,第44页。 ⑦周叔昭:《家庭问题的调查》,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62页。 ⑧王维樑等修、廖立元等纂:《明溪县志》卷11《礼俗志·礼仪》,1943年铅印本,第5页。 ⑨詹宣猷修、蒋振坚等纂:《建瓯县志》卷19《礼俗》,建瓯:芝新印刷所铅印本,第5页。 ⑩徐恕修、张南英等纂:《平阳县志》卷5《风土·风俗》,1760年刻本,第5页。 (11)《僧人宿娼累及巡长》,《申报》1914年6月25日,第7版。 (12)《通令禁止寺僧滥唱淫词》,《申报》1914年5月18日,第11版。 (13)《女尼亦贩烟土》,《申报》1914年9月14日,第7版。 (14)真禅:《玉佛丈室集》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87页。 (15)马龢鸣等修、杜翰生等纂:《龙岩县志》卷21《礼俗志》,1920年排印本,第9页。 (16)徐葆营修、仇锡廷纂:《蓟县志》卷3《乡镇·风俗》,1944年铅印本,第58页。 (17)舒孝先修、崔象毂纂:《临淄县志》卷15《礼俗志·丧葬》,1920年石印本,第40页。 (18)葛廷瑛等修、孟昭章等纂:《重修泰安县志》卷5《政教志》,1929年铅印本,第4-50页。 (19)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11页。 (20)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12页。 (21)叶楚伧等主编、王焕镳纂:《首都志》下卷14《宗教》,1935年铅印本,第1217-1278页。 (22)王葆安修、马文焕等纂:《香河县志》卷5《风土·宗教》,1936年铅印本,第1页。 (23)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745页。 (24)王暨英等修、曾茂林等纂:《金堂县续志》卷1《疆域志·礼俗》,1921年刻本,第65页。 (25)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743-774页。 (26)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22页。 (27)蔡元培等:《社会改良会宣言》,《民视报》1912年3月19日,第3版。 (28)夏时行等修、刘公旭等纂:《安县志》卷55《礼俗·迷信》,1938年石印本,第8页。 (29)张汉等修、丘复等纂:《上杭县志》卷20《礼俗志》,1939年铅印本,第6页。 (30)《三教大会议》,《大公报》1912年12月19日,第3张第2版。 (31)金良骥等修、张念祖等纂:《昌黎县志》卷5《风土志》,1933年铅印本,第20页。 (32)王葆安修、马文焕等纂:《香河县志》卷5《风土·宗教》,1936年铅印本,第1页。 (33)张玉法等:《民国山东通志》卷21《宗教志》,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2002年,第2046页。 (34)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22页。 (35)窐德忠:《道教史》,萧坤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87页。 (36)牟钟鉴、张践:《中国民国宗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2-116页。 (37)《全国清真寺调查表——安徽省》(1—6),《月华》1931年第3卷第16-17、19-23期。 (38)《全国清真寺调查表——广西省》,《月华》1931年第3卷第24期。 (39)《全国清真寺调查表——察哈尔省》(1—2),《月华》1931年第3卷第25-26期。 (40)《全国清真寺调查表——绥远省》(1—2),《月华》1931年第3卷第27-28期。 (41)《全国清真寺调查表——江西省》,《月华》1931年第3卷第29期。 (42)《全国清真寺调查表——河南省》(1—5),《月华》1931年第3卷第32-36期;《全国清真寺调查表——河南省》(6—11),《月华》1932年第4卷第2-3、5、9-13期。 (43)汪沛辑:《中国清真寺寺址调查表》,《突崛》1940年第7卷第5-6期。 (44)汪沛辑:《中国清真寺寺址调查表》(续),《突崛》1940年第7卷第9-10期。 (45)汪沛辑:《中国清真寺寺址调查表》(续),《突崛》1940年第7卷第11-12期。 (46)汪沛辑:《中国清真寺寺址调查表》(续),《突崛》1940年第8卷第1-2期。 (47)李提摩太:《新政策(节录)》,载《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年,第234页。 (48)牟钟鉴、张践:《中国民国宗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128页。 (49)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72页。 (50)遒铎:《嘲旧神诗·文昌怨》,《申报》1912年2月3日,第8版。 (51)范钟湘等修、金念祖等纂:《嘉定县续志》卷5《风土志·风俗》,1930年铅印本,第8页。 (52)彭作桢修、刘玉田等纂:《完县新志》卷8《风土》,1934年铅印本,第4页。 (53)金良骥等修、张念祖等纂:《昌黎县志》卷5《风土志》,1933年铅印本,第25页。 (54)刘志鸿修、李泰棻纂:《阳原县志》卷10《礼俗》,1935年铅印本,第4页。 (55)姚家望修、黄荫柟纂:《封丘县续志》卷2《地理志》,1937年铅印本,第23页。 (56)朱之洪等修、向楚等纂:《巴县志》卷5《礼俗》,1939年刻本,第58页。 (57)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52页。 (58)王钟纂、胡人凤续纂:《法华乡志》卷2《风俗》,1922年铅印本,第2页。 (59)刘维清等修、罗宝书等纂:《临江县志》卷7《民族志》,1935年铅印本,第10页。 (60)马龙潭等修、蒋龄益等纂:《凤城县志》卷12《礼俗志》,1921年石印本,第14页。 (61)关定保等修、于云峰等纂:《安东县志》卷7《神道》,1931年铅印本,第45页。 (62)侯锡爵修、罗明述纂:《桓仁县志》卷9《风俗志》,1930年石印本,第6页。 (63)朱之洪等修、向楚等纂:《巴县志》卷5《礼俗》,1939年刻本,第58页。 (64)滕绍周修、王维贤纂:《迁安县志》卷19《谣俗篇》,1931年铅印本,第9页。 (65)彭作桢修、刘玉田等纂:《完县新志》卷8《风土》,1934年铅印本,第4页。 (66)姚家望修、黄荫柟纂:《封丘县续志》卷2《地理志》,1937年铅印本,第23页。 (67)余正东纂修、黎锦熙校订:《宜川县志》卷23《风俗志》,1944年铅印本,第3页。 (68)王暨英等修、曾茂林等纂:《金堂县续志》卷1《疆域志》,1921年刻本,第65页。 (69)王玉璋修、刘天锡等纂:《合江县志》卷4《礼俗》,1929年铅印本,第50页。 (70)冉晸修、张俊颖纂:《兴仁县志》卷9《风俗志》,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油印本,第18页。 (71)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890页。 (72)符为霖修、吕懋恒纂:《龙山县志》卷11《风俗》,1878年刻本,第14页。 (73)遒铎:《嘲旧神诗·月老怨》,《申报》1912年2月3日,第8版。 (74)遒铎:《嘲旧神诗·玉皇怨》,《申报》1912年2月3日,第8版。 (75)邹古愚修、邹鹄纂:《获嘉县志》卷9《风俗》,1934年铅印本,第17页。 (76)赵兴德等修、薛俊昇等纂:《义县志》中卷《民事志》,1931年铅印本,第47页。 (77)张向农修、张炘等纂:《续荥阳县志》卷2《舆地志》,1924年铅印本,第13页。 (78)朱之洪等修、向楚等纂:《巴县志》卷5《礼俗》,1939年刻本,第55页。 (79)高如圭原纂:《章练小志》卷3《风俗方言》,1918年铅印本,第2页。 (80)关定保等修、于云峰等纂:《安东县志》卷7《神道》,1931年铅印本,第45页。 (81)陈大齐:《辟“灵学”》,《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号。 (82)胡绳:《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与科学》,载龚书铎主编:《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95页。 (83)《妖道造谣骗钱之诡术》,《大公报》1914年6月27日,第2版。 (84)《女巫接到吓诈信函》,《申报》1917年10月8日,第10版。 (85)高文垣等、张鼒铭等纂:《双城县志》卷6《礼俗志》,1926年铅印本,第35页。 (86)覃卓吾等纂修:《三江县志》卷2,1946年铅印本,第22页。 (87)邹古愚修、邹鹄纂:《获嘉县志》卷9,1934年铅印本,第17页。 (88)祁卓如等修、韩敏修纂:《广宗县志》卷4,1933年铅印本,第4页。 (89)覃卓吾等纂修:《三江县志》卷2,1946年铅印本,第22页。标签:祖先崇拜论文; 迷信活动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化论文; 申报论文; 祭祀论文; 中华民国政府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