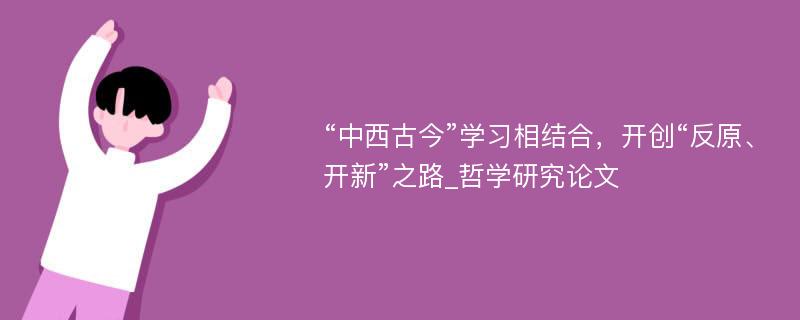
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古今论文,中西论文,开新论文,之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六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 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影响着中国文化的 进程。第一次是自公元一世纪以来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第二次外来文化的传入可以说 是自16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两次重大外来文化的传入大大 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罗素曾在他的《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说:“不同文明之间 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注:罗素《中西文明比较》, 引自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上述两次外来文化的 传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它每一次都使得中 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它深刻地反映着一个 时代的精神面貌。为了说明“在西方哲学冲击下的中国哲学发展”,本文打算先回顾一 下印度佛教传入的历史,看看是否对西方哲学的传入有什么可以借鉴之处。
印度佛教(包括它作为哲学思想)传入中国大体上说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1)由西汉末 至东晋,佛教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佛教传入中国后 ,开始相当长一个阶段所讲的内容主要是“魂灵不死”、“因果报应”之类,在中国实 有这类相似的思想,故佛教可依附而流行。至汉末魏初,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渐多,而 分成两大系在我国流传:一为安世高系,是小乘佛教,重禅法,时《安般守意经》、《 阴持入经》等已译成汉文。或讲呼吸守意,而与道家、神仙家相类;或以“五阴”(即 五蕴)配“五行”,“五戒”配“五常”,说“元气”即“五行”即“五阴”。这些附 会之说自与佛教不相牟合;二为支娄迦谶系,为大乘佛教,讲般若学。支娄迦谶一系认 为人生根本道理最重要的是使“神返本真”,而与“道”合,此已见受老庄思想之影响 ,而渐依附于魏晋之玄学。盖因玄学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而佛教般若之“ 空”、“有”问题与之颇相接近。东晋初,般若学虽有“六家七宗”之分,但其讨论的 基本问题仍是玄学的“本末有无”之辨。而僧肇之《肇论》既是魏晋玄学之总结,又是 中国佛学中国化之初始。(2)东晋后,佛典翻译渐多,且系统。已见印度佛教与中土文 化之不同,而引起两种不同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并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影响和吸收。从今 日保存之《弘明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争论的问题有“沙门应否敬王者”、“神 灭、神不灭”、“因果报应有无”、“空有关系”以及“夷夏之辨”等等,且此时期佛 道两教的争论则更为激烈,如有“老子化胡问题”、“轮回与承负问题”、“神形与生 死问题”等等。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儒、道、佛三家也在互相吸收着。特别是道教大量吸 收了佛教的思想,而佛教则容纳了儒家思想的若干成分,此时已有儒士而信佛,如刘勰 ,道士而立佛道二堂,如陶弘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说,存在着中国朝野对外来佛教 文化,采取的是吸收、容纳、甚至在某种程度抱着欢迎的态度。(3)自隋唐以后,印度 佛教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六 经数十百倍”。同时中国文化又深深地改变着佛教文化的形态。特别是在儒、道两家的 影响下,形成了若干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例如天台、华严、禅宗在心性问题上融合了中 国儒家的心性学说,天台甚至吸收着道教的某些思想,而华严和禅宗无论在内容与方法 上都与老庄思想(如“任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宋后,可以说印度佛教完全融 化在中国文化之中(此时印度佛教在印度几乎已经断绝),形成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
西方文化(景教)早在唐朝已传入中国,后因唐武宗灭佛而波及景教。此后景教在中国 逐渐消失,而元朝的也里温可教也随着元朝的覆亡灰飞烟灭了。西方文化真正对中国文 化发生影响是在16世纪末,当时传入的主要是西方基督教耶稣会的一些学说。这时的传 教士采取的策略是使基督教附会于原始儒家思想(如利玛窦),而中国之士大夫除个别人 (如徐光启、李之藻)皈依了基督教外,绝大多数士人或对基督教持反对态度,或以中国 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来了解基督教,或欣赏西方的奇巧技艺。这点从某个方面看有点 像佛教传入之初。至清初,因礼仪之争,西方文化的传入有所中断。19世纪中叶随着西 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中国。自此在中国存在着长达百多年的“中 西古今”文化之争。
清末,“中体西用”开始曾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尔后随着某些学者对西方文化了解 较多而逐渐有所改变,其中介绍西学最有力者为严复。民国以后,“中西古今”之争仍 然不断,袁世凯称帝之前有“孔教会”之建立,以儒家思想排斥、批判西方文化。其后 于1915年始有以杜西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青年》杂志的争论 。大约与此同时或稍后,有胡适与李大钊等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五四运动前后 可以说是中西文化论战之高峰。以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 主义派和属于实用主义阵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胡适联合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提倡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由五四运动引进的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力,自然也会引起 “中学”的反击。当时最著名的维护中国传统的学者一是梁启超,一是梁漱溟。梁启超 的《欧游心影录》对西方科学的批判虽有广泛的影响,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相当深刻的回应。1923年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 论战,这次论战表面上看来以“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等等)对 “中学”(以张君励为代表的“新宋学”)的胜利告终。但其结果造成了陈独秀为代表的 马克思主义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派的分裂。自此以后,在中国文化问题实际上 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激进派、实用主义改良派和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发生 在20年代末的“哲学问题”论战和其后的“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问题”论战,都表现 在“中西古今”之争。1935年,萨孟武等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再 次掀起大规模的“中西古今”之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抗日,中西文化论战 缓和了一些,但仍然发生过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和维也纳学派洪 谦教授与冯友兰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争论,这些也都反映着哲学上的“中西古今”之争 。
1949年后,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中国的文化也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 化,当时有所谓“一边倒”的政策,全盘倒向苏联,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全盘 西化”的表现。这时要求中国思想文化界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以及日丹诺夫的三个讲话为指导,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大搞所谓“破四旧”,其结果造成中国的思想文化与世界思想 文化的隔绝,使中国思想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断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虽然在政治路线 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文化上的“古今中外”之争仍然没有停止。80年代中 国思想文化界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因此必须批判封闭式的专 制主义的新老传统的影响。90年代初,在学术文化界有两种思潮逐渐活跃,一是“后现 代主义”思潮;一是“新保守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进入中国, 但没有广泛流行,到90年代初突然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特别流行的思潮。为打破思想 文化上的一元化,因而大量引进和阐发“后现代主义理论”。稍晚,大约在1992年在祖 国大陆出现了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部分学者有见于西方文化给人类 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或许可以纠正西方文化的某些偏失。1994年 6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一些人宣扬孔夫子、董仲 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中国哲学新体系”,“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 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摈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1995年初在《孔 子研究》杂志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不少学者对上述《哲学研究》的看法提出了批评 。同年,《东方》杂志有署名文章也批评了《哲学研究》,认为把“国学”研究与马克 思主义研究对立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可能,“即把马克思主义与国学研究对立起来,重 新以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国学’的怀疑和批判”。这场发生在90年代中期的争论虽 未发生重大影响,但从一个侧面看,仍然是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的表现。与此同 时,某些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基督教文化有较深研究的学者,对中国文化持强烈批判 态度,也就引起了某些传统文化的保守派的反击,并促使了在海外流行的现代新儒学在 祖国大陆得到某些学者的认同。其时还有一部分学者对中西文化都有所了解,而企图调 和两者之间的分歧,在不同中求得相互理解,以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至90年代末发生 在中国的“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之间的争论,至今仍在继承之中,但旁观者一般 都认为仍然围绕着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不能不看到这还是与“中西古今”之争有 关。
近百年来,在我国一直存在的“中西古今”之争,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全盘西化”和 “本位文化”之争。其中包含着把“古”与“今”对立起来的思想趋向,这种简单化地 处理文化间问题思想方法,是不利于文化健康合理发展的。当前,我们应该抛弃把“中 ”与“西”和“今”与“古”对立起来的观点,走出“中西古今”之争。根据以上的分 析,我们是否可以说,我国目前文化发展似乎正处在如南北朝至隋唐之间,印度佛教对 中国文化冲击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化之初,即由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阶段转向本土 文化,开始消化外来文化的第三阶段。在这第三阶段中,我们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走出 “中西古今”之争,而进入全面、深入地吸收、融合西方文化的时期。要走出“中西古 今”之争,也许应把握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我们应该看到中西两种文化虽有相异之处 ,但也有“相同”之处,而且即使所谓“相异”,也可以在对话与商谈中得以调和,而 做到“和而不同”。第二,任何文化都会因其地理的、历史的、民族的甚至某些偶然的 原因而有其优长处,也有其短缺处,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完全地解决所有民族存在的问题 ,或者说它可以解决人类存在的一切问题。古代的思想固然是在当时环境中产生的问题 ,它虽有时代性,但是古人所考虑的问题也是人类的问题。所以它同样存在着超时代性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哲学虽千变万化,但它思考的问题大体上仍然是古希腊哲学家提 出的问题或者是那些问题的延伸。当代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同时大体上也还是先秦时代 各家提出的问题或者是那些问题的延伸。所以雅斯贝尔斯说的:“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 所产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 焰。”(注: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4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我认为 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
下面我打算以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为例,来说明中国哲学在与西方哲学相遇后,现在 正是处在如同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三期之初那个时期,正在走向吸收和融合西方哲学的 时期,并可以预期在经过一个不太长的时候,会形成全新的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同的现代 中国哲学。
中国原来没有“哲学”一辞,甚至相当多的西方哲学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例如 黑格尔认为中国所有的只是意见,“与意见相反的是真理”。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 中说到东方思想,他说:“我们在这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他谈到孔子时说:“孔子 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他那里思辨的哲学一点也没有——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 、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97页,119页,北京,商务印 书馆,1959年)“哲学”(philosophy)一辞最早是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借用汉语 “哲”、“学”两字指称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学说,中国学者黄遵宪(1848—1905)将 这个名称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如果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大概可以 说在西方哲学传入之前,在中国还没有把“哲学”从“经学”、“子学”单独分离出来 ,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而“哲学思想”、“哲学问题”的研究往往包 含在“经学”、“子学”等之中来进行的。这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自觉地把“哲学”作 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对象。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中国没有哲学”。从中国历史上 看,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这点大体上已得到许多现今中外学者的承认,不 过我们也得承认正是由于有西方哲学的传入,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参照系,才逐步使“中 国的哲学”由“经学”、“子学”等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把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最有影响的应该说是严复,他翻译《天演论》等书,进化 论思想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哲学观念,可以说他是介绍西方哲学到中国来的第一功臣。 其后,继之以康德哲学、叔本华哲学、尼采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古希 腊哲学、实用主义,实在论、黑格尔哲学、分析哲学(罗素等)、维也纳学派哲学、现象 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先后进入中国,影响着中国哲 学界(这有点像由南北朝到隋唐印度佛教的大小乘经、律、论的各种思潮传入中国的情 形一样)。从20世纪初起,“中国哲学”的建立可以说是从研究“中国哲学”的历史入 手的,先是出版了若干种《中国哲学史》,其中可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英文 本原名《先秦名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于1916年,早于胡适的《中国哲 学史大纲》,其后有不少《中国哲学史》的书出版,这里不一一例举了)和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为代表,以证明自先秦以来中国就有自己的哲学。这说明,中国学者自觉 地把“中国哲学”从“经学”和“子学”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了。这正 是在西方哲学输入后的态势,其间又有若干中西哲学比较的书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有 代表性的可以说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它以文化的类型不同来说明中西哲 学之间的差异。特别应说明的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对五四运动 以来“反传统”、“提倡西学”的一次认真的反思。在这本书中,梁漱溟认为中国应引 进西方文化与哲学,让“科学与民主”也在中国得到发展,并反复申明:“我们提倡东 方文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文化不同。”在这本书中甚至可以明确地看到他的哲学思想 受着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深刻影响。但同时梁漱溟对西方哲学进行了批评,并主张把中国 原有的文化精神拿出来,救助当时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自30年代初起,中国哲学家在 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现代型的“中国哲学”,先有熊十力和张东荪,后 有冯友兰和金岳霖等,还有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一定中国特色的毛泽东的《实践论》和《 矛盾论》等。这些都说明,中国学者(包括个别政治人物)都在努力吸收西方哲学,以建 立中国自己的哲学的尝试。
熊十力著《新唯识论》只完成了其哲学的“本体论”(境论)部分(在其中也可以看到一 定程度受到柏格森哲学的影响),但他原计划还要写“认识论”(量论),这点我们可以 从他的其他著作中看到他的“量论”的基本思路。他认为,“中国哲学”原来缺乏“认 识论”,因此他主张要在中国哲学中创建中国式的认识论,如他说:“吾国学术,风尚 体认而轻辨智,其长在是,而短亦伏焉”,故“中西文化,宜互相融合”,“中国诚宜 融摄西洋而自广”。(注:熊十力:《答某生》,见《十力语要》,卷二,《复性书院 开讲示诸生》(收入《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和《十力语要 初读》(收入《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为此之故,熊十 力提出:“余常以哲学为思修交尽之学”,盖因“专尚思辨者,可以睿智,而以缺乏修 为故,则理智终离其本,无可语上达。专重修为者,可以养性智,而以不务思辨故,则 性智将遗其用,无可成全德也。是故思修交尽,二智圆融,而后为至人之学”。(注: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收入《熊十力全集》,第三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 01年。)可见熊十力是在吸收西方哲学,为创建中国现代哲学而努力。特别是熊十力哲 学的“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等都是沿着《周易》哲学在新时代的对中国哲学的重 要发展。熊十力开启了现代新儒学,继之者有牟宗三引康德入现代新儒学、唐君毅引黑 格尔入现代新儒学,成为传承当今儒学者的中坚力量。张东荪提出其“多元认识论”体 系和“架构论”学说,他的学说是在吸收新康德学派学说和批判实在论思想基础上,提 出的一种以研究“认识论”为中心的一种现代型“中国哲学”。张东荪的哲学思路与金 岳霖不同:金岳霖哲学是知识论向本体论看齐;张东荪哲学则追求宇宙论向知识论看齐 ,并否认中国有“本体论”。(注:张耀南:《张东荪》,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 年。)照我看,他们两位的哲学正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两大系:《周易》哲学中的本体论 思想和宇宙生成论思想,但都是借助了西方哲学来建构他们的哲学体系。金岳霖是用分 析哲学和逻辑实论证的方法来写他的《论道》和《知识论》的,他的哲学的特长是在借 助分析哲学上。从形式上看,他的哲学很不像中国哲学,但就内容上看却可感到他的思 想深受儒道两家哲学之影响。例如他以“不存在而有”来说“理”就更加体现其中国式 的智慧。冯友兰的《新理学》明确地说,他的哲学不是照着宋明理学讲,而是接着宋明 理学讲。他的“接着讲”实际上是把柏拉图的“共相”与“殊相”以及新实在论的思想 引入中国哲学,把世界分为“真际”(或称之为“理”或称之为“太极”)和“实际”, 实际的事物依照所以然之理而成为某事物。冯友兰哲学区分“真际”和“实际”一方面 上可接宋明儒的“理一分殊”学说,另一方面又可以把西方哲学“共相”与“殊相”的 观点贯穿于中国哲学之中。他的《新知言》更是企图从方法论上调和中西哲学。冯友兰 认为西方哲学长于分析(形而上正的方法),而中国传统哲学则长于直觉(形而上负的方 法),他的“新理学”的方法则是这两种方法的结合。这些都说明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 在努力借助西方哲学来建立新的“中国哲学”的尝试。同时,汤用彤为证明中国也有其 本体论,并有其特殊的哲学方法“得意忘言”而研究了魏晋玄学,为这方面开辟了一新 的领域。他为打通由魏晋到隋唐思想发展之线索,效法德国哲学史家蔡勒尔(Zeller)治 希腊哲学史的方法来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已成为今日权威之作。而用彤先生 早年留美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因此他的思想也打上了西学的烙印。在这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新的“中国哲学”在中国影响比较大,有些则比较小,例如冯友 兰、熊十力两人的哲学影响就比金岳霖、张东荪大,这是因为冯友兰、熊十力都是较好 地“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而金岳霖、张东荪哲学则更加较为西化一些。但这些学 者在创建现代中国哲学中,都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缺乏“认识论”(Epistemology)这个 事实,而力图为中国哲学补上这个缺陷,这当然正是受到西方近代哲学影响的结果。如 果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参照西方哲学为了说明有“中国的哲学”,是建立中国 哲学的第一步,那么这里说的熊十力、张东荪、冯友兰、金岳霖等的哲学则是在西方哲 学冲击下,或深或浅地借助西方哲学,来建立他们的现代中国哲学。但是我们客观地说 ,张东荪、金岳霖的哲学不能不说相当深刻,但他们的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则比不上 熊十力和冯友兰。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正是熊十力、冯友兰哲学是较好地接着宋明理 学之故,因此他们的哲学更具有中国特色。而张东荪、金岳霖的哲学从方法论上说更重 分析,而多少有外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之倾向。我们可以看到,熊十力哲学虽然容纳了西 方哲学的若干“思辨性”,也较中国传统哲学增加了若干分析成分(其分析成分或更多 来自印度佛教的“唯识学”),但它仍然是沿着中国哲学整体性和直觉性的特征发展着 。他的后继者或者更多地吸收了西方哲学的理论与方法,但仍然没有离开熊十力开创的 路子。冯友兰在运用逻辑分析方面自然比熊十力高明,而且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大得多, 但如前所说,他的哲学仍接着宋明理学的“现代中国哲学”。而较多逻辑分析的哲学( 如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在中国比较难以有较大影响。从这点看,两种不同哲学在相遇 后,必然在互动中有着双向选择的问题。但我们同时可以注意到,某些研究西方哲学( 或中西哲学同时都研究)的我国学者都曾努力利用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进行解读(或者说 他们在解释西方哲学时多少带有中国特色),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把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尝 试吧!这种企图使西方哲学中国化或者吸收西方哲学而使中国哲学具有现代意义的各种 尝试,这些学者的努力虽非常可贵,但他们都还不能和隋唐时期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哲 学的影响及其意义相比,中国哲学仍然还未如宋明时期在批判和吸收印度佛教哲学后创 造的新儒学那样,创建出适应中国现代社会以及世界哲学发展形势的要求的“现代中国 哲学”。
1949年后,由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开始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全盘学习苏联。 在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上,一方面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日丹诺 夫的《在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另一方面以极“左”思想来批判中国传 统文化,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这仍可说是一种有着浓厚政治 色彩的“中西古今”之争,致使中国哲学出现了断层。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由于实行 “改革”、“开放”政策,自80年代起,西方哲学各派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先是存在 主义、尼采哲学、接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以至解构主义、后现代 主义和诠释学、符号学等等都被介绍到中国来,这不仅打开了中国哲学界学者的眼界, 而且给中国哲学界多角度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照系。这真有点像南北朝到 隋唐时期印度佛教大量传入中国一样,再次大大地冲击着中国的哲学界。这正是给中国 哲学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用一句套话说这对中国哲学既是一次机遇,又是一次挑战。 进入21世纪,中国哲学应如何发展?这当然是众多中国哲学家(或者中国哲学工作者)所 十分关心的问题,但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现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很 可能会像唐朝时期那样出现众多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一样,出现若干中国化的西方哲学 的流派。例如我们也许应该在学习和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中国化的存在主义、 中国化的现象学、中国化的解构主义、中国化的后现代主义、中国化的诠释学、中国化 的符号学等等。如果中国哲学界真能如此,我想至少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两个方面非常 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我们不仅是单方面的吸收西方哲学,而与此同时使中国哲学加入到 西方各派哲学之中,这样可以使西方哲学增加若干中国哲学的资源,丰富了西方哲学的 视野,并使中国哲学与当今世界哲学的主流接轨。另一方面在创建中国的现象学、诠释 学等等之中,提升着中国哲学的内涵,把中国哲学引入到关注世界哲学发展的主潮之中 。也许会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使中国哲学失去其为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 学的附庸?我认为不会的。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 百倍”,中国并没有因此变为佛教国家。更何况正是由于中国哲学受惠于印度佛教,才 促使中国哲学大大发展了,并通过佛教的中国化,才形成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当然我们 在创建中国的现象学,中国的诠释学等等的同时也并不妨碍同时发展不同派别的现代新 儒学、或者创建现代新道家。但是,无论现代新儒学或现代新道家都必定是经过西方哲 学洗礼的现代中国哲学。中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化根基,它的哲学不会因为受到当前 的西方强势哲学而失去自我的,它的生命力应该正是在大力地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和国 家的文化中来壮大自己的文化。正因为当今中国是处在一个大的文化转型期,文化上的 多元化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应该自觉地走出“中西文化”之争的阶段。
也许人们会问,能否举出例证来证明我的观点。对此我无力作全面的回答,但我想可 以举出一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我认为,在上个世纪末中国最应注意 的哲学家是冯契先生。冯契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但他力图在充分吸收中国传统 哲学和西方分析哲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的《智慧三说 》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得较为 成功的典范。冯契先生在他的《导论》中一开头就说:“本篇主旨在讲基于实践的认识 过程的辩证法,特别是如何通过‘转识成智’的飞跃,获得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冯 契先生不是用实践的唯物辩证法去解决“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而用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来讨论中国哲学“性与天道”问题(“性与天道”问题主要不是讨论认识 论的问题,而是讨论人生境界问题),而如何获得“性与天道”的认识,又是借用了佛 教的“转识成智”,他说:“通过实践基础上的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人与 自然、性与天道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互相促进,经过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 终于达到转识成智,造成自由的德性,体验到相对中的绝对、有限中的无限。”接着冯 契先生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经验”、“主体”、“知识”、“智慧”、“道德”等 等层层分析,得出如何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转识成智”,由此他提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命题:“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他对这个命题的解释说:“哲学 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研究的领域;另一方面又要通过 自己的身体力行,化为自己的德行,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无论“化理论为方法 ”,还是“化理论为德性”,都离不开实践的辩证法。“化理论为方法”,不仅是取得 “知识”的方法,也是取得“智慧”的方法。但“智慧”与“知识”不同,“知识”所 及为可名言之域,而“智慧”所达为超名言之域,这就要“转识成智”。而“转识成智 ”要“凭理性的直觉才能把握”。对此冯契解释说:“哲学的理性的直觉的根本特点, 就在于具体生动的领悟到无限的、绝对的东西,这样的领悟是理性思维和德性培养的飞 跃。”“理性的直觉”是在逻辑分析基础上“思辨的综合”而形成的一种飞跃。如果没 有逻辑分析,就没有说服力;不在逻辑分析基础上作“思辨的综合”,就不可能为哲学 研究提供新的方向。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冯契同志运用逻辑的分析和思辨的结合的深 厚功力,正是由于此,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才具有理论的力量,也说明他研究哲学的目 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用实践唯物辩证法来解决“性与天道”这一古老又常新的中国哲学问 题。我认为,只有像冯契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解释中国哲学问题,才是创建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经之路。
这里我还想再举一个例子,这就是自1998年起我提出的“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我 们知道,中国有着比西方更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但是中国却没有建立起一套系统的解 释哲学问题的理论与方法。而在西方,主要是由解释《圣经》开始,经过了好几个世纪 漫长的酝酿过程到德国哲学家兼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rmacher,1768— 1834)和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狄尔泰(W.Dilthey,1835—1911)才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哲 学理论体系。这就是说,在西方“解释”成为一种“学”也只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为 什么中国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而没有“中国的解释学”,这里有一个“文化自觉 ”的问题。因为在西方解释学传入中国之前,我们还没有自觉到要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对 经典解释的各种方法和理论总结起来使之成为一种“学”。一种“学”(理论体系)的建 立应该是对其研究的对象有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即自觉地把要研究的对象作为“对 象”来研究,并能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系统的理论与方法。现在西方解释学传到了我国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参照系,来考虑创建中国解释学了。我们能否建立起不同于西 方解释学的“中国化的解释学”呢?我认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我 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解释经典的资源以及对经典解释的独特 的方法和理论,如果我们对之加以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定会得到某些不同于西方解释学 的理论与方法,这样无疑将会对人类文化,对世界哲学做出重大贡献。当然要创建中国 解释学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现在我国已在多种学科中运用着解释学,但大多用的是 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也有一些学者在创建中国解释学,但很难说已经得到学术界 的公认),故此,在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过程中,我们也许应做三个方面的努力:(1)应该 很好地研究西方解释经典(特别是解释《圣经》)的历史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创造的西 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当代西方各流派哲学如何动用解释学和在西方不同哲学流派 运用解释学问题上的不同点(争论);(2)对有长达两千多年的我国解释经典的历史,我 们必须作一系统的梳理,以发掘我国解释经典的某些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并使之 系统化,成为一种哲学;(3)研究近年来我国在多种学科中运用西方解释学所取得的成 绩,找出西方解释学在解释中国经典中存在的问题。为此,我写了六篇有关研究“创建 中国解释学”的论文,就教于学界同仁,以期能引起重视,并通过大家的努力创建出有 中国特色的解释学,这就是说创建中国化的解释学将不仅丰富“解释学”本身,也是把 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大潮的一重要途径。
一个世纪以来的“中西古今”之争应该结束,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各有 所长,而且事实证明目前中西哲学已在对话中相互吸收着。中国哲学因吸收了西方哲学 ,而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学者(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弗 朗索瓦·于连、恩巴托·艾柯等等)都先后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得到某 些启示。同时现在人们已经注意人类文化正在走入新的轴心时代,而“新的轴心时代” 必定是回顾其文化的源头,传承其文化命脉,汇通古今之精华的新时代。中国哲学正在 这一中西融合、古今交会的转型期,如前所说它一方面在创建着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中国 化的种种哲学流派(如中国化的现象学、中国化的解释学等等);另一方面也在吸收着西 方哲学(和其他各民族、各国家的哲学)中更新中国的传统哲学,创造着新的现代中国哲 学(如现代新儒学,或者现代新新儒学、现代新道家等等)。展望21世纪,中国哲学必将 在“反本开新”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体系,取得辉煌的成就。“反本”必须对 我们的哲学源头有深刻地把握,即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回顾两千五、六百年前那个轴心 时代的我们的哲学源头。我们对自己哲学的来源了解得越深入,才会有面对新世纪的强 大生命力。“开新”,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传统哲学作出新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另一 方面又要利用我们传统哲学的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 论。“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传统哲学的真精神,我们才能适 时地开拓出哲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并给以新的 哲学解释,才可以使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中国哲学在21世纪的“反本 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当今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我们必须抓 住这个时机,实现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创建出新时代的新 的中国哲学。
标签: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哲学论文; 冯友兰论文; 熊十力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国学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金岳霖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