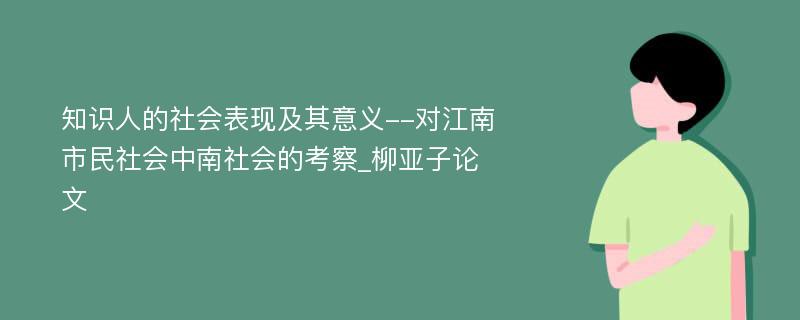
知识人的社会呈现及其意义——关于江南民间社会中南社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江南论文,民间论文,意义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国同盟会的“犄角”和“宣传部”,(注:柳无忌编,柳亚子:“我们发起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南社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屈武《在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南社发起八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当时人们把它(指南社)看作同盟会的宣传部。”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磨剑室文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以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等知识分子为领袖的文学革命社团南社,1909年在苏州正式成立,此时已是辛亥革命的前夜;如果迄止于1927年柳亚子被国民党右派政权赶出苏州吴江的黎里镇,南社基本上以江南区域社会作为活动的舞台。由此,一个应当回答的基本问题摆在辛亥革命研究者面前:在晚清—民国社会变革时代,以近代思想观念或者说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扩散为职志的南社知识分子,与江南民间社会的近代变迁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历史的研究者在涉及到南社的作用发挥时,常常从南社留下的抽象文本出发,阐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种文本式演绎已经得出了诸如“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舆论准备的作用”[1]、“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开辟了道路”之类的结论;在所谓“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的结论中,也暗含了辛亥社团的思想启蒙作用。
但是,翻开辛亥革命学术档案,我们发现,上述结论的获得显然与南社在民间社会的“真实存在”相去甚远,进而言之,对于知识分子世界(包括日常生活世界和思想观念世界),与社区普通民众思想变化的关联,语焉不详。事实上,只有背倚南社生活世界,再现其在民间社会中的田野图景,才能说明南社知识人与社会启蒙的确定关系;而一旦涉足于此,将会发现,原先据以结论的许多重要论据不能直接说明结论,而能够说明结论的材料却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对这些边缘材料的重视,同时也意味着处理这些材料的认识和方法的更新,其结果自然不会是许多现成结论的简单重复。
一 “南社”世界的内向呈现
与其他社团没有什么不同,共同的集体经历是造就南社的惟一途径,而造就文人共同体的过程,首先以知识分子真实的日常交往形态展现出来,南社自称为“雅集”。(注:“雅集”的具体情况,参见郑逸梅编著:《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73页,南社大事记);柳亚子:《南社纪略》“我和南社的关系”。本文所谓的南社“雅集”,包括新南社的“聚餐会”。)
从形式上看,南社雅集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传统士大夫是一个极富想像力和浪漫气息的特殊阶层,这不仅仅表现在作品创作上,更直观地体现在生活方式上:荷塘月色,流觞曲水,对酒当歌……几乎成为描述他们的专门术语。南社雅集的地点都在江南(私家)园林,“天人合一”的园林布局天然地就是休闲的空间,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南社文人的生活形态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现,而这种形态,在中国社会里,通常被认为具有与生俱来的休闲娱乐性。
1909年虎丘雅集前一个星期,陈去病在《民吁报》发表了一则文辞婉约的《南社雅集小启》,柳亚子在会期前4天就赶到苏州,投宿于阊门外的惠中旅馆,恰巧名伶冯春航在苏州演戏,便天天喝醉老酒,前去捧场。11月13日正午以前,一行人雇了画舫,从阿黛桥出发,循七里山塘,一橹双桨,摇到虎丘。职员选举是在觥筹交错中进行的。19人开了两桌,菜肴是早就备好了的船菜,由船娘纤手调羹,风味独特。喝酒当中,便选出职员。
选举既毕,酒兴勃发,醉意之中,大家忽然说到了诗词问题,一阵激烈的争论由此引发。柳亚子后来回忆道:在清末的时候,本来是盛行北宋诗和南宋词的,我却偏偏要独持异议。我以为论诗应该宗法三唐,论词应当宗法五代和北宋。人家崇拜南宋的词,尤其是崇拜吴梦窗,我实在不服气。这就惹恼了庞檗子和蔡哲夫。庞是词学专家,南宋的正统派,蔡哲夫也搅在里头与我争论起来。当时,助我张目的只有朱梁任,可我们两人口吃,期期艾艾,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檗子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2](p14)
在南社雅集中,多少人,有过多少次的烂醉如泥,恐怕谁也记不清了;半醉半醒之间,文人意气勃发,口角相加,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同光体之争”只是牛刀初试,1912年的第7次雅集,闹得简直不可开交了。会上,柳亚子提议修改条例,把编辑员由三人制改为一人制,并毛遂自荐,理由很简单:“我觉得南社的编辑事情,老实说,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出相当的人来担任的了。”表达虽说率直,但大家很有些想法,只能投票解决了,结果反对票多,赞成票少。这已经让柳亚子很失望了,高天梅又把一年前柳亚子的一句酒后谑言甩了出来:“究竟谁是得道多助呢?”这还不算,又讥刺道:“今天到会的社友,知识程度很高,自然黑白分明,不会受人家的利用了。”柳亚子后来回忆道:那天“晚上……雅园聚餐,喝了许多闷酒,天梅还在冷言冷语,自鸣得意,自然更使我觉难堪。还到朱少屏家里,一夜睡不着,决定明天登报声明永远脱离南社。我的脾气,是说得到做得到的”;等到见了报,大家觉得事情给弄糟了,高天梅叫人前来疏通,但柳亚子“给他们一百个不理”[2](p51~52)。
1915年时的南社,因为不断的“内讧”,已经很不景气,而时局又变得愈来愈坏,柳亚子愁苦万状。是年中秋之夜,他与里中友人顾悼秋发起酒社,踏灯秋禊桥畔,泛月金镜湖头,长歌当哭,借酒浇愁,柳亚子不善酒,却“天天狂歌痛饮,喝醉了便在堆满瓦砾的空场上乱跳乱滚”。[2](p75)自此,每届中秋,必集酒会,凡6年。中秋佳日,丹桂飘香,清风嘉月里社,不闻尘事喧嚣,但求心灵慰藉。黎里是脆弱书生的精神家园!继酒社之后,1916年夏有“销夏社”之结,1917年冬有“销寒社”之会。块垒郁结于心,何得逸豫自恣?
这也是南社世界,一个人们过去不太愿意提及的世界,只因为它的传统承继,因为它的文人弱点,因为它的休闲特征。
确实,刚刚从旧式士大夫身份转变而来的南社人,身上还散发着经年熏染而成的传统气味。就南社3个发起人说,柳亚子和高天梅生长于广有田地的“耕读世家”,(注:《柳兆薰日记》载: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已经来到吴江,柳家还能收到地租1300多担;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柳兆薰为柳亚子之曾祖父。高天梅“生于读书世家……高氏宅第,环境清幽,出尘绝俗,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可见其家世(见徐国昌《高天梅与南社》,《吴江文史资料》第9辑,1989年)。)陈去病亦出身于“贸迁有术,拥有世资”的工商主家庭。[3](p179)来自于传统小家庭的知识分子,赶上了社会变革的大时代,在最早受到欧风美雨浇灌的江南土地上,开始了思想转型,他们悄悄改变着自身的知识结构,确立了迥然不同于旧式士大夫的人生目标追求,但其生活方式仍然是传统型的,一如陈去病对于高天梅的描述:“意气傲岸,自负弘远。喜饮酒,长于雄辩,醉辄侵其座人。捉座为诗歌,缠绵数十百言立就。”[3](p239)积淀于其中的东西也许可以称之为“诗酒精神”。生活于专制主义之下,逸出于官僚体制之外的传统文人,尤其是诗人,以诗酒沉醉的方式获得了精神的超脱、人性的伸张,尽管它是短暂的。不管人们对此如何评价,文人们从传统思想逻辑中衍生而出的诗酒精神对现实生命的悲剧意识起了极大的消释作用,而文人社团为他们营造了一个消释的空间。这样的社团,文人们对它怀有了强烈的归属感和投入感,是为“我团体”。南社也有类似的吸引力:画地为牢,互相认同,自我实现。这是南社世界的一种呈现方式,不妨称之为“内向呈现”:指向南社自身,局限于团体私域,旨在促进南社成员自我实现和道德选择的领域,诗酒雅集是他们独具特色的活动方式。
但是,承继传统而来的这种生活方式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休闲。苏州虎丘是一个休闲的好去处,而会址设在虎丘张公祠,在南社的心目中,它是别有深意的。张公名国维,明末崇祯年间,曾任苏松巡抚,南明时代以起兵抗虏殉节。著有《吴中水利书》,不但义烈载诸史册,又复惠爱泽被民间。虎丘雅集中的“同光体”之争,亦不同于旧式文人的意气之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诗坛,呈现出比较保守的“同光体”诗人与比较进步的南社派诗人争霸的格局。同光体的代表人物陈立三、郑孝胥等官僚派诗人,宗承宋代江西诗派,远离社会现实,词句僻拗,生涩瘦硬,正如柳亚子一针见血的批评:“盖自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不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4](p200)南社反其道而行之,实际上是与旧文化的一场较量。
至于消夏社、消寒社的借酒浇愁则远离了真正的休闲本意了。其实,真正的休闲不在于生活方式,而在于生活心态,所以美国休闲社会学家杰弗瑞·戈比(Geoffrey Godbey)这样定义休闲:“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的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5](p14)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社会变革时代,南社人根本不可能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社团名称所包孕的政治意义足以说明了他们的心境,所谓“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6],暗含着“反抗北庭(清朝)的意思”。[7]由此可见,进入南社世界的统一门票是其共同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观念。由于社团活动的排他性和成员关系的亲密性,他们着力展现的是南社人的生活世界,也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他们“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的感到有价值的方式”表现自己。这是社会变革时代文人共同体共同的实践模式。
二 南社世界的外向呈现
社会变革时代的南社有别于旧式文人雅集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志愿社团。从近代社会关系的角度考察,它也是清末民初正在建构中的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与一个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资产阶级集团相联系。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将之称为“知识分子阶层的有机性”:
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知识分子便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所行使的是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葛兰西所指的“有机性”单单指那些将工人阶级作为惟一革命能动力量的知识公子。(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为了行使“下级职能”,南社必须走出小团体私域,迈进南社圈外的民间社会,由此伸延至作为社团存在环境的公共领域。这是一个社区民众对公共权威及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议论和评判的领域,置身其中,南社知识人显现出另外一种与诗酒雅集完全不同的面貌,从其指向性上看,不妨称之为南社世界的“外向呈现”。
苏州光复第二天,江苏都督程德全拟办一份报纸,进行舆论配合。陈去病四天便出了一份油印的《大汉报》,发刊词极尽张扬革命。尽管当年的南北政治形势扑朔迷离,陈去病对新生民国充满了信心,已经在考虑有关民生方面的问题了。辛亥年秋,苏南大水,他在《大汉报》撰《吴中水利之义》,详说水系,规划疏导,以期当政者的重视。陈去病又领衔在《大汉报》发表《南社临时雅集广告》:“自光复以来,本社之目的已达,惟建国伊始,一切事宜正资讨论,亟应组织共和政党,以策进行。”[8]
跟苏州相比,作为近代文化中心的上海更有气势。辛亥革命前后,南社社友们,纷纷来到上海。其时,重要报刊多由社友们主持笔政,各种杂志也大都是他们的地盘,当时的柳亚子颇为踌躇:“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的天下。”(注:郑逸梅编著:《南社丛谈》第3页。辛亥前后南社社友主持笔政的上海报刊主要包括《民立报》等15种。)
让我们最不能忽略的是,南社领袖们不但活跃于江南大中城市,更多地也在江南乡村;乡村是南社的重要据点。
1920年底,柳亚子作周庄之行,支持陈蕺人等创办《蚬江声》,次年9月16日《蚬江声》正式出版,在“宣传新文化反抗旧势力方面”,成为“革命军的急先锋”。一个月之后,柳亚子又赞助王大觉创办《新周庄》(此为《蚬江声》之后身)。[9]《蚬江声》及《新周庄》,“欲取风会而更新之,盖犹是亭林氏治始于乡意也。于是吾邑诸地区,若《新黎里》,若《新盛泽》,若《新吴江》,若《新震泽》、若《新同里》,若《新莘塔》之流,纷纭并起,霞焕云蒸,读者至目不暇给,盖蔚然成一时风气矣。”[10](p1632)通过一张地方小报《新黎里》,柳亚子告诫人们,在近代地方小社区与外部大世界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历史的联系:
治始于乡,哲人所乐道。黎里虽偏小,比于全中国,不足一黑子之着面。然声名文物,亦自有其数百年之历史,彪炳于邑志里乘。今者旧礼教已破产,而新文化犹在萌芽。青黄不接,堕落实多。旧染污俗,孰为当铲除者,思潮学理,孰为当提倡者?讲求而实施焉,宁非先知先觉所有事哉?[11]
“新字号”的报纸,依循着同样的理路。在稍后的《新严墓》创刊号上,柳亚子希望它“做一个报界的彗星,横冲直撞,扫净旧社会反动的势力,开辟新世界文明的纪元”[12](p885)。在拥有17位南社社友的嘉善西塘镇,1921年由郁佐梅等牵头创办了《平川》半月刊,推广白话文,提倡新文化,在西塘和附近小镇有过不小的影响。(注:《平川》半月刊,1923年创刊,八开小报,每期五六千言,自费。始为平川印刷所石印刊出,后改铅印,1927年3月停刊,1936年8月复刊,由平川金石书画研究社主编,出9期,同年12月停刊。《西塘镇志》,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综观近代以来的传播历程,大众传媒的发展是与民间社会的成长同步而行的。20世纪以来,市民们利用报纸这一主要的传播媒介,争取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同时它也普及了大众教育,提高了民众素质。南社显然已经掌握了这一理论武器,并以此打入民间社会,进入公共领域。
西方传播学者L.W.帕伊揭示,近代社会的传播体系,分为两个层次,除大众传播媒介外,还有在人际接触基础上进行传播的意见领袖。作为过渡时期的近代传播,常常表现出这样的特征:以都市为中心的大众传播媒介过程和村落共同体内部的人际传播过程呈分离状态,低层次的传播体系是孤立、分散的。[13](p29)让我们惊喜的是,在南社领袖的努力下,“城乡分离的传播状态”在社会变革时代的20世纪20年代已经迅速地“过渡”过去,取而代之的近代传播体系,不仅在城市,更重要的在乡村社会构筑起来;在江南乡镇社会,建立在人际传播基础上的近代型意见领袖,南社为其一。
1924年初,柳亚子以同盟会员的资格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8月,吴江县党部在黎里成立,柳亚子被选为吴江第一届执委会常务委员。从1924年到1926年,吴江县党部分别在盛泽、黎里、震泽、平望、同里召开了5次代表大会。从此,乡里社会发现了柳亚子这位鲜明的社会政治活动家:
国民党吴江县“三大”是1925年10月10日在震泽召开的,次日,震泽区教育会(会长是杨剑秋)发起了各校各界庆祝双十节大会,地点在体育场。与会者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柳亚子作演讲,杨剑秋是这次庆祝会主席。下午国代会继续开会,其中讨论议案甚多,晚上各校提灯游行庆祝,国民党员参加,手提“三民主义宪法”之红灯,绕市一周而返。另一部分在城隍庙开映幻灯,并露天讲演,仍由杨剑秋君介绍,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特派姜长林来演讲。[14]
这样的通俗演讲,在黎里每周常有:
本月十五日夜,(中国国民党)党员特办纸灯锣鼓,游行、演讲。演讲者若朱季恂、侯绍裘、徐蔚南诸人,均非本镇(指黎里镇)人,故听讲者较平时更多。十九日上午更有杨贤江、汪大千、邵仕昂、沈复镜诸人至各茶馆演说。[15](p29)
在盛泽,据老人们回忆,柳亚子经常在东庙向民众发表演讲,听者十分踊跃。他还与群众一起上街示威游行。柳公平时说话口吃,但演讲时却慷慨激昂,口齿流利。(注:这一段口述资料在1925年7月1日的《新黎里·各区通讯·盛泽·国民党演讲大会纪事》上得到印证:汪大千兼任盛泽平民教育促进会主任,办理识字运动,以幻灯教授,已逾两载,为学为国,夙著热心。自“五卅惨杀案”发现后,每逢星期日夜间,教授完毕,即召集同志,演讲国事。六月二十一夜,为循例演讲之期,适闻柳亚子自黎(里)来盛(泽),即请其加入演讲。二十二夜间续讲,地点在东庙庙场。八时开会,首由汪大千宣布会议宗旨,次由柳亚子演讲:先说明上海、汉口屠杀惨案真相,继述帝国主义侵掠中国之历史及其野心,阐发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精义,继讲孙先生遗嘱大意,且用幻灯映出遗嘱全文,末言国民欲自救国,非加入中国惟一之革命政党中国国民党不可。)
只有在社会变革的豪情驱动下,只有在与公众的心灵沟通中,思想才会蓬勃而出。体育场、学校、祠庙、茶馆……在这些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公共空间,(注:公共空间是从城市规划领域借用过来的一个概念:近几年来,城市公共空间与民众社会生活关系受到社会史学者比较多的关注,尤其是(在)国外的学者。不过,乡村公共空间似未专门有人涉及。在江南,乡村公共空间除了本文所列举的以外,还有诸如航船、村肆、乡镇公园等,参见(国民党)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浙江农村调查·到农村里去的一段日记》,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小田:《近代江南茶馆与乡村社会运作》,《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南社人身体力行,参与或引领着公众舆论,经过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乡村人们,日益贴近波澜壮阔的时代。
无论是舆论形式的大众传媒,还是乡村公共空间中的身体力行,南社人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诗酒雅集的新形象,以一种抽象的观念形态加以呈现,也就是说,这里着力展现的是南社人的观念世界。事实上,这也是知识人能够贡献于社会的惟一资本:“一旦世俗权力要求他们为新的、更美好的社会的建立提出建议,那么,他们所提出的自然只能是他们最擅长于创造的那一个或那一类,也就是说,唯一能够使他们填满对建立一个新社会之欲求的,只能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那个世界,他们最了解的那个世界,和作为他们的家园的那个世界。”[16](p132)
三 社会呈现的不同意义
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过去冠之以“文人集团”(注:在中国更常见的名词是“封建士大夫”或“传统士大夫”。)的社会共同体,20世纪以来在“知识分子”的名义下受到了世界性的关注。在对纷然杂陈的知识分子定义检视之后,一些颇有卓见的学者指出,所有这些定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自我定义。[16](p9)所谓“自我定义”,葛兰西的表达更明确,“在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去寻求区别的标准,而非从关系体系的整体中去寻找,这些活动(以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团体)正是以此在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占有一席之地”[17](p3~4)。
这是社会学的思维方式;以此为出发点,鲍曼告诫我们:应“把知识分子范畴当作一种社会整体(societal figuration)的结构要素,要界定这个要素,不能从它自身性质出发,而应从这一结构要素在社会整体结构形式所呈现出来的依赖系统中所占的位置出发,从这一结构要素在维持和推动整体结构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出发。”考察问题的方法也就自出机杼了:“知识分子范畴的社会学含义,只能通过对作为一个总体的整体结构形式(figuration)的研究才能成功地获得。”[16](p23)
沿着上述思路,去研究南社的历史,即进行历史—社会学的追溯,我们发现,南社世界的不同呈现方式对于民间社会的近代变迁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这样的晰分,对于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南社及其活动,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南社世界的不同呈现方式并不只是表明社会呈现的向度,在社会互动的意义上,它表明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圈子”(social circle)。(注:“社会圈子”意指知识人对其发表自己思想的一批听众或公众。见[波兰]弗·兹纳涅茨基(Znaniecki,F.):《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很显然,“内向呈现”的“社会圈子”狭窄,所谓“听众或公众”只是社团私域中的同道或同志,在传统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精英”层次,而“外向呈现”的“社会圈子”广泛,“听众或公众”便伸延至作为社团存在环境的民间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南社一旦进行这样的转向,就必须改变自身的“话语”形式。因为,南社人企图进入民间社会,毫无疑问,就得满足民间社会的期待,按照民间圈子的要求,懂得民间话语,否则无法沟通。
葛兆光先生在论述18世纪的江南文人“共同体”时指出,当时他们使用三种不同的话语:一种是在公众社会中使用的“社会话语”,一种是在学术圈子里使用的“学术话语”,还有一种是在家庭、友人之间使用的“私人话语”。[18](p519)南社世界的内向呈现基本是所谓的“学术话语”和“私人话语”:“学术话语”以知识的准确和渊博为标准,只在少数学者之间通行和认同,并不是一个流行的话语;而“私人话语”“不宜公开,满足心灵却不可通行,最多形之诗词。”[18](p519)所以,南社每次雅集之后编印的《南社丛刻》,其字句之艰涩,自非一般百姓所能理喻,主要在南社同仁和社会精英之间传诵,其间所包含的“革命意义”也一再被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所挖掘,但从社会影响力上说,恐怕很难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既然是“学术话语”,南社圈内人可能深得其中三味,却很难引起普通民众的共鸣。更重要的是,由于文人相近的传统惯习,南社人之间常常因为某一个“学术”或“私人”话题的分歧,转向人身攻击,这种意气用事又常常以“外向呈现”的方式公之于民间社会(比如登报声明等),由此而生的思想偏执,对于民间社会的近代变迁,很难说得上有什么作用。
伴随南社世界的“外向呈现”而来的话语形式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与南社内部唱和的《南社丛刻》不同,报纸,特别是其中面向大众的内容,迫使他们改变表达方式。在五四新文化大潮的洗礼之下,力图以现代观念改造民间社会的南社人实现了语言形式的转变。柳亚子后来回忆道:“我最初抱着中国文学界传统的观念,对于白话文,也热烈的反对过;中间抱持放任主义,想置之不论不议之列;最后觉得做白话文的人,所怀抱的主张,都和我相合,而做文言文去攻击白话文的人,却和我主张太远了,于是我就渐渐地倾向到白话文一方面来。同时,我觉得用文言文发表新思想,很感困难,恍然于新工具的必要,我便完全加入新文化运动了。”[18](p101~102)后来,在与民间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柳亚子对于“民间话语”和“精英话语”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做几篇骈散体的文章,和几首近体的诗歌,当然不算国学——对于新文化,更完全是门外汉。”话意虽带有自谦的成分,但不能忽略另一因素:为了适应“外向呈现”的需要。[19]
由此,对与南社相关的“礼拜六派”的评价,也更公允一些。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通俗文学流派,它历来颇遭物议,以致于包天笑和周瘦鹃等人都极力否认自己的流派归属。是的,在礼拜六派的作品中,鸳鸯、蝴蝶、可怜虫、同命鸟之类的香艳词句不少,也有一些淫邪儇薄的货色羼杂其间,但就其所拓展的“社会圈子”(市民)来说,就其社会圈子所接受的作品主体来说,就其主体作品的反对传统专制主义的观念来说,特别是就其反传统在民间社会中的现代意义来说,礼拜六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探索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也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从社会呈现的内容来看,南社世界的内向生活呈现和外向观念呈现对于民间社会的近代变迁具有非常不同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到来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大潮冲天,各种主义和思潮相激相荡;大浪淘沙,柳亚子在进行艰难的选择。此刻,他来到周庄古镇。周庄贞丰桥堍有卖浆家曰“迷楼”,1920年12月柳亚子邀陈去病、叶楚伧等10余人,在此酣歌痛饮,日夜忘返,三天乃散。后,有《迷楼集》行世,其中以酒家少女阿金美貌为题者不少。柳亚子曾有解释:“我们尽日沉醉于此,差不多像入了迷楼。从前,隋炀帝的迷楼是迷于色,我们这个迷楼是迷于酒。所迷不同,其为迷一也。”[20](p240)柳亚子袭“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典,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哑谜。这群“醉翁”既不在酒,那么所迷何为呢?在后来出版的迷楼唱和之作《迷楼集》序中,柳亚子自陈,“仆本恨人,埋愁无地,填胸块磊”,借酒而浇。这是符合实际的率真之言,但柳亚子同时也意识到,“迷楼”非世外桃源,不可能所有的人皆作此想:“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世有碻士,必曰夫柳子之志荒矣。”[21](p611)据民间流传,当时小镇及周边村民“亦视他们为风流才子”。[22]换言之,南社人在他们心目中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形象。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南社世界在江南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一种内向的生活呈现,无论是“销夏社”、“销寒社”,甚至包括稍后的“迷楼”酣饮,乡村人还看不出什么“现代性”来。
同样是在民间社会,如果是外向的观念呈现,影响的性质则非常清晰,无论是南社人“缺场”的报刊,还是南社人“在场”的活动都是如此。在现实公共空间,尤其是乡村社区中,人们常常把南社人视为“公众人物”,他们的人格魅力和舆论导向颇具震撼力,从而影响着民间社会的变革进程。据嘉善籍“新南社”社友余湘1989年的回忆:1919年冬,父亲迎娶后母,吴江一带包括柳亚子在内的许多南社社友前来道贺,畅欢之际,余家老大依仗其在家族中的权势,意存挑衅,横加殴骂后母之伴娘,懦弱的祖母亦无可奈何。柳亚子见状,发动南社社友,和同来的宾客群起而攻,与老大当众理论,有恃无恐的老大竟不理会;慑于众怒,警局将其逮捕。南社社友与传统家族势力在稠人广座中的抗争,极大地震动了乡村人。(注:余湘之父余十眉为南社社友。余湘:《柳亚子轶事》,《吴江文史资料》第9辑,1989年。)
纵观南社的演变,其社会呈现在不同的时段具有明显的侧重性:从(旧)南社侧重于“内向呈现”转变为新南社侧重于的“外向呈现”,其间的关节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注:具体地说,是在1922年前后;1922年撰《〈乐国吟〉后序》,自题“李(列)宁私淑弟子”,1923年作《〈吴根越角集〉后序》,自谓“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萨维克之主义。”故柳无忌、柳无非编《柳亚子年表》在“1922年”目下称:“盖此时思想大变,尽废酒社、迷楼乐国之消极活动,而于下一年有新南社之举。”见陈一飞、马巧根主编:《柳亚子早期活动纪实》(1907~1925),档案出版社1991年。)
清末出现的南社是当时全心致力于民主共和的革命党人所造就的有机知识分子社团,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作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造其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17](p5~6)应该说,在意识形态上,南社已经区别于传统知识分子,但是南社的理想目标又是十分狭隘而肤浅的:“民元以前,唯一使命,是提倡气节。”[2](p91)于是,“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宫威仪’,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23]
历来的南社研究者,大多在文学的意义上关注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清初民初)那么几年间的活动状况,高度评价其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所发挥的舆论准备作用。这样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但基本上是对南社的文学文本的理论演绎,倘若触及南社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纷争和此后不断的内讧,特别是涉及到民元之后近10年的南社情状,论者通常以“时代的局限性”一笔带过,如今,我们发现,这样的“局限性”与其说是时代的,不如说是社团自身的;与其说是局限性,不如说是社团特质使然,更明确地说,就是知识社团的内向呈现方式;这种的方式,至今变化不多;在南社之前的传统社会中也大概如此。明乎此,我们便可以全面认识南社的活动,而不必因为某些“局限性”领域而讳莫如深。
民初10年间,既已完成“提倡民族气节”使命的南社衍化成“新南社”,开始了“追随着新时代,与民众相见”的新使命。[2](p91)“新南社”与民众相见于民间社会,引纳世界潮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着民间社会的近代变迁,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新南社”明显重视不够,似乎没有一次次的雅集,新南社就算是“无声了”。实际上,新南社缺少的只是南社“内向呈现”时的“生活闹嚷”,却不乏“外向呈现”时的观念震撼,对于民间社会的近代变迁来说,应该说更值得尊重和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