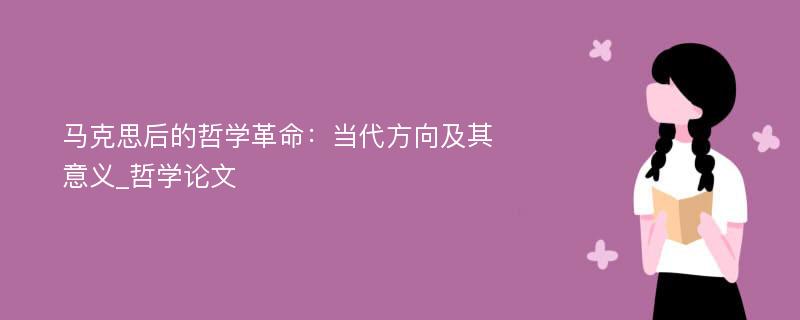
马克思之后的哲学革命:当代路向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0-0049-10
近年来,如何看待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对于当代哲学路向的影响,成为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的确,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性质和本真意义,是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及其理解当代哲学的关键。然而,同样重要甚或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之后,哲学革命的当代路向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历史进程?它呈现出何种历史的和理论的形态?解读这一进程有何意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地反思并作出解答。
一、马克思是否终结了哲学革命的世界进程?
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以“改变世界”的实践颠覆了以往思辨先验的形而上学,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革命,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变革,创立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工具。
但是,一个重大问题依然没有被科学解答:马克思是否终结了哲学革命的世界进程?换言之,在马克思之后,世界范围的哲学革命进程是否还在延续?形而上学是否彻底灰飞烟灭、消散殆尽,再也没有绵延存续?这一追问涉及如何看待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进而涉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意义问题,不可不辨。新中国建立后的六十年来,在不同的语境中,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先后出现过三种对立的见解,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术路向。
一是封闭的语境与传统见解。在以往封闭的学术语境中,学界曾持一种文化激进主义的见解,认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宣告了以往一切形而上学的非法性,进而从哲学的根基处实现了哲学革命,在变革哲学观的同时就颠覆了一切旧哲学,宣告其终结的命运。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既然马克思已经完成了最深刻的哲学革命,那么自此之后,除了延续哲学革命精神的即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哲学”或者是以往哲学的“残汤剩汁”,不是“开倒车”、“翻穿旧衣”,就是“没落阶级的话语行动”,完全失去了与时代的任何关联,失去了生命活力,再也没有思想价值,只能被当作“历史弃子”而沦为批判对象。这一观点强调:在马克思之后,“哲学进程”唯一本真意义的存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是开放的语境与反思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发现:世界哲学进程并没有因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而终结;相反,出现了更加多元化、多形态、多向度的发展态势。人们发现:马克思之后,作为时代精神的表征、文明活的灵魂,反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进程并没有完结,依然与时代相伴而行。其十分活跃的哲学思维、繁多的哲学形态,既具有反形而上学、崇尚“实践哲学”的时代共性,但又在实践哲学内部分化为不同的路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化批判、过程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等。部分学者不仅着力探索当代哲学“继续革命”的路向、方式和价值,而且依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绪,尝试地探索海德格尔生存论路向、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路向、德里达和鲍德里亚等人的后现代主义路向等等对于深化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意义,将当代西方哲学的某一派别或多数派别直接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精神对接,由此在哲学革命理解上形成所谓的“以西解马”范式。
三是文化保守主义与重构形而上学。在颠覆形而上学、走向感性世界的思想道路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启蒙现代性传统的继续。但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遭遇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现代性传统的颠覆和解构之后,出现了所谓“现代性困境”。主张“返本开新”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回潮,在祛神时代呼唤神灵,在祛魅时代重新建魅,从生存论、解释学、价值论和宗教哲学到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等等,都在重构本体论、召唤形而上学的幽灵。在这一语境中,某些最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与前现代传统对接,成为颠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同谋。形而上学传统不仅没有被消灭,相反却渗透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成为教条主义不断滋生的思想来源。
有鉴于此,这里有必要提出“马克思之后的哲学革命路向及其当代形态”问题。解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在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大冲突中重新阐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真意义与当代价值,需要在世纪转折和新轴心文明对话中重新探索马克思主义创新之路。为此,笔者特提出三个见解:其一,马克思发动了哲学革命,但是并没有结束这一革命的世界进程。在马克思之后,特别是20世纪,哲学革命沿着不同方向继续行进,出现了多元化的结果。总结哲学革命的当代路向和当代价值,是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我们应当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语境的变化中看待整个世界哲学的走向,在对话中深刻阐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当代路向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原则差别,厘清两者的关系,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既不能完全将当代西方哲学摒弃在哲学革命的脉络之外,更不能将当代西方哲学的革命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真意义完全等同。其三,应当站在新旧轴心文明对话的高度重新评估文化保守主义对形而上学的重建及其反渗的影响力,既坚持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意义,又对未来形而上学的趋势作出新的科学判断。
二、探索哲学革命当代路向的三个维度
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本真意义,一直是学界深度关注的重大主题。有关探索从两个角度展开。
一是追寻当年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原像”。以文本解读或出场学视域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首先是批判地揭示资本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本真结构与内在矛盾,对资本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两大根基(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进行反思批判,进而对以往一切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和感性直观的旧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的产物。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出场开启了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实践哲学路向。① 这一新世界观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宗旨,以“改变世界”为己任,以彻底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立场,将改变世界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作为新世界观的基础和本质,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而批判地划清了与只诉诸“感性直观”的旧唯物主义以及诉诸“精神劳作”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界限,根本颠覆了以各种“解释世界”经院哲学方式为其他阶级和阶层统治利益辩护的旧形而上学。
二是从马克思哲学革命对当代哲学路向的影响与折射中反观。在马克思之后,世界哲学并没有终结哲学革命的历史进程,相反,多向度地沿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路向继续行进,在现代性、后现代与新现代性三个维度上阐释出马克思哲学革命中原本人们未充分关注的意义,成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某种“效果史”。因此,从效果史角度反观马克思哲学革命内在意义,可以多向度地启迪我们的思考。
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之后哲学革命的当代路向?我们可以选择以下三个维度:第一,在现代性视域中,发生了所谓“实践的转向”。各种哲学都在摈弃形而上学,都成为以实践观作为基础或逻辑中心的实践哲学。因此,实践哲学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有品格,而是成为整个20世纪哲学的普遍品格。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原则差别,已经不再是实践哲学与传统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之间的差别,而是转换为实践哲学内部的原则差别。第二,现代性困境与哲学革命的后现代路向。后现代主义着力“解构”形而上学,彻底颠覆“大写理性”和“大写主体”,阐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后现代意蕴”,开辟了哲学革命的“后现代路向”。第三,现代性、后现代困境与哲学革命的交往实践观转向。在批判和消解现代性哲学过程中,哲学革命的后现代路向不但没有根本制服形而上学,相反,其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必然召唤旧的形而上学幽灵。超越经典现代性和后现代思维而向前进——在新现代性视域中,哲学革命既彻底变革了以往实践哲学“主—客”二分模式,又超越了“主体际”的后现代思绪,将实践视为“主体—客体”与主体际交往关系统一,重新阐释马克思彻底反形而上学的交往实践观——交往实践观成为哲学革命的新路标。人们不难看出:当代哲学革命的三个维度之间尽管展现为共时态的多样性,但实际上存在逐层递进、不断深化的关系。
三、“实践的转向”与哲学革命的深化
走向实践哲学,可以说是启蒙现代性思想史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发生在资本现代性世界的开端,既是对资本现代性实践批判的产物,也因此成为重写现代性的思想产物。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随着大工业迅猛发展及资本现代性进程的日益深化,人类改变世界的实践能力显著强大,世界哲学的主导性思维方式经历了从本体论、认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也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大陆哲学,都发生了“实践论转向”运动,并在这一运动中演化为这种或那种形态的实践哲学。将实践观作为建构哲学体系的起始点、一以贯之的基础和总体性指导性原则,成为20世纪实践哲学的基本范式。作为现代性思维转换的效果史,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和解构,一直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走向。
其一,实用主义革命:实践效用路向。以皮尔士、詹姆斯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公开将“实践”及其“实效”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并以此作为反叛先验形而上学的标准。继此之后,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莫里斯的符号学、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等等,都先后秉承其先驱,将实践及其效用作为新哲学的规范。尽管美国的实用主义流派之间呈现出若干差别,创始人之一的皮尔士起初甚至在康德哲学语词意义上认为“practisch(实践)和pragmatisch(实用)之间的差距就像地球的两极那样遥远”②,但是,实用主义反对的是以往在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先验“实践理性”,尔后詹姆斯强调的“实践”含义与实用主义相一致。实用主义自称为“类似实证主义”的基本命题:“一个概念应被它的实践效果来检验”,或者说“如果考虑你的概念的对象可能有什么意识到的实践关系的效果,那么,你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是你关于这些对象概念的全部”;③ 以实践效用为基础,“实用主义的方法是解决形而上学论的基本方法”④,它将形而上学当作是无效的假说而用奥卡姆剃刀削去,“实用主义学说清除了形而上学”。⑤ 因此,反先验的形而上学、反本体论、主张实践效用原则,构建实践哲学,是实用主义一以贯之的轴心。应当注意的是:实用主义不仅强调实践的“唯一性”,将实践主义推到极端,而且引入了实践的效用、效果等价值维度,从而启迪人们在理解“感性活动”客观性的同时,高度关注实践的价值维度,这对于深化理解哲学革命至关重要。
其二,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革命:拒斥形而上学。在欧洲,实证主义继承康德传统,一直以“拒斥形而上学”为旗帜,用经验的可实证性作为建立新哲学的阿基米德支点。从实证主义、证伪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到历史主义和新实在论,科学哲学始终沿着这一思绪前进。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所强调的实证性(强理论)或概率支持(弱理论),还是波普的证伪和判决性实验,都在强调实践的基础性作用。他们的哲学,本质上是科学的(经验的和逻辑的)实践哲学,而不是自然哲学或自然本体论。就历史主义或新历史主义而言,库恩的“范式”革命、拉卡托斯的“科学纲领方法论”替换⑥、普特南的“理论总体验证”⑦ 最终都建立在实践及其经验的“超量证认”之上。这充分表明了科学哲学的实践论本性及其反形而上学立场。与此相应,分析哲学主流之一的语言哲学,本质上是语言实践论。这一本性如果说在弗雷格、罗素及前期维特根斯坦那里还不太鲜明,还残存某些本体论的“踪迹”(如指称理论,“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⑧)的话,那么经过后期维特根斯坦所开创的“语言游戏论”或“语言即生活方式”观,与摩尔的日常语言学派一起,从语言的逻辑句法分析走向语用分析,在言语行为和实际交往中考察语言的意义,因而就完成了向语言实践论的转变。塞尔、奥斯丁和克里普克均从不同的方面发展并强化了这一主题。这一路向,至少深化了我们关于实践哲学的三点认识:即便我们在知识论上确认“实践第一”,但是“实践标准”并不能简单操作,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即使从科学辩护角度看,实践不仅是知识论范畴,而且还是社会历史观、文化论的范畴;实践是话语行为的现实根基,话语行动可以是实践的一种形式。
其三,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实践哲学转向。如果说结构主义的早期代表如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还主要致力于发掘语言自身及其隐于野蛮人亲属体系的称谓、神话和心灵中固定不变的结构本体的话,那么到了皮亚杰、戈尔德曼等后期结构主义那里,结构就逐步摆脱了先天预成论的纠缠,走向实践活动决定论。结构不再是先天预存并一成不变的了,而是由实践活动沿“主—客”双向分化的结果。因此,实践、活动成为相关结构的基础,结构不再是先天本体。符号学(semeiology)成为考察人们行动和实践的符号化转换的思维产物,符号操作就替代了实在的行动。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到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符号学成为深化和替代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这一方式能够更深入地解释形而上学话语和文化意识形态产生及与现实世界二元分裂的根源,从而推动哲学革命达到了新的高度。
其四,现象学的革命:意向性实践和生存论的逻辑。胡塞尔摈弃自然思维,要求将纯粹意识作为哲学的阿基米德支点,然后通过意向性一意向性行为一意向性对象三位一体来构成主体化、价值化的实践哲学。循此思路,海德格尔的“Dasein”(此在、亲在)不再是一个被给予的“Vorhandenheit”(现成在手状态)的客体,而是通过“Zuhandenheit”(当下上手状态)来谋划并领悟存在过程的意义的“在此具有生命活动的个人”⑨,一个可以通过自我谋划、打开世界而在场的个体,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者;他无论是通过“在手”(打开物的世界)或“上手”(打开与他人共在的世界),都是通过日常活动、实践、劳动、交往而实现的。周围感性世界就作为一个由日常生活来界定的“境遇”,因而形成了被某些学者推崇与马克思哲学革命本真意义完全一致的“生存论”路向。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先登台亮相,尔后在行动中造就自己的本质。因此,人的本质既不由预成的某物决定,更不由自然对象决定,而是取决于主体自身,由个体自由的活动、实践决定。人怎样活动、实践,人的本质就怎样。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他进一步认为:马克思的整体实践与存在论的个体自由实践的关系决定了历史的生成。这是一种实践论的存在主义。
其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转向。以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开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以实践哲学和文化批判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真意义。例如,马尔库塞认为,人的实践是人本的直接证明,因而也就是人化与异化的总根源。⑩ 前南斯拉夫出现“实践哲学”派,等等。
从以上粗略勾勒的轮廓就可以看出,现代哲学在总体上完成了实践哲学的转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至少可以说:马克思哲学革命开启的实践哲学先河,在当代演变为一种多形态、多路向然而又具有时代共性的趋势。因此,马克思哲学革命开创了实践哲学。但是,在当代,无论是实践哲学还是哲学革命本身,并非无条件地就等于马克思的哲学。既然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实践哲学仅仅成为当代多元路向中的一种,我们就不能在哲学革命和实践哲学理解上无条件地“以西解马”。在当代哲学革命与实践哲学问题上,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区别和对立出现了时代性的变化,不再是本体论意义的,而是进展到实践哲学内部。我们需要在实践哲学共性基础上认真分析各自的个性,研究在新的时代底版上两者对立的新形态、新特点,进而在共性和个性的联结点上全面把握两者的对话关系。
四、后现代主义:消解形而上学的激进策略
后现代主义出场的历史语境固然缘于后工业文明的来临和资本新形态的转换,然而,在精神层面则缘于更激进地反形而上学、终结哲学传统的谋划。更为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始终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用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的话语来表达,就是后现代(解构)的激进主义是“马克思幽灵”的后现代哀悼和复活方式。
其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全面颠覆,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出场历史指向的继续。马克思哲学革命并不是封闭在哲学之内的话语行动,而首先是对资本现代性和全球化历史批判的哲学解答。对资本现代性的思维前提(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的彻底批判的需要,使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抽象和大写的人”、黑格尔“大写的抽象的理性”而发动哲学革命,从而完成对资本现代性意识形态根基——形而上学的颠覆。后现代主义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传统,集中批判现代性的“主客二分”、“整体性”、“同一性和普遍化”、“中心性”、“肯定性和实证性”、“连续性”、“科学至上”、“人类中心主义”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主张“差异化”、“多元化”、“边缘和撒播”、“生态化”、“断裂”等后现代思维,着力解构现代性。
其二,消解现代性的根基,将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作为形而上学的最后的堡垒而加以攻击,继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抽象和大写的人”、黑格尔“大写的抽象的理性”的批判。从阿多诺批判“启蒙蜕化为神话”、“启蒙就是新神话”,将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到福柯以知识考古学方式宣布“人”的历史性死亡,犹如沙滩痕迹被浪涮净;再到德里达对海德格尔最后一个“在场的形而上学”形态的批判,完成了对“主体性哲学”和“理性哲学”的最后消解。后现代“激进主义话语”特别重视马克思辩证批判思维的“后现代向度”,如德里达认为应当承续马克思两大“思想遗产”——对一切事物无情批判的“否定的辩证法”与解构向度的一致性,对现存意义的否定性超越与“延异”将意义“托付于未来”的一致性。两者都在用后现代思维方式“彻底地反在场的形而上学”。(11)
其三,强调“断裂”、“非同一性”、“碎片化”,消解形而上学先验的“逻格斯中心主义”,解构一切意识形态。福柯先援用知识考古学,继而以谱系学方法将一切意识形态还原为历史流淌的、相互断裂的知识型转换。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也将启蒙现代性的主体性哲学和理性哲学当成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余脉一并否定。它深度瓦解了实践哲学任何主体的单一性(主体性哲学、人类中心主义等)企图和理性的在场。在这一层面上,一切以第一人称(“我”)命名的哲学不过是一种知识型话语结构的历史形态,理性形而上学都是精神统治的历史工具。
其四,反对主客二分,消解哲学,延续马克思终结哲学的旨趣。的确,当年马克思哲学革命面对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因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最终结论就是终结哲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都以彻底批判的姿态对待作为思辨体系的“哲学”,而后再也没有在肯定意义上言说哲学。后现代主义延续这一思想遗产。德里达在《哲学的边缘》、罗蒂在《后哲学文化》等论著中都解构了作为“一切科学之上科学”意义的哲学,宣布哲学的死亡,我们已经携带符号文本进入了一个后哲学时代。
然而,哲学革命的后现代路向也存在着致命的弊端。在激烈的反形而上学话语背后,是一个个没有确定意义的虚无主义思想谋划。思想的恐怖性消解并不能真正建构一个时代积极的思维方式。历史表明:正如晚期斯多噶主义成为欧洲中世纪神学的奠基石之一,谈玄论妙的魏晋玄学和“放浪形骸”的魏晋风度成为佛学东渐的精神条件之一,今日深刻思想的缺场将为重新打开形而上学之门提供便利。此外,后现代主义本身也是四分五裂的流淌体。激进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在否定一切在场性和形而上学性思维的同时,所谓“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又在探索如何重建没有“主客二分”的“第三种形而上学”。(12)
五、主体际困境与交往实践观的出场
当代哲学革命超越启蒙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双重视域的路向,就是重写现代性。其中,主体际问题的凸显成为这一路向的重要标志。“主体际”问题的出场,基于全球化普遍交往向哲学的叩问;也源于后现代主义消解启蒙现代性实践哲学的“单一主体性”而对多元差异性思维的推崇。
“主体际转向”是20世纪以来哲学的第二次转向。这一转向既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原本意义的启封,更是一种深化。在变革哲学、标志着新世界观出场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针对费尔巴哈撇开历史进程,将主体当作“抽象的”、“孤立的”个体,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马克思集中阐释了“交往实践”内涵和形态,特别是在资本全球化社会中的主要形态。进入20世纪,对仍然持有单一主体性的实践哲学来说,主体际困境是普遍的。“主体际转向”和交往实践观的出场,标志着实践哲学开始摆脱虚假的纯粹知识论传统,走向社会历史领域;更标志着启蒙现代性的单一主体性哲学模式的破产,而转向多元主体间社会交往关系的行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历史观的革命才是形而上学彻底瓦解的标志。这一转向,是由马克思哲学革命开始,继而在20世纪世界哲学进程中展开的。
无论是胡塞尔的纯粹意识,还是海德格尔的“此在”,主体首先是自我,实践以单一个体主体方式存在的。以主体为基点,即以自我为基点;主体论的哲学逻辑,往往直接变成自我论的逻辑。于是,主体论就与哲学的本性和诠释发生冲突。晚年的胡塞尔苦苦思索的问题是:现象学的还原,如何能超越自我而达致他者?“只有当先验自我的现象学揭示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在它当中包含的共在主体的经验也达致向先验经验的还原时,这一切才获得其充分的意义”;“先验主体共同体因此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其中实在世界是作为客观的,作为对‘人人’都存在的东西被构成的”。(14) 在此,“先验主体共同体”概念的出现显然是为了弥合现象学与主体际问题之间的裂隙,因为它比“先验的自我”更接近主体际问题的解决。
海德格尔在继承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论的同时,也面临主体际问题。他从“Dasein”即个体主体存在出发,通过“上手”来指向一个他者,将某某在场性显示出来。因此,此在就转化为“共同此在”——共在。(15) 共在是存在的共同体,其主体际关系是通过活动而相互关联的。海德格尔在主体际问题解答上超越胡塞尔而更接近真理。
同样的困惑也贯穿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生涯中——主体际何以可能?在《哲学研究》一书中,他反复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我的经验何以可能变成他人的经验?他自觉唯我论有失偏颇,但却在语言哲学范围内找不到通向主体际、从而摆脱唯我论的桥。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那普的视野中,作为能够在主体际交流的物理主义语言是远高于个人语言的。他甚而反对个人语言、私人科学,主张物理主义语言和公共科学。到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那里,主体际问题依然是研究的中心视界——库恩的“范式”革命讨论的是不同主体所持的新旧范式的交替,虽然他分析了同一范式下的群体共同体的思维特征,但是他坚决反对范式之间的通约性;拉卡托斯的科学纲领方法论将主体际的理论竞争作为研究的主线,用超量的实践论证作为主体际科学纲领方法论比较的尺度;弗耶阿本德“反对方法”,主张“什么都行”,既强调了主体际文化范式的多元化,又认同了超越性选择的自由。虽然这些讨论都在知识论的层面上进行,主体际隐没在知识、纲领和方法的背后,但在实质上是主体际的。哲学家们都在按照主体际框架建构各自的理论假设。
后现代主义消解单一主体性,促使实践哲学更加面对差异化、多元化的主体际关系。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一方面坚持主体际存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另一方面强调交往、对话和理解是弥合主体际差异鸿沟的基本方式。解答实践哲学的主体际难题,使之转向交往实践观。
自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中的核心范畴——主体的本性即自主性、自我意识性和自为性,是在与客体的相关中规定的。主体与客体的相关律表明:与主体面对的只能是客体。在主体目光审视下,一切对象——不管是他人或物都将变成客体。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一再谈论“他人的目光”之可怕,因为一旦目光加身,自我便成为他人的客体。既然如此,一个主体何以可能面对另一个主体呢?主体际关系,在逻辑上何以可能建立呢?(16) 尽管当代西方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主体际转向”,但是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包括哈贝马斯在内,都将主体际和交往行动理解为一种“主观际”精神交往活动,而未能从交往实践、物质交往的角度对主体加以现实的、客观的规定。显然,将主体际交往理解为一种精神的交往、意义的理解、文本的诠释、认知的交流,这是一种主体际交往层面的唯心主义。它们的谬误不在于肯定和弘扬精神交往中意义理解与诠释的重要性,而在于忘却和否定了真实的基础——现实、客观的交往实践;不在于肯定“主体际”框架对于“主—客”模式的扬弃,而在于对这一转向作了唯心的、片面的理解,导出了一种新的唯心论的交往哲学。
如此说来,主体际问题只有在交往实践观中转化为交往实践问题,才能获得科学解答。
首先,交往实践观科学地解释了以往理论的困境和难题。主体际问题在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交往实践的境遇中才能作科学解答。交往实践是多极主体间为改造和创造共同的中介客体而结成交往关系的物质活动。交往实践观实际上是“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它将“主体际”交往视为一个包含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在内的交往体系,而交往实践是这一交往体系的基础。意义理解和语言解释,不过是交往实践的派生过程和衍生形态,是精神交往层面的存在,是对交往实践的反映、派生和表象。因此,这一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对以往交往行动的唯心主义解释的超越和否定。它将交往和主体际理论提升到实践的唯物主义层次。更重要的是,主体之所以能够面对另一极主体,主体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着中介客体。这一客体,是中介化的客体和客体化的中介。它向多极主体开放,与多极主体同时构成“主—客”关系,因此成为“主体—客体—主体”三极关系结构。其中,任何一方主体都有中介客体作为对应范畴,符合“主—客”相关律的定义规则;同时,异质的主体通过中介客体而相关和交往,相互建立为主体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交往实践观对“主—客”哲学框架的变革是划时代的,是从现代实践哲学走向未来哲学的转折点。
其次,交往实践观更是这样一种历史观意义上的重写。资本全球化的当代格局既多极化又一体化,主体际已经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新的科学解释理论来批判地反思和把握当代全球的趋势,并预测未来。交往实践正堪当此任。因为,只有它一方面指明了全球发展的多极性之源正在于交往实践的多极主体性,另一方面又指明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格局的形成源于交往的宏观整合。全球交往结构是由交往实践的实体结构、意义结构、辩证结构逐层递进模式构成的。
总之,由于交往实践观能够较为科学地解答主体际难题,对全球发展更具预测力,从而可能成为跨世纪全球哲学的中心视野。
当然,这也引发出一个相关的重大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哲学革命与当代哲学革命的关系?我想,有两个观点需要坚持:一是应当肯定当代哲学革命路向与马克思哲学革命之间具有时代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并没有终结哲学革命的世界进程,当代哲学革命仍然在其时代路向上深化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某些方面,并取得了时代思维的重要成果。因此,它们仍然是这一时代精神的表征。这些深化一方面是时代造就的,另一方面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影响的效果史。从此反观,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许多问题还需要我们再认识。二是应当反对“以西解马”范式,不要因为当代哲学革命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路向有一致性就忘记两者的原则差别。马克思开创了实践哲学传统,但是如今已经成为新时代的哲学形态,成为共性,因此不能反过来说,实践哲学就是马克思的哲学。进而,马克思的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差别,由此不再是本体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而是进入实践哲学内部,成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与交往实践的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我们需要在交往实践观这一时代地平线上,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划界关系。
六、形而上学的“革命性”复活:可能性与未来走向
从启蒙运动以来,哲学革命一直沿着文化激进主义路线延续至今,在彻底反神学、反形而上学中走向感性实践和生活世界,最终导致哲学的消解。祛魅的“感性化”成为这一路向的轴心。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彻底颠覆康德和黑格尔的先验思辨的形而上学(抽象的能动性)的同时,深刻批判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而诉诸“感性人的感性活动”,从而走向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实践世界观。20世纪,世界哲学在多元路向上继续着反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事业,形成了多元化的结果。但是,形而上学并没有因此而退场。相反,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瓦解逻辑和文化保守主义守成逻辑的交叉点上,各种“返本开新”的形而上学又重新活跃起来,成为超越现代性“感性逻辑”链条的一个新趋势。
后现代主义激进的瓦解逻辑在摧毁一切现代性的肯定、规范、同一和理性的同时,导致了如当年尼采曾经预言的那样:“一个虚无主义时代的来临。”(17) 否定的后现代主义本身如果仅仅是一种思想的自我消解剂和自爆装置,那么文化的恐怖行动不可能带来任何积极成果。如果说,现代性哲学是反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的主体,那么,彻底反现代性,主张“什么都行”,只能是为前现代形而上学甚至各种神学幽灵的重新复活打开方便之门。我们因此也不难理解: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为何要重构“第三种形而上学”。
两极相通。最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的谋划与最保守的文化守成主义的交叉对接,或者说,文化保守主义扮成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策略和思维路向,就顺理成章了。最为重要的是:形而上学不再是一种倒退和反动,而是一种对现代性文化矛盾和困境的解答,作为一种哲学的“革命性”复活而出场的。从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主张的“公众家庭”到施密茨的“新现象学”,从法国的“身体哲学”到德国的“哲学人类学”,从主张“第三种形而上学”的美国的“过程神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到主张“回到亚里士多德去”而“返本开新”的社群主义者麦金泰尔,从晚年海德格尔心仪《老子》、呼唤“天地人神”的在场到罗尔斯《正义论》中重用“无知之幕”的先验方法,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哲学”到中国的所谓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各种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思维都在重新出场。这一跨世纪喧嚣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两大相关的理论支点,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所谓现代文明危机理论。启蒙现代性以来,包括哲学革命在内的文化革命在摧毁以往轴心文明的根基——世界各大宗教和延续的形而上学传统,推动思想解放和文化变革走向感性世界的同时,自由思维的现代性进程也遭遇自身的文化矛盾。或者说,现代性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无可调和的深刻矛盾。一是人与理性的矛盾。现代性文化革命主要包括两点:人战胜神,理性战胜蒙昧。如果说,早年启蒙现代性强调人性就是理性,人借助于理性反对蒙昧(祛魅和启蒙)才能完成德里达所言的“巨人与神之战”,人与理性达成统一;那么,20世纪科学主义(理性)与人本主义的大分裂表明两者矛盾冲突的彻底化。晚期现代性的非理性人本救赎不但没有挽救现代性,相反直接打开了既消解理性、又解构“人”的后现代主义大门。二是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启蒙现代性肇始的感性化、世俗化运动,在马克思和当代“实践哲学”中达到了极致,但是,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对立,感性活动与理性思维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始终成为现代哲学的主客二元困境。消解形而上学之后,感性化世界背后不再有一个根基(基础主义),萨特鼓吹的“我”的自由选择遭遇“烦心”,没有深层的、“他者”文化根据,人变成一个“是无所是”的无根飘零的存在。三是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碎片化和文明冲突,使人类文化整合和文明共识成为稀缺资源。后现代主义所描绘的由思想的“众声喧哗”和无序撞击导致的文化碎片化、边缘化和撒播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众生相”。由于文化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盛行,再也没有召唤人类的普遍价值,因而导致人类文化的深层矛盾即所谓现代文明危机理论的出现。从19世纪的尼采、斯宾格勒到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和各文化保守主义流派所主张的这一理论,直接引发了重建形而上学的冲动。
——所谓新文明轴心时代即将来临的理论。雅斯贝尔斯曾将公元前6世纪到1世纪的几百年间称之为世界千年文明发端的“轴心时代”。各大世界性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也包括中国的先秦诸子的思想,都产生于这一时代,决定了两千年人类文化史的基本走向:“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18) 然而,在现代性和后现代的冲击下,这一千年文明的脉络正在衰微,无力应对当代人类困境。面对当代难题,我们的文化选择究竟是重新回到上一个千年文明轴心去体认意义、“照着讲”,还是“返本开新”地在现存文化余脉中“接着讲”?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文化崩溃、文明衰退的当今时代,要做文化的“重新讲”功夫,即杜维明提出的“开辟文明的新轴心时代”。(19) 因为,只有站在迎接未来生活和文化挑战的意味上重新创造一种或数种可以应对时代、影响未来新千年的新文明,才能重新召唤人类共识、整合文明。而新轴心时代的文明设计,不可避免地要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作为主要形态来加以推崇。在现代性批判的效果史上重新呼唤远去的诸神,呼唤道德(伦理)形而上学,呼唤文化灵魂的回归。孔汉斯等人的《全球伦理》被重新追捧,反映出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又开始被学界所关注。
面对跨世纪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形而上学幽灵的重新出场,如何看待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就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两者的尖锐对立是毫无疑问的。面对文化矛盾的挑战,我们真的需要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吗?真的需要在现代性或后现代语境中再次像当年康德那样提出“作为任何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吗?或者如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改变世界”表示疑惑所说的那样:解释世界也从来都是一种实践方式?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然而是在创新理论中被不断否定的。
七、哲学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历史深化
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后,作为哲学革命的开创者和旗帜,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自身的存在问题,相反,形而上学思维不断反渗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不断继续提供了历史的必要性。
形而上学的反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抽象化和教条化。马克思生前坚决主张自己的理论只是世界观和“行动指南”,而不是脱离西欧语境、超越一切民族和历史的“历史哲学”或“普世哲学”。“无论如何,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痛斥那些将他的思想变成教条主义的企图。但是,在马克思之后,为了满足国际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对普及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恩格斯认为有必要以“马克思”命名这一理论是恰当的,而简要阐释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思想,就需要对此作出“系统而连贯的阐述”。这些阐述被第二国际思想家们解释为原理(如考茨基的《历史唯物主义》),再经过列宁的“整钢论”,原苏联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因而就转换为一种教科书样态的原理体系。无疑,教科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但是,其弊端是一旦将其教条化、抽象化,就在实质上背离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精神。无论国外的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曾经发生过非常严重的教条主义,从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实践的重大损失。可见,重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进而通过教条主义反渗为形而上学,不仅可能,而且是经常化的事实。重新肯定“哲学”、进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框架,必然导致一种体系化的哲学重建,与马克思当年的“终结论”相去甚远。
第二,为了完整和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学界不得不尝试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ontology)基础,而与形而上学传统保持着联系。无论是“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还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等等,都在寻找一个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本体论基础。无论东西方本体论有何差别,它在哲学史上都曾经是形而上学最核心部分。尽管当代本体论含义和模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存在着多元化的路向,然而仍然与传统本体论、进而与形而上学保持着内在的通道。此外,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仅仅当作是“本体论革命”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第三,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形而上学,为了阐释现实,从所谓原理出发,成为“两个凡是”的哲学版。更进一步,追求“文化的形而上学”、“道德的形而上学”、“法的形而上学”和“政治的形而上学”已经成为构建哲学的新时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或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塑形而上学,这是一种貌似激进、实质倒退的理论企图,是没有出路的。
事实表明:即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哲学革命也没有终结。不断否定形而上学化的企图,使我们有在新时代条件下不断继续推进哲学革命的必要。创新和与时俱进,始终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保持历史性在场总是不断出场的结果。理论形态对于产生理论的历史语境和对象语境都有根本的依赖性。正如马克思说他的理论不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不断反对“超越历史”、一成不变的僵化的形而上学企图,就必须不断明确地揭示自身存在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出场学视域。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把理论形态看作是出场形态、以探索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逻辑为己任的出场学,将会成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当代走向的必然结果。
注释:
① 任平:《论马克思哲学革命出场的现代性路径》,载《江海学刊》,2005(3)。
② [美]约翰·杜威:《实用主义》,第31页,杨玉成、崔人元编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③ [美]约翰·杜威:《实用主义》,第35、36页,译文略有改动。
④⑤ [美]约翰·杜威:《实用主义》,第60、60页。
⑥ [英]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⑦ [美]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李光程、童世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⑧ [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⑨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89页,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⑩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11)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2)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460页,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5)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44页。
(16)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7) [德]尼采:《权力意志》,第732页,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8) [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4页,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9) [美]杜维明:《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载《杜维明文集》,第1卷,武汉出版社,2002。
标签: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现代性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实用主义论文; 范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