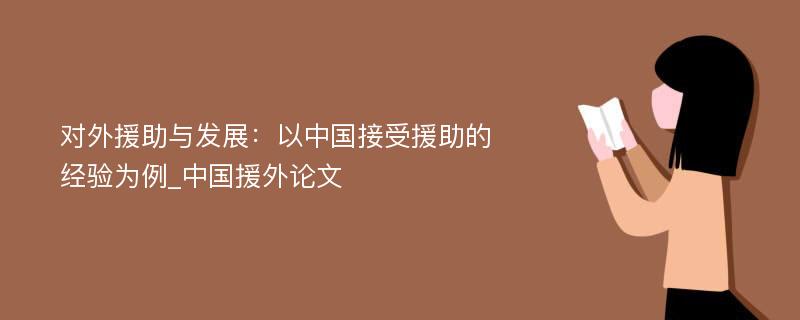
外援与发展:以中国的受援经验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援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备受关注的受援国。作为受援国,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首先,中国曾经在不同的时段接受过来自不同渠道的援助,中国接受外援① 和中国对外政策的取向密切相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署与苏联对华援助同步,而中国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又开启了中国接受西方援助的大门。其次,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丰富的国家,容纳了各类的援助活动,但是任何援助方都难以单独通过简单的经济援助手段,操纵中国的发展方向。援助方在中国的主导权低于它们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导权。第三,由于上述原因,外援在中国不仅找到了最佳的试验场,同时从中国吸纳了大量和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发展实践经验。第四,随着中国发展速度的加快和国力的增强,各类对华援助开始通过相互协调转向一个相对统一的方向:即从对经济领域的援助转向对社会领域的援助,再转向对政府政策和国家制度改革的援助。第五,流入中国的援款不仅仅是“优惠外资”,随着这些援款流入中国的还有援助者的技术、观念和方法。对于这些技术、观念和方法的消化、吸收、借鉴促使中国在至关重要的发展阶段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外援不仅仅是外交工具,而且可以成为外交的先导。
从上述情况中产生了一个理论的,也是实践的问题:外援是否能够影响受援国对于发展道路的选择?又如何影响受援国在各个领域里的制度建设?其中是否存在规律或原理?我们根据外援资金的流向和方式对流入中国的外援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发现,流入中国的外援数额远远低于外资的数额,但是外援所产生的影响却不亚于外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外援的活动领域并不局限于经济。援助原则和援助方式中凝聚了国力、社会力和文化力,而这些是难以用简单的数字加以概括总结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将外援援华活动放在当代历史的大背景下去理解,一方面依靠很不全面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另一方面尽量寻找局部的可靠统计数字,同时使用其他定性的分析手段,并在访谈方面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在此基础上,运用财政转移、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理论和视角,对外援在中国的实践进行分析,重点考察外援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由外援直接和间接引起的理念、方式和机制的变化。
一 现代外援活动的历史背景及理论概述
(一)历史背景
现代大规模的外援活动起始于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但是要想真正理解对外援助的性质和作用,还要往前追述。1944年初,苏军发起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总反攻,同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国法西斯政权的瓦解指日可待。劫后余生的人们开始反思人类历史上那场最惨烈的战争,筹划着建立一种能够长久维持和平的体制,当时已经有人想到,这一维持和平的机制与促进发展的方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正是在1944年,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伟大的转折》。他在书中指出,对于19世纪的西欧文明史来说,起决定和规制作用的是市场。市场自我发展的推动力最终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内外的双重恶性竞争。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的十月革命、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1931年金本位制的崩溃,动摇了西欧的制度模式和西方的文明基础,导致了西方国际安全体系的瓦解。1926年,凯恩斯宣告了“自由放任的终结”,② 10年后他又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实行社会再分配。凯恩斯经济学不仅丰富了欧洲的公共政策理论,而且在后来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将凯恩斯主义化为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的催生剂。波兰尼认为,恢复与维持世界和平的关键固然在于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国家,但是重建起来的国家不应再是自由主义的国家,而是能够有效地平衡竞争性的劳工市场、维护大众民主的政治制度、并且能够对社会进行保护性干预的国家。③
又是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布雷顿森林机构④ 和同时期出现的联合国及其专业机构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帮助成员国实现战后重建,但是它们的方式却因为设计者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联合国的主要机构采取的是成员国政府间的决策机制,可以说,它强调的是“代表成员国”⑤,虽然这种代表是分层的;相对独立的布雷顿森林各机构虽然也采取政府间主义的决策机制,但却以国际资本市场为后盾,以辅助成员国政府为基本原则,所以它强调的是“服务成员国”⑥,其服务方式是利用西方控制国际银行体系的优势,调动世界资本市场,帮助成员国解决就业问题,保持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和收支平衡。在布雷顿森林机制的设计者们看来,推动世界发展的真正动力不是来自于国家而是来自于企业家。所以,国际多边机制应当支持国家为企业家提供必要的发展条件,在超出国家能力的情况下,由国际多边机构直接提供这些条件。在这种以企业为核心的西方世界市场体系之内,非工业国家和殖民地的发展当时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⑦
苏联没有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发展理念与其发展理念相互矛盾。在联合国体系内,苏联在联大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但是由于联合国的一些专门援助机构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的资源和理念,常常有意排斥苏联的影响力,因此苏联在整个世界多边援助体系中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它通过“共产党情报局”,以及“经互会”等组织,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进行援助活动。这样一来,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就分为两大部分,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也分别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种类、内涵和执行方式都不相同的援助。
结果,在二战结束之后不久,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很快就恢复了起来,但是主权国家内的体制不尽相同。在西方,《马歇尔计划》致力于在重建国家的同时重建市场;在东方,国家重建伴随着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制。在西方(这里主要指西欧),国家内部结构形成了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制衡;在东方,中央政府在规划企业和社会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和主权国家体系同时建立起来的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它们由于内在结构的不同而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方式和国家间关系。美苏的对外援助活动分别服务于各自阵营的建设。在东方,苏联在援助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建之后,又在1949-1959年的10年间,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为56.76亿旧卢布的巨额援款,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⑧ 在西方,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建战后的西欧,在那里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随着东西欧经济的恢复,通过接受外援而选择发展道路的情况又出现在刚刚脱离殖民统治的广大发展中地区。二战后,亚非拉前殖民地获得了独立,成为两大阵营中间的“灰色地带”,随即由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陆续获得了来自东西双方的援助。接受西方援助的国家往往同时引进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而接受东方援助的国家则学习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中国先后从东西方两种体制获得援助,其利用外援的经历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
(二)理论概述
二战后关于外援问题的理论探讨门类繁多,其中有两种视角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对外援的实践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经济学的视角,主要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二是国际政治学的视角,主要是分析援助作为对外政策工具的特性。
经济学的分析主要讨论“如何通过外援推动发展?”争论的焦点是:发展应该更多地倚仗国家干预,还是应该依靠自由市场机制。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对官方发展援助活动的看法。在20世纪50年代,倡导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是主流经济学理论,当时的发展经济学也打上了这样的时代烙印。《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西方经济持续繁荣,学术界因而对于国家干预主义抱有普遍的乐观情绪。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瓦尔特·罗斯托(Walt W.Rostow)⑨ 和钱纳里(Hollis B.Chenery)⑩ 等人强调,外援帮助不发达国家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制度方面的瓶颈,对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向受援国转移的资金、技术和经验还可以“替代”西方经过数百年的原始积累、漫长的技术革命和消耗时日的人才成长过程,带动发展中国家用比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同时可以将发展的经验和繁荣的成果自上而下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如涓涓溪流般滴入发展中国家的土壤,产生带动发展的效果。(11) 根据这个逻辑,更多的投入必然带来更快的发展,因而国家干预和资金转移是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因素。这种资金转移的理论也就成了早期发展援助的主要理论依据。
然而,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的资金转移在一国之内可以是弥补市场缺陷、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但是如果跨越了国境,特别是作用于不发达的受援国,就可能成为一国干预他国的工具。这种工具所实现的政策目标不仅仅限于弥补市场的缺陷和提供公共服务,而是可能夹带着其他许多非经济目的。
由于早期的援助活动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带动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由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复兴,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受到了自由市场经济支持者的严厉批判。(12) 这些评论认为,影响发展有诸多的因素,政府拨款并不能解决发展问题。这种意见直接影响了国际领域里发展援助政策的嬗变,导致了80年代大范围的“结构调整贷款”(Structural Adjustment Loan)的出台。
与发展经济学者不同的是,国际政治学者把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在内的外援看作是一种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这种分析力图揭示外援活动所确立的权力关系,即谁主导了援助活动,谁从援助中获益,以及外援活动如何加强了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原本存在的不对等关系。这些分析认为,在外援实践中,提供援款的主要目标往往不是推动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是服务于援助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其次,由于援助活动的特殊性质,它可以覆盖受援国几乎所有的国内政策领域,并能够深入到受援国社会的最深处,带动自下而上的变化。由于这些原因,讨论谁主导发展援助活动就具有非常明显的现实意义。目前讨论的一些焦点问题,例如外援活动的所有权(Ownership)与伙伴关系(Partnership)(13)、外援的附加条件(14),以及一度盛行、至今仍然发挥影响的“依附论”等,(15) 就从不同的角度回答过上述问题。
二 作为跨国财政转移的对外援助
(一)对外援助的基本性质
我们理解的财政转移通常是在主权国家内部发生的,但是对外援助这种财政转移却是一种跨国的行为。由于对外援助的资金来源于援助国的政府财政支出,并依靠援助国的政府机构(或通过体现援助国利益关系的国际多边援助机构)执行。因此,没有人否认,外援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国家干预形式,是国家行为。(16) 不仅是国家行为,而且是跨国的国家行为,是援助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形态和行为方式在边界之外的延伸。正是因为如此,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外援这种跨国的财政转移的分析就深入到对援助国的国家特性的分析。一种典型的观点认为,西方援助国的国家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因此,这些国家就会利用外援活动,为资本的扩张创造更好的条件。(17) 与此相对应,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有两种动机:一种代表援助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特性,另一种则代表援助国的民族利益。可见,外援所代表的援助国国家利益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在于,援助国都希望通过提供援助获得利益,但是从不同的国家形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利益的理解是不同的,有些是统治者私利的表现,有些是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也有些关系到许多国家或人类生存的普及性利益。
这样一来,对外援助资金作为一种跨国财政转移就有了至少三种主要的性质:一是国家的工具,二是资本的工具,三是发展的工具。而判断外援资金到底属于哪一种或哪几种具体的性质,需要考察援助方提供援助的目的和方式,更需要考察受援方的立场和作用,因为对外援助在实施的过程中涉及提供援助方和接受援助方的意志、能力和作用,是双方深层合作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外援最终的形态往往是双方关系结构的体现。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凯恩斯主义国家与以往的自由主义国家不同的是,它的力量来源和服务对象不仅是资本,还有迫使国家规范资本的社会团体。市场经济是西方制度的基石和出发点,但是有组织的民众通过选举决定国家的政策,国家则通过宏观调控干预市场,通过社会再分配服务民众。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赋予凯恩斯主义国家以干预经济和社会的行政、立法和财政手段,使得它能够通过转移支付,创造投资环境,弥补市场缺失,促进稳定发展。但是,在进行跨国转移支付的时候,外援资金的缴费主体和支付对象是分离的。资金来源于援助国的公民,而支付对象却是受援国的国民。由于国家的对外政策是相对独立和不透明的,所以资本和社会对于国家在这个领域里的约束程度同时降低。提供援助的政府和团体可以根据自己对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理解,决定外援的投向和政策。因此,对外援助这种“国家行为”作为“国家对外干预的一种形式”与对内财政转移相比较,就表现出“供给导向”的基本特征。(18)
供给导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援助国或援助方以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为摹本去引导受援国的发展,例如苏联援助提供计划经济的经验,而西方援助则提供市场经济的方法。第二,援助国除了向外输出用于发展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以外,必然将本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特性附着在外援活动中。对外援助作为向外国提供的财政转移,必然在转移资金的同时使国家利益和国家特性得以延伸,所以西方援助国的官方文件对于外援作为特殊的外交工具的作用也从不讳言。
(二)外援作为国家的外交工具
外援的使命绝不仅限于发展。它的初始目的也并不是发展,而是外交。外援能够行使特殊的外交使命是因为这种财政转移不仅是各国领导人为树立国家形象和获取国际友谊而常常赠送的“礼品”,而且是超越传统外交领域的工具。
首先,外援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实现援助国在受援国的经济利益。在很多情况下,援助活动起到了为贸易和投资开路的作用。除了在外援项目协议中附加购买援助国产品的条件之外,援助国往往与受援国进行生产技术标准等方面的战略性合作,或投资于改善受援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及法规,用以改善贸易和投资的软环境,为本国的投资和贸易做前期的准备。
其次,外援活动还可以通过资助受援国,使之就敏感问题进行与援助方之间的政策对话,加强双方政策立场的协调,促进援助国在受援国的政治利益的实现。例如,援助国在要求受援国提供项目意向计划的时候承诺在贸易、投资、公共政策等关键的政策领域进行改革,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进而推动受援国的全面改革,使之接受援助国的价值观念和政策立场。
因此,外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个无法替代的战略工具,它不仅帮助援助国实现短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还可能影响受援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乃至对于发展道路的选择。外援还是观念传播和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它创造了观念交流和碰撞的机会。通过人员交流与合作,援助方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援国的观念、制度和行为方式,在受援国培养了一大批“志趣相投的”(like-minded)政府官员、项目执行者、技术人员和学者。因此,对外援助输出的绝对不仅仅是资金,在援助项目结束后,援助方的那些“软力量因素”会继续在受援国发挥影响。
外援活动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往往包括了国计民生的所有方面,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外交政策渠道能够与之相比。通过在这些领域里与受援国的各个阶层进行合作,援助国的影响力渗透到受援国最边远的角落和社会的最深处,极大地扩展了外交空间,丰富了各国人民之间交往的内涵。
(三)外援作用于发展和发展道路的选择
在苏联大规模削减乃至基本停止了对外援助活动以后,西方援助继续活跃在国际援助领域里。苏联援助提供的是如何制定“五年计划”,怎样发展重工业,以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大工业生产的具体操作方法,西方援助则提供了适应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源开发培训,传授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用市场的方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继之援助社会发展,从事扶贫减贫、基础教育、环境保护、提供企业能够平稳发展的市场环境,最后通过“能力建设”项目,关注受援国的政策转变和制度建设,在政策观念转变、市场机制建设、法律法规制定和社会分配体制改革等许多被称为“政府治理”和“法制建设”的领域里发挥影响。
这些通过外援在提高生产力水平、调整生产关系、改革国家管理体制等各个发展阶段和层次上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被固化为受援国的内部机制之后,一般能持续地发挥作用,使受援国的发展路向在制度、观念和方式上趋同于援助方,成为发展中国家逐渐接受国际标准和“融入国际社会”的保证。所以,在供给导向方面,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并如何在援助活动中体现受援方的“所有权”和受援国的“自主权”。出现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各主要援助方倾向于将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看成是唯一成功的经验,并且努力在发展中受援国推广这些经验。这些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受援国在援助方的影响下持续不断地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环境的改革,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普遍地改善它们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恶化,外援引导的政策干预往往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地情况,结果导致受援国门洞大开,跨国公司如入无人之境,并形成国际资本垄断的结果。(19) 在这种情况下,受援国对于发展项目的决定权、设计权和所有权就成为发展领域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发展中受援国争取“所有权”的斗争体现在给援和受援双方关于援助项目的谈判、决策和实施的过程中。在这个方面,中国提供了为世界瞩目的成功经验。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接受援助时对援助方产生了反作用力,援助领域里的主导概念正在发生变化,从“发展援助”变成“发展合作”。这里体现了受援国在选择发展道路和方式方面的参与,(20) 而外援在发展方面的经验和作用也随之而丰富起来。
(四)外援与国际发展的不平衡
援助方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国际资本,扩大世界市场,为资本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方便。国际社会外援机构帮助国家进行战后重建的“辅助性原则”随着跨国企业的发展和社会力量的国际化而逐渐演化为鼓励多元行为者的“参与式原则”。多元国际行为者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主权国家的影响力,但是国家作用的减弱却未能带来国际社会的平衡发展,相反,贫富悬殊和数字鸿沟却日趋严重。要了解外援活动与这种国际现象之间的关系,需要从援助和受援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从援助方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承认世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西方援助方倾向于把发展援助的失败归咎于受援国政府的失败,而不从市场规则的无序和跨国企业的无度中去寻找原因,更没有设法理解受援方自身的发展历程和历史逻辑。它们以为,只要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律,将外援资金投入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社会领域,就会在受援方产生与援助方发展进程雷同的效果,但结果却是把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不对等关系带入了社会领域,使社会服务成为“社会资本”,使得援助国对受援国的干预从经济和技术层面向社会和文化层面深入。(21)
从受援方的角度来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制订发展规划、争取外来资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主要的原因是提供援助和接受援助双方力量对比的严重不对等。援助国将十分有限的国内资源用于极端贫困的国家,在那里转化为各种经济和政治力量。受援国出于不同的目的去争取这些对它们来说是数额可观的资源,甚至不惜为之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由于力量对比的失衡,掌握了资源的援助国就获得了一种超越传统主权国家的政治力量或筹码,用以实现对于弱国的政策干预,甚至政治干预和渗透。而且,这些干预或渗透往往是在受援国自愿的基础上发生的,因为它们急需资金、技术和设备等“硬件”,而同时缺乏抵制不良影响的“软件”。(22)
(五)外援作为全球治理的工具
外援的提供者是多元的,包括双边援助国、多边援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它们之间正在形成融资合作,构成国际性交流平台,并通过这些合作与交流,形成对于主导观念、投资方向和附加条件等一系列与发展援助相关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形成规范各个援助提供者行为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国际援助体制。这个国际援助体制的存在,对于全球治理的方式和方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外援活动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几乎同步,是全球化进程中重要的跨国流通渠道之一。1994年,斯科斯托·洛克塔斯(Sixto Roxas)在回顾世界银行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时承认,这个机构建立之初的“辅助性原则”其实暗含着一种深谋远虑的哲学理念,其核心概念是:“决策应当在尽可能最低的层面上做出”。因为“最低层面”可以是社区的,可以是民族国家的,也可以是全球的,所以“辅助性原则”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在多样性组织中相互作用的方式”。(23) 在二战结束初期,布雷顿森林机构作为政府间的多边机构,“辅助”的对象当然是各国政府,但是因为它的初始原则并不忽视非国家的行为者(包括跨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所以在二战后50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向国际层面的发展,布雷顿森林机构理所当然地把它们作为全球行为者来对待,使之成为主权国家的挑战者。事实上,代表着国际资本力量的布雷顿森林机构自成立伊始就认为,“持续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核心动力”来自于“新的一族经济人”,他们不是企业的所有者,却是巨型企业的领取薪水的管理者。(24) 多边和双边援助为这种企业家在全世界打开市场付出努力的同时,帮助造就了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由主权国家、跨国公司、地区和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构成的多层、多元、多行为者的新的全球秩序。
国际援助方为建立这个世界市场体系所付出的努力不胜枚举。它们通过提供类似结构调整贷款、技术援助以及各种各样的外援项目,鼓励受援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厌其烦地教授受援国的政府和企业如何习惯市场思维方式,掌握市场管理工具,建立市场监管体制,培养市场管理人才,甚至投资与市场经济配套的社会服务设施,使市场和跨国企业的引进不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成熟的市场机制在西方经济的发展史上经历过无数的社会动荡,而通过外援投资建立的市场竞争机制与相应的社会服务配套设施却可能在短时间内以较小的社会震动完成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性替代”,进而进行市场经济的全球性建构。
随着新型企业家的成长和跨国巨型企业的出现,国际舞台就不再是主权国家独大的天下了。外援资金不仅帮助跨国企业打通国界,也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国际舞台。无论是以发展为目的的官方发展援助、还是用于救灾的人道主义援助,受援的人群多是受援国的弱势群体,这些人或是处于受援国的不发达地区,或是处于社会底层。援助方调动了各级政府和非政府的组织资源,直接参与到对受援国的基层援助活动之中,通过项目执行,在基层社会传播援助方提出的计划、方案、观念和方法,在那里,通过与受援方的合作,形成了社会工作规则和人际网络,再通过援助方提供的国际网络资源,使那些地方经验能够传播到世界各地,让“全球性思维和地区性实践”(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的口号响遍全球,也让各地社会基层的工作者成为国际性论坛和舆论的参与者。
此外,外援回应经济全球性带来的全球性挑战。随着各种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全球性问题也日益突出:空气污染、土地退化、瘟疫流行、毒品泛滥等等都产生了跨国性的后果,也带来了实现全球治理的现实要求。但是,主权原则仍然是不可撼动的国际政治体系的基石,治理活动也大都局限在主权国家的疆域之内。随着跨越国界的需求的出现,外援资金的国际性流动和外援机构及人员的跨国工作就成了弥补现状和需求之间差距的一个重要工具。
所以,从国际援助体制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看,它不仅帮助了跨国企业的发展,也通过它在世界各地的网络关系,将局部的发展经验传播到更大的范围,并且通过对于资源的导向性利用,促成了对全球问题的共识。“可持续发展”、“参与式管理”、“小额信贷”等新概念和新方式的推广背后都有外援的力量。
三 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受援国
在当今世界上,提供外援的目的和方式,执行援助项目的结果,以及外援对于发展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援助方和受援方的分别努力,更取决于援助方和受援方之间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也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转化的。在中国接受外来援助的历程中,这种转变尤为明显。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外援在中国
中国接受外援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大规模地接受苏联援助;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接受的援助主要来自于西方发达世界。
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对于国际援助都采取积极审慎的态度。毛泽东早就指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是一种错误的想法。(25) 在毛泽东看来,世界上的许多力量都是可以利用的,需要根据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和力量变化来确定中国的战略和策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伊始,面对世界形成两极格局,而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数轮的外交谈判,从苏联争取到了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和其他援助,资助了“156项”重大工程的建设,不仅引进了中国急需的资金和设备,而且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和经验。借助苏联援助,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发展,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初步实现了在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基础上建设现代化工业国家的发展目标。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邓小平提出,应当主动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外国的管理经验,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26) 中国政府自此开始了历时近30年的接受西方援助的历史。目前,活跃在中国的援助方包括了国际多边援助机构、为数众多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成员以及规模和形式各异的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可以容纳各类援助方,同时在开始接受西方援助的时候就确立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因此中国比其他受援国更加能够有意识地引导外援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借助外援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从1979年至2006年,中国共接受多双边无偿援助63亿美元,实施了1000多个项目。(27) 1995年,中国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援助达到峰值,成为世界最大的受援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外援试验场。在中国这个试验场上亮相的外援项目经过了一个由硬变软、由东渐西、由国内及全球的发展过程。在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援助方和受援方的相互作用。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受援国,其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这个外援试验场不是由援助方左右的。
所谓“由硬变软”是指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外援主要集中在农业和工业生产领域,用于农业技术开发和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投资,而后随着市场扩大和生产发展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出现,外援逐渐转向投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妇女发展和基础教育等“软”领域。此后,援助项目逐步软化,开始介入市场管理和市场机制建设,出现了大量的政策咨询项目。最近,中国与援助方开始了在立法和司法领域里的合作、人权领域里的对话和民主建设领域里的交流。目前,援助项目集中在两头,一头达到高层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领域,如司法合作、村民选举等;另一头维持在基层工作领域,如综合扶贫、环境保护等。
所谓“由东渐西”是指援华重点地区由东部省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国的“九五”计划提出:“中西部地区,要积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28) 援助方根据这个要求调整了援华政策重点,将更多的项目投向中国中西部地区。目前,大约70%的外援资金用于中西部地区的开发。一些援助方明确划定了云南、甘肃、四川和西藏自治区为重点援助省份。(29)
所谓“由国内及全球”是指对华援助越来越关注全球性问题,鼓励艾滋病、大气污染、跨国犯罪等领域里的国际合作,支持中国目标人群和境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与这种合作同时出现的还有援助方之间相互融资,共同支持一个跨国发展项目的现象。
(二)外援在中国的作用:方向与方式的互动
中国接受的外援总额并不多,但是效果却始料未及,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作为受援国和各个援助方之间的特殊关系结构。这种关系有时是“方向决定方式”,有时又是“方式决定方向”。在接受苏联援助的时候,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但是缺乏管理计划经济的人才和经验,中国通过接受苏联援助引进的不仅是先进的设备,而且是建设工业体系的方法,制定“五年计划”的思路和管理大工业的体制。这些方式、方法、体制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后来的发展路向。
1978年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对发展道路的又一次重大选择,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次选择与革命的核心是“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此,中共中央要求“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30) 改革的方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31) 在发展的大方向确定了之后,方式就成为关键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中外都无经验可以参照,特别是中国在实行了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之后,对于市场经济的运作缺乏基本的常识。因此,西方援助方一进入中国,就开始投资于组织涉外金融、财政、收支等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培训,填鸭式地灌输有关市场经济运作的知识和技能。(32)
此后,援助方开始帮助中国大批量地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受训人员,让他们去实地考察市场经济在西方社会的运作。同时,援助方又利用自己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强大的国际网络,在计划经济影响力最薄弱的农村支持技术改造和市场发展,取得了实效。不少农业品种、耕作技术(如大棚、地膜等)直接来自于援助方。在城市里,援助方通过持续、大量地培训各个领域里的专门人才,不仅使中国人接触到市场经济的原理,而且掌握了管理市场经济的手段。从可行性研究、招投标程序一直到财务监督、过程管理、意见反馈和成果推广,中国执行外援项目的过程就是逐一汲取援助方经验和方式的过程。
正像援助方所希望的那样,在华外援项目不仅“成功地”引入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而且“引入了政策改革”。(33) 中国在1979年之后频繁地接受来自世界银行、联合国援助机构和双边援助国的政策咨询,把援助机构的领导人作为咨询专家来讨教,世界银行针对中国的第一份报告甚至成了“中国高官的入门读物”。(34) 世界银行也由于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咨询而获得了“知识银行”、“经验银行”的称号。这些来自援助方的政策意见和市场知识运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政策变革的效果,例如,“企业住房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项目帮助企业改变了企业办社会的状况,转变了政府职能,解决了部门和地区之间的“无形壁垒”、“福利屏障”和大大小小的“属地原则”,使统一国内市场进而发展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能。再如,外援资金调动了中国的财政转移从投资企业转向投资社会、扶贫和环保等领域,中国政府通过财政转移为外援项目配套的资金比例逐年增加,外援项目因之而越来越“本土化”、“合作化”。
外援还带动了中国的机制改革。西方援助方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们往往要求在中国成立相对独立的“外资办”或“项目办”。这些外资办和项目办以英文为工作语言,按援助方和受援方协议中规定的工作程序办事,直接使用外来的观念和方法,并且在受援国本土培育消化这些观念和方法的能力。这种嫁接产生的机制随着外援项目的建立而在中国各地各部门复制,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通过这些方式的转变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渐进的”体制转轨和机制创新。
通过外援资金引进的市场管理方式和理念也影响了国家改革目标的制定和体制改革的方向。在重新接受外援短短5年之后,中共中央于1984年认真总结了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以来的利弊,提出“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路,并且强调要“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35) 此后,根据邓小平在许多场合的讲话精神,根据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36) 的提法,也根据历年来政界、学界和社会各界通过多种渠道获得的关于市场经济的知识,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大量地吸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管理方法和社会分配机制,标志着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
可以说,中国首先选择了走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方向性的选择决定了中国对于外资和外援的引进,而外援在中国的活动和外援的方式为中国提供了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案和方法,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外援在中国的国际意义
外援在中国的实践是否具有国际意义?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是否可以看到世界发展的脉络?二是中国是否借助外援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三是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否证明并丰富了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原则?
(1)从外援在中国的实践可以透视时代的变迁
外援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经历了两次大的时代变迁:中国对于苏联援助的吸收和使用,在战略上巩固和扩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体制和机制上探索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方式。苏联援助帮助中国奠定了工业现代化的基础,同时在客观上限制了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西方援助的吸收和利用使中国熟悉了西方发展的经验,并且借助西方的资源和利用资源的方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轨道。中国不仅从世界市场获取资金和技术,更向世界市场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外援帮助了中国的发展,同时加强了世界市场的力量。外援在中国的实践正是市场力量在全世界扩张的时AI写作照。
(2)中国借助外援走上了一条“渐进型”的独特发展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快速而又相对平稳地发展起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解读。据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的观察,中国的快速发展曾经触动了俄国人最敏感的神经。这个曾经仰赖苏联援助的贫穷国家是否因为选择了非社会主义道路才发展起来?如果是,俄国人也想尝试一下。(37) 他们放弃了社会主义,选择了“大爆炸”(Big Bang)的“激进型”变革,结果却事与愿违。
中国选择了“渐进型”改革方式,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从引进外援项目开始,学习市场知识,引进市场经营方式,带动相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发展,影响着政府职能逐步从计划式管理向市场化管理的方向改革。在接受外援的整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是最有效的中介。无论是主管援助贷款项目的财政部门,还是主管赠款项目的商务部门,都以邓小平提出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根据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金短缺、知识短缺、技术短缺、人才短缺以及观念、体制陈旧等问题,引导援助方在上述各个领域里的投入,使外援能够直接地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服务,从而保证外援在中国服务于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大政方针。
1979年以后的外援项目并不都是加强政府权力的,但即使是在政府改革领域里的外援项目,也往往是由中国政府提出来的,是为了转变政府的职能,加强政府的能力而设立的。例如,援助方引进了通过“参与式”方法进行扶贫工作的经验,导致了以社区为主导的自主发展,政府从社区扶贫工作的决策者和经营者变成了服务提供者。中国还引进了一些以改革观念和体制为目标的外援项目,其目的不是要进行全盘的自我否定,而是在“强有力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38) 的保障下,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39) 改革和引进使中国政府在改造自我的同时改造外部世界,这是中国“渐进型”发展模式能够成功的一个关键。
(3)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人类发展多样性的财富
经过外援渠道流入中国的资金数量虽然远不能与外资相比,但是其影响力却超越了经济领域,涉及经济以外的社会和政策领域,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政策取向和制度建设。因此,外援不仅是援助国向受援国施加影响的一种“温和的”方式,同时也是受援国利用援助国资源的一种“沉默的”方式。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它还是受援国以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影响世界的一种“主动的”方式。
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中国通过外援影响世界的方式首先体现在认知上,外援在中国建立起的是一种双向的“学习过程”。中国接受援助的过程一方面是中国了解国际规则、融入国际体制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成功地实现了发展的目标,为“发展”这个概念的规律性认识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丰富了世界发展的多样性。世界银行多次总结中国发展的独特经验,并且在国际上广为传播,有些经验被用于其他国家,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从外援在中国的实践中既可以看到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也可以看到中国发展与世界其他文明发展之间的共通性。从共性的角度看,发展生产力是一个关键。就像邓小平多次指出的,任何社会制度,如果不能有效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会丧失自身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中国接受的外来援助作用于发展生产力:苏联援助通过对基础工业设施的投资和对大生产的组织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西方援助则通过资金投入,带动市场建设,促进了中国的改革事业,使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释放出来。因此,中国发展模式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优先发展生产力的共识。
中国消化吸收西方发展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走出的发展道路对于援助方的援助政策和措施产生了反作用力。当援助方对投资上层建筑趋之若鹜时,中国政府提出,发展基础设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推动减贫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世界银行等援助方从2004年开始重新肯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扶贫的作用,并强化了对这些领域的支持力度。当国际援助体制在美国的引导下讨论“失败国家”导致发展援助失败时,中国则在2005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讲坛上提出,受援国的政府能力建设和自主发展能力培育是保证国家长久稳定发展的关键,应当得到特别支持。中国的意见得到许多参会代表的支持,重视“国家能力建设”(building state capacity)也因此而被写进了会议公报,因而将引导世界外援的走向。
外援通过多种渠道将中国和国际社会相连接,在世界上形成了各种新的力量组合。作为受援国,中国与援助方就发展问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层合作。中国的发展经验使得中国和援助方之间的关系组合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从接受发展援助变为进行发展合作。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不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而且这些经验由于加进了发展中受援国自身的因素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具参考价值,并可能使中国在发展问题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本文为作者在其专著《外援在中国》一书的导论部分基础上修改而成。
注释:
①这里指“对外援助”,为行文方便,文章中有时简称为“外援”或“援助”。
②波兰尼认为,西欧19世纪的文明史建筑在四大机制上,它们分别是:防止强权相互征战的势力均衡机制,使市场机制能够向国外发展的国际金本位机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市场机制,以及鼓励市场扩张的自由主义国家机制。金本位固然总要,但是动力源是市场。参见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New York and Toronto:Rinehart & Company,Inc.,1944,p.3。凯恩斯1926年6月在柏林的讲座,载于1972年由伦敦马克米兰公司出版的《凯恩斯文集》第9卷(John Maynard Keynes,Collected Writings,Vol.Ⅸ:Essays in Persuasion,London:MacMillan,1972,pp.272-274)。
③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New York and Toronto:Rinehart & Company,Inc.,1944,p.223.
④这里主要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⑤英文原文为" by the member states" 。
⑥英文原文为" for the member states" 。
⑦Sixto K.Roxas," Principles for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Jo Marie Griesgraber and Bernhard G.Gunter eds.,Development:New Paradigms and Principl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luto Press,1996,pp.5-6.
⑧1949年6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向他表示要给中共提供3亿美元贷款,利息1%,为期5年。参见沈志华《建国初期苏联对华援助的基本情况》,http://www.shenzhihua.net/zsgx/000140.htm。1959年苏联单方面终止了对华援助活动,并于1960年撤走了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258页。
⑨Walt W.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⑩钱纳里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外援的论文,如:"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Development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1,1961; "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6,1966; " Foreign Ai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ase of Greec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48,No.1,1966,等等。
(11)参见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自1960年以来(特别是1980年)的年度报告。
(12)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人物有:Friedman,Bauer,Yamey以及Krauss。参见Roger C.Riddell,Foreign Aid Reconsidere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p.86-87。
(13)Alf Morten Jerve," Ownership and Partnership:Does the New Rhetoric Solve the Incentive Problems in Aid? " ,Development Studies Forum,NUPI,December 2002,pp.389-407.
(14)Olav Stokke ed.,Aid an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London:FRANK CASS,1995; Tony Killick,Aid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Change,Routledge,1998.
(15)周弘:“对外援助与现代国际关系”,《欧洲》2002年第3期,第1-11页;Roger C.Riddell,Foreign Aid Reconsidere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p.129-156。
(16)Roger C.Riddell,Foreign Aid Reconsidered,pp.86-87.
(17)Neil Middleton and Phil O' Keefe,Disaster and Development,Pluto Press,1998,pp.16-31.
(18)Roger C.Riddell,Foreign Aid Reconsidered,pp.86-87.
(19)Jan P.Pronk," Aid as a Catalyst:A Rejoinder" ,in Jan P.Pronk et al.,Catalysing Development? A Debate on Aid,Blackwell,2004,pp.191-208.
(20)参见2006年11月24日姚申洪访谈记录。
(21)P.Q.Van Ufford,A.K.Giri and D.Mosse," Interventions in Development" ,in P.Q.Van Ufford and A.K.Giri eds.,A Mor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Routledge,2003,pp.3-35.
(22)周弘:“对外援助与现代国际关系”,第1-11页。
(23)Jo Marie Griesgraber and Bernhard G.Gunter eds.,Development:New Paradigms and Principl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roduction" ,p.xv.
(24)Sixto K.Roxas," Principles for Institutional Reform" ,pp.7-8.
(25)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页。
(26)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83页。
(27)这组数据由商务部2004年12月7日在京召开的第五届捐助国协调会议正式发布,资料来源:人民网2004年12月7日。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参见http://www.people.com.cn/zgrdru/zlk/rd/8jie/newfiles/d1150.html。
(29)资料来源:商务部2004年12月7日在京召开的第五届捐助国协调会上发布的数字。
(30)《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参见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3/5205/200104281/454803.html。
(31)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236页。
(32)由于西方经济学基础知识的匮乏,在20世纪80年代初举办的一次培训班上,中方竟然将“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marginal utility/marginal cost)翻译成了“边角料的用途”和“零碎材料的成本”,将“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翻译成了“破碎了摸平的一点”,参见彭运鹗:“知识胜于资本——我所认识的世界银行”,《当代金融家》2005年第12期。
(33)世界银行业务评估局:《中国:国别援助评价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34)世界银行业务评估局:《中国:国别援助评估报告》(2004年),参见http://www.worldbank.org/oed。
(35)《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84年10月20日通过),参见http://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41/20010429/455410.html。
(36)邓小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
(37)信息来源:莱斯特·瑟罗2001年访华时的一个晚餐会谈话。
(38)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39)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