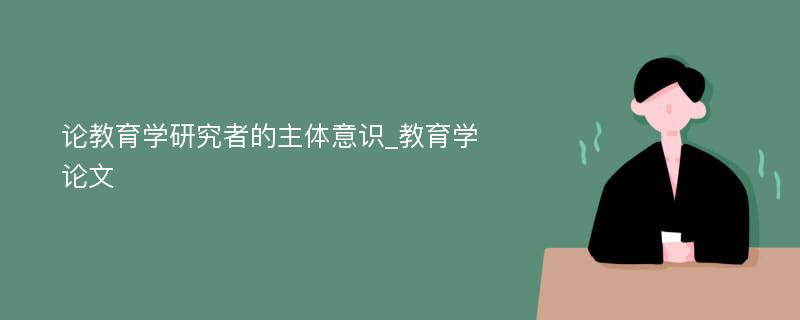
论教育学研究者的学科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者论文,教育学论文,学科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学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似乎要突围,要突研究视角的围,要突研究范式的围,要突分析框架的围,要突主流话语所隐含的权力之围……,而种种突围的成功,系依于或体现于另一种突围:教育学研究者自身的突围,武器即是方法论革新,表现方式即为研究者意识的形成。“表面看来,……方法论研究似乎离开解决具体的教育理论或实践问题很远,看不见,摸不着,有些玄乎……”(注:叶澜著:《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页。),是的,这只是表面上,实际上,方法论离我们很近,它就在我们的意识中,就是我们的研究意识,“是自觉的思想的活动。”(注:莫兰著:《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5页。)我们认为首要的是研究者要有明确的学科意识。
一、自觉的科学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以其客观性、可重复性、价值中立等特征为卡尺,使社会科学在这种标准前无地自容,总是发出自己是不是科学的“深刻”的扪心自问。自然科学工作者以一种超然的态度,以一种外在的旁观者的身份,持一种主客二分的立场去从事研究;而社会科学研究者则不一样,是以一个介入者的身份去体味世界。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认知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不具备可比性,因而不能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要求社会科学研究。
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者曾试图用自然科学的认识模式,以旁观者的身份,采用中性的语言来研究和说明社会。但赞同这种主张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已越来越少,因为他们觉得这不可能。事实上,“在社会科学中人们认为可以排除观察者,这是个十分虚妄的观念。”(注:莫兰著:《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社会科学研究者们越来越感受到:必须以参与者的身份而不仅仅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研究社会。而且社会科学家的这一信念已逐渐为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所接受(注:林德宏等著:《科学认识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因而社会科学研究者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研究社会现象与社会事实。进一步讲,自然科学中也有研究主体的介入。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系统论述了科学作为一种人的社会活动及其历史发展这个侧面,把科学从认识论范畴放大到社会历史范畴。他认为,科学所描述和再现的世界不是取决于世界自身的样子,而是取决于科学家观察和解释时所采用的范式和模型。
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本身就存在着种种前提与出发点的不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本身就属于两类不同的规律,具有不同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封闭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差异:一个追求永恒,而另一个则追求关联与变化;一个追求外在因果关系,力图使用简化方式;而一个则倡导内在因果性,非常重视自组织。我们在外在因果性中发现数据和可操纵性,却在内在因果性中发现观念和可操作性。作为一种自觉的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必须消除掉自己的盲目运作:自然科学必须把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现实来认识;而社会科学则必须从生物——物理的根源来认识自己。这样做,实际上是寻求一种内在因果性与外在因果性联系,也正是这种相互作用而引起和维持了一个系统的自主性。
反思一下教育学领域中的学科意识,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存在着两类教育学:一种是自命为科学的教育学。这种教育科学采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规范,用因果性。客观性来消解掉了行动者和主体自觉概念。另一种即是抵抗这种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式的教育学。它承认目的性与主体性,尊重个性与经验,而对教育中采用自然科学式研究持不信任态度。由此看来,教育学尚未具备自觉科学的意味。因为教育学尚未关注这种外在因果与内在因果性之间的统一,仍是一种学科的二元。
科学在这种连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建设,然后自我破坏,再自我重建,这是自觉的科学的运作方式,它是“自我产生”的。这种自我产生促成了学科多方面的新发展,从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起对自身的“反思”与“自我诘问”的方式。元科学及新的元元(……)系统的发展即成为这样一种长期而深刻的“自我产生”的促进机制——当然是在与文化、社会与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而不是在封闭的容器中的转换。
二、充盈着生命的学科
教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要树立自己的学科意识,使自己成为一种自觉的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所遵循的是一条“人择”原理,是“人”的,而不是“熵”的。但自然科学的“标准”对我们教育学肯定会有所触动,因为我们是开放的。最大的开放就是教育学必须向生物学、人类学开放。这种开放是正视生物(个体)——教育——社会(人类)的复杂性,这种开放使我们的学科变得更深刻、更丰富、更生动也更真实。这样一来,我们的学科才是充盈着生命的科学。而且教育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实现的过程,教育是人与人、人与人类的一种深刻交往的历程。在其中,是生命的相互碰撞与激活,正是因为教育学的这种生命性与生命意识,才使其具有永恒的魅力以及与人类共存亡的生命力。
在教育学研究中,我们是从两方面,即从其双重面目来理解生命:繁衍面目与现象面目(注:莫兰著:《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1页。)。前者即自然意义上的生命(物种的、类的),后者即是社会意义上的生命(个体的、所表现的)。繁衍的生命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敬畏的,因而教育学研究与教育实践中必须进行生命伦理的熏陶,贯彻一种敬畏生命的意识,使学生的生命意识日益浓郁,使生命之树长青。而现象的生命值不值得敬重就要看生命的展示与表现如何了。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渴望被肯定的潜意识,都有一种展示自己生命的追求与意义的冲动,并总在维护着生命价值的尊严。因而,指导我们教育行为的就应是这种对原初生命动机的肯定。教育学研究与实践都必须从如何培养有个性的人、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及追求人类完满的人为基本出发点,进行研究与实践。
另外,教育学研究及教育实践中,最有意义的激情点是未经设计的“事件”,是这些“事件”让整个教育活动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使教育活动脱离了机械的铁轨,走上了生活与生命的康庄大道。在这些“事件”中教师与学生都是在场的亲身介入。教育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要求介入的过程,只有真正的介入,教育活动才可能真正发生,没有介入,就没有教育。因而,教育学研究亦需有介入的性质,教育学研究者应重观这种介入意识的养成,也就是说教育学研究者必须锁定于教育中的事件。教育事实中的锁定是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锁定,教育学研究中的锁定则是指教育研究者与教育现象之间的相互锁定。锁定就是介入后的相互影响与互动。这种锁定就使得我们的教育学研究真正处于一种“接地气”(注:王晓明主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第19页。)的研究——教育学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处于一个历史情境中,能比局外研究者更真切地感受到研究对象的流变与脉动。也正是这种“接地气”的研究,才不会导致理论阐述的“底气不足”现象。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主体性,以自己的视角、经验、感受、理论去研究教育,从而得出富有个性的,具有特色的教育研究成果。如果说自然科学的事件是一种“类事件”,那么在教育的“人——人”关系中的事件则是“个别事件”。对本来作为“个别事件”的教育现象与行为我们不应强求其普适性。教育研究的成果必须首先满足个体的解释与描述。因而教育规律也就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情境规律”。
三、教育学研究者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似乎谁都能弄一弄关于教育的文章,我们称这些“业余爱好者”为“教育研究者”,而不是“教育学研究者”,教育学研究者应是有明确的教育学学科意识,是把教育学研究当成自己生命一部分的研究者,这即是我们用“教育学研究者”的缘故。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教育学研究者对此大为不满。其实大可不必。这不应被看成是对教育学和教育学研究者的嘲弄或轻蔑,任何学科都是对外开放的,都可以是一个研究领域,教育学自然不能例外。如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中班级社会学的发展,这实际上是可以看成教育学进军社会学的一个成功的“事件”,而不是社会学向教育学的侵略。
我们强调要有学科意识,那是从学科的自主性角度,而不是要树立一种森严的学科壁垒,以求自保。这不符合我们所强调的开放与共通的信念。事实上,学科之间都是相通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简单而意义深远的描述。
教育学研究者必须具有宽厚的学识基础,教育学研究者的学科结构应该是T型的,而有多宽,有多深则是不可强求统一的。每一个教育学研究者都是一直“走在路上”,走在“积学”的人生之路上。如果有一天发现自己没有继续学习的欲望,捧起文本没有阅读的激情时,那么也就是应该淡出学术道路的时候了。这不仅是一种学术的自觉,更是一种学者的自觉,是对学者命运的真切领悟。
研究教育学的人若只局限于教育学内,恐怕难成气候。但我们也并非无所不读,无所不用,也并不是随便抓住一个都能派得上用场,而且能用得比较好。我们更注重在自己的兴趣与根底的基础之上,去拓展“手边”的世界,去获得“上手的工具”。在学科之间穿梭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熟习:由博返约(一切及一),由精达广(一及一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进行教育学研究时,有进行“运算”的素材。
四、元教育学素养
尽管大家对“元”的理解不一致,但在“元教育学研究的对象则主要是对教育学研究活动及其理论的研究”这一点上,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元教育学研究的论争中,曾提出教育学的反省研究与元教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是交集,并非所有的反省研究都属于元教育学研究,也并非所有的元教育学研究都属于反省式的教育学研究。从自觉的科学这个角度与意义上来讲,教育学的反省研究应属于元教育学研究。他们对于教育学成为一种自觉的学科起着积极的作用。元教育学研究正是通过这种对活动与理论的研究,从而对教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方式以及现状进行深刻的反思;对教育学发展机制及内容结构进行认真的梳理,从而形成明确的教育学学科的“自我意识”(注:叶澜:《关于加强科学“自我意识”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7年第3期。),从而使教育学自觉地寻找自己继续发展的方向,增强学科发展的自控能力。这实际上也就是使教育学研究更加规范化与深化,使教育学研究进一步完善。
作为教育学研究者必须持有这样一种元教育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教育学研究者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研究视域与兴奋点,而且随时从系统与整体的立场来纵观整个教育学研究,并在这个系统中找到自己的研究与理论所处的位置或系统之层次,进而随时做出调整,使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更加合理,而不至于像一团乱麻或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碰,弄得鼻青脸肿。形成一种元教育学意识,是实现教育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性与学科自觉性的最好的途径。只有这两种自觉性都得到充分发挥,才能使教育学研究更充满活力与有序——尽管这种元教育学研究开始时可能会激发更深层的无序,但其目的是为了使教育学研究起向于有序。元教育学研究实际上也包括着对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本身的评论、省察及重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论的重建,才能帮助教育学研究者找到新的突破口,使教育学研究者走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