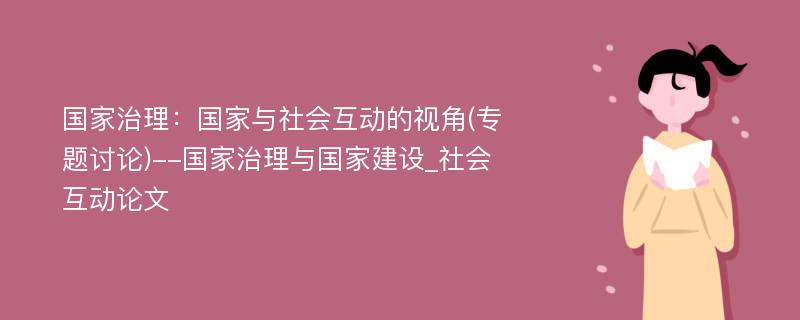
国家治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专题讨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专题讨论论文,互动论文,视角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治理与统治是不同的,治理有几个重要特点:治理的主体不限于政府,还包括公共或私人社会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和责任日益变得模糊不清;参与治理的主体形成一个自主网络,权力运行不再是政府单方面发号施令,而是各方合作共治。然而,“多中心”治道并没有否定国家的重要性。即使是治理理论最坚定的信徒也不会否认国家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之一。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下,国家在治理中的地位有所不同。中国的政治现实决定了党和国家依然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力量的成长固然重要,国家建设的加强更不容忽视。 一、社会中的国家 大体上,以社会为中心、以国家为中心和以个体为中心的国家理论是关于国家经验研究的三个主要视角。多元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不同利益集团为影响政策而相互竞技的场所,经典马克思主义则视国家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对于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论者来说,国家这个概念甚至被抛弃了,而代之以“系统”。在这里,国家都没有自主的地位,社会团体是主角。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主义者(statists)不赞成社会经济条件决定国家性质的论点,转而寻求韦伯对国家的认知传统,提倡“把国家找回来”。国家主义者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坚持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把国家找回来,但是又不把社会踢开。以个体为中心的理性选择主义者注重对个体的行为及其与他人互动的结果进行分析。莱维(Margret Levi)直截了当地说,理性选择理论就是要把“人”带回国家分析之中,因为“国家”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关键的决策是由具体的人或者统治者而非国家本身做出的。① 米格代尔独树一帜,发展出一种被称之为“社会中的国家(state-in-society)”的研究途径。在他看来,国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复合体,在观念层面,国家是可以清晰界定的、高度统一的行为体,比如,外交辞令中“中国对日本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提出严正抗议”,中国和日本就被当作一个拟人化的单一行为体;在实践层面,国家其实是碎片化的,不构成一个统一行为体,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的国家机构与国际国内社会发生联系,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没有清晰的边界。②因而,国家和社会都应该分解,碎片化的国家与分殊化的社会相互改变和相互构成。 “社会中的国家”这一理论路径告诉我们,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特别需要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如何超越社会又嵌入社会?社会如何参与国家建设又对国家权力进行制衡?国家社会平衡对国家治理有何意义?下文将讨论这些问题。 二、国家对社会的超越和渗透 作为单一行为体的国家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实践中的国家是碎片化的,与社会中的团体和个人犬牙交错。因此,国家治理中的国家建设必须在个体层次上超越关系和人情,在团体层次上超越社会利益集团,在相对独立基础上又要有效渗透社会。 (一)理性化:对关系和人情的超越 从制度组织上看,官僚体制(或科层制度)的健全是国家建设的核心部分。在韦伯那里,官僚体制不仅是特定的组织形态,而且是法理型权威类型的支配方式的理想类型,其合法性基础在于一个特意制定的理性规则体系。③官僚制严格遵循理性精神,组织结构等级分明、分工明确、官员行事受到规章制度约束、官员职业生涯有正式规则,其运作体现出非人格化的稳定和高效。官僚体制在管理上不无弊病,新公共管理运动呼吁“摒弃官僚制”以再造政府。这种超越官僚制的企图只是在组织层次上看到其不足,然而在国家治理层次上,官僚制的理性精神依然是国家建设的内核,不可抛弃。 理性精神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超越关系和人情,做到非人格化运作。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层次社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亲戚关系的超越和国家机构非人格化。在最初的家庭和族团层次,人类祖先的生活(如结婚、敬拜、分享猎物等)受到周遭亲戚的制约,他们体验的是“表亲的专横”。④在部落社会,亲戚关系和私人的恩庇—侍从关系决定了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不论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如社会契约、灌溉、人口压力、暴力战争等),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一定地域范围内暴力的集中和垄断,从亲戚关系过渡到非人格化的国家机构是国家建构的题中之意。 中国是国家建设的先驱和成功范例,有着悠久的强国家传统。东周战争的残酷性迫使各国寻求变革,以理性精神强国自保。亲戚关系这时成为了强国的障碍,商鞅变法就是剪除老旧贵族势力阻碍的大变革。按照福山的说法,西汉开国一百年后,周朝封建主义的残余变得无权无势,开科取士,独尊儒术,使得当时的中国政府几乎符合现代官僚机构的全部特征。在抑制亲戚关系对国家建设的损害方面,起源于9世纪哈里发帝国阿巴斯王朝的军事奴隶制与中国的科举制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后继的埃及马穆鲁克苏丹国和奥斯曼帝国继承和发展了军事奴隶制。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每隔四年,近三千名富有潜力的十二岁至二十岁的男子被挑选出来强行带走,与父母永远分离。他们中最优秀的一群会在伊斯坦布尔接受伊斯兰世界最好的培训,为充任帝国高级官员做准备,极少数奴隶军人担任将军、总督甚至大维齐尔(Grand Vizier,即政府首相)。多数军事奴隶被迫终生保持单身,即使有子嗣,其职位和财富也不可传承。这种类似于柏拉图倡导的护国者培训计划虽然在伦理上难以接受,但成为了抑制亲戚关系的有效机制,铸就了帝国的强大。 国家建设的理性化在世界各国并非一帆风顺和均衡一致。比如,与中国相反,印度的国家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虚弱地位。印度社会关系对国家建构的阻碍主要体现在瓦尔纳(varnas,阶层)制度和种姓制度。福山认为,印度国家建设的阻碍在于宗教,印度在公元前600年走上了一条大弯路,没有经历漫长的战争,以开发现代非人格化的集权国家,权力没有集中于国王,而在界限分明的祭祀阶层和武士阶层之间平分。强国家在中国被视为理所当然,然而,时至今日,第三世界不少国家依然没有完成国家建构,“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无力的国家”(powerless state)和“无国家社会”(stateless society)的例子屡见不鲜。 家族政府复辟带来的政治衰退也不乏其例。中国历史上的外戚和宦官专权以及门阀政治都导致了王朝的衰败,亲戚关系再次成为权力、地位和财富分配的主要途径。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伦理的差序格局依然是国家建设中理性精神的反作用力。亲戚关系和家族制渗入埃及马穆鲁克制度,苏丹国走向衰退。从17世纪开始,家族制和世袭原则重新抬头,奥斯曼帝国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历史兴替,可为镜鉴。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要推进国家的理性化建设,超越亲戚和人情关系。 (二)自主性:对社会团体的超越 国家能力意味着国家执行政策的能力,尤其是面对社会集团的强力反对以及在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执行国家政策的能力。如果国家被社会团体所俘获,丧失自主性,那就没有国家能力可言。 国家被利益集团劫持的案例并不少见。米格代尔颠覆了国家主义者对国家自主性的理论预设,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并非高度自主或无所不能,在这些地方,国家和社会在争夺社会控制权,强大的社会(包括家庭、宗族、企业、部落、政党和庇护组织等)可以成功抵制国家权力的渗透。⑤布鲁金斯学会李成认为,中国呈现出“弱政府、强利益集团”的态势,各地区利益、各官僚机构、地方政府、军队、国有企业、日益商业化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都有自己的利益,都对政府有强大的影响力。姚洋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伟大的经济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有一个“中性政府”,没有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然而,国家自主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姚洋注意到,“中性政府的基础在丧失”。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如果完全超脱于社会的控制,则成为绝对主义国家。完全超脱的代价是国家不能取得社会的合作,国家目标的实现只能靠强制,这是一种不能长久维持的国家能力。较好的状态是国家对于社会的嵌入型自主性,国家既独立自主,又有效渗透社会。 (三)嵌入性:国家对社会的渗透 国家持续的自主性和有效的权力渗透离不开与社会的合作。埃文斯通过对产业转型的研究,认为国家能力的最重要源头就是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嵌入型自主性。⑥曼恩区分了专制性权力与建制性权力,专制性权力是国家利用强制手段实现目标的能力,而建制性权力是指国家通过稳定的沟通渠道以及与社会合作来实现目标的一种能力。⑦可以说,专制性权力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建制性权力是国家嵌入于社会的权力。 国家可以培植和依靠社会网络来贯彻国家意志。杜赞奇在研究20世纪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发现国家权力渗透乡村需要依靠非正式的乡村社会网络。晚清和国民党政府为了取得对乡村的控制权,遭到了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抵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需要依靠这些网络,否则权力就无法有效下乡。⑧舒绣文(Vivienne Shue)对国家权力触角在乡村的延伸做出了一个反常识的判断,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并没有有效渗透到农村,类似于帝国时代乡绅阶层的地方官员是自利的,保护着本土的利益,构筑了蜂窝状的保护层,这一保护层的瓦解应该归功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市场化改革才使得国家权力能更加有效地渗透进乡村社会。⑨然而,杜赞奇和舒绣文都夸大了地方社会网络和地方官绅对国家权力渗透的敌意和负面作用,事实上,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社会网络来协助治理,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当今中国,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单位体制的逐步瓦解和乡村传统社会网络的溃败,国家正在丧失社会网络这一重要的合作对象,治理的责任全部落在了国家身上。社会建设之所以成为重要课题,是因为社会力量不仅可以协助国家贯彻意志,而且可以参与国家治理和制衡国家权力。 三、社会对国家的参与和制衡 国家与社会相互构成和相互改变,国家治理中的国家建设自然不能忽略社会建设对国家建设的意义。社会既可以参与国家治理,也可以制衡国家权力。 首先,社会可以通过法治和问责制两种制度安排对国家权力进行制衡。如果单方面强化国家权力,缺乏对权力的制衡和对人民负责的追求,国家这个“利维坦”就真的成了令人恐惧的海怪。国家建设就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和行使,为社会制定游戏规则,在一定地域内垄断暴力;法治则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问责制意味着国家建设的目标是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福利。政治精英不受法律约束,司法体系丧失权威意味着政治衰败,民主化进程滞后、民众有效参与不足、政府信息不透明以及公共利益被私人利益侵蚀等都是政治衰败的表现。在这里,政治衰败表现为国家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公器私用,不受约束。 中国并没有法治传统,战国时期中国哲学上的突破追求内在的超越,很少有外在的超越,中国人没有用超验的宗教和自然法来遏制王权。中国人驯化王权的机制是儒家思想的教化,要求皇帝做道德表率,以德配天,官僚权力发展出各种制度来约束皇权(如言官制度),百姓以帝王的政绩来提供合法性支持。但是,这种对国家权力制衡的传统并不能带来法治。因此,如何有意识地培育和支持社会力量,探索实现法治的现代途径,是国家建设的重要课题。在问责制建设方面,国家统治精英完全可以主动培育和利用社会力量来驯化和监督官僚体系。在碎片化的国家机器中,底层政府和官员与社会力量接触最多最广,最易受到社会力量的制衡,中国历史上的“三明治”治理结构依然值得借鉴,即上层统治者与底层民众合力监督中间层的官僚体制。 其次,国家与社会分享治理权力可以使得国家权力更加巩固、国家治理水平更高。国家治理的一个辩证法就是国家权力因为分享而得到增强。社会参与国家治理,既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前文提到,社会团体和个人总是在与国家争夺社会控制权,这是主动的一面。被动的一面是指,国家可以有意识地赋予社会更多的治理权限,以制度化的方式征询民意和集中民智。当今世界,技术变革迅猛发展,全球化持续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与工业化时代大大不同,社会动员调动了更多的政治参与者,这些发展对政治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制度创新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变迁就会导致政治衰败。在社会通过竞争性选举参与政治不发达的情况下,有韧性的政治制度可以主动通过咨询民意来克服政治衰败。比如,有学者认为,民意调查就可以成为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有效手段,科学的民调可以准确反映民意,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和评价权,在当前的政治大背景下,民调是“用嘴投票”,是最可行的政治参与方式。⑩民调与群众路线一样,都是国家主动让社会参政的治国策略。 国家治理涉及谁来治理和如何治理两个基本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离不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国家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主体,国家建设必须放在社会中去讨论。国家与社会的界线并不分明,从横向和纵向分解开来的国家机器“浸泡”在社会之中,国家与社会相互构成和相互改变。因此,一方面,国家建设必须超越社会中关系、人情和利益集团的束缚,同时又要构建有效渗透社会的机制;另一方面,国家建设不能被动进行,被社会逼着或拖着走。政治精英应该着眼长远,发挥国家能动性,主动培植社会力量以推动法治和问责制,从而制衡国家权力,积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学会与社会分享权力、合作共治。 ①Margret Levi,"The State of the Study of the State",In Political Science:State of the Discipline,edited by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Milner,New York W.W.Norton; Washington,D.C.: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2002,pp.33-55. ②Joel S.Migdal,State in Society: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③周雪光:《国家治理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 ④[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3页。 ⑤Joel S.Migdal,Strong Society and Weak States:State-Society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⑥Peter B.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⑦Michael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Mechanisms,and Results",In States in History,edited by John A.Hall,Cambridge(Mass.)and Oxford:Blackwell,1986,pp.109-136. ⑧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⑨Vivienne 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⑩胡伟:《民调可构成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手段》,《文汇报》2014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