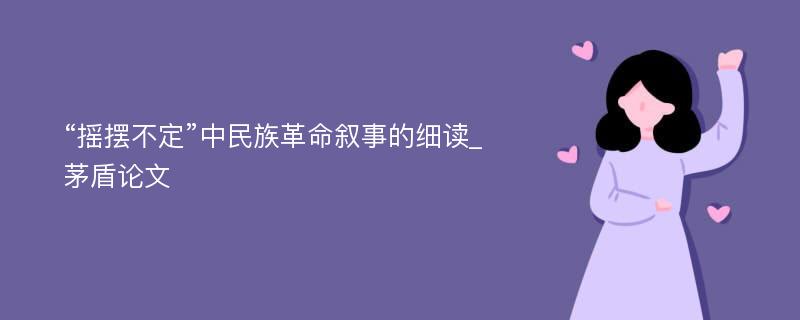
《动摇》中的国民革命叙事之细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民革命时期,茅盾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接触了大量反映湖北各地革命状况的新闻稿。茅盾《动摇》的创作即取材于这些新闻稿。《动摇》描写的是湖北某县城1927年1月至5月国民革命中的复杂局势,期间的混乱、矛盾、荒唐、残酷是匪夷所思的。《动摇》刚发表时,遭到了一些人的误解和非难。茅盾说道:“在对于湖北那时的政治情形不很熟悉的人自然是茫然不知所云的,尤其是假使不明白《动摇》中的小县城是哪一个县,那就更不会弄明白。”①张立国、孙中田在《论〈动摇〉的历史真实》②一文中认为,《动摇》所写县城的原型是鄂西地区的钟祥县。鄂西地区是1927年年初由北伐军从土匪和乱军中解放出来的。北伐军到来之前,鄂西地区兵匪横行,民不聊生。被北伐军解放的鄂西,工农革命蓬勃发展,成立了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店员工会、商民协会等。但被解放的鄂西一直处于立足未稳的状态,反动势力猖獗。夏斗寅的独立十四师即是一大隐患。该师驻扎在鄂西与四川交界的宜昌地区,目的是防范四川军阀杨森东下。但1927年5月14日,夏斗寅按照蒋介石的反革命意旨背叛了武汉政府。他勾结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残酷屠杀工农革命群众。茅盾的《动摇》即以上述史实作为背景。
茅盾又曾说道:“《动摇》是经过冷静的思索,比较有计划写的。是要借写武汉政府下湖北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利用县城的小场面,由小见大。”③笔者在查阅了大量关于武汉国民革命的历史资料后认为,《动摇》确实是由小见大,反映了当时国民革命中的一些典型现实、典型现象。《动摇》是茅盾《蚀》三部曲中最成功、也最复杂的一部,广泛而深刻地涉及到当时混乱而复杂的革命现实。倘不考察当时武汉国民革命的现实,不联系历史资料,很难获得对《动摇》精准的解读。鉴于此,本文将联系史料,对《动摇》中重点写到的店员风波、解放婢妾运动,重点刻画的革命动摇者方罗兰做分析,力求获得对小说翔实、有深度的解读,并探询茅盾在小说中体现的并不明朗的思想立场与倾向。
一 矛盾胶着的店员风波
国民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以罢工和政治斗争的形式援助北伐军。北伐军所到之处,工人阶级也获得了应有的解放和权利。据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1926年10月以后,武汉地区爆发罢工300余次,参加者数十万人。湖北省总工会会同国民党省党部、总商会等组成湖北省解决劳资问题临时委员会,与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等一起,共同调解了110起劳资纠纷。结果,废除了资本家随意打骂、开除工人的权力;每日工作时间减少到8至10小时;每人平均月工资增加5元,部分人增长一倍左右。④《动摇》描写的是湖北某一刚被北伐军解放的小县城,立足未稳,百废待兴。小说写到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店员风波。深受剥削压迫的店员,此时有店员工会助阵,向店东们提出了改善自身待遇的三大要求。但店东拒不接受店员要求,双方处于尖锐的矛盾对立中。实际上,国民革命时期,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是很有限的,武汉店员总工会是武汉总工会属下最大且异常活跃的工会组织。对于店员与店东的矛盾,小说中县党部也莫衷一是,难做决断。加之反动派的造谣与破坏,矛盾不断升级,处于胶着状态。店员的要求是否存在 “左”的倾向?该县城的店员风波何故如此棘手?最后的解决是否得当?茅盾对此又持什么态度?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对小说中的店员风波作分析。
店员向店东们提出的三大要求是:(1)加薪,至多百分之五十,至少百分之二十;(2)不准辞歇员工;(3)店东不得借故停业。店东们认为第一、二款尚可接受,第三款则万难承认,理由是商人应有经营自由权。店员工会则坚持第三款,认为凡想停业的店东大都受土豪劣绅的勾结,要使店员失业,并且要以停业来制造商业上的恐慌,扰乱治安。店员与店东的说法各有道理,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县党部对此也意见分歧,难做决断。县党部商民协会会长方罗兰就无法确定自己究竟该持什么立场。他见到店员时,慷慨激昂地说了许多支持店员的话,这些话是真诚的。当店东们向他请愿诉苦时,他又真心地对店东表示同情。店东与店员的矛盾实际上是在不断激化,加上土豪劣绅从中煽动、破坏,局势变得十分危急和混乱。店东们有悄悄转移货物之嫌,童子团则监视各商店。反动势力散布谣言,殴打革命群众。纠察队则带枪出巡,农民协会派农民自卫军进驻县城。恐怖的气氛充满在这县城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该县城的店员风波何故如此难以解决?省特派员史俊宣布该县店员风波的解决按省里例行的办法时,县党部陈中所说的一席话,触到了问题的实质。陈中讲到了土豪劣绅与店东们的联络,并说道:“敝县的土豪本就很有势力,能号召千把人。他们新近收罗了几百打手,专和党部中人及民众团体为难。刚才史同志说过省里的办法,自然应当遵照,但省里有大军镇压,办事容易,敝县情形,似乎不同。如果操之过急,激成了巨变,那时反倒不容易收拾了。”⑤没有强悍的革命力量做保障,行政人员就不可能有解决问题的铁腕。店员的要求不管是否合理,既然触动了店东的利益,就不会轻易实现。
现在需要辨明的一个问题是:店员们的要求是否存在“左”的倾向。在史学界,关于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工人运动是否存在“左”倾错误,不同学者有不尽相同的看法。刘继增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有一种严重的“左”倾错误:“就是不断提出使企业和商店无法承担的要求”;“无限制地游行集会,政治和经济的罢工,使生产不断下降”;“当时工会还自动减缩工作时间,有的名义上是工作八小时或十小时以上,而实际上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再一种表现,就是在经济上对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侵犯”。⑥曾宪林则认为,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的主流是好的,确实出现过“左”的错误,但也有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在发展变化的。“左”倾错误主要存在于1926年冬和1927年初。1927年1月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刘少奇等已经采取措施,整顿工会组织,严肃工会纪律,逐步纠正“左”的错误。1927年4月以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不断地发展膨胀,以至到最后断送了革命。⑦
笔者认为,该县城的店员风波或许不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但有“左”倾之嫌,至少省特派员史俊到达该县城后,对于店员风波的处理是“左”倾的。关于如何领导武汉工人的罢工斗争,当时的中共湖北区委采取的是积极领导和区别对待的政策,即由总工会发布一个湖北工人的总要求,各工会再按照客观情况,提出具体要求,以指导工人斗争。史俊到达该县城后,并不多了解实际情况,只依据省里对于店员问题的办法来处理:一加薪,二不得辞歇店员,三制止店东用歇业的手段来破坏市面。这实际上是满足了店员的三大要求。最终所造成的结果是:“店东们的抵抗手段,由积极而变为消极;他们暗中把本钱陆续收起来,就连人也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的铺面,由店员工会接收了去。”⑧这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史俊在该县城处理店员风波时,所做的一个尤其错误的事情是提拔了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劣绅胡国光。
茅盾对于《动摇》的写作,采用的是客观冷静的叙事手法,对于许多问题,并未显豁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茅盾对于土豪劣绅和反对派当然是持抨击、诛伐态度。经推敲,笔者认为,茅盾对于店员的行动,并非一味支持,对于店东,批评的态度也并不明了。茅盾在1927年5月20日和5月21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上分别发表有题为《巩固农工群众与工商业者的革命同盟》和《工商业者工农群众的革命同盟与民主政权》的政论。这两篇政论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明了茅盾在《动摇》中对店员风波的态度。在《巩固农工群众与工商业者的革命同盟》中,茅盾强调了小有资产的工商业者亦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亦有革命的要求,与工农群众是同盟的关系,都是革命依靠的对象。茅盾又写道:“但是因为工农运动的突飞进展之故,使工商业者疑虑不安,因而自惑国民革命这伟大事业中,仍没有他们的份儿,甚至形成工农阶级与工商业者中间的裂痕,影响及于工农阶级与工商业者在革命战线内的同盟,这也是事实,不容讳言的。我们认为此种现象,一方面由于工农运动之不免稍带幼稚病,而一方面亦由于我们没有十分努力对工商业者解释国民革命之主要力量及在工农阶级与工商业者之同盟,以致工商业者有此误会疑虑。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事。”这里谈到的是,带有幼稚病的工农运动对工商业者利益造成的损害及政策宣传的不到位,使工商业者对革命存有误会和顾虑,并没有与工农一起成为革命的同盟。工农阶级与工商业者之间甚至存在裂痕。上述状况对革命是不利的,是令人遗憾的。
由上述文章可以看出,茅盾的立场,或者说他所代表的调整了政策的中共的立场——《汉口民国日报》是中共执掌实权的报纸,是将工农群众与工商业者看作革命同盟的,而想极力避免两者成为相互斗争的敌对阶级。因此,茅盾是不赞成店员对于店东的激进做法的。当然,他也非常反对店东与反动派勾结,破坏革命。当革命正在进行中,局面往往是复杂而难以控制的,尤其是当有反动派掺杂其中,有力的中央政权尚未建立。小说中所描写的店员风波正是如此,混乱成为无法避免的结局。它成为革命中的一个标本和教训留在了文本中。茅盾写作《动摇》正有展示国民革命中的不良现象及总结经验教训的用意。
二 沦为丑闻的解放婢妾运动
国民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成立后,至1927年3月上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等19个省、特别区、特别市陆续成立了妇女部,妇女运动逐渐展开。1927年3月8日,湖北全省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同日,武汉各界20万人在汉口举行纪念会。会议提出湖北妇女总要求13项,要求国民政府制定男女平等法律,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从严禁止买卖人口、蓄婢纳妾,废除娼妓,严令各地官吏禁止缠足等。对于国民革命时期蓬勃开展的妇女解放运动,相关现代史著作和文学作品基本都持高度褒扬态度。《动摇》中写到的重大事件,在店员风波之后,便是该县的妇女解放运动,或曰解放婢妾运动。但茅盾的用意决不是表彰该运动。实际上,该县的所谓解放婢妾,在“左”倾幼稚思想与反动分子的捣乱破坏下,上演的是一幕幕荒唐而可鄙的闹剧,沦为远播四方的丑闻。该如何认识茅盾《动摇》中这匪夷所思的描写呢?这里对此做一分析。
《动摇》首先写到的是南乡农民协会的“分妻”行动:把寡妇、婢女、尼姑通过抽签的方式,分给没有老婆的光棍。当农协正在调查农民的土地时,土豪劣绅就放出“共产”的谣言来攻击农协。后来,土豪劣绅又放出“公妻”的谣言:“男的抽去当兵,女的拿来出公”。农民竟然被这些谣言蒙骗了,纷纷要退出农协。县农协派特派员王卓凡来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王卓凡不但没有澄清已有之误解,申明农民运动之政策与共产主义之含义,反而在农民运动的口号“耕者有其田”之后,添加了“多者分其妻”。南乡农协就是在这种“左”倾幼稚思想下组织了“分妻”大会。土豪黄老虎的小老婆、一个将近30岁的寡妇、前任乡董的一个婢女和两个尼姑是被分的对象。由于男多女少,抽签进行。男多女少引起叫骂和争论,对抽签结果不满意又引起对骂和殴斗。由于农协成员在分妻大会现场抓到了进行捣乱的宋庄夫权会的成员,而宋庄夫权会又很和南乡农协作对,分妻大会的目标就转移为对宋庄夫权会的扫荡。当宋庄夫权会的俘虏被农协押着游行示众时,许多妇女加入了进去,呼喊的口号在她们口中变成了“拥护野男人!打倒封建老公!”由此可见,“分妻”大会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的胡闹,也是对妇女尊严的践踏。
但更荒唐、恶劣的事情还在后面。南乡农协的“公妻”运动四面传播,已造成恶劣影响,理应及时给予制止和纠正。但妇女部的孙舞阳在“三八”妇女节的大会上,竟称其是“妇女觉醒的春雷”,“婢妾解放的先驱”。她还惋惜城里的妇女运动反而无声无臭,有落后的现象。应当说,孙舞阳对于妇女解放的认识是激进而“左”倾的。她所引导的舆论也是错误的,使得“公妻”运动蔓延到县城中来。胡国光见风使舵,他“革命性”的提案就诞生了:主张一切婢妾、孀妇、尼姑,都收为公有,由公家发配。胡国光的真实用意是想趁此浑水摸鱼,择肥而噬,满足自己荒淫的欲望。胡国光的提案虽并未完全通过,但“解放妇女保管所”却是成立了。该所的原意是,已经解放的婢妾尼姑,先由公家收容之,给以相当的教育和谋生的技能,然后听凭她们自愿去生活。但在胡国光之流的胡作非为下,“解放妇女保管所”完全成了淫妇保管所:几乎每个妇女夜晚都有男子去睡觉。这一事件轰传远近,严重败坏了革命的声誉。
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与叶紫的《星》,也写到了国民革命中的妇女运动,但笔法不同,侧重的是一种正面的赞扬。三位作家的描写之所以出现大的差异,我认为,首先与他们接触到的素材不同有关,其次,作家的主观因素也在起一定作用。蒋光慈在妇女运动描写中显示的乐观与明朗,与他对革命的乐观有关。叶紫在家乡湖南亲身经历了大革命的高潮与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他的多位至亲都是革命与妇女运动的参与者、领导者,并在反动派的屠杀中牺牲了,这使他写出了《星》中梅春姐的命运曲折。茅盾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幻灭心境里,则是比较注意揭示国民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并寻找失败的原因。而茅盾在《汉口民国日报》任主编时,所接触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材料,大约也正有如《动摇》中所描写的情况。
其实,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发生有轰动一时、耸人听闻的裸女游行事件。⑨1927年“三八”妇女节的盛大游行活动中,名妓金雅玉等受蒙骗、教唆,赤身裸体冲进游行队伍以示“革命”和“解放”。此后图谋破坏革命的反动势力和地痞流氓,便阴谋策划在“五一”节这一天发动“千名妇女裸体大游行”,并声称是由国民政府组织的。他们打着号召妇女解放的旗号,加以威胁利诱,几天时间就在武汉建立了几十个秘密的“妇女协会”。不久,《市民日报》也披露了这一消息。武汉三镇顿时满城风雨,纷纷传言说“五一”节这一天,湖北省和武汉市妇协将举行妇女裸体大游行,中央军校的女生队将带头裸体游行,国民政府实行共产共妻等。最终这一阴谋事件被彻查,妇女运动的方针政策也做了调整。
该事件发生时,茅盾也正身在武汉,且任大型日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编。他对这件事应该是十分了然的。比较《动摇》对解放婢妾运动的描写与此裸女游行事件,会发现两者在性质上极其相似,都反映了妇女运动中的“左”倾,反映了反动派从中阴谋捣乱造成恶劣影响以破坏革命声誉。由此可见,茅盾《动摇》中的相关描写是实有所据的。此外,茅盾在短篇小说《泥泞》中也写到了国民革命中乡村的所谓“共产共妻”事件。应当说,此类事件并不是事出偶然的个例。它引起了茅盾的关注和忧虑,形之于笔端,成为对现象的展示和教训的警觉。
三 革命动摇者方罗兰
投机革命者胡国光形象的成功塑造,是《动摇》的亮点之一。但本文着重要分析的是另一更为复杂的典型形象:革命动摇者方罗兰。关于《动摇》的写作,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说道:“《动摇》所描写的就是动摇,革命剧烈时从事革命工作者的动摇。”在这篇文章中,茅盾又说道:“《动摇》的时代正表现着中国革命史上最严重的一期,革命观念革命政策之动摇,——由左倾以至发生左稚病,由救济左稚病以至右倾思想的渐抬头,终于为大反动。”⑩茅盾欲借这小说所表现的“动摇”,就体现在小说主人公方罗兰身上。方罗兰被汹涌的时代风浪卷进了革命的漩涡,他虽身为革命工作者,革命中的种种现象,却使他迷茫。在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较量中,他也没有始终坚决地站在革命的一边,而是动摇不定。在大反动到来之时,他最终是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动摇”是那一时代的一种现象,方罗兰这种人物在当时也很具代表性。该如何认识方罗兰的“动摇”呢?茅盾对于他的“动摇”又是什么态度?本文将对此做分析。
方罗兰是该县县党部要人、商民部长,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新思潮,大学毕业已六年,32岁。在同做革命工作的同事中,他很有威望,性格沉稳,但另一大特点是优柔寡断。他的这种优柔寡断与动摇不定,既表现在对于革命上,也表现在对于爱情上。小说花了不少笔墨描写他在爱情上动摇于妻子陆梅丽与浪漫的革命女性孙舞阳之间。据茅盾所讲,这些描写并非闲文,是有衬托方罗兰性格及在政治态度上动摇之意。关于方罗兰对于革命的动摇,小说的描写主要有三处。首先是胡国光贿选商民委员而被指控是本县有名劣绅一案,方罗兰并未彻查。方罗兰何故并未彻查呢?由陆慕游带胡国光到方罗兰家里说情一段可以看出,方罗兰不但对胡国光素有所闻,而且对他的一贯行径很是知晓。他是极为反感这个狡诈的尖嘴猴腮的老狐狸的。但他何故不将其作为劣绅果断处理呢?原由只能解释为方罗兰不愿得罪人,且他与胡国光又是同县乡里。其实,这也正是方罗兰的一贯作风。他总想两面讨好,既不得罪革命群众,也不得罪反动势力。他这种姑息养奸的做法,最终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后果。其次是在店员风波中,面对店员与店东的冲突,他迷惘而矛盾,不知该站在怎样的位置。正如茅盾所说:“他和太太同样的认不清这时代的性质,然而他现充着党部里的要人,他不能不对付着过去,于是他思想行动显得很动摇了。”(11)
再者是叛军兵临城下,流氓攻打妇女协会与县党部,制造了残酷的暴力事件时,面对流血与混乱,他对革命产生了严重动摇。小说描写他的内心独白:“——正月来的账,要打总的算一算呢!你们剥夺了别人的生存,掀动了人间的仇恨,现在正是自食其报呀!你们逼得人家走投无路,不得不下死劲来反抗你们,你忘记了困兽犹斗么?你们把土豪劣绅四个字造成了无数新的敌人;你们赶走了旧式的土豪,却代以新式的插革命旗的地痞;你们要自由,结果仍得了专制。所谓更严厉的镇压,即使成功,亦不过你自己造成了你所不能驾驭的另一方面的专制。告诉你罢,要宽大,要中和!惟有宽大中和,才能消弭那可怕的仇杀。现在枪毙了五六个人,中什么用呢?这反是引到更厉害的仇杀的桥梁呢!”(12)在这里,方罗兰已完全把革命与工农运动给否定了,并几乎是站在反动势力的立场上发表言论。该如何理解方罗兰的这段内心独白呢?它透露了茅盾的某种心声?
对这段话的理解其实存在分歧。但准确而可靠地理解这段话极其重要,因为这不但关涉到对方罗兰这一人物的评价,还关涉到对茅盾对方罗兰之态度、对革命之看法的认识。大多数学者认为上述方罗兰内心独白中对革命的认识是错误的,他由动摇而至反动,是茅盾所要批评的对象。蓝棣之等一些学者的观点与此不尽相同。蓝棣之在论文《论茅盾〈蚀〉三部曲的连贯性》中写道:“作者茅盾所叙述的他笔下人物方罗兰的这番话,值得仔细研究。作者不像是在批判方罗兰这些错误观点,相反倒觉得给予了好些理解和认同。……一个革命的历史学家要严格按照革命的意识形态来正确地叙述历史事件,而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不妨允许他可以在文学作品里描述他在历史过程中的体验和观感,允许他有意无意地在文本里渗入一些困惑和疑惑,允许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13)蓝棣之的意思是说,茅盾并非批评方罗兰,而是给予了理解和同情。我认为,这种理解与茅盾写作的本意有偏离。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道:《动摇》“是要写大革命时期一大部分人对革命的心理状态,他们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失败之间。《动摇》里的重要人物,国民党‘左派’方罗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动摇的结果是思想上的矛盾、迷惘乃至错乱。”(14)在这段话里,茅盾明确指出方罗兰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结合小说文本,如果说小说前面部分表现的是他的“矛盾”与“迷惘”,那么这里所表现的就是他的“错乱”了。茅盾既然将方罗兰上述对于革命的认识称为“错乱”,就不可能对方罗兰的此种认识持理解和认同态度,方罗兰的“困惑和疑惑”也就不应是茅盾的。
茅盾还曾说道,《动摇》 “是要借写武汉政府下湖北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那么,茅盾在小说中重点描写方罗兰这样一个国民党左派人物的动摇就不是偶然的。国民党左派是支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但国民党左派中的许多人物对于革命的态度是动摇不定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左派的代表是汪精卫。到了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就开始公开反共,向蒋介石妥协投降了。《动摇》刻画方罗兰这样一个人物对于革命的动摇,实际上是在刻画国民党左派人士对于革命的动摇及走向右倾。茅盾的态度只能是批评或客观描写。茅盾不可能对方罗兰的上述动摇心理持理解、认同态度。
从文中可看出,方罗兰的最终动摇与工农革命中的过火行为很有关系。国民党左派和中派支持农民减租斗争,赞成以和平的方式实行孙中山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一般不赞成对地主进行人身斗争,更不赞成以斗争方式夺取地主的土地。随着农民运动的激烈化和土地革命的发展,国民党中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右派一边,国民革命阵营的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方罗兰这个国民党左派对革命的动摇与右倾化也正有上述背景。
但茅盾是否也认为工农运动过火并进而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呢?茅盾在发表于1927年6月14日的《扑灭本省各属的白色恐怖》中写道:“我们须知湖北各属土豪劣绅土匪的大联合的蠢动不是偶发的事件,也不是‘农民运动过火’所起的反响,如反宣传者所云云,而确是反动派摇撼武汉的大阴谋中的一部。其存心是在动摇北伐大军的后方。……扑灭各属的白色恐怖,便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刻不容缓的工作!”(15)茅盾在发表于1927年6月18日的《肃清各县的土豪劣绅》中又写道:“请翻开本报的本省新闻来看罢,所有各县消息全是土豪劣绅捣毁党部,残杀民众的消息。……或者有人把此等土豪劣绅的反攻认为农民运动过火或太幼稚的反响,以为只要将农民运动放缓和些便可以太平无事;这个意见,不能不说是很错误的。”(16)这两段话正是茅盾对方罗兰对革命错误认识的辩驳,茅盾不认为土豪劣绅的反攻是由农民运动的过火与幼稚引起,也不认为宽大、中和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秦弓在《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叙事》中认为,革命使得人的占有欲与复仇欲等原始欲望被调动起来,造成暴力与仇杀,是方罗兰动摇的原因。他写道:“然而,他对盲目的仇杀与新式专制的担心却并非毫无道理。人的占有欲与复仇欲等原始欲望被无节制地调动起来以后,其破坏力不可估量,如果任其宣泄泛滥,势必在打破旧的不平等之际,酿成新的人间悲剧。方罗兰并非放弃革命与暴力,而是对盲目的暴力表示忧虑,对专制的更迭表示怀疑。而这恰恰表明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精神。”(17)秦弓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认识方罗兰的动摇也是有启发性的。总之,方罗兰这一人物在当时很具代表性,茅盾对于这一人物的客观描写具有历史价值。
注释:
①⑩(11)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第183页,第184页;最初载于1928年10月18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
②张立国、孙中田:《论〈动摇〉的历史真实》,载《文学评论丛刊》第17辑,1983年7月。
③(1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391页,第391页。
④参见李新、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中华书局1996年2月版,第239页。
⑤⑧(12)茅盾:《蚀》,《茅盾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第220页,第246页。
⑥刘继增、毛磊、袁继成:《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载《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
⑦曾宪林:《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中“左”倾错误有关问题之商榷》,载《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3期。
⑨参见安广禄:《北伐时期武汉裸女游行风波》,载《文史天地》,2008年04期。
(13)蓝棣之:《论茅盾〈蚀〉三部曲的连贯性》,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15)茅盾:《扑灭本省各属的白色恐怖》,《茅盾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6~397页;最初载于1927年6月14日的《汉口民国日报》。
(16)茅盾《肃清各县的土豪劣绅》,《茅盾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1页;最初载于1927年6月18日的《汉口民国日报》。
(17)秦弓:《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叙事》,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