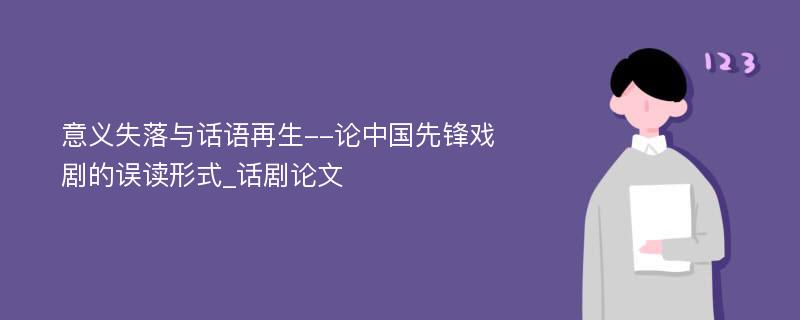
意义流失与话语再生——论中国前卫话剧的误读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卫论文,误读论文,话剧论文,中国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从接受美学角度而论,都是一次误读的过程,而所谓的外来文化传统,正是千百次误读的结果,而且,正如斯宾格勒所指出的:“我们赞美一种外来思想的各种原则愈热烈,我们实际上对于这种外来思想的性质的改变也愈根本。”(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153页。)都是创造性的叛逆, 存在着“前理解”与“历史性”的背景关系,都注入了各自个人与民族的文化指数,并由此进行了修正与重整,异质文化的本质内涵已经变奏,开始本土化了。
毫无疑问,中国话剧是外来的艺术类型,而且不是原产地欧美引进的,而是从日本这个亚洲国家中转而来的。这里面是否包含了二度误解的因素,暂且不去讨论,单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话剧从“苏联模式”中走了出来,大量西方的戏剧学说、观念与方法涌了进来,跨文化的戏剧交流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频繁过。这种交流,给中国话剧带来了阵痛,从观念、类型、结构、风格,以至于母题或原型,把西方戏剧一百年的诸多艺术成果,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演示了一遍,随此戏剧互文的误解与偏移现象,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频繁过,表现出一种焦虑的情怀,以及企图进行自我拯救的责任感。如果带着一种理性的心态,去解读这一种误读状况,也许能带来一种温馨而又凛冽的历史开放情怀,并以殉道的戏剧精神,在血淋淋的文化互斗中实现新的大戏剧乃至大文化的整合涅槃。
一
中国话剧曾经经历两次大的中西文化应战,而且都是自觉的,带有新启蒙主义色彩,但在美学态度上,二次却体现了迥异的文化选择,第一次所重视的写实主义精神,正是第二次所坚决抛弃的,已经转向更能表达现代人文灵魂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一些戏剧实践者随着国门初开,从长期封闭的戏剧生态中,开始把关注的目光移向陌生甚至有点神秘的欧美舞台,并以中国人特有的判断力得出结论,“当今世界上严肃戏剧的探索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都处于实验阶段。也就是说,从剧本到演出,从导演到演员都没有能够得出明确的结论和答案。这也许正是实验戏剧的魅力所在。而中国戏剧的实践无论从娱乐功能还是从教育功能上都需要赶上世界戏剧发展的潮流”,(注:孟京辉:《实验戏剧和我们的选择》《戏剧文学》1996年第11期。)正是这种对世界与中国戏剧形势的分析,产生了一种求新求异的强烈冲动,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用另一种眼光注视世界”,“使我们身上新鲜的东西从陈陈相因的桎梏和毫无才气的恶习中解放出来”,(注:孟京辉:《实验戏剧和我们的选择》《戏剧文学》1996年第11期。)并与西方戏剧实现对话,进行一种文化自赎,组织新的戏剧话语体系。这种求新求异,其中最便利也是最必然的就是到西方戏剧里去寻找灵感与依据。表现派戏剧和现代派戏剧以及后现代派戏剧,成为仿效的最直接与最频繁的艺术对象。
其实,中国六十年代即已有西方现代派理论与剧作的译介,但远没有七十年代末开始的这样蓬勃,欧美各种哲学、美学、戏剧思潮大量译传进来,西方文化英雄一个个象走马灯似的,成了中国文化界的精神教父,构成一种中心话语权威能力。在戏剧界,各种西方学说、流派,尤其是西方戏剧家的个性反叛与美学反动,确实给中国戏剧家的艺术人格产生冲击性乃至革命性的影响,并从中受到启迪,确立了新的艺术方向。正如上海话剧导演胡伟民所宣称的:采取“东张西望”的视角,实行“无法无天”的独创。正是由于这一种中西戏剧的碰撞与交流,引发了一场意义大于成果的“戏剧观念大讨论”,对中国保守的戏剧观念,进行了反省与检讨,并由此使中国前卫话剧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学术色彩,产生对理论的强烈依赖心理。应该说,新时期的中国前卫话剧,已经摆脱了中国话剧以前凭直觉的混沌阶段,而相对进入了一种艺术自觉阶段。这种对西方戏剧的皈依心理,主要从三个方向进入。
第一,舞台修辞语汇。首先,作为外在艺术形态,虽然没有触及到本体性的原则方面,而且具有改良性质,但对原来陈腐的传统形式,确实带有一定程度的偏激性,急迫地想与世界舞台语法接轨,使中国话剧舞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修辞改革浪潮,展现了一种崭新的戏剧语汇美感体验。对于中西戏剧而言,重要的不是对方是戏剧门类,而是一种非我,采取了否定的非我形式,由此,带来的艺术的陌生度与新鲜感,并把这一种快感移植到自我的戏剧身上,便成为最大的任务。中国前卫话剧空前地运作起了各种新颖独特的戏剧形式语法:面具、歌队、舞蹈、电影、哑剧、说唱、皮影、动画、体操、相扑、魔幻、杂技、傀儡、相声、技巧动作、节目主持人,还有各种引文技巧,这里也包含一些中国传统艺术手法,都走上了中国话剧的形式表现中心。林兆华导演的《罗慕路斯大帝》,让戏剧人物、演员、木偶艺人、木偶同台表演;高行健的《野人》出现了许多非陈述性语言:暗示,象征与假定,以及音乐性的语言:多声部的,和声的和对位的,按照乐名与曲式方式进行处理;林兆华导演的另一部戏《哈姆莱特》,当舞台上演到最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时,出现了三个哈姆莱特,这些都不仅是一种形式的选择,而且迫近了人文主题,带有一定内涵的深刻性质。
其次,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辞嬗变以后,中国话剧确实从单调而贫困的语汇困境中摆脱出来,又必然会运用这些语汇去表现更多的戏剧内容,其中最自然的就是对心灵的舞台拷问。西方现代戏剧一个重要的实质,就是描写人的内心分裂。对自我灵魂的抒情,就必然要把人物的心理世界放大,从中烛照出哲学意味与人生感悟。这种内向化的品格,从中国前卫话剧的几部开山之作,如《屋外有热流》、《绝对信号》,就已经显露出来,并呈现蔓延之势。回忆、梦魇与幻觉等心理时空,采用意识流、象征主义、表现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派舞台手法,成为内向化战略的重要语言体系。王晓鹰导演的新版《雷雨》,就有许多成功运用。当周朴园终于认出侍萍,此时,死一样寂静的舞台上,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周冲呼喊四凤的声音:“四凤……四凤……”。这若真若假的深情呼声,是对当年周朴园与侍萍美好恋情的一种呼唤,还是展示了一种轮回的宿命:现在的周冲,就是当年的周朴园。这种潜意识的外化,甚至不再是标点符号或短句式的象征,而是全局象征,舞台语汇发生策反,产生高度化与形而上的表意功能,大量采用内心外幻化的技术,与非理性和非逻辑的言语结构,成为中国前卫话剧与世界现代艺术精神激情拥抱的重要抒情形式。
再次,对心理描写的再度深化,必然要求作为物质载体的剧场空间的重新结构,这甚至成为舞台修辞改良最显著的视觉标志。镜框式舞台被伸出式舞台、弧形舞台、中心舞台、环形舞台与多平台、多表演区的剧场所替代,小剧场的演出形式也逐渐普及起来,并从残酷戏剧、贫困戏剧、行动戏剧、机遇戏剧等西方后现代戏剧舞台技法中受到借鉴,空间构造更加走向极致,成为修辞革新有力的物理意义上的支持与表达手法。
第二,戏剧本体哲学。如果说修辞美学还只是限于形式阶段,西方现代主义戏剧在中国的不断被译介与传播,必然会导致戏剧本体意义上的皈依,从“如何表现”转化为“表现什么”,这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戏剧主题语法相似,采用一种瓦解与颠覆的狂热姿态,主观感受高度放大变形,思想内容以激进与解构为文化时髦,以超越群体意识为立足点,自由嬉戏,众声喧哗,怀抱一种孤芳自赏式的精英感觉,与既定社会秩序采用疏离态度,拆解“权威”,亵渎“崇高”,与常规戏剧的讲故事、树英雄,布道说教不同,它只表现一种情绪,一种状态,甚至是一种歇斯底里的情感渲泄,表达一种受压抑与被扭曲的痛苦。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前卫话剧的这种话语表述,确实有点后工业社会艺术的味道,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对灵魂与精神的挤压,是社会人格一种不和谐的表现,由此产生异化带来的孤寂、隔膜、无聊乃至生命结构的分裂,表达了中国话剧对西方现代艺术精神的某种敏感性。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尚处于前工业社会阶段,城市化还是一种明日的欲望,还没有充分领略物质高度发达所带来的享受,便产生了物质状态对精神状态的挤压体验,大概是无病的呻吟,显得苍白做作。但是,这种对西方戏剧精神的借鉴,乃至直接搬演,对中国前卫话剧艺术人格的影响,确实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名噪一时的荒诞派戏剧,它在中国的大量译介与传播,对中国新时期实验话剧具有很强的渗透力量,《车站》、《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潘金莲》、《天才与疯子》等都从一种独特的人文阐释角度,以荒诞不经的形式,表现了一种形而上的抽象哲学理念,在激进与解构的外表下,主题因子呈现出对西方现代派戏剧的亲昵元素。
第三,前卫话剧类型。中国话剧自然是一种舶来品,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在她尚未充分民族化的无奈时,西方大量的前卫话剧类型却走马灯似地涌了进来。从某种意义而言,短短十几年时间,西方各种先锋戏剧类型,都已在中国舞台上或算作是舞台的场景上全部献演亮相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残酷戏剧、贫困戏剧、荒诞派、意识流、达达主义、装配戏剧、环境戏剧、行动戏剧、机遇戏剧、仪典戏剧等话剧类型都已在中国粉墨登场。就以中国普通民众较为陌生的“达达主义”为例,其代表人物马赛尔·杜桑曾于1917年把莫特工厂生产的瓷器小便池送到美国纽约独立沙龙,作为戏剧展出,其戏剧哲学核心就是否定一切传统和常规,取消一切人为的艺术,主张生活与艺术无界线,破坏就是创造,由此,联想到牟森的《关于〈彼岸〉的汉语语法讨论》、《与艾滋病有关》,以及孟京辉的《我爱×××》,似乎散发出同样的艺术气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杨青及其她的戏剧工作室,在北京饭店的“伊甸园酒吧”,上演机遇戏剧《爱在伊甸园》,每次剧情都根据演员和酒吧顾客的交往情形而定,而这种机遇戏剧,在欧美七十年代即已流行。还有环境戏剧,西方六、七十年代早有探索,并构成了相对稳定的理论,中国前卫话剧也逐渐开始体验这一种戏剧类型的演出美感,广州一家舞厅里演出的《爱情迪斯科》、哈尔滨一家夜总会演出的《人人都来夜总会》、上海的《屋里的猫头鹰》、北京的《情感操练》、《武器与人》,都把现实空间作为了戏剧的性格环境。“装配戏剧”曾在美国传播,新时期的中国话剧也开始涉及这一领域,演出了多部组合形态的“装配戏剧”,虽然影响不是很大,但却从诗意美学的角度,作了重新阐释。这种戏剧类型的引进与渗透,甚至影响到了演员训练方法,如牟森就实行美国现代舞以及印度瑜伽的办法,完全打破传统,十分强调身体语言的表现力。从某种意义而言,随着这些戏剧类型在中国的不断推介,前卫话剧在现代派风格上已逐渐与西方接轨,在气质上开始形成某种默契。
中国话剧在发现西方的同时,也对自身进行了调整与改革。以上三个方向,并不一定平行运作,而绝大部分确实是兼而有之,只是相对有所侧重而已,而且这种方向,到了后期也进行了分化与深化,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的阶段。
二
在中国前卫话剧的人格体验与修辞传达中,其实,早已可以感觉到似乎有一种温和的品质悄然出现,即用另一种语言讲述另一种故事,组织新的戏剧话语,而大多不象西方先锋戏剧那样,采取一种“暴力”的狂飙风格。在这里,东西方戏剧的气质,虽然有了某种默契,但隔阂仍然是天然存在的,各自把对方作为否定的形式,中国话剧企图嫁接与引进西方现代戏剧,并从中证实自我,但其实仍然是一种自言自语,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误读,表现了一种交流现象的冷酷性。
从某种意义而论,中国前卫话剧在艺术实验与革命的自觉程度与终极目标上,实践者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很大的差异性,乃至相互矛盾与消解。多数处于一种“盲从”状态,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必要的现代戏剧文化积累,匆忙上阵,或有朦胧的冲动性,或仅作为文化时髦,还来不及细细咀嚼,去粗存精,就一知半解地摇旗呐喊,玩票上场了,把整个西方现代先锋话剧演示了一个遍,但也仅仅是玩票,缺乏专业能力,终因底气不足与收纳功力弱化,而有点步履维艰了。即以直接搬演西方现代戏剧分析,中央戏剧学院的鸿鹄集团曾上演了《升降机》、《秃头歌女》、《深夜动物园》、《风景》、《黄与黑》、《等待戈多》、《蜘蛛女之吻》等西方实验剧目,但舞台实践者们对作品所传递出来的人文内涵,其实仅停留在朦胧感知的程度,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性解读与感性体验,对相应的舞台技术手段,也大多是貌合神离,并未合理准确体现。中国原创剧目,许多是对西方现代戏剧的“东施效颦”,体现出一种浮躁的心态,甚至显得有点造作。对西方后工业时期的异化情绪,也许只是在生活中有点感悟与领略,便匆忙在艺术文本中加以浓彩重墨地抒写。而实际上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度,最多只进入了前工业化时期,城市化还是远期的目标,摆脱贫困还是一个当务之急,这种物质高度发达后所带来的社会综合症,在中国确实是缺乏现实依据的,至少是不够典型的。它仅仅是西方哲学观念的演绎与陈述,没有现实人生的深切而独特的生命体悟,甚至是西方现代思潮的舞台教化,而变成了一种哲理宣泄。表面上似乎很深沉,有点张牙舞爪,但实际上人文抒情非常苍白。从接受美学角度来谈,提供给观众的文化信号也是有限的,甚至是错位的。因此,有的学者早已指出,“‘先锋话剧’在国内并不多见”,“近年国内有人陆续搞了先锋派的戏剧,但按国内的情况,真正符合先锋派两个特征(反传统、反商业化)的很少”。(注:转引自娄靖:《〈时装街〉与先锋话剧》《上海文化艺术报》1989年。)误读现象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戏剧实践界学术准备不够,只有了一些感性与初步的体验,便急于在舞台上发言,表现出对传统戏剧的否定或修正姿态,所名与所实存在相当的认识差距。
其实,中国前卫话剧对常规戏剧形态,仍只表现了有节制的反叛,真正走向极度巅覆的并不具有主流意义。与西方戏剧现代与后现代不同,中国经典意义的传统文化心理,会从结构、功能与价值的整体思维理念,组成一种本土特色的戏剧美学编码,从而对异己的艺术体系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对欧美先锋话剧语义,大多进行了改造,变成了中国式的母题与类型。虽然有着一种激情,在人文抒情上欲与西方完全取得一种默契,渴望得到一种现代感的满足,以及与白人世界的平等待遇,但一种民族的无意识,已经规范了误读的必然性。中国将接受西方现代与后现代戏剧的选择重点放在对话上,企图进行沟通,但同时无意识中实际上又误解了西方的对话精神。一种跨越种族与国度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在此背后隐藏着的民族精神底色,其实都有一种严重的自怜性倾向,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孤独的。经过多年文化传承,已经板结成了根深蒂固的一种恋母情怀,互相之间移植、传递,偏移的出现是一种前提性的现象。从语法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美学一直注重理性思维的引导,而对叙事的要求是自给自足,构成一个文本的自我意义体系,也架构了相对稳定性的接受阅读机制。中国前卫话剧对西方现代与后现代戏剧受文化界的动力艺术、波普艺术、新达达主义、装配艺术、欧普艺术等先锋流派的影响,所体现出来的倾慕“偶发事件”,以及任意环境中的多种艺术种类的“装配”快感,表现了一定的理智批判态度。除了牟森与他的“戏剧车间”演出的《关于〈彼岸〉的汉语语法讨论》、《与艾滋病有关》和《零档案》等少数几个剧目,大多数前卫话剧仍遵循中国传统叙事原则,而没有走到西方先锋戏剧“无情节”的极限冲动。人物抒写也是如此,也不完全是一种符号式的与抽象性的“非人物”倾向,非人化以及无人类逻辑的人的形而上的舞台梦呓,在中国前卫话剧似乎并非出现标准的范本,而大多仍企图在寓言或童话式的故事结构中,追求人物性格描写的生动性与复杂性。传统美学的惯性作用,与俯就现实的功利思维,对与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对话渴望,也许构成了一种矛盾心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纠缠在这一种情绪中,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正是这一种传统与现代的搏斗与交锋,丰富着当代中国戏剧文化的层次,指示着一种方向,尽管这种心态是有些茫然,甚至是失措的,但仍提供了一些启示。后来一些较为成功的剧目,如《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就体现了这种成绩。
在与西方现代派戏剧的激情拥抱中,中国哲学仍体现了它独特的价值能量。文以载道,一直是中国文化主题阐析的先决条件。这种文人精神,在中国前卫话剧组织新的话语中,用另一种意义与另一种精神,来抒写生命体验与人性关怀,与西方实验戏剧相同,也是表现一种深层焦虑,但中国前卫戏剧仍表现了相当入世的姿态,有一种使命与责任的意识。以批判的真情,对具有合法身份的封建观念、道德与禁忌发出了不合理与不人道的呐喊,对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颠覆与瓦解,并对人的生存处境与情感给予可能性的关怀与同情,与西方现代派戏剧世纪末日一般的绝望情绪不同,并不是去展示“恶之花”、“丑之萃”,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去对现实发言,体现了颇富特色的人文哲学传统思想背景。例如红极一时的荒诞派戏剧,中国前卫话剧在借鉴的同时,实际上也进行了一番具有批判色彩的创造性转化,将侧重点置于形式化的引进,但对其赖以支撑的哲学观念却进行了改造,转变为一种永恒的真理与品质的象征隐喻。由此,《车站》与《等待戈多》不同,它的主题并不是彻底的悲观,而是本质的乐观,只是表明实现理想的艰巨性,而不是某种带有神秘性的精神危机,在哲学立意上已发生了位移;《魔方》也更多的表现的是一种群体所带来的充实感与希望感,而不是孤独与幻灭的渲泄。正如魏明伦在《我做着非常荒诞的梦》中自况的:西方荒诞派戏剧“是以存在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以荒诞形式表现荒诞人生,得出荒诞结论”,而他则是“运用‘满纸荒唐话,一把辛酸泪’的艺术辩证法写戏,以跨朝越国的‘荒诞’形式,去揭示人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现实与未来的必由之路”。这种哲学背景,为误读的产生提供了必然性与独特性的前提依据。
中国前卫话剧自身存在中的现实状况,也使误读成为某种无奈的现象。在高昂着先锋的头颅,而现实的艰难,又不得不俯低宝贵的意志,从而产生某种变奏。例如小剧场戏剧,虽然不能说它就是实验戏剧,但在小剧场戏剧的多种制作动因中,先锋性与实验性确实是它的主体动机。如果说中国早期小剧场戏剧尚主要体现为常规戏剧的反动,但93年北京汇演以后,已然放弃了对前卫性的追求,以及由此必然出现的“出语惊人”的实验经营,更多的考虑是一种经济上的目的,小投资与低成本,与民众的可接受程度,“世俗化”成为一种流行主题。西方小剧场戏剧多数是不被主流戏剧或现实政治所接纳,因此被称为“地下戏剧”,都是一种“爱美”即业余化的行为,由业余戏剧爱好者自愿结成团体演出,有着一种“发烧友”精神,而中国小剧场戏剧多是清一色的正规军,即使一些民间剧社,成员也都是专业人员,在各种艺术元素上更关注商业利益与社会效果,对自身内在的规律性,缺乏更加精深的研究,成为一种大剧场戏剧的艺术附庸。
由此,一种文化误读现象,其实有其内在的必然与规律,都是从自身的哲学理念、文化构成、现实愿望与情绪出发的,无一不打上深刻的自我烙印。尽管这一种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可能是无意识的,而且对误读产生的影响力可能由于主体的存在处境有所差异,但确实对每一种文化的解读与认同,进行了一次按需理解式的扬弃与改造,并在这一种误读现象中,使自我的文化构成与气质,产生一种新的“造血”功能,呈现改良后的整合气象。
三
新时期的中国前卫话剧,对西方现代派戏剧实行战略性的引进,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误读性结果,实际上是一种“新启蒙主义”,都是一种自觉应战,而且带有很悲壮的现代色彩,主观企图无法与实际效用一致,新的焦虑又不断产生。这种戏剧误读,是一种带血的理解械斗,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堡垒式文化的国度,如皮亚杰认识发生论所阐释的,其顺化与同化、调节与平衡诸机能分外显得激烈,也分外显得精神与灿烂,在近乎革命的意义上寻找新生的启示。
在这一种自觉性的文化革命中,中国话剧体验了第二次接受西方影响的快感,尽管由于过度冲动,还来不及分清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界线,但对于中国话剧重铸戏剧诗学,产生了内在精神意义的深度变化,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以现代主义为用,在现实主义为体的戏剧范例内,大量吸收形式与修辞语汇,使戏剧语言现代化,使传统单一的叙述体例多元化,并拓展戏剧表现的内心空间;二是将现代主义本土化,移植与改造成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戏剧,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一次策反,产生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变革。这种深度律动,中西方戏剧的情与理、间离与共鸣、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创造幻觉与破除幻觉的对立、交流与融合,经过一次次成功与失败的戏剧实践,与随后的理论论战,无法有统一的学术结论,但却在这一次次实践与理论论争中,终于碰撞出了几部集大成的优秀剧目:《中国梦》、《狗儿爷涅槃》与《桑树坪纪事》。它们是前一阶段中西方戏剧自觉应战的戏剧成果,也是误读现象在舞台上的成功反映。
在为误读现象感到忏悔与负罪的同时,二律背反又一次在这里发生了效用。在自以为成为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全知全能者,已是它的认知主人,其实离西方现代派戏剧的本体,还是一种遥望。但是,这种在无意识中于对方精神的误解,确实带来了一种新的艺术整合。从辩证角度分析,它比自身的意义更大,甚至会带来文化心理结构整体性的变化。各自通过对方更好地理解了自我,互为主观又互为批判,从而促动乡土文化变革发展,如同梁启超所云的,“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有,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注: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改造》3卷11号1921年7月15日。)文化交流中的误读存在,不仅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而且也不失为有益的。只要处理得圆满,将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外因,是推动其进步与更新的原动力量之一。这是一种辩证关系,是悖论的艺术现象体现。
对误读现象的哲学检讨,对仍处于文化迷惘与生存困境中的中国前卫话剧而言,有些负面的误解行为,依然需要保持警戒。在肯定误读正的一面时,反面的一切并不一定具有同样的意义。“先锋”并不能够代表所有,标榜“前卫”也不一定性质相同,它很可能成为一种“文化快餐”,乃至是一种“文化弑父”的行为,只是一种成名策略,在功利的喧闹中,淡化建设意义,而是进入一种地道的“文化陷境”,对本土的文化贡献,产生了一种消极与瓦解的意义,使误读的正面价值全面弱化。其实,一种有价值的误读行为,并不是表层体认与机械照搬,而是从自我出发的重新改造,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是为了坚强自我文化建构的精华吸收。同样这种误读,也并非不需要戏剧实践家来自人生或人本体的深层体验,它仍需要感性的营养,才能产生沉实的底气与收纳的功力,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运作,在生命的感悟中完成误读的角色转换,在重新选择中成为自我本体的最具现代前瞻性意义的命运发言。
从某种意义而言,前卫具有很大的流变性,转瞬就会转化为古典。中国前卫话剧误读所带来的效应,也并没有穷尽一切,当然也无法也不可能退回到原处。在观众流失的丧钟中,误读的正面价值不断退化,而变得日益浮躁与狂热,在传统思维定势的挤压下,而迷失在一种病态的极度反动中,仍看不出明确的方向。这里需要一种科学的理智,因为“对于实验探索的选择,就是对我们自身命运的选择”,(注:孟京辉:《实验戏剧和我们的选择》《戏剧文学》1996年第11期。 )应该是一种生命的真诚倾诉与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