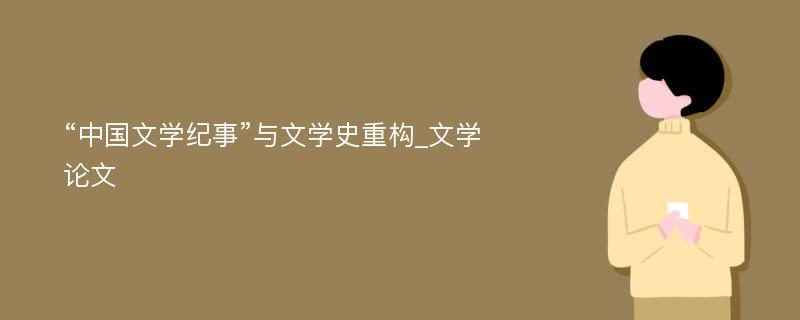
《中国文学编年史》与文学史的重新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年史论文,文学史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学史的撰著,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近十多年来,基于对文学史著作中长期占主流地位的教科书模式的反思,学界在重新建构文学史的问题上探讨尤勤,诸如“悬置名著”、“进入过程”、“大文学观”、“话语体系”等,都是与之相关的颇有价值的思路。由知名学者陈文新教授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以下简称《编年史》),正是在此学术背景下,以编年体的形式重新建构文学史的一次尝试。
一、史料:消解“等级”与建构“意义”
作为20世纪文学史著作的主流体裁,纪传体的一般写法是,按照作家的“等级”安排章节,“一流”作家一章,“二流”作家一节,“三流”作家几个人合起来占一节或一段。这种写法固然有利于清晰地梳理历代重要作家以便于读者掌握(尤其便于教学),但其局限就在于把文学史变成了重要作家和文学名著的历史,而缺少对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的关注。与纪传体以作家(大家、名家)或作品(名著)为基本单位不同,编年体以时间点(年、月、日)为基本单位和叙述支点,其优势恰在于关注文学发展过程中有价值的细节。与此相关联,在对基本文献的占有和使用方面,纪传体可以只关注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而编年体则要求对每个时间点上的文学事件和人物通盘考虑,即便是名家名著,也应置于当代文学的“话语体系”之中。
抛开“等级”观念,对几乎所有文学史实以及作家进行观照,所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文学史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全体作家年谱合编”,那么,究竟哪些史实和作家应该被写入文学史?这时,或许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更为适用,即重新建构文学史的目的不是还原或再现历史,而是用新的话语或文本表述新的“意义”。试以清代作家洪亮吉为例,《编年史》除了收录他的生卒、功名、交游、历官、创作等活动之外,还关注了这样一些史实:1765年,在外家授表弟一人,岁得修脯钱二千八百;1766年,在外家授表弟三人,岁入修脯钱七千;1774年,入常镇通道袁某署授徒,岁修百二十金。又在扬州安定书院肄业,膏火费亦及百金;1779年,入四库馆校雠,岁修二百金;1780年,自二月至七月,代人作颂述之文凡五六十篇,得酬金四百两……。这些史实,让我们看到清代中期文人经济生活的一个侧面。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尽管注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但主要立足于宏观大局,而对作家个体的经济状况和物质生活关注不够。《编年史》收录此类史实,旨在凸显这一长期被忽视的层面,所谓话语或文本的意义即在于此。
至于哪些作家应该纳入《编年史》的视野,当然不必如钱锺书先生所调侃的那样,像选举理事会,面面俱到,但应该力求呈现文学格局的多元化。譬如女性文学研究的崛起,是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现象。尤其是女性文学最为兴盛的明清时期,更是为不少研究者所关注。《编年史》清前中期卷收录了华浣芳、徐昭华、陈端生、侯芝、曹贞秀、王照圆、梁德绳、吴藻等数十位女性作家,他如满洲作家、释道作家皆有收入,即旨在重构完整的文学版图。
由于以时间点为叙述支点,《编年史》尤其注重历史时间的考辨。譬如有关作家生卒年的著录,在纪传体著作中的微小失误可能无关大体,但在编年体著作中却影响到史实的排列位置。如有文学史著作将袁枚的生卒年著录为1716—1797年,则没有考虑到袁枚卒时(清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历已进入1798年;或称其卒于“公元1798年(清仁宗嘉庆三年)”,则是简单地根据他人换算过的公元年份来添加对应的年号纪年。① 面对此类问题,《编年史》采取的是如履薄冰的审慎态度。再以清前中期卷(上)所引《四库全书总目》为例,卷一四四称钮琇《觚剩》续编成于康熙甲午,实为康熙壬午;卷一八四称梁机为康熙癸巳进士,实为康熙癸巳举人、辛丑进士;称查祥为康熙辛丑进士,又谓其早岁尝举博学鸿词,晚乃登第,查祥实为康熙戊戌进士、乾隆丙辰词科征士,其举博学鸿词在登第之后;等等。如果是纪传体著作征引此类文献,有可能忽略其中的错误。而编年体的性质要求对史实的时间进行准确定位,因此《编年史》在征引文献时,对此类错误尽量予以考订辨明。
二、共时态:以体裁为单元与以时间为支点
文学史著作的又一通常做法,是在叙述某一阶段的文学面貌时以体裁为单元,具体表现为按照诗文词、小说、戏曲等体裁安排章节。(与作家的“重要性”相结合,通常是文体为“章”、作家为“节”,只有像苏轼这样的少数“全才”才有幸单独列“章”,而其诗文词则分别列“节”。)如果我们把这类文学史的章节重新排列组合,就可以得到诗歌史、散文史、词史、小说史、戏曲史等等。这种写法尽管有诸多好处,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源于西方的四大体裁的划分,与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存在很大差异。以“四分法”来撰著文学史,容易导致对文体特征认识上的混乱。其二,这种写法极易给造成一种假象,即诗文词、小说和戏曲按照它们各自的道路发展着,互不相干。
“四分法”的惯性常常使我们把作家的某些创作当成另外一些创作的论证材料,从而失去了对该作家全面观照的可能。例如吴敬梓,通行的文学史著作多以《儒林外史》列章,有关吴敬梓的生平列一节,其中吴敬梓的诗文作品作为作家生平的史料而存在,作家生平又作为《儒林外史》的背景材料而存在。这实际上人为地给吴敬梓的创作分了先后,分了层次。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谈到文本和历史背景之间关系时曾说:“很多被我们用来作‘历史背景’的东西只不过都是由不同的文体所表述的同样的材料而已。换句话说,我们不拥有纯粹意义上的历史背景知识,只拥有在同一话语系统中由不同文体根据各自的文体特点对同一本源材料所做的不同角度的表达。”② 宇文所安的这段论述出自他的《瓠落的文学史》一文,以“瓠落”为标题,表明这类观点尽管有价值却不大实用,不便于操作。而实际上编年体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较好形式。在《编年史》中,吴敬梓的各种活动按时间排列,从而有别于以此文体论证彼文体的惯例,同时这种排列又与当时其他作家的文学活动共处于同一“话语系统”之中。
“四分法”的惯性还常常使我们过于注重某位作家的某种文体而忽略了他在其他文体上的成就,因而文学史总是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小说家蒲松龄、骈文家汪中……。《编年史》则力求全面反映作家的创作成就,更重要的是,这种全面反映对于我们了解古人真实的思想世界或许有着不一般的意义。《编年史》中的蒲松龄,不仅仅有《聊斋志异》,有《聊斋诗集》、《聊斋文集》,甚至还有《妇姑曲》、《翻魇殃》等俚曲,有《日用俗字》、《农桑经》等文化普及读物。汪中虽以骈文名家,而其早年喜好为诗,四十岁以后则甚少作诗而专治经术,这种转变源于怎样的思想认识,在当时是否具有普遍性,相关史实的排列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回答问题的线索。
《编年史》在叙述文学历程时凸显的是时间点而不是体裁。在某个时间点上,中国各地的文人都在干什么?这是一个具有图像意义的话题。以清嘉庆四年(1799)的北京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王昶正月入都,与法式善、何道生、张问陶时相过从谭艺,四月返,七月抵里;洪亮吉三月至京,八月获罪,遣戍伊犁,张惠言等送行;钱泳在京师寓郑亲王惠园三月,与法式善、汪端光、王芑孙交游……。《编年史》所收此类史实,没有也不可能涵盖本年全国各地所有文人的活动。不过,它涉及了作家活动的多方面,包括科举、历官、谪戍、出使、游幕、坐馆、讲学、交游、创作等,呈现出一个活动的、原生态的、可闻可见的文学时空。
相对于以体裁为单元的叙述方式,以时间为支点可能会因头绪过多而显得凌乱。但一方面,文学史本身是千头万绪的,所谓规律、逻辑是后人归纳出来的(如以体裁为单元),另一方面,《编年史》注重通过某些史实将作家聚合在一起。这些史实包括乡试、会试、游幕、集会、唱和等。如以乡试或会试为纲,可以聚集该科主考官及同榜作家;以某人入幕为纲,可以聚集同时游幕者;而集会、唱和则可以展示作家的交游及流派状况。甚至皇帝出京巡视这类看似与文学无关的活动,也因其与作家的功名或创作有关,而在《编年史》中记上一笔。如1780年,与乾隆南巡相关的史实有:江浙上演迎銮大戏,王文治、沈起凤制新曲;沈叔埏、赵怀玉、杨揆等应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蒋知让赐举人,孙星衍报罢。因一事而聚集多人,这种“归纳”因为没有先验理念的介入而显得更加客观。
三、历时态:“说书人”与“记录员”
在某些方面,文学史家有点像说书人。譬如说书人讲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而所谓“有话”和“无话”则取决于说话人对事件重要性的主观判断。文学史家也是这样,常常在“重要的”文学阶段花费较多的笔墨,而在“不重要的”阶段言简意赅甚或付诸阙如。这样,文学史著作的页数与文学的历史过程并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在通常情况下是必要的。但同时,这种不一致是否会遗漏某些可能不“重要”但很有“意义”的历史过程,则是我们不能不谨慎考虑的问题。譬如明代前期一百多年的小说发展状况,长期以来在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几乎是不占有页码的。而实际上,明代前期市井民间的小说创作和传播从未间断,这一点,最近几年已经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
要处理好上述不一致,固然需要审慎的研究态度,而在撰著体例上,编年体比纪传体更为有利。这并不是说在编年著作中,文学进程按照时间平均分配页码,而是指编年体本身要求对所有文学时间作平等的扫描和客观的记录,因而不会出现所谓平庸的文学时代或文学史的空白时段(至于因文献缺失而无法纳入视野的时间点则另当别论),从而避免有意义的文学史实的遗漏。
“记录员”的优势不仅在于重新发现“说书人”遗漏的空白,还在于把握历史进程中的细节。譬如清代以古文名家的储掌文,一生中不同时期进行古文创作的直接动机多有不同:青壮年时期流寓仪真、扬州逾三十年,其《自叙》云:“年二十六七始游扬,自后馆洪氏、方氏、程氏、乔氏,历数十寒暑。扬俗尚奢华,富贵家遇吉凶事,辄屏障连楹,其辞多假手于流寓之士有名者。亦问及余,余业抗颜皋比,义不得谢,因靦颜为之。文出,而讪笑者殊少,遂群目为能古文矣。”至六十岁始官四川纳溪县,《云溪文集》卷首储樵识语云:“及捧檄入川,上奉宪台之命,下应寅僚之请,其作始多。”六十六岁自蜀归里,其《自叙》又云:“比投檄归,则邑中著作手凋落殆尽,以予齿加长且藉草堂馀荫也,戚友间不朽之托,诿諈滋多。予亦晚景萧聊,于不相知者时复卖文为活。”文学史上诸如此类细节,在《编年史》中由于对时间点的客观扫描而得到了较多关注。
在历时态地展示文学发展历程方面,编年体有其自身的缺陷,即不具备宏观把握历史事实的功能,历史进程被分散在各个时间点中而缺乏高屋建瓴的概括。因此有必要借鉴纪事本末体的叙事方法,在适当的时间点对重要史实详其起讫,作历时态的叙述。如清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编年史》在本年一并交代康熙五十二年结案。有关此案的史料颇多,《编年史》引全祖望《江浙两大狱记》,即因全氏此文详其始末,有助于把握此案大局;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编年史》引李调元《淡墨录》卷十《再举博学鸿词》,叙述雍正十一年、十三年雍正帝两次降旨要求各地奏荐人才之事;乾隆九年鄂尔泰驳舒赫德上废科目疏,《编年史》引方濬师《蕉轩随录》卷六《试士废八股文》,述及康熙年间乡会试曾改用策论之事;乾隆二十二年会试易判表为五言八韵律诗,《编年史》引《清稗类钞·文学类·试帖诗之遗闻》和《晚晴簃诗汇》卷九六“吴锡麒”诗话,述及此后试帖诗之盛行;等等,以求前后呼应,见首见尾。
四、结语
作为叙述形态,任何文学史著作都假设了它的读者的知识程度。教科书模式的文学史之所以招致不满,一个主要的症结就是“叙事者假设自己和读者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不对等;叙事者访得了知识的火光,然后传递给蒙昧的读者”③,于是这类著作充满了全知全能、自上而下的自信。而重新建构文学史的前提就是要消解这种嘉惠后学的自信,确立“叙事者”和读者在知识上的平等地位。由此而形成的文学史著作也就不可能如教科书那样,主要反映学界已有的成果,而是以探索的、尝试的面貌呈现出来,或即所谓带有“偏见”的、不“全面”的、“个人的文学史”。《编年史》在前述诸方面的尝试,建构了一个新的文学史形态。诚然,任何一种尝试都无法涵盖文学史的全部,《编年史》在诸多方面仍然有向前延伸的必要和可能。仍以清前中期卷为例,尽管在关注作家“行”的同时也注意收录重要的“言”,对文学文本的精读深研仍显得相对薄弱。如何在关注众多文学活动的同时“回归文本”,将文学活动与文学文本有机结合起来,仍是《编年史》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 参见朱则杰《两种高校通用中国文学史教材亟须修订——以清代诗人生卒年问题为例》,《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宇文所安自选集《他山的石头记》,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③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附编一《文学史的探索——〈中国文学史的省思〉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