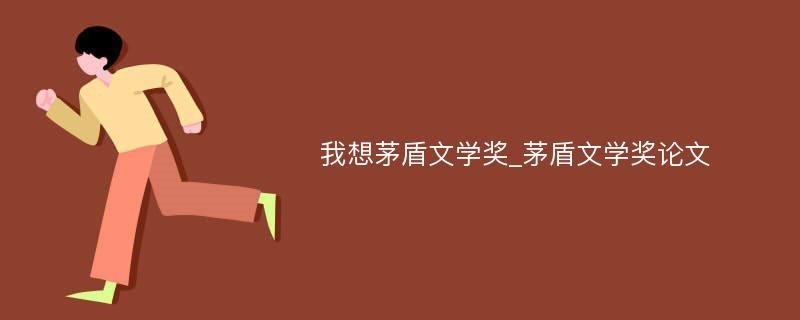
我看茅盾文学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看论文,文学奖论文,茅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茅盾文学奖第四届评选结果于1998年初出台了。到此为止,它已走过了16年(1982年—1997年)的历程,其获奖作品则涵盖18年(1977年—1994年)。这应该是它的“童年期”。
茅盾文学奖被人们普遍看作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甚或是中国当代文学界的最高奖。然而随着评选历史的延伸,这个“最高”被越来越多地投上了难以抹去的怀疑的目光。人们对它曾有过的热情,信赖和企盼仿佛也越来越淡薄了,尤其是后两届评选结果出台以后。
任何一种文学奖项都被看作是对其历史发展的肯定和引导,而到了现当代,长篇小说又往往被认定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它的评奖更具有这样的性质。从这一角度观察,茅盾文学奖的偏颇则更突出。
我们且从科学性和权威性进行讨论。
我认为,所谓评奖的科学性首先是评选标准的明晰、确凿、崇高、一贯性及其艺术审美的前置性,文学发展的前瞻性;其次是评选程序的规范性。所谓的权威性则体现于评选的各个环节上:评选标准,评委的组成状况,评选的具体操作过程,最终落实在评奖的结果上。科学性是权威性的保证,没有科学性就不会有真正的权威性;权威性是科学性的目标,没有权威性科学性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科学性和权威性,任何评奖不过是一文不值的儿戏。
关于科学性
首先是标准。标准即准则,它表明评奖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指导和制约着评奖的全过程,具有“法”的意义。严格科学的标准才能保证评奖的严肃性,这是走向目标的基本前提。对茅盾文学奖,局外人从未在报刊上或其它传媒体得到它的明晰、确凿、一以贯之、具有“法”的意义的标准;局内人则透露说,该奖“居然历来是在不予阐明评选的艺术标准的情况下展开工作并敲定评选结果”的(注:朱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之我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二期。)。当然,我们不会认为每次评奖毫无标准可言,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标准是临时性的,即每次开评前大致规定的,因此它不具备“章程”或“法”的意义。而且,这种临时性的标准在具体操作中也有很大的通融性和主观随意性。比如,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弘扬主旋律,鼓励贴近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创作是评选的一个指导性原则”(注: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小说评说》1998年第一期。)。显然这只是针对该届的指导原则,即“标准”而“指导”的结果也只是选出一部《骚动之秋》这样的作品,占获奖作品的1/4,还是在“对这类题材作品无法要求太高”的情况下比较勉强评出的,可见其指导原则的脆弱性。
从上面的“指导性原则”也见出一个事实:作为一个标准,它主要的还是停留在“政治”对话的层面上,而小说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应予首先重视的艺术审美性则大大后置了。应该说这种倾向在历次评奖中是一贯的,第三届则最突出。这样说,并非是仅仅抓住某人透露出的只言片语(这当然也是重要的信息)而形成的片面结论,更主要的还是从评奖的实践结果去看。从历次公布评选结果对入选作品的评价中我们看到,其政治内涵是十分鲜明突出的,那就是所谓的“主流意识”,或曰“时代精神”、“主旋律”,而其艺术信息则是十分含糊、微弱的,且淹没在前者之中。如果人们认为“政治第一”甚至“唯一”仍然主导着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活动,那么主办者将怎样去辩解或反驳呢?至于那些具有相当深厚社会内涵,并显出相当艺术功力,也产生了相当社会影响的作品却与此奖“失之交臂”又将作何解释呢?正因为如此,象《白鹿原》这样建国以来难得一见的厚重之作却成了第四届评奖“困难的症结”——不评吧,文坛内外都过不去:“1989年至1994年间,被公认为最厚重也最负盛名的作品首推《白鹿原》”;评吧,“《白鹿原》通向茅盾文学奖的道路上荆棘丛生、吉凶难卜”(注: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小说评说》1998年第一期。)。“症结”到底在哪里?明白人不言而喻:《白鹿原》的某些历史观念同现实的政治观念的龃龉。传统文化昭示聪明的国人以灵感:走“中庸”之路,评其“修订本”。阴霾消散,皆大欢喜。不过这却给中国文学历史留下一个大尴尬,一个使人无法发笑的笑话:所谓的“修订本”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存在”,接受殊荣的只是一个假想的经过“整容”后的“新生儿”!如果以评奖的时限1994年计,其时此“新生儿”的影子还不曾在作者的脑海里孕育。这一新版之“皇帝的新衣”只给历史留下悲剧性的思考。
文学属意识形态范畴,它无法摆脱社会时代及意识形态其它部门尤其哲学、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但另一方面,文学(包括小说)首先是一种艺术存在,是“艺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们在艺术这一特殊的“自由王国”中的审美创造,所以,审美属性是其根本属性。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思想内涵其实只是作者的情感价值的体现,其中包括认识价值和道德价值,而这种价值的真理性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却表现为绝对的相当性。这只要是回顾一下文学历史,尤其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再清楚不过了。作者的情感价值只有融入艺术的审美创造中才会造就真正的艺术,才能体现真正的艺术价值,反之,只能诞生低廉的宣传品或商业广告。表达理念是容易的,创造审美的艺术价值是困难的。作为文学奖,首先评的是“文学”,即对象的艺术属性和艺术品质、艺术成就,这其中就包容了作者的“情感价值”,即思想性。
其次是程序。十分明显,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程序很大程度上是非科学化、非规范的。
其一是评委的组成非规范化。历届的评委不是由文学界依其具有评奖操舵作用的学术水平、艺术观念及其他综合素质遴选产生的,而是由领导部门指定组成的,而且,这一组成从不具有相对稳定性,倒是常常投映着社会“气候”的色彩。应该说,每届实际参评的评委都是具有相当“资历”和“名气”的,但是“资历”和“名气”并不能完全决定参与的“资格”。如果这“资历”和“名气”同不被新时代认可的观念、情操相伴随的话,参与的结果更容易使评奖失去权威的分量。事实恰恰如此,尤其后两届评奖。
其二是每届获奖作品的时限非规范化。第一届五年(1977—1981),第二届三年(1982—1984),第三届四年(1985—1988),第四届六年(1989—1994)。第二届比较规范。第一届因为首评,把新时期以来的几年一并计入情有可原。第三、四届就使人摸不到头脑了。尤其第四届,它所涉及的作品的时限实际上还大大超过了六年(向前考虑到了1987年出版的《活动变人形》,向后则是尚未出世的《白鹿原》修订本)。为何如此?实在令人茫然。
其三是入选作品与奖项非规范化。第一届六部;第二届三部;第三届七部,而且特设了“荣誉奖”;第四届四部。为什么会如此?因时而定?因势而定?因人而定?尤其第三届那个“荣誉奖”更叫人莫名其妙。
至于评选过程,更难以谈得上规范化。尤其后两届,庞大的班子,断断续续工作两年左右(加上准备、推荐时间还远远不止如此),才勉强出台结果。在世界日新月异的今天,如此马拉松的过程人们何堪引颈以待?当我直书这此话的时候只能向辛辛苦苦工作的参评的同志们深表欠意并乞理解,我只望我们的“大奖”能进入真正的科学化轨道,以慰茅盾先生的在天之灵。
鉴于上述,我认为,评奖的主办单位应在公开、民主的前提下选拔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文学声望、较开放的艺术观念的专家、学者、作家组成常任的(非专职)评选委员会,制定出相应的具有权威性的评选章程(包括标准),以此保证茅盾文学奖评的科学性,使之真正成为我国文坛具有较高声誉的大奖,也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创造更好的契机。
关于权威性
前面已有涉及,这里主要从评奖的结果上看。结果具有终极性。权威的结果首先应具有历史的公正性,即能真正反映一个历史阶段长篇创作的实绩及其发展方向,并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这样的结果才能使人信服,给人以鼓舞。但是,这是失去了科学性的评奖难以达到的。比如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同主办者的高度评价(注:参见《文艺报》1991年3月30日:《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在京举行》。 )相反,在获奖结果公布四年以后有人撰文指出:“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全然回避了1985年至1988年间长篇创作领域最富有特点也最有发展意蕴的实践成果,对那一时期许多很有艺术价值且艺术反响不凡的创作现象和作家作品,采取冷漠和忽视的态度;甚至在客观上标志的评选范围和价值走向上,所选择的个别作家作品,也不堪与同期同类作品比照相抗衡”(注:朱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之我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二期。)。实践证明,这样的意见更符合实际,它是历史检验的结果。今天,把这些话用在最近一次评选结果上也是完全合适的,虽然这一届有了一定的改善。我们不妨逆向推论,1989至1994年中,已问世的长篇小说至少在二千部以上,这次评奖进入初选圈的112部, 进入表决圈的20部,最后入选四部。如果这四部作品能代表中国六年间二千余部长篇的最高成就及其发展方向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深感中国的长篇创作太寒酸了!更何况象《白鹿原》这样的作品还历经磨难,经过折中“处理”才忝列其位的。(即使如此,也使贾平凹为之长出了一口气,从而感激这“上帝的微笑”。)(注:贾平凹:《上帝的微笑》,《小说评论》1998年第一期。)由此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历届入选作品中,艺术上真正有棱角的实在是凤毛麟角。《白鹿原》命运乖蹇的关键也在于此。虽然在裁判者眼中它只是个“擦边球”,但也必欲校入“规范”之中,否则,“吉凶难卜”……只是人们要问:公正在哪里?
为什么会这样?问题盖出于价值之取向。
首先,是思想内涵的价值取向。在这方面,茅盾文学奖的传统功利主义色彩是否太浓重了?不能否定功利性,任何作品都有社会功利性。但是,也不能把这种功利圈得太狭隘了。文学是人学,是人的灵魂、人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形象化、艺术化的审美表现和创造,它的内涵是极其复杂的。而我们强调的仅仅是“主旋律”、“时代精神”,并且这都是比较模糊的概念,这样在具体操作中既排斥了一批有高度艺术价值又无法进入“主旋律”的作品,同时也增加了评选的主观随意性,这不仅仅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这种价值取向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它引导作品追求现实的时效性,停留在生活的表面真实上;它们的“主题”往往一两句话即可概括得十分彻底;公式化、概念化、传统化是其挥不走的影子。这样的作品入选,必然是以牺牲某些更优秀的作品为代价的,那些作品往往深层次、全方位表现人及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以开放的艺术方式展示生活的本质真实,人的灵魂的本质真实,却不被评选的价值标准认可。
其次,艺术方向的价值的取向。前面说过,文学是“艺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任何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学奖(比如诺贝尔文学奖)都十分注重作家作品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开拓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只有这样,才有文学的真正发展。文学奖项应肯定和总结这种成果,以此展望更新的前景,推动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走向新的艺术高峰。然而,在茅盾文学奖的历届获奖作品中,给人以艺术新鲜感的只有极少几部,不少作品给人的是强烈的艺术陈旧感,有的作品在接受过程中唤起接受者的那种沉闷感、疲劳感真使人难以卒读,这样的作品即使用传统的“五老峰”标准去衡量也算不得上乘之作,而它们却登上了今日长篇小说的“最高”领奖台!与此相反,众多在艺术上有较大突破、创新,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中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却被无端“忽略”了,这不能不反映出茅盾文学奖艺术方向的价值取向上的保守性和滞后性。
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创作上的艺术“探索”到八十年代中期形式大潮,旧有的艺术樊篱几乎被彻底打破,标新立异、各领风骚、多元竞争一时成为文坛的眩目风景。西方艺术观念、艺术方式的引入和借鉴,使文学彻底失去主潮,“千条江河归大海”,文坛呈现着色彩纷繁、空前壮丽的景观。这其中虽然难免泥沙俱下,虽然充满形式主义乌托邦和语言魔术的恶作剧,虽然难免极端,难免“东施效颦”,虽然……,但是,这一潮流不论从艺术观念上还是艺术方式上打破一无独尊、一花独放的格局,冲破文学狭隘天地,走向广阔的艺术世界都具有历史性的功绩;而且这期间也确实产生了一批经得起历史筛选的作品。到了九十年代,这一潮流经过反省和沉淀,经过比较和淘汰,它的发展日趋走向健康和成熟,而且中西艺术观念、传统和新潮艺术方式互相供借鉴、融合,也产生出一批新质、具有较强生命力、开放性的艺术成果,为文学展示了一种可喜的前景。《白鹿原》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茅盾文学奖对这一历史性变革表现得十分冷漠、麻木和无所作为。从第三、四届评奖中根本看不到对这种现实的真正正视和包容,虽然《白鹿原》最终还是入选。评选的结果使人觉得仿佛拿着长袍马褂,或者中山装的式样在眼花缭乱的服装市场上选择“时装”,其结果只能是力不从心、不伦不类、甚而啼笑皆非。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现实的情况是,具有“现代”或“先锋”倾向的作品从不被评奖者青睐则是无庸置疑的,其中包括被文坛看好的优秀作品。当然这里不是鼓吹唯“新”是求,唯“新”是崇,我们主张的是公平竞争,我们要的是公正的比较,虽然这一比较常常是困难的,难免失误的,但总不能有亲疏之分,总不能抱残守缺,总不能顾此失彼,总不能仅仅是“回头张望”,还要“放眼未来”吧?
第三,从题材的价值取向上我们还可以发现,茅盾文学奖对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恋情结。从第一、二届的占1/3,到第三届占2/3,发展到第四届的畸形化程度3/4,与现实题材的比例形成了3∶1的对局。应该承认,新时期以来,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创作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历史题材,自八十年代初期崛起之后,一直保持较旺盛的创作势头,并且佳作不断。但是,也应看到另一方面,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现实题材逐渐开始占压倒优势;到九十年代中期,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不论在总的数量比重上,还是整体艺术水准上早已处于弱势,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然而这种情势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上得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反映:现实题材只有一部《骚动之秋》独领风骚,“它的获奖使许多人感到惊讶”。对此我们能获得的唯一解释是,依前述“指导原则”衡量,“1989年至1994年间,在长篇小说创作范围里,正面反映改革现实的作品不多,质量好的更少”,因此象《骚动之秋》这样的作品,“也还说得过去”(注: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小说评说》1998年第一期。)。这里有些问题需要澄清。首先,“指导原则”中的“弘扬主旋律”,“体现时代精神”,必然“合乎逻辑”地把“贴近现实生活”仅仅定位于改革题材上,这种十分偏狭的政治化“原则”也必然“合乎逻辑”地将一大批非改革内容的现实题材作品排斥在候选圈之外。其次说六年间“正面反映改革现实的作品不多,质量好的更少”也应有所分析。很清楚,自89年以来,长篇创作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势头,尤其93年的“陕军东征”和94年以后以“布老虎丛书”为先声的“集团冲锋”,使长篇创作在题材的取向上、艺术方式上更加开放,更加异彩纷呈。这种无序之“序”,甚至使批评界也“失去了方向”,“错位”、“失语”之类的惊呼声不绝于耳。长篇创作“热”首先体现在数量上,包括大量“改革现实作品”,因此言其“不多”显然不是事实。当然另一方面也很清楚,89年以来的长篇创作由低谷到升温到“热”,数量在飞跃,而飞跃的主要是平庸之作,“精品”,“大气”之作微乎其微。但是,这种状况不独现实题材如此,历史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尤其如此,那么,第四届评奖的结果为什么唯独现实题材数量之少、质品之弱位居于“最”?问题的症结恐怕在操舵者的视野和早已凝固的“构思”。
这里仅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范围举一个突出的例子。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熊尚志创作的《骚乱》就是一部反映改革初期社会现实的相当有分量的作品(应赶紧声明:我与作者、编辑从未谋面,纯为客观读者,决无“唤朋呼友”之嫌)。只要稍有艺术鉴赏力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部作品在表现“改革现实”的内容上,挖掘深度上,艺术开放性及其语言功力上,典型人物及典型环境的刻划上,乃至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地方色彩方面都甚称新时期以来少有的佼佼者。我将其概括为:深刻、独特、美。其艺术成就并不在《白鹿原》之下,其厚重度远在《骚动之秋》之上。(因篇幅有限,恕不在此作具体分析。)遗憾的是,这部作品问世以来,至今不见批评界的只言片语,我想,其原因除了作者与出版者都未进行时下流行的商业化炒作外,重要的在反映批评界的“失语”了。如果这样的作品在评奖者那里被“忽略”了或被淘汰了,那实在是一种悲哀了。类似的作品不会仅此一部,它们都是怎样被淘汰出局的?为什么只剩下一部孤独的《骚动之秋》?
《骚动之秋》也是一部较好的作品,它有相当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但总体说它给人以单薄之感。它的主要成绩在于塑造了岳鹏程这一艺术形象。不过,这一形象也很难说是独特的。辽宁作家于德才发表于1986年的短篇小说《焦大轮子》与《丁大棍子》中的主人公,尤其“丁大棍子”同岳鹏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电影《被告山杠爷》中的山杠爷也与之有较大的思想共性;现实生活中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更是其“模特儿”。这部作品在艺术表现上也说不上什么创新。它的获奖“使人感到惊讶”,主要在于它不足以代表1989年至1994年间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实绩及其发展方向。如果说,“至今,改革题材小说在套路上相比《骚动之秋》等作品,还没有显著的突破,因此《骚动之秋》获奖也还说得过去”(注:朱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之我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二期。),这只能是为评奖者作勉为其难的自圆其说。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就是说,这部作品在“套路”上有“显著的突破”,然而,它的突破在哪里?相反,以它去对照一下《骚乱》的“套路”吧,后者才是一种自然、和谐又十分鲜明的“套路”!至于象梁晓声的《浮城》,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余华的《呼喊与细雨》等一大批作品又是怎样一种“套路”?(只是这些作品不符合直接表现“改革”的“原则”,而被置之不顾了;然而他们对国人灵魂的拷向却是与今日的“改革”息息相通的)。已有的文学现实被大量忽略或删除了,问题还出在价值向上:偏狭后视的思路只能在有限的小圈子里打转转。话说回来,就改革题材小说而言,如果认为《骚动之秋》这样非常传统的“套路”仍是今日长篇创作最高水准或最高典范的话,那么其一,这就完全否定了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多元竞争的事实及其成就,尤其否定了那些“实验”性、“探索”性的实践成果;其二,这就把新时期以来踏上文坛的一批又一批灿若群星的作家的艺术才华和审美创造一笔勾销了。如果已成的定局体现了一种历史公正的话,那真不知文坛中人(尤其作家)对我们的文学发展作何感想,遑论当从世界角度看中国文学发展现实的时候。值是庆幸的是,现实并不会使人如此悲观,也就是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所印证的1989年至1994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实绩实态同第三届一样,也是“极其苍白无力的”(注: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小说评说》1998年第一期。)。
中国应该,也有充分条件建设一个具有我们民族特色,具有高度科学性、权威性,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奖,一如其它民族的塞万提斯奖、但丁奖、龚古尔奖等文学奖那样。茅盾文学奖是最具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的。我们企盼经过反思、总结,走出“童年”的某种误区,把它建设得更好,更完善。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是中国文学步入世界之巅的需要,是历史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在这方面,我们也不应辜负文学先辈茅盾先生的遗愿。
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