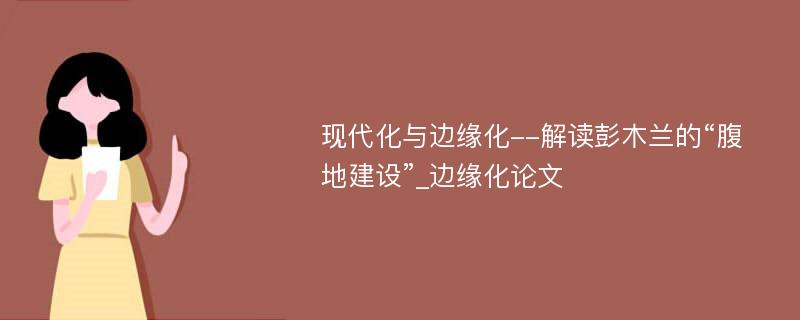
现代化与边缘化——读彭慕兰《腹地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腹地论文,化与论文,慕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黄运”地区(黄河与大运河交叉地区的简称,即山东津浦线以西地区)为何没能随着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大潮走向繁荣,相反却日趋衰落,这是彭慕兰教授《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①一书最为关注的问题。在他的笔下,这个地方性问题与近代中国治国方略的转变密切相关。②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清政府被迫逐步转变治国方略,开始推行富国强兵的自强国策,而民国时期的历届政府也都延续了这一国策。那么,这一战略转变的效果如何?与之相伴始终的中国“国家构建”又是否成功呢?西方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不少争论,一些学者强调中国旧的政治体制的衰败,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及由此增强了国力。围绕洋务运动、晚清新政、北洋时期和南京政府的“黄金十年”,国内学界也存在很多争论。彭慕兰的观点是:“黄运的事例要求并揭示了把我们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国家的两种相反的印象合到一起的新方法。”一方面,19世纪及20世纪初中华帝国逐渐衰落,这种衰落在中央政府对农村控制的缺失及其基本功能(秩序的维持、自然灾害的防治和保卫中国主权免于外人的破坏)的糟糕表现方面反映了出来;另一方面,近些年的研究又“为我们提供了一幅20世纪初中国国家构建的图画”,它展示了从清末开始,中间经过民国时期,并最终与1949年后“出现的最强大的国家联系在了一起”的连续发展进程,这一进程既包括国家的现代化,也包括社会的发展,它甚至堪与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相媲美(第302页)。这样,彭慕兰的“新方法”简单说来,或表面看来,就是将两种相反的历史叙述综合到了一起。在谈到衰败时,他主要指内地农村,而在谈到发展时,其目光则转向了沿海城市。
毫无疑问,在工业增长等方面,近代中国(尤其是在沿海城市)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在内地,远不是现代化高歌猛进的历史:“政府的主要失败似乎一直是在其传统使命方面——维护公共秩序和治水、救荒、军事防御——并一直集中在特定的内地区域。由于它们对本来就已贫困的地区以及纳入国内生产总值统计以外的那些活动(如拾柴)打击最重,这些失败可能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不大。不过,它们对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影响极大”(“导言”第24页)。于是,在黄运地区就呈现出两个看似怪异的现象:强有力的政府却无力挽回这个地区跌入深渊;谋求现代化的政府却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福利损失。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矛盾?彭著强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850年以后“中国的治国方略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根本性突变”。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放弃了传统国家曾履行了数百年的传统使命,转而推行新的治国方略——自强战略,以求实现新的目标。彭慕兰认为,“这种重新定向”有着几乎无人留意的深远影响,这就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所推行的自强战略,不仅有其表层含义——富国强兵(建工厂、练新军之类),而且还有第二层含义—国家“中心”地区的转移。“官员们寻求生产和动员财富以用于国际竞争……这种新的经世方略既改变了国家专注的任务,也改变了它认为最为重要的地方”(“导言”第1—2页)。
在明清时期,大运河持续繁荣了数百年,而黄运恰好环卫着这条“中国的咽喉”,从而在数世纪里都是华北大区核心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的核心地区之一。但从19世纪中期开始,黄运受到了双重打击。从市场方面看,“运河的衰落与沿海贸易……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在山东半岛上造就了新的核心地区,并把黄运的大部分变成了边缘地区”(“导言”第2—3页)。从国家方面看,“中国的国家转向了一种自强的逻辑。在那套方案中,问题的关键是一个项目是否有助于维持对中国富有竞争力的地区的控制,是否有助于中国现代部门的建设,或者从总体上减少威胁中国国家主权的债务……国家把它的注意力转向了关键地区、而不是落伍的地区;而随着海洋运输的兴起,黄运没有一处变得重要起来”(第156页)。③对于黄运的衰落,彭著曾做过一个十分直观的对比:尽管从交通运输方面看,穿过黄运中心的大运河被环绕其四周的铁路(津浦线、平汉线、石德线、陇海线)所取代,尽管按当时流行的看法,铁路的效率要高于运河,但黄运仍旧日趋衰落——石家庄从铁路修筑前的一个村庄变成了大城市,而济南赶上并超过了济宁,相反,临清和聊城却式微了。此时的黄运,其北部附属于天津、青岛等正在兴起的沿海城市,而其南部则变成了一潭死水。“这是中国的一个地区从在这些旧网络中担当至关重要的地位,向在新的、更强大的网络中沦为边缘性地位的痛苦演变的过程”(“导言”第2页)。随着交通设施的现代化,黄运的地位反而下降了,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这颇有点吊诡的味道。我觉得,对此的解释或许是:尽管从经济学上讲铁路的效率更高,但因为它是为沿海经济服务的,从而没有像大运河那样为黄运地区运入木材和石料,以维持该地区脆弱的生态平衡和解决当地人民的生活难题,它也没有能舒缓当地因人口密集造成的失业问题,等等。④
随治国方略突变而来的是资源的转移和重新分配,资源向较为富裕的而又直接面临列强威胁的沿海地区倾斜。“维持黄运的基本事务变得无关紧要了;通过从国外为它运来商品(如木材)或服务(如水利规划)来缓解这类次优地区的困难,实际上具有危害(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作用”(“导言”第4页)。实际上,国家财富再分配的方向正好被颠倒过来,从“通常要求富裕地区接济较为贫穷地区”,转变到“放弃黄运而把财力集中于更容易改变及通常更富裕的地区”,并“鼓励某些地区‘先富起来’”(“导言”第3页,第120、307页)。这里仅以漕运为例。在彭著中,停罢大运河漕运,既是转变治国方略的关键决策之一,又是黄运的经济和政治走向衰败的直接原因。该书写道,虽然为北京供粮,“与那些为了供应马德里、柏林和其他较近的周围地区无法提供粮食供应的首都的情形极为相像”,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确实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并“需要剥夺巨大的区域”。“明清的经世方略……如果有某些地区被牺牲的话,那么,这些地区应该是江南和其他富裕的南方地区,这些地区为运河承担的漕运体制付出了代价”(第129页)。然而到1850年前后,一方面,海运和东北粮食生产的增长为“改漕”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治国方略的突变为此提供了必要性。不过,裁撤耗资巨大的漕运,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合乎“理性”,因为这种改革的“结果却是在黄运造成了每况愈下的政治分化,既使这个地区、也使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193页)。据此可以说,自强战略事实上产生了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清政府把江南地区(及其他富裕地区)从资助更贫穷地区的使命下解脱出来,而民国政府则采用了“淘汰失败者”的政策,这一政策颇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味,只是它通常用于种族、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这里却用于国内。彭氏在“中文版序言”中表示:《腹地的构建》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经济财富方面的地区性分化。他认为,尽管中国历来就存在着较富和较穷的地区,但沿海与内地之间的鸿沟在近代日益扩大,其原因之一便是支持沿海、损害内地的政治经济战略。
优先发展沿海的新国策给近代黄运民众福利造成损害最大的是水患,因而,晚清、民国政府将治水资金挪作他用便成为其最大“恶政”。彭著指出,政府所面临的侧重点和压力改变了,于是,河务资金被挪用到其他事情上:在长江下游地区减税,编练新军,对外赔款以及北京和天津的现代化项目上。“毫无疑问,政府的资金从以内地为中心的水利方面大量转移到了以沿海为中心的其他项目上。”他又写道:“自1855年以来,水利问题不断恶化,但并没有变得不可收拾。变化最大的是国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兴趣,以及面对这些问题,它为了治水而使用其收入的程度”(第173、180页)。据彭著,1890年以后,政府治水支出急剧减少。河南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山东在19世纪80年代,每年的常规开支达200万元以上,到20世纪20年代,河南、河北、山东三省加在一起才117万元。黄河的大修更是花费惊人:“大体上每隔20年黄河就要作一次大的维修,通常要花费巨额的资金。早在1815年,仅河南睢州一地的工程就几乎花费了560万元……1888年,黄河在开封决堤后,仅河南一省的维修费用就花费了1544.4万元……不过,1890年以后,像这样的大修只进行过一次”(第177—179页)。据估计,在山东,漕运废弃后大运河治理费用的预算从白银16万多两削减为7.5万两;1894-1900年,黄河的治理费用每年为99.2万两,1900-1906年每年为67万两,20世纪20年代再减为37万余两。河南方面,道光年间每年为150万两,清末降为43.2万两(第169—173页)。中央政府的情况甚至更糟,其治水费用在1850年以前占总支出的12%,1850-1900年下降到3%,1905年再降为1.38%,几乎降了9/10(第179页)。
中央政府“向沿海倾斜”的政策转向自然引起了从晚清到民国内地地方官员的不断抱怨和抵制。1905年,河南巡抚陈夔龙甚至直言清廷的资金转移政策是用内地的血汗来资助沿海的发展。然而,以内地民众福利为代价来追求富国强兵是时人的共识,岂止中央,各级政府莫不如此。如在山东,就是将越来越少的公共水利资金集中用于它认为最需要的地方——本省东部沿海。1891年后,在仍由政府负责维护的1256里的黄河堤坝中,有约5/6位于济南以东,这些河段仍旧作为官堤,政府通过征调民间劳役及原有的河营进行维护,工程资金则来自国家预算;而黄运地区的大部分河段被认为是最不危险的,改为民堤体制,政府抽身退出,把沉重的治理水患的“包袱”留给了当地民众。实际上,许多靠近黄河河口的县——利津、滨县等—与黄运一样贫穷,因此,指责近代中国政府“嫌贫爱富”是将问题简单化了,正如彭慕兰所说:“资金从上段(指济南以上的黄河河段)大量移入下段,与国家在靠近最受威胁的沿海地区保卫其主权的自身利益的关系极大,而受这些沿海县份任何特定阶层的影响极小。”“山东河务局侧重于靠近沿海和与津浦线交界的地方的黄河治理,似乎可以归结于担心被外国人所越俎代庖……总之,民族主义、竞争的出现和沿海经济所造成的机遇,合起来使政府全力以赴地重视靠近沿海……的水灾治理。不过,黄运却没有这些推力;结果,政府从这个曾经偏重的地区撤走了它对水灾治理的许多资助,并把这些资金用来发展靠近沿海的地区。随着资金方面出现的这种变化,水利问题也重新分布了”(第223、306、230—232页)。
上引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它提示我们注意到在山东的两个同时进行而方向相反的运动:资金从西部移到了东部,但水患却从东部移到了西部。对此,彭著在第162页讲得更为明确:“19世纪末强加在水利体制上的经费削减和制度性的变化,不仅把治水(特别是黄河的治理)的负担转移到、而且把水患问题本身从靠近沿海的地区(及后来靠近铁路的地区)重新分布到济南和北京均认为较不重要的内地地区。”在彭慕兰看来,“更少的支出几乎总是意味着更多的水灾”,因此,在第163页他的评论甚至有些尖刻:“19世纪90年代的‘改革’对剩余的河务资金和人员不是按照减少水患、而是按照改变水患发生地的方法进行了重组:水患问题在极大程度上从更受重视的地区被重新分布到了黄运地区。”
近代新治国方略那“进步”的光环消失了,与此相对应,传统治国方略也不再是蒙昧愚腐、顽固不化的形象。彭氏认为,数百年来,传统国家为维持较为贫穷的鲁西地区的中心地位,曾长期施行挹彼注兹的政策,尽管治理黄河与大运河要花费巨额公帑,而其目的是保障京师的粮食供应,并不是黄运当地人民的福利,从而“提醒我们不要把它的动机过多地描上玫瑰的颜色”,但这毕竟在客观上具有在地区间“均贫富”的效果,“是在400年的时间里让富裕的南方地区承担维护像黄运这样较贫穷地区的全面生态平衡的代价”。为进一步说明传统国策的这种客观效果,彭著中还举了其他证据:“例如,对军费支出的重新定向,在明朝和清初,军费主要花在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边界地区,并伴随着促进粮食贸易和以别的方式稳定西北生计的尝试。在新时期中,对中国的威胁来自沿海地区,军费主要花在创办一些现代军队和江南、福建沿海、京津地区及其他东部核心地区的军事工业方面”(第130、308页)。
军费支出也好,水利支出也罢,似乎都表明彭慕兰是在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现代化的实际历史进程。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出不应用“二分法”来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我曾对此深感疑惑,因为现代化在中国造成了有目共睹的巨大变化,如果不讲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又能用什么来区分呢?现在,《腹地的构建》就提供了一套新的区分标准。我大概归纳了一下这两种视角的几个基本差异。
第一,“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历时”的视角,现代化进程被看作以今代古,而今古不能并存,传统国策转变为自强国策也被看作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它虽然也承认新旧并存,但这只是过渡阶段的暂时现象,改革或革命、变化或转型,均终有完结之日。而在彭氏那里,“传统”与“现代”却成了并存于“共时”结构中的不同组成要素。彭著曾批评说:“通过忽略某些国家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不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现代化理论未能看到这两种现象都是现代世界构成部分这样的事实。同样,杜赞奇……未能看到不同的亚区域是沿着不同的方向在运行,某些地区的成功与其他地区的失败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第210页)。彭氏在谈到他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异同时也承认,自己“采用了这两种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见解:不同于认为某些国家(或地区)已经‘现代化了’,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则没有,我们必须记住富裕和贫困地区都是现代世界的组成部分,一个地区的飞速发展可能造成其他地区的停滞或恶化。”也就是说,某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加剧了其他地区的“落后”(“导言”第27页、“中文版序言”第7页)。简言之,在“历时”视角看来是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而在“共时”视角看来则变成了强大与弱小,中心与边缘。
第二,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内地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暗含一个假定:现代化是一个从中心向外围呈梯次扩散的累积过程,沿海率先富裕,然后内地再跟上来,共同富裕;这种“有先有后”并不是要以内地的不发展为代价,而是由于国家财力有限,说到底是由于现代化进程客观的渐进发展规律。然而这个当代的理论却似乎不甚符合1850-1949年在中国实际发生的现代化进程。在彭慕兰笔下,黄运等腹地并未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展而结束衰落走向繁荣,虽然它也取得了棉种改良之类的成就,但其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日渐扩大。⑤这尚在其次,在我看来,更为关键的是,他区分了“不发达”(或贫穷落后)与“腹地”这两个概念。这样的看法与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及德里克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解释类似,他们都认为,不是说腹地(或边缘地区)不能实现现代化,而是说即使全球都实现了现代化,中心/边缘结构仍将持续,二者的矛盾及边缘地区的相对贫困化仍不会消除;即使旧的腹地变成了中心(如今日之东亚),仍然会有新的腹地出现。所谓的“现代”与所谓的“传统”共同构建了现代中国与现代世界。
第三,“现代化理论”往往以西方为“正道”,以所谓“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为“歧途”。而彭著似有多元主义的意味,各国各地区不分正道歧途;与彭慕兰持相似观点的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亦曾提出,在做中西比较时,可以中国为“经”,以西方为“变”。
第四,“现代化理论”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极度富裕、文明、民主、自由的未来社会,一个尽善尽美的愿景。而彭慕兰、柯文、杜赞奇等学者似乎认为,尽管依据某些客观指标(如GDP或人均寿命),社会的财富将大大增加,人类的知识将大大增加,但“自然的报复”也将随之而来,矛盾和冲突也不会减少;甚至在亨廷顿看来,战争是否会减少亦在未定之数。
我认为,虽说上述看法确有值得我们深思之处,但其中或许也存在偏激的东西。另一方面,“历时的”普世主义视角并非一无是处,而其正确的地方正是柯文等学者失误的地方。
首先,这种观点否认或过度淡化中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巨大变化,用一句柯文和冯客都曾引用过的西方学者的话来说,西方对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冲击,只不过是“大象耳朵里的一个跳蚤”。由此,他们进而忽视近代中国人(不仅是精英,而且包括广大民众)对于现代化的追求。然而历史事实是,且不说近代中国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至少从曾惊呼“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在为适应这个新世界而致力于改造中国。
其次,与淡化近代中国变化相对应,一部分西方学者着重在前现代中国(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历史中探寻近代中国变化的起源。描述清中期华南的军事化与揭示明清时期市民社会的萌芽,都属于这一类努力。但前者至多只能解释中央政府合法性的丧失与地方精英权势的增长,却根本无法说明那些“史无前例”的“西方化”或“世界化”的新事物;后者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就像“自由”、“民主”一样完全是西方概念,其与中国历史不啻南辕北辙。
再次,另一部分西方学者采用“多元主义”的观点,力图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明近代中国的动荡只不过是数千年来循环上演的一幕而已。这实际上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观点,即文化本质决定着历史命运。这种多元主义与普世主义虽有诸多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普世主义认为历史将殊途同归(只有一个归宿),这种多元主义虽认为“殊途异归”(会有多个归宿),但二者均认为这个“归宿”,或曰历史的终点,是确定的或宿命的,人只能顺应它。在我看来,这种对历史的看法并不正确。人当然受传统的影响,但传统并非固定不变之物,而是不断被人们的社会实践所重建,这就是所谓“发明传统”。更为重要的是,人们重建传统的实践受到其动机的指导,即离不开他们对未来的筹划,且这种筹划和对未来的追求是变化万端的。上述这种文化本质主义还有实际操作方面的困难,即人们难以依据其空间范围确定其历史变化的未来方向。
我通过对上述几种西方理论的批评得到了两点认识。一是每一种与现代化有关的历史理论都是从特定的视角去观察实际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就此而言它是有效的;同时,也正因为如此,其解释范围也必定是有限的,不可能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和史料。后现代理论的出现尽管在时间上晚于“现代化理论”,但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解释后者解释不了的史实,而后者在其解释范围内依然有效。
二是几十年来“现代化理论”被当作惟一的对现代化进程有解释力的理论,从而遮蔽了构建其他理论的可能性,这种局面应当改变。在我看来,“现代化理论”从时间的角度切入现代化进程,因此使得中国现代化史具有单线的、直线的性质,历史相应地也就只有两种趋向:进步或倒退。与之不同,若从空间结构的角度切入则可以展示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如中/西的或西方/非西方结构划分,再如种族、民族、文化、国家、地区间的对立统一或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的对立统一,当然也可以是多中心或无固定中心的。此外,人们在运用“现代化理论”时往往将韦伯的“理想类型”当作现实样板,这一点亦应改变。20世纪50年代曾流行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近三十年来,在一些人的心中(未曾说出来)也有一句话: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怎么可能呢?中国能变成美国吗?美国的明天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总之,“现代化理论”有其用处,但也有其局限性;其他理论自然亦如此。进一步说来,甚至现代化本身也是这样,它解决了一些老问题,又制造了一些新问题,但更为基本的问题,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并未解决,只是变换了表现形式。现代化实现之日并不是历史终结之时。
注释:
①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马俊亚、徐秀丽、王也扬诸教授曾对拙文提出很中肯的意见,特此致谢。本文所引用彭著文句的页码均注在文内。
②彭著涉及问题甚多,由于篇幅所限,拙文只谈这一个问题。另外,该书出版后,海外学者曾有不少评论,但由于知识背景及关注角度的差异,在我看来,对国内学者的帮助不大;而在国内,据查“中国知网”,真正的学术性书评仅见译者马俊亚发表在《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上的一篇专文。
③马俊亚先生认为,淮北(包括鲁西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已经被中央政府边缘化了。但我觉得,马先生的“边缘化”的含义与彭著有所不同:第一,彭著中的边缘化是“国策”的转变,而黄河“夺淮”入海似没有这种意味;第二,在彭著中,边缘化是国家现代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马先生那里,其与现代化无关。
④这也提示我们,尽管有不考虑政治和社会因素的纯粹经济学,但却没有这种纯粹的经济史;历史上曾经实际发生过的经济活动,总是要“嵌入”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之中的,经济活动总是与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纠缠不清。
⑤王也扬先生在审读拙文时指出:“中国近代由重‘黄运’到重沿海,实际上是早期‘全球化’(或曰野蛮时代的‘全球化’)列强东侵的结果,也是清政府一种被迫的政策改变,不得已而为之的拆东墙补西墙,当时似还来不及作出更长远的‘先富带动’之类战略设想。洋务、维新思想中有民富带国富思想,至于‘沿海带内地’思想,我印象不深,即使有,也没有成为主流。不要把历史问题与现实政策简单重叠。”我完全接受他的最后一句话,即“自强战略”的含义是与时俱变的;我也承认,在19世纪中期,清朝的决策者恐怕尚未想到“先富后富”之类的问题,也许直到半个世纪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流行时,“种族竞争”、“赶超欧美”之类的说法才被提了出来。另一方面我还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中,含有不少“先富带动”之类的设想;而研究者的这些设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史被书写出来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