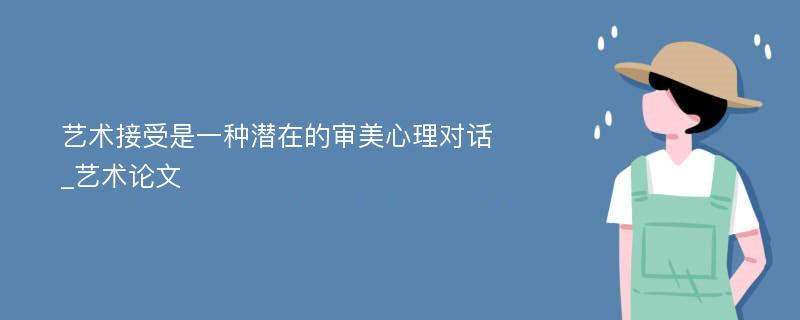
艺术接受是潜在的审美心理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艺术接受活动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一种高级的复杂精神活动,它有着深层的审美心理动因。探讨艺术活动的心理动因已成为现代艺术心理学的重大课题之一,不少理论家都在深入探求是什么样的心理因素激发一个人去凝神欣赏文艺作品?一代又一代的艺术接受者为什么痴迷沉醉于那些并不直接关乎物质生存的艺术幻象?这仅仅是饭饱茶余之后的遣兴消闷还是有着更深的动机、需求?在此不必罗列对这一问题的种种分歧的解释。我们认为,虽然就具体的艺术接受来讲,其动因和目的的表现形态固有不同,对艺术作品意味层次的把握亦有深浅差异;但是,整体说来艺术接受者的鉴赏欲望和趣味都深深植根于人类的审美心理需要,系源于人类对于审美情感和艺术生命及其意味的审美交流的需要,——这是一种对于生命情感形式的审美心理沟通和潜在的审美心灵对话的欲求和愿望。人类社会的艺术奇葩之所以永不凋谢,人类对于艺术的眷恋、追求之所以执着而永无止境,正在于人类对于生命情感和艺术意味交流的渴望和需要日新月异、绵延不绝。自然,我们把艺术接受活动与满足人类的审美心理交流和潜在的审美心理对话这一需要联系起来,是从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侧面来看待艺术接受活动的。我们把艺术接受活动与人类一般的生理—心理活动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地加以考察,旨在指出艺术接受活动在实质上是一种审美的心理活动,是人类所具有的高级复杂、幽眇深邃的精神现象。由此,我们在另一个层面上揭示出作为审美心理交流的艺术接受活动所呈现出的独特形式:潜在的审美心理对话。本文试就艺术接受的独特形式问题作一深入探讨,以就教于同行专家。
当我们把艺术接受作为审美心理交流活动来看时,实际上已把它看作是一种审美心理对话。交流的需要是以交流的方式来满足的,交流意味着双向的对话和沟通。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艺术接受者在艺术活动中,都处于不同的相互对话之中。法国作家缪塞谈到他的创作体验时说:“你要知道,当手在书写的时候,是心在说话、在呻吟、在融化;是心在舒展、在流露、在呼吸”〔1〕。 艺术家的创作起于深层的审美心理交流的需求,又弥漫在与自我、与艺术角色、与读者、观众进行或断或续、或强或弱、或缓或急的对话氛围与洪流之中。美国作家海明威把这种状态称作“恋爱的时候”,“犹如你已经向你所爱的人倾诉爱情一样”〔2〕。在这种氛围之中,艺术家倾听、谛视、诉说、回答。 当这种状态和氛围消失时,艺术家的创作也就中止或完结。如果说艺术家的创作是在审美心理对话的氛围和活动中进行的,那么,艺术接受者的欣赏活动也不仅仅是接受;作为审美交流的一极,他的欣赏活动也是在审美心理对话的动态过程中展开的,“如果用M.M.巴赫金的习惯术语来说,对艺术的知觉,按其纵深的、特殊的本质而言,是对话性的。”〔3〕
问题在于这种对话的心理机制何在?为什么我们不泛泛地把艺术接受作为仅仅“接受”艺术家所传达的信息而把它看作是一种审美心理的对话?从社会心理学所揭示的人类交流理论中,我们可以窥测到艺术接受的实质及其深层机制。
研究人类交流的理论把人际沟通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信息的传递;一类是相互交往。前者表现为单向的和非对称性的,后者则是多向的和对称性的。如果说在信息传递形式中的双方中,一方是主体,另一方是客体的话,那么,在相互交往形式中,每个参与者对于对方来说都是主体。也就是说信息的传递是主体同客体之间信息联系的形式,而相互交往则是主体同主体的联系,是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这种联系方式的不同,人所处的位置、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在相互交往形式中,由于人们处于主体地位而具有能动的作用;在信息传递形式中,由于接受者处于客体地位,其作用就仅是接受、理解主体所发出的信息。按照前苏联美学家卡冈的说法:“当一个人积极地、目的明确地、自由地、有选择地和反思地(即自我意识地)行动时,他起主体的作用;而当他行动消极(或者他的积极性是为了准确理解向他发出的信息而压抑自己),当他只完成对方的指令,而不是自由地选择行为的目的和方式时,他就成为对方行为的客体”〔4〕。事实上, 人在现实中是既处于主体又处于客体的地位的,尤其是在大量的学习活动、社会组织活动中更是处于这种接受的客体地位。“而在艺术中,我们碰到的是艺术价值的创造者和接受者的另一种类型的联系。”〔5 〕这种联系使艺术进入人类相互交往和对话的范围,使它同信息传递的任何方式在本质上区别开来。对于艺术家来说,他是把作品的角色、作品的接受者作为在心理上具有亲和性的主体;而对于欣赏者来说,他是从自己的心灵世界出发同艺术家、作品进行独特的对话活动。接受者之所以拒绝任何抽象说教的作品,其深层心理正在于这些作品的制造者蔑视乃至否定艺术接受者的主体地位,破坏了审美心理对话的亲和性、能动性。“只要读者或者观众发现小说、戏剧、绘画的作者企图指教、教诲和训导他,真正的艺术知觉氛围就遭到破坏”〔6〕。 而那些以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和心理个性来唤起接受者的心理体验并与之对话的艺术家才能受到艺术欣赏者的青睐和共鸣。鲍列夫认为这样的艺术家有一种“向亲密的人倾吐自己的深切感受或强烈印象的愿望”〔7〕。 这无疑揭示了艺术活动的心理对话性质。当然,艺术活动中的心理对话究竟不同于普通的相互交往中的那种对话关系。人们之所以不满足于普通的相互交往并追求着艺术中的心理对话,是因为艺术的对话活动是审美心理交流的形式。另外,现实的相互交往和心理对话,在许多方面有其本质的、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囿于生活的空间、时间、容量和选择可能性,人们不可能自由地、无拘无束地进行心理的沟通,满足“披露心曲的需要”〔8〕, 或领悟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就在这时候,艺术的交往前来帮助现实的交往:在艺术中我同生活在彼地、彼时的艺术家和人物交往,因为艺术交往在想像中展开,它使人摆脱空间和时间的桎梏,……而且,艺术使人的关系摆脱偶然性的控制,让每个人在无限的艺术世界空间里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的朋友。”〔9〕我们同莎士比亚、但丁、托尔斯泰、曹雪芹、贝多芬、 柴科夫斯基交流;同蒙娜丽莎、卡门、克里斯多夫、卡拉玛左夫兄弟、斯梯芬和布鲁姆交往,同所有的艺术家和艺术世界中的角色进行心理对话与沟通,全身心地亲历人类总体的精神历程,把自我融入人类的审美心理洪流,从而达到对社会人生、文化心理、未来永恒的无穷意味的沟通与感悟。
如果说在人类交往的宏观范围内可以确立艺术接受的心理对话实质,那么,在具体的接受领域,艺术欣赏者所扮演的特定角色及其效应则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艺术接受的心理对话的内涵。艺术活动内在地要求艺术接受者扮演一个相应的角色,期待着他以相应的审美心理加入到艺术活动中来。波兰的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加登在晚年曾把艺术创作活动与艺术接受活动联系起来考虑〔10〕,在他看来,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在艺术活动中都处于一定的角色地位,创作和接受作为一种交流和沟通“都存在被动与接受的阶段,即理解与接受的阶段,也存在主动的阶段,即超越已给定的东西,产生从前并不存在、由艺术家或观赏者真诚创造的新东西的阶段”〔11〕。这无疑是说,艺术创作并不是总是主动的,而艺术接受亦非完全被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乃是整个艺术活动的特定角色,它们处于相互适应和相互克服的交流与对话的关系之中。对于艺术接受者来说,他总是被邀参加到艺术创造的活动中来,他的角色作用是活跃的,有时甚至是难以捉摸的。美国的杰·威廉斯不无感慨地说:“观众就是神秘的所在。没有人能确切懂得观众是什么,但是一出戏的诞生却非得有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心理上的,也许还有精神上的情感交流才行。”“每一出戏在观众面前演出时,未知的和心理上无法预料的可变量实在太多了。”〔12〕艺术接受者是一个最活跃而又无法预测的因素。在艺术接受中,接受者一方面把作品中的形象和情节“移植”到自己的独特生活境遇中来,把主人公与接受者的“自我”同一化,另一方面,又与人物对立并把他视为“别人”。鲍列夫曾把这种现象归结为艺术的表演性。他认为:在文学欣赏中,欣赏者兼具表演者(“自我表演”)和接受者两种身份。〔13〕正因为艺术接受有这种机制,接受者才有可能在艺术接受中扮演特定的角色。也正因此,艺术接受者的角色效应和对话过程才显得举足轻重。正如美国的戏剧理论家巴斯费尔德所说:“观众的情绪、兴致、笑声和眼泪,都是戏剧动作的一部分。”〔14〕如果接受者未能或不愿成为对话的角色,仅分配给他一份责任,演出就会成为碎片。当然这种角色效应和对话性无论是对艺术家还是接受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说艺术家应当像契诃夫所说的那样,“不应当把果戈里降到人民的水平上来,而应当把人民提高到果戈里的水平上去”〔15〕,那么,接受者则不能仅仅追求简单统一的角色对话。正如悔特克林所说,这种对话“不像我们以前曾经听见过的东西,因为诗人已经把内在和外在的对话熔铸在一种表现之中。……其中所说的一切既隐藏着又宣示了未被认识的生活和宝藏”。所以,接受者更应期待那些“我所不认识的存在、力量或上帝与我同处于斗室之中。……某些更高的生活以奇异的刹那在我尚未觉察的情况下忽然掠过我最惨淡的时刻”。〔16〕
我们的上述讨论已经涉及到心理对话的另一个问题,即艺术接受者同艺术家、同艺术世界的角色所进行的对话和交往并非现实的、真正的“对话”和“交往”,而是一种潜在的审美心理对话。卡冈称这种对话为“准交往”,“因为它仅仅在我们的想像中展开,用心理学家的术语来说,仿佛是一种‘自动交际’;或者用K.C.斯坦尼拉夫斯基的术语来说,是一种‘自我交际’”。〔17〕
艺术接受之所以是一种潜在的审美心理对话,是因为它在审美心理体验的基础上进行。对于接受者来说,这种审美心理体验超越了现实功利的单维情感,调动起多种审美心理功能共同活动,把艺术家的情思意绪和审美创造在内心深处弥散、交融,从而达到一种潜在的心灵沟通和内在的自我交流。这种审美心理体验又要求艺术接受者同与之心心相印的审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潜在对话的又一层意思。审美体验中的心理对话并不表现为积极的行为,而是表现为艺术的深层感受。1909年美国芝加哥歌剧院所发生的枪击演员威廉·勃茨的事件并不是真正的审美欣赏〔18〕,相反,现实的冲动代替了潜在的审美心理对话。前苏联艺术心理学家维戈茨基说:“读者从两个方面观察悲剧:一方面,他通过哈姆雷特的眼睛察看一切;另一方面,他又用自己的眼睛察看哈姆雷特,所以,每个观众既是哈姆雷特,又是他的观察者。”〔19〕这段话说明,审美心理对话是在接受者心中发生的“自我交往”和“潜在对话”。在艺术接受中,接受者一方面要投入艺术的世界,成为艺术创造的合作者,另一方面又要沉潜于审美体验的潜在对话之中,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二律背反。然而,正是这种矛盾的统一才赋予艺术接受活动以极大的主动性、创造性,给艺术接受者带来独特的人生体验和丰富深刻的审美愉悦,从而使审美交流活动和潜在的心理对话具有自己显著的审美特征。
首先,审美交流活动和潜在的心理对话是一种通过审美体验进行的非语言信息沟通的高级的潜在对话。人类的交流与沟通通常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语言信息沟通,另一种是非语言信息沟通,即所谓“有言之辨”和“无言之辨”。语言信息沟通以自然语言为媒介,非语言沟通则不以自然语言为媒介。在一般交流活动中,人们往往程度不同地交互使用这两种语言方式,两者可以相互渗透和补充。但语言信息沟通和非语言信息沟通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一般说来,语言信息沟通表达人们的逻辑推理过程,而非语言信息交流则“反映了我们所讲的含义的‘无穷无尽性’。它超越了语言的范围,变成深不可测的感觉和感情,因而不容易用语言来描述”〔20〕;另一方面,语言信息传递只经过一个通道,按照字、词、句的顺序发生作用,而非语言信息的相互交流则是多通道的,可在瞬间作用于人的视听触味等多种感觉和情绪,因而常常使人回味、体验、心领神会。按照苏珊·朗格的观点,艺术是一种区别于推理符号的表象符号,前者着意于指示功能,后者注重表现功能。指示功能虽然具有直指性、明晰性特点,但却因而难以表现出对象的丰富性和寓意性,而艺术符号的表现功能却能够克服这种局限,如庄子所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21〕审美交流活动和潜在心理对话所沟通的,正是具有表现性的非语言信息。作为高级的非语言信息沟通,其特征在于交流审美的情感和艺术的意味。这种审美交流的特性内在地要求接受者通过领悟和体验而达到心灵的沟通,因而我们说审美交流是通过审美体验进行的非语言信息沟通和潜对话。当我们面对并吟诵法国现代象征诗人瓦莱里的诗歌《棕榈》时,也许会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幅耸立青天、甘实盈枝的棕榈树的画面,它交织着青天、绿丛、白鸽和少妇的明媚色彩;也许会在震颤的心灵里久久回荡着一种呼唤:“忍耐着呀/在青天里忍耐着呀!/每刹那的沉默/ 便是每个果熟的机会!”这是久候的爱情,还是艰辛的困劳?棕榈的沉毅在灵魂里荡漾出几许情愫?你尽管去感受、体验,在含蓄而深长的诗节中,从绚丽的声、色和跳动的节奏里与自然、生命沟通,与灵魂、宇宙对话。“我们读他底诗时,我们应该准备我们底想像和情绪,由音响、由回声、由诗韵底沉浮,一句话说罢,由音乐与色彩底波澜吹送我们如一苇白帆在青山绿水中徐徐前进,引导我们深入宇宙底隐秘,使我们感到我与宇宙底脉搏之跳动——一种严静、深密、停匀的跳动。”〔22〕
其次,审美交流和潜在对话是接受主体心理诸功能的整体直觉。接受过程中的审美体验既是对于审美符号的感觉和体味,就必须与接受主体丰富的审美心理需要和复杂的审美心理机制相联系。与现实的或单方面的意识交流活动不同,审美对话包含着主体的心理因素,诸如感觉、知觉、联想、想像、情感、意志、灵感、思维、意识与无意识等丰富的审美心理因素。在整个接受活动中,各个因素彼此之间并非单独地、孤立地起作用,而是在相互的渗透、补充、综合、交叉的整体中起着一种复合作用。这是审美交流和潜在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正如卡冈所说:“一个人在阅读小说、观看戏剧、电影和绘画时,在心理上移居到艺术家在他面前展开的幻想的形象世界中去,以自己整个精神世界——想像、体验、思考、回忆和预感的力量——沉溺于其中,开始同自己的角色——奥赛罗和苔丝蒙、奥涅金和达吉雅娜、别谢梅诺夫或图尔宾家族……一起在这个世界中‘生活’”〔23〕。这种综合心理功能的特征是和审美交流的独特本质,即形成“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马克思),从而超越单一的生理需要和功利需要相联系的。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通过幻想,交流和沟通生命的情感与艺术意味,它在直觉过程中把人的心意诸力激活,使其丰富、充实、秩序化〔24〕。这无疑精辟地阐述了审美交流和潜对话的特殊性。人们都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有一种销魂的魔力,那便是永恒的微笑。然而,这销魂的魔力和神秘的微笑究竟从何而来?它给予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当我们凝神观赏这幅绘画杰作时,一种莫测高深的神秘震颤了我们的整个心灵,那浮动着生气的轮廓,细腻妩娇的笑容,无数细致的衣褶,美丽圆润的手以及笼罩在烟雾之中的青绿色风景,在我们的心灵中展现了多少细致的感觉、丰富的想像和无尽的回味!至于那多少蒙了一层惆怅情绪的似笑非笑的颜面,又给予我们何等微妙的情绪感受。“你悲哀吗?这微笑就变成感伤的,和你一起悲哀了。你快乐吗?她的口角似乎在牵动,笑容在扩大,她面前的世界好像与你的同样光明同样欢乐。”〔25〕在整个心灵的自由体验中我们全身心沐浴在审美交流和潜在对话的氛围之中。如果说这幅画能牵动我们的种种心理因素,那么当我们倾听莫扎特的《安魂曲》、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阅读歌德的诗剧《浮士德》、济慈的《秋颂》等作品时,这种体验就更为突出了。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直接诉诸我们底整体,灵与肉,心灵与官能的,它不独要使我们得到美感的悦乐,并且要指引我们去参悟宇宙和人生底奥义。而所谓参悟,又不独间接解释我们底理智而已,并且要直接诉诸我们底感觉和想像,使我们全人格都受它感化与陶熔。”〔26〕这又涉及到审美交流和潜对话的另一特征。
第三,艺术接受活动作为审美交流和潜对话具有创造性和超越性相统一的特征。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像言语过程一样,艺术过程是一个对话的和辩证的过程。甚至连观众也不是一个纯粹被动的角色。”〔27〕审美交流和潜对话在审美体验过程中进行,“而审美体验有显著的主动性、拓展性、创造性特点,……审美体验是以过去的审美经验为基础而又超越它进入现时情景之中,并在现实氛围中直接悟到永恒和未来,这是一种过去、现时、未来的瞬间合一。”〔28〕在整个审美交流活动中,接受主体处于感受、创造和超越的统一之中。接受者拥有“创造性的想像力和反映力”〔29〕。这是审美交流活动中的一种重要心理机制,用康德的话说,“鉴赏是关联着想像力的自由的合规律的对于对象的判断能力。”〔30〕他对创造性想像这种心理功能在审美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具有重要意义。艺术接受离不开创造的想像,虽然接受者是在再造想像基础上进行审美交流,但他不只是简单的接受,被动的复制,或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情感记忆去补充、领会;它与面对的审美世界有着相互作用的特殊关系,同艺术家更是一种“共同创作”〔31〕。中国古代诗论、画论中强调的“超于象外”、“神游象外”、“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等,都是把创造引伸到接受,把创造性想像赋予接受者。一篇《锦瑟》之所以众说纷纭,乃在于接受者在审美交流和潜对话中创造出无穷的想像境界。温克尔曼能从一座残存的赫刺克勒斯雕像(只余躯干)中想像出完整的大力士形象,体味出丰富的艺术意蕴,正赖于审美交流的创造。〔32〕只有这种想像的创造性特点才使审美交流和潜在对话具有独特性、鲜明的个性和生动的体验性。另一方面,审美交流活动作为一种双向的心理对话又是接受者在创造性的审美体验中自我升华与超越的过程。艺术交流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情感体验(如托尔斯泰所认为的那样〔33〕),正在于它是普通情感的超越与升华。维戈茨基不同意托尔斯泰的艺术交流说,“诚然,如果艺术除了以一个人的情感去感染许多人而外别无其他任务,那么它在生活中的境状将是多么凄惨。……因此艺术的真正本性总是包含着改变和克服普通情感的某种东西”〔34〕。审美交流是对双方“自由的情感的拓展与深化”〔35〕。它表现为在创造中使身心净化、提升,“艺术仿佛来补充我们的生命,并扩大它的可能性”〔36〕。总之,艺术交流和潜对话的创造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特征是审美心理沟通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的,它“从整体上正视个人的存在,正视个人在行动和激情上竭尽全力的全面发展”。〔37〕
注释:
〔1〕《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 中国社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
〔2〕《冰山理论:对话和潜对话》(上),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65、63页。
〔3〕〔4〕〔5〕〔6〕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55、252页。
〔7〕〔8〕鲍列夫:《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04页。
〔9〕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256页。
〔10〕英加登早年主要把精力投入研究文学本体论方面,重点放在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认识论和价值论上面。
〔11〕Journal of Ase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75春季号。
〔12〕《论观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
〔13〕鲍列夫:《美学》第313—314页。
〔14〕《作家是观众的学生》,见《论观众》第113页。
〔15〕《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
〔16〕《给观众以启示》,见《论观众》,第73~74页。
〔17〕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254~255页。
〔18〕这是指在上演悲剧《奥瑟罗》时,一位观众开枪打死扮演埃古的演员,参见鲍列夫:《美学》第321页。
〔19〕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20〕《传播学概论》第76页。
〔21〕《庄子·秋水篇》。
〔22〕梁宗岱:《诗与真》,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
〔23〕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175页。
〔24〕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6页。
〔25〕傅雷:《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8页。
〔26〕《诗与真》第107页。
〔27〕《人论》第189页。
〔28〕胡经之:《论审美体验》。
〔29〕《情感与形式》第461页注〔1〕。
〔30〕《判断力批判》(上),第79页。
〔31〕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223页。
〔32〕《美术史文选》第66~68页。
〔33〕〔34〕〔35〕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第322~323、328页。
〔36〕〔37〕《情感与形式》第468页、4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