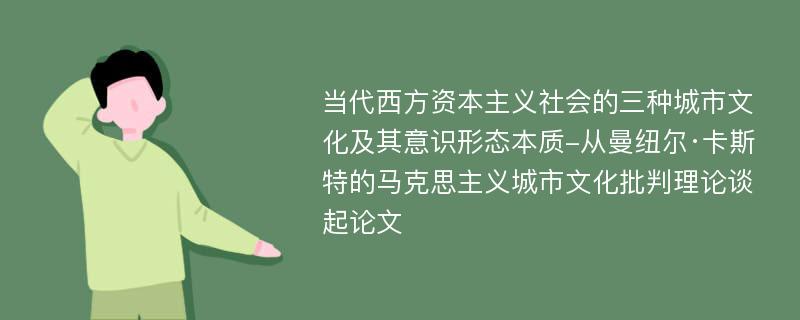
栏目主持人:吴向东
主持人话语: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总体起步较晚。它是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实践的呼唤与西方城市社会理论的接纳和冲击共同促成的结果。就当下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理论研究有必要加强学科交叉,既要注重对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地方城市的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又要注重对城市文化理论、社会空间批判的元哲学资源的利用与深耕。如此,才有可能构建出一种科学性、严密性与包容性、开放性相统一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才能够在元理论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性的学科架构上为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学科做好充分的准备、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期的几个选题既有对西方主流城市文化叙事的批判,也有对新时代城市发展问题转换的回应;既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也注重从逻辑谱系维度上审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颇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城市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本质——从曼纽尔•卡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批判理论谈起》基于曼纽尔•卡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批判理论,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城市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本质进行了详细深刻的论述。《论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研究理路:回到马克思“资本批判”原初语境》力图以更加积极、更有效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的研究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论城市哲学视域下〈共产党宣言〉文本中的历史逻辑与阶级意识》逐一阐明了《共产党宣言》中所包含的城乡分离、城乡对立、以及阶级对立等城市哲学论题,在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程中寻找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全新方案。《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一个逻辑谱系维度的审视》从逻辑谱系维度上审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实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推动城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发展。
主持人简介: 吴向东,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城市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本质
——从曼纽尔·卡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批判理论谈起
温 权
摘要: 在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激进语境中,检视西方城市文化的意识形态内涵,是曼纽尔·卡斯特体认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症候的重要出发点。藉此,他先后归纳出三种与当代资本生产与积累模式相呼应的主流文化形态,并分别对其作用机理和政治效应进行了详细地分析。首先,是由资本新自由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共同催生的精英政治文化,对城市发展路径和大众交往秩序的排它性宰制;其次,是与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和社会财富区域性集中密切相关的社区隔离文化,对城市规划格局和个体空间身份的碎片性修饰;再次,是受资本知识更新机制和信息传播媒介深刻影响的网络虚拟文化,对城市社会经验和居民日常实践的目的性削弱。不难看出,它们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现代城市景观的外化。后者不仅扭曲了普罗大众之于城市文明体系的历史性建构关系,而且还在文化符号对劳动属性的隐秘编码中遮蔽了原本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其实质,不啻为资本逻辑对自身结构性危机的转嫁和对异化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的维护。这无疑反映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所谓的西方城市文化,实际上是资本价值剥削与政治压迫的空间性表达。
关键词: 生产关系再生产;精英政治文化;社区隔离文化;网络虚拟文化;城市意识形态
建构并维护现存不合理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西方城市文化的基本政治属性。后者作为大众物质实践与群际交往得以展开的符号性载体,又进一步折射出资本逻辑的人类学内涵之于城市景观的空间性叙事。鉴于此,曼纽尔·卡斯特专门指出,“当我们谈论‘城市社会’时,该议题并非囿于纯粹的空间形式。与之相反,它被所有确定的文化所定位。……换言之,这是一种价值形式以及贯穿于历史特殊性及其组织与转换之自我逻辑当中的社会关系。”① nuel.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London:Edward Arnod,1977,p.75.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如何界定能够表征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城市文化形态?围绕资本生产结构的时代性特征,卡斯特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视域下,将其概括为以下三方面彼此呼应的板块:
应当说,与政治压迫和价值剥削并行不悖的现代西方城市文化,可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向社会空间弥散的结果。它试图在居民日常生活得以展开的地理学维度,“构建一个有关真正存在的社会景观,构建一个没有被对抗性的分工所割裂的社会,构建一个其各部分的关系呈现有机性、互补性的社会。”③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76页。 进而,从文化符号之于社会症候的目的性编码出发,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空间性再生产提供必要的条件。因此,在当前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文化形态,毋宁是资本权力能指的具象化。它们既标识出资本逻辑对其下辖人群之社会实践方式的总体性操控,又从相反的方向表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长时段内在危机。
一方面,与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和价值积累的弹性化趋势相呼应,旨在更高效调节资本部类结构及其整体生产节奏的技术性官僚体系,必然为占据市场竞争有利地位且主导城市发展走向的统治阶级,营造出能够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的所谓“精英政治文化”。它促使“权力集中在上层阶级”,并于权力网络对普罗大众的无情压制中,同时完成“整个国家的非正式化以及权力结构的个人化。”藉此,再次确认资本掠夺式统治的制度合法性。② [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的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其实质不啻为传统劳资关系已然发生形变的情境下,资本逻辑凭借市场竞争与权力主体间不对等的相互关系,对价值剥削机制的策略性巩固。于是,在另一方面,当据此形成的等级性社群结构同资本地理性不均衡发展的空间后果彼此耦合,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区域性集中和职能机构的选择性分布,资本就从“权力的顶峰与其文化中心起始,组织了一系列象征性的社会-空间层级。”①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11页。 而这通常意味着原本完整的城市文明景观,将转化为片断性的社区利益集合。后者进一步衍生出能够瓦解劳动者政治联盟的“社区隔离文化”,并以夸大群际间利益分歧的方式,维护资本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强化统治阶级空间霸权的“精英政治文化”,还是削弱被统治阶级反抗运动的“社区隔离文化”,都相继与当下正在崛起的“网络虚拟文化”达成共谋。在“信息的发展及其垄断成为统治阶级实现社会控制的基本来源”的前提下,为社会权力、阶级结构以及网络体系共同修饰的城市文化棱镜,无疑彻底剥离了个体空间交往和日常体验的真实性。② [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的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如此一来,资本就在现实与虚拟的倒错关系中,通过对信息反馈机制的操纵彻底遮蔽了已然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
首先,通过溴代物与硫代羧酸之间的亲核取代反应合成了两种含羧基结构的双硫酯(1,2),两者的合成路线如图1所示。
一、资本灵活性积累、技术官僚主义和城市精英政治文化
资本生产与积累方式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彻底改变了西方城市景观的社会学意义。在充斥着“弹性专业化、弹性生产体系、弹性积累以及弹性劳动管理方式与弹性技术的弹性时代,城市已然成为后福特主义工业空间的代名词”,④ Edward.W.Soja.Postmetropolis:Critique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224. 并预示着嵌入其中的资本部类结构和传统劳资关系将同时发生历史性的重组。对于卡斯特而言,该过程“既是社会性和技术性的,又是文化性和政治性的。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对市场利润最大化原则的补充。”⑤ Manuel Castells.“The 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Capitalism”,Cf.IdaSusser.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Massachusetts:Blackwell,2002,p.259. 其实质不啻为资本剩余价值剥削与空间权力垄断的精致化。反映在具体的社会治理层面,这意味着能够高效调节资本生产节奏且巩固统治阶级政治威权的文化-制度性空间正在逐步形成。而后者又直接表现为,占据市场竞争有利地位的城市上层人群,对西方民主制度内的“精英政治文化”进行刻意渲染。藉此,构建出与普罗大众的利益诉求完全悖离的排它性管理-决策体系。事实证明,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残酷市场法则下,围绕“金钱与控制权的斗争势必将一部分人彻底排除在平等之外,而由此引发的政治分歧,则使拥有充足金钱力量的精英对空间权力进行长期垄断。”⑥ David Harvey,The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Oxford: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33. 如此一来,一旦底层群众参与城市治理并限制精英阶层决策范围的民主权利被削弱,城市自身必将陷入资本及其附带的空间权力向少数人集中的恶性循环。
无独有偶,在卡斯特看来,“精英政治文化”的产生,往往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阶级属性,以及资本灵活积累模式对技术官僚体系的依赖直接相关。而它最终所要达成的目的,就是凭借“文化符码已嵌入社会结构里的方式,使得持有这些符码便形同开启了通往权力结构的道路,而无需精英阶层的任何有意识谋划。”⑦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510页。 换言之,作为“精英政治文化”母体的西方民主制度及其内涵的技术官僚体系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操纵,意味着城市空间将沦为资本财富掠夺的无意识容器。届时,饱受摧残且无力反抗的城市底层人群,只能被迫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性强制规训。而这主要涉及以下两方面内容:
由此可见,寓于西方城市空间的“精英政治文化”,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孤立的社会现象。它作为统驭社会利益节点和强化资本政治压迫的中介,毋宁是城市规划路径与发展节奏被统治阶级事先设定好的文化主题所整合的结果。⑥ Cf.Manuel.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London:Edward Arnod.1977,p.219 既然人们无法在资本灵活积累的变动不居性中获取稳定的连结纽带,那么为精英操控的异化交往机制就获得了可乘之机。在这样的前提下,与资本剥削彼此耦合的社会空间秩序,势必“在城市政治与经济结构中,生产出与资本发展趋势相一致的社会意识。”⑦ David Harvey.The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Oxford: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266. 后者自觉服从现存的资本空间规划,并以既成事实的形式,转化为统治城市居民的意识形态。而这在卡斯特看来,不啻为“精英政治文化”在社会关系再生产层面的自律性赓续。它意味着处于市场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将自身携带的霸权嵌入到四分五裂的城市空间,并在劳动群众各行其是、地方利益争斗不休的情形下,牢牢占据了城市政治秩序的核心地位。
其次,与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和资本弹性积累法则同时崛起的技术官僚主义,通常构成“精英政治文化”协调资本部类生产关系,并借助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政治程序驯服普罗大众的操作性手段。这无疑彰显出资本对劳动生产效率和劳动者社会属性的双重规训。卡斯特认为,新自由主义浪潮下资本灵活积累模式的最大负面效应,就是它在地理学维度没有一种相对稳定的市场逻辑可以遵循,而总是由于市场被扭曲、操控和转化等原因,时刻处于“多重文化的群众心理,以及全球资本流动和互动越来越复杂所导致的不可预期的狂乱之下。”⑦ [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的终结》,第412页。 其最为典型的后果,就是在城市不同空间单位或差异性人群之间,围绕资本某一部类同时展开的生产活动,为争取各自的市场利益而陷入无休止的恶性竞争。从而,导致资本阶段性价值获取总量的无谓耗散。在这样的情形下,引入用于市场管理的技术性协调机制,并将之升格为资本官僚体系的内在职能,就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资本长时段有效积累的必然选择。如此一来,能够兼顾精英阶层狭隘利益和社会总体财富诉求的全新城市治理模式就呼之欲出。它为处在市场竞争场域内的资本部类生产代言人或受益者提供了彼此媾和的政治性平台。但在相反的方面,“抛开非常特殊的时期不谈,大众阶级并没能进入到这些不同程度上,不同社会秩序中,让上层阶级(资本家与管理者)实行‘内部民主’的机构中去。”⑧ [法]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陈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0页。 这无疑显示出以“精英政治文化”为导向的技术官僚主义,自身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质:后者不仅克服了精英阶层在瓜分社会财富时遭遇的瓶颈,而且还“在政治经济上建构了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大众文化,满足分化的消费主义和个人自由至上主义。”①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44页。 应当说,劳资双方在技术官僚体系中的不同处境,恰好折射出围绕“精英政治文化”而建构的现代资本城市决策中心,与其治下的边缘性劳动群体彼此疏离甚至相互敌对的态势。按照卡斯特的说法,该状况既是现代西方城市之“剥削-异化-压迫属性的无意识结构性根源,又是将其境况表征为一种日常提示的特殊空间组织形式。”② Manuel Castells.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London:Edward Arnod.1983,p.326. 二者相辅相成,从“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管理机制”的共轭关系中,再度确立了资本政治威权的空间合法性。
选取两套告警频繁的SGSN进行所有Gn接口镜像抓包:对CE1和CE2相同时间段的数据包进行echo包统计发现:SGSN1和SGSN2之间的gtp echo消息都可以一对一对应。再看设备间业务地址的ping包,也是没有丢包的。针对第一种可能产生告警的情况,对于承载网丢包的问题可以排除。
值得一提的是,“精英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在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架构中转化为现实的物质操控力量,还与其内涵的“迫切感文化”(culture of urgency)因子,对被迫介入资本新自由主义场域的城市底层群体之非正常竞争意识的刻意渲染密切相关。事实证明,它用“一种没有未来、没有根源、只有现在的趋利性思考方式”,矮化了主体间固有的长时段稳定协作关系,并凭借资本即时性积累的单向度逻辑对劳动者日常生活每一瞬间的压缩,促使“非常个人式的消耗和围绕利益争夺而展开的冲动行事成为其生活的唯一写照。”③ [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的终结》,第184页。 于是,当群际交往的全面性让位于受资本裹挟的个体自由的片面性时,“一个达尔文式的世界就以这种方式出现了。它是在科层的各个级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每个人在充满不安全感、遭受痛苦和压力的条件下形成对其工作和组织的依附。这些制度和劳动后备军的并存成功地建立起生存竞争的世界。”④ [法]皮埃尔·布迪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2页。 这就与“精英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诉求不谋而合。它需要在普罗大众微妙的社会联系中,以“自由”之名植入足以涣散工人阶级政治凝聚力的负向干扰因子,进而以所谓“中立”的调停者身份牢牢地掌控已被资本异化的城市社会秩序。从根本上来说,这不啻为统治阶级为剥离底层群众的城市公民权,而进行的文化符号强暴。其最终目的,就是把精英阶层的“特定历史经验和特殊需要说成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全面推广。”⑤ 孙兰英:《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政治文化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06页。 从而,在文化学的语境中,突显出资本的政治优先性。
首先,以货币逻辑和竞争法则为先决条件的民主制度及其决策体系,实际上是“精英政治文化”维护资本自身合法性,并使财富向城市空间内少数人那里选择性集中的条件性保障。一方面,从西方城市民主政治制度与决策体系得以确立的前提来看,资本毋宁是衡量城市景观内所有政治行为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而受其裹挟的政治关系,除了向公民交往的一般领域渗透之外,还在“个人、肉体、行为举止的层面复制出一般的法律和政府的形式。”①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这就促使资本逻辑的运转轨迹与财富分配的现行方案,能够在单向度的市场机制推动下,毫无阻力的向精英阶层大规模倾斜。一旦民主决策的可操控范围“退回到市场自发性调节的层次,那么其后果必然是,原本用于制约财富不均衡分配的政策导向机制,丧失它对价值法则的控制能力。”② 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141. 在这样的情形下,西方城市中所谓的民主制度不过是资产阶级攫取财富,并钳制底层群体的空间把戏。后者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货币始终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形式,是规训社会关系的工具,而非中立的”组织原则。③ [美]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46页。 另一方面,从西方城市民主政治制度与决策体系得以运行的原理来说,既然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主要任务“就是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86页。 那么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就必须与资本稳定增值的节奏彼此吻合。进而,使现存的社会关系成为资本空间性再生产的基础与条件。以此为出发点不难看出,“如果资产阶级要对自身和它对劳动的控制进行再生产,就必须使工人赢得的任何让步都与资本积累中决定投资生产率的规则相一致。”⑤ [美]大卫·哈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化进程:分析框架》,《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 也就是说,由劳资双方共同参与并尝试在其中消解政治分歧的民主决策过程,始终不能触及资本空间积累的政治底线。对此,卡斯特专门指出,“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及其引发的冲突(即一般意义上的劳资对立——笔者注),城市中的国家干预将不断强化;但是,作为阶级社会的一种表达,依据阶级和社会群体间权力关系的国家实践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霸权。”⑥ Manuel.Castells.City,Class and Power.NewYork:St.Martin’s Press,1978,p.3. 而这反过来又充分证明,“精英政治文化”恰好以资本逻辑为基本运行原理。
基于大数据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与服务创新探索 …………………………………………………………… 卢 海 周 翔(1/23)
二、资本选择性集中、群际利益分歧和城市社区隔离文化
第一,从城市内不同社区的形成机理与资本逻辑的地理规划二者间的关系来看,既然城市空间作为一种隐喻,同资本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确立(货币与商品不断流通的‘自由’贸易)以及主体性(流动单子的个人主义)息息相关”,那么在资本主义市场的修饰下,它必然被“描写为可牵制、可操控的空间。”③ [美]本·哈默:《方法论:文化、城市和可读性》,《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这集中反映在,原本统一的城市辖区被资本循环序列依次拆分为具有不同职能的碎片化空间单位。而后者通常构成隶属社会各个阶层的城市人群展开日常生活并参与政治实践的地理学边界。如此一来,“在空间的象征性、中心性和文化认同的明确界面之间,以及流动空间能被主流文化制度化的场域,社会群体的物理性-本质性分隔的临界点就出现了。”④ Manuel Castells.“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Cf.IdaSusser.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Massachusetts:Blackwell,2002,p.384. 它们在日趋多元且更加精细的资本部类生产中,使“劳动力在地理上更加分散,在文化上更加异质,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样,在人种上更加层次化,在语言上更加分裂。”⑤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4页。 从而,形成彼此孤立并携带明显政治分歧的社区性聚居群落。由此可见,西方城市空间中星罗棋布的社区景观,及其对差异性群体“特定文化认同的政治意义的(再)建构,正根本地挑战着公民权的概念。”⑥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96页。 这恰好印证了大众协作体系的瓦解和社会原子主义的兴起。而社会景观中不断出现的堡垒式分割、封闭型社区,以及终日处于监控中的私有化的公共空间,无疑是该状况的直接表现形式。它们在造成资本不均衡分配的同时,又于城市规划体系内引发剧烈的空间张力。
作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城市政治格局的地理性症候,前者“既是充满私人的和阶级张力的奇特混合体,又能在社会基础设施的再生产中,将个体的社会习俗、文化传统以及政治过程都包含在等级化的组织形式之内。”① David 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85,p.11. 因此,在空间上彼此孤立的异质性社区,可视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向日常生活转嫁的产物。与资本主义的“精英政治文化”相呼应,它直接构成“社区隔离文化”由以诞生的前提。鉴于此,卡斯特不无疑虑地指出,“这种全新的城市文化形态,同(资本)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夹缝内的多模态‘意义-交互性’结构密切相关。它实际上是社会中已然发生断裂的各组成部分,根据碎片化的孤立社群或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彼此间的并置而实现的。”② Manuel Castells.“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Cf.IdaSusser.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Massachusetts:Blackwell,2002,p.382. 也就是说,所谓“社区隔离文化”,可视为资本弹性积累模式下城市多元利益马赛克的一般称谓。它揭示出财富和权力的极化效应,正在深刻影响当代城市空间格局的尖锐事实。而后者在卡斯特看来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二,从城市内不同社区的空间定位与资本逻辑的政治预设二者间的关系来说,由于资本增值与循环系统具有鲜明的剥削属性,它势必将一段时间内所获财富的总量,按非正义的分配原则不均衡地配置于城市的各个空间单位当中。因此,以之为出发点的一般政治行为“所产生的地理景观不是平衡发展的,而是有极大差别的。通过不平衡的资本投资的简单逻辑……‘差异’和‘他性’在空间中被生产出来。”⑦ [美]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第339页。 这就意味着,已然呈碎片化分布的城市社区景观,将再度以财富占有量为尺度,被打上具有明显隔离标识的“贫民窟”或“富人区”烙印。对于卡斯特而言,后者在当下又集中体现为“高收入或中高收入群体从城市当中分离出来,并且建构出更加异质性的社区。从而,促使富人聚居区的空间指标远高于贫困人口聚居区的空间指标。”⑧ Manuel Castells.“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Cf.IdaSusser.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Massachusetts:Blackwell,2002,pp.376-377. 如此一来,在资本的财富分配序列和政治规划格局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差异性社区,就成为履行资本剥削职能或承担被剥削后果的社会各阶层人群,强化自身空间身份的地理性标签。在这样的情形下,“阶级(资本-工资)矛盾,就延伸到社会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政治的(统治-被统治)矛盾中。人们不能从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凝聚力当中看到生产关系是怎样再生产。人们只能看到在广大区域中不断扩大和加剧的矛盾。”① [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3页。 而彼此疏离甚至相互敌对的社区作为矛盾的载体,则据此充分佐证了为资本逻辑催生的城市社区分化“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polarization)”②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
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精英政治文化”对资本弹性积累法则的默许与操纵,无疑强化了具有不同价值创造潜力的城市各空间单位在财富拥有量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就导致身处其中且为市场竞争机制裹挟的社会多元群体,因资本“物”的尺度而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彼此疏离甚至相互攻讦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形下,“大规模的工薪阶层就越来越在居住、工作、娱乐、购物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分化倾向。”⑧ Manuel.Castells.City,Class and Power.NewYork:St.Martin’s Press,1978,p.29. 进而,在地理层面衍生出以文化-政治隔离为主要特征的群际社区关系。
微网作为智能电网的重要模块,可完成能量转换,监控,通信与保护等功能,可并网运行,也能在大电网产生故障时,孤岛运行。微网中的供电板块和负载较为分散,在微网运行的过程中很难避免涡流产生,在这种状态下长期运行对微网损坏严重。
初始化时为避免粒子遗漏边界上的点,将粒子的覆盖范围延伸到定义域1.1倍的区域,其初始化速度如式(6)所示。
第三,从城市内不同社区的生存样态与资本逻辑的社会愿景二者间的关系来讲,地理上持续的财富分配不均与政治上日益严峻的两极分化,无疑加剧了“城市人口在关乎其日常生活能否得以维系的食物、能源,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性资源的多元网络体系中的冲突与争端。”③ Stephen Graham.“Urban Metabolism as Target”Cf.NikHeynenEd.In the Nature of Cities: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6,p.238. 于是,当城市内各个阶层的人群希望最大限度占有社会资源,并防止他者染指其既得利益时,以共同居住的社区为地理坐标的阶级联盟就应运而生了。它们是个体资源相对匮乏与资本价值绝对积累的消极产物。但在卡斯特看来,这种以“物”为尺度而构建的“阶级联盟”和由此推动的地方/区域的自主性,通常以加强“其领域内的精英阶层的认同,并削弱此自主性的政府机制中不具地方代表性或被隔离的社会弱势群体的认同”为代价。④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315页。 于是,精英和大众在城市政治格局中的不对等关系,就很容易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特权并据此监控被统治阶级社会活动的手段。它“一方面利用社区间的竞争机制,加重了对工人趋利性联盟的压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利益最大化原则,将全部工业生产体系整合进资本的统治地位不被动摇的投资性区域。”⑤ Manuel.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London:Edward Arnod.1977,pp.214-215. 从而,在实现资本价值稳定积累的同时,将其可能遭遇的反对性力量最大程度地削弱并分别置于与资本财富增值无涉的隔离性区间。由此可见,“城市空间的分化和社会关系的弱化,是资产阶级努力发展自身经济实力和社会领导权的核心。而空间重构结合高强度的监管体制,则使资产阶级可以建立起新的代表文化差异的围墙。”⑥ [英]史蒂夫·派尔等:《无法统驭的城市:秩序与失序》,张赫等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后者的实质,就是在城市空间中确认资本之于个体的绝对优先性。
显而易见的是,在差异性群体的空间利益分歧被过分渲染的“社区隔离文化”中,一旦连结普罗大众的“社会纽带被定义为形式差异的变动游戏而非显而易见的内在品质时”,有关“个体身份和地点的界定也就变成了幻灭的符号”① [澳]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1~72页。 。此时,对于由社区网络形成的城市公共空间来说,它早已随着大众权力的退场而沦为资本攫取特权并加剧社区隔离的异化场所。马克思曾尖锐地讲道,“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Gemeindewesen),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而所谓“一般政治”的实质,毋宁是在资本地理性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被隔离社区内“居民极少量权利片断的维持,进而在作为整体的城市大背景下,将其大部分利益予以摈弃。”③ Don Mitchell.The Right to the City: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New York,London:The Guilford Press,2003,p.210. 这就促使城市的公共空间与资本的意识形态彼此重叠,并进一步衍变为钳制底层群众命运的“它者”霸权。其中,居于西方城市化进程核心的,仍然是马克思之前所指认的异化事实:即“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既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此时,城市就不再是个体得以栖居的生活空间,而更像是彼此利益争夺的角斗场。纵然城市的经济指数持续攀升,但因社会关系异化而导致的阶级压迫却早已渗透到社区的各个角落。
不难看出,作为阶级冲突、政治分歧以及社会异化的空间性集合体,在地理上相互隔离的城市社区网络,实则以取消大众社会共识的合法性为代价,通过强化资本的地理性不平衡发展,进而巩固了资本非正义的剥削制度。“它不仅提供了为权力斗争而进行权力斗争的嗜好,而且通过大规模强占和集团性奴役的手段”,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各种劳动产品,而无须自身终日参加苦重的劳动。”⑦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因此,“社区隔离文化”既是资产阶级对城市底层群体的地理规训,又是资本对城市政治权力进行非法垄断的意识形态叙事。它预示着原本统一的社会发展进程,将发生不可逆转的自我分裂:一方面,为精英阶层主导的社会文化认同“趋于涵化包容,并以其对地方制度的控制来扩充认同的社会和人口基础”,进而实现资本生产关系的全面泛化;另一方面,与底层群体的利益旨趣休戚相关的“地方社会却防御性地退缩,并以社会排斥的机制来建立其地方自主性”,以此消极地维护自身狭隘的政治-经济利益。⑧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316页。 换言之,“社区隔离文化”最终意味着资本空间生产与积累的碎片性,对城市内差异性群体之社会契约的整体性的褫夺甚至取代。对此,卡斯特专门指出,“城市契约是由隶属不同文化背景、拥有不同资源配置的市民彼此协商的产物,这是一种部分共享的文化以及存在部分分歧的制度性平台。但城市不断加速的空间碎片化过程,却从根本上破坏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可能。”⑨ Manuel Castells.“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Cf.IdaSusser.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Massachusetts:Blackwell,2002,p.377. 它标识着城市政治景观的彻底失序与个体日常生活的完全异化。
三、资本结构性重组、数据信息空间和城市网络虚拟文化
由资本灵活积累和选择性集中共同催生的“精英政治文化”与“社区隔离文化”,不仅重构了现代西方城市的空间文明形态,而且还以转变社会权力叙事的方式,促使整个资本生产体系发生结构性的变革。而它们对市场竞争机制的强化以及财富高效积累的推崇,则昭示了用于创造价值的手段和平台将陷入愈加频繁的更迭状态。于是,能够以不断的自我更新满足资本即时性利润诉求的网络信息环境就应运而生了。在卡斯特看来,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城市图景正在形成。其中,“信息技术革命、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随后发生的再结构,连同文化上的社会运动……共同产生了一个新的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即网络社会、信息化/全球经济和真实虚拟的文化。而深植于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之内的逻辑,已经成为整个相互依赖世界里的社会行动与制度的基础。”⑤ [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的终结》,第403页。(引文略有改动) 后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资本-地理”格局,并在劳动的真实性与数据的虚拟性彼此倒错的关系中,逐渐衍生出消解大众直接社会体验的“网络虚拟文化”。作为“精英政治文化”和“社区隔离文化”在当下的最终言说载体,它凭借“个人身体网与建筑网、建筑网与社区网、社区网与全球网彼此连结的方式”,⑥ W.Michell.City of Bits:Space,Place,andthe Information,Cambridge:MIT Press,1995,p.3. 把资本的空间宰制力发挥至极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由资本信息网络操纵的数据性流动空间,对地方空间内大众日常生活经验的蚕食。对此,卡斯特专门指出,“流动空间乃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它标识出“社会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结构中,社会行动占有者所占有的物理上分离的位置之间那些有所企图的、重复的、可程式化的交换与互动序列。”⑦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05~506页。 其实质就是为网络环境下资本脱域性积累提供必要的准备性条件。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既然资本逻辑的“形式化与数量化功能意欲摆脱事物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意义之网的束缚,并且还可能以暴力的方式消除它所遭遇的所有障碍与抵抗”,⑧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7,p.49. 那么将资本运行的路线图整合进去疆域化的虚拟信息符码当中,就不失为一种祛除地缘限制的柔性举措。这就涉及信息网络对资本自身和城市景观的双重虚拟作用。对于前者而言,资本的周转动向与财富的获取节奏通常被抽象化为数据性的信息函数,并在网络媒介之于个体交往的干预过程中,呈现出不受其他社会参数影响的独立属性。在这样的状况下,资本逻辑就游离于现实的社会日常情境之外,并据此获得了自在自为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对于后者来说,“由于网络虚拟空间的理念与现象正在兴起,而且虚拟空间有可能给使用者脱离‘真实’世界,并真正参与到被想象和再现的世界中去的机会”,① [澳]德波拉·史蒂文森:《城市与城市文化》,李东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2页。 因此原本稳定且真实的城市文明景观就不得不接受信息符号的编码,进而沦为以虚拟网络为前提的依附性存在。由此可见,正是凭借网络信息环境对资本存在样态和社会日常生活的不同定位,自律性的资本逻辑才在数据性的虚拟镜像中,实现了对依附性的城市景观的全面操控。它既意味着受资本裹挟的流动空间对个体真实社会经验得以生成的地方空间的褫夺,又揭示出资本将“核心的经济、象征以及政治过程从社会意义能够被建构而政治控制能够被执行的领域中转移出来”的阴险狡计。② [美]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143页。 而在“资本逻辑-网络媒介-城市景观”的倒错关系中,“审慎周密的网络虚拟文化势必渗透我们城市的各个角落,并将其内在的多种维度缩减为一种单一连贯的视觉再现,一种主要建立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再现”③ [英]斯蒂芬·迈尔斯:《消费空间》,孙乐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82页。 。以此,实现资本对城市空间的长时段政治霸权。
其二,是由资本信息网络激化的生产力更新速度,对传统社会中群际利益对抗张力的加剧。毋庸置疑,资本生产模式由工业主义向信息主义的历史性转向,标志着知识性的“文化创新在逻辑上成为决定生产力是否提高的关键指标,并因此作为财富的源泉而增强了资本化城市的竞争强度”④ Manuel Castells.“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Cf.IdaSusser.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Massachusetts:Blackwell,2002,p.370. 。这表明,在网络信息时代,资本生产与积累效率在质和量上的双重飞跃无异于数据信息体系自身的程序性更新。这同时意味着,为满足资本的竞争需要,“任何想要将网络中的位置凝结为特定时间及空间之文化符码的企图,都会造成网络的废弃过时,因为它会变得过于僵化,无法适应信息主义之多变几何形势的要求”,并与资本创造性破坏的内在文化属性相悖离。⑤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245页。 然而,在卡斯特看来,资本生产的信息化趋势在城市空间层面并非是一个均质化的过程。它通常在城市不合理的劳资关系而不平衡的区域发展结构中,增大了资本价值剥削的历史惯性。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此新模式下,……被信息化资本主义视为无价值且无政治利益的地区,财富和信息的流通跳过这些地区绕道而行,甚至连设施都被剥夺了。这个过程导致社会/区域所排除和接纳的地理分布极度不均,并使得大部分人无法经由信息科技的全球网络积累财富、信息及力量。”⑥ [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的终结》,第78页。 由此不难看出,被资本信息化潮流催化的城市两极分化趋势,不啻为“网络虚拟文化”对“精英政治文化”和“社区隔离文化”之地理学旨趣的最终表达。这无形中肯定了与资本生产力提升相对应的信息即时性更新机制,对身处城市发达区域的精英阶层之政治-经济权益的接纳与维护,以及对落后街区底层人群社会诉求的隔离与排除。其实质,毋宁是被信息网络虚拟化的“城市日常节奏和活动例行地将城市空间编码、划分”,进而使资本的空间剥削机制“在一个鲜为人知的不平等基础上隐秘地进行”⑦ [英]多琳·马西等:《城市世界》,杨聪婷等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7页。 。因此,信息时代的城市景观毋宁是极度分裂的,它一方面促使“信息化生产者与可替代的无标签一般劳工之间,也就是劳动者内部出现片断化”,另一方面又引导“社会排斥在社会内造成明显区段,而这些区段由被社会抛弃的个体所构成。”⑧ [美]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的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15页。 二者彼此耦合,共同显现出资本“网络虚拟文化”内在的阶级利益对抗属性。
其三,是由资本信息网络支配的多元化传播媒体,对当前时代下统治阶级政治意图的修饰。从直观上来看,日趋完善的数字化传播媒体,在当下毋宁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向城市景观植入的首选文化性介质。它“与现代城市主义间的相互交织,改变了地点与经验、熟悉与陌生、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纽带。”并通过“人类感知与技术幻想之间模糊的界限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意识的空间,进而促使主宰着现代性的自治模式和内部性模式变得越来越难以与日常经验相协调。”① [澳]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在这样的情形下,统治阶级带有明显剥削属性的政治倾向,就很容易在虚拟与现实的夹缝当中获得特殊的伪装。它以看似呼应城市日常生活之琐碎、无聊甚至娱乐化特质的开放形态,充分满足了普罗大众之于现代资本政治结构的全部想象。然而,对于卡斯特来说,事实的本质却是,个体及其社会关系已然成为媒体领域的俘虏,并在统治阶级的个人领导权不断强化的基础上,通过“技术上的复杂操弄,被推向不法的金援,被丑闻政治推着走并越来越接近丑闻政治,政党系统已失去其诉求吸引力及可信度,同时,对所有现实目的而言,它是一个不再具有公众信心而仅剩官僚的残余物。”②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397页。 这恰好说明,现存的城市日常生活及其涵盖的政治行为预期,都不过是受资本逻辑操控的网络信息媒体,对大众负面诉求进行刻意编织的消极产物。作为“网络虚拟文化”的政治性投射,后者又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城市人群进行文化催眠的手段,将转变为嵌入文化产品和具体日常实践之中的“神话修辞术”。③ [澳]德波拉·史蒂文森:《城市与城市文化》,李东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3页。 它使“生活本身也逐渐成为一种媒介,如同电影、电视、收音机和书刊一样,其中的人群既是媒介中的表演者,又是这些正在表演的恢宏剧作的观众。”④ N.Gabler.Life the Movie:How Entertainment Conquered Reality.New York:Knopt,1998,p.9. 通过现实空间与文化空间的置换,原本尖锐的阶层对立,就在虚拟的网络文化层面获得和解。加之“媒体对于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的掌握,也变得更具全面性。”⑤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370页。 这就导致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被掩盖之后,资本又在“客观上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稀薄的幻象和超现实世界”,⑥ [英]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戴从容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 以此来软化社会矛盾对资本主义政治秩序的冲击。而在被拜物教化了的虚拟文化空间当中,“人们对自己茫然无知,且思想也不会想到与这种抽象空间保持批判性的距离”⑦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7,p.94. 。
4)保持阿曼地理描述的一致性,使其符合标准规定,在将其转化为其他国家语言时,保证不失去其原意,从而保证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统一;
毋庸置疑,围绕“精英政治文化”“社区隔离文化”以及“网络虚拟文化”而建构的当代西方主流城市文化叙事,不啻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空间性表达。而后者之于普罗大众的意义性编码及其产生的社会物质性后果,则再度凸显出马克思有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等经典论断的正确性。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鉴于此,反观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城市文化形态,不难看出,它们依然是资本价值剥削与政治压迫的外化。而唯有彻底变革决定现存城市社会图景的异化生产关系,才能最终打破资本文化霸权的空间座架。
精确称取芦丁、野黄芩苷、橙皮苷、柚皮苷对照品,分别配制成 1. 0 mg/mL 的对照品溶液,用0. 45 μm微孔滤膜滤过,4 ℃保存备用。分别取配制的对照品溶液适量混匀,制成混合对照品溶液。
中图分类号: B7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9)03—0002—09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卫·哈维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哲学思想研究”(项目号:17FZX0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温 权,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谢雨佟]
标签:生产关系再生产论文; 精英政治文化论文; 社区隔离文化论文; 网络虚拟文化论文; 城市意识形态论文;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