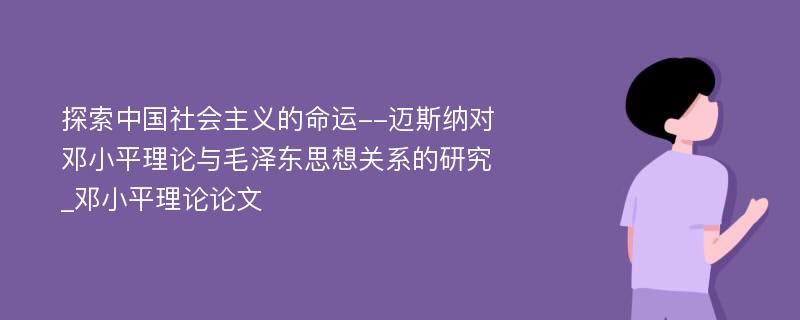
探寻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迈斯纳关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命运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国际学术界一般将他视为具有“左翼”倾向的重要学者之一,其代表作有《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寻,1978—1994》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对“毛泽东主义”② 有着深入的研究,对创造性发展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给予了有价值的分析。对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他更是有着自己比较深入的理解,涉及对毛泽东时代遗产的评价、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主义之间的差异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与命运等问题。
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及评价
迈斯纳认为,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遗留下来的一笔十分巨大而复杂的遗产,尽管这份遗产是模糊而矛盾的。从其论述来看,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大致可以分为政治和社会经济两个方面。
政治方面,迈斯纳指出,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分裂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后,“毛泽东主义者的革命建立了统一的中国,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在当代世界寻求‘富强’建立了政治前提”③,并给各民族人民灌输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社会意识,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行了土地改革,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工业革命,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保留了对未来的重要的社会理想,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各种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同时,毛泽东又保留了斯大林官僚政治统治的方式,制造了自己的个人崇拜和教条,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造成了惊人的人员伤亡以及人们肉体和精神上的深深伤痕。“不管文化大革命在其他方面可能如何,它都是一个使人类遭受巨大痛苦的时代”④;这场革命“所得到的仅仅是失败后的人民在政治上的幻灭感,接踵而至的便是群众的愤世嫉俗的情绪……斗争和阴谋玷污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史的最后篇章”⑤。然而,迈斯纳也富有深意地谈道:“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⑥
社会经济方面,迈斯纳认为,尽管毛泽东主义尝试在中国脆弱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失败了,并且造成了许多失误和挫折,“人们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⑦,“达到了非常有影响的工业化程度”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他分析说,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在不利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现代工业和科技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最大的6个工业国家之列。迈斯纳坚持说,如果不去正确评价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⑨。而“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⑩ 此外,在毛泽东时代,教育得到了普遍发展,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措施得到了贯彻实施,并且建立了比较普及的医疗卫生系统。
面对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正面和负面的遗产,迈斯纳表示,对毛泽东进行历史评价是一项十分危险的政治事业。一方面,为了新时代的顺利发展,邓小平要使毛泽东非神秘化;另一方面,作为中国革命的“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不但是公认的革命领袖和新社会的建立者,而且他还统治了后革命国家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简单地谴责毛泽东并列举他过去的罪恶,“不但会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陷入危机,而且革命的道义上也说不过去”(11)。而最后的决议结果既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积极作用,又严厉地批评了其所犯的“错误”。迈斯纳强调,这种评价结果“绝不只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要寻求政治上的合法性,它还反映了现在的领导人对早期毛泽东的真正的尊敬和由衷的钦佩……即对作为公认的革命领袖、中华民族的解放者的毛泽东,以及在受‘错误的左倾’观念影响前曾经(一度)是一个杰出的经济现代化者的毛泽东的尊敬和钦佩”(12)。他进一步指出,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毛泽东时代挫折的同时,“肯定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何评价)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时期之一,作为一个取得了社会成就和人类成就的时期”(13)。
迈斯纳看到,正是在继承毛泽东时代遗产的基础上,邓小平理论表现出与毛泽东主义许多相同的地方:邓小平的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体制,仍然是马列主义政党统治着的国家;邓小平继承和贯彻了“四个现代化”方针,并和毛泽东一样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放在政治日程的重要位置上,都想将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国家;都要面对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手段同其目的之间的矛盾问题;邓小平时代的发展战略和毛泽东主义革命战略一样,都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混合经济模式、现代工业和科技基础以及外交关系等等。
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主义的差异
迈斯纳也指出,虽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毛泽东主义的某些方法和习惯已经越来越不适合于当代中国的情况了”(14)。因此,迈斯纳断言,毛泽东的继承人将不可避免地抛弃那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的毛泽东主义的内容。也正因如此,邓小平理论表现出了与毛泽东主义的诸多差异,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15) 毛泽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含蓄地抵制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16)。它以唯意志论为特点(17),高扬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强调社会生产关系和人民觉悟的改造;对资本主义怀有敌意,将“一穷二白”视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与此相反,邓小平理论“最显著、最普遍的特点之一就是开始信奉历史及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18),并将毛泽东主义时代的经济失败及政治动乱归咎于过分强调人的意志和觉悟、过早地改变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后果;它强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汲取了许多经济决定论思想,并将优先使生产力发展到很高水平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首要根本前提;它恢复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有进步作用的观点,并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采用许多在历史上曾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形式和实践。”(19)
第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上,邓小平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以缓和、和谐的方式进行的。迈斯纳指出,毛泽东主义将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看作是“连续不断地同过去进行彻底的革命决裂,对现实进行实质性的改造,并在他所设想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不断的革命中尽可能迅速地实现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觉悟的改造”(20),强调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长期性,并将其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动力。与此相反,新的理论将社会发展“看作是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渐的和缓和的发展过程,它的每一个阶段都反映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21),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发展而非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建设,提高生产力,而其他非主要矛盾都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和平的方式逐渐得到解决,因此社会发展是和谐地进行的。
第三,邓小平理论更强调“集体领导”的作用。“重新定义后的‘毛泽东思想’中,又突出了集体领导的精神。在清除了其中过于激进的概念和思想后的毛泽东思想,如今被称为是党的集体智慧而非某个人的创造物。”(22) 相比于毛泽东时代对除毛泽东外其他党的领导人的贡献几乎不提的做法,新的党史承认了其他革命领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所作的重要贡献。而且,官方决议在谴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也承认除毛泽东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均对大跃进的错误负有责任。在迈斯纳看来, “较之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国家在许多方面已不那么专制”(23),现在是以更加有规则、更有预见性的方式来行使政治权力。
第四,在经济结构和政策方面,邓小平时代采取了改革开放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迈斯纳称邓小平为“实践派”、“改革派”。改革派将市场机制看作是解决“计划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的途径,首先采取的经济步骤就是增加农业和消费工业的投资以纠正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比例失调”的问题,并用市场关系模式来对城市工业经济部门进行改造。此外,还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重新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后毛泽东时代的北京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于大规模地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输入资本和技术”(24)。而对于“开放”意味着中国开始了新的依赖外国时期的质疑,迈斯纳表示,“现在的中国已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在外国的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屹立着一个由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领导人领导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5)。而在农村,“生产责任制”被作为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推广,集体劳动被个体农民的生产所取代,国家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并颁布了鼓励发展农村市场和专业户的政策,“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所产生的经济结果都是十分显著的”(26)。
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担忧
对于中国新时期取得的许多积极成就,迈斯纳坦率地表示说,这应该归功于邓小平理论,不管改革的最终路线和结果如何,“毫无疑问,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邓小平时代将是一个最成功地创造了经济发展记录的时代”(27),“以任何理性的判断标准来衡量,这些都是进步的发展,并必然受到了一切真正关心中国人民幸福的人的欢迎”(28)。但是,他也敏锐地看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些消极后果,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将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表示出了担忧。
迈斯纳指出,改革开放政策虽然带来了普遍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靠严重的社会破坏和空前深刻的精神穷困来完成的。……尤其在年轻人中间,‘信仰危机’日趋严重”。(29) 这种破坏首先就表现为不平等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旧有的省份与地域、城市与乡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平等差异在邓小平时代由于各种原因日趋扩大。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旗号下实行的市场化改革又产生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问题。在城市,工资、奖金的差别扩大了工人中的不平等;工厂里强化管理和技术人员的权力拉大了管理者与工人间的差距;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促进了官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大众之间的分化和差距。市场化改革引起的最糟糕的长期后果是农村社会经济不平等的迅速发展,这使得农村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集体组织的弱化使得对弱势人员进行照顾的福利事业大幅度减少;农村学校入学人数减少、质量下降;组织农民从事像兴修水利这样的大型工程项目变得越来越困难;乱砍滥伐林木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并进一步缩小了可耕地的面积;农业生产单位小型化和分散化,给未来最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带来了新的障碍等等。此外,新采取的教育制度从整体上扩大和强化了社会差别,成为形成不平等的一个强大力量;工业化的发展使得环境污染变得更加严重;“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日益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的变化,造成了官方与非官方的贪污腐化现象大量增加;市场经济颠覆了社会主义与传统价值观念,造成了意识形态的真空和道德危机日益严重。
更让迈斯纳所忧虑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将会面临共产主义理想的弱化甚至缺失问题。迈斯纳指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奋斗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但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无论他们在晚年怎样苦于目的和手段的分裂,但他们还是坚定地为实现他们在青年时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想而奋斗。毛泽东之后的新一代领导人虽然也在继续促进中国现代经济和现代政治的发展,但是他们在发展的同时,却将技术当作解决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忽略了协调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手段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矛盾,“发展经济的手段变得越来越像最终目的了”(30),社会主义目标则被推延到更为遥远的未来,“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等同于现代化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邓小平的中国资本主义方式的经济成功越多,就越压倒他们原来想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结果。他不无忧虑地质疑道:“他们是否也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热心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奋斗?这正是毛泽东在晚年最担心的一个问题。”(31)“如果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发展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又表现在何处呢?中国现今的政治、思想领导人相信他们正在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迈进,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对此信念的真诚。但有人会问,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和他们宣称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否一致呢?”(32) 他忧心忡忡地分析说:“当马克思主义被简化成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时,当其理论实质被‘实事求是’这一法则作了新的定义时,当社会主义本身实际上等同于现代经济发展时,理想主义被明显淡化也就在所难免了。”(33)
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与手段之间关系的担忧、对社会主义理想被淡化的担忧,有着相当的思想深度。这也提示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关系。但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较分析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时,只是从浅显的字句而不是从精神实质与内涵来对比分析,就显得有些过于教条主义了,这种近似教条主义的观点再加上其思想、文化背景的差异与限制,他所得出的一些观点与结论,诸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政治民主没什么进步;毛泽东主义以唯意志论为特色、思想中一直有民粹主义的暗流;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将会在反对现存政体中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等等,就显得十分偏颇和不当了。
注释:
① 迈斯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较宽,本文仅从论题所选角度对其部分思想进行介绍和讨论。
② 迈斯纳所说的“毛泽东主义”与我们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有差别,其内涵偏重于指毛泽东个人的政见、著作和方法策略以及由此而发展成的意识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独特的(和特有的中国式的)解释”。见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本文从忠实原意出发,使用“毛泽东主义”一词。
③(16) Maurice Meisner,Mao Zedong,Polity Press,2007,p.193,pp.198—199.
④⑤⑦(12)(13)(14)(19)(22)(23)(24)(25)(26)(27)(28)(31)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463页,第549页,第540页,第572页,第543页,第550页,第594页,第568页,第596页,第581页,第582—583页,第587页,第587—588页,第590页,第531页。
⑥⑧⑨⑩(11)(29) Maurice Meisner,The Deng Xiaoping Era: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1978—1994,New York:Hill and Wang,1996,p.53,p.344,p.189,p192,p142,p.x.
(15)(18)(20)(21)(30)(32)(33)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第191页,第199页,第199页,第204页,第204页,第207页。
(17) 对于迈斯纳这一观点,国外许多学者并不赞同。尼克·奈特就指出,一看到毛泽东强调人的思想意识,就说毛泽东犯了唯意志论、乌托邦之类的错误,就说他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决裂或严重偏离,这种说法是不当的。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对变革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反映出毛泽东特别关注建立一种能够解释许多历史特殊情况的理论。参见尼克·奈特:《论毛泽东的社会变革因果观》,《关心亚洲学者报》,1990年夏季号第22卷第2期。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